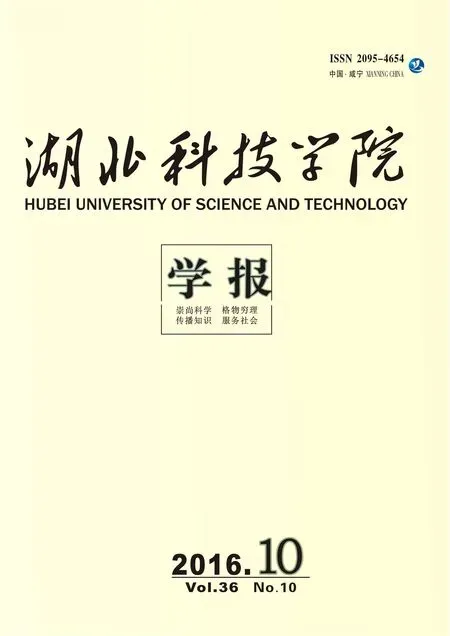论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成长主题小说
——以哈尼夫·库雷西的《黑色唱片》为例
唐 红
(蚌埠医学院 公共课程部,安徽 蚌埠 233000)
论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成长主题小说
——以哈尼夫·库雷西的《黑色唱片》为例
唐 红
(蚌埠医学院 公共课程部,安徽 蚌埠 233000)
成长小说是英美文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类型和分支。在《黑色唱片》中,哈尼夫·库雷西一方面继承了成长小说的传统写作技巧;另一方面描绘了当代亚裔移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探寻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小说通过主人公沙希德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焦虑、摆脱这一焦虑的出路等方面的描写,出色地表现了当代英国亚裔青少年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提出了要勇敢地跨越各种人为藩篱,建构自己的“第三空间”的建议。
《黑色唱片》;成长小说;多元文化;“第三空间”
苏珊·荷在研究了英国文学中的成长小说之后认为,“成长”指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由于自身的性格历经磨难之后,在引路人的指导下,调整自身,融入社会。而成长小说,根据莫迪凯·马科斯在论文《什么是成长小说中》,他将成长小说定义为:“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兼有之;这种改变使得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把他最终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1](P7)哈尼夫·库雷西(HanifKureishi)是继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在世界文坛有重大影响的亚裔作家,同时也是独树一帜的成长小说家,他的一系列小说《郊区佛爷》、《黑色唱片》以及《加百列的礼物》都在“忠实地记录着主人公们在经历一系列矛盾冲突后痛苦成长的过程”[2](P113)的同时也展现了当代移民后裔在全球多元文化和后殖民语境下在异质国的真实生存状态。《黑色唱片》(The Black Album,1995)是哈雷夫伦敦三部曲第二本,是一部关于巴基斯坦第二代移民在伦敦成长的小说。文章为读者描述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英国背景下长大的新一代巴基斯坦移民生活画面。亚裔少年沙希德在种族歧视和家庭纷争中,渴望进入大都市开始新的生活。来到伦敦之后,他在身份的寻找中逐渐成长,在与周遭的经历和冲突中,在母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痛苦挣扎中,最终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从不经世事的莽撞少年成长为稳重从容的青年。
一、成长的烦恼
主人公沙希德在少年时期的成长烦恼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少数族裔在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英国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文化殖民;二是他和父辈移民之间的摩擦和矛盾。移民作为流散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经历了物理、文化,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变迁,在保持民族性和融入居留国文化的两难选择中备受折磨,同时居留国的主流文化对于出生在、居住在英国的少数族裔并没有表现出欢迎和接纳。小说以1989年的英国为创作背景,当时的英国已经逐渐丧失了全球霸主的地位,为了挽回颓势,英国政府不得不鼓励之前附属国的居民移居英国以重振经济,但非白人的外来定居者并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据 Keith Hoggart和EmrysJone合著的书籍《伦敦:一个新的大都市》所述“海外移民被视作是有限制源的争夺者,在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许多公开的冲突,这也反过来印证了种族歧视的真实存在”。[3](P151)小说中英国虽是沙希德的出生地和成长地,但他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其中,民族印记和在学校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自己是个格格不入的“异类”和“他者”。即便说着流利的英文、小心翼翼地不去僭越少数族裔聚集的边缘地带,沙希德还是被学校同学们叫嚣着“滚回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唯一一个深肤色的人”,他确信别人对他的心中“充满了讥讽、厌恶和敌视”。在敌对和仇视的环境中,沙希德逐渐感到自己“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不像一个正常人 ,反而变成一个怪胎,我一直被踢来踢去,被穷追不舍”。[4](P14)“我是谁?”“我属哪里”这些散居族裔世世代代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使得沙希德在身份寻求道路上陷入困惑,“我变的偏执,我出不去,我很迷惘,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沙希德的成长焦虑还来自于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沙希德的父亲作为第一代移民,移民到英国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个不受独裁统治的国家过上一种富裕且安稳的日子”。[4](P73)通过父亲的不懈努力,沙希德一家在伦敦附近的肯特郡定居下来并跻身中产阶层。父亲希望沙希德和哥哥齐力可以继承家中的生意。崇尚撒切尔主义,一身名牌、金钱至上的哥哥齐力是全家的宠儿,相较之下,沙希德则是家中的“二等公民”,被自己的家庭成员呼来喝去。比起金钱沙希德自幼就更加热爱文字,这一爱好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年轻时和沙希德一样热爱写作,但是在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父亲质问他为什要写“那些该死的残忍玩意儿”。[4](P103)父亲训斥沙希德“就不是干这件事的人,你就不能好好读书吗?我那些侄子是律师、医生、银行家。那些艺术家类型的人永远都是在受穷——你该怎么面对那些亲戚的眼光”。[4](P103)在父亲眼中,沙希德显得不切实际,是个“书呆子,没有实际生产力的男人”这样不仅带不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并且会成为家庭的负担。父亲的态度无奈地折射出散居族裔在异质国的窘迫处境,而即使到了移民第二代,他们仍然无法挣脱“他者”身份的束缚,始终徘徊在社会的边缘,正如书中所言移民“就像是刚过门的娘子”,这场和移居国的婚姻“是多么的悲惨”[4](P74)。在家中,父亲苦心维系的家庭随着他的离世而分崩离析,沙希德也萌生了离开家庭的想法。他计划去伦敦读书,他渴望“拉开与家人的距离”、思考自己“来到英国的目的”和寻找自己的身份坐标。这样的情节安排遵照所有的成长小说的发展模式,少年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庭,开始了自己的成长之旅。
二、成长的领路人
青少年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方面丰富着他们的生活阅历和社会认识。因此,成长的引路人在成长小说的叙事中充当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反引路人的言传身教,主人公确立起自己的人生方向。总的来说,沙希德的成长过程中既有正面引路人,也有反面的引路人,他们共同的作用下也使得沙希德最终厘清了自己的选择。
(一)反面引路人
在沙希德离开家来到抵达伦敦学校之初,结识了拥有相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同学利亚兹和查得。天然的文化联系使得渴望“结交几个亚裔朋友的”沙希德对二人产生了自然的亲近感。沙希德觉得他们之间是相似的,“理查兹特她们是他遇到像他的人,一切都不必解释,沙希德相信他,称他是兄弟,他和他们的关系比家人还要密切”。[4](P43)远离母国文化的沙希德也在和朋友的交往中第一次真切的接触到模糊的想象中的民族,这使得对无法被西方文化接纳的沙希德重新获得身份认同的一线希望。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沙希德发现利亚兹和查得是本质主义身份观念的拥趸,而他们由于无法真正融入主流文化以及远离家园的物理和心理上的错位,使得无归属感在心中慢慢积淀。主流文化霸权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歧视、排斥与打击,使得利亚兹和查得对英国主流文化和英国白人产生反感的心理。他们盲目地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切接触都被视作是“有辱灵魂”的,并且逐渐演变成极端主义的暴力团体,这开始引起了沙希德的反感和厌恶。其次,尽管最初沙希德想要融入其他亚裔中,他很快便意识到他的这些“朋友”并不赞同他的艺术创作或者他对于文学的好奇心。查得,这个曾经的西方文化的拥护者,觉得沙希德对于文学的热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劝他“不要再浪费时间讨论文学这些无聊的话题,还有好多正经事需要处理”。[4](P30)查得希望沙希德和他们一样停止独立思考,只是简单地遵循教义和遵守巴基斯坦的刻板文化习俗,这无疑是沙希德所无法接受的。再次,在与二人的交往中,沙希德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Deikman曾断言“大多数的社会团体和家庭结构相似,有占据主要地位的(家长)和被支配的(孩子)”。[5](P34)利亚兹组建的小团体和沙希德不如意的家庭结构如出一辙,沙希德在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平等对待,他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利亚自的命令,依旧扮演着“边缘人”和“他者”的角色,从而无法获得身份和自我认同。
(二)正面引路人
沙希德成长道路上的正面引路人则是英国女教师迪迪。迪迪是沙希德所在学校年轻的文化课讲师。她在课堂上和学生们热烈地讨论黑人历史和当代文学。迪迪崇尚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背后所宣扬的自由和民主,以至于在她的办公室门上醒目地挂着“一切限制都是监狱”[4](P34)的牌子。迪迪对于美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于美国文化和自由民主的关联与当时的世界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二战后,随着英国帝国形象的轰然倒塌,美国成为政治寡头,1989年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加固了自己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象征的地位。随后,美国的流行文化偶像,像书中不断提到的“王子”、“麦当娜”逐渐成为席卷全球的文化符号,受到全球青少年的追捧。迪迪深受其影响,她毫无民族偏见,并鼓励自己的学生“研究一切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从麦当娜的头发到皮夹克的故事。”[4](P26)而被英国文化隔绝在外的沙希德,也得以在迪迪的陪伴下出入以前自己单独无法涉足的场所,他有机会体验伦敦本土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正如Homles所说“迪迪教自己的学生通过当代文化、种族和性别政治的理解去阐释自己生活的世界。她鼓励沙希德,并且向他展示了他之前从未遇到的世界”。[6](P41)
对于美国流行音乐的共同热爱也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自然的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最初的沙希德表现的像个“脆弱的小男孩”,而迪迪则在两人的爱情中扮演着引领者的作用。她鼓励沙希德涂抹上女性使用的化妆品,鼓励沙希德找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勇敢寻找真正的自己。迪迪深深地影响着沙希德,她使得在母国文化和居留国文化之间进退两难的沙希德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她所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使沙希德免于在母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备受折磨,而美国音乐给身心带来自由使得沙希德最终确定了自己想要拥有的生活方式。但是最终他意识到迪迪所代表的自由和爱才是救赎自己的最好方式,而最终没有滑向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的深渊。
三、成长出路
在《黑色唱片》中哈雷夫显然对于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持强烈反对意见,并且对于保持“英国性”的做法嗤之以鼻。小说的标题《黑色唱片》就源自于美国著名黑人歌者王子的同名黑人音乐专辑,而王子本人“半黑半白,半男半女,半阴半阳,既阴柔又阳刚。”[4](P35),正是杂糅文化的最好的证明。此外小说中处处透露出文化杂糅的痕迹,这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理论不谋而合,巴巴认为“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是杂糅文化”,而文化的杂糅不仅是解构本质主义的利器,也为沙希德这样的亚裔移民提供了获取流动、可建构身份的可能。
沙希德这也为少数族裔提供了在母国和宗主国的文化冲突之下的间隙中,沙希德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
他选择了美国的流行文化,选择了蕴含在流行文化后面的杂糅本质和当今文化多元趋势的认可。沙希德没有选择像父辈移民那样一位地膜拜西方文化,也没有选择和朋友一样盲目地维持自己的“民族性”。这里也表现出作者哈雷夫对于传统身份观念的质疑,沙希德的选择展现了身份的叠加而非分裂,这是对“英国身份一种灵活而动态的解读,也可以被视为成为英国人的一个新方式”。[7]他在自由思想的推动下,“找到一支笔尖尚好的自来水笔,满怀兴奋的开始写了起来”。[4](P366)在写中沙希德“可以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在工作和爱情中”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同时,写作也成为沙希德宣泄情绪和重新建构身份的方式。在后殖民时代,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依旧以文化输出的方式奴役着第二代的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根”,甚至“不会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只会说着标准的英语,他们会以英语来继续续写殖民国的意识形态,本民族始终处在失声的状态,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听见,湮没在居住国的文化当中,长此以往,他们无法解构殖民国的霸权统治。而沙希德通过写作,解构了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他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被压制的弱势文化,可以对占据主导的霸权文化进行“改写”,通过写作,可以打破壁垒,逐渐消除种族、性别的差异,改写自己的边缘文化身份,改变没有话语权的现状,在写作中,也可以找回自己的民族记忆,让世界重新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小说的结尾,沙希德由一个迷惘的少年最终成长成为一个初露锋芒的艺术家。至此这部小说也真正地成为了一部kunstlerroman(艺术家小说的德语版本)。[5](P311)
四、结语
《黑色唱片》中主人公沙希德是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缝隙”中的新型“英国人”。通过追寻和选择美国的流行文化,他打破了原有的种族、阶级、性别的界线,跨越了人为的藩篱,构建出既不属于东方文化也不属于西方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沙希德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着亚裔群体在英国的成长体验,沙希德个人的成长焦虑也可以上升为群体的焦虑。借用成长小说的创作形式,库雷西不仅仅向读者们讲述了一个亚裔少年的成长故事,也揭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移民后裔的成长选择。
[1]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
[2] MOORE GILBERT,BART. HanifKureishi[M].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113.
[3]SenAmartya.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151.
[4] 哈尼夫·库雷西.黑色唱片[M].师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Arthur J. Deikman.Them and Us: Cult Thinking and Terrorist Threat[M]. Berkeley: Bay Tree, 2003.
[6] Holmes, Frederick M. The Postcolonial Subject Divid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Kureishi’s The Black Album as an Interest of Rushdie’s The Satanic Verse[J].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01,(3)37:296~313.
[7]钱程. 英国小说家哈雷夫·库雷西——英伦巴基斯坦裔文化的前驱[J].外国文学动态,2009,(2):22~26.
2095-4654(2016)10-0058-04
2016-08-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消费主义的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小说研究”资助(12YJC752043)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