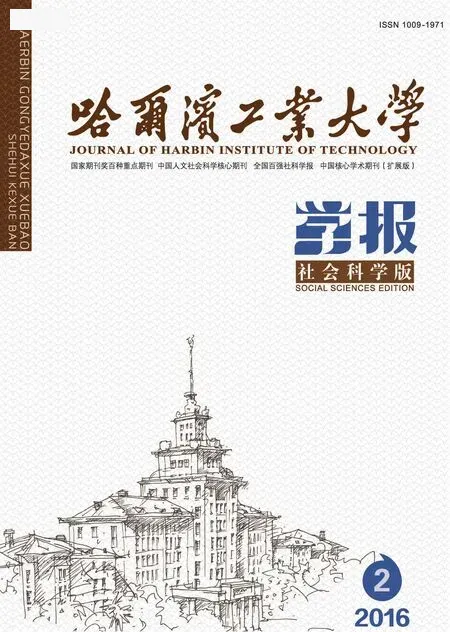陈莲笙的道教文学创作研究
曾小明,雷丽茹(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06)
陈莲笙的道教文学创作研究
曾小明,雷丽茹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06)
摘 要:陈莲笙肩负着敬道、悟道与弘道的宗教使命,在诠释道教经典与提升大众道教素养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其“天道至公”的创作主题与“从道为事”的行文结构,十分形象地反映出当代道教徒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情趣,为道教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陈莲笙;弘道;道教发展;精神情趣
陈莲笙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其信道弘道的心路历程与宗教体验,记录了道教在宗教理想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生存发展,成为道教与历史时代互动的鲜活个案。通过陈莲笙道长的文学作品,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道教随着历史发展与时代需求而不断进行调整和重塑的努力。
一、“道以文传”的创作理念
陈莲笙(1917-2008)10岁拜师于朱星垣道长门下,研读道教经书,并四处访道求学,成为道教正一派高道。在长期的学道与传道生涯中,他不仅积极进行道教的实践活动,还将对道教的所思所想融于文学创作之中。其文学创作首先以《道风集》刊行,去世后又结集为《陈莲笙文集》,代表作有《道教徒修养讲座》、《道教与当代社会生活》、《人生赠言》与《道教常识答问》等,基本上贯穿了他学道、弘道的整个生命历程。他在其《道风集》序言中明确写道:“十余年来,余思之甚者,以当代道教之发展为最;十余年间,每有所思,即述之以文,随作随发。”[1]6随着识道、悟道、传道的生命实践,陈莲笙对“当代道教之发展”的思考亦不断趋向全面与成熟,以对《老子》所倡导的“大善若水”的思考为例:
太上曰:“上善若水”。水的一个德行就是“动善时”。道教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像“水”那样,适应发展的时代和变化的社会。[1]251
学道的人,需要将自己的身心和行为都修炼得像“水”一样的透明、纯净、无私和奉献。这样才是真正上善得道的人。[1]41
水悄悄作着自己的贡献,牺牲着自己,但是,从来不同万物相争。我们学道的人,就应该学习“水”,去为万物服务,使万物得利,这就是“道”。拿“水”的教义思想去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学道为人”。[1]39
本来,水是万物之源,又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物质生活资料,并因此上升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寄托,由此,人的心灵世界又通过水的意象折射出来。水之意象在中国古典各类文学作品中被大量运用,被赋予丰厚的情感,既蕴含着真美善等崇高情感与缠绵悱恻的思绪,又滋生着时光流逝、人寿苦短、命运无常的感伤与哀愁。陈莲笙通过对独具东方古典美韵的文化内涵水之象的构建来实现对道之意的追寻,水的意象呈现出道的风貌与意蕴。不言而喻,陈莲笙在对水顺势而为虽弱而坚以及虚静无争而利万物的思考中,完成了对崇尚阴柔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并努力将水利万物内化为当代民族性格,为个体生命的润泽和民族生命的延续做着重要的贡献,体现出其建构当代人文精神的努力,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道的认识与体悟。正如陈莲笙所说:“前辈道长对于道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改和发展,以丰富道教的教理教义。”[1]173这亦是他“每有所思”的原因和目的所在。
纵观陈莲笙的文学创作,贯穿其思考始终的便是对“道”的坚定信仰,以宁静淡泊的自然关照心态,在对自然的认识与观赏中领悟道的魅力。总体上呈现出“适应时代,采纳先进,弘扬道教,服务社会”[1]220的创作旨趣,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陈莲笙的文学创作负有弘扬道教经籍的神圣使命。陈莲笙本着对道教事业的深厚感情,弘扬、振兴道教成为其神圣使命,而弘扬和发展道教又离不开道教经籍。道教经籍涉及道教的方术、戒律、科仪等诸多领域,蕴含着道教的宗教精神实质,记录着道教历史发展的过程,是道教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力量与源泉。陈莲笙《在上海城隍庙住持升座典礼上的开示词》明确指出:“经是道教教义、典籍之经文,是历代祖师所著作的经文。所谓无文不立,无文不度,无文不光,无文不成,无文不生,因此,学经,尊经,至关重要。”[1]201正是因为此,在陈莲笙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道教经籍成为其文章的基石,有对道教经籍直接介绍的如《道教常识答问》中的“道教教义和经籍”,有对道教谶书名篇名句进行生活化诠释的如《人生赠言》,有对道教经籍中的基本教义进行深入阐释的如《度人先度己》、《以“啬”治人事天》等。正如陈莲笙所说:“道教的信仰却因为种种历史上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未能作出新的丰富和诠释,使得道教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也使得道教不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多的贡献。”[1]252由此可知,为了突破道教自身发展的局限,促使道教适应当代社会,从而赢来道教健康发展的春天,丰富和诠释道教经籍成为道教徒应有的使命之一。
追本溯源,道教经籍又有“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的神话传说。《道藏》指出:“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2]由此可知,道教经籍都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凝聚了金、木、水、火、土五德的品质,又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如此,介绍、诠释、丰富道教经籍,一方面可以保持道教信仰的神圣感,充满想象力的道教经籍无疑给当代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从而树立起道教作为宗教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正常的道教活动与封建迷信区分开来,强调斋醮活动不是谋利职业,而是“济世度人”,是以道教经籍清正身心、拔除是非邪恶之念,由此来坚定大众对道教的认可与信仰。正是基于此,“写经弘教,功德无量”的创作理念贯穿于陈莲笙的道教文学创作始末。
其次,陈莲笙的文学创作又负有提高道教徒修养的使命。在陈莲笙看来,“道教的‘命’有赖于道士”[1]49,道教的兴衰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高低。道教的发展和道教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道士的积极参与,而道心坚定、道艺精湛、道风清正的道士,才能真正承担起道教传承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道教的传承亦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和谐程度亦取决于道教徒的文化修养与道学素质,离不开“主动去适应社会需要的道士”[1]129,这亦为道教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道由人显,东汉末期,因为有张陵,才有道教的正式创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有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道教教义才系统精密起来,其仪式才得以丰富恢弘;唐宋金元明等朝代,道教中人才辈出,连绵不断,道教也得到很大发展。可是,清代以来,道教出现了衰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道教缺乏人才,道教徒的素质低。[1]25
陈莲笙站在历史的高度,面对清代以降道教衰势所得出的经验教训,将道教的发展与道士素养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出于此一创作理念,《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迈向新世纪》、《道教徒修养讲座》、《道教常识答问》、《上海道教音乐集成》等著作得以诞生。这些作品又结集为《道风集》,陈莲笙指出,《道风集》“一言以概之,即当代道教之发展与道士之修养,故以名集”[1]6。在《道教徒修养讲座》中,陈莲笙基于对《太霄琅书经》中“人行大道,号曰道士”这一道士身份的阐述,将“学道为人”“奉道行事”“斋醮度人”作为道教徒安身之本与行事之则,把“爱国爱教”“适应时代”作为道教徒提高自身修养最重要的内涵式发展路径,在学道、悟道、得道的过程中完成度己与度人。陈莲笙编选上海道教音乐亦是出自同样的目的,希望藉助“风格细腻、庄重、优雅,节奏上板眼分明”而又富有“清新、活泼、欢快、明朗的韵律和生活气息”的道教音乐,来“给人宁静、超凡脱俗之感”[1]253,从而形成“清静无为、大公无私、淡泊名利、克勤克俭”的道风。
再次,陈莲笙的文学创作又承担起促使道教适应社会与服务社会的重任。“道法自然”是道的基本属性,陈莲笙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界与社会”,如此,道教适应当代社会就成为“道法自然”的应有之义。基于此,陈莲笙又将“道法自然”在适应社会与服务社会中具体诠释为五个方面:一是教义思想必须增加新内容;二是宗教生活必须作出新调整;三是教徒规戒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四是积极进行各种服务社会、壮大自己的道教事业活动;五是在团体和庙观管理中,借鉴社会成功的经验。以“教义思想必须增加新内容”为例,陈莲笙明确指出:“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观和神仙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教义的解释。”[1]13由此可知,陈莲笙本着对道教的坚定信仰,以当代社会的发展来丰富与诠释道教教义,从而为道教的健康发展赢得了足够的政治空间。正如陈莲笙的弟子所说:“(陈莲笙大师)著写了《道风集》,从教义思想、规戒伦理、组织建设和宫观管理等方面为道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创建了丰富的思想平台。”[1]584
值得一提的是,陈莲笙促使道教适应社会与服务社会,并不是要改变道教祖师们传下的清规戒律,而是推崇道教传统,强调行善去恶对于延年益寿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明确指出,个人的身心健康离不开万物的整体和谐,生命的延年益寿不仅在于个体的修炼,亦同样受着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基于此,陈莲笙以道教向善的伦理道德来影响与完善世俗伦理,一方面,道教正一派一直推崇“济生度亡”,作为正一派得道道士,陈莲笙顺道而行,时刻不忘将“济生度亡”的教义融入生活,并以此指导人生。另一方面,生命理想的原型在其文学创作中不断受到强化,《人生赠言》中所列举的历史人物都在积极地探索生命的奥秘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成为种种修道延生路径的代表与典范,正如陈莲笙所说:
我们道教徒都向往神仙,做神仙就是自顾自的吗?不是的,经籍里对于神仙世界有许多描绘。《太平经》里说到天上“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神仙们是相亲相爱,相扶相助,没有私心杂念的,否则怎么能算神仙呢?太平道向往的理想社会就是“太平”。太是天的意思,像天那样胸襟开阔,毫不偏袒照耀万物;平是地的意思,像地那样养育万物。天地对于万物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道教向往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我们道教徒在社会上也应该有无私的牺牲精神[1]40。
毫无疑义,神仙是道教的理想典型,其超人的技能与超越生死的生命修炼又成为道门中人以及广大信徒效法的楷模。依据道教教义,道士的职责是引导人们飞升仙境、交接仙人而获得永恒的生存,以仙境生存的自由、享乐与美好来战胜人生苦难与死亡的可怕,这亦是道教“修道度人”的永恒主题。陈莲笙站在“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立场上,以神仙化的故事演绎当代的善恶观念,倡导“仙道”对“人道”的规范,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人道”树立起楷模,让仙界的“忠孝节义、和顺仁信、长生不老、扶幽济困”成为道教徒以及广大信徒的伦理规范。
总而言之,陈莲笙将道教徒的文学创作看作是提升人的宗教境界、实现社会教化、进行人格培育的途径和工具,这显然是对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继承与发挥。他延续了老子、庄子等道家文学以虚空的心灵去观察天地万物,探究人生,从而上升到对“道”的认识与体悟,并遵循“道”的原则臻至生命自由和无限的境界;同时,陈莲笙又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论”,从而将弘道与弘扬社会传统文化、将道教发展与服务社会完美地融为一体,体现出道教文学创作的新特色。
二、“天道至公”的创作主题
陈莲笙主要创作畅玄体与叙事体散文,在其散文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天道信仰,道心坚定的道教情怀又是天道信仰的重要载体,在道教徒责任感的驱使下,陈莲笙将天道信仰又以文学创作的形式通过天道至公这一人类永恒主题表现出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通过历史人物成败得失以此引起对天道至公的关注;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陈莲笙对天道至公的关注就是要寻找一条引导广大信徒对道的信仰之路,为广大民众建构出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同时,陈莲笙又以其一生对道的坚守与信仰为当代人提供了现实榜样。因此,通过对陈莲笙文学创作主题的探究,既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天道的坚守,又可以十分形象地感觉到当代道教徒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情趣。
作为畅玄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人生赠言》,陈莲笙在其著作中展现出许多得道者的成功人生,展现其道德信仰、生命意识与幸福观,又以失道者的失败人生作为比照,十分鲜明地表达了道在生命过程中重要指导作用,并不断凸显天道的大公无私与无所不在。《人生赠言》始于“天上仙花难问种,人间尘事几多更。前程已注公司薄,罚赏分明浊与清”条,终于“法度三千八百语,此节未必通于君。善恶两条均在律,一生祸福此中分”条,共100条。这些条目具有章回小说标题味道,概括了整篇散文的主旨,这些散文又可以大致分为以道解释人生与以道指导人生两大部分。一方面,人处尘世,生老病死以及功名利禄均会带来种种人生困惑,如何化解世俗烦恼的缠绕而进入淡泊明净之境,就需要不断地从道教经籍中获得智慧与启示,以道的心境与智慧来打量人世间的一切。比如“人能乐道自修身,疏水曲肱岂厌贫。不义而富且富者,我心都做是浮云”“可比当年一塞翁,虽然失马半途中。不知祸福真何事,到底方明事始终”。另一方面,在识道、传道与弘道的过程中,陈莲笙又以道师的身份给人以劝诫与警醒,比如“生前结得好缘姻,一笑相逢情自亲。相当人物无高下,得意休论富与贫”“从前作事总徒劳,才见新春时渐遭。百计营求都得意,更须守己莫心高”“行藏对时要知机,老鹤何天不可飞。道合可行非则止,此身莫为稻粱肥”,“休论富与贫”“守己莫心高”“莫为稻粱肥”都包含着世事洞明后的一种人生智慧。显然,《人生赠言》的创作始终以对道的领悟为其精神内核,个体生命对道的体知与把握的层次不同,其人生成败得失便迥然有异,从而树立起天道至公在人生中的无上权威。
作为叙事体散文典范之作《道教常识答问》,以“问答体”形式系统地介绍了道教常识,从道教历史、道教教义、道教科仪、道教宫观到道教修炼,涉及道教信仰的各个方面。《道教常识答问》虽然着重于道教常识的基本介绍,但是从其选材与行文来看,又具有道教叙事散文的典型特征。在介绍道教人物、宫观、经籍时,《道教常识答问》多采用传统的“传记”叙事手法,侧重于故事的记述,既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比如“蓝采和”条:“蓝采和,游方道士,一脚着靴,一脚赤足,手持大拍板,往来于街市上半醉踏歌。夏天穿棉袄,冬天卧冰雪。行路则边走边歌,歌词很多,都是劝人为善,看破红尘的仙意。后在濠梁酒楼轻举升仙。”[1]444叙事简约,又十分注意人物形象,字里行间亦充盈着对道教的深厚情感,并寄托着道教的哲理,具有了叙事散文的审美特征。
在《道教常识答问》的序言中,陈莲笙强调“道法无边”,在《人生赠言》的序言中,陈莲笙反复强调“天道至公,人道无私。至公者昌,自古以来,尽然”。并且又明确指出:“人们对于生活有如此不同之态度,生活也会相应给予人们以不同之回报。这就是天道之至公,人生之因果。”[1]249基于道体基础上对生命的理解是道教既有的宗教传统,生命修炼与得道逻辑具有同一性,成仙便是得道。陈莲笙所说的对于生活的不同态度,亦是建立在对于天道的体知与把握基础之上。个体生命的善恶、是非、死生、逆顺,取决于对天道的好与恶以及在践履过程中的顺与逆,这亦是陈莲笙“天道至公”的主要内涵。纵观陈莲笙的文学创作,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表达“天道至公”这一创作主题。
首先,崇尚立志,顺道而行。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指出:“凡事无大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安即万物自成。”[3]由此可知,道教创教之初就确立了对道的遵从与信仰,并且为后世所沿袭,在道教的传承与发展中凝炼为“道心坚定”的教义。陈莲笙又进一步将“道心坚定”的教义与世俗社会需求相融合,大力倡导立志与顺道而行。作为人生成长的心灵鸡汤《人生赠言》,处处流露出人生志向的重要作用。他在《久抱凌云吉未舒,荷竿渭水钓游鱼。文王千里求贤士,灭纣兴周任意如》中就明确指出:“为人处世一定要有大志,同时要有耐心,顺势而行。”[1]340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陈莲笙所推崇的志向都是建立在善道教化这一观念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志又具有浓厚的天道因子。他在《雪拥桥头马不前,风狂渔父莫开船。水流花谢人谁惜,早立坚心志勿偏》中说道:“水流花谢,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实难预料。人们要珍惜时光,尽快地正确决策,坚定意志,不偏不离,积德行善,超脱名利。”[1]343
如果说志是树立起对天道的信仰,那么行便是志于道基础之上的“奉道行事”。在顺道而为的生命实践场域之中,一方面,陈莲笙认为行可以提升生命的长度,他在解释道教传统观念“我命在我不在天”时指出:“道士的‘命’既有天神的主宰,亦有赖于自身的努力,这也是‘我命在我’。”[1]49另一方面,陈莲笙又认为“行”可以提升生命品质,成为道教信徒的楷模,他说:“有道之士,身体力行……我们的信徒就会从我们的‘行’中受到不言之教。”[1]17正是基于此一理念,在对羽化登仙道长的追念与缅怀中,陈莲笙最为看重的是道长的志之坚与行之勤。宋祖德道长“勤学仪范,于斋醮法务都有造诣”,傅圆天大师“勤奋朴质、公正无私”,龚群先生“道心坚定,坚韧不拔,嫉恶如仇,为中国道教之振兴鞠躬尽瘁”,都成为陈莲笙效仿的典范,并愿意将诸位道长的“道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永不止息”[1]234。显然,从尚志到重行,陈莲笙将提升人类生命智慧的道,引入到世俗人生的成长与发展之中,流露出了一种积极有为的儒家意识心态。
其次,积善立功,成仙之道。陈莲笙的散文创作有意模仿道教传统的善书体例。他在《道教常识答问》中指出:“善书大多以通俗简易的语言,结合儒释思想,讲解道教的伦理原则,加上历代注家引用丰富的历史事例解释,因此,自问世起,善书就发挥了有效的社会教化作用。”[1]484《人生赠言》所选取的历史人物,或者是道门中人具有宗教性格如葛洪等,或者利用神话传说赋予其宗教品质如韩愈等,或者是背“道”而行的失败者如蔡邕等,正反对比中凸显得道之人平安于世。无论是心灵鸡汤的《人生赠言》,还是春风化雨的《道教常识答问》,都有着规劝世人积德行善、以期终获福报的内在理念。在《道教徒修养讲座》中,《多行善功》对善作了高度的概括:“道教的善就是一切行为要符合天地万物的自然,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1]42基于这一理念,《人生赠言》100条,条条都是劝人为善。值得一提的是,“善”字出现在标题中的就有16条,“善为善应永无差”,“奉行善事要虚心”,“早宜崇善诵真经”,“若能向善子孙旺”,“善念心存福自来”,“善得根基保康宁”等等,均体现出陈莲笙积善立功的创作主题。
善不仅是个人修炼圆满的标志,同时亦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法宝。陈莲笙在解释《太平经》“天道无亲,唯善是与”时,将“亲”理解为“血亲”和“亲朋好友”,如此,善从个人的修炼延伸到社会伦理。在处理社会关系之中,陈莲笙将《太上感应篇》中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进一步具体为“忠、恕、俭、诚、朴、孝、信、慈、礼、义”,以这种品质与美德去处理社会关系便是“善行”,而“积善立功”才能名列仙班。显然,在陈莲笙的文学创作中,善既具有宗教信仰功能,行善成德以至于道,得道成仙而进入道的境界;又具有提升世俗伦理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提出道德修养的目标。陈莲笙将道德修养与宗教修炼完美合一,以宗教空灵的态度来面对烦琐的人生,又以道的境界来解脱世俗的纠葛。透过其文学创作,亦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陈莲笙的宗教心态与精神旨趣,陈莲笙推崇的善就是为了给人类生命创造出一个包容、和谐与适宜的生态环境,其宗教修炼的出发点并不是摆脱世俗人情,而只是要去掉世俗人情中的浮华,运用彼岸世界的智慧来认识、处理此岸世界的事物,从而体现出与尘世诗人共同的创作旨趣与美学观念。
再次,遵循天道,服务社会。陈莲笙一直认为社会需要是道教发展的历史机遇,因而继承传统、适应时代与服务社会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既定主题,其唯一的一首步虚词《大道颂》便明显地体现出这一主题思想:“大道生天地,大道爱人民。我们敬大道,大道随我身。天地呈吉祥,人际像亲人。社会多和睦,祖国更昌盛。”[1]211在《大道颂》中,陈莲笙毫不掩饰地抒发了对道的“敬”与“爱”,日常的生活修炼、炽热的思想情感以及真实的心理体验都集中在对道的信仰与体悟之中,流露出淡泊尘世名利、追求返璞归真的宗教心态,给人一种一尘不染、澄澈透明之美。“我们敬大道,大道随我身”,在如此直抒胸臆的诗歌中,道心坚定的人生志趣,以及由此催生的是非、善恶和美丑观念,在道涌动着一种百折不挠的生命活力中获得艺术化呈现。值得一提的是,《大道颂》的情感落脚点是“社会多和睦,祖国更昌盛”,这与《为洪伯坚道长制作道藏光盘成功题词》“弘扬道教,服务社会”基本一致。在陈莲笙看来,道教服务社会主要体现在度己与度人:
此经名为“度人”。这里的“人”,指的是学道的人和不学道的人,行善的人和无善心的人,甚至道德丑陋、行为卑劣、犯有错误的人。因此,学道的人,我们要度;尚未学道或者不学道的人,我们也要度。学道的人已经努力在走进道门了,需要我们拉一把,需要度。尚未学道的人更需要我们帮助,有的还需要我们当头棒喝,加以挽救,使其醒悟,脱离错误和罪恶的火坑。这就是我们道教的济世胸怀,也就是我们道教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之一。[1]166。
概言之,道教度人就是道教教义既要为信徒“生”的需要服务,又要满足信徒对“死”后世界的愿望,要切实关心人的精神世界,给人以伦理、精神和信仰的有益帮助与启迪。从度己到度人,再到“度社会”,重视的是度己所获得的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精神境界的外化,凸显的是个人修炼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亲密联系,正如詹石窗所说:“道教之所以把‘德养’的治身与治国联系起来,从治身到治国,又从治国到治身,是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无法离开国家整体的,只有国家整体达到和平的境界,个体生命的修炼也才能趋于完善。”[4]也就是说,服务社会成为修身向善的一个显著标志,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境界最终要成为救度民众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道教徒的宗教追求与人生价值体现为对社会、对国家有所作为。显然,陈莲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阐释道教之道,体现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创作趋向,并流露出在当代社会实现天道之自然这一文化体系的努力。
三、“从道为事”的创作结构
道教经典《太霄琅书经》指出:“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称道士。”陈莲笙理解为:“按大道行事的人才称为道士,做道士的人,要信仰道,追随道,按道的内容身体力行,奉道办事。”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说到‘奉道’,大家都知道太上的《道德经》五千言……包含着许多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道门中人当然就要更加重视《道德经》。”[1]30在陈莲笙看来,道士便是奉道行事,而道教之道又蕴含在道教经籍之中,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陈莲笙文学创作的艺术结构,又清楚地回答了陈莲笙为何最擅长畅玄体与叙事体散文创作。
《道教常识答问》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行文,立足于其青年时期学道经历,本着其传道弘道的历史使命编撰而成的一部道教信仰入门书。这种“问答体”散文创作,明显脱胎于道教语录体散文。道教创立之初,道教领袖以建立教义、弘扬道法而形成的语录体散文,为《道教常识答问》弘道的创作旨趣提供了十分灵活的表达形式。比如:
问:“守一”的修炼方法,有什么要领?
答:守一,是指在修炼养生时,保持身心宁静,并将意念集中于自身体的某个部位。守一之术源于《道德经》所说的“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抱一即守一,一即道。早期道教的《太平经》有“清身守一法”、“守一明之法”、“守一法”、“守一长存诀”等,称“守一”为“长寿之根也”。《西升经》的《慎行章》称:“恬淡思道,臻志守一。”守一之法必须恬静淡泊,一心守道。《云笈七谶》称:“凡守一者,身神常安。若体中不宁,当反舌塞喉,漱漏醴泉,满口咽之。讫又如前,咽液无数,觉宁乃止。止而未宁,重复为之。须臾之间,不宁之疴,即应廓散,自然除也。当时有效,觉体中宽软都平,便以逍遥复常。太极众真、太虚真人、南岳赤君、妙行真人,莫不修此,以成圣真矣。”修炼守一者,既可以是守思想上的道,也可以守体内纯阳之气,也可以守身体某个部位,例如丹田等,各家之说不尽一致,但是,集中意念,身心安静,以达到健康除病,这又是一致的。[1]502
从回答“守一的修炼方法,有什么要领”条,可以清楚地看到陈莲笙的行文结构。首先简单解释“守一”的基本含义,其次便立足经典,引用《道德经》、《太平经》、《西升经》、《云笈七谶》等道教经籍,追溯“守一”的源头,例举“守一”的方法,探究“守一”的境界,最后又以个人的宗教实践来辨伪识真,博采众长,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洋溢着其对道教经籍的厚爱与虔诚;引文简练、生动,灵活多变而又极富表现力,体现出陈莲笙对道教经籍的娴熟与深入,在神圣的信仰中又以个人的真实体验来完善和发展道教经籍。毫无疑义,《道教常识答问》采用问答式结构,以初学道者的身份发问,又以师长的身份作答,不断“开启学道人的眼目”,客观地呈现了陈莲笙在“利万物”中学道、悟道与弘道的宗教实践,又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了一个道教徒在“道心坚定”的信仰中所流露出的宗教情感。同时,陈莲笙以宗教视角来阐释传统文化中诸如“道”、“无为”、“我命在我不在天”、“做七”、“上清宗坛”等范畴与术语,融传道弘道的自觉与“道法无边”的慎重于清晰的历史脉络之中,又呈现出用典文学的庄重美。
纵观《道教常识答问》中的“一问一答”,其行文都体现出与“守一的修炼方法,有什么要领”一样的内在逻辑,那便是“释道——载道——得道”创作结构模式。当这一结构模式与道教传统的教义“道由人弘,教由人传,法由人显”[1]201相契合时,亦同样形成了《人生赠言》的基本创作结构,不同的一点是,《人生赠言》中道之载体不是道教经籍,而是历史人物所呈现出的成败得失的人生。比如陈莲笙在解释“新来换得好规律,何用随他步与趋。只听耳边消息到,崎岖历尽见亨衢”条时指出:
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总会碰到许多困难,经受许多折磨,这就是人生的艰难崎岖。但是,人生也会有许多新的机会,只要善于抓住机遇,崎岖是可以终结的,磨难是可以度过的,光明大道是可以来临的,西汉末年王莽起兵,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兵弱将衰,根本无法抵抗,这时候,王莽已经率领军队来到昆阳,兵临城下,刘秀情急之中,命将兵百余人赶来一些虎豹、犀象等野兽前来助威,自己带了万余名兵将跟随在猛兽之后,冲向王莽的军队。结果,王莽的军队慌乱起来,立刻崩溃。刘秀的军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此时,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猛兽全皆逃遁。刘秀乘机打扫战场,缴获了王莽军队的装备,为东汉建立准备了物质条件。应该说,刘秀当时的困难真是生死存亡,但是他把握时机,施展奇招,终于走出险境,开创了新的局面。[1]444
在“释义体”叙事随笔中,其叙述方式一般是:开头或叙述某一现象,或叙述某一事件的背景,或探究社会中某一困惑,引出主要故事或人物活动,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人生经验教训,对人进行劝诫与勉励,其内在逻辑仍旧是遵从“释道——载道——得道”这一基本行文结构。《人生赠言》从现实中的困惑或现象入手,既体现其关注现实以及解决现实困惑的努力,道教徒所倡导的践履道就是要摈除杂念,远离阻止个体修身养性的天敌,将思想意念集中于天道之中;又沿袭着民间艺人的叙事方式,以读者本身的渴求来引起其注意,从而抓住观众求道的心理,循循善诱,促使其自然进入到他人的成败得失的人生经历之中,在感同身受中或获得成功的经验,或获得失败的警醒。
从《道教常识答问》到《人生赠言》,道之载体从道教经籍转换为成败得失的人生,源于道教徒崇奉“道、经、师”道教“三宝”的基本教义。经宝便是道教三洞四辅各种真经,是度世的桥梁;师宝是十方得道圣众,能够开启学道人的眼目,又可以进一步扩大为顺道而行的人。学道修道的人一定要敬奉三宝,因为“道由经传”、“道由人显”。在陈莲笙看来,“道由人显”有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方面,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有高层次修养的道士,“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另一方面,道就存在芸芸众生的成败得失之中,顺道而行的历史人物成为道的载体,如“百事随缘”的顾况,“和气生福”的楚庄王,“一心向善”的邵雍,或善待他人,或淡泊功名,或远离欲望,各个短篇具有内在的完整叙事结构。从整体来说,各篇章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又彼此有所渗透,在勾连与扩展中成为同一主题不同生活情境的叠现,又使得《人生赠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整体的叙事结构既不体现在情节的连续性,又不体现在人物间的交往,而是体现在对道的领悟之中,以顺道而行的人生世事历程的哲理意蕴为总纲,从而形象地呈现了道在万物之中的宗教体验与人生思考。显然,由道这一主题统率世情世相,反映出一个道教徒以生活化的故事传道弘道的宗教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
对道进行故事化的描述,不追求人物故事的完整性,重视的是道的生动描写,其目的只是确立了道在人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既不讲究情节的曲折复杂,亦不重视人物静态的介绍以及与情节无关的性格描绘。如此,人物经历的叙述并没有成为叙事重点,而是伴随人物经历之成败得失的道成为关注的焦点。截取人物生平中的某一事件进行因果探究,集中于此一事件所蕴含的智慧的生动描写,与完整人物生平经历的叙述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其事件的选取又符合该人物生平的基本走向。人物性格与人物形象的忽略,使得处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物又能真正构筑出一个顺道而行的“人”,共同展示着“道由人显”的宗教意蕴。如此,在《人生赠言》中,如同现实生活一样,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孤立存在,每一个事件都不会孤立发生,人物和人物,事件和事件,汇成道的内涵与载体。这个“人”既是“道由人显”中的“人”,又是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识别道、践履道而渴望成为的“人”。
如上所知,道教正一派传统的授箓仪式影响了陈莲笙的思维方式,授箓仪式中需要跪诵《道德经》、《度人经》、《三官经》、《功课经》等道门经典以及聆听度师宣讲的活动,又直接影响了陈莲笙文学创作的思想情趣与行文结构,而道教徒应有的爱道、敬道、弘道的神圣使命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情感基础与思想主题。简言之,陈莲笙以文学创作诠释经典,推动道教文化发展;又以文学创作提升道教徒的宗教素养,促使道教更好地服务社会,其弘扬文化与服务社会的热情构成了陈莲笙文学创作的基本底蕴。
参考文献:
[1]陈莲笙.陈莲笙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道藏:第22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12.
[3]太平经:上[M].杨寄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78.
[4]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0.
[责任编辑:郑红翠]
·文学与文化研究·
Chen Liansheng's Literary Creation of Taoism
ZENG Xiao-ming,LEI Li-r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nan Normal Universty,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Shouldering the religious mission of worshipping,appreciating and promoting Taoism,Chen Liansheng forms his writing theme -“Impartiality of Natural Laws”and writing structure -“with Taoism as Business”in literary creation for annotation of Taoist scriptures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Taoism attainment,which vividly reflects the thinking mode and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contemporary Taoists and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Key words:Chen Liansheng;Taoism promotion;Taoism development;spiritual temperament
中图分类号:I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2-0087-08
收稿日期:2016-01-05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课题“中国宗教文学史”(15ZDB069)之子课题“现当代道教文学史”。
作者简介:曾小明(1975-),男,湖南武冈人,讲师,博士,从事中国文化与电影批评研究;雷丽茹(1991-),女,湖南永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道教文化与电影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