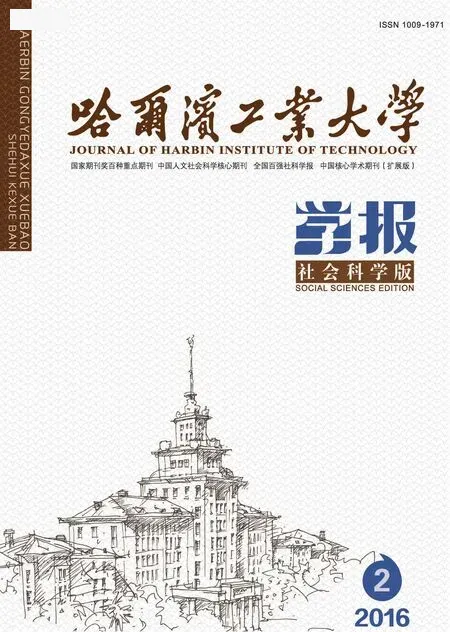中国铁路文明的现代化意蕴
王德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
中国铁路文明的现代化意蕴
王德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
摘 要:中国铁路工程文明源自西方重要的“物器”文化并承载着工业文明精神。以牵引动力方式为分期标准看,中国铁路工程文明展示出蒸汽机车的“中西文化”碰撞,内燃、电力机车的规范的“科层制”,动车组“和谐”的“技术理性”和磁悬浮嵌入“国际化”交通枢纽的历史发展过程,由此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与其说是人类创造“人工界”的科技理性主义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人本主义的胜利。中国铁路的变迁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的工业精神,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在推动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铁路文明;现代化;工业精神
工业化不仅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础,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工业经济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扩散的过程,由此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作为西方工业经济技术扩散的结果,中国工业在这个世界性的从低到高的阶段性转移扩散中,绝大多数产业尚处于这一转移过程的初级阶段。如何向高端发展,实现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和极致化,在更高的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标准下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这除了需要物质投入以外,更需要培育工业强国最深层的基因,即现代工业文明精神[1]。然而,在不太长的中国工业化中,与物器层面的“茁壮成长”相比,具有与传统农业文明不同的理性文化模式的工业文明精神,却离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相距还远。
源自西方物质文化并承载着工业文明精神的铁路工程系统,是中国工业化的典型。对中国铁路工程文明历史演进的分析,即通过对中国铁路工程的第一类文化如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和第二类文化如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演进和变迁,能够合理地透视出当代中国工业文明精神特质的生长点和发展路径。而深入认识和把握工业文明精神的内涵,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工程哲学关注的理论内容,也是工商界关注的焦点。那么,现代工业文明精神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一、现代性——现代工业文明精神的特质
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精神对英国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发展的“引擎”[2]。“工业精神”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是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已雄霸全球[3]。作为工业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工业精神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人提出其内涵主要包括崇尚科学,对探寻自然规律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有着崇高的使命感;勤奋敬业,诚信经营,对财富和事业的最大化有着不倦的追求;敢于冒险,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对推动工业化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注重法治,强调规则和标准意识,追求经济和社会生活运作的规范化;实业兴国,把推进工业化、提高经济竞争力上升到实现应有的国际地位的高度[4]。其实,对工业精神的探讨,离不开对工业文明内涵的理解。
工业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而言的,有人分析其特征包括“充分自由的市场及其体制、敬业的工人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5]。实际上,“现代工业文明引起的显著变化是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世界性的交往等社会活动领域的急剧扩大,以及科学、艺术、哲学为主要形态的精神生产领域的空前自觉与发达。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真正体现人的精神自觉的文化模式。……即把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6]。而其特质就是“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它的精神性维度包含理性、启蒙、主体性、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它的制度性维度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7]10。而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成机制,即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度机制,吉登斯认为,是社会行动从原始地域性情境中脱离出来,然后用“人为的”理性化的抽象体系“再嵌入”的过程[8]。铁路工程文明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它的内涵又是怎样的呢?
二、铁路工程文明与分期标准
在了解铁路工程文明内涵前,先要理解文化以及工程文化的含义。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是人对自然的超越,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活动产物。人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角度出发,提出了第一类文化和第二类文化的分类。所谓第一类文化是基于人类在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自然过程取得的成果,表现为自然科学、技术等以及由此造出来的工具、器皿、机械等物质文化。第二类文化是指人类在创造物质文化过程中,认识、改造、适应、控制社会环境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组织、制度、政治、法律以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语言、教育等规范文化和宗教、信仰、审美、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9]。也就是科技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等。
我国对工程文化的深入探讨是从工程哲学开始的。殷瑞钰院士等著的《工程哲学》一书中给出工程文化的含义,即人们在从事工程活动中,关于思维、决策、设计、建造、生产、运行、管理等过程的理念、行为规则等[10]。尽管这一含义的文化含量不够丰富,但其奠基性不容置疑。如果结合工程哲学、工程系统理论、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等理论,可以给出工程文明模式的含义:它是指在特定民族和特定时代的工程共同体在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历史地形成工程科技、工程规范和工程价值等多系统因素互动联系的存在方式。即工程文明主要内含了工程物质、工程科技、工程规范和工程价值。
基于以上所梳理的文化和工程文明的基本含义,可以给出铁路工程文明的概念。所谓铁路工程文明就是以车头、车厢、铁轨、车站及铁路科技等物质文化为基础所形成的铁路制度、管理规范,并含有“现代性”精神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
对铁路工程文明的历史划分是对其研究的前提,对此,许多人做过一些工作。如在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工程演化”课题中,傅志寰院士提供的《铁路的演化过程与规律》学术论文等。傅志寰院士以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为分期标准,将铁路发展阶段分为快速发展阶段、质量升级阶段和综合运输阶段[11]。论文具有宏观性、概括性和指导性。
如何推进和深化对铁路工程文明的研究,还赖于我们如何确立铁路工程文明的分期标准。而能够成为铁路工程文明分期标准应符合四个条件:第一,全过程反映铁路工程文明的科技发展进路和成果;第二,基本反映铁路工程文明的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第三,能反映出铁路工程文明中包含的精神文化特质;第四,能够揭示铁路工程文明的物质、规范和精神这三个层次文化因素的互动和联系。
符合以上条件的铁路工程分期标准应该是铁路牵引方式。通过以铁路牵引方式作为铁路工程文化分期标准,能全面而又鲜明地反映出铁路工程文明的发展脉络和逻辑线索。
三、中国铁路工程文明的分期
自19世纪第一条铁路诞生以来,铁路牵引动力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组和磁悬浮列车的迥然不同的技术变革,由此演绎出铁路工程文明改变中国社会交通的历史画卷。
(一)蒸汽机车的“中西文化”碰撞
蒸汽机是一种把热能转变为机械能的动力机械,是由瓦特最终改进已有蒸汽机而发明的重要动力机,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重大成果。而蒸汽机车则是蒸汽机这一产业技术在铁路交通领域的扩散与融合。1829年1月8日,英国人斯蒂芬森发明了蒸汽机车,人类进入机械化的动力时代。人们称他为蒸汽机车之父[12]。它是通过车轮运转前进的,它自带能源,并由其他站台补充,能源介质是煤和水,在供给能源方式上,它是多次离散地向炉子供煤。带动列车运动的动力源来自蒸汽机车车头。它的鲜明的工程特性是“有轮、单点离散能源自给性”,这是它与以后列车不同的实质。
我国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由英商在上海擅筑的吴淞铁路,全长15公里。但因与当地官民的冲突,被清政府赎买后拆除。由中国自营且保留到今天的铁路是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为开平煤矿开发而修建的唐胥铁路。全长10公里,1881年修建并通车[13]。铁路管理复杂,当时清政府没有会计概念,各路段没法统计车务情况,19世纪末张之洞引入银行会计制度筹建中国铁路公司,这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4],也为中国开启了现代企业制度。
蒸汽机车其热效率低,牵引性能差,工作环境特性和劳动条件极坏,无法适应铁路运输增长的需求[15],1952年7月,四方机车车辆厂仿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解放型蒸汽机车。2005年12月9日,全世界铁路干线最后的蒸汽机车终于从集通铁路正式退役,为人类服务了180年的蒸汽机车终于退休[16]。
(二)内燃、电力机车“规范”的“科层制”
世界内燃机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1894—1922年的萌芽阶段;;1923—1945年早期发展阶段;;1946—1960年战后恢复和大发展阶段;1961—1976年持续稳定发展阶段;1977— 1992年机车水平显著提高的发展阶段,在1984年,内燃机车正式进入了微机时代;1993年起内燃机车交流传动大发展时期[17]。采用先进的内燃机车和电力机,发展我国内燃化和电气化的机车,是老一辈铁路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及广大铁路员工和各级领导的长期心愿[18]2。1958年9月9日,我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在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研制成功。
与蒸汽机相比,内燃机车的效率和清洁性大大提高,它不像蒸汽机车要不断地加水和煤,运行条件只需加煤油就能一直行驶下去,也不像电力机车必须依靠架空接触导线才能行驶,因此,世界各国的内燃机车所占机车比重都很高。如2007年,我国内燃机车保有量达到12261台,占总保有量的67%。[18]6
内燃机车也是通过车轮运转前进的,它也是自带能源,能源介质是油,在供给能源方式上,它是相对连续地向内燃机内供油。而带动列车运动的动力源来自内燃机车车头。它的鲜明的工程特性是“有轮、单点连续能源自给性”,它与蒸汽机车最大区别在于能源供给的相对“连续性”而不是“离散性”。一些国家,由于铁路电气化一次投资过大,先由蒸汽牵引过渡到内燃牵引,然后在某些适于电气化的线路上再由内燃牵引逐步过渡到电力牵引[19]。
电力机车是随着电动机的创造而发展起来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首先在铁道上采用电力来牵引车辆试验的,是俄国工程师毕罗茨基在1876年进行的[20]。电力机车具有功率大、过载能力强、速度快、整备作业时间短、维修量少、运营成本低、污染小、工作条件较好等特点。电力机车的发展很大程度受社会电气化程度和铁路沿线架设输电架空电线的影响。我国电力机车发展与内燃机车发展时间同步,1958年,湘潭电机厂和铁道部株洲田心机车厂联合研制的第一台大功率6Y1型电力机车问世。
电力机车也是通过车轮运转前进的,它的能源介质是电,在供给能源方式上,它由列车体系外的社会电网提供。而带动列车运动的动力源来自电力机车车头。它的鲜明的工程特性是“有轮、单点连续能源它给性”,它与内燃机车的最大区别即能源供给是绝对连续而不是相对连续,且是“它给性”而不是“自给性”。
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发展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年。我国铁路工程的规范化大都是在这个时候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中,“理性化的经营活动的出现和快速发展,越来越复杂的管理机制的形成必然采取科学的理性原则和技术手段来加以调节和管理。行政管理中现代性确立的标志是科层化的理性管理取代了传统的经验管理”[7]12。
由于铁路规模的扩大和运行复杂性的提高,要求经济运行的理性化,即会计制度的确立和行政组织制度的“科层制”。如由铁道部到铁路局,也即铁路枢纽,再到各火车站,由此构成铁路系统的管理体制,是经济运行理性化的制度保证。而站长、段长、列车长、列车员又构成铁路系统组织体系。铁路系统工作人员的层次化、专业化、职业化是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科层制”的表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公布、制定、修改了国家铁路规范标准近千个左右。
(三)动车组“和谐”的“技术理性”
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在行驶中全靠前面的车头拉动,并顶多在车尾加挂另一车头,而动车组不光是车头带有动力,车尾甚至列车中间的车厢也有动力,使列车行驶的速度大大提高。在载客方面,拖车、动车均可载客。
动车组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先进、安全可靠、乘坐舒适、节能环保等[21]。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上行驶的由中国制造的CRH3型动车组,以每小时350公里的最高时速,在120公里中用时30分钟,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营速度的世界纪录[22]。据铁道部人士介绍,中国完全掌握了动车组9大关键技术及10项主要配套技术。时速200公里动车组的国产化程度已达到70%以上。
动车组也是通过车轮运转前进的,它的能源介质是电,在供给能源方式上,它由列车体系外的社会电网提供。而带动列车运动的动力源来自列车的多个动车。它的鲜明的工程特性具有“有轮、多点连续能源它给性”,它与电动列车的本质区别在于列车动力能源供给的“多点”而不是“单点”。正是这一工程特性使它达到了高速的目的。
动车组体现的绝非是单纯的“工具理性”,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相比,它更多地以“工具理性”作为手段而张扬出具有人本精神的“价值理性”。我国动车组的工程文化精神内涵就在它的名称上,即“和谐”。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我国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掌握了包括动车组设计制造九大关键技术,以及十余项主要配套技术。这些高科技奠定了我国动车组的节能环保特点,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CRH系列动车组成零部件大约有12000件,分为145个子系统,其产业链涉及12个省,直接参与设计制造的企业达100多家。这说明了人与人的协同;而在设计和制造中采用高速转向架、全自动恒温空调系统、气密性车体结构及隔音降噪措施、车厢座椅可调节、旅客目视车窗也不会眩晕等等[23],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四)磁悬浮“嵌入”“国际化”的交通枢纽
磁悬浮列车是自蒸汽机车问世以来铁路技术最根本的突破,1922年德国工程师赫尔曼·肯佩尔首提电磁悬浮列车,1934年申请了磁悬浮铁道基本专利。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日、美、加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始筹划进行磁悬浮运输系统的开发[24]。磁悬浮列车是依靠电磁场特有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特性将车辆托起,使整个列车悬浮在线路上,利用电磁力进行导向,并利用直线电机将电能直接转换成推进力来推动列车前进的最新颖的第五代交通运输工具。它具有“高速运行、稳定安全、污染小、易维护、运输效率高”等特点[25]。
磁悬浮列车的问题也很突出,如无法利用既有铁路线路,由于无法从一条铁轨借道岔进入另一铁轨,列车只能从起点驶向终点,再原路返回,易出现磁悬浮轨道越长,使用效率越低的情况,所以采用“全程双线折返运行模式”。
磁悬浮列车是无轮列车,它的能源介质是电,在供给能源方式上,它由列车体系外的社会电网提供。它鲜明的工程特性是“无轮、全线连续能源它给性”,与其他列车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无轮”而不是“有轮”,还有动力能源的供给是“全线”而不是“多点”。
我国上海磁悬浮列车西起轨道交通2号线的龙阳路站,东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专线全长29.863公里,是由中德两国合作开发的世界第一条磁悬浮商运线,2003年1月4日正式商业运营,是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专线。作为城市交通工具,上海磁悬浮列车最突出的特点是融入了上海虹桥交通综合枢纽。上海虹桥交通综合枢纽涵盖航空港、高速、城际铁路、磁浮、城市轨道交通、公交车和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轨、路、空三位一体的、旅客人次在110万/ d的超大型、世界级交通枢纽中心[26]。它的建成和投入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成为贯彻国家战略,促进上海服务全国、服务长江流域、服务长三角,进一步促进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重要载体,成为上海西部重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之一[27]。
铁路牵引动力的现代化,是铁路运输科技进步的先导。自18世纪初叶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诞生以来的长达2个世纪的时间里,铁路牵引动力经历了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动车组的变革。而技术变革还在继续,真空管道高速磁悬浮列车方案已经浮出水面[28]。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铁路工程文明在塑造人的“理性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塑造中国“工业精神”的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工程对人们的习俗、观念、价值的冲击和改变,主要是通过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实现的。
如青海的格尔木市就是在1954年,青藏公路动工修筑,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兴修,开始繁荣起来。城市人口由1954年的几百人发展到2011年总人口30万。再比如兰州市,由于铁路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和物资运输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在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机械、纺织、电力等一批国家重点企业的建设与发展,成为甘肃省的经济中心。在铁路交通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现在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等。一位社会学家称: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29]。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大众化交通工具,具有运力大、成本低、占地少、节能环保、安全性好等多种比较优势,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30]。不仅如此,作为现代交通运输系统,铁路工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们交往空间的国际化,还有力地促进了“个体超越纯粹的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阈限,同科学、技术、理性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或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发生实质性的关联”,使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发生实质性的断裂[7]11。
中国铁路工程文明的历史分期表现出一个事实,现代社会生产力不仅是纯物质的生产过程,而且包含了人的精神、人的思维能力、人的自信、人的感觉,是人类智慧的体现[31]。从蒸汽机车到磁悬浮列车的工程特点的变迁看,尤其是动车和磁悬浮列车阶段,更是反映出“工程本身就是按照主体的需要和能力——主体尺度,去超越客体尺度的制约,创造新的存在物的主体价值取向与价值实现的过程,进而也就是自由个性与类本性的丰富与提升过程,以及人的成人和社会发展过程”[32]。
中国铁路工程文明的历史变迁,与其说是人类创造“人工自然”的科技理性主义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人本主义成果。对于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思维样态本质上依旧是以经验代替理性、以人情代替法治和契约的情况,以中国铁路工程文化的变迁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化,不仅为培养“脱域”的“现代性”的工业精神,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而且为推动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变迁,展现出巨大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金碚.中国走向工业强国的艰难前程[N].东方早报,2012-06-05.
[2]喻维勤.英国工业精神的演变和嬗变[D].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
[3]冯淼,等.美国“金融精神”取代“工业精神”的失败[J].当代经济研究,2009,(11):60-62
[4]董建锴.工业精神的内涵及其培育[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5):124-125.
[5]李宏图.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探索与争鸣,2000,(1):43-46.
[6]衣俊卿.文化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22-124.
[7]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4,(7).
[8]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
[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13.
[10]殷瑞钰,等.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5.
[11]殷瑞钰,等.工程演化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75-179.
[12]杨桂珍.蒸汽机车之父——斯蒂芬森[J].知识就是力量,1998,(6):58.
[13]贾兆鑫.清朝晚期铁路的兴起及其影响[J].世纪桥,2009,(2):73.
[14]叶士东.晚清时期的铁路管理立法思想浅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0).
[15]张波,等.世界铁路牵引发展50年[J].铁道机车车辆,2005,(12):8.
[16]贾世骏.蒸汽机车——世纪的回忆[J].实践:党的教育版,2009,(4):42.
[17]韩才元.90年代以来世界内燃机车的发展和开发国产第四代内燃机车的建议[J].内燃机车,1997,(2):1.
[18]韩才元.中国铁路内燃机车发展50年[J].内燃机车,2008,(9).
[19]傅景常,等.内燃机车的发展前景[J].内燃机,1997,(11):4.
[20]杜庆萱.铁路运行的新动力[J].大众科学,1956,(11):484.
[21]王福康.动车组大揭秘[J].自然与科技,2008,(6):8.
[22]吕彪.京津旅客列车的变迁[J].铁道知识,2009,(4):13.
[23]薛淳,方鸣.中国和谐号CRH动车组[J].中国科技投资,2008,(12):38.
[24]史筱红.磁悬浮列车的发展及现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23):28.
[25]张金平,张奕黄.磁悬浮列车的原理及现状[J].交通科技,2002,(6):81.
[26]郭炜,郭建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设计[J].上海建设科技,2009,(3):2.
[27]贾广设,李伯聪,等.工程哲学新观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66.
[28]于晓东.真空管道运输系统危险因素辩识及评价[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8.
[29]成昆铁路技术总结委员会.成昆铁路[M].北京:人民铁道出版社,1980.
[30]何华武.创新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J].中国工程科学,2007,(9):4.
[31]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36.
[32]张秀华.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87.
[责任编辑:郑红翠]
·文学与文化研究·
The Impl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s Railway Civilization
WANG De-wei
(Engineering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Centre,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s railway engineering has originated from the important‘object’culture in the west and possessed the spiri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aking the railway traction mode as the staging criteria,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s railway engineering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ing processes. They are the cultural colli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ime of steam locomotive,the bureaucracy of normative culture in the time of diesel and electric locomotives,harmonious technical rationality in the time of the electric multiple unit,and the embedded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hubs in the time of the maglev. It is the victory of humanism in the human pursuit of“freedom”rather than the victory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st in the human creation of‘artificial world’. Meanwhile,the cultural changes of China's railway engineering,together with its industrial spirit of modernity,namely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and humanism,shows the cultural power of engineering in the social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railway civilization;modernization;industry spirit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2-0068-06
收稿日期:2016-01-18
作者简介:王德伟(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哲学博士,工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科学技术哲学、工程与社会发展、文化哲学研究。
——评《中国现代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