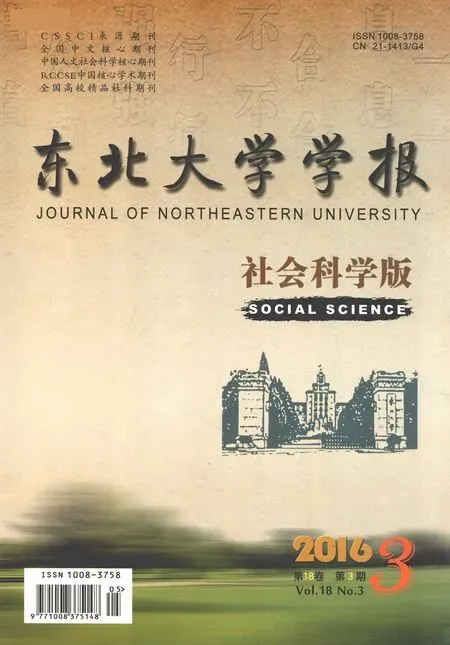马克思生态幸福思想探析
王 宽, 秦书生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马克思生态幸福思想探析
王宽, 秦书生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110819)
摘要: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异化劳动、社会制度形态及共产主义四个维度上渐次展开了对“幸福”与“生态”的阐述,并据此把生态幸福理解为人的一种体现了其本质的、生态化的生存形式,为当下中国人勾勒出了其应该追寻的生态幸福是何模样;揭示了生态幸福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为当下中国人准确地诊断其生态幸福处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提出了生态幸福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逻辑,为当下中国人获取生态幸福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 幸福论; 生态观; 生态幸福
生态幸福是当今人类追求幸福的最新维度。就当前学界来看,学者们多以西方哲学的视角来解析生态幸福的本质意涵,将生态幸福置于人类精神哲学系统中进行运思,要么把生态幸福的研究引向一条由生态哲学追问转向文化哲学反思的研究理路,要么依据传统形而上学对幸福的理解来为现代人框定其应有的生态幸福观。而从马克思的幸福论与生态观的视角来理解生态幸福的论述还尚未看到,本文将呈现出一种与当下相迥异的生态幸福思想,即马克思的生态幸福思想,为当下中国人探寻生态幸福另辟蹊径。
一、 马克思的幸福论
在马克思以前,主观主义、心理主义幸福论盛极一时。马克思则第一次把幸福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把幸福置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加以考察,提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把对幸福的理解从精神文化领域,带到人的现实生活中来。马克思关于幸福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幸福的本质在于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实现人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认为,幸福的本质是人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的过程中丰富人性、完善自我、享受属人的生活,进而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就是人的“现实幸福”。但是,宗教异化使人把自己的本质献给了上帝,使人丧失了从人本身探寻其本质的权利,人匍匐在神的脚下靠虚妄的宗教幸福来麻醉自己。马克思则指出,人的本质在于人自身,他对那种试图通过“此岸世界彼岸化”的方式来追求幸福的神性逻辑进行了彻底地批判,确立了在此岸世界追求人的“现实幸福”的劳动逻辑。马克思把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劳动使人的生存状态具有了比动物更为自由、广阔和丰富的意义,使人成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使人能够按其本性实现一种属人的存在,过着一种属人的生活。但是,劳动的异化又把体现人的本质的劳动贬低为一种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本质力量变成了对人来说异己的力量,异化劳动使人成为简单而贫乏的、被奴役被压迫的对象,阻碍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此劳动从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快乐行为变成了使人丧失其本性的痛苦煎熬。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劳动入手,揭示了人之“现实幸福”的实质,以其独特的“异化劳动”理论描述了人遭遇苦难的现实境遇,从而走上了一条从人的本质之视角阐释人之幸福的全新路径。
第二,幸福的获取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的制约。人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收获幸福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那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它既可能为人追求幸福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可能使人陷入苦难的境遇。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表明,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展现其全部的历史意义,劳动只有在特定的、合理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中才能顺利地成为人的本质,幸福也只有到活生生的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的、特定的社会制度形态中才能探寻得到,幸福与否及幸福的程度如何都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制度能否促进人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能否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现实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深层次地反映着人们的幸福状况和生存状态。马克思把人的幸福状况归结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状况,从而为找到人之不幸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埋下了伏笔,发现了人获取幸福的正确途径,即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来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由此马克思全面地开启了人之幸福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
第三,共产主义是人类获取幸福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把幸福的获取理解为一种实现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共产主义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现实表征。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节点,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着的历史过程;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更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伴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539;不是人所面临的异化的“当下”,更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化的“未来”,只是人类实现其彻底解放的历史“瞬间”。“人民的现实幸福”就在与历史同行共进、不断生成着的共产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185,它是“人民的现实幸福”真正诞生的地方。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时候,我们便会摒弃盲动地“奔向”或者消极地“坐等”共产主义的虚妄行为,而是与历史一道,通过社会历史实践来现实地“创造”共产主义。于是获取幸福的有效手段也就随之清晰地显现出来,获取幸福与实现共产主义走的是同一条路,那就是立足于当下人类发展的现实的历史羁绊,面向人类必然达到的日益迫近的未来,变革使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进而捕捉人的本质完全向人复归的那一历史瞬间。
总而言之,马克思把幸福理解为在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中消解人与其本质的异化,在全面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过程中重新占有人的本质,进而使人从受压迫、被奴役、遭蔑视的苦难世界中解脱出来,创造一种有利于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生存形式,在“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行程中追求属于“人民的现实幸福”。
二、 马克思的生态观
马克思的生态观是以一种作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之哲学根基的形态实现其当代出场的,而马克思人与自然相同一的自然观正是这一哲学根基的根本所指。当我们以此自然观来反思生态危机的时候,在哲学层面上,人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消解。由此,人类开始真正地走向生态文明。马克思的生态观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人与自然相同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相同一的自然观是其生态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具有原初的内在关联性,人与自然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乃是同一存在物,也即是说“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4]196。这就使得马克思不仅突破了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二元论”,而且比单纯高扬自然界对人具有先在性的所谓的“一元论”更加彻底,更具生态意味。首先,从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视角看,人就是自然,人通过自然界使自己成为人。马克思把主客体关系理解为一种主体通过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给客体,再通过客体来显现、确认自身本质的“对象性关系”,而这种“对象性关系”的达成是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依此逻辑,马克思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209-210。自然界就是人借以表现、确证自己的“对象”,人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其作为“自然存在物”,才能实现其作为“类存在物”,人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其“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才能实现其“类本质”。一句话,人靠自然界来使自己成为人。其次,从只有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对人来说真正的、现实的自然界之视角看,自然就是人,是人的“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4]194。马克思认为,完全脱离了人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不具有感性现实性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是被概念化的、抽象化的,对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的自然界,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19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界通过人使自己成为了一种人化了的存在,自然界通过这种人化了的形式使自身成为对人来说有意义的、社会性的存在。由此“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161。人通过自然界来成为人自己,自然界通过人来成为人本身,人成为了有机的自然界,自然界成为了无机的人体,关爱自然就是关爱人类自己,毁坏自然就是人类的自残。
第二,人与自然相同一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中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相同一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为前提条件,即“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4]187。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一旦通过社会历史实践而形成,便立即对其所处时代的人与自然之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由此,马克思成功地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主张到包含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制度中去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变革人与人的关系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那种绿色乌托邦式的生态治理模式,对试图通过人的价值观维度的自我省察来实现人类社会之生态救赎的妄想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拨。
第三,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相同一的历史过程。人与自然相同一的生态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相和谐的社会关系不断实现、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实现人与自然相同一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始终处于相互制约的动态统一之中,在人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相分离的、相异化的;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同一的、和谐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实现人与自然原初性关联,即人与自然相同一的历史过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193。
概而言之,马克思的生态观以人与自然相同一为思想核心,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归结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提出了一条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类解放同时也是自然解放的生态文明实现之路。
三、马克思的生态幸福思想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把马克思的幸福论与生态观置放于一处,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理解的“幸福”与“生态”在内容上具有内在的贯通性,据此我们有机会遵循马克思幸福论与生态观的分析视角来阐发其生态幸福思想,并以此为当下中国人探寻生态幸福指点迷津。
第一,马克思在人的本质的维度上提出了生态幸福的本质内涵,并帮助当代中国人勾勒出了其应该追求的生态幸福是何模样。马克思眼中幸福的本质是人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即人能够自由自觉的劳动,也就是人按照一种属人的方式生存,而马克思人与自然相同一的生态逻辑的确立,表明人只有通过对象化了的自然才能占有其本质,人只有作为“自然存在物”才能成为“类存在物”,人只有通过自然才能按照属人的方式生存。一句话,人只有通过“自然”才能收获“幸福”。由此,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生态幸福在本质上就是人通过人与自然相同一而实现的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它是人在确证其作为“自然存在物”因而也是“类存在物”的同时,所形成的一种体现人的本质的、生态化的生存形式。这种人的全新的生存样态,以人与自然相同一的生态逻辑作为确证属人的生命形式的内在根据和必经环节,它使人能够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找回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它完成了人道主义面向自然的伦理关怀,实现了自然主义面向人的生态复归,它为人性的丰富与完善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本就应有的生态维度。
就当下中国而言,马克思的生态幸福具体地表现为,中国人民因其能够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形成的一种人与自然同时也是人与其自身相和谐的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自由自觉的劳动可以在创造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同时,实现人与其自身相和谐的自我改造与自我完善,它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源泉,是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标志,因而它构成了中国人民生态幸福的基本内容。按照人的本性进行着自由自觉劳动的人是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其自身相和谐的人,是真正能够享受生态幸福的人。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根本生命形式生存的人,就是生活于一种生态化生活方式之中的人。这种生态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人之生命本相,它使中国人有机会重新面向自然、走进自然,在与自然界的深度融合之中重拾本我、升华自我、实现超我;它使中国人在静谧而又充满生机的自然界中感悟人生的真谛,实现人性的自由、人格的完善,以及交往的丰富;它鼓励中国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的心境中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这就是中国人应当自觉追寻的现实的生态幸福。
马克思对生态幸福本质的理解是站在人的本质之立场上观察“幸福”与“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本学”,生态幸福代表了一种以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况来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全新的价值尺度,它始终表征着人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回自然后,所能达到的对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理解程度,它为中国人民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生态维度的现实关照。
第二,马克思用其独具特色的异化劳动理论描绘了现代人的生态幸福状况,并揭示了生态幸福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为当下中国人准确地诊断其生态幸福处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参照马克思生态幸福的本质及其具体表现来看,现代人的生态幸福状况显然令人担忧。人与其自身关系的异化使人丧失本性、遭受痛苦,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自然遭受破坏,使生态系统失衡,由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日渐疏离,人无法依其本性生存,人被迫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这正是当今人类所遭遇的生态幸福危机的真实写照。
在马克思眼中,人之生态幸福状况根本上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正是人之生态幸福危机的根源,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异化劳动则是撕裂“人与自然同时也是人与其自身相和谐关系”的直接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围绕其增值逻辑的需要塑造了一整套有利于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历史性跃迁,为人类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做了必要的物质准备。然而,同时也使本应表征着人之本质的劳动沦为服务于资本逐利的、令人厌恶的谋生手段,使人与其本质彻底地疏离,劳动的不自由还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残存的最后一丝内在关联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它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4]163。异化劳动使人与自然因而也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彻底退化为单纯的物与物的关系,自然界和人都沦为满足资本增值欲望的物。至此,我们认识到:生态幸福危机的罪魁祸首乃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也为实现生态幸福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应该是既克服又保留地扬弃,充分利用资本因素中的积极成分来促进其消极成分的消解。
就当下中国而言, 一定程度的异化劳动在一定范围内仍有残留, 只不过是以膨胀了的经济理性所驱使的技术异化, 以及奢靡浮夸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催生出的消费异化的面目在当代中国显身的。 技术作为中国人提升其劳动能力的有效手段, 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立下过汗马功劳, 但吊诡的是,技术在把中国人从落后、贫穷中解放出来的同时, 又使中国人屈从于技术的统治与奴役之下, 使人成为了单面化的技术的附庸; 技术在实现中国人对自然界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全方位开发与深度认知的同时, 又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初性关联与和谐性关系。消费作为中国人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手段, 它直接地与生产劳动相连, 马克思有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在中国的消费规模与生产规模逐年扩大的同时,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并未明显提高, 中国人反而开始对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产生抵触的情绪, 转而沉沦于消沉的、奢靡的、非理性的消费快感之中。 随着中国人被“虚假的需求”所煽动起来的消费欲望的节节攀升, 消费规模与生产规模日渐超出人的合理需要及生态系统的可承受范围, 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人们疯狂扩张的消费活动中走向危险的境遇。
由此中国人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反思技术、消费与幸福、生态之间的关系, 或者更确切地说,技术异化、消费异化与生态幸福危机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 中国人的生态幸福危机是对技术理性过分崇拜所导致的人性单一化的体现, 是经济理性催生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内在张力的爆发, 是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不可避免地渗透所导致的幸福观的偏失, 是“消费主义”文化所煽动起来的无限的消费欲望与有限的生态承载能力之间矛盾的凸显。 从深层次上说, 中国人所遭遇的生态幸福危机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背景下,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诸多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进一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资本因素之负面效应的历史性显现。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 准确把握当下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各类矛盾, 在自信地利用“资本”实现发展与自觉地限制“资本”规避风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消除各种异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 使中国人民能够真正享受生态幸福。
第三,马克思提出了生态幸福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逻辑,并为当下中国人获取生态幸福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针对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生态幸福危机,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来消除异化劳动,从而解放劳动、解放人的同时解放自然界,把生态幸福的实现理解为一个由社会历史实践所决定的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和毫不停息的历史运动,在“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行程中实现人的生态幸福。
实现生态幸福的根本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首先依靠的还是“劳动”(异化劳动)。 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离不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3]538, 这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3]538, 而这一切都潜藏于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异化劳动)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 异化劳动构成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最直接、最现实的物质力量, 而运用异化劳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则是扬弃。 劳动者必须对异化劳动采取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 最大限度地利用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来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积累物质力量, 为消除异化劳动自身创造物质条件。 其次, 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还需要被提升到了“生存论的本体论”[6]高度的劳动, 即由全体劳动阶级参与的社会历史实践。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从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 从经济上废除私有制, 才能在“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中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同样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现实地“创造”共产主义,“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去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 才能最终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 最后, 我们还要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还必将存在的现实,它“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 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4]232。 实现生态幸福也是一个不断随社会历史实践而生成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是一场与“创造”共产主义相一致的不容懈怠的历史运动。
就当下中国而言,实现中国人民的生态幸福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三者是高度一致的。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认为,社会主义“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就说明,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为实际地“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创造”共产主义是同一历史过程,而这也正是实现中国人民生态幸福的根本所在。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当代中国最为准确、基本的历史定位,中国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失去实现人民之生态幸福的机会,中国也不能自我封闭在思想僵化的藩篱之中,盲目地排斥与打压资本因素,要认清中国仍将长期存在资本因素之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实践中,依照生态幸福的原则,为技术的设计与选择、消费的内容与规模增添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生态理性。同时努力在资本因素内部找寻、培养最终毁灭资本因素的力量,逐步消除资本因素之负面效应所推动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在实践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充分利用资本因素之正面效应推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搭建合理的制度平台,为实现生态幸福创造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把经济建设、生态建设、民生建设合为一体,实现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生态美好三者的协调并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即是“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行程中实现中国人民的生态幸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
[2]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01.
[3]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5.
[6] 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05.
[7]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 列宁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5.
(责任编辑: 付示威)
An Analysis of Marx’s Thought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WANG Kuan, QIN Shu-she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Karl Marx interpreted happiness and ecology 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the nature of man, alienated labor, societal system and communism. In view of the above, he regarded ecological well-being as a living form that embodied the nature of man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helps to outline what ecological well-being should be like for the present Chinese. Marx revealed the capitalist origin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crisis, which may provide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diagnose the plight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for the present Chinese. He also revealed the realization logic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which can offer feasible paths to obtain ecological well-being for the present Chinese.
Key words:Karl Marx; happiness; ecological view; ecological well-being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3.014
收稿日期:2015-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KS056)。
作者简介:王宽(1987- ),男,辽宁鞍山人,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发展研究; 秦书生(1963- ),男,辽宁宽甸人,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 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6)03-03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