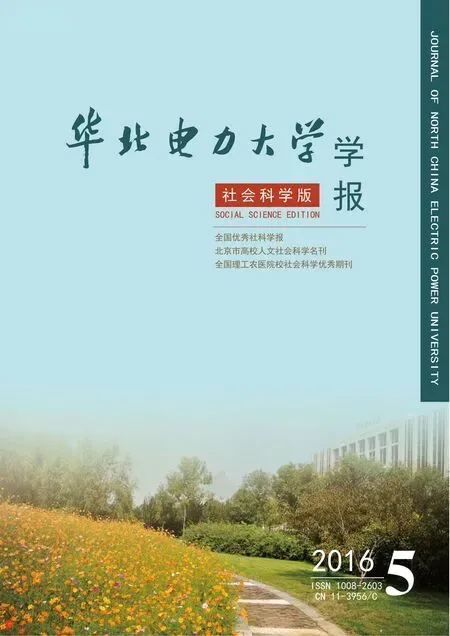索赔期的类型及其法律定性
蔡 恒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 法学前沿
索赔期的类型及其法律定性
蔡 恒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索赔期可分为法定索赔期和约定索赔期,两者法律性质不同。法定索赔期体现国家意志,因而应定性为诉讼时效;而约定索赔期则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应定性为约定免责条款。
诉讼时效;除斥期间;免责条款
索赔是一个立法上很少采用而实践中经常提到的概念,有法定和约定之分。法定索赔期我国立法规定有保险索赔期和货运合同索赔期,而约定索赔期则以建设工程索赔期最为典型。司法实践中,常有索赔期经过后能否起诉和胜诉的争论,特别是在建设工程领域,对约定的建设工程索赔期属于何种性质及是否有效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常常困扰着参与建设工程实践的各方人士。实际上,索赔期经过后能否起诉和胜诉,取决于如何认定索赔期的性质,如何认定索赔期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关系。本文从索赔期概念和现行立法入手,结合法理与实践,对索赔期性质予以厘清,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 索赔期的概念及其类型
索赔这一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但没有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所采纳,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辞海》中,索赔被解释为“交易一方因对方不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契约上规定的义务而受到损失,向对方提出赔偿的要求”;在保险领域,一般将索赔定义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遭受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以后,要求保险人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的行为”;而在建设工程领域,则一般将索赔定义为“在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不履行或未能正确履行合同,或者由于其他非自身因素而受到经济损失或权利损害,通过合同规定的程序向对方提出经济或时间补偿要求的行为”。笔者认为,虽然就索赔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仅从字面理解而将索赔局限于要求某种赔偿显然过于狭隘,应更宽泛地理解为包括赔偿在内的有关资格、财产、金钱等方面的要求。以建设工程索赔为例,应既包括业主与承包商之间基于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主张和因一方或双方违约而产生的违约赔偿请求,也应包括因工程过程中的重大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侵权赔偿请求,以及因不可抗力、法律变动、物价上涨等而导致的风险负担请求,还应包括因设计变更、工程量变更等而导致的费用增加或减少请求,甚至还应包括没有任何合同和法律依据而提出的道义补偿请求。总之,对索赔概念应做尽可能宽泛的理解,不能将其与民事责任方式之一的“赔偿损失”作同一解释。
索赔期就是法定或约定的提出索赔的时间要求。该概念也没有在我国立法中明确提出过,但在保险领域和运输领域有关于索赔期的实质规定。1995年通过的《保险法》第27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该规定确定了人寿保险索赔期为5年,其他保险索赔期为2年。1986年12月1日颁布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承运人与托运人或收货人彼此之间要求赔偿的时效,从货运记录交给托运人或收货人的次日起算不超过一百八十日。赔偿要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对方应在收到书面赔偿要求的次日起六十日内处理。”1986年12月1日颁布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该规定已于2011年废止)第20条和1986年12月1日颁布的《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2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上述水路、公路、铁路三个运输合同实施细则都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相互索赔期限规定为180天。本文将上述立法中规定的索赔期统称为法定索赔期。
除了法定的索赔期外,实践中也有一些约定的索赔期,其中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索赔期最为普遍和典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2013年版)第19.1条规定:“承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人未在前述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权利”;第19.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发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发包人未在前述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赔付金额和(或)延长缺陷责任期的权利”;第19.5 条规定:“承包人按第14.2款(竣工结算审核)约定接收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视为已无权再提出在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承包人按第14.4款(最终结清)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中,只限于提出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发生的索赔。提出索赔的期限自接受最终结清证书时终止。”上述规定不但约定了索赔期,而且明确了索赔期内没有提出索赔的法律后果。
索赔期依不同的标准可有不同的分类,如依索赔的性质可将索赔期分为违约索赔期、侵权索赔期和其他索赔期。之所以只将索赔期分为法定索赔期和约定索赔期,是因为只有这种分类才对索赔期的法律定性有意义,具体理由将在后面阐述。
二、 法定索赔期的法律定性
《保险法》实施后,学理界就保险索赔期的法律性质究竟为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存在分歧。主张保险索赔期为除斥期间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除斥期间是向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而诉讼时效则是向法院寻求救济的时间,而《保险法》第27条指的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要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的时间,而不是向法院提出请求的时间,保险索赔期此点与除斥期间同而与诉讼时效异。其二,诉讼时效期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作为起算时间,但《保险法》规定的二年和五年时间的起算点都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知道保险事故的时间不等于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只有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要求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被拒绝时,才能确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利被侵害了,因而从起算点来看保险索赔期也是与除斥期间同而与诉讼时效异。[1]主张保险索赔期为诉讼时效也有两点理由,其一,除斥期间针对的是形成权,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请求权,毫无疑问保险索赔权是请求权。其二,除斥期间可以通过约定改变,而诉讼时效为强制性条款,不能延长也不能缩短,因而将保险索赔期定性为诉讼时效可以防止保险人通过约定缩短法定的二年和五年时间,从而损害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此外诉讼时效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的特点也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因而从实践看,将保险索赔期定性为诉讼时效更有利于实现对弱者即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保护。[2]
从《保险法》生效以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将保险索赔期定性为诉讼时效似乎顺理成章,几乎没有争议。2000年12月1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保险法》索赔时限有关问题的批复》(保监复[2000]304号)中,对《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二年”和“五年”都理解为诉讼时效期间。2003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8条第1款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七条中规定的“二年”“五年”为诉讼时效期间。”上述两个规定尽管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反映了主管部门和最高司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态度。2009年修改后的《保险法》明确地将第26条修改为“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至此,从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到立法机关,已经一致明确地将保险索赔期定性为诉讼时效。
上述公路、水路、铁路三个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中规定的180天索赔期的法律性质究竟为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尽管在学理上也有类似保险索赔期限的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将其定性为诉讼时效的态度也非常明确。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水路货物运输索赔期限问题的请示批复》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41条及我院法(办)发[1988]6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通意见》)第176条,水路货物运输中的索赔期,应按国务院颁布的《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即托运人或收货人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应在收到货运记录的次日起180日内提出。”《民法通则》第141条及《民通意见》第176条都是关于特殊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的形式将运输合同中的180天索赔期纳入了民事特殊诉讼时效的范畴。此后,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被废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和《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则被修改。然而,让人疑惑的是,修改后的水路和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并没有如2009年《保险法》修改时将保险索赔期明确定性为诉讼时效那样将180天索赔期明确定性为诉讼时效,而是依然保持原有的表述,没有作出任何修改,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修改时的疏漏。
要确定法定索赔期究竟为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首先要弄清楚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究竟何在。教科书在谈到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时,一般都会将起算点的不同作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主要区别之一,认为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为“权利发生时”,而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但事实上,此种观点与我国及各国立法实践严重不符。撤销权为典型形成权,撤销期为典型的除斥期间,《日本民法典》第126条规定:“撤销权,自可追认时起五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我国《台湾民法典》第93条规定:“前条之撤销,应于发现欺诈或胁迫终止后,一年内为之。”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可见,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也可以是主观的。对于诉讼时效而言,尽管《民法通则》采主观主义,即以“知道或应当知道”作为起算时间,但纵观各国立法,诉讼时效采客观主义,即以“权利发生时”作为起算点的立法例所在多有。如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第198条规定:“普通时效自请求权产生之时开始计算,以不作为为目的的请求权,自发生违法行为时开始计算。”《日本民法典》第166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得行使时起进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作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因此,不能以起算点的不同作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区分的标准。
此外,教科书一般认为诉讼时效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因而是可变期间,而除斥期间不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因而是不变期间,此点也是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主要区别之一。[3]但从立法上看,也有规定除斥期间也可以中止的立法例,如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124条第2款规定:“(因欺诈、胁迫产生的撤销权),对于期限的届至,准用第206条、210条和211(第206条、210条和211条都是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条关于时效的规定。”从法理上看,除斥期间不可能象诉讼时效那样因主观原因而中断,因为作为除斥期间适用对象的形成权,一经权利人主张权利即可实现,除斥期间已经没有中断的必要和可能。但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一样也存在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不能行使的情形,在诉讼时效期间可以中止的情形下也没有理由不允许除斥期间中止,因为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制度目的都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因而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不能行使权利的时间不应算在期间之内,在这一点上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应同等对待。因此,除斥期间虽然不可能中断,但不允许中止则没有充分的理由,因而期间是否可变也不是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分标准。
实际上,真正能够将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区分开来的,只能是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因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制度目的虽然都是要确认和维持某种秩序,但除斥期间是通过使形成权消灭来维持原来的旧的秩序,而诉讼时效则是通过使请求权消灭来维持现在的新的秩序。只有将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这两种制度分别适用于形成权和请求权,才能使这两种制度各得其所,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才不至于因相互冲突而徒增叠床架屋的烦恼。以此为判断标准,在索赔权利确定无疑为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定索赔期的法律定性只能是诉讼时效。
三、 约定索赔期的法律定性
探讨约定索赔期的法律定性之前,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为什么要区分法定索赔期与约定索赔期来探讨其法律定性,而不是一并讨论?也就是说,如果二者的性质相同,则区分就没有意义;如果二者的性质不同,则作出不同法律定性的正当理由又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探求民法上“法定”与“约定”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以及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在民法上,“约定”完全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规定,就应依约定的内容确定其法律效力。“法定”的内容则有两种,一种是法定强制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改变,否则无效;另一种是法定任意性规范,只有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才适用法定任意性规范,即“约定优先于法定”。依此来看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我们发现,除斥期间有法定也有约定,但诉讼时效只有法定。但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当中的“法定”究竟是属于法定强制性规范还是法定任意性规范。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除斥期间中的法定两种情况都有,如撤销权行使规定的“一年”属于强制性规范中的法定,不允许约定改变;而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规定的“三个月”则属于任意性规范中的法定,只有在当事人对解除权没有约定解除期的情况下才适用三个月的规定。诉讼时效中的“法定”究竟属于法定强制性规范还是法定任意性规范,在86年的《民法通则》中尚未明确,只在第137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但没有规定当事人可否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既不能约定缩短,也不能约定延长,确定诉讼时效为双边强制性规范的性质。可见,无论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都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比较而言,诉讼时效的国家意志色彩更浓一些。那法定索赔期中的“法定”究竟是法定强制性规范还是法定任意性规范?从现行立法来看,无论是保险索赔期,还是货运索赔期,都应属于法定强制性规范。
需要说明的是,说诉讼时效属于法定强制性规范只是依解释论得出的结论,从立法论的角度,诉讼时效也完全可以是法定任意性规范。从立法例来看,诉讼时效期间在有些国家或公约中可以通过约定缩短或延长,如原《德国民法典》第225条规定:“消灭时效不得以法律行为排除或加重。”《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7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协议中约定缩短诉讼时效期间至一年,但不得加长。”上述两个规定都允许诉讼时效缩短但不允许延长;《日本民法典》虽无明文规定,但判例、许多学说均赞成此观点。而现行《德国民法典》第202条既允许当事人协议缩短诉讼时效期间,又允许当事人协议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但延长的幅度限制在30年之内。有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四个公约中,除了《海牙规则》外,其他三个公约(《维斯比规则》第3条第6款第4项、《汉堡规则》第20条第4款、《鹿特丹规则》第63条)都明确规定了可以协议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从法理上看,台湾有学者认为:“加重时效要件,足使权利之证明愈加困难,固不应许可,然如减轻时效要件,则不但于公益无碍,且足以发扬时效制度之精神,实无不应许可之理。”[4]我们认为,将诉讼时效期间定性为法定强制性规范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根据民法原理,在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在当事人约定缩短或延长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并没有损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共利益。相反,约定缩短诉讼时效完全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制度设立目的;而约定延长诉讼时效则给了当事人更长的协商解决争议的时间,不至于因为担心过了诉讼时效而被迫匆忙起诉,有利于纠纷以非诉讼的方式得以解决。
由于本文探讨索赔期的法律定性是建立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还是要依解释论将诉讼时效认定为法定双边强制性规范。这样,考虑到法定索赔期(无论是保险索赔期还是货运索赔期)在我国都属于不可以通过约定改变的强制性规范,加上索赔权的请求权性质,将法定索赔期定性为诉讼时效显得顺理成章。但约定索赔期不同,完全是合同当事人的自由约定,连法定任意性规范都算不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其法律定性与属于典型强制性规范的诉讼时效联系起来。因此,就属于约定索赔期的建设工程索赔期的法律定性而言,尽管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不少人将其理解为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甚至为建设工程索赔期究竟是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争得不可开交,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仅凭建设工程索赔期是约定而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是法定这一点,就可以切断建设工程索赔期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包括建设工程索赔期在内的约定索赔期的法律性质,既不可能是诉讼时效,也不可能是除斥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没有就建设工程索赔期是否为诉讼时效作出专门规定,但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不许约定诉讼时效延长或缩短的规定来看,应该理解为否定了建设工程索赔期的诉讼时效性质。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也是肯定过了建设工程索赔期依然可以向法院起诉和胜诉,也应理解为对建设工程索赔期为诉讼时效性质观点的否定。
但否定作为约定索赔期典型的建设工程索赔期的诉讼时效性质是否意味着约定的工程索赔期无效呢?认定建设工程索赔期约定无效的观点很难解释我国建设工程领域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与国际惯例严重不符。我国无论是1997年的《施工合同范本》,还是2013年的《施工合同范本》,都明确约定了建设工程索赔期,且明确了未在建设工程索赔期内提出索赔的法律后果。虽然组织制定和颁布合同范本的国家工商总局不是立法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但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工作部门推出的合同范本中的重要条款居然是无效条款!这无论如何让人很难以接受,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很大的伤害。放眼全球,在国际建设工程领域极具权威的国际咨询师联合会(FIDIC)制定的《施工合同条件》中也明确地约定了建设工程索赔期及其法律后果,且在国际建设工程索赔争议的仲裁与诉讼中一般都会承认建设工程索赔期约定的法律效力。因此,作为约定索赔期的建设工程索赔期的法律效力还是应该承认的。但要肯定约定索赔期的法律效力必须解释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约定索赔期如果有效,究竟是作为什么样的约定而有效,也就是约定索赔期的法律定性问题;二是约定索赔期如果有效,在否定其为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的情况下,如何解释和解决约定索赔期届满后诉讼时效届满前这一段时间的效力冲突,即约定索赔期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将约定索赔期定性为约定免责条款,可以圆满地解释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既肯定约定索赔期的法律效力,又不与诉讼时效制度相冲突。
免责条款实质上就是为是否免除责任设定一个条件,符合条件则免除责任,不符合条件则要承担责任。免责条款有两种,一种是法定免责条款,一种是约定免责条款。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7条,只有不可抗力一个法定免责条款,且要求很严格,只有在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不可抗力不是发生在迟延履行期间才能免责。至于能否约定免责条款,我国《合同法》第53条没有从正面作出回答,而是从反面作出规定:两种情况下约定的免责条款无效,一是造成人身伤害的,二是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依反对解释,只要不是这两种情况,约定的免责条款都是有效的。当然,如果是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0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约定索赔期实质上就是一个附条件免除责任的约定免责条款,一旦合同一方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主张权利,合同相对方就不再承担责任。也许有人会说约定索赔期是一个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因为索赔期是确定会到来的。虽然索赔期是确定会到来的,但在索赔期内是否提出索赔是不确定的;约定索赔期约定的不是过了索赔期就不承担责任,而是约定在索赔期内没有提出索赔才不承担责任,因此约定索赔期是附条件而不是附期限。从我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只要约定索赔期内不提出索赔所免除的责任不属于人身伤害的责任或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责任,该约定免责条款就是有效的。当然如果是格式条款,还要满足《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且不说《合同法》第40条自《合同法》颁布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和质疑*学界普遍认为该规定几乎排除了约定免责条款的可能性,与《合同法》第52条相矛盾,且不符合意思自治的民法精神。,就算该条规定有效,也不能排除约定索赔期的法律效力,因为规定约定索赔期的《施工合同范本》不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由合同一方提供,而《施工合同范本》由国家行政机关提供;格式条款不能修改,而合同范本可以修改。。
将约定索赔期定性为约定免责条款,可以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与诉讼时效的冲突问题。在约定索赔期为免责条款的情况下,即使过了约定索赔期没有提出索赔,依然可以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法院起诉,只是因为约定了索赔期作为免责条款,在所免除的责任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所列两种情形的情况下,没有在约定索赔期内提出索赔的一方因免责条款的存在而不能胜诉。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求得了一种妥当的平衡。
[1] 栾桂玲.保险索赔时限的法律定性——对《保险法》第27条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实证分析[J].山东审判,2008(2).
[2] 李沛烨.浅析保险索赔时效的不完善”[J].企业家天地,2005(3).
[3] 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30.
[4] 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40.
(责任编辑:李潇雨)
Conformity of the Claim for Compensation Qualitative Type in Law
CAI 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The claim for compens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legal conformity and the conformity agreement, and they are different in legal nature. Legal conformity of the claim for compensation embodied the national will,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conventions conformity is the autonomy, the parties shall be agreed as exceptions.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during the scheduled; disclaimer items
2016-08-20
蔡恒,男,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D920.4
A
1008-2603(2016)05-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