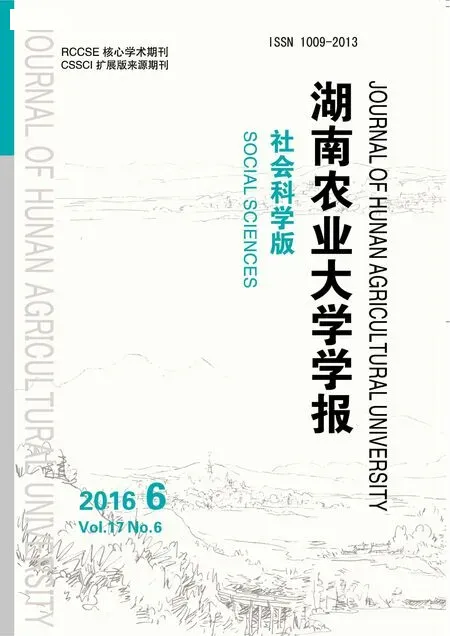华北农村“随姓”结合现象及其村落社会结构考察
——基于石家庄白石村的个案研究
蒋志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华北农村“随姓”结合现象及其村落社会结构考察
——基于石家庄白石村的个案研究
蒋志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通过对华北农村以红白喜事互助为主要目的的“随姓”结合现象的考察表明:“随姓”结合关系具有多缘选择性、功能指向性、对等互惠性及代际传递性等特征;多姓聚居的历史沿革、传统文化中的族群集团意识以及村落认同的内生性力量,是“随姓”结合关系生成的主要诱因。“随姓”结合现象呈现出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阶序性”、“文化互嵌性”及“混合性”等特征,并折射出村落社会变迁过程中村民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日益疏离性。
华北农村;“随姓”结合关系;生成原因;社会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社会结合,是指人与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1]。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结合方式,主要体现在农民们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常常以血缘、地缘、姻缘等传统关系为纽带而结成协同、合作、互助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需求、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并以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2]。村落中的社会结合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仪式型社会结合,如与祭祀、庙会等相关的结合关系;另一种是互助型社会结合,如日常生活中的帮工、换工,婚丧嫁娶、建房中的帮忙等结合关系。有关村落社会结合的研究一直是乡村人类学研究的重点,然而已有研究多关注于外显的、热闹场面的仪式型社会结合,对于扎根于乡土而形式简单的互助型社会结合却关注不够。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反思如何对文化进行分析时曾经指出,“细小的行为之处存在着一片文化的土壤”[3],因此乡村人类学对于村落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仅仅借助于表露在外的仪式型社会结合,对于乡民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型社会结合也应当引起重视。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语境中,互助型社会结合往往建立在亲密关系的血缘、地缘、姻缘等基础之上,并以具体的互助方式表现出来,它是乡民获得村落内源性社会资源以及情感慰藉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广泛地存在于民间社会当中。对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互助结合关系,学术界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费孝通等以禄村为例,研究了当地具有经济互助功能的社会结合形式“賩”,并对其组成方式和结合关系进行了探讨[4]。王铭铭对福建溪村的民间互助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具有互助性质的结合关系是“道德经济”与“理性主义”的糅合产品,同时社会经济与文化传统的转变会影响村民结合过程中的交换逻辑与功能取向[5]。张思则以沙井村为例,结合史料分析以及田野调查,对华北地区以“搭套”为代表的农耕结合习俗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发现建立在村民之间互助基础之上的结合关系对于维持乡村社会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认为通过对村民互助的社会结合研究,有助于“纵向或者横向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格”[2]。卢成仁等探讨了云南娃底村傈僳人“伴”的互助结合关系,发现社会结合既可以建立在血缘、亲缘为代表的差序格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地缘等非差序方式之上……傈僳人“伴”的地方概念提供了娃底傈僳人非血缘个体间社会结合的行动框架[6]。
已有研究多从社会结合的性质和功能角度出发,对村民之间日常生活中的互助结合关系进行分析,但对互助型社会结合形成的原因,及其与村落社会结构的关系缺乏较为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互助型社会结合的出现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有对其结合关系的生成因素有所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结合关系背后的村落社会结构。笔者拟以石家庄市白石村①为典型个案,通过考察当地普遍存在的“随姓”结合关系的特征,剖析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诱因,以探析当地的村落社会结构。
二、“随姓”结合关系及其特征
白石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角,始建于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至今已有1 400余年的历史。该村原属于河北省正定县,后并入石家庄市。从村落类型来看,白石村属于介于现代都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边际性村庄”②。该村一直保留着聚族而居的村落格局,婚丧嫁娶和生活习惯仍保持着以往的传统方式。全村共4个村民小组,2 300余户,8 600余人。除去征用的土地外还有100余公顷耕地,多数村民以在市区打工为主要生计。全村共 19个姓氏,其中张、白、王、杨、卜为村里大姓,这五姓约占全村总人口的90%以上,此外还有诸如焦、何、冯、成、吴等独门小姓。
2016年6~9月,笔者在白石村进行驻村田野调查,发现“随姓”结合较为普遍,并在当地的红白喜事等人生过渡仪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地由来已久的“随姓”结合,是指村里的小姓由于家族成员较少,无法独立操办红白喜事,因此通过“依附”于其他大姓家族来共同操办红白喜事。“随姓”结合关系的确立无需任何仪式,只需口头协定即可。一般而言在确立“随姓”关系之前双方家族就已保持良好关系。“随姓”之后小姓家族也并非真的改姓,而是与对方在仪式过程中确立为暂时的本家关系,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来确保红白喜事可以体面、顺利地进行。在当地村民看来,家族成员在红白喜事的操办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成员数量越多“过事儿”③也就会显得越有面子。然而,由于村落中的小姓家族人员数量太少,“随姓”于大姓家族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按照当地习俗,某个家庭的红白喜事如果没有“当家的”④参与,不仅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情,而且按照习惯相关仪式也无法进行下去。因此不仅是小姓,某些属于大姓的家庭如果触怒了本家族人也不得不“随姓”。如该村大姓之一的Z姓家族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儿媳不孝顺老人,招致该家族所有人的反感并与这对夫妇断绝关系。老人去世后Z姓家族所有人拒绝作为“当家的”出席老人的葬礼并不愿提供任何协助,族人的“集体退场”迫使老人的儿子“随姓”于本村王家来保证丧事顺利进行,以尽量挽回颜面[7]。
“随姓”结合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亲戚或者乡亲的帮助,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1)多缘选择性。作为一种多缘性社会结合,需要“随姓”的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与对方的感情来选择合适的“随姓”对象,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等都可能成为实现双方结合的纽带,其中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结合最为常见。有的“随姓”的双方家族本身就是亲戚关系,如该村的独门小姓成姓最早居住在离白石村不远的留村,后因贫困成姓家族中的一支投靠到了白石村的王姓舅舅家。由于成姓家族一直人丁不旺,所以在村里是独门小姓,再加上早与原村落家族脱离了关系,所以红白喜事一直“随姓”于王姓家族。基于地缘关系的“随姓”一般都是两个家族关系较好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如该村的小姓李家与同村的大姓张家关系甚好,因此李家的红白喜事也就都“随姓”于张家。
(2)功能指向性。“随姓”作为一种功能性的社会结合,缔结之初就具有非常明确的功能指向,主要在红白喜事中提供作为“当家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在主持仪式方面,大姓家族的族长或者管事的就要积极操办,并给大家分配任务,以保证“过事儿”能有序进行。在红白喜事具体的准备、操办过程中,具有“随姓”结合关系的人也不同于其他帮忙的亲戚、乡亲,而是像“当家的”一样帮助对方置办仪式所需要的用品、负责接待等。
案例1(201607152):ZFH,53岁,一直“随姓”于Z姓家族,他提到,“在农村红白喜事里没有‘当家的’可不行,像主持、置办东西都需要‘当家的’帮忙,不可能啥事儿都让亲戚和乡亲操劳,毕竟人家是客……,但是像俺家人就不旺,如果不‘随姓’(的话)红白喜事儿啥的根本没法办,(所以)必须‘随姓’了,人家才像‘当家的’一样帮衬你,这样过事儿才能有保障啊。”
可以看出,即使在都市文化元素日益增加的白石村,家族在村落社会中依然发挥着具体而重要的功能,并诱发互助性质的“随姓”结合关系,进而“随姓”的双方家族形成了一种类似家族内部的情感和义务关系。
(3)对等互惠性。“随姓”结合的对等互惠性一方面表现在小姓家族“随姓”于大姓家族并得到其帮助和支援,同时,在大姓家族遇到婚丧嫁娶的时候,小姓家族也应当如同“当家的”一样过来帮忙。可见,“随姓”并不是一种小姓单方面求助于大姓的行为。对于“随姓”结合关系的双方而言,他们的地位是对等的,因此双方也都应当承担起充当对方“当家的”的义务。虽然对于家族人口多的大姓而言,即使不需外姓人帮助也能“过事儿”,但如果拒绝“随姓”的小姓过来帮忙,就会伤及对方的感情。因此,在“随姓”结合关系中,小姓和大姓在红白喜事中互为“当家的”成为其重要特征。
案例2(201607153):WGH,43岁,随姓于该村大姓B家族。WGH表示,“虽然我们‘随姓’于人家,但不是说我们光接受人家帮助,人家过红事白事的时候我们也得像‘当家的’一样去帮忙……,只有关系好的才跟人家‘随姓’,遇到过事儿肯定要相互帮衬啊,要不以后咋在村里抬头。”
由此可见,“随姓”结合关系的双方不仅有较为深厚的感情基础,同时也会通过互为“当家的”的方式来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感情。从本质上讲,“随姓”结合中的对等互惠性也显示出在都市文化元素日益增加的白石村,在某些日常生活方面依然保持着村民共同体的属性。
(4)代际传递性。“随姓”结合关系的代际传递性主要表现在它并不是某一代人的时段性的结合,而是可以在“随姓”的双方家族中传承下去。一般而言,“随姓”双方家族的结合关系较为稳固,没有特殊情况不会轻易解除双方的“随姓”结合关系。“随姓”这一结合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只要缔结了“随姓”结合关系,那么双方家族就会有别于一般的亲戚或乡亲关系,而是如同基于血缘的本家关系,彼此之间始终保持较为亲密的关系。在调查中发现,“随姓”双方家族都共同遵循一套清晰的辈分关系,在过年或其他节庆的时候双方家族的晚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也会去拜访对方家族的长辈。在这种代际互动的长期运行中,“随姓”结合关系也会较为稳定地传承下去。
案例3(201607154):CXX,63岁,“随姓”于W姓家族,他说,“俺爷爷那辈儿就‘随姓’W家了,从那时候起两家关系就一直很好,过事儿的时候就像‘当家的’一样相互帮衬,从没断过……,村里有句话叫‘乡亲辈,瞎胡论’,但是你要是和人家‘随姓’了那就跟‘当家的’一样,啥辈儿就是啥辈儿,可不能瞎叫……,虽然现在忙,但是过节啥的有时间还是要走动,尤其是小辈儿要过去看看人家(大辈),毕竟过事儿的时候人家照应多,不能让人家挑理儿是吧。”
“随姓”结合关系并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结合,而是两个家族团体的结合,所牵涉的关系比较复杂,因此也不会轻易解除。同时在明确辈分关系语境下的代际互动也能对双方家族的年轻成员起到教化的作用,并有利于“随姓”结合关系的传承。
三、“随姓”结合关系的生成原因
“随姓”结合关系在白石村以及周边地区长期、普遍的存在,有其特有的历史原因和村落社会基础。一方面,自明朝洪武之后,华北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多姓共居为主的乡村聚落形态。在一个村落中,除了大姓以外还有更多的小姓,小姓家族由于人口较少,为获取必要的村落内源性社会资源,就必须与其他占有优势的大姓缔结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村民在经济上实现了家户的独立,但是在红白喜事等方面依然具有较强的集团意识。因此,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白石村村民在利益、情感和习惯的影响下,必然依赖村落内部的社会文化网络,以保障自己在村里的利益和声誉。“随姓”结合关系之所以成为当地村民较为普遍的建构性结合关系之一,有其具体的生成因素。
(1)多姓聚居的历史过程。刁统菊通过对山东南部村落的调查认为,多姓聚居是华北村落的典型结构形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姓氏的人会通过多种方式迁到一个村落,同时在实际利益的驱动下,异姓村民之间形成各种互助关系,并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增进感情,使得地缘关系有时比血缘关系更具有凝聚力[8]。白石村与刁统菊所调查的村落一样,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姓共居、地缘关系较为密切的村落。从历史上来看,白石村最早的居民基本都是在明代洪武和永乐年间迁来,随着世代的繁衍逐渐形成了张、白、王等村里的大姓。而村中的小姓则多为清末和民国时期或解放后迁移过来的。在迁移途径方面,有的是通过白石村的亲属网络迁进来的,有的则是通过白石村的朋友介绍迁进来的。可见在小姓迁居白石村之初,就已经与该村大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小姓迁入以后,为在村落中立足,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求同大姓家族的合作并维持与其良好的关系,因而依靠最初引荐自己入村的大姓家族,成为其获取社会资源的便利手段,在这一情境下“随姓”结合关系也就随之出现。另外,在移民的过程中不同姓氏的迁入也意味着给所迁入村落带来了更多的异质性网络资源,在血缘、地缘、亲缘等关系所编制的社会网络中,很容易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结合。因此,“换工、代耕、帮工、搭套等农耕结合以及安全防卫、娱乐庆祝、修屋建房、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生活结合,共同构成了近代以来华北地区多姓村落的社会结合图式。”[2]其中“随姓”作为其中重要的生活方面的结合,就根植于白石村多姓共居的村落社会结构当中。
(2)传统文化中的族群集团意识。依照现代化理论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本较强同质化的村落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方面也会不断分化,在利益的驱使下经济单位逐渐分化为以家庭为主,村落共同体的封闭结构也会随之瓦解。然而,“从文化论的立场上看,尽管村落共同体的弱化趋势难以避免,但是村落共同体的作用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发挥着维系村民之间认同意识的作用,加强村落的凝聚力,对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9]
在白石村,受城市化以及村落经济结构分化的影响,很多建立在以经济互助为目的基础上的社会结合方式已经极度萎缩甚至消亡。在实际利益驱使下,村民更习惯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单干,而非以往建立在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之上的共同经营。然而,“经济共同体”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以文化为基础的结合习惯也同样走向衰败,如具有文化性质的“随姓”结合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白石村村民而言,婚丧嫁娶是人生阶段的大事,关系到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荣誉与“面子”。在红白喜事的操办中,不同关系的人在其中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旦缺失了其中一个角色,无论红事还是白事就很难运转下去,这对于举行仪式的家庭而言也是较为尴尬的。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个不孝子,在家族成员拒绝以“当家的”出席其父亲葬礼的时候,他也必须通过“随姓”这一结合方式来创造出“当家的”来充门面,虽然这样也较为尴尬,但至少要好于没有“当家的”。可见,经济社会的变迁并不会轻易改变村民头脑中的文化逻辑这一深层结构,以文化为基础的族群集团意识依然较为强烈,并体现在村民的实际生活中。
(3)村落认同的内生性力量。“对于逐渐纳入到都市范围的村庄的村民而言,某些集体记忆、共同的利益环境,决定了他们认同边界的生成。因此他们在与都市文化的互动中,并没有丧失固有的行为方式和交际范围,而是在维系初级关系的同时,又平添了许多次级的联系。”[10]白石村虽然在地理空间上完全被纳入到城市行政区划当中,但是其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化认同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浪潮而湮灭,村民在利益和习惯的影响下依然保有对村落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内”、“外”不同层次的认同结构。在生活实践中,本村村民享有在村中建宅基地、征地分红等特有权益,形成了与外界相别的村落利益群体。在婚丧嫁娶的过程中,一个家庭即使再富有,也不能凌驾于家族以及其他传统关系之上而单独举办,否则就会意味着失去自己在村落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因此,都市化的村落在利益驱使下依然会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力量。在这种背景下,“随姓”也就成为小姓家族维持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一种现实手段。
四、“随姓”结合现象背后的村落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基本单位之间的有机联系,地位、群体、角色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贺雪峰根据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异曾将村落社会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华中地区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庄,华南地区的宗族性团结型村庄和华北地区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12]。然而从实际考察中发现,白石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同于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类型,尤其不同于贺雪峰所认为的“华北村落的社会结构建立在五服以内的小型血缘群体的互助之上”。总体来看,白石村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随姓”结合关系呈现出一种阶序性、文化互嵌性和混合性的村落社会结构,并分别表现在村落中的社会地位、社会群体和社会网络等方面。具体分述如下:
(1)社会地位的阶序性关系结构。所谓阶序是指“一个整体的各个要素依照其整体的关系来排列等级所用的原则”[13]。在阶序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并按照具体的身份来确定自己地位的高低。不过阶序中的身份与权力、财富、社会阶层无关,同时它对这些要素具有支配性而不是相反[14]。在华北乡村,阶序性关系在不同家族或个人之间比较明显,如刁统菊通过对华北乡村的研究发现,在联姻的宗族之间,姻亲双方存在着明显的阶序关系,即给妻者家族的身份地位要高于娶妻者家族,因此舅舅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外甥家无论多么富有也不可怠慢舅舅一家[15]。同时乡村中的辈分原则(无论家族内部的辈分还是乡亲辈)也强化了较为缜密的阶序性关系。总体而言,阶序性关系维持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平衡性。“随姓”社会结合同样具有阶序性特征。首先,基于亲缘关系纽带的“随姓”,都是外甥家“随姓”于舅舅家,这主要是因为在阶序地位上,舅舅家要大于自己,因此在“当家的”不足以支撑婚丧嫁娶等人生过渡仪式时,舅舅家所属的家族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其次,基于地缘关系的“随姓”,也同样是必须找乡亲辈排序上高于自己的家族,尤其是家族内部有年龄大、辈分高的长者要优先考虑。如果在仪式中乱了辈分,不仅自己尴尬,也会被他人耻笑,因而无论何种“随姓”结合关系,都是以阶序关系为基础的。可见,在仪式性和公共性关系当中,阶序性社会地位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按照阶序的原则来处理文化方面的结合关系,并体现了村落阶序性的社会结构。
(2)社会群体的文化互嵌性结构。传统的华北乡村社会是一种互嵌性质的结构,具体而言,就是村落内部不同姓氏主体的家族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互信互赖的共同成员感和共同归属感,村民在婚丧庆吊、共同防御、农业生产等方面都保持着一定的协同性。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白石村推行以后,以往各种经济互助性质的结合关系开始瓦解,但物质方面的外层的变化并没有完全改变心理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里层,在婚丧嫁娶等重大人生过渡仪式方面,村民们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结合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乡村社会最为稳定的是其文化内核,如曾红萍对江汉平原S村落考察时就发现,在该村的原子化过程中,相较于经济方面互助关系的快速瓦解,红白喜事上村民互助关系的瓦解却相对缓慢[16]。一旦文化上的结合关系崩溃,也就意味着文化内核的变质,村民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原子化状态。从白石村的“随姓”结合关系依旧稳固的状态来看,村落的文化内核还未受到严重影响,虽然经济性质的社会结合趋于瓦解,但是文化性质的结合关系依然较为稳固,村落依然保持着文化互嵌性社会结构。
(3)社会网络的混合型关系结构。所谓混合型关系是指兼情感型关系和工具型关系为一体的关系类型[11]。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来看,情感型关系所构建的是内部结构互嵌的团结型村庄,工具型关系所构建的则是内部结构松散的原子化的村庄。从白石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结合在经济上的式微以及文化上的相对稳定,使其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混合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混合”型村庄社会结构。具体表现为,村民之间在经济上体现更多的是工具型关系,“亲兄弟,明算账”已经成为大多村民的共识,然而在文化上则更多地体现为情感型关系,在婚丧嫁娶等仪式过程中依然要保持群体之间的互助精神。从白石村的“随姓”结合关系来看,虽然村民之间通过这种文化上的互助结合关系在人生过渡仪式中保持着亲密感,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往来,但是在经济互助方面却保持着相当的疏离,“随姓”结合关系双方无论在红白喜事中合作多么紧密,在经济方面仍习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经营,经济互助远不及文化互助那样流行,同时村民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认为应该是“一码归一码”。
综上所述,华北冀中大部分村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阶序性”、“文化互嵌性”和“混合型”的社会结构特征。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村民之间保持着“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形态,即精神层面的文化互助的结合性及物质层面的经济互助的疏离性。核心家庭的经济独立性虽不能脱离村落的阶序性文化网络,但是村民之间的文化互嵌也无法掩盖以核心家庭为单位逐渐经济原子化的社会事实,村落社会网络所呈现出的是“工具型关系”与“情感型关系”之间的糅合。
五、“随姓”结合嬗变折射的村落社会变迁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17],因此通过对村落某一文化现象变化的探析,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村落社会的变迁。“随姓”作为一种村落社会结合现象,有着深远的历史根基和社会文化基础。因此“随姓”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村民结合关系,更是嵌入在村落社会结构之中的乡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性质的“随姓”结合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宏观上来看也折射出村落社会变迁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脱离家族“随姓”的现象逐渐增多,呈现出当前村落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从传统本质来看,“随姓”是由于村里小姓的家族成员较少而采取的权宜之策。相对而言,大姓由于家族成员多,因此内部家庭成员无需通过“随姓”这种结合方式来操办红白喜事。以往的历史也表明,大姓家族中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其他家族“随姓”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然而,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家庭掌握了经营自主权并以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事务决策,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对于家庭的控制和影响已经大为减弱,因此由于家族内部矛盾所导致的脱离家族而进行“随姓”的家庭也逐渐增多。在白石村,由于某个家庭的不孝行为所引发的族人“集体退场”而使其不得不“随姓”并非个案。同时因为利益关系所导致的家族内部各家庭之间关系破裂,而在红白喜事的时候“随姓”于其他家族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种脱离家族而“随姓”的现象,实际与传统上的“随姓”在本意上相距甚远,同时也呈现出当前村落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
(2)“随姓”结合关系的“经济脱嵌”与当前村落社会关系的疏离性。传统上的“随姓”是一种互嵌型的结合关系,“随姓”的村民不仅在红白喜事等文化方面保持着亲密性,在经济互助方面也保持着紧密的结合性。根据白石村老人回忆,以往缔结“随姓”结合关系的双方家族除了红白喜事的帮忙以外,在农耕、做工等生产活动方面也时常搭伙,同时在村民之间的借贷、救急等方面,“随姓”结合关系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村民之间在红白喜事、生产劳动、房屋建造等互助方面都是无偿的,完全建立在村民之间深厚的感情基础之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打工经济”的兴起以及村落内部的劳动力商品化,核心家庭的独立性与经营自主性大为加强。如以往建造房屋,都由村民们过来帮忙来完成,而现在都花钱请建筑队来完成。受此影响,传统“随姓”结合关系所包含的经济功能也已大为衰弱,而基本仅限于红白喜事等文化性质上的互助,经济方面的结合关系已逐步衰弱、瓦解,凸现出当前白石村社会关系的二元格局,即文化关系的情感亲密性和经济关系的工具疏离性,“随姓”结合关系的“经济脱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村落社会关系结构的弱化,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疏离性趋势。
综上所述,“随姓”结合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呈现出当今华北冀中村落相应的社会变迁。白石村内部经济性质结合关系的逐渐瓦解以及文化性质结合关系的延续,表明村落社会在逐渐经济原子化的同时,作为个体的核心家庭对于村落内生型的文化性互助方式依然存在着强烈需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在村庄内部的不断渗透以及村庄的日益开放,村民越来越容易从村庄以外获得社会资源,核心家庭的独立性也在逐渐增强。虽然在“随姓”结合关系下村民们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但是物质层面上的经济互助的式微,以及在市场经济浪潮下村庄的文化内核是否必将受到侵蚀,也是值得深思的。
注释:
① 根据学术规范,本文出现的地名和人名均做了相应的技术处理。
② 所谓边际性村庄的相关概念最早是由孙庆忠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村庄》中所提出,指在城市扩张的背景下,处于都市化影响下的村庄虽然其村落经济已高度市场化、商品化,但是村落传统文化以及聚落形态却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是一种介于城市中心和边远乡村,居于边缘地位的社区类型。
③ 在冀中村落社会,红白喜事的操办过程都称之为“过事儿”,举行白事叫做“过白事儿”,举行红事叫做“过红事儿”。
④ “当家的”也就是本家族的人,也可称之为“本家”。在冀中地区,“当家的”的叫法在生活用语中较为常用。
[1]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Geertz, 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New York:Basic Book,1973.
[4]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
[6]卢成仁,史艳兰.村落社会结合中的个体——怒江傈僳人“伴”之地方概念的人类学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38.
[7]肖唐镖.乡村治理中宗族与村民的互动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8(6):93.
[8]刁统菊,扬洲.多姓聚居与联姻关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37.
[9]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J].社会学研究,2005(6):199.
[10]孙庆忠.都市村庄南景:一个学术名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1):67.
[11]于凤春.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
[12]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9.
[13]路易·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
[14]王晴锋.路易·杜蒙的学术肖像:从“阶序人”到“平等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1.
[15]刁统菊. 不对称的平衡:联姻宗族之间的阶序性关系——以华北乡村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2010(5): 31.
[16]曾红萍.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与社区社会资本的变迁[J].中国农村观察,2016(4):28.
[17]耿瑛.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J].东方论坛,2010(4):32.
责任编辑:曾凡盛
Study of phenomenon of combing according to family name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in North China villag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aishi village in Shijiangzhuang area
JIANG Zhiyu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village society in North China, this paper found the phenomenon of combing according to family name aiming at mutual assistance in wedding and funeral was very popular. The relationship combing according to family name has its features of multisource selectivity, functional guidance, reciprocity and mutual benefit as well a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he history process of people composing of different family names immigrated to the village, group consciousness on cultur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endogenous forces from village are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is combining phenomenon. From this social combining phenomenon, we can see the features of order sequence, cultural embedded structure and mixtur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North China.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combing according to family name reflects the instability and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social change.
rural area in North China; relationship of combining with same family name; forming reasons; social structure
C912.82
A
1009-2013(2016)06-0035-07
10.13331/j.cnki.jhau(ss).2016.06.006
2016-10-20
新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干旱区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XJEDU030114Y0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MZ083)
蒋志远(1987—),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转型期财政项目制研究述评
- 先秦神话的独特风格及其教育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