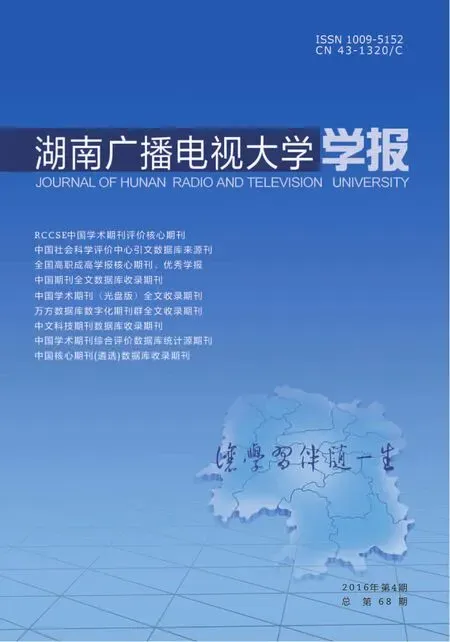《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差异管窥
——读《秋水堂论金瓶梅》有感
张 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差异管窥
——读《秋水堂论金瓶梅》有感
张 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词话本和绣像本是《金瓶梅》一书的两大版本系统,而这两大版本在对《金瓶梅》主旨的阐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风貌的展示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根据《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中采用“春秋笔法”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中西文本批评方法,对词话本和绣像本三大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认识词话本与绣像本不同的美学原则和意识形态、以及进一步理解田晓菲教授的慈悲的文化含义。
《秋水堂论金瓶梅》;词话本;绣像本;差异
《金瓶梅》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一,是小说中的杰作。“当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的时候,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1]便是秋水堂主田晓菲对《金瓶梅》一书的评价。《金瓶梅》先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袁宏道在其《与董思白书》提到:“《金瓶梅》从何处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2]这封信是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写成,这是有关《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载,可惜这些抄本都早已亡佚,今天我们都无从得见。因此,目前可知最早的《金瓶梅》传抄本为万历丙申本。约经半个世纪的传抄后才有刊本的出现,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是现存《金瓶梅》的最早刊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列于词曲之下,且详细地记载了他自己抄录《金瓶梅词话》抄本全书和别人将另外一种抄本全书在苏州付刻的情况。1932年,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被发现,此本便作为研究《金瓶梅》词话本的代表。《金瓶梅词话》刻印问世之后,在天启年间出现刻本《新刻绣像金瓶梅》,后出现附有插图200幅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刊行时间作过考证,他指出:“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3]后来研究者便以“崇祯本”作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通称。在康熙乙亥年(1695年)出现的张竹坡评点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一奇书”四字肯定了《金瓶梅》的历史地位,是批评家参与小说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的代表,使《金瓶梅》文本得到新的展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张评本形成自成体系的《金瓶梅》艺术论,已在艺术经验、小说理论方面为《红楼梦》奠定了基础。与张评本属同系类的还有康熙戊子年(1708年)满文译本《金瓶梅》和乾隆丁卯年(1747年)《四大奇书第四种》,此后的本子多根据绣像本和张评本翻刻或删节而成。国内和日本所藏的明清刊刻的《金瓶梅》约有三十多种,但《金瓶梅》小说版本可划分为明万历词话本、明崇祯绣像本、清康熙张竹坡评点本三大系,《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正是明清时期最主要的三种版本系类,也是现今研究《金瓶梅》三大系统版本的代表。但由于张评本是以崇祯年间刊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底本,因此《金瓶梅》的版本大体上可分为词话本和绣像本两个大系统。韩南教授在其文章《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也将《金瓶梅》版本大体分为甲、乙、丙三系,指出重要者为甲系的万历丁巳本和乙系的崇祯本的两个系统。
自上个世纪在山西介休县发现了万历年间的词话本,《金瓶梅》版本研究逐渐成为小说研究的热点。对于《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两种版本的差异,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而对于词话本和绣像本两个版本的先后关系问题、孰优孰劣的评论等研究自1932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学界也一直存在分歧。而不少文章都针对《金瓶梅》两个版本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关于二者的文本部分却少有涉及。王汝梅先生在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时,在其前言部分大致比较了词话本和绣像本两种版本关于文本中的散套、小令及诗词的不同;学者小野忍在其《〈金瓶梅〉解说》一文中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二个版本的六点不同。在《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和《〈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定本的转变》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刘辉先生与寺村政男分别从二者内容的删削与刊落、艺术价值入手,较为详细、系统地比较其文本不同。在仅有的著作中本着文本原则出发的,涉及这方面内容较多的便是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不仅列出了二者回目的不同且在各回评论中,细致分析和比较两大版本系统文本和思想的不同,见解新颖、独到。“介入纷繁的版本产生年代及其相互关系之争不是本书的目的,我的愿望是通过我们能够确实把握的东西——文本自身——来分析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的奇书”[1],做到必要的追寻“原本”。秋水堂主将“春秋笔法”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金瓶梅》两种版本所带来的差异中的独特艺术力量。但《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是根据《金瓶梅》的回目顺序创作的,所以秋水堂主对词话本和绣像本二者“原本”的分析也分散在每一回中,未能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本文将针对《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中关于词话本与绣像本在思想主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风貌上的差别进行归纳总结。
一、主旨差异
《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对词话本和绣像本思想主旨的比较,也是通过《金瓶梅》两大版本的卷首诗词文本的差异和首尾结构的不同分析而得,由此可得出的结论为: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希望通过劝诫的教化作用让世人正确地应对俗世;而绣像本则是意在构建一个强大的佛教精神背景,利用书中男男女女的生离死别来唤醒读者对生活与死亡的反思,进一步产生对人生空幻救赎的同情与慈悲的结论。
首先,通过卷首诗词的不同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大版本的不同倾向。词话本主要传递儒家思想,而绣像本则是继承的佛教思想。比如第一回,词话本的卷首词,其目的为阐释情色的消极作用,例如:“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未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1]。接着,入话用“虎中美女”的意象向读者暗示,美容情色只是杀人老虎的化身而已,淫荡妇人招致杀身之祸,而迷恋其色的男子也因此送命,贪淫害人又害己。“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4]其意图在于劝诫读者洁身自好、远离情色,不要蹈书中人物之覆辙。而绣像本第一回的卷首诗采用了程长文的《铜雀台》:“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1]表达了对繁华如梦、人生易逝的感叹,用这样一首表现今昔对比的开篇诗词,表明绣像本《金瓶梅》是一部由热到冷的炎凉书。在佛教的空色世界中,人生中财色的诱惑不过是人生万事的“无常”,佛经《金刚经》的引述,“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1],就更加揭示了红尘世界的虚空本质:人生有尽,死亡无情。在第一百回中,两个系统版本的卷首诗词也充分显示了不同的思想主旨。“先看词话本:‘人生切莫将英雄,术业精粗自不同。猛虎尚然遭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七擒孟获恃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珍重李安真智士,高飞逃出是非门。’再看绣像本的:‘旧日豪华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黄芦晚日空残垒,碧草寒烟锁故宫。隧道鱼灯油欲尽,妆台鸾镜匣长封。凭谁话尽兴亡事,一衲闲云两袖风。’”[1]词话本依旧采用正面忠厚的口吻,用孝子李安不屈服于春梅的财色诱惑、不愿意背叛守备离开了观众的视野,为读者塑造了儒家为人处世的楷模,洁身自好,及时脱离财色是非;而绣像本依然本着现实,打破虚象,点出“兴亡”,从人生的豪华锦绣写到碧草寒烟,正如《金瓶梅》中的各类人物由热闹出场到他们残忍死去,繁华中酒色财气最终不过是人生一纸黄粱,充满了万事皆空的悲哀。
再者,两个版本首尾结构的不同也体现了二者不同的思想倾向。绣像本多引述佛经,不仅是直接体现文本主旨,更通过小说叙事结构的建构以表明思想主旨。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在绣像本的第一回中提到的《金刚经》:“倒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生死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1]可见在第一回中作者已埋有伏笔,而第一百回月娘逃难被普静和尚拦住,带往永福寺以及后来普静和尚对冤魂的超度、点化孝哥则是通过第一回中吕洞宾的诗、谢希大口中玉皇庙和永福寺的对峙以及西门庆认为十兄弟结义不是僧家该管的事而选择了玉皇庙这样的叙事,这样的精心安排使首尾形成了和谐的照应和“人无永福”“人无永寿”的讽刺性预兆,成为一个圆圈式的结局。结局处,作者安排孝哥出家,被普静和尚点化,这一描述不是表面的让文章结局堕入佛教空门、印证“色即是空”的道理而已,而是达到了“化阵清风不见了”的境界。如此收束,实在达到了“空”的极致。用首尾结构来表明佛教中所体现人生的空无空灭,而这也正是绣像本着力体现的主旨。“绣像本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本身,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的完美实现”[1]。这一主旨与词话本儒家的劝诫不同,词话本的第一回以“虎中美女”的意象开头来强调女色害人,以不为财色所动的李安承载了儒家戒除四贪的思想。除此之外,词话本的道德劝惩意味还体现在文本的内容上,比如在第八回中:“盛言和尚乃‘色中饿鬼’,又引诗为证,道此辈‘不堪引入画堂中’云云,共二百三十二字,绣本无”[1];第十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宣扬道德的诗,绣像本则是以一首《踏莎行》若隐若现地抒写;第二十五回中惠莲打秋千时,被风吹起裙子,月娘便笑骂一句,此绣像本无;第九十四回春梅放走陈敬济时,词话本便加入了长篇的解释和道德说教,而绣像本在九十七回中才由春梅道出当日不相认的用心……因此词话本首回是从惩戒世人的目的出发,始终站在情欲的反面,认为情色害人。文本中间情节时常出现劝诫引导的词曲或评论;故事结尾时还特意地描写李安一人,实为儒家正面的形象,与西门庆形成鲜明的对比,文章中浓厚的说教意味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树立起生活的榜样,达到教导作用。因此,“绣像本比起词话本来,少了很多儒家道德说教,多了佛家思想中的‘万物皆空’,或者道家思想中的‘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1]
二、人物差异
《金瓶梅》全书一共出现了人物八百五十多个,除了在思想主旨、结构安排上的不同,词话本和绣像本最突出的差异就是对西门庆、潘金莲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相较之词话本,绣像本的人物描写更胜一筹。例如第一回中对西门庆的介绍,“词话本却作:‘从小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绣像本则作:‘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萧洒……这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学得些好拳棒’”[1]。在第七回中,西门庆与孟玉楼相亲时,“绣像本中的西门庆说:‘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门,管理家事。’把丧妻与娶玉楼连在一起说出,又云‘管理家事’,的确造成娶玉楼为正的印象,然而细细推究,西门庆又的确一句谎话也没说……词话本中的西门庆说道:‘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门为正,管理家事。’”[1]可见,词话本比绣像本多了“为正”二字,西门庆便坐实了有意骗娶孟楼之罪;而绣像本写西门庆的“骗”,妙在其话语的含含糊糊,因为其妻亡是真,欲娶玉楼入门也是真,分管家事也是真,而偏房也未尝不可管理家事。西门庆的话到底是有意含糊还是无意,绣像本并未给出答案;而词话本直接给出了道德判断,将西门庆变成一个片面的小人,少了绣像本的圆滑,不能给读者留下遐想余地。由此可见,西门庆的浪荡形象在绣像本的描写中更为复杂和全面。
而关于潘金莲的描写,书中第三回西门庆和潘金莲在王婆房中调情的故事情节安排都基本来自于《水浒传》,《金瓶梅》虽只是稍作改写,但几个字的不同却使金莲淫娃荡妇的形象大变为一个娇羞的少妇。这一回中,“西门庆拿起金莲手中的活计看了,对金莲的针线大加赞美,词话本作‘那妇人笑道:官人休笑话’。绣像本作‘那妇人低头笑道:官人休笑话’。说起那天被叉竿打到头,词话本作,‘妇人笑道:那日奴误冲撞,官人休怪’。绣像本作‘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绣像本评点者在这里眉批‘妖情欲绝’。”[1]所以在本回中,词话本与绣像本的差异正在于绣像本多了几处潘金莲见西门庆时的妩媚低头,称得上是史家的“春秋笔法”。而此时秋水堂主由金莲的七次低头联想到了张爱玲笔下《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因白善于在男人面前低头而更显其可爱。在十二回中,“在词话本里,金莲叫了一声:‘我的傻冤家!’说:‘你想起甚么来,中了人的拖刀之计,把你心爱的人儿这等下无情折挫!’绣像本在这里作:‘我的俊冤家!’”[1]“俊”与“傻”两个字形状十分相似,但表达之意却相去千里。金莲抱怨西门庆相信他人的挑拨,大可不必用极为普通的“傻”字来泄怨,反而“傻”字容易引起西门庆的不乐,没有化解矛盾的作用;而“俊冤家”虽同是抱怨但却有女人对情人的无线娇媚婉转,表达了金莲对西门庆的情不自禁的相思。绣像本正是通过这样的细微之处来还原金莲一个青年女子该有的妩媚羞涩。因此,在人物塑造上,绣像本比词话本更为仔细地处理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三、风格差异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明之人情小说:“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为有名”[5]。但简单地将《金瓶梅》归为世情小说,还不足以概括这部小说独特的书写个性。因为《金瓶梅》处处写世情却又步步拆穿世情,显示出世情的可笑与虚伪,而讽刺艺术便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绣像本通过文字的增删和回目侧重点的不同增加讽刺的表达,反讽艺术比词话本更纯熟。例如在三十三回中,对韩道国的一段白描,颇有《儒林外史》的手法。“道是‘五短身材,三十年纪,言谈滚滚,满面春风’。词话本此作‘五短身材,三十年纪,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1]词话本比绣像本多了“相貌堂堂”四个字,便不如绣本讽刺为甚。在第七十四回中,词话本的回目作“宋御史索求八仙鼎”,绣像本为“潘金莲香腮偎玉”。“然而金莲偎玉之时,正是索取瓶儿皮袄之时也。绣像本作者对宋御史讽刺得极毒,妙在含蓄出之。”[1]除此之外,在九十七回绣像本的回目相较词话本也更具有讽刺艺术,绣像本以真武家兄弟和假十结义兄弟开头,到结尾又重归“真假”二字,形成结构上的照应;再者,春梅与敬济这对假姐弟借以姐弟之名来行夫妇之实,暗刺春梅与敬济确为假夫妇,绣像本作者的玲珑文心便是通过这样的细节体现出来的。《金瓶梅》两个版本都存在不少韵文穿插,但相比而言,绣像本的穿插部分已大大减少,“里面诗、词、曲、赞、赋等可唱的韵文达599种。说散本虽然将韵文删掉了不少,但仍保留有约三分之一”[1]。《金瓶梅》书中穿插的词曲,往往意味深长,人物的唱曲更是作为泄露心迹或有意借曲抒情,例如在第三十八回中,词话本里,“金莲弹弄琵琶所唱的曲子比绣像本为长,也更为深情。比如唱词中穿插‘好教我题起来,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这样的话。”[6]在第九十九回中,爱姐思念敬济,题诗抒情,词话本录有“春、夏、秋、冬”四首,而绣像本只录第一首,虽然词话本比绣像本具体而丰富,但是这里爱姐题诗抒发相思,还比较合乎人物的情境与心理,题春夏秋冬四首,反而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在文章体式上,词话本较多的继承了说话艺术的传统,词话本中叙述者的插入,尤其是以“看官听说”为开头的叙事。因此在叙事形式上,明显地受到了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影响。绣像本对韵文穿插的删改,使全书的主线更清晰,结构更紧凑,绣像本是文人处于对章回小说的摹拟阶段,逐步书面化和文人化,属于早期章回小说中的词话体。
最后,还可以从语言风格分析词话本与绣像本的风格差异,绣像本的语言有着鲜明的精致雅化倾向,而词话本较为粗朴浅俗。比如词话本有很多插科打诨的夸张描写,绣像本却无。在第九十二回中,在描写拐带陈敬济货物的伙计杨大郎一段时,“词话本道:‘他祖贯系没州脱空县拐带村无底乡人氏,他父亲叫杨不来,母亲自氏。他兄弟叫杨二风,他师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龙庵精光道人,那里学的谎。’”[1]词话本以人名寓言,利用谐音做戏,达到插科打诨的效果。而在九十三回中,描写陈敬济以老实人身份以骗取任道士信任时,用了一个在民间流行的传统笑话,绣像本则无,因此绣像本显得比词话本更加写实。再者,就语言的讽刺效果而言,《金瓶梅》一书“妙就妙在哀而能笑,笑而愈哀,是一部带着笑声来暴露现实的悲剧。”[1]看似可笑的字词言语却蕴含着作者反讽的深意,在一片凄苦的笑声中也能体会得到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揭露批判。又如在九十四回中,“词话本写春雨本来要请敬济相见,‘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口中不言,内心暗道:‘剜去眼前疮,安上心头肉。眼前疮不去,心头肉如何安得上?’于是分付张胜:‘你旦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这段话绣像本作‘忽然沉吟想了一想,便又分付张胜’云云。”[7]可见绣像本的语言比词话本含蓄许多,更使得读者意识到词话本的直露。
所以,秋水堂主总结两种版本之别时说到:“一来见得绣像本细致,注意上下文逻辑,更有写实作风;二来也可以使得绣像本比词话本简洁是因为商业原因的说法不攻自破:我们知道绣像本并不是处处都比词话本简洁,而且,也不是只为了简洁而简洁耳。”[1]绣像本《金瓶梅》不是简单的删改本,绣像本较之词话本而言,是思想主旨上由单纯的儒家说教到佛家意识形态的深化;情节描写由拖沓说教到把握全局、结构紧凑的独立意识;文章体式上由说唱话本向文人章回小说上的突破;艺术风貌上采用的是带有文人自觉地周密思考的提升。这些也是本文对比两者版本的意义所在。当然,通过对词话本和绣像本的文本比较所归纳出的结论并不是衡量这两大版本优劣的结论,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文本差异都只能体现创作者不同的思想倾向而已。秋水堂主在对词话本与绣像本的比较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远不止将词话本与绣像本的差异归纳为思想主旨、人物塑造、艺术风貌三方面而已,将“春秋笔法”与“文本细读”法结合起来,还追索出了《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部分应有情节。无论是词话本还是绣像本,《金瓶梅》始终诱惑着我们,既让我们身处同一个成人世界中,又想方设法地让我们不敢接近,最后眼看着人物一个个由生到死,生活一步步由热到冷,使我们能够在不愿意接纳结局的同时让书中人物得到原谅和宽容。我们可以痛快地咒骂或原谅,正因我们变成了同谋,因为书中的故事情节或人物是非会出现在各朝各代、随时随地而不受限于时代地域。秋水堂主在书中一共配有15幅插图,除了一幅来自绣像本外,其余均选自名画或近现代的照片,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部《金瓶梅》,而书中正饱含着慈悲。
[1]田晓菲. 秋水堂论金瓶梅[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2]朱一玄. 金瓶梅资料汇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167.
[3]郑振铎. 谈《金瓶梅词话》[J]. 文学,1933,07(01).
[4]戴鸿森校点. 金瓶梅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
[5]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0.
[6]刘辉,杨扬. 金瓶梅之谜[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75.
[7]黄霖. 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A].金瓶梅论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7.
A General Review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Golden Lotus’ Cihua Version and Xiuxiang Version
ZHANG Shuang
Cihua version and Xiuxiang version are two versions of The Golden Lotus’ system.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Golden Lotus on the purpose of elaboration, the creation of characters’ images and the expressions of artistic style. According to the text criticism method in the book, QiuShuiTang’s Comments on The Golden Lotus, which is a combined meth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riting style and Western close reading style, mak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ihua version and Xiuxiang vers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To recognize the Cihua versions’ and Xiuxiang versions’ different aesthetic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and get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Professor Tian Xiaofei's mercy that she had said.
QiuShuiTang’s Comments on The Golden Lotus; Cihua version; Xiuxiang version; differences
2016—07—10
张爽(1993— ),女,四川师范大学2015级古代文学研究生。
I207.419
A
1009-5152(2016)04-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