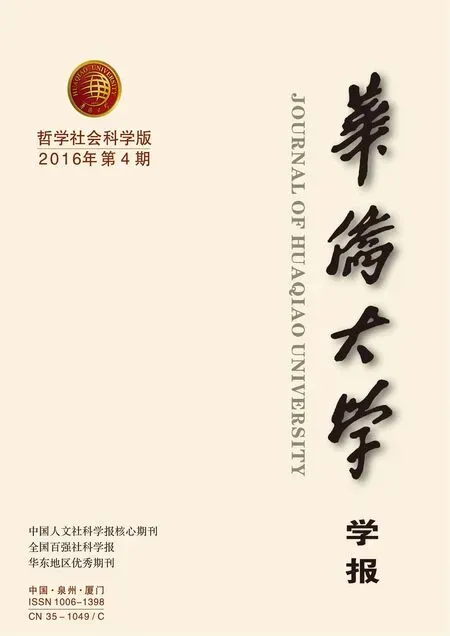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吴苑华
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吴苑华
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也作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其中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理论的反思。后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作“经济决定论”加以批判和解构,并且用“接合”理论重新界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时提出“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作为新社会的“接合实践”,取代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运动为“接合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以期变革和中介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和冲突,建设马克思追寻的那种自由民主社会。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复杂的,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一理论,揭示其价值,批判其错误。
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社会主义
以英国学者欧内斯托·拉克劳(Laclao,Emesto 1935—)和尚塔尔·墨菲(Mouffe,Chantal 1943—)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已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熟知,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它的基本状况和理论构建情况,分析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之理论内涵及意义,所有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学术资源。不过,迄今的研究对后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这样的研究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内容。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当作“经济决定论”加以批判,用“接合”理论重新界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用“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取代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作为“接合实践”,创建自由民主社会等等理论内容,揭示后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一 批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的一个最基本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奠基石。可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质疑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的正确性,由此质疑整个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理性,进而走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当然,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批判五花八门,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激烈地批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犯了“经济决定论”错误。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犯了“经济决定论”错误,根源于它们将社会理解为受单一的经济力量决定的有机体,可事实上社会运动受多元力量驱动,不可能仅仅受制于单一的经济力量。后马克思主义者安娜·史密斯认为,“每一个社会结构都是由多元决定的”,比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和性等都能成为“跨阶级联盟”*[美]安娜·史密斯:《主体立场、接合与本质主义的颠覆》,付琼编译,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51页。的纽带,“如果经济对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那么“就必须加以满足”如下条件:“在经济形成的原初因素中,政治关系的影响必须完全缺席”*[美]安娜·史密斯:《主体立场、接合与本质主义的颠覆》,第252页。,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政治决定经济的发展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时常发生,一方面,在原初因素中,政治和经济关系呈现为“必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关系并不是“一个纯粹非政治的空间”生活,政治是“经济的基本构成部分”*[美]安娜·史密斯:《主体立场、接合与本质主义的颠覆》,第253页。。总之,政治与经济始终处于无法分解的纠结状态,更何况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中,政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拉克劳和墨菲也认为,“假如经济是一个可以最终决定任何社会类型的客体,这便意味着,至少在这一最终的实例中,我们面对的是单一决定,而非多元决定”;“假如存在一个决定社会运动规律的最终实例,那么多元决定实例与最终决定实例之间的关系肯定会按照后者简单的、一维的决定来理解”*E.Laclau and C.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tics,London:Verso.1985,p99.。由此,他们赞叹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蕴含了合理思想。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4页。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犯了“经济决定论”错误,根源于它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绝对地对立起来,其实它们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它们彼此之间时常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作用之状态。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是绝对的,仅仅是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抗的双方各自具有不可公度的话语”*转引自《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其结果:要么“对抗仅仅是某种根据自身可以得到解释的客观的基本过程的外在表现”,要么“对抗沉没了”*转引自《后马克思主义》,第187页。。事实上,对抗并“没有通过自己来表达的历史的潜在的逻辑”延续下去,反而“用多种方法导致更多的民主成果”和“更多的历史行动者的感情和感觉”*《欧内斯托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访谈》,山小琪编译,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也在历史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历史的“主体立场也将由多元所决定”*[美]安娜·史密斯:《主体立场、接合与本质主义的颠覆》,第256页。。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而是民主的依存关系。
再次,从上述内容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犯了“经济决定论”错误,还根源于它们推崇“霸权专制”而非“霸权接合”。所谓“霸权专制”是指单向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经济决定论就属于“霸权专制”理论。所谓“霸权接合”是指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个“接合点”,这个“接合点”发挥着葛兰西所说的“霸权/领导权”作用,以拉克劳和墨菲之见,霸权接合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体,因此这个“霸权接合”又称为“接合实践”。在拉克劳和墨菲的视野中,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之所以陷入经济决定论错误,就在于它推崇并主张实施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霸权专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霸权专制,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通过霸权接合实现双方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他们认为,其一,由于阶级之间的斗争往往是表面的、偶然的,况且社会主体并不能按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加以界定”*[美]安娜·史密斯:《主体立场、接合与本质主义的颠覆》,第251页。,因此阶级斗争影响社会发展是有限的、短暂的;其二,由于社会主体所在阶级都有客观的利益诉求,因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其三,很多时候,政治都优先于经济而获得发展并且远早于经济因素作用于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因素的社会作用也只有在政权较为稳定之后才被凸现出来。因此,既不可夸大经济意义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作用,也不可夸大经济因素的社会作用。
齐泽克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陷入片面地抬高内容决定形式的“霸权专制”,更严重的是忽视了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在历史上时常出现,结果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释成“大致契合于蛇的隐喻”*[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即像蛇一样不断脱皮,生产力不断脱下生产关系这层皮,经济基础不断脱下上层建筑这层皮,社会就是如此自然地进化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历史变化过程失去了本真意义,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幻象”。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穆泽利斯先生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个“粗糙的地形学类比”,这在历史发展中也是“日益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类比把社会看作双层楼,楼房的上层拙劣地被设计,偷工减料地加在底层上”,因此现今“有必要更进一步并创造新的工具以能够有助于提供对于整体社会构成的概念化,它(1)避免基础/上层建筑二分中某些主要的缺陷,以及(2)保留马克思主义范式中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英]尼科斯·穆泽利斯:《技术、占有与意识形态: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二 “接合”的出场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论是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解释效力的“孽障”和“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因此消解经济决定论错误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务’”*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41—42页。,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一个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如何消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错误呢?为此,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接合实践”方案,以他们之见,接合实践是消解经济决定论错误的“解毒剂”。
所谓接合实践是指将各个社会方面联接起来的关联性活动,它起着缝合点作用,因此接合实践又称为“接合”。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斯图亚特·霍尔对接合作了如下解释:“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可以说,接合“是一个关联”,但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ed.L.Grossgerg),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Verso,1996,p.141.关联。我国学者周凡先生认为,在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接合是指“通过一种中介或活动将不同的要素或构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94页。,是“一个遇合式的建构过程”,“一种磨合的动态效应和建构活动的展现”*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第94—95页。,因而接合其实就是接合实践,是将各种因素集合起来的活动。质言之,接合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本质上作为一种中介活动而展现,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霸权”,也类似于拉康的“缝合点”和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所发挥的作用。这样说来,接合在实践中能够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接合起来,实施霸权接合,而不支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拒绝霸权专制。
首先,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接合在实践中发挥霸权接合作用,这样,接合是能够消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霸权专制。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是“对葛兰西的moral and intellectual hegemony(道德的、智识的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解读’”*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第39—40页。,“是对葛兰西霸权概念更制机化的描述,也是对其更充分、更动态、更自治化的表达”*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第40页。。问题在于,葛兰西用“市民社会”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接合,这样,葛兰西的霸权(或领导权)实质上就是霸权接合,起着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接合起来的中介作用,从而也实现了消解它们之间的经济决定论错误。由于葛兰西将市民社会既定义为文化、意识形态范畴的,又定义为经济基础范畴的,因此他的霸权(或领导权)也就是霸权接合而不是霸权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合原初性地消解了经济决定论的霸权专制,并且以原初的方式将各种因素(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基础因素)接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霸权接合,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源自于接合”而“不是先验决定”的,都是由“接合所赋予的”*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第148页。。
其次,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接合在实践中扮演“崇高客体”角色,这样,接合也就可以消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幻象”。齐泽克在拉康的引领下以“征兆”为“缝合点”,“穿越幻象”(interpretation of symptoms-going through fantasy)*[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寻找历史的本真。所谓“征兆”就是拉康的“纽结点”(nodal point),亦即“缝合点”,它能够将“众多‘漂浮的能指’,众多原型意识形态因素,被结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121页。,这样,诸如国家、自由、领导权、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等“漂浮的能指”,都可以作为缝合点,并且都能够“把那些漂浮的因素聚焦在一起”*[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122页。,形成一个“能指”的有机体。关键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决定论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社会都可能借助某个“漂浮的能指”——即缝合点,将各个领域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社会。在拉康的启示下,齐泽克提出“剩余快感”这个“崇高客体”作为缝合点,以此来消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幻象”(即经济决定论错误)。
与齐泽克有所不同,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意义剩余”作为“崇高客体”,以此来消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所谓意义剩余是指“在一具体的话语体系内,不断从能指意义链条中‘外溢’的部分”,它“决定了每一话语对象的必要的话语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话语实现最后缝合的不可能性”,而且“彰显了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但同时造成了意义的局部固定”*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第44页。。关键在于,意义剩余在不造成意义最终固定的同时却又能造成意义局部固定,这样,它不仅仅为能指漂浮的意义外溢提供可能性,同时也为能指漂浮的意义缝合提供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意义剩余其实就是接合的中介实践。因而,当你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和非决定论的”关系时,那么它们的接合点就是其意义剩余,正如社会不仅仅是多元因素的对抗场所,更是在意义剩余的接合实践中相互链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就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处“在一个身份变化迅速、认同过程困难、主体位置多样化、利益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状况下”,但是只要“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特定阶级”的领导,就能够实现“解放全社会或全人类”*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第45页。,换言之,在接合实践中,只有在一个领导阶级的领导下,借助它的权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新社会运动,才能“建构平等的多重主体之间的政治认同的主导权的”*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第46页。社会。
三 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
为什么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在他们看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在今天难以担当自由民主社会的接合实践,于是他们自己就设计一个“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缝合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分裂和异化了的现代社会,创建全新的民主社会。
(一)为什么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在今天不能继续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接合实践?拉克劳和墨菲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建立在阶级斗争运动和经济决定论上。
首先,从阶级斗争运动上看,虽然阶级斗争一直存在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运动始终都是必需有的,也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运动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决定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将“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一方面,在现代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新政治主体(妇女,民族,种族,性偏好,反核及反体制运动等等)”参与的抗议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的自由民主运动,“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这类新情况不仅预示着“修正阶级斗争的观念”*[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周凡 译,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已经成为必要,而且更加说明阶级斗争运动在今天已经不必要了。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议会斗争和个人自由的组织构架的维持及延伸现在越来越明显地依赖工人阶级运动和大众斗争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运动成为必要,恰恰相反,这一新情况预示着阶级界线不再那么分明,尤其“资产阶级”概念在今天有必要重新界定。简言之,这些问题宣告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原因所在”*[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51页。。
其次,从经济决定论看,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遭遇的种种危机还根源于她的社会主义战略奠基于经济决定论上因而无法继续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接合实践。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坚持“把社会主义构想成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极点”*[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3—64页。,但是仅仅停留于“批判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这一认识层面是远远不充分的,必须走向“抛弃在资本主义之下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确立创造可能性条件(通过政治斗争)”*[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4页。这一认识层面。正如他们所说:“今天越发变得清楚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之下的生产力的发展恰恰导致了自然资源甚至是文明本身的破坏。因此,我们必须摧毁经济主义的最后棱堡并坚持在经济本身之内政治优先性。远不是构成一个由利润最大化的简单逻辑所支配的同质性领域,经济在实际上是各种不同社会作用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生产力本身屈从于统治阶级加于其上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经济像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它的‘运动规律’并不被单一的逻辑所宰制,而是由存在于特定社会中的异质性的接合所支配。”*[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4页。
那么,这个“异质性的接合”又是什么呢?拉克劳和墨菲这样回答道:“被建构的一致性必须从底层打造,它发端于社会运动本身”而不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下的阶级斗争运动或纯粹的经济活动,它本质上是自由民主运动,“它必须由庞大的联盟体系所构成”,联盟体系中的所有同盟成员都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下进行着平等、民主的对话和协调,达成“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集体意志的结合剂”,保障所有同盟成员“真正地被结合为一体”。关键在于,这个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且“这一观念的基石必须确凿无疑地由新的激进民主观念所提供”,一方面“超越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限于通过单单增加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而参与议会,通过基层民主公民将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人将参与工厂的管理”;另一方面承认在传统主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及其政治特性的存在是重要的”,比如“妇女和各种少数派团体也有平等和自决的权利”*[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4页。。一句话,这就是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
(二)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可行吗?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战略倡导多元主义的民主观念,既表现为“政党多元主义”,也表现为“主体多元主义”*[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4页。;而且主张,只有以多元主义方式理解民主,建构新社会运动,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也才能在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下,有效地“抛弃具有破坏性的、独裁主义的作为完全同质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并且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解决对抗的社会问题的“一种真正的民主方式”,实质上就是“霸权接合”——“它将尊重自治性以及它的每一要素的特定原动力”*[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5页。。
质言之,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是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可行性的“接合实践”方案,实施这一方案在社会主义史上属于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实现了“与经济主义决裂”,亦即与那种“由列宁开创、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的社会主义观念决裂;另一方面,实现了“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亦即与那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形式上的科学形式决裂”。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指导下,我们想要实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是这样的:“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这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第65页。合法地存在和协调地发展。
李尔·纽曼说过,“随着经济与政治之间、阶级地位与政治观点之间的断裂变得日益明显化”,接合实践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已经不可逆转地“出现了通过综合的政治建构”*[澳]李尔·纽曼,《激进政治的未来》:周凡编译,载《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将各种因素接合在一起,这样,“接合实践”就既不是“本质主义的联系”也不是“还原主义的决定”,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斗争,在其中,“任何一种身份(而不像马克思所坚持的那样,只有无产阶级才必然具有这种资格)都可能充任主导角色,只要它能够设法‘接合(articulate)’成一个共同的立场”。这一“共同的立场”,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维护民主权利的新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立场。
当然,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把民主权利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领域,同时“也就是把目标指向普遍的社会改变”,允许民众组织和展开“各种不同的新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环境主义、黑人及同性恋权利斗争、反对新形式的国家权力的斗争、反对生活的日益商品化的斗争等等”。因此它“不能再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范畴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相反,工人的斗争必须被看作各种不同的民主斗争中的一种”*[澳]李尔·纽曼:《激进政治的未来》,第300页。。
正如西姆所说,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命题和核心范畴”“总体理论逻辑和分析模式”,但是这一战略仍然以“弘扬马克思的激进批判精神”,“重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继承马克思的解放事业”*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索》,第46页。为己任。由此来看,后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接合点,并且将实施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战略作为推进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接合实践。
结束语
以上内容显示,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有别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重建理论,具有某些独特的理论品质。不过,以下三项内容尤其显示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品质:
第一,以批判经济决定论为切入点,实施批评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经济决定论最早出现在第二国际时期的考茨基等人的理论中,他们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不过,当时就遭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批判;后来,青年卢卡奇也加入了这一批判队伍,指责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由于青年卢卡奇开启了一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路径,因此批判经济决定论也因之被西方学者延续至今,且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反思历史唯物主义时必做的一个惯常活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介入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并非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独门创举。正如前文所说,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批判过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在他之后,人们日益强化了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比如,哈贝马斯曾经强调过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他还率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的论断,由此否定经济的最后的决定作用,并将经济发展归功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实际上,持有与哈贝马斯主张的学者还包括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和乔万尼·阿瑞吉,前者强调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扩张取决于资本主义霸权和不平等的交换*吴苑华:《马克思主义:在沃勒斯坦的理解中》,《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后者强调过利润率的增长取决于制度(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制度)*吴苑华:《世界体系视野中的马克思理论——乔万尼·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年第1 期。;还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和威廉·莱易斯,前者强调过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然与文化的矛盾状况,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平稳发展与否取决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安排是否得当,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都不主张经济决定论。
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前后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有区别的。青年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然而他之后的西方学者则在认同了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的指认之前提下批判经济决定论,换言之,青年卢卡奇之后的西方学者,包括拉克劳和墨菲,几乎一致地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就是经济决定论,甚至认为这个“决定论”严重地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严重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效力,必须清除经济决定论这个错误理论及负面影响,还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
我们承认,批判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拉克劳和墨菲等人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了考茨基的做法,把马克思主义直截了当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加以批判和修正,这样一来,尽管他们的用心是好的,可是其前提错了,怎么能保证其道路和结果的正确性!因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人是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比如考茨基,他用经济决定论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向人们传播了这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只是表明考茨基先生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并不等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就真的属于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不是经济决定论的,他们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者!如果把这种批判延伸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展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批判,就从正确的走向了错误的一边了。
我们也承认,批判经济决定论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可以警示人们不用这种理论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经济决定论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任何意义的经济决定论都是不可取的错误理论,不仅需要杜绝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再出现经济决定论的荒唐行为,而且需要在批判经济决定论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内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第二,创立“接合实践”理论,实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后马克思主义汲取拉康的“缝合点”思想,经过一番改造和包装,创建一种“接合实践”理论,发挥着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以他们之见,社会之所以可能,生活之所以可能,历史之所以可能,皆在于有了某个“接合点”,比如意识形态,它将诸多社会要素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所以,作为接合点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粘合剂”。拉克劳和墨菲声明过,他们的接合概念汲取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或者说,他们的接合具有与葛兰西的“霸权”(或“领导权”)一样的功能和意义,进一步地说,甚至具有与青年卢卡奇、柯尔施的“总体性领导权”一样的功能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的接合理论也具有某种积极意义,至少告诉人们:从整体性视域上理解社会、生活、历史是首要的选择。
然而,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实践无法替代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前者也不具有后者的理论效力。1)接合实践是一个观念意义的概念,属于认识论范畴,社会实践是一个物质意义的概念,属于本体论范畴;2)接合实践倾向于领导权,意在加强管理和监督,难道管理和监管就是历史、生活和社会的本真维度吗?社会实践倾向于生产与再生产,强调了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生活和社会的本真维度;3)接合实践可以是意向性的活动,而社会实践则必须是人的感性的活动;4)实际上,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实践属于抽象的政治生活内容,正因此他们特别看重国家、民主、意识形态和法等政治生活内容,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则属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而且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根基,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劳动的优先性地位。显见,接合实践与社会实践是两个异质性概念,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实践无法取代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而成为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本质内容。因而,任何想借助接合,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合理地并且创造性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才有可能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
第三,以激进民主政治为方向,重新设计社会主义战略。为什么拉克劳和墨菲选用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着力点?这仍然源于他们的接合理论。在他们看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民主和社会主义都曾充当过社会的接合点。虽然民主被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社会主义被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过,但是它们都没有发挥出自身的效能,在西方国家,这种困境根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魔障”对民主的蒙蔽和限制,而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困境根源于斯大林主义“霸权专制”对民主的压制和边缘化。因而,为了消解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上述困境,拉克劳和墨菲设想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重建理想社会。
如此看来,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方案似乎创新了民主的内容和实现途径。其实不然!他们沿袭了西方惯常思维模式,一方面将民主简单地区分了激进民主与保守民主,激进民主是指社会主义的民主,保守民主是指资本主义民主,这样区分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尤其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倾向于保守的社会主义,尤其钟情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样的选择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将激进民主与保守的社会主义相结合,造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方案呢?显然,它是不会造就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
其一,他们的社会主义方案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闭口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其二,他们的社会主义方案倡导激进民主,所谓激进不过是激烈地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贪婪和凶残,并没有激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反而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持有激烈的抗议,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方案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其三,他们的社会主义方案走了一条调和主义路线,追求一个全社会各阶级大团结的共容共存的和谐社会,也就是,希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容共存,实质上是希翼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主义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责任编辑龚桂明】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Post Marxism
WU Yuan-hua
As a new theory of foreign Marxism,Post Marxism has also been explored in many aspects,including of the reflection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productivity determin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economic base determining the superstructure of Marxism are criticized and deconstructed as “economic determinism” by Post Marxism,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re replaced with bonding.At the same time,the paper proposes the “radical political Socialist Strategy” as the new society,and replace the economic decision theory and the class struggle movement of Marxist socialist strategy,so as to contradict and conflict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termediary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and construct the freedom and democracy society of Marxism.Undoubtedly,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Post Marxism is complex,and we should hold an objective and dialectical view and analysis on its theory,its value,and its mistakes as well.
Post Marx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economical determinism;socialism
2016-04-20
吴苑华,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福建 厦门361021),主要研究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生存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世界体系论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6BKS085);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世界体系论视野中的‘一路一带’研究”(FJ2015A010);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009A003)。
B089
A
1006-1398(2016)04-0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