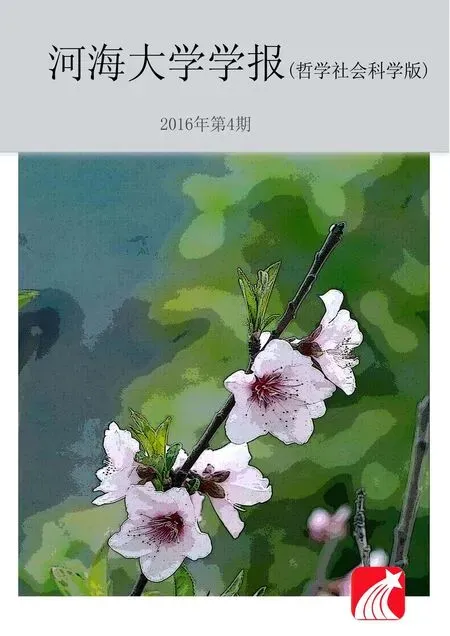近十年中国公民精神海外研究评述
杨四海,程 倩
(1.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2. 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江苏淮安 223000)
近十年中国公民精神海外研究评述
杨四海1,2,程倩1
(1.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210094;2. 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江苏淮安223000)
公民精神具有公民主体性和公共性两个特性,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是中国公民精神整个研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海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为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必要条件;儒家思想尽管与现代文化之间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其对现代公民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绝无裨益的;在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中国公民精神呈现出逐步成长的趋势;国家主导下的中国公民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较快,而政治权利发展滞后,表现出与西方经典公民理论不同的特点;中国公民精神的未来走向,是扩大公民政治权利和培养世界公民意识。但是,海外研究存在着否定中国政治制度等问题。
中国公民精神;儒家思想;多领域;不平衡性;发展走向
公民精神显然是与公民内涵的理解和公民行为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公民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在现代的意义上,其狭义或者传统的理解是:具有政治国家成员资格的社会个体,既拥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又需要履行对他人和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广义的公民内涵,则突破传统国家的界线,把关注领域扩展到地方、跨国地区和全球等多个不同等级的层面;公民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从传统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扩大到社会权利,后来甚至还出现了“文化权利”*持有公民文化权利观点的主要是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等,他还出版了专著《文化公民身份:全球一体的问题》,王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公民精神是公民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取向基础上的内在信念和信仰,同时也是基于公民信念和信仰的行为表现。公民精神具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公民的主体性,主要指作为主体的公民具有自由和平等、独立和自主的气质,能够自主做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另一个是公民的公共性,主要反映的是公民行为的公共取向及其实际表现。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是中国公民精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
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当时在法律上赋予个体公民权利和义务,但是这基本表现在形式上和文字上。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发生逐步改变。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40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作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公民和公民精神塑造情况在中国究竟如何,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内对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研究文献较多,研究主题大多围绕公民认同、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道德等问题展开,而海外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但是它是中国公民精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海外研究在角度的切入方面也与国内有所不同,可以拓展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的视野。因此,考察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必要性。
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涉及问题比较丰富,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公民精神发展的未来趋势。在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的研究中,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公民精神的概念,*在H.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2012)著作中,张成福等直接将citizenship译为“公民精神”,暗含着“公民身份”等同于“公民精神”的判断。此外,袁祖社还认为,“公民性”与“公民精神”可以互换使用,civility汉语意思可以表达为“公民属性”、“公民精神”等,如果直译就是“公民精神”。但是,其探讨的主题往往与公民精神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近十年,海外学者涉及中国公民精神发展方面的研究,其涵盖的主要问题大致可以归纳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可否塑造现代的公民和公民精神;二是通过研究公民教育、流动人口和社区建设和多层次公民身份等问题,多学科、多领域地勾画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状况;三是考察和分析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进程,揭示中国公民权利成长的特殊性;四是从公民政治权利和世界公民精神两个方面,指出中国公民发展的走向。当然,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也带有明显的不足,比如:过分强调公民权利,自由主义公民观念的色彩比较浓厚;怀疑和否定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推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和文化价值观。
一、探讨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形塑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作用
西方公民理论是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发育起来的,是西方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想结晶,也是西方社会实践的成果。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儒家思想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文化有着截然的不同。那么,中国能否塑造出公民,何时出现公民,传统的儒家文化有何影响,海外研究者对此均进行了探讨。
海外学者一般认为,公民的形塑是与建立在市场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中国公民问题,研究者没有选择以政治作为起点,而是以经济和社会为着眼点,考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以及与此有关的城市化进展。这似乎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不谋而合。托马斯·雅诺斯基认为,现代意义的公民身份“是随着西方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1]51。西方城市的出现,为市民的经济活动及其权利诉求提供了空间,当市民的活动进入公共领域,往往也就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市民便向公民进行转变。城市化的发展是公民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个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当现代城市在西方以崭新的面目示人的时候,中国以市民为活动主体的现代城市却迟迟没有出现。尽管民国以前漫长历史中也有人群高度集聚的生活之所,但是人们相互之间不能进行广泛和自由的市场交易。韦伯对于东方国度的研究表明,这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相去甚远[1]52。当然,在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出于回应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安全威胁的需要,改革者提出了教育和培养现代公民的主张,但是从主张到目标的实现,期间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付诸大量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培育公民的理想并未实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经历动荡和战争的困扰,公民身份几乎无从发展。此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中国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建立,使得真正的“公民身份发展缺乏必要的空间”[1]53。中国改革开放把国家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步提升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这才为市民的发展和公民的塑造和成长提供了条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公民才真正得以出现。
不可否认,在公民精神的发育和成长过程中,文化一定会发挥影响作用。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根本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其对中国公民的发育具有何种作用,这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外学界一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工具,服务于统治者专制统治和利益谋取的需要。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理想王国中,主张公共权力属于百姓,而不是统治者和国家。然而事实上,帝王们常常选择“三纲五常”作为统治国家的思想基础,并视作社会控制的手段,维护一种以皇权和父权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关系。“三纲五常”的实质是依据专制统治的要求,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给予明确和强制的等级规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着重突出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并对个人归化以“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后者在本质上依然是对人们之间关系的设计和规约。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儒家思想中对人们关系的伦理规定,都与西方自由、平等的理念相去甚远。托马斯·雅诺斯基提出儒家思想中的所谓“公共性”因素,把国家和家庭的地位凌驾于个人之上,名之曰“公有制社会”[2],其显然与西方公民得以诞生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制度不同。同时,他还指出儒家思想中“天命观”等阻碍了“公民”这个新生儿的降生[1]53。天命观把帝王位居统治地位与“天命”相连,被统治者只有臣服的命运。从海外研究者的论述看来,在儒家思想的文化语境中,公民的产生似乎绝无可能。后来,儒家思想在现代政治思想和公民理论的影响下,同时又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冲击,其势力已经被减弱。于是,就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不见得对这一问题(公民发展)有什么实质性影响”[1]63。实质性的影响也许并不存在,但是对一些观念产生思想意识的作用则是确定的。“把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公有社会性质的公民政体”[2],“具有儒家伦理素养、维护社会和谐以及为国家奉献”[3]的公民价值导向,似乎已经告诉人们儒家思想文化对公民精神的渗透和影响。这着实与西方自由、民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以权利为中心的公民大异其趣,表明儒家思想可以看作是现代公民精神在中国发展的一股影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对西方公民理论具有一定的改造作用。
二、多领域探究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状态
海外学者通过考察民国以来的公民教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以及社区建设对公民发展的影响,认识和把握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状况。同时,研究中还包含着对地方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观照,研究的角度涵盖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教育学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通过民国时期的中等教育历史分析、现代城市孩子权利讨论和当代教科书的修订得以呈现的。Culp 以民国时期的中等教育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他们的教科书、学生自治组织、学生对公民的理解以及文化表现,揭示了民国公民教育的不同纬度。同时也提出,该时期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参与教育,与社会秩序之间相互促进,“催生了一个直接参与、以实际行动为国服务的公民概念”[3]。Naftali 在全球自由主义及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讨论中国城市未成年孩子的权利问题,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关于孩子及其权利思考和阐述的新模式,即“孩子应当成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孩子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附属”[4]。其研究还揭示了在孩子权利方面父母们面临的矛盾:一方面具有实际承认孩子权利的意愿,另一方面却受到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传统观念影响。孝道思想的再度流行,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制约了父母把孩子培养为自主和自治的人。教科书的研究在时间上,既有民国时期又有改革开放时期。Culp 在研究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分析,有助于讨论国家概念及其与种族、文化和领土的关系。他还重点考察了与公民有关的教科书和课程。Thomas在对1997年与2005年的两版教科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在青少年精神和性格的塑造上,学校课程充斥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所变化,“尤其是中国在走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新版教科书弱化了意识形态,吸纳了关于人权和世界公民的主张。”[5]由此可见,教科书的出版和修订也好,学校教育也罢,它们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对现代公民塑造的愿望,也表明了中国对公民精神认识的提升。
在社会学领域,通过探讨流动人口的赋权和城市社区的建设问题,诠释当代中国公民权利现状及其发展的态势。Jakimow 认为,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呼吁承认他们流动人口的身份和城市身份,反映了他们打破城乡边界的愿望,“其在客观上打开了东方主义公民身份的空间”[6]。城乡协调发展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地方,“居住权业已成为衡量社会权利的基本标准”[7],而不再考虑城市身份还是农村身份的因素。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地方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政府的行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公民的社会权利边界已经从城乡差别向公民权利自身转变。学者从比较的视角,指出中国与欧盟一样,已经成为国民可以自由流动的地区,但是在流动人口获得的保护及其公民社会权利方面,“中国则与欧盟有着较大差距”[8]。城市社区的建立,促进了中国现代公民的发育,海外学者从“社区治理参与和草根选举、社区自治和居民态度、自主性个人的发展、政党-国家价值观的影响”[9]四个方面,检视了中国社区居民从大众向公民的转变。
立足政治学的视角,研究者考察了作为主导公民身份的国家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教育,是民国时期和改革前的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1912年~1949年是中国社会个体向现代公民转变的开始时期,此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两个存在明显政治冲突的党派,在塑造公民方面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虽然两方面的主张并不一致,但是它们都把培养国家主义公民身份、重视公民教育作为主要任务。这段时期的课程设计,也突出了国家认同和政治参与,努力培育为国谋利的共和公民。1949年以后,国家倡导培养红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化的趋势,体现了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公民精神的塑造也随之打上了国家的印记。
除了国家公民身份以外,研究者还从政治学的视角还探讨了地方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中国地方公民的培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抗时期,当时的目的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当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公民身份是香港的地方公民身份。由于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了中国,对于香港公民身份的研究,需要考虑“三个影响要素”[10]:一是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产生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影响;三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相对立的反应。关于全球公民身份的内容,在教科书的改版中就有所体现,如“2005版教科书吸纳了人权和世界公民意识的相关内容”[5]。有研究者通过中美公民教育的比较发现,“全球化和世界主义在公民教育中被归并和加强,并指出这个可能是一个崭新的公民教育方向,它是对地方和全球共同体的回应”[11]。碳排放对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碳排放问题不断恶化,培养与国家经济影响力相适应的、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意识成为紧迫的任务”[12]。协调中低阶层收入不断分化的矛盾,改善民生和公民社会权利,各个地方政府应当采用绿色环保的技术,投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然而,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研究者对中国公民精神是否正在走向全球化抱有疑问,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暴力抗议之后,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对中国统一的公民身份产生了争议,但是,“主张构建一体化的公民身份,依然是国家的主导性行动”[13]。公民身份是否能够包容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这是世界公民精神的要求,研究者对这个疑问的提出,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思考。但是,包容差异和文化的多样性,并不表示对暴力活动和分裂势力采取容忍的态度,这是应当高度警惕的。
三、诠释中国公民精神发展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公民精神的发展,包含着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发展两个方面,而海外学者的研究则大多仅关注公民权利。西方经典公民理论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发展路径和发展顺序论述是十分明确的,T.H.马歇尔就是为此做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其有关公民身份权利的思想被认为是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他主张公民身份由公民、政治和社会3个要素构成[14],因此,公民权利相应地就出现了3种类型,即法律权利(也有将之称为公民权利、民事权利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英国为研究背景,马歇尔分析了3种权利在英国出现的顺序和时间。他认为,公民的权利起初并没有类型的划分,3种权利混沌一体。后来,随着国家机构的分化和独立,公民的权利便呈现出融合和分化的双重过程,融合表现在地域上,而分化体现在功能上。法律权利发展于18世纪,而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分别发展于19世纪和20世纪[15]11。而且,三者的发展是前后承接的线性关系,即政治权利的发展是以法律权利发展为基础的,同时政治权利的发展又是社会权利的发展条件[15]20。公民权利的发展就其整体来说,有学者认为是平稳演进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在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战争的状态”[15]220中进行的。马歇尔公民理论,成为学界后来研究公民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其本人也因此成为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尽管批评者对其论述和观点提出批评,但是其公民理论产生的影响依然十分广泛和深远。
较之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则显得不同,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导之下的选择性。尽管中国公民权利是交叉式的发展,但也基本显示了先法律权利、后政治权利、再社会权利的发展路向[16],在发展的顺序性上与T.H.马歇尔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可是,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不仅具有国家主导的特点,而且公民3个权利的发展显示出不均衡性,这两个方面显然与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的主张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公民权利或者说公民精神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马歇尔公民权利理论中,不管是三类公民权利的先后平稳发展,还是其在公民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前进,都没有看到国家主导的影子,而中国公民的3个权利发展则是在国家的选择和推动下实现的。另一方面的特殊性是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的不平衡性,即法律权利、社会权利较快,而政治权利发展比较滞后[2]。中国公民法律权利的发展,表现为公民通过法律诉讼维护自身的权益,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取得尤为瞩目的进步。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发展,尤其是城市公民的社会权利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明显高于同期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然而其背后却是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尽管在城市有所下降,但是就其总体而言,用于公民社会权利的福利支出比例在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由占美国和日本的1/3增长到1/2。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意味着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远远超过同期的政治权利,与同期的法律权利大体相当[1]61。“文革”以后,对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压制明显减少,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地方层级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基层选举制度改革得以进行,民主的发展取得了重要进步,村民选举被学者视为迈向民主的重要举措。总体上来说,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发展水平较低,不仅与“西方和东亚国家相比差距较大”[1]60,而且与中国公民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相比,发展较为缓慢。虽然中国政治权利的发展滞后,但是取得了自中国革命以来的最大发展。
这种政治权利发展滞后的发展格局,尽管与经典的公民权利发展理论不甚吻合,可是其发展逻辑却又是接受的。郑永年提出,中国的发展路向应当是先经济改革、后社会改革,最后进行政治改革[17]11。其分析认为,改革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应当遵循由难到易的原则。经济是生产蛋糕,靠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实现,目标达成比较容易。社会改革则是分配蛋糕,是对社会利益的再调整,常常会让富裕阶层失去一些利益,因此会变得相对较难。而政治改革则是让当权者放弃一些权力,在权力主导的中国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较大。中国改革30年才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社会改革尽管已在进行之中,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推进都在进行中,但还尚未“进入一个以选举民主为目标的主体性政治改革阶段”[17]13。因此,与经济改革相关的公民法律权利、与社会改革相关的社会权利发展较快,而与政治改革相关的政治权利则发展较为缓慢。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公民精神发展的不同所在。
四、表明中国公民精神的发展走向
通过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中国公民精神有两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发展和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
托马斯·雅诺斯基在对中国公民权利发展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大胆预言:未来几十年,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中国公民培育和民主发展的可能路径[2]。中国公民团体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志愿活动大幅增加,公益慈善事业开始起步……网络、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应用极大地革新了中国的传媒领域,营造出过去几乎未曾有过的公共领域。”[1]69它为中国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公共领域。但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托马斯·雅诺斯基认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党—国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和主导。中国共产党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登记和资金来源进行管控,同时禁止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政见不同党派的建立,对网络言论和活动进行审查[1]64-67。二是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中国经历两千多年发展的儒家思想,也许对自由和开放以及公民社会没有实质的影响,但是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党”等主张,削弱了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力量,对公民政治生活发展的约束和削弱是不言而喻的。
海外学者提出,世界公民精神的培养是中国公民精神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教科书的内容选定中体现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公民教育的讨论被置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背景下”[11],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提到了世界主义的高度,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利也通过世界主义的眼光进行审视。上海、香港等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公民的培养,同样提出了全球化视野的要求。在探索国家政治认同的同时,还是离不开对公民世界主义意识的关照。在21世纪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国家普遍地意识到公民教育仍然是适应时代挑战的有效选择,但是,此时的公民教育必须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培养具有世界身份、国家身份和地方身份的多层次公民,让公民成为文化多样性世界中积极的和负责任的自觉主体。但是,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虽然全球化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公民和公民教育仍然被限定在国家的层次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常常把国家主义的培养和强化,作为公民课程设置所考虑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公民课程内容选择的重要指导。
五、结 语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不仅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且考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者揭示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是塑造中国公民提供的社会条件,论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公民精神培育中的影响,并主张要构建包含公民精神在内的中国的公民理论。他们还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从地方、国家和世界主义的3个不同层次,从多学科的角度展开对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情况分析,基本展现了中国公民精神特别是公民权利的面貌。研究者指出了中国公民精神发展的特殊性,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国家主导下的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较快,而政治权利发展显得缓慢,与西方经典公民理论所持观点并不相同。研究者还表明了中国未来公民精神的发展走势,主张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发展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适应自由、民主社会的要求;要培养世界公民精神,共同应对世界主义的各种挑战。
然而,海外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之一:关于公民精神的诠释不够完整。公民精神的完整构成,不仅包括公民的主体权利,其常常被称作为公民的消极权利,而且还应当包含公民的公共精神,也就是公民的责任、义务和美德。否则,公民精神是不全面的,不能真正勾画出公民轮廓和样貌,从而难以准确地评价公民的成长水平。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恰恰存在着片面性的明显缺陷,把研究公民的重点基本局限于公民权利这个单一的主题,而对公民责任尤其是公民的国家责任则基本忽略。表现之二:对中国政治体制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的国家价值观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公有成分,大多进行否定和批判,并将中国公民精神划入“专制的社群主义”[9]。由此可见,海外学者的学术和政治立场依然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是他们评价中国公民精神发展的主要标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简单地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方式,这将不得不陷入文化和政治单一化、甚至霸权化的误区。表现之三:研究基本仅限于检视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比如,研究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和个体成长,考察中国海外留学生的灵活性公民权利,研究社区自治和公民参与,基本局限于历史和现状。而对中国公民精神规范性研究不够,对于中国公民精神的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没有提出系统的建设性建议。虽然研究者也把发展中国公民政治权利、培养中国公民的世界公民意识,作为重要的任务和议程提出来,但是仍然缺乏从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本土出发的深入思考,海外研究者关于“中国公民概念和公民理论的构想”[2]可能就会落空。
[1] 托马斯·雅诺斯基.中国的公民身份与公民团体:对权利与公共领域的概述[C]//郭忠华,译.中国公民身份: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THOMAS J. Citizenship in China: a comparison of rights with the east and west[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4(19):365-385.
[3] CULP R.Theorizing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2012(16):123-148.
[4] NAFTALI O.Empowering the child:children’s rights,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J]. China Journal, 2009(61):79-103.
[5] THOMAS K T. Creating good citizens in China: comparing grade 7-9 school textbooks,1997—2005[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11(2):161-180.
[6] Jakimow M. Chinese citizenship “after orientalism”: academic narratives on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J]. Citizenship Studies, 2012(5-6):657-671.
[7] SHI S J.Towards inclusive social citizenship?Rethinking China’s social security in the trend towards urban-rural harmonis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2(4):789-810.
[8] KOVACHEVA V.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movement and social citizenship for internal 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converging trends?[J]. Citizenship Studies, 2012(3-4):545-561.
[9] HEBERER T.Evolvement of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or authoritarian communitarianism? Neighborhood d ̄e ̄v ̄e ̄l ̄o ̄p ̄m ̄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2009(61):491-515.
[10] FAIRBROTHER G.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Hong Kong’s citizenship education policy paradigm[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2006(1):25-42.
[11] STEVEN P. Citizenship education under discourses of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illustration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J].Front Education, 2011(4):602-619.
[12] RIAD A. The path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tentative observation on China and India[J]. Journal of Asia-Pacific Business, 2007(3):1-4.
[13] LAGERKVIST J.Global media for global citizenship in India and China[J]. Peace Review: 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2009(3):367-375.
[14] T· 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郭忠华,刘训练,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
[15] 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M]. 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6] 肖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权利成长的历史轨迹与结构形态[J]. 广东社会科学,2014(1):70-78.
[17]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许宇鹏)
10.3876/j.issn.1671-4970.2016.04.007
2016-04-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Z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4YJA710035);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金项目(16SSL046/AE89630)
杨四海(1969—),男,江苏盱眙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公共管理研究。
B824
A
1671-4970(2016)04-0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