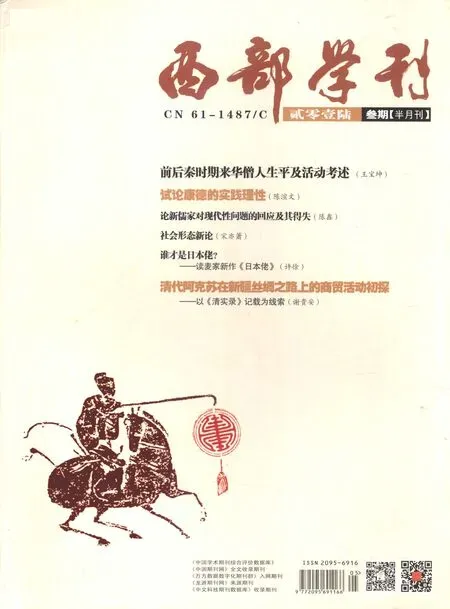谁才是日本佬?——读麦家新作《日本佬》
许 徐
谁才是日本佬?——读麦家新作《日本佬》
许 徐
麦家新作《日本佬》,把目光聚焦到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通过抗战后这个家庭的生活遭遇来写战争和战争之外的影响。通过四组矛盾的组织,麦家创造性地把战争的影子、政治运动的影子、自己的影子,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形成了更加庞大、更加幽暗、更加压抑、也更加瑰异的“重影”,从而将反思的触角伸向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和制度本身。如果说,麦家在2015或2012年之前的作品,是在努力探索“人的高度”;2015或2012年之后,则是在苦苦思索是什么一种东西能将高尚的人也随意踩在脚下?对麦家来说,这是一次新生。这指题材上的,也指精神上的。
麦家;日本佬;革命;制度;反思
但小说情节的确没有多少新意,甚至有点老套,也不复杂。小说以“我”的叙事角度,写“我父亲德贵”十几岁时被日本人抓去当了几天壮丁,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回村以后当本事显,结果村里人起了一个绰号“日本佬”,想改也改不了。战后的政治运动,因为当壮丁期间救过一个日本佬的孩子,“父亲”被打为“汉奸”、“反革命分子”,小说用一向要强的爷爷自杀的场景结束。这和麦家谍战小说传奇曲折、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相比,确实有点简单,甚至简单得有点寒碜。然而,读完小说,我却并没有因为情节的简单而感到阅读的苍白感、轻飘感,反而,我觉得这篇小说就像北方深冬屋檐下长长的冰凌,透明但坚硬无比,发出冷冷的带刺的白光,故事里的人物、情节、语言和我的阅读过程碰撞在一起,产生冰凌袭击人的身体而后落地破碎的那种尖尖的痛感和沉沉的脆感。为什么如此简单的小说,会有如此质感的阅读体验呢?
一、真的日本佬和“日本佬父亲”
我想,这种体验首先来自于小说所组织的四组矛盾。不大的篇幅,围绕父亲的四个身份,不慌不忙地布置了四组不小的矛盾,这也见麦家叙事的定力。按照小说叙述的逻辑顺序,四组矛盾分别是:真的日本佬和抓了壮丁的“日本佬父亲”的矛盾,生产队副队长关金和“村民父亲”的矛盾,公社武装部专政和“黑五类分子父亲”的矛盾,以及爷爷和“不肖子父亲”的矛盾。
第一组矛盾是因为真的日本佬抓父亲做了壮丁。这是所有矛盾的由头,也是故事发展的契机。十五岁时,父亲因为一早上山打柴,不知道鬼子进了村,结果一回村,就被鬼子抓个正着。鬼子的马死了,所以父亲被逼着做了挑夫,一直挑到铜关镇鬼子的军营。在军营里,先是养马,后来养狗。有一次,因为给狗洗澡,救了落水的一个日本大官的孩子。救人这件事,让父亲获得了身体的自由,从军营回到村里过上原来的生活。然而,也让父亲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斗,重又失去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身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精神的自由: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父亲想不答应都不行,不答应人家叫得更响。就像爷爷说的:“人的绰号像脸上的疤,长上去了就消不掉。”[2]“日本佬”成了父亲一辈子挖也挖不掉的疤。
“日本佬”这个绰号已经像一枚钉子,深深地钉进了父亲的大脑。所以,麦家专门写了一个父亲“变形”的细节:父亲后来的长相、脾气都越来越像日本佬,个儿不高,但壮实如牛;话不多,但脾气火爆,逞强好胜。(《日本佬》第4页)那个十几岁的老实巴交的农村少年“福贵”,从此不见了。这个日本佬脾气既让父亲在村里威风头十足,也让父亲在村里树敌不少,比如后来对父亲使坏、代表公社监管父亲的关金。这样写,麦家似乎在说父亲的这一切悲剧命运都是咎由自取,是这样吗?我们知道,在血统论盛行的时代,血统身份是决定一切的。麦家用他的卡夫卡式的变形手法,写父亲这种奇怪的“变形”,写父亲的这种日本佬脾气和带来的后果,其实更想说明的是血统决定论对人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比如父亲从长相到行为上的怪异变形),不仅是一时一地的,更是影响人的一生命运的。假如父亲没有被日本佬抓去,假如父亲的绰号不是“日本佬”,而是和村里人一样的随便什么的“癞皮狗”、“馊豆腐”、“矮脚凳”,父亲就不会遭受这样的打击,父亲完全可以像村里其他人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说不定因为爷爷“长毛阿爹”的名头,也能当个村干部。但父亲就是“日本佬”,所以父亲的性格和行为在身份的重压之下不可避免地扭曲变形了,父亲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悲惨了,小说的一切故事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副队长关金和“村民父亲”
“日本佬”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小说的第一个进展,就是关金和父亲之间发生的第二组矛盾,起因是“我”,但源头却还在父亲“日本佬”的绰号和脾气。还没当上干部的关金,一次在生产队开夜会时,随手从旁边妇女手上抢了一把瓜子,对“我”说:“小鬼子,你的过来,这里的,有米西米西的。”结果,父亲转身对关金飞起一脚,骂他:“你狗日的,以后要再这样叫我儿子,老子把你舌头割了!”(《日本佬》第5页)从此,关金和父亲的关系恶掉了,在关金当上村干部后彻底恶掉了。原本怕父亲的关金,有了干部身份后,时不时地会对父亲使坏。在槽厂(民间造纸的作坊)做活,父亲一个人干的是派料的力气活,五点起床、六点上工,关金的亲兄弟关银和堂兄弟关林则轮流负责造纸,七点钟到。如果关银或者关林上班后料还没派好,就会不高兴,不高兴就会告诉关金,关金就是一句话:“回去跟日本佬说,今天扣掉两分工。”一天做满十小时活才十分工,就算迟到一小时也只能扣一个工,父亲很不服气,但关金是副队长,怎么吵得赢他?为此,麦家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偷闹钟和藏闹钟。为了父亲不迟到,母亲走了二十里山路偷来了娘家的闹钟,为了不被外婆找到,父亲把闹钟狡黠地藏在了爷爷的夜壶里,总算暂时解决了关金随便扣工分的问题。然而,这个小矛盾、经济矛盾的暂时解决,换来的却是第三组更大的、更沉重的政治矛盾。
麦家让矛盾这样发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关金不只是“关金”,而是乡村基层政治权力的代表,麦家设计的“关金欺负父亲”的矛盾,既是关金和福贵之间的,也是作为“村干部”的关金和作为“村民”的父亲乃至更多村民之间的,或者说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乡村政治与普通百姓间的矛盾,是一个只不过夹杂了一点个人纠葛的政治矛盾。如果我们熟悉关于土改的历史和关于土改的作品,我们一定会发现“关金”这个坏分子当权的形象并不陌生。《十里店》一书所记录的贪污腐化、虐待群众的支部书记王绍贞,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村长王喜堂,专横跋扈的支部组织委员王来山,诬陷得罪自己的人为“敌特”的王池勇,都有关金的影子。[3]这也难怪,“土改工作组进村两三天就建立起贫雇农小组,由于工作粗糙,基本群众没有发动,结果不少贫雇农代表或者是地主和伪保甲人员操纵的流氓、地痞充当,或者是伪保甲人员摇身一变而成。”[4]273不能说关金就一定是流氓、地痞,但他身上这种以权谋私、挟私报复、不可一世的品行,却有明显的匪流气。选关金做干部,既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谭其骧日记就记载过选一个叫叶凤领的二流子当领导的缘由:“凤领为西头领袖,积极,但为人有二流子习气,不正派,苦于此外无适当人选,只得如此。”[5]小说中公社武装部的老吴第一次来调查父亲,对还是治保主任的关金也并不放心,在做调查记录时,不仅事先警告关金“记错了就撤职”,而且事后又仔细检查了记录。但同时这更是一种政治的结盟和相互利用,比如土改小说《月晕》中的马队长,是一个老辣的群工干部,他并非不知道混成干部的黄九子的流氓无赖,但是为了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他需要利用黄的这种可怕的影响力,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而小说中的关金,虽然不干好事,但也一路升迁,从治保主任一直做到了副队长,并且最后还光荣地担负起替公社监管“黑五类”父亲的重任,就因为他是一把好用的专政的“枪”。可怕的是,虽然从苏区起就经历过数次整顿,但这种乡村政治的流氓性,直至今天依然幽灵般游荡在中国农村。于建嵘指出:“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利用‘合法的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从乡镇领导的主观愿望来说,主要有‘以黑治黑’、‘以黑治良’、‘同流合污’等三种情况。”而乡镇领导“引狼入室”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那些被他们认可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组织‘三主干’的一把手”。[6]这多么触目惊心,在土改小说销声匿迹而反映当代农村基层政治的新作还未形成气候的时候,①麦家通过并非农村政治题材的小说,通过对关金这个“坏分子”的冷峻刻画,通过关金与父亲的矛盾,漫不经心地写出了这个中国乡村根深蒂固的流氓政治的弊端,他至少再一次暗示我们:“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权,且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7]
2) 采用粗糙集约简属性对评价因素进行约简,从数据本身出发,由计算机完成筛选,避免了主观确定的不足,同时融合了界面设计师与程序开发人员的观点,也避免了他们之间意见相左的矛盾。
三、公社专政和“黑五类分子父亲”
关金这个“坏分子”掌权,果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第三组矛盾的到来,即公社武装部对“黑五类分子”父亲的专政。虽然矛盾的根子还在父亲被日本抓壮丁以及救人的经历,但公社之所以调查,最有可能的就是关金的告密。专政总共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还是治保主任的关金领着公社武装部的老吴到了我家,调查父亲1938年给驻扎在铜关镇的日本宪兵队做事的事情。这一次专政,主要是用老吴和父亲的对话来展开,波澜不惊,不痛不痒,顶多算个前奏。对话之前,爷爷挑衅关金,在老吴面前故意暴露出了关金和我家的矛盾,为谈话的好结果铺了个好垫子。对话中,父亲编造了进城之后就与鬼子分手、讨饭、在理发店做事的经历,期间还穿插了鬼子像捅稻草人一样捅了又捅逃跑的挑夫、鬼子用鱼手淫、鬼子劈吃食的土狗等恐怖、恶心的细节,增加了叙述的传奇性,也激起了老吴的好奇心和情感共鸣,成功地骗过了老吴,最终拿到了公社的盖着大红公章的清白结论。爷爷和父亲用农民的智慧,成功地暂时击退了革命专政的进攻。但暂时终究是暂时,当燕子第二次飞来的时候,专政也第二次降临了。这一次,没有语言,只有行动,没有对话,只有武力。公社武装部科长亲自带着老吴和一个扛长枪的,把父亲拷走了。这一次可不是关金的告密,而是父亲救过的日本佬的孩子,为了报恩托人来找父亲,父亲在日本军营的一切细节于是全部公之于众,父亲“汉奸”的罪名这次是坐实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是被五花大绑回来的,大光头的父亲回来的样子太丢脸了,甚至我都没有、或者说我不想认出来。开完批斗会,关金押着父亲游完街后,把父亲送了回来,“村里服刑,必须接受我管制”,“今后他必须听我的”,关金这样对爷爷宣布(《日本佬》第15页)。父亲真正的厄运开始了。
很显然,麦家这次瞄准的是革命专政的问题。父亲因为做了一件救人的善事而被组织、被人民、被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了,麦家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地写了专政后父亲的形象:
父亲回来的样子太丢脸了!他被剃成大光头,胸前挂一块大木牌子,上面打着红叉叉,还写着什么“反革命分子”、“汉奸”、“卖国贼”。
从我的位置看过去,大光头没有手,只有一只肩膀,肩膀上勒着一根粗麻绳。手其实被反剪在背后。我也看不到他身子,因为大木牌把他身子全挡掉了,只露出膝盖以下的半条小腿。但很快小腿也看不到,因为押他的人用枪托砸他膝窝子,他不得不跪下去。
父亲什么都变了,头发光了,两颗门牙不见了,两只耳朵出奇的大,两个腮帮子深深地凹进去,像两个陷阱,可以填两个鸡蛋……(《日本佬》第14-15页)
那个壮实如牛、脾气火爆、逞强好胜的父亲,不见了。当回来后的父亲和爷爷长谈时,麦家故意让父亲的语言突然变得异常的干瘪、简短、无力,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在嗫嗫喏喏地不停辩白,那个张口闭口“狗日的”、老子天下第一、在村里说话掷地有声的汉子,也不见了。当父亲宽慰爷爷,“我改造好了就好了”,父亲对革命的天真与无知,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可怜孩子。还是爷爷看得清楚:“这回过不了了,天塌下来了,我们翻不了身了”。所以麦家把专政后的父亲写得越猥琐、越狼狈、越弱小、越可怜,与专政前父亲的形象反差越大,就越能说明走入极端的革命运动对人的彻底无理与无视,就像老吴告诫父亲的:“让你做牛鬼蛇神”,但就是“做不了人”。可奇怪的是,麦家对公社武装部科长、对老吴的描写却都是十分客气的,不像把关金写得像一条哈巴狗。麦家通过爷爷的口写老吴,老吴对关金的警告、对父亲的善意,都让人觉得“这个领导不错,眉毛里有颗痣,是个善人”。(《日本佬》第12页)更重要的,父亲第一次调查后的清白证明,就是老吴给开的,而且后来应爷爷的要求,又给原样开了一份,一份爷爷收着,一份爷爷拿在村里贴了大字报,爷爷说老吴不仅没抽他的烟,还给自己递了两根,“真是好领导”。写武装部科长,看到爷爷说父亲有五个崽并阻拦公社拷人,科长反而软了口气,放下枪说:“老人家,你不要害他,你儿子犯了大罪,你不要再给他加罪,罪加一等,命都要没有。”(《日本佬》第14页)后来考虑到父亲上有老下有小,就不去县里坐班房,安排在村里服刑。但就是这个科长、就是这个老吴,而不是关金,拷走了父亲,专政了父亲。麦家为什么写得一点都不恨呢,甚至还写得很有人情味、很有好感呢?麦家不是糊涂了,相反十分清醒,因为他想批判的并不是执行专政制度的人,而是专政制度本身。在这个制度面前,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逾越,否则,下一个被专政的人可能就是科长,或者老吴自己。所以老吴才不断地对父亲解释:“我今天不是代表个人,而是组织”,“不是我专政你,是组织,是人民,是无产阶级革命”。(《日本佬》第11页)不是人心自己变了,而是制度让人掩藏起了自己的真心,伪装起来,是制度造成了人的扭曲,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或者说“集体抽风”(陶东风语)。就像《受活》的城里人因为受活人绝术团的表演抽风,《日本佬》的村里人是因为批斗的好戏上场抽风,而且像汛期的鱼一样,一拨一拨地抽。但有意思的是,这场批斗会进入高潮的场面,麦家却用自己从姑父的肩膀上飞走了,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省了。麦家是聪明的。这样,用爷爷和父亲再狡猾的生存智慧也瞒不过组织雪亮的眼睛,来说明个人在政治运动前的无能为力;用只是“我”没听见、“我”没看见,来暗示更加暴力血腥的武装批斗将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处热火朝天地进行;用温情的科长和老吴,来反比无情的具体化为批斗、游街等一系列暴力行为的政治运动本身,麦家写得不露声色,而就在这不露声色中完成了批判。
四、爷爷和“不肖子父亲”
当父亲因为救日本佬的孩子东窗事发之后,当父亲被作为“黑五类”批斗游街之后,爷爷和父亲之间的第四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原本很不错,爷爷非常支持父亲,父亲常常在村里耍日本佬脾气,爷爷支持他;父亲打关金,爷爷支持他;父亲因为我觉得“小鬼子”绰号不错给了我一巴掌,爷爷支持他,而且还加了一巴掌。但这一次,当父亲救了一个日本佬的孩子,爷爷却没有支持他。被关金押回家后,爷爷和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父亲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爷爷。对话是在父亲的辩解和爷爷的斥骂中交替进行的:父亲说自己为了活命不得不在日本人手下养马、养狗,不得不救日本人的孩子,爷爷骂他:“我真替你害臊,什么好事不做去做这缺德事,咱们村里一只狗都知道”;父亲说那个日本人的孩子托人找我,托的人揭发了我,爷爷说:“揭发得好,我要早知道也会揭发你的”;父亲说我改造好就好了,爷爷骂:“好个屁!……今后我们都做不成人了!……还不如死,早死早好”;父亲说你吃口茶吧,爷爷把杯子摔在地上,骂:“还吃什么屁茶,你吃吧,就像狗一样去舔”。(《日本佬》第16-17页)爷爷真的是气急了,真的是不肯原谅父亲了,气得一个人坐在堂前屋祖爷爷、祖奶奶的遗像前幽幽地哭,像一只小猫在寻妈妈,气得像曾经杀鱼一样,光着身子在天井里摔打、翻滚、翻来覆去、死死挣扎,杀死了自己。麦家还是有英雄情结的,他把爷爷的死也写得轰轰烈烈、悲壮无比。但“我”吓坏了,“我感到我们家的整栋房子都在摇晃了”。
这似乎是在讨论人性,甚至似乎还可以上升到中日民族矛盾的高度。被鬼子抓进军营做工,是有尊严地死去,还是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落水的日本佬孩子面前,是做残忍的“英雄”,还是做善良的“汉奸”?这的确是个大问题。爷爷和父亲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所以决绝地选择喝农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否认,爷爷和父亲的确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坚持家族国族的尊严高于一切、包括生命,爷爷说,隔壁村,有个女的,被鬼子强奸,生了个小鬼子,要说也是她的骨肉,可她硬是把他活活掐死,丢进粪坑里:“这才叫有骨气!有种!解恨!”一种认为为了活命可以有些暂时的变通,父亲说,怎么跑?跑多远都追得上,追上就是死!不救他,那我也得死。(《日本佬》第16页)一个十几岁的普通的中国孩子,遇到了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我们回答不了,麦家也回答不了,所以,麦家最后只能无奈地选择让其中的一方死去,来快点结束这个争论,但争论停息了,问题依然还在。其实,“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是佛家的古训吗,见义勇为,不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德吗?这些本来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呀,那它为什么还是成为了一个问题,成为了爷爷跨不过去的坎?我们完全可以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往后移,来回视这个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是在今天,那个日本佬的孩子来找父亲,父亲不仅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酬谢金,而且可以马上拥有让人羡慕的海外关系,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救人的善举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并受到人们尊敬。但关键是,父亲不是活在今天,而是活在昨天,活在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所以,一切全都变了,父亲不仅酬谢金被全部没收,甚至还搭上了老酒、米酒、鸡蛋、大公鸡、老麻鸭、包括那只闹钟,反正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父亲不仅没有因为洋亲受到羡慕,反而被打为“黑五类”最最黑的那类;父亲不仅没有因为救人赢得尊重,反而被人们唾弃、批斗,任人骑,遭人骂,更重要的是搭上了爷爷的性命。这么看,麦家最想说的,还是时代和制度的问题,或者说,麦家所设计的第四组矛盾其实还是一个时代性矛盾、政治性矛盾。麦家想批评的还是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对人的影响,还是对革命专政的进一步指责,爷爷是干净地死去了,但父亲还要污秽地活着,而且在“坏分子”关金手里污秽地活着(公社的宽大处理反而带来的是父亲更加失去尊严、更加痛不欲生的生活,这个悖论完全可以用于指责制度本身的漏洞,但更适合用来解释一个“好制度”为何从上到下最后变成了“坏政策”),想想就觉得可怕。在这个时代,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壮丁——不幸,被关金当作专和他作对的刁民——不良,打成了“黑五类”最最黑的——不忠,逼死了爷爷——不孝。就这样,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把父亲变成了不幸、不良、不忠、不孝的“四不之人”,这才是最残忍的“变形”。这是战争没有做到的事,但革命做到了。这样,与麦家自己的或者其他同类抗战题材的作品相比,麦家由对英雄哲学、普遍人性的讨论具体到了中国政治运动对普通人的钳制,由对人的对抗命运的现象悲歌追究到了革命政治悲剧的本质和原因。麦家,中国化地深刻了。
五、自传抑或其他
不得不说,麦家的语言还是那样坚韧、利落、有嚼头,不拖泥带水,又有浙西北乡下的泥土气。当麦家用他一贯的锋利、干脆的语言把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比一个更让人喘不过气的矛盾毫不间歇地、一个紧接一个密集地抛出来的时候,阅读的阻力就有了,思考的压力就有了,于是小说的力量也在这个接受的瞬间有了。在麦家笔下,一个矛盾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结束,而是带来另一个更大的矛盾的发生,因为被鬼子放了,所以有了“日本佬”的绰号;因为“日本佬”的脾气,所以才会和关金发生纠纷;因为与关金的斗智斗勇,所以加速了革命专政的到来;因为革命的批斗和回村监管,所以视尊严为天的爷爷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从父亲的侥幸获得自由到最后父亲从肉体和精神上再次完全失去自由,从一家人的平静的生活到最后爷爷失去生命的家的摇晃与碎裂,在逆转、在行进、在爬坡中,父亲的四个身份在纠缠、在扭斗、在密谋,小说就这样慢慢起潮,最终掀起思想的巨浪。其实,在这四组矛盾之外,麦家还像蛛网一样密布了很多小的矛盾,比如爷爷、父亲和我之间关于“小鬼子”绰号的矛盾,爷爷、父亲和母亲之间关于“日本佬脾气”的矛盾,外婆和我们一家的矛盾,班主任和我的矛盾,村民和我们家的矛盾,等等。这么多、这么复杂的矛盾,是可以用一个中篇、甚至长篇来写的,但麦家却把它挤压到一个不到两万字的短篇写出来了,而且从容不迫地聊天一样地写出来了,一点也不觉得牵强,一点也不觉得抽象,一点也不觉得累赘,就像王安忆对《风声》的评价:“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但并不因此而损失事物的生动性,因此逻辑自有其形象感,……这是一条狭路,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但正因为狭,于是直向纵深处,就像刀锋。”[8]麦家对叙事线索的累进铺展,对叙事节奏的精准调控,对叙事空间的大手笔排布,就这样自己跑出来了,而小说就此沉甸甸、硬梆梆的。
“父亲”和“我”的遭遇,是不能不让人想到麦家同样孤独的童年,是不能不让人进行相关的互文性阅读的。麦家的家在浙江富阳大源镇蒋家门口村,小说中的“我”,父亲是“反革命”、是“坏分子”,现实中的麦家,父亲是“右派”、外公是“地主”,黑五类当中,也是占了两类。麦家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份和阶级的时代,……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9]3“我”和麦家同样都是因为成分和阶级,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羞愧”,像被丢进“黑黑的冰窟里”,又像是在“熊熊烈火中”,恨不得立即死掉。小说中,“我”对那个来自上海的知青班主任没有一丝好感,就是在她一阵振臂高呼的口号声中,父亲被押上了批斗的戏台。生活中的麦家,同样有一段关于老师的黑暗记忆: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是在课堂上!
这个狗日的!(《非虚构的我》第3页)
麦家是有多难过呀,对这个老师是有多恨啊,才会骂他狗日的!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所以,小说中的“我”愤怒得失去理性,“像浑身长满刀子,恨不得杀死身边所有人,包括父亲,包括我们班主任、校长、同学、全部人,一个不剩,通通死光”。(《日本佬》第15页)小说中的“我”,爷爷说是“洞里猫”,生活中的麦家,母亲也取了一个绰号——“洞里猫”。出身,经历,连绰号也一模一样,让人不想把这篇小说当作麦家的自传都不行。真是这样吗?的确,麦家的个人经历为小说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让小说写得更加有生活感、有亲历感。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果真的把这篇小说看成麦家童年日记的简单整理,那就太小瞧麦家了。在麦家的《致父信》中,有一个和小说形似但实际完全不同的细节:12岁那年,麦家因为同学骂父亲是“反革命”、“四类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骂自己是“狗崽子”、“小黑鬼”、“美帝国主义的跟屁虫”,为了捍卫尊严,一打三。麦家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可父亲却把他当混蛋,当猪狗,“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地扇了我两个大耳光,把我已经受伤的鼻梁都打歪了,鼻血顿时像割开喉咙的鸡血一样喷出来,流进嘴巴里,我像喝水一样,一口口喝下去都盛不下,往胸脯上流,一直流到裤裆里”。[10]但小说是怎么写的呢?小说中的“我”,也是被父亲打了一巴掌,但父亲打“我”的理由正好相反,是因为我觉得“小鬼子”比“小畜生”的绰号更有威风。这完全反过来了,一个是我(麦家)因为争取尊严被打,一个是父亲因为维护尊严打我。所以麦家伤心地写到:
父亲,你怎么会这么狠心!
父亲,你怎么能这样打我!(《致父信》)
于是,麦家变了,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蔫了,废了。他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只跟自己交流,天天写日记,第一篇日记就是发誓以后不再喊爹。麦家说到做到了,直到1993年麦家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家,才做贼似的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声爹。麦家在35岁之前一直是在刻意回避家乡富阳,刻意回避自己的父亲,刻意回避自己不堪回首的欺辱的童年,所以他很少回家,有意走得远远的,南京、西藏、成都,六个省市,就是没有浙江,没有富阳。麦家赢了吗?没有,麦家后悔了,当父亲1999年摔了一跤差点去世,当父亲突然患上老年痴呆,麦家后悔了,后悔回来的太迟,虽然他在2008年调回杭州市文联当专业作家,但一切都太迟了。麦家痛苦地倾诉:
三年里,除了母亲,我陪你说话的时间最多,可你对其他亲人都清醒过、笑过、说过话,就是不给我机会。有一天,你出奇的连续清醒了几个小时,母亲紧急地给我打电话,我紧急地赶回去,想赶在你清醒前看到你,和你说说话,看你对我笑一笑。可就在我进门前几分钟,你突然又回去了,回到那种一成不变的蒙昧状态,见了我毫无表情,一声不吭,像一块石头对着一根木头。(《致父信》)
父亲一直都没有给麦家赎罪的机会,这让麦家痛彻心扉,这让麦家的心中永远都有一种负罪感,一种愧疚感。这种痛与悔,也让麦家得以重新正视自己的童年,正视自己的过去,2012年父亲去世一周年时,麦家写下了《致父信》,2013年,麦家出版了回顾前半生的《非虚构的我》,2015年,麦家发表了这篇《日本佬》。所以说,与其把这篇小说看作是麦家的自传式记录,不如看作是麦家关于自我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麦家知道造成自己和父亲之间永远无法挽回的悲剧性结局,不是因为父亲,而是因为那个只有黑和红两种颜色的时代,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阶级的制度。父亲,只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而我,实际上也是加害者之一。但你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麦家的反思不是受到了卡夫卡或者博尔赫斯的影响呢?也许吧,但卡夫卡讨论的是普遍的现代大工业文明对人的压抑,而麦家讨论的是具体的中国式政治革命对人的影响。至于博尔赫斯,姑且不论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反独裁者,麦家爱读博尔赫斯的1993年,他还是活在对父亲深深的仇恨中呢,哪会反思制度本身!而且,麦家自己也说,“诡秘的叙述”是博尔赫斯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11]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了麦家这一次珍贵的反思,因为,清教徒式完全依靠自我炼狱与煎熬而达到灵魂的内旋式上升,是最难的。麦家是用生离死别,才换来了对历史的正视与反思,那我们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应该回望和正视的部分呢?但愿我们不要像麦家一样,用那么惨痛的代价,才明白了那么明了的道理。这,正是麦家在小说之外要告诉我们的大彻大悟,这,也正是这篇小说文本之外的价值。
六、谁才是日本佬
现在,我们就来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谁才是日本佬?
鬼子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日本佬”,但“日本佬”显然也是个代名词。爷爷说“心像才是真像”,“关金才是真正的日本佬,心肠大大的坏。”(《日本佬》第13页)是啊,关金心思像日本佬,蛇蝎心肠,不像人,像鬼,老是害人。不仅我们家怕他,村里人都畏惧他(请注意麦家的用词,是出于对暴力的“畏惧”而不是出于对能力的“敬畏”、“尊重”或其他)。麦家虽然承认绝大部分人的坏是制度使然,并非本性,但关金是个例外。麦家厌恶像关金这样的把持乡村基层政权的“坏分子”,麦家童年的痛主要也就是身边这些离得最近的人给的,所以关金当然就是仅次于真鬼子的排名第二的“日本佬”。但只有关金吗?那个热衷于在每一次批斗会上带头喊口号的班主任,那个骂父亲“反革命”、“四类分子”、骂自己“狗崽子”、“小黑鬼”的同学,那个在课堂上公开羞辱我(麦家)的狗日的老师,那个为了清白掐死自己孩子的隔壁村的女的,那个邪恶地想要杀死父亲的小说中的“我”,那个一拨一拨抽风式的观赏批斗会的村民,甚至那个深深伤害了父亲的麦家自己,是不是都或多或少有“日本佬”的影子。然而,是谁让我们变成了“日本佬”?是——制度/运动?原来,曾经的错误的极端的非人的残暴的专政运动,才是隐藏最深、最大的“日本佬”!
这样看,麦家写的不是战争,而是革命。写的不是战争的影响,而是革命的后果。写的不是外部侵略的危害,而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政治运动的可悲。
这样看,麦家写的不是“我”,而是每一个“我们”。写的不是“日本佬”,而是我们“中国人”。写的不是日本佬式的人,而是日本佬式的制度本身。
这样看,麦家在2015或2012年之前,写的是刻意逃离历史后威风的、神秘的、成功的、洗白的特情生活;2015或2012年之后,写的是重新反思童年屈辱的、孤独的、落魄的、黑暗的“狗崽子”生活的心灵质询。前者是在努力探索“人的高度”,后者是在苦苦思索是什么一种东西能将高尚的人也随意踩在脚下?前者是用“魔术的方式再现”,后者是用笨拙的现实主义书写。两者都抵达真实,但我更喜欢后者。
麦家说:“文学的创新决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经验,而是要在公共经验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12]麦家还说:“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不是写生活,而是开创生活,是创世记”。[1]麦家的创造性在于:他把战争的影子、政治运动的影子、自己的影子,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形成了更加庞大、更加幽暗、更加压抑、也更加瑰异的“重影”。
这样看,短篇《日本佬》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是一块只属于麦家的丛林,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创世记,也是麦家的一次新生。这指题材上的,也指精神上的。
注释:
①反映当代农村基层政治的作品,如杨少衡的《村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周晶斗的《沦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
[1]麦家.短篇小说应开创生活[N].文艺报,2014-12-08.
[2]麦家.日本佬[J].人民文学,2015(3).
[3](英)柯鲁克夫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M].安强,高建译.北京出版社,1982 .
[4]罗汉平.土地改革运动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5]葛剑雄整理.谭其骧日记选(之一)[J].史学理论研究,1996(1).
[6]于建嵘.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J].战略与管理,2003(5).
[7]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J].中 国农史,2003(2).
[8]麦家,季亚娅.小说写作之“密”[EB/OL].中国文学网,http:// 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73367.
[9]麦家.非虚构的我[M].花城出版社,2013.
[10]麦家.致父信[N].南方周末,2013-12-06.
[11]麦家.博尔赫斯和我[J].青年作家,2007(1).
[12]麦家.文学的创新[J].文艺争鸣,2008(2).
(责任编辑:杨立民)
I207.42
A
CN61-1487-(2016)03-0045-06
2016年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68)。
许徐(1979-),男,安徽六安人,合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