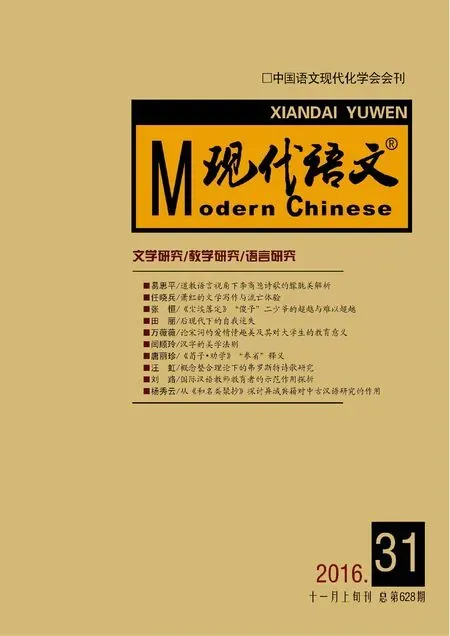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陈 莹
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陈 莹
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既有现代的一面,同时又深深打上了传统的印记,呈现出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复杂风貌。主要表现在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以及两性关系建构上的男性眼光和价值标准。诗人在爱情观上所表现出的调和色彩,反映出当代女性写作想要真正超越男权文化的羁绊,建构女性自我认同的主体意识,依然任重道远。
舒婷 爱情诗 女性意识
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舒婷的重要贡献在于她的诗接续了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这一在50-70年代受到压制的线索。与同时代的其他朦胧诗人相比,“舒婷更偏重于爱情题材的写作,在对真诚爱情的呼唤中融入理想,展露出一种强烈的女性独立的意识”[1](P268)。纵观她的爱情诗,其女性意识既有现代的一面,同时又深深打上了传统的印记,在对两性形象及其关系的探寻上,呈现出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复杂风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留在读者记忆中的是舒婷作为抒情诗人所传达出的一种新的爱情观,而对其中所包含的矛盾性重视不够。这种美化与简化的解读实际上遮蔽了舒婷诗歌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完整的舒婷的认知。当朦胧诗人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甚至连舒婷本人也开始转向散文写作时,重读舒婷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诗人的意义,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女性写作困境与出路的重要话题。
一、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之一,舒婷的诗歌集中表达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人的渴求与希望。在文革政治乌托邦理想的驱动下,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铁姑娘”“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巾帼英雄,女性的性别特征荡然无存,女性和男性一样陷入到政治的狂热之中,成为政治呐喊的动物。与此同时,人性、人情等被视为文学表现的禁区,爱情则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受到猛烈批判,甚至结婚也要在革命的名义下结成“革命伴侣”。然而,政治的压抑并不能抑制人们对爱情的渴求,反而使得这一渴求更为强烈。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舒婷在政治刚开始解冻之时,就以朦胧诗的形式发出了爱情的宣言。
对女性而言,爱情不仅意味着女人源自天性的本能追求,而且是女人确证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舒婷独特的艺术个性就在于她很少以理性的姿态正面介入现实世界,而是以自我情感为表现对象,以女性独特的情绪体验辐射外部世界,呈现个人心灵对生活溶解的秘密”[2](P143)。这一独特的艺术个性,使得舒婷的爱情诗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象征性,其情感的抒发明显带有个人和时代双重复合的特征。
代表作《致橡树》作为新时代的爱情宣言书,无疑成为新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作品。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歌表达了一种以独立的人格为基础的新的爱情观念,向爱情这个古老的诗歌题材,灌注了一种新的人生理想。”[3](P141)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要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里,诗人对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强调,实际上揭示出了现代爱情的实质,因为“爱是在保持自己尊严和个性的前提下的感情交流的行为。倘若失掉了个性和尊严,也必然失掉爱。”[4](P9)这是对传统的依附型和奉献型爱情观的否定,成为新时期文学女性意识觉醒的先声。与此同时,诗人在强调人格独立的同时,并没有刻意突出两性之间的某种对立,而是描绘了一幅双方在共同的人生理想追求中所达成的心灵默契的温馨画面:“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该诗的新颖之处,在于把男女双方有共同的事业追求作为现代爱情的基础:“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强调女性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男女性别上差异的一面:“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诗人虽然拒绝做“攀援的凌霄花”,但仍然选择要有“红硕的花朵”。这一选择显示出诗人对中国传统女性性别特征的认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花”来比喻女性自古有之,在文学作品中更是习以为常。由此可见,舒婷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既有传统女性温柔多情的一面,又具有现代女性自尊自强的一面,是集古典美和现代美为一炉的新时代女性。
但这种熔铸是艰难的,一方面要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现代理想,这就使得舒婷的探索主要局限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对传统道德的坚守是其诗歌的主基调。比如在她的诗歌里,读者可以经常发现她对诸如夫唱妇随、温柔贤淑、温柔多情等传统女性品格的认可与赞赏,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强女阴柔”等传统观念的认可。因此,在《神女峰》中有“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所表现出的对男性皈依的向往;在《赠》中有“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所表现出的对爱的牺牲奉献;在《春夜》中有“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所表现出的对爱人的亲密依附;在《双桅船》中有“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所表现出的对两情相悦心灵相通的渴望。这表明舒婷在价值取向上,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留恋和皈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重复着五四时期关于“爱”和“人性”的主题,明显带有80年代文学启蒙的色彩。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致橡树》在女性意识和个性意识这两个层面上阐述了诗人对人的关怀,就带有这种明显的启蒙意义。这是一首爱情诗,历来的爱情诗多柔婉缠绵,本诗却一反传统情诗的风格,奏出了现代女性尊重自身价值、保持独立人格、弘扬自我追求的时代强音。即女性应当和丈夫一样,以自己事业的成就立足社会,双方应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承担逆境的考验,共同分享幸福与成功。”[5](P194)这就意味着,舒婷这首受到广为赞誉的诗歌,在总体思想倾向上依然没有超越80年代思想启蒙的限度。
从总体上看,舒婷爱情诗中女性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显示出诗人对父权话语下女性社会角色和分工的认同,本质上仍然是“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同样能够办到”的另一种表达,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彻底。虽然诗人在《神女峰》中对“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在《惠安女子》中对女性品行的“被看”悲剧有深沉的反思;在《致橡树》极力宣传爱情中男女人格的平等,但诗人并没有全面否定传统的女性行为规范,只是对诸如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贵妻荣等带有女性歧视色彩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与坚决背弃。
究其原因在于朦胧诗兴盛的80年代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受制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在“传统与现代,与旧的伦理道德之间,舒婷进退徘徊,对传统伦理和道德理性的反叛并不坚决彻底,终于忍不住流露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妥协和回归。”[6](P62)这就决定了舒婷笔下的女性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现代语境中的古典少女情怀,其笔下的女性诉说总是保持着一种古典式的温婉与柔情,内心深处对男性的依恋之情不时流露于笔端。从这个意义上看,舒婷诗歌的反叛是有限的。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发前人所未发,发前人之不敢发,舒婷的探索依然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苛求作者,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她的作品,而是要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背景中去考察,“必须把它与那些同它具有相同性质和效用的东西加以比较”[7](P275),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我们就会产生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
二、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
女性意识不仅关涉到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觉醒,而且关涉到女性眼中男性形象的建构。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及其创作,被中国理论界和作家广为认识和接收,并大量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与创作中。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作家虽然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中国特色更为明显:“她们在反对阳性中心,而我们在寻找阴性的世界,一个愿意向阳性退赔若干领土的阴性国度。中国的女性在经历双重幻灭后正面对困惑,有些不知所措。她们既经历了普遍的偶像幻灭,又经历着特殊的对男性偶像的幻灭。当西方妇女在大煞男子汉的威风,破骑士对妇女的‘礼貌’时,中国妇女从劳动服里退出来后要求受到特殊的女性待遇,包括‘骑士’‘风度’对妇女的尊敬和怜爱。她们在寻找真正的男子汉,她们想做真正的东方女性。当她们失望的时候,她们经历了对男性偶像的幻灭感。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艺术(包括电影)里就是召唤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8](P5-6)对舒婷而言,虽然她在散文中声称“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9](P101),但她的创作中却又时时表现出女权主义的色彩。这不仅表现在她对诸如妇女命运、爱情平等的关注上,而且表现在对阳刚美和阴柔美的召唤上,这一追求集中体现在他笔下的男性形象身上。
舒婷笔下的男性大都以她认识的北方青年诗友为原型,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早醒者和孤独者。社会和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时牵动他们敏感的心灵,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不甘沉沦的传统士大夫品格,以及儿女情长、重情重义、善解人意、尊重女性、呵护女性等现代好男人品格,是集阳刚美和阴柔美于一体的理想男性形象。
首先,在外表上,理想的男性形象要有阳刚之美。在诗歌中,诗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传统男性阳刚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兄弟,我在这儿》中有这样的描述:“你原属于太阳∕属于草原、堤岸、黑宝石的眼眸∕属于道路、火把、相扶持的手∕你是战士∕你的生命铿锵有声∕钟一样将阴影/从人心震落∕风正踏着陌生的步子走开”。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男性阳刚的外表,但整首诗的意象都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男性阳刚之美的欣赏与肯定,这种美是女性所没有的。这里的“你”,属于“草原”、属于“堤岸”,而“草原”与“堤岸”都具有宽广、伟岸的意象;“你”属于“道路”、属于“火把”,道路是绵长的,具有男人才有的厚重与执着,火把是热情的,具有男人才有的热血与方刚;“你”是“战士”,具有战士的坚毅与勇敢,生命“铿锵有声”,连风也“踏着陌生的脚步躲开”。这表明诗人理想中的男性要刚强不屈,凛然无畏,充满了雄性的伟力与昂扬的斗志。
其次,在内涵上,理想的男性还须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一般人眼中,多愁善感属于女性,男儿有泪不轻弹,对男人而言,理想和事业高于一切。舒婷的爱情诗颠覆了文革时期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男性形象,突出了现代男性内心深处柔弱的一面。诗人并不认为多愁善感仅仅属于女性,理想的男性也难免儿女情长,他们都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以及个人情感世界的律动都不时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泛起阵阵感情的涟漪。在《落叶》中,舒婷刻画了这样一位林黛玉式的多情诗人。这个“你”“轻轻叹着气”,究其原因“既不因为惆怅/也不仅仅是忧郁”,而是因为在送我回家的路上,“那落叶在风的撺掇下/所传达给我们的/那一种情绪”。显然,诗人笔下的男主人像林黛玉一样,是一位感情细腻,多愁善感的诗人,对岁月流逝、青春渐远而事业无成,有着最深、最痛苦的心灵体验。与此同时,舒婷在诗歌中还表现出对男性在理想追求过程中的精神痛苦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在《童话诗人》里,舒婷以诗人顾城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个向往美好,一意孤行寻找自己乌托邦世界的男人形象:“你相信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新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这个男人虽然看到了“病树”“颓墙”般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却只是一味地逃避,只敢相信自己编写的童话,试图用童话里“幽蓝的花”般美丽的语言来隔开他眼前所有的丑陋,永远蜗居在早就产生怀疑的童话般的精神家园里。如果说童话诗人只是在内心让舒婷女性柔软的心房充满感伤的话,《赠》里的男人形象则让诗人内心充满着由内而外的悲戚。“我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荡的舷边∕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地∕深藏着你的思想”。这样的男人身无他物,在寒冷的天气里,只能自己给自己保暖,这不仅给自己冰冷的身躯,也给自己挨冻的心灵。可是,就是这样,“我为你举手加额∕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说春洪又漫过了∕你的堤岸”。在寒冷中,他没有屈服于寒风的恣虐,而是徜徉在书的海洋中,和他人一起分享觉醒的快乐。由此看来,这个男人身上有着古代困顿书生的一切特征:不屈于逆境,在逆境中吸取知识,徜徉书海,能独自舔抚自己的忧伤。
总之,舒婷爱情诗中的男性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文学中自屈原以来的潦倒文人和落魄文人的诗歌精神。他们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思想,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同时又有一颗敏感而柔弱的内心,体现出一种阴柔美,阳刚精神与落拓情怀混杂于一体,散发出80年代特有的感伤气息。
三、两性关系建构上的男性眼光和价值标准
女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两性关系。爱情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最能体现两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及社会处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性和女性关系常见的比喻是阴/阳,树/藤,磐石/蒲苇,等等,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两性关系上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女性不仅在人身关系上依附男性,而且女性价值往往也只能通过男性表现出来。因而相夫教子成了女性生活的主要内容,夫唱妇随成了女性言行的基本准则,夫荣妻贵成了女性人生的最高理想。虽然这一传统观点,在五四时期的第一次女性写作高潮中受到全面质疑,提出了爱情婚姻中女性作为人的权利的要求,但随即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迷茫。80年代的女作家接过了五四启蒙的旗帜,她们试图突破男性中心意识的重围,努力建构女性主体。但遗憾的是,“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形成足以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而且,很多作品虽然在话语方式和叙事风格上与传统话语体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真正控制话语权的男性中心观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即便是被女性作家自身无数次颂扬的爱情,也无不以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作为取舍的依据。”[10](P64)这一遗憾在舒婷的爱情诗中同样存在。
一方面,舒婷站在女性觉醒的角度对男性中心主义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主张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在《致橡树》中,她宣称“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来炫耀自己”,而是要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枝木棉∕以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她明确提出,女性要求和男性一样在爱情中有相应的地位,而不能只是作为男人的陪衬和附属。另一方面,她对男性中心主义又不是绝对否定,而是潜意识里承认男性性别上的优势,认同传统性别文化下的女性价值取向标准。在《致橡树》中,诗人并不是要求女性要像男人一样有树的形象,她只是要求以木棉的姿态站在深爱的男人旁边。虽然木棉也有挺立的形象,可它毕竟不能像树一样遮挡狂风暴雨。可见,诗人在内心深处还是认同女性的价值只有通过男性才能显示出来这一传统的世俗观念。《神女峰》“表现了对女性长期受压抑的愤怒和悲哀”[11](P191),进而发出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爱情宣言。这一源自女性生命体验的呼唤,虽然震撼人心,但诗人内心深处所流露出的依然是女性潜意识深处对男性的依附。也就是说,诗人虽然表面上反对女性对男性做出牺牲,号召女性大胆追求现世的幸福,但其潜台词是提醒女性要珍视自己的牺牲,不要把这种奉献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让男性忽视了自己的奉献。“美丽的忧伤”,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源远流长的闺怨诗的现代翻版,“就此而言,舒婷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女性自觉,她的女性意识是在某种承认既定男权中心的社会秩序里所抒发的女性人格与生命的需求,女性与时代同构。”[12](P126)据此而言,舒婷在对现代两性关系的建构与呼唤中,始终没有摆脱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的潜在影响。
舒婷爱情诗在爱情观上所表现出的调和色彩,既源自于传统对女性的性别角色的规范,也来自于女性传统心理的积淀。承载着千年性别枷锁的现代女性,虽然获得了在法律保障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平等是表面上的平等,她们并没有获得在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女性言说的话语方式和文化资源都是男权性的。舒婷的个案表明,中国当代女性写作要想真正超越男权文化的藩篱,建构女性自我认同的主体意识,依然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这正是今天我们重读舒婷的意义所在。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刘福堂译,[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刘树元主编:《中国现当代诗歌赏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杜昆:《知识分子的荣与衰:论舒婷的创作转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7][美]勒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8]郑敏:《女性诗歌:解放的梦幻》,诗刊,1989年,第6期。
[9]舒婷:《露珠里的“诗想”》,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赵妍:《女性主义视野下的80年代海峡两岸爱情诗——以舒婷、席慕蓉的诗歌为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
[1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晶晶:《从“拯救”到“彻悟”——舒婷、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嬗变》,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
(陈莹 贵州贵阳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25)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创新及其文本阐释”,项目编号:[14SSD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