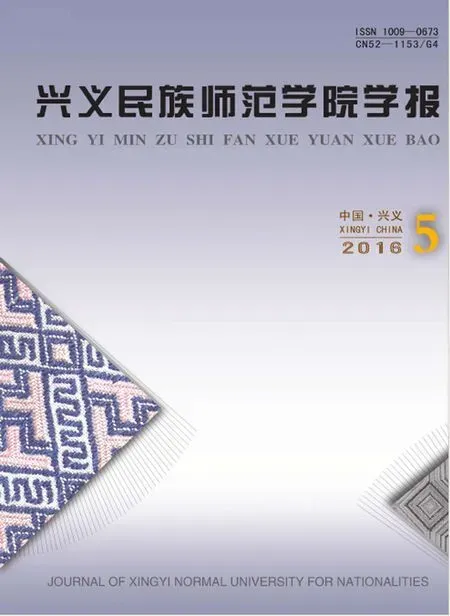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困境启示
——基于《马背上的法庭》的叙事
杨振宁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困境启示
——基于《马背上的法庭》的叙事
杨振宁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习惯与法律之博弈由来已久,在学界的讨论也是方兴未艾,大多学者都从法律科学的形成及其体制性来论述。然而,对于习惯与法律之间,不应该局限于此,应该从更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去审视。《马背上的法庭》这部影片,从文学角度生动地刻画出了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割裂,一系列案列的审判过程,凸显了乡民们对于习惯的坚守和对于国家法律的无知、无畏,一次次的展示出民族地区传统习惯与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的灰色幽默。故,要破解二者之间的隔阂,先要辨明其缘由,就是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国家法律与民间传统习惯还存在着二元格局,影片给出的启示就是要二者互相交融,方可和谐互利,这也是我国一体多元的社会构架之内涵。
少数民族;司法;社会学;叙事
Abstract:The game between custom and law has a long history,so it i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s well,where a majority of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m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legal science and its system.However,the discussion about custom and law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is,it should be surveyed from the broade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The film of Courthouse on Horseback depicts vividly the current split between the Chinese minority traditional custom and stat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in which,with a series of case trial,it highlights the villagers’persistence in the traditional custom and their ignorance and fearless to the state laws,and it also show out repeatly the black humor in the ethnic custom and the law regulations of national level.The reason that makes the barrier between them is the sequence pattern of Chinese society,in which national law and folk customs still exist dualistic structure.To crack the barrier between them,the film supply us with the enlightenment that is to blend them with each other,and make mutual harmony,which is our country’s connotation of a pluralistic social framework.
Key words:ethnic minority;judicial;sociology
《马背上的法庭》取材于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杂居之地的几次法庭审判活动,比起作为影片主题的法律审判戏份,导演对于人物内心及外在条件的刻画更加深刻,同时也是给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法制生活的一次写实,看后发人深省。该影片从开始到结束都弥漫着神秘的沉重感,是文学作品揭示社会生活的一次巡礼,通过讲述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的困境,揭示了在当代中国一体多元格局下,国家层面法律规则与地方传统习惯的博弈的主题。
一、引
法律与生活的关系无需多言,马克思对于习惯权利的论述,在其《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表述:捡枯枝、采野果、拾麦穗,这是自古以来为占有者所允许,因此就产生了孩童的习惯权利。[1]由此看出,合理的立法活动应该是一种揭示客观规律的活动,立法者的任务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思的现行法律中,而不是制造和发明法律,应该在于表述一种社会规律。在法理上,“法无禁止即自由”所包含的实质也就是承认了对于人们习惯权利的尊重。埃里克森指出,是规范,而不是法律规制,才是权利的真正来源。这种规范源于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博弈,最好的法律应该是这种社会群体长期博弈中产生的规范的承认和演化,界定权利的这个“法律”其实未必是真正的正式的制定法,而更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博弈形成的规范;或者说有效的、好的法律其实就是符合这些规范的,或者是对这些规范的官方表达。[2]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秩序演化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的二元观,而个人与内部规则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都存在一种互动的联系,因此两种秩序又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个人、组织及内部规则之间的复杂互动联系构成社会演进的原动力。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和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的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和居民的家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秩序有关。应该从所有这些因素去考察法律。德国学者耶塞克认为:任何人不得仅仅根据习惯法受到处罚,并且,对于行为人有利的习惯法,例如建立新的合法化事由,则是允许的。[3]耶塞克的思想,则从法律规范的法学理论层面来释义:法律规则的功能之一,应该是为人类利益做最基本的维护。
二、一体多元的法律生态叙事
为了细腻表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困境,影片中选择的案例也是独具匠心,情节安排由低到高,循序渐进。
1.民族地区纠纷写实。第一个案件是妯娌矛盾,因一个价值五元的泡菜坛子引起,而根源在贫穷。其实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不但农民收入低下,而且,政府财政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全国发达地区,也就意味着:担负国家审判职责的法院,其办公条件自然十分艰苦,该案可以说是一个介绍当地的社会司法环境的铺垫。
第二个案子引人入胜,在当代社会的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多元文化日益交汇的环境下,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尚且保有一些传统习惯,案中原告家的“罐罐山”即其祖坟被拱了,在当地属于一件大事,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此习惯,我国《宪法》第四条就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法条里面一个具体问题是:风俗习惯的定义和范围是什么?由于风俗习惯缺少像法律一样有明确的制定和颁布制度,显得相对抽象和模糊,由此说开,很多种传统风俗习惯都可以纳入《宪法》保护范围,但是其中有的风俗习惯不一定有积极意义,有的甚至是恶俗,如某些地方有“配阴婚”的风俗,[4]这也奠定了差序格局下的价值观念的冲突。
我国目前已经识别的民族有56个,还有的人群尚未识别[5],千年的族群繁衍,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各族传统文化,包括维系着各个族群生存发展的形式多样的传统习惯,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其个体间具有相当多的相似性的习性,传统习惯在族群里具有强大的道德与规范效力,被族群普遍的认可。在各个少数民族社群中,都有着扎根于该民族的一套沿用千百年的习惯规范,苏力教授对此问题研究十分精透,他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互相交往和行为[6]。
第三个案例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写,一个并不复杂的借款法律关系,然而,尽管不复杂,但仍然闹上了法庭,原告主张的理由是其怀疑被告的标的物价值与诉讼标的不符,即被告打算用来抵债的那头猪太小,不值其所借的价值。双方对于权利、义务没有异议,纠纷关键不在程序,而在于实体,让人不禁思考“不患多寡而患不均”的程序正义理念之外,还不能遗忘“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人性基本需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无权无端剥夺他人的生存权,这也是人类作为社会性组织的本质要求。然而,社会的发展存在多样性,个体的存在自然也有差异性,法律文本的规定,是司法机关的职能依据,故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应当承当原价返还原告债务的义务,现实情况却是被告家里最值钱的一头猪,依然不能履行义务,这也是该案启动的原因。其实,在我国,长期以来执行难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与那些“老赖”不同,本案被告家徒四壁,法庭一纸判决,令被告限期履行义务,恐怕又是一张“空头支票”,老冯深谙其情况,自己又一次出钱将被告的猪买下,以原告要求的价格,了结诉讼,自己牵着猪继续上路。离婚案与债务案有相通之处,被告人在地上抓爬干嚎,给人一种无以名状的愤懑与无奈,两案被告其实就是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居民生态的隐喻,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根于物资基础,要求法律要与物质基础相互依存,在一定特殊情况下,执法者应该变通执行,这也是我国法律政策所明确的。该案结果以原告复婚为结果,无奈地从法律程序上结束案件,这样的结果告诉人们,法律不是万能的,追求和谐的路径除了法律还有很多。
作为案例安排的高潮,阿洛岳父姚葛宰羊案可谓浓墨重彩,在阿洛结婚当天,对方来到现场要说法,气氛的反差,给人一种不祥之兆,果然,双方将目光集中到法官身上,原本胸有成竹的村主任姚葛,自然想通过法官的女婿阿洛来说出他是合法的,结果适得其反,老冯也批评其“不懂法”,气的姚葛大骂女婿胳膊往外拐,怒言“退婚”,导致了新郎带着新娘不辞而别。而正是这一行为,使得彝族群众对老冯一行心生怒气,邻村羊的主人说:你们坏了我们彝族的规矩,不再打官司了。
2.民族地区司法资源困境。影片中一个特殊人物——杨阿姨,情节安排意蕴深长。她开篇就知道被领导传递自己被“清退”的消息,按理说,一般情况人此时心情都会波动很大,但杨阿姨很淡然,似乎她知道自己的这一天终究会来临,毕竟作为合同工,随时都等待单位的“清退”,她的出现,其实还有一层含义:杨阿姨是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她是影片要表达的一条暗线——作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代表,在与国家法代表——阿洛的对话中,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老冯跟阿洛说过:杨阿姨走,是为了给你腾出位子……。而就是这个不得不给科班出身的阿洛让位的“合同工”,在和老冯一起共事的几十年里,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到了少数民族村寨开庭,她可以担任法庭翻译,了解各家的具体情况;特别在盗马案中,在老冯和阿洛一筹莫展之际,是她想到了当地的宗教头人,并且通过宗教头人的权威,将马和国徽找到,以至于老冯高兴的无言以对。另外,杨阿姨因为进城而错失了“走婚”机会,致使到了离岗仍然未婚,但是,我们都看得出她对老冯的情义,那种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革命情义,有是多么纯洁、高尚;正如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二者是有着和谐共融的基础的,关键要看决策者如何安排。其中老冯和杨阿姨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个小小的片段,但若仔细品味,却意味深长:老冯是正式国家工作人员,杨阿姨是临时工,在那条他们闭眼都能走通的道上走了30年,最终楞是没有走到一起,难道只是剧情的安排?我国当下在规划进行司法改革,其目标就是提高司法效率,追求公平、正义。在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资源的配置与革新,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资源配置,其首要因素为人才的培养。毋庸置疑,中国55个少数民族,要打造一支有学历,能面对众多的民族文字和语言,以及通晓少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人才队伍至关重要。此外,在司法财力投入上,不但要补清历史“欠债”,需与时俱进,还要加大一定投入,改善司法办公条件,不能回避司法条件对司法效率和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情感的积极作用。苏力教授在《送法下乡》里指出,国家法律要进入到具有相对完备规则文化的社会群体,必须找到二者的契合点,这对于二者来说都是个长期的历程。
全剧看起来是行进中的乡土中国司法现实境遇的一个叙事,山路蜿蜒,众声喧哗,法律要面对各种民间习惯,曲折、尴尬、质疑、冲撞,甚至孤独而行,坠入悬崖……,在这里现代司法体制就像驮在马背上的国徽在颠簸中缓缓向前行。
三、二元规则在差序格局下的博弈
不难看出,《马背上的法庭》不仅可以被视为弘扬三位国家权力行使者——法官对于职责热忱主旋律的教育片,另一面则可以视为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二元冲突范式下的一个叙事文本。
1.二元规则的内在默契。电影的案例选材十分精准贴切,片中的几个镜头值得思考,开篇就是领导与杨阿姨的谈话:意思就是她将在本次庭审之后就要被“清退”[7]。接着就是新人啊洛带东西想多给马主人10元钱被老冯拦下,嘱咐道,凡事得有规矩,今后日子还长,坏了规矩就不好办事了,这一点,有着入乡随俗的潜台词的寓意。到了山道口,老冯用马帮的号子呼唤一声,得知马帮即将到来,便让道等候并且主动打招呼,一看便觉得,老冯是个轻车熟路者,这也是其对往返于此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的画外音。在第二个案子里面,猪拱罐罐(骨灰盒)在当地为大忌,原告将肇事猪绑到法庭现场,此做法原告其实不符合诉讼法规定的,阿洛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然而,老冯看出后面的危机,并及时处理,到执行之时,被告因为家人原因不让原告牵走执行标的物的那头猪,老冯不得不自己动手牵猪执行,以至于晚上阿洛闹情绪说他腰痛活该,并指出,老冯身为国家司法人员,自己不注意现象,别把国徽也贬低了,那时,老冯没有说话,而是与他相伴几十年的搭档杨阿姨喝令阿洛闭嘴,此时,代表国家法的新人阿洛与代表民间习惯法的老冯之间的矛盾已经初现。在剧中出现两次由老冯自己贴钱给当事人的情况,这虽然与程序法无关,但是应该得到启示,包括被盗的马匹,老冯说他赔得起,这不是说他作为法官多有钱,而是现实逼得一个老法官不得不如此。老冯找到国徽十分激动,欲只身进入沼泽地,其不要命的行为被杨阿姨喝止,外人不明问道:那是金银还是铜铁?老冯将摩梭人信奉的菩萨当做比喻,顿时事态转机,众人甚至将自己家门板拆下来铺垫,将国徽“请”了出来,并且还将其供奉高台,举办隆重仪式,与众人瞻仰,从那时起,在当地能与“菩萨”享有同样规格的国徽,对于当地人民有了另一种解读,我们更应该看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通的。
2.二元规则的冲突。就在阿洛结婚当天,其岳父姚葛,该村主任,按照该村规民约将另外一村民的羊杀了,原因是羊吃了姚葛家庄稼,导致双方在婚礼当天出现激烈冲突,于是婚礼现场变成案件审理的“公堂”,姚葛及其村民所定的“村规民约”,其实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在滇西邻居,贵州黔东南许多苗族、侗族村寨都有,作为局部地区的集体“规范”,在该地区范围内通常起到村民自治的作用,早在南朝时期宋代,范晔在《后汉书·邓训传》就有记载:“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如今与国家法出现冲突,如何取舍,这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规定十分相似,这也是影片的高潮所在。该案例中两个问题需要考量;一是其所规定的“村规民约”即使在本村通过大多数人的“民主”表决,那么,对于外村的人是否有约束力?法律的适用范围从属人和属地原则而行使,这也揭示了当今全世界司法的一个问题:法律冲突问题,在国际层面,国际法的有关法律冲突规定解决规则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准据法,从程序上设定了冲突规定。那么,可以推测到其他村也可能有类似的“村规民约”,如果双方规定出现冲突,如何解决?[8]这主要由于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一个程序设定的冲突解决规定,我们似乎看出,在此类冲突的案例中,我们再想为什么国家法律不介入?事实上,上述案例中姚葛所言代表的就是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寨状况,其根源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论述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个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就如西洋外交家在国际回忆里为了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及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在姚葛看来,其世代生活于此,所有的纠纷解决都是依据“村规民约”,如果双方接受则和平相处,如果不接受,正如猪拱“罐罐山”一案,双方所处理的方式就会回到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终极的方式——武力。而反观国家法律,法律的运行过程,其背后就是国家暴力机关作为保障,如此看来,在乡村,其习惯法从产生到执行,都有一套和国家类似的体系,所以,姚葛也就不再去找国家机构来解决了,影片中有此思维者还有一个代表就是,在处理盗马案例中的摩梭法师老太,其认为:盗马人将马归还的行为,已经说明偷盗者有了好的作为,可以原谅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法律上的“返还原物”的权利补救措施,而在刑法中,盗窃犯退赃行为不影响定罪,只有在量刑中作为考量因素。而摩梭法师那里,其考量的因素或许是,规则对于犯错人不仅用于处罚,更应该用于教化。
3.二元规则的互动。送法下乡就是把国家的标准送到乡土社会,让乡土社会的人按照新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体现出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权威。在中国老百姓中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自古对于官方的法律制度是很难主动去了解把握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乡土社会的人们没有积极地学习或者没有学会这些新的法律标准的原动力,再加上也没有合适的学习条件,而国家司法机关就假设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法律知识;仅仅因为,法律对全体公民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法律并不需要乡民“学会”才对他们发生效力。相对于法律,乡民们更加熟悉自己的“习惯”,那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身体力行的,祖祖辈辈就是那样按照习俗过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明了的道理:国家法对老百姓而言就如两条铁轨,一直平行向前,难有交集,于是就出现在离婚案中,阿洛看到一直在自言自语,爬地耍泼的被申请人,怒斥道:哪个给你的权利这样做?此时我们不禁要问:她们如何知道?她们甚至连汉语都不会说,又能如何?法律的实施,并没有给作为公民的乡民留出多少可以熟悉的时间,法律也没有把乡土社会的规范作为自己的源泉,让乡民有点熟悉的感觉。法律对于乡民,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新事物。当下,中国法律的推广还在艰难而缓慢的进行,这两种规范的冲突自然还要长期存在,如何来调节冲突将是国家权力机构和法律人要慎重考量的问题。
四、生、死之间,新、老继替
影片以冯法官之死来结尾,在一种呛然愤懑的格调下耐人寻味,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是暗示了其作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形象,更是其深谙民间习惯规则的“多元”知识结构的化身,二者之间尚未能真正达到共融共生。那条曲折蜿蜒的山路,老冯对着几十年前落下山崖的同事“长腿”在喊话: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他那嘶哑的长嚎,是对阿洛这样的新一代科班出身的法官的呐喊:要将“马背上的法庭”承载着中国法治的艰巨责任担当起来,继续走下去。老冯的死,看似意外,却在情理之中,阿洛内心的逃离念头,使得老冯在落下山崖那一刻,变成远方山头留下的一抹夕阳。托着国徽的马,又要历经一个漫漫长夜,去等待不知身在何处的接班人——阿洛。
中国的民间习惯法,包罗万象,都由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繁衍至今,作为上层建筑,法律规范必然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其中就包括经济,而活在社会上的人,则是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连接点,不同的民族,就有不一样的上层建筑,包括习惯法,而该民族的习惯法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地域等因素。夕阳下,老冯形影相吊,却又雄心不死,他坚信这条山路,哪怕再艰险崎岖,也要前行,这是一条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必经之途,没有捷径,唯有在“一体多元”的格局下,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习惯规则,尊重当地的实际情况,疏通由地方到中央的自下而上的信息链接模式,再确定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贯通,二元结构的社会,在中国城镇化的途中,将与我国法治进程一起,走向理性共融。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德]耶塞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田艳,少数民族习惯权利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6]王林敏,送法下乡与民族习惯法的变迁——以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为材料说明[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7]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8]谢晖,再论法律的民间叙事[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1).
责任编辑:杨欢欢
The Revelation of Judicial Dilemma in Minority Areas——Based on Courthouse on Horseback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YANG Zhen n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ng100081)
1009—0673(2016)05—0001—05
D920.4
A
2016—10—08
杨振宁(1980— ),男,侗族,贵州黎平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民族2014级法学博士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法学、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