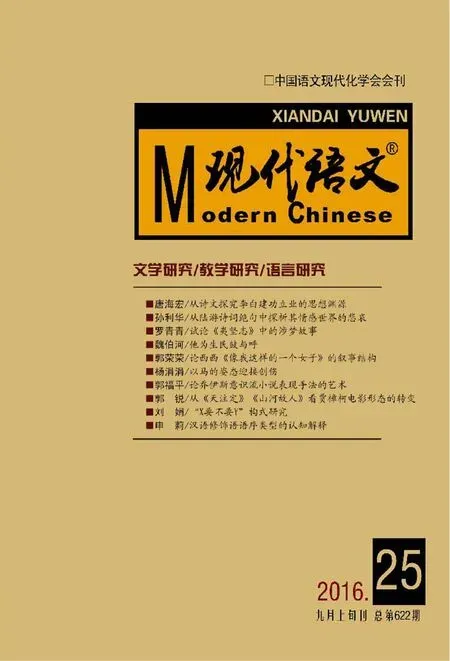无骨绵羊地上的兴衰枯荣
——浅探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的植物书写
○吴 佳
无骨绵羊地上的兴衰枯荣
——浅探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的植物书写
○吴 佳
《生命册》获得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使得更多人将视线聚焦于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在这个被构建出的“中原大地”上,李佩甫立足于当代农民特有的生存环境与社会背景,刻画着在这个现代化时代的乡村特有的焦虑、挣扎与归途,一如既往地从日常生活入手,创作与丰富着属于他自己的“平原植物”形象。李佩甫在他的“平原三部曲”中的植物叙述,对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化意义的分析,与植物叙述背后的文化精神和深层内涵的探索,具有一定意义。
绵羊地 李佩甫 平原三部曲 植物书写
《生命册》的出版,让李佩甫松了一口气。至此,“平原三部曲”完成,李佩甫全面而系统的传达出了自己的“中原声音”。凭借对于“平原说”在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等方面上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总结[1],该书不仅成为畅销书籍,更获得2015年茅盾文学奖,而作者成为人们谈论“文学豫军”时绕不过去的人物。
“中原”这个李佩甫用文字构建出的精神场所,正如马尔克斯构建的马孔多,承载了李佩甫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忧虑与向往,承载了对于中原大地厚重而深沉的爱恨。李佩甫在东奔西突、苦苦寻觅七年后,才真正找到了属于他的领地——“平原”[2],开始将文字扎根在这片广阔的中原大地中。
河南,古来被称为中国版图上的中原,“阃域中夏,道里辐凑。”[3]作为天下之咽喉与胸腹,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李佩甫的文中,中原却因为它特有的地理环境造成平原人的无所依托,“以气做骨”的特点,致使在这没有脊梁的土地上演了一代代兴衰荣辱,日升月落,春荣秋谢的故事。
一、一脉相承的横纵城乡坐标
“三部曲”虽展现不同的故事,却同发生在“无山无水”,人只有靠着“气”站立的无骨地上。李佩甫在文中建立出一个横纵二轴的坐标系,乡村与城市。不难发现,三部小说传达出一个共同的精神依托:对中原大地的深沉情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深邃忧虑。
如果说《羊的门》是对于扎根土壤上的人物苦心经营,最终成为弄权人物耕作出的“土地与植物”的关系网的展现;《城的灯》是揭露乡村土地的人们在邂逅城市后对城市之光的向往和诱惑无奈假面下的惆怅情怀;那么《生命册》就是历经时代、时间、生活的多重淘洗后作者对于“土地”精神内核的自省与归复。
“平原三部曲”名字皆出自《圣经》:上帝用泥土制造出了人,然后吹气泥人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因此,自《羊的门》开始,虽有些叛逆者(如刘庭玉等人)或掌权者(如呼国庆等人)离开了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壤去往城市谋生,但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口仍附着在土上,有着大地般农民的气质——他们厚重、沉静、坚韧,德化同类,又兼有乡村的土地给予他们的“贫瘠”“愚昧”“自私”。
不同于《羊的门》着眼于“人与土地”对话,《城的灯》已将视角着重放在城市,是乡村土地根基上对城市进步主义观念的本质性批驳,它表现出的城市异化、分隔、外部化和抽象化了由乡土社会衍生出的宗亲血缘关系,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宗亲血缘的全盘否认与背弃。正因城市那处于中心、充满动感、灯火辉煌[4]的无限诱惑使平原人试图离开与他们血肉共生的故土,以致人类社群自古以来珍视的坦率、亲密、联系和分享的经历被这些自乡村涌入城市的“他者”单向割裂开。
以往的小说中,李佩甫显然承认城乡的二元对立观点并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生活方式加以对立的。但到《生命册》一书,乡村与城市已达到某种默契与共生。那些离开“脸朝黄土背朝天”生产方式的人们在繁忙嘈杂的都市开始新的人生,但他们最终仍为“衣锦还乡”的古典小说情节所笼罩,最终达到了城市对乡村的反哺与改造。
可以看出,纵使李佩甫笔下的人物曾经挣扎着要脱离这块世代黏着的“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进入现代化城市打工生存、择偶成家,但却仍摆脱不了血缘与地缘的联系,及这一生取给,魂牵梦绕的泥土地。
二、一分为二的乡村植物书写
文学作品中素有对植物的描述。据统计,《周易》出现植物14种,《尚书》33种,《诗经》137种,十三经中基本都有植物出现,此外,《玉台新咏》《唐诗三百首》等书含植物的诗词首数均超过百分之四十,可见自古以来在中国这个农耕乡土社会,植物在文学中占有特有的位置。
中原地区这块农耕文明的至高地上,“古代中国人以农开元,以农立国,以农为基”[5]。因此,在这片一马平川的广袤土地上的植物,必然有着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深厚历史底蕴与人文生态特征。在当代作家李佩甫对于“平原三部曲”的书写中,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平原上有着特有称呼的各种植物的钟情,眷恋与乐此不疲。
“平原三部曲”中涉及到的植物很多,主要描述的草本类植物有二十八九种,主要描述的木本植物有十二三种,还有多种粮食作物的描绘。李佩甫曾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说,世间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大地上的‘植物’,所以他笔下的人都是当做“植物”来书写的。正是基于这种比喻关系,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存在大量的植物描写,意图建立一种人与植物的生存发展状态与土地历史养分、现实社会气候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此进行拷问。这种书写并不是单方面的刻板印象,而是辩证的描述,这使其笔下的人物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与多元的情感走向。
(一)草本植物
平原的田埂上、麦田里、村郊小路上,随处可见草本植物。这些植物既卑下贫贱,又生生不息,坚忍不拔,既有一种奴性,是无赖般的韧性和耐力,又渴望权力,具有反奴役的心态。正如它所象征绿色一样,既代表着成长、春天与生命,又代表着弱小、腐朽心生嫉恨。[6]
1.卑下贫贱的“小”中求活
《羊的门》开头曾提到:“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它从没有高贵过,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7]。
作者笔下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与这些“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草是相似的。他们没有光鲜亮丽的称谓(狗蛋、铜球、根宝等),不响亮也不气派,就像狗狗秧、灰灰菜等植物,毫不出彩。他们的外貌也不起眼,黧黑的脸庞,枯涩的眼窝,矮小朴实,很疲劳的样子像“灰灰菜”,平和乖顺的像“毛毛穗儿”,总是弯着腰低着头像“驴尾巴蒿”。
虫嫂——作为作者笔下众生之一,正是“败”与“小”的最好阐释,她名字取自一种无来由、非人工的飞来的草本植物——小虫儿窝蛋。这花“看上去小身小样的”“白日里是不长的。它只在夜里长,夜里趴下细听,似有滋生。”[8]正如虫嫂一米三四的小个子,发现被骗嫁给了残疾且懒惰的老拐后,毅然用幼小的身躯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几个孩子地出生让原本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时,为养活孩子,虫嫂变本加厉地顺手牵羊,或在夜色掩护下“打家劫舍”,最终失去了贞洁。在被人发现后破罐子破摔,她甘于接受传统礼治社会的制裁,任人践踏与辱骂。虫嫂是典型的草本植物的化身,低贱卑下,渺小而平凡,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扎本不是她愿意,但是她却逆来顺受并甘之如饴了,她将自己的世界缩得很小,只能看见自己家庭这一方天地,无暇他顾。
2.坚忍强韧的生生不息
平原人如草芥,在这个没有脊梁的土地上出生。但是,他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领出了真谛,一个“忍”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韧”字,使他们能在走投无路时绝处逢生,是他们绵绵不绝的奥义。
虫嫂,她偷窃,失贞,全村人都对其唾骂与不屑,却不可否认,她的确富有平原人坚忍与强韧的性格特征。她在自顾不暇时仍养活了一家人,洗心革面后,她在城里收垃圾供出三个大学生。嘲讽的是这三个孩子因怨恨与羞耻最终并未给她善终,她只能孤独地回到无梁村默默死去,无人收殓。她那孱弱花苞好像一个子宫一样高高地托着包裹着的孩子,发射出惊天动地的能量,将她的子女们送去更温暖的土地,子女们生根发芽却忘了回望日渐枯萎的母体。她的人生就像“小虫儿窝蛋”的果实一样,极为苦涩,那仅存的回甘成为她所有坚忍与强韧的坚实后盾与不竭动力,供她做出了人生最大的献祭。
(二)木本植物
中原一马平川,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最适合植物生长。因此,大量的木本植物在这里存活、繁衍。“树的种类很多,数起来最原始的怕也有二十几种,以榆、桑、槐、楝、桐、椿、柳、柿、桃、杏……为主要树种。”[9]
李佩甫曾说当一个人进入“平原”之后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自己植入了平原,成为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平原上的“草”卑微又低下,它迎着人生的风雨扎根生长,最终长成了一棵棵树。它常年与平原的“风”博弈,它的汁液苦涩,躯干弯折,保持着最易存活的姿态生长。它的根紧紧地扎入土壤,攫取水分和养料,保持着与土壤的血肉联系。然而,我们会发现它的枝杈也努力的生长,树冠努力长出一把伞状物,它一生汲汲营营,不忘为人遮出一片阴凉与慰藉。中原大地的树木也是矛盾的个体,与人一样。
1.随风而向的脆弱易弯
平原的风是染人的,皴裂了表皮,浸透了经脉与骨骼,它不仅吹得中原这块土地没有了脊梁(如中原的祖先在一次次抗暴中被打断),也将这土地上的树吹出一个可怕的共性:离开土地,容易变形。这块本应该四季分明的土地上,竟不长栋梁之材。
“三部曲”中充斥着大量的树木。《生命册》中吴志鹏,是一颗柳树,生长周期短,枝干插下即活,吴志鹏吃百家饭长大,带着乡亲的期望与满身的芽儿,来到高楼大厦钢筋围墙的城市扎根,奈何柳树见风起舞,遇事则弯,吴志鹏最终甩开了无梁父老的情感“包袱”,到一线城市打拼,至几十年后老姑父迁坟才又回无梁。梁五方大概是榆树,杜秋月也许是楝树,春才应该是椿树。
《羊的门》中呼天成也是一棵树,是最盘根错节、最气势参天的老树,不同于离开土壤就变形的易弯曲的树木,他更像松、柏,一生没有离开过挚爱的呼家堡,他将这块贫瘠的土地养育得肥沃,但一生也背负着土地,承受平原风的吹拂,“木秀于林”使他经受较他人更甚的欲望与考验,但他用赤诚的情感尽数克服,纵使皮开肉绽,伤筋动骨。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它是平原上离死亡最近的树木的象征。
2.予人庇护的祖荫权力
“在平原的乡村,能给人以庇护的,除了房屋,就是树了。”一旦树木站住了脚跟,最首要的便是开枝散叶,撑开一把大大的保护伞,将脚下的土壤荫蔽在自己的范围内。从呼国庆到冯佳昌,从蔡苇香到刘汉香,纵使出发点不同,却都用自己的能力庇护着情人、家人、乡人,这是来自祖荫传统的庇护。
呼天成是作者构建出的一棵参天大树,手眼通天,给予了与呼家堡人莫大的庇佑,呼伯是无所不能的传说,是李佩甫笔下的“东方教父”。他在呼家堡辛勤耕作四十年,在土地上种植出了顺从的声音,种植出“潇洒”的威望,也种植出一棵以他为化身的精神之树。这种常年累月的种植,恩威并施,是一种情感的经营,更是一个“人场”的关系的构建。得益于这种种植,呼家堡的声望如日中天,邱处长、范行长、冯主编、呼市长等许多从呼家堡走出的人,构成了一把巨大的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被呼天成这颗大树,呼家堡这块沃土庇护。文章最后呼伯去世与呼国庆的释放,俨然是祖荫权力的更迭与交接仪式。只要这种祖荫权力的种植不消失,呼家堡便不会消失,接受庇护的人群也会绵远地存在着。
(三)粮食作物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中提到了许许多多的粮食作物,在描绘人物形象时也常用“脸苦得像倭瓜”“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等比喻。可见,粮食作物对平原人而言,是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中必不可少的。
纵观粮食作物,它们在李佩甫的笔下作为喻体来象征女子,尤其是年轻漂亮女子并不少见。这些女子一方面象征着往昔最美好的念想与回忆,是令人向往的美好;另一方面,却成为潜藏在人心底的最幽暗的欲望的象征,是罪恶的渊薮。
1.令人向往的乌托邦理想
乌托邦理想,顾名思义,即是一种极致美好的、自由的、平等的,不可能完成的理想,李佩甫笔下的美丽女子大多环绕着这种梦幻的色彩,都是粉红、愉悦,但却遥不可及的形象。他笔下女子大都结局悲惨,说明作者潜意识认为乌托邦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存在。
《羊的门》里秀丫是个白嫩的信阳女子,在银色月光下稍稍泛出一点蓝,让呼天成这样一个男人也心动不已。《城的灯》里冯家昌初次观摩刘汉香时被深深地震撼:“那是伏桃的细腻,那是麦杏黄的滋润,那是白菜心上的水嫩,那是石榴籽般的晶莹,那是苹果枝上的嫣红。”[10]而《生命册》中吴志鹏脑海的梅村是“樱桃,向阳坡的,鲜艳欲滴的”,是“葡萄,吐鲁番的,晶莹剔透的,熟了的玉色”[11]。所以虽然几十年后他看到面目全非的梅村,却依旧无法改变他对梅村以及美好的缅怀与向往。
2.引人堕落的潘多拉魔盒
无论中外,“女人”自古以来就带有祸水与诱惑的含义,在李佩甫的笔下亦然,红色在象征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还象征着谋杀、愤怒、诱惑,宛如一个即将被开启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就要堕入罪恶的深渊。而向来以纯洁庄严著称的白色,却也因为太过纯粹而脆弱,容易染上杂质,并且透露着死亡的气息。
这在文本中有着大量的佐证:《羊的门》中的秀丫这个“大白菜”成为四十年来身居高位的呼天成最大的诱惑与挑战;《城的灯》中冯家昌为了李冬冬抛弃了那人生中的一束光——刘汉香,从此在唾骂、自责、痛苦与黑暗中度过;《生命册》里的范家福为了爱情丢了自己多年挣来的清廉与成就,骆驼在女人里左右逢源最终却因为情人而落入法网。梦想通常美好而纯粹,而追求它总是让人付出巨大代价。
三、结语
李佩甫一直立足于当下性的书写,“平原三部曲”讲述的是一条人们“出走”离开故土,在城市这座“障碍的标尺”里挣扎、迷失最终又探寻到人的根本在土壤,而达到一种乡土与城市交替共生的轨迹。因此,在其文中不难发现土壤对于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他们就是乡村土壤里走出的一株株植物。
正如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小说题名皆取于《圣经》,与土壤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他文中象征式的植物书写正是对这种血脉关系的辉映。这种书写,是他对于现实世界的内质与外在的探求之后,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深入挖掘之后,对于精神内核的复归与内省之后,给出的成熟的回答。
注释:
[1][2]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8期。
[3]杨玉厚主编:《中原文化史》,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4]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英]雷蒙·威廉斯著:《乡村与城市》,北京:商务印刷出版社,2013年版。
[5]徐光春:《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6]谢康等译,[美]肯尼思·R·法尔曼,切丽·法尔曼著:《色彩物语:影响力的秘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7]李佩甫著:《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8][9][11]李佩甫著:《生命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第110页,第11页。
[10]李佩甫著:《城的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谢康等译,[美]肯尼思·R·法尔曼,切丽·法尔曼著.色彩物语:影响力的秘密[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3]李佩甫.城的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4]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潘富俊.中国文学植物学[M].香港:猫头鹰书房出版,2011.
[8]徐光春.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9]杨玉厚.中原文化史[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10]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英]雷蒙·威廉斯著.乡村与城市[M].北京:商务印刷出版社,2013.
(吴佳 广东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