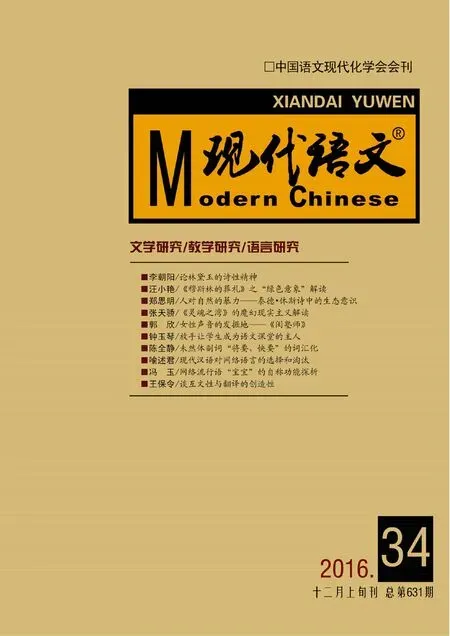徐浩峰武侠电影的美学风格与叙事策略
○董 蕾
徐浩峰武侠电影的美学风格与叙事策略
○董 蕾
徐浩峰的武侠电影尊崇中国武学的本质,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扎实的武术根基融汇于影像创作中,使其武侠电影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文章从其作品的美学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分析徐浩峰电影的独特意蕴,并阐释其对中国武侠电影发展的意义。
徐浩峰 武侠电影 美学 风格 叙事策略
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之一,武侠电影已有百年历史。2011年,徐浩峰以小成本电影《倭寇的踪迹》登陆院线,这部电影对于经济转型期热衷于“场面”“技巧”和“一个有趣故事”的大众观众而言,的确算不上一部“好看”的电影。随后上映的《箭士柳白猿》和《师父》,三部曲一出,徐浩峰的武侠电影风格基本呈现,《师父》更是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至此,学界开始将“新锐武侠”“新硬派武侠”等命名给予这位文武并重的电影新人,而这三部略带有文艺片气质的武侠电影,虽然在票房表现上呈现意料之中的不尽人意,但良好的口碑大有将徐浩峰推向“开门立派”之势。徐浩峰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扎实的武侠根基融汇于影像创作中,使其创作呈现出独特的美学意蕴,构成了别具一格的硬派江湖。
一、奇观化的武侠电影症候
影像术发明之前,中国人的武侠世界大多由文学文本构成。从《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开始了中国早期侠义精神的书写。司马迁笔意鲜活灵动,传记体叙事颇有小说叙事的风采。他笔下的侠者古道热肠、重誉轻生,更重要的是太史公指出了侠者的生存方式:“或依附于权贵,厕身庙堂;或散居于市镇,混迹江湖。前者为武士,后者为任侠。”[1]太史公之后,国史笔意写法几经转换,侠客形象被正史逐渐驱逐,只占据说部一角。民国初期,救亡图存之下武侠小说突然兴起,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这部小说的改编电影《火烧红莲寺》分别作为近代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的开端。《火烧红莲寺》中僧道有神功,武术在幕布上表现为剑光四射、掌心发雷、吐剑飞行的视觉特效,开启了“用电影把神功视觉化”的拍摄观念,将小说文本语言呈现为更加直观的非现实主义的盖世神功,构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怪力江湖。
源头的影响,不可小觑。“武”逐渐沦为技巧或形式。建国后,由于大陆地区革命文化政策的实施,除了部分革命历史电影如《林海雪原》中依然保留有“武侠”成分,武侠电影已被驱逐出革命话语建构的内地电影。同时期的香港,武侠作品已开始将文侠与武侠形象合一,各类小说改编和独特编剧的武侠片开始广泛受到观众的欢迎,并成为香港电影业的主要支柱。邵氏影业公司出品的张彻《独臂刀》,阳刚写实;胡金铨《大醉侠》《龙门客栈》等更富古典人文意趣。在武术动作设计上也很“好看”,处处充满表演设计。武打明星制造出来,武术指导成名,直到70年代由李小龙将这种“好看”的“功夫”推向西方世界。李小龙集西洋拳、空手道、合气道、跆拳道、咏春拳、北少林等各门功夫于一身,打造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功夫奇观。到徐克时,电影特效派再次占领市场,《蜀山传》《华英雄》《风云》等影片用特效表现神功,用爆炸效果提供虚幻刺激,形成了徐克电影独特的风格。
在电脑特效塑造的仙侠与超级英雄充斥荧幕的新世纪,既有张艺谋的《英雄》、陈可辛的《武侠》、徐克的《龙门飞甲》之类特效武侠电影的探索,也有李安《卧虎藏龙》、王家卫《一代宗师》以及并不能称为武侠电影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之在“文戏”与“武戏”间寻找自我叙事风格的文学武侠。这些电影在呈现各自对庙堂江湖观念的同时,表面上看确乎有对传统武侠电影创作的突围之意,却更显现出武侠奇观化的电影症候。细看之下,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卧虎藏龙》,武打动作几乎转变为了写意舞蹈。阿城在谈论徐克等人电影时就认为当时的中国武侠片应该是舞蹈片的一个变种,“因为一个理由,就动作起来了,打,所以武打片里的人是打不死的,永远在打,死了再起来,接着打,跟舞蹈是一样的。你看武打片里专门有武术指导,我看应该是舞蹈指导。”[2]阿城无意间道出了当时武侠片对于武打动作的过分表演化,“功夫”依然是高度艺术化的银幕奇观。炫技之下,侠义何在,江湖何处。
二、硬派武侠的美学风格
在上述背景下,徐浩峰电影的意义已经凸显。何为“武侠”,何处“江湖”,这是横亘在中国武侠电影面前最关键的命题。作为形意门传人的徐浩峰,在《倭寇的踪迹》中首先解决的就是“武”的基本命题:武者存在的意义,武是靠什么打、怎么打、打完之后又如何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环节。而这样技术的突破点不是电脑CG特效技术,更不是吊威亚、舞蹈、华丽服饰和演员的“颜值”,而是江湖规矩与真招真式。
《倭寇的踪迹》中戚家军要对抗日本倭刀,采取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古典方式,刃不全开,既可以承接对方兵器,也可以转为进攻。梁痕录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生前的贴身侍卫,他的梦想只是想让戚家军改制的兵器能够得到“正宗”门派的认可,能在武行开宗立派或者流传到民间。当军营原指挥史被四大门当为倭寇俘获之后改变意志,梁痕录依然固守自己的信念:“戚家军不在了,为戚家军留个影子”。为此,梁痕录必须遵守四大门两百多年来的规矩,通过“打门口”的方式,凭一杆戚家刀挑了四大门。动作干净利落,高手过招,没有来回,只有一下。到了《箭士柳白猿》,徐浩峰有意用影像复原已经失传的古代箭术。影片的情节简洁至极,一个先叫双喜后意外改名柳白猿的普通人,通过进入武林之后的身心洗礼。片中展示了“划勒巴子”式的格斗,即两个高手在不足三尺的间隔里,坐一小凳,靠手、肘、膝来攻击对方。《师父》中陈识最后的巷战片段中,陈识拳法高强,只身面对手持十八般兵器的各门派高手,并能做到礼让在先,静待对手准备。双方始终是一对一的对垒,用械斗的方式展现八斩刀与戟、单锋剑、三尖两刃刀、子午鸳鸯钺等北方兵器的交手,两三招之间便有胜负,依然做到点到为止、伤人不伤命。文化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传统的中国是礼俗社会,重视行事的礼乐规矩。展示人与人之间充满仪式感的相处方式正是中国人的“样”。陈识在巷战中一人一步的过招,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样”,既展现了武行本身的井然秩序,也是中国人群像式的文化仪式。武术指导袁和平曾评价徐浩峰的武侠电影,他认为徐把动作设计得太实在,电影拍得很好,但观众看起来“没有一个兴奋点”。袁和平曾是香港武侠电影的传奇人物,和徐浩峰的观点不同,恰也说明了徐在动作设计的创新之处。正所谓高手不用威亚,行家不玩特效。一招一式都能由人做出,由人使用,为人服务。能够做到化繁为简,并尊崇中国武学的本质,比起以往武侠电影的“花拳绣腿”,徐的电影更具有看似平凡而又变幻无穷的中国美学风格。
对真实的还原就要去除各种电影“添加剂”。徐浩峰塑造的武者侠客往往表现出和普通人相同的世俗气质。《箭士柳白猿》中,柳白猿只是村中一介布衣,因目睹姐姐被村霸侮辱,变为“跳墙和尚”后机缘巧合成为武林秩序的维护者箭士“柳白猿”。《师父》中的陈识,作为咏春拳传人,因希望南拳北传,只身离开佛山来到北方的武术之乡天津。陈识秉承着“刀法我给了,得多少,在你们”的理念,从一开始他就明白自己在门派观念严重的天津武行的地位。为了能开宗立派,他娶天津本地女子,收天津本人为徒。各种动机可谓并不高尚。陈识漂泊南洋十三年,给货船当保镖;徒弟耿良辰原本是脚行,习武后是街头摆书摊的商贩。他们都只是民间布衣,武人生活于世俗之中,经济来源同样是社会劳动。这种“凡人建制”使得影片主角有着普通人的思想和欲望,他们的功夫真实可考,他们的言行更接地气,他们的失意与悲剧更显示出彼时武林环境的真实。
三、叙事策略与武侠电影的现代性困惑
市井民间的低调身份本是徐浩峰武侠电影真实性的呈现之一,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却也道出了“武侠”这一形象本身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失落感。后期新历史主义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关于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套用福柯的批评观点,对于武侠电影而言,讲述同样的年代,怎样表现不一样的江湖往事,电影呈现的其实是导演对“武侠”这一命题的阐释。徐浩峰总是将电影的时代背景设置在中国社会的关键转型期,或是传统武术遭遇现代西方“热兵器”的失落时代。在这种情态下,作品往往让结局呈现出一种非悲剧亦非喜剧的荒诞感。从戏剧美学的角度来看,荒诞感实则为更深一层的悲剧感,是现代人无法阐释和把握的无奈。《倭寇的踪迹》发生在明朝中后期,此时正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方现代文明入华时期。戚家军制服倭寇后,倭寇彻底消失,武林失去了“敌人”。“倭寇”出现,其实是两个被霜叶城四大武林世家全力围捕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旧部。梁痕录的愿望被四大世家以“抗倭军刀”刀型形似“倭刀”,是“邪道”为理由拒绝。经过努力和较量,梁痕录终于获准在武行中立派开宗。但反讽的是,当戚家军军刀被拿到冷清阴暗的兵器库时,却是随意一丢,最终留下了“影子”。有意味的是,完成“使命”的梁痕录,最后和吉普赛舞女赛兰去了苏杭。一个是抵御倭寇的武人,一个是西洋女子,他们要去文人汇集之地“苏杭”,徐浩峰最后给人的留白是回味无穷的反讽与无奈。
如今,更多的武侠电影中“功夫”却需要科技特效来“实现”,这种二律背反的情态本身也注定了当代武侠电影表现自身的无奈。徐浩峰怎能没有看出武侠电影先天的无奈,“虽然我的理念可能会像片中的柳白猿和匡一民一样,被时代淘汰,但我之所以这样拍电影,是想为一些老手艺、老观念作一个挽歌。”[3]可贵的是他能给直面这种无奈,并在影片中表现出来,这也是徐式电影意义的呈现之一。
注释:
[1]王嘉然:《庙堂江湖——徐皓峰作品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年,第71-76页。
[2]李洋:《阿城先生谈电影》,2005威尼斯访谈,2011年02月09日。http://cinephilia.net/archives/3273
[3]吴冠平,徐浩峰.武之美学 器之精神——徐浩峰访谈[J].电影艺术,2013年,第2期,第44-50页。
(董蕾 河南郑州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451464)
——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