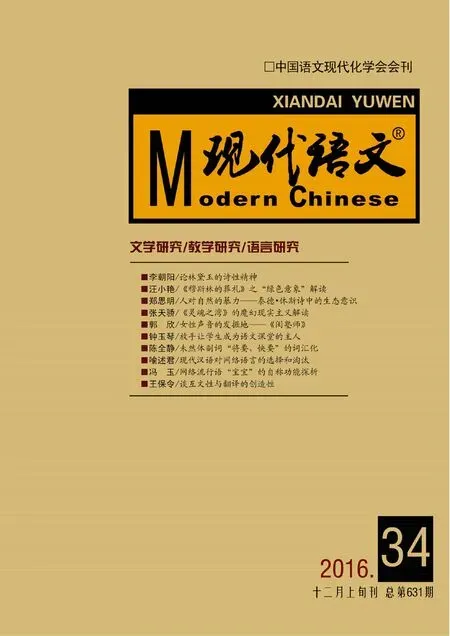阅读门罗,我们读什么
——《漂流到日本》的“心理现实主义”及其它
○杜慧敏
阅读门罗,我们读什么
——《漂流到日本》的“心理现实主义”及其它
○杜慧敏
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详细分析了门罗的短篇小说《漂流到日本》;并以此为个案,总结了门罗小说创作在心理现实主义、结构和意蕴方面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达到的成就。
门罗 《漂流到日本》 心理现实主义
三年前,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她82岁,是第十三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作家。瑞典学院认为,“门罗以精致的讲故事方式著称,清晰与心理现实主义是其写作特色。”2012年,门罗出版了她最新的一部小说集Dear Life,2014年有了中译本,题为《亲爱的生活》。她这样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集:“我希望读者从《亲爱的生活》开始读我的小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1]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亲爱的生活》中一系列作品最为出色地表现了女作家讲故事的“精致”,——“清晰”与“心理现实主义”的特色。通过细读《漂流到日本》(《亲爱的生活》中的第一篇作品),我们将依照作品本身的顺序还原这些为人所称道的“心理现实主义”等特色,并尝试揭开门罗作品内在价值的冰山一角。
《漂流到日本》这篇作品的题目,源自小说女主人公格丽塔写给偶然邂逅的男记者哈里斯的一封短信:
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
希望它能
漂流到日本
再结合上下文的情境,这个题目意味隽永地表达着一种飘渺的不抱希望的希望,又因为过于渺茫,万一变为现实,其后果也是不得而知。终归,这是一个属于心灵、精神乃至情绪的萌动。所以,题目向读者扑面而来的,正是门罗最善于捕捉和表现的女性的味道。
但题目的这一寓意,并不是凌空而来,它还与作品的结尾遥相呼应,或者说读到结尾,读者才会体味到此寓意的现实回响。
而现在也有人接过了她们的箱子。接过箱子,搂住格丽塔,第一次吻了她,坚定的吻,仿佛在庆祝什么。
哈里斯。
先是震惊,接着格丽塔心里一阵翻腾,然后是极度的平静。
她试图抓紧凯蒂,但就在这时孩子挣脱了她的手,走开了。
她没有试图逃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
此时,漂流瓶竟然真的“飘流到了日本”,然后呢?
一、火车开动之前
小说第一个场景是火车站送别,出现的人物是“丈夫彼得”“女儿凯蒂”和“妻子格丽塔”,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三人家庭组合,里面包含着夫妻、父女、母女三层人伦关系,如果再进一步,这三人当中的任意两人组合对第三个人来说都意味着家庭。就是这样简单的、最为常见的三口之家,就是这样最平常的一个送别场景,门罗却能够三言两语不着痕迹地让其中的不和谐显露在读者再三捉摸回味之中。她会让读者觉得,在这个场景背后一定还有场景,在这个心情背后一定还有心情,在这个目光背后一定还有目光。
“彼得把她的旅行箱拿上火车后,似乎急于下车。但不是要离开。他对她解释说,他只是担心火车会开。”——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彼得理性特质的表现。这句话从“女诗人”的站位去感觉,又可以生出几种解释:不愿意、没必要,或者,没热情。因为那不仅仅是拿捏时间计算最佳效果的时刻,重点也不仅仅在于火车会不会开,此一场景最应该的命名是“离别”。在整个第一段里,门罗以第三人称反复而刻意地强调一些东西,比如丈夫对女儿灿烂的笑容,对妻子信任的眼神。因为这是一篇时间错综的小说,读到后边我们会发现,这么明显的反复和刻意是为什么,这个场景那明显的“背后的眼睛”究竟在哪里。“而她会赞同他,认为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解释,那样不自然。”然而第一个行动,丈夫彼得就已经在为了显得自然而解释了。不显山不露水,但这里边全是裂痕。
小说随后追述了丈夫彼得的成长历程,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歧:“他学过商务实践,虽然不是在母亲的课上学的,与此同时格丽塔却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有用的东西。他却似乎恰恰相反。”这个分歧意味着,“丈夫”也许能够为家庭更好的维持生计,但他不可能在更高的精神追求上与格丽塔产生共鸣,“他认为多说没有意义”,更别说灵魂方面的引领和依赖了。所以,后文哈里斯•班内特是在格丽塔生理和心理都需要出口之际适时出现的。事实上,作为女性叙述者,很容易无意识地跌落进谴责和怨怼情绪之中,毕竟拽着头发把自己拔出“洞穴”几乎不可能。而在这方面,门罗叙述的“克制”非常值得称道;当然克制背后的精神修持更值得肯定,门罗的眼界既不局限在男性那边,也不局限在女性这边(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她的注视既在她的女性人物之内更在之上。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门罗这个常常并不在场的叙述者高悬于横在男女主人公头顶的钢丝之上,她看得非常分明又免于失坠于哪一方。
回到火车站送别的场景。妻子还在观察着车窗外的丈夫。
再从妻子格丽塔的角度追溯几个过往的典型对话和生活场景:丈夫的宽厚包容、不加干涉,以及“女诗人”的问题。同样,这里也可以多义地理解成没有共同语言、无所谓,因为那就是看上去心有灵犀的“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空洞和乏味”。其实这种解释更加符合小说所要表达的那层潜隐的意思,不言而喻也是格丽塔的内心想法。生育女儿后爱情和自我的空洞乏味,这正是格丽塔此前几近疯狂又毫无理由地爱上哈里斯时的情感状态。“女诗人”格丽塔的追求是不被理解的,不被接受的,她的精神注定是孤独的。
当我们再仔细推敲小说叙述节奏的时候,作者精心安排的时间重置和转换非常耐人寻味。要知道,我们最初看到的火车站送别那一幕,以及那有诸多遮掩的“自然”,是发生在格丽塔与哈里斯相遇之后。格丽塔心里同时装着分量如此巨大几乎不可遏抑的“背叛”,来看此时她的丈夫和女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小说开头那第三人称的视角其实就是格丽塔内心的另一个主观视角。同时兼有“妻子”格丽塔内心独白的性质,更像她不安的自我心理暗示和心理安慰。这正是门罗“心理现实主义”手法的精彩展现。于是,在格丽塔乘火车离开之前,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跳动的叙述节奏展现了当下的全部时间性的历史,产生了隽永的艺术效果。到此,我们不禁要赞叹门罗精湛的短篇小说创作才华,并沉浸于品味艺术品的陶醉之中。
再回到火车站送别的场景,“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
二、“去年秋天”
时间又被跳转到“去年秋天”,格丽塔“和其他作家一起受邀参加一个聚会”。这件事前后讲述的非常细致,几乎让人相信这个聚会里必然有门罗自己切身的真实经历为蓝本。
那是一次格丽塔放下很多矜持(酒后)的邂逅:
他们头顶的大树枝繁叶茂。你没法看到天上的星星。但有些星光映在了水面上,在星星所在的位置和城市灯光的倒影之间。
“就这么坐着细细地想。”他说。
她被这个词迷住了。
“细细地想。”
意境之迷离让人想起梵高的《星夜》。格丽塔爱上了开车送她回家的记者哈里斯。哈里斯有儿子女儿和疯掉的妻子,而格丽塔呢,“她急忙告诉他她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但其实,哈里斯不代表任何人,或者说哈里斯并不代表具体的哪个人。这正如普鲁斯特《在少女们身边》里描写的那种感受。哈里斯是一个符号,这件事也不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因为在整篇小说所跨越的时空范围里,除了结尾以外,他只出现过一次,适可而止地说了那么一句关乎利害的话:“请原谅我刚才说话的语气。我在想应不应该吻你,结论是不应该。”不可思议的是,此后,“情人”格丽塔出现了,在精神上坠入了自己的情网,和自己谈了一次恋爱。门罗对格丽塔思念(爱)哈里斯的描述,真实到难以置信:门罗何以竟能深刻至此?这一部分的表现,让作为具有“心理现实主义”写作特色的小说家门罗精彩绝伦。很多作家都看不到身处此中的人物(或者说被自恋溺亡的女人)内心的挣扎,但是门罗能够看到。
她对他如此渴望,几乎要哭出来。但当彼得回到家时,所有这些幻想都消失不见,蛰居起来,而日常的爱意凸显出来,和已往任何时候一样真实可信。
两种同样真实,“妻子”格丽塔和“情人”格丽塔同样真实;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难以区分的矛盾。这爱强烈、无法压抑,但因有背负而不可能明丽。门罗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来表现,流露了深邃的感受力又不失准确。
这个梦其实很像温哥华的天气,——一种阴郁的渴望,一种像雨又像梦幻的忧伤,一种环绕着心脏的重负。
“阴郁”“雨”“梦幻”“忧伤”“重负”,想想这些词里边的无力和痛苦吧,它们的反义词,证明着这段带有心理阴影的爱的色彩。门罗接下来强化了、具体化了格丽塔双重身份的矛盾和挣扎。
当然大多数时候她是在凯蒂午睡时才给这样的心情一个容身之所。有时候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欣然拥抱自己的愚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她鄙视自己的极度羞耻。
确实是愚蠢。
愚蠢。
正是因为没有实存,只是一个名,格丽塔才爱他,也许因为实存让人丑陋。一边是实存的丈夫、女儿、家庭,另一边是几乎没有实存的一个名(符号)——“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所以格丽塔感到自己的愚蠢,但是爱,并不在精明里边。
她发现自己在写一封信。(She found herself writing a letter.)
这是非常富于门罗“心理现实主义”风格的一种表述方式:“她发现自己在做什么”而不直接是“她在做什么”。关于“风格”,罗兰•巴尔特说:“因此,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则几乎在文学之外:形象、叙述方式、词汇都是从作家的身体和经历中产生的,并逐渐成为其艺术规律机制的组成部分。”[2]门罗笔法的细腻、深刻、简洁——用瑞典学院的话说是“清晰”就在这里。风格在文学之外,从作家的身体和经历中产生,动作先于思想,女性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的特点用这一个特殊表达法就浑然地“显示”出来了,她的无意识,她的被情感乃至生理所支配。门罗的小说从来不夸饰、不做作,从不为了赢得别人的同情而故作苦难,从不越过作家本分一分一毫,但(女性)人生本身那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的残酷却更加实实在在地让人不寒而栗。
三、火车上
既然“漂流瓶”最终真的“漂流到了日本”,格丽塔在火车上的遭遇和行为看起来就更加不可解释了,人们完全可以因此而把格丽塔看作一个行为放荡的女人。这个时候,最好借助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说的:小说艺术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3]门罗当然不会以此来取悦读者,刺激读者道德评判的癖好。那么门罗为什么要让格雷格出现呢?这里正是门罗的精妙和深刻之处,在这段有点突然和过于不可思议的经历中,包裹着一个巨大的对立和矛盾,那就是男女之性和母爱之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具体而言,是格丽塔-格雷格、格丽塔-凯蒂这两组关系在格丽塔人性中的巨大挣扎。格雷格作为“火车上”阶段的重要标志的出现,成全了这一女性心理的巨大挣扎。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针对人性心理提出了那个著名的“俄狄浦斯情节”,《漂流到日本》的这一部分内容转换了角度和性别,补充了那个属于男性的心理情节的很多漏洞,而这些通常被人们所忽略。
你总是加快脚步走过这些走道,这里的撞击和摇晃提醒着你,归根结底,事物被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几乎有些漫不经心,却又那么匆忙仓促,那些撞击和摇晃。
当然,由此而引发的凯蒂走失和对格丽塔内心挣扎的充分揭示才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凯蒂的走失和复得令“母亲”格丽塔深刻地反省自己:
不仅仅是因为家务事。其他各种想法也将孩子从她心里挤了出去。甚至在她对多伦多的那个男人产生毫无益处、令人疲倦、白痴一般的迷恋之前,她也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她似乎大半辈子一直在脑子里做的写诗这件事。她突然发现这是另一种背叛——对凯蒂,对彼得,对生活。
一种罪恶。她将注意力放在了别处。固执地四处寻觅关注对象,却没有关注孩子。一种罪恶。
如果考索门罗自己的作家历程,[4]相信她也一定为这个挣扎过。曾经,“诗人”格丽塔内心拥有着这样的傲慢:“除此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和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词(女诗人,笔者)的特性。”但是现在,她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定为一种罪恶和背叛,难道她蔑视的那些人反而是对的?如此触动到根基处的自我否定,怎能不令人痛苦甚至绝望幻灭。女性这层微薄的力量,要想透出点光芒,实在太难了。即使她能够将怀疑的目光“抛在身后”,又如何将孩子“抛在身后”呢?“孩子”本身是女人成其为女人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两难。但是,男性却很少能触碰到这一层,因为这不是他们生命里的必然的困难。这个问题,中外皆然,古今皆然。《红楼梦》第一回说绛珠草“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5][6]这段话可以说是女性特质的诗意显示:不牢固,主情感,以异性为因果。《红楼梦》第四十二回里宝钗劝黛玉:“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我们也很难否认,一直藏在格丽塔身上的“诗人”身份,对格丽塔的自我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行为具有重要的暗示和影响。
四、总结:“心理现实主义”、结构、意蕴
应该说,《漂流到日本》这篇小说在“心理现实主义”手法上典型代表了门罗文学创作的特色。形成这篇小说的“客观现实”是叙述者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出来的直接关于母女乘火车旅行的种种,比如火车上格雷格与凯蒂玩耍的情节,再比如母亲格丽塔寻找凯蒂的情节,都非常具有真实的画面感。这些可以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若以此“客观现实”作标杆,我们会发现,丈夫彼得的过去、夫妻间关系的各种小细节、与哈里斯的偶遇乃至疯狂思恋,甚至那封“漂流到日本”的短信……换言之,母女上火车前的所有,都沉沦为女主人公格丽塔的“心理”。然而这些在读者阅读小说之初几乎无法察觉,因为作者同样使用了类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叙述。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艺术效果和阅读体验:看似重重叠叠的故事,其实都是格丽塔的意识之流,既发生在读者以为的现实里,也发生在女主人公格丽塔的心里。读者仿佛被推到了一个内外互通的神一样的位置,既可以从外向内看,也可以从内向外看。而且因为门罗可贵的“克制”和精准的心理现实把握,读者不会一下就掉进伍尔夫《到灯塔去》、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那样的“意识流”的迷雾当中,也不会像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样,慢慢在现实中迷失,读者只会在字缝之间透露出的那么一点点“现实”与“心理”无法重影的细微处,品尝到隽永的味道。比如,小说开头:
他站在月台上,抬头看着车窗,挥着手。微笑着,挥手。他对凯蒂绽开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没有一丝疑虑,仿佛他相信她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奇迹,而他在她眼里也是,永远如此。他对妻子的笑则似乎充满希望和信任,带着某种坚定。某种难以付诸言辞也许永远也不能付诸言辞的东西。
比如格丽塔思念哈里斯的举动:
她只是把这件事删除了。彻底忘记了。
那么她的诗怎么样了?一行也没有写下,一个词也没有写下。没有一丝她曾经喜欢过诗的痕迹。
罗兰•巴特说:“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写作的例证,其作用不再只是去传达或表达,而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与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7]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门罗小说是另一种“写作的例证”,而它们强加给读者的“语言外之物”既是心理又是人们在心理中看到的现实。而且,门罗的“心理现实主义”又同她短篇小说的“精致”结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心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小说的结构愈显精致,而精致的结构又加强了心理现实主义手法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无论哪种现实主义,甚至文学的哪种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文学之“真”的话,那么门罗就用她的短篇小说一小步、一小步地向这个顶点攀登着。
与“心理现实主义”相关的,我们还要再次谈谈门罗小说的叙述视角。在《漂流到日本》这篇小说里,明显有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存在,而门罗写作手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能够不着痕迹的将叙述视角在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女主角格丽塔、甚至是女儿凯蒂之间游移,在格丽塔外看的视界和自省的内心世界之间游移,那是一种精妙的心理把控。其实,在小说阅读体验里,第三人称叙述者的眼睛也就是读者的眼睛,作为读者,我们跟随它走进小说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样一来,我们不仅瞬间穿越进格丽塔眼睛看出的视界,还能瞬间走进格丽塔的内心。由此可以想见,门罗给予我们的“自由”是何等精彩。
《漂流到日本》这部短篇小说内在的主干结构,是格丽塔带着四岁的女儿凯蒂乘火车去往多伦多,对,就这么简单;这也是小说叙述所定格的现在时态。这个看似简单的母女火车旅行,其实并不简单,它的起点是丈夫彼得的送别,终点是情人哈里斯的迎接,中途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格雷格;站在前台直接被读者看到、身处各种情感矛盾焦点的是母亲格丽塔,但在母亲庇护之下的那个小小女孩(以后也会成为女人,这些就是她的成长之所从来)凯蒂的身影始终挥之不去。所有这些亦不是从天而降,于是,与丈夫彼得的过去种种、与情人哈里斯的一次偶遇和深深迷恋,都被以过去时态“精致”呈现。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这个故事的结构就如同英语繁琐复句的结构一般,各个核心词汇(人物、情感)都被复杂定语从句包围着,主人公就裹挟着如此众多而沉重的各种过往的故事、各种复杂的心情一路向前,向着未来生活的方向。
再从小说的意蕴来讲,门罗毫无疑问是做过精心安排并且是深思熟虑的。首先是女主人公格丽塔,她事实上同时具有诗人格丽塔、妻子格丽塔、情人格丽塔和母亲格丽塔四重身份。门罗在创作中强化乃至夸张凸显了这四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一重身份,也不可能完全在各个身份之间游刃有余,所以门罗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困境和无奈。其次是“火车”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门罗小说中经常出现“火车”的意象,《亲爱的生活》这部小说集中还有一篇专门以“火车”命名的作品,其内涵非常深远。而在这篇作品中,火车出发前、路途中、下车以后,对于格丽塔来说几乎就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火车引发了时空的改换,也标志了时空的改换。它几乎成为了一种象征。
短篇小说对作家形成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短小的形式与巨大的包容性之间的矛盾和反差。门罗却用“精致”锻造了她的短篇小说的质地,用“清晰”平衡了故事叙述的“放”与“收”,又用心理现实主义拓展了同一形式中双重的意义空间。英国作家A.S.拜厄特说:
即便是在她写作生涯的最初阶段,她也几乎没有写过传统的那种“结构结实”的小说。她的故事是片断性的,时空颠倒的,启示性的,但是它们通常能在很短的篇幅中表达出一种整体性,一种完整的生命体验,并指明背后所蕴含的哲理。[8]
从《漂流到日本》这篇作品,我们能够看到足以让门罗赢得此番评价的那些短篇小说的卓越之处。是门罗,让短篇小说重回诺奖。
注释:
[1][加拿大]艾丽丝•门罗:《亲爱的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所引《漂流到日本》的引文均出于此,门罗的这句话见本书封面。
[2][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4]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第二章第一节《爱情还是文学——从文艺青年到家庭主妇》,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5][6]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第568页。
[7][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8]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第二章第一节《爱情还是文学——从文艺青年到家庭主妇》,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杜慧敏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