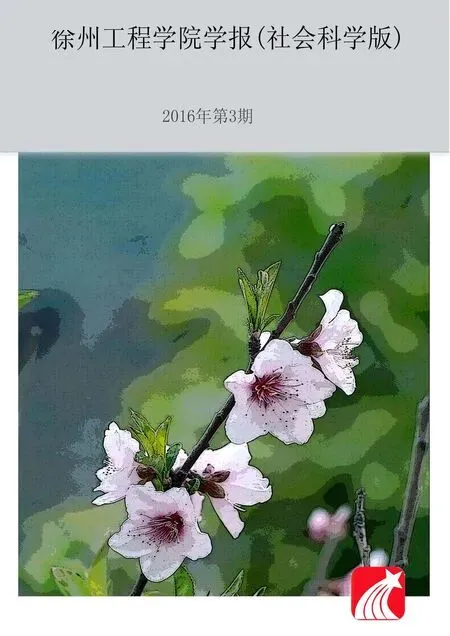审视成说与学术求真
——我们如何研究元代文学
查洪德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审视成说与学术求真
——我们如何研究元代文学
查洪德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受某些观念的影响,也存在大量不客观的认识,这些认识至今仍有一些以权威结论的面目流行着,影响着元代文学研究的推进。这些成说不清理,客观的认识就难以为学界接受。我们必须以求真的精神,认真审视这些成说,凡属主观解读不合历史真实的,都应清理,从而使我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尽可能回归客观。
关键词:元代文学;元代文学研究;成说
学术研究的宗旨应该是求真。但很多时候,学术研究受到外力的影响,偏离了求真的宗旨,所有的研究,都被要求符合某一观念、某一学说,去说明、验证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这样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不少权威结论,流行的成说,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得出的。这些结论或成说,一部分已经从我们的学术话语中淡出,但还有不少依然流行,影响着我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但这些说法很多是没有根据的。要使学术研究回归求真的精神,就必须认真审视并清理这些成说。
一、以求真的精神审视成说
什么是成说?成说就是通行的说法,权威的结论。在我们学术史上,是学术定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信奉成说,不加怀疑。因为成说定论,都是被学术界公认、有强有力事实或文献依据证明了的,同一学科学者认定的,是具有权威性的结论。
但是,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很多成说,是在当时意识形态主导下,按照某种先验的观念推论出来的,而不是依据历史文献,从文献中抽绎、概括出来的。也就是说,有很多成说,是不“真”的,缺乏真实的文献依据,而是一种主观的解读,不符合学术求真的精神。这些成说形成在20世纪,但其根源可能更深,有一些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王元化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这是受一种“意图伦理”的影响:
意识形态化往往基于一种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许多观念改变了,但这一传统未变。“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得很历害,但意图伦理的传统却一脉相承下来。我那篇为《杜亚泉文集》作的长序,曾谈到1919年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时,蒋廷黻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了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近数十年来此种思维模式大盛。……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1]
要符合既定的意图,就无法“求真”,“真”是客观的事实,既定的意图则是人的主观观念。比如说,文学史要反对形式主义,那么六朝文学就被定性为形式主义,六朝文学就是应该被批判的;又如,按照诗要用形象思维的理论,宋诗缺乏形象思维,宋诗就应该否定。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封建和反封建”,于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反封建”,“反封建压迫”,“反封建礼教”。很多经典的主题,被说成是“反封建”,比如《西厢记》等。这些成说一度都是绝对权威的结论。但20世纪末,一些成说被推翻了。六朝文学、宋代诗歌,各自的价值被文学研究者肯定了。一些不客观的成说被清理了。但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成说没有清理,很多仍以权威结论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其中不少观念,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比如“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容易被否定,但这种观念植根于古代道德批判重于诗学批判传统,就很难清除。文学史的评价于是就很难摆脱“意图伦理”的预期,于是缺乏文献依据的结论,按照某种逻辑主观推理出来的结论,就会流行在我们的学术话语中。这需要我们继续审视,破除这些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不客观、甚至本身不能成立的成说,让我们的文学史更客观。
清理不实成说,学术才能回归真实。学术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求真。就文学史研究说,学术求真,就是追求文学史的客观真实。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但我们应该努力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不是按照研究者的愿望去描述历史。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中,以逻辑推论代替历史求证的情况普遍存在,这已为学者指出并给予批判。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不符合学术求真的观念,这些观念容易造成新的主观解读,造成新的非真结论。
有些重要的提法,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推而广之,在不适当的研究领域套用,就会造成弊端。比如近十多年流行“守正出新”说。就现有材料看,这一主张应该是袁行霈先生提出,是其编写通用本《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方针。他在1999年发表题为《守正出新及其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的文章,谈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有关问题说:“守正出新是我开始就提出的编写方针,得到各编的主编同意,并贯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他对“守正出新”的解释是:
所谓“守正”,首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的精神,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学生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这部书的基点,如果不能守正,就会走上歧途,也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出新是这部书的生命,如果不能出新,就失去了编写的意义。[2]
袁先生这里对“正”和“新”都有明确界定:正是学术求实之“正”,正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新”是当前学术前沿之“新”,这“新”是建立在“严谨求实”基础之上的。“正”和“新”都指向“实”的精神。“求实”,体现了求真的精神,是学术研究永远需要追求的。从现实操作的层面说,编写一部作为通用教材的文学史,特别是官方推荐的文学史教材,为求稳妥和普遍的适用性,提出“守正出新”,自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它泛化为文学史研究普遍的原则,就不合适。“守正出新”的观念,古代已有。古人文学理论中的“正奇”“通变”观念,就与“守正出新”精神相通。这样的观念,用在文学批评上,要求文学创作既要守正,又要出新,是应该坚持的。但文学史的研究,是对既往历史的考察。这种历史的考察,无疑应以求真为第一要义。历史考察之“正”,应在“真”中。所以,作为一种泛化的原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提倡“守正”和“出新”,我都不赞成。什么是“正”,正与不正是有指向性的,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正,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就不正,甚至是“邪”。文学史研究要“守正”,就得以某些人、某些团体、某些阶层的意志为准则,那就很难求得真学术。要求古代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守正”,就回到了“态度”和“立场”问题上来,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等观念的影响,不符合求真的精神*袁行霈先生在谈论文学史的研究时则说:“要强调文学本位,文学史是文学本身的历史,不要把它看作社会史的附庸,或者把文学史当作某种意识形态的验证。”(《关于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古代文体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2月)。“出新”似乎符合当前的时代要求,但不一定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真学术应该是求真的学术。而一味地强调“出新”,有可能将我们研究引向为创新而创新的路子上去。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科学技术研究不同,与文学的创作也不同,它的宗旨不应该是创新而应该是去伪存真,“新”在“真”中,认识到了过去没有认识的“真”,或者更正了过去不“真”的认识,“新”就在其中了。去伪存真是努力接近历史的客观,而一味创新则可能为求“新”而偏离甚至失去客观。近些年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怪论,与一味求新、为创新而创新不无关系。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清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的主观解读,力求回归文学史的真实。
二、元代文学研究不实成说之检点
直到今天,元代文学研究中由主观解读形成的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成说依然存在,清理这些成说,学术研究才能进步。这些成说很多,我们略举几例。
从小到大,大家以往接触到的,多有审视的必要。大的,最难以立足的,比如元杂剧反封建、反传统道德说,元代叙事的俗文学占居文坛中心位置说。元杂剧作家为市井文人,失去了传统士人的品格之说,元代的诗文作家队伍与戏曲作家队伍对立说。现在看来,这些结论,多是研究者想象或依据某些理论推出的结论,不符合元代历史的真实。小的、具体的学术问题,如关汉卿生平问题,汉族士大夫耻为元用问题,以及“九儒十丐”问题,蒙古人反对开科举问题。有些曾被当作权威的结论,现在看来多不客观,有的还有些荒唐。这些成说不清除,文学史的研究就很难求真。但是,这些成说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清理,可能一下子还不容易接受。
先从小的、容易接受的说起。比如关汉卿的生平。有关关汉卿生平的材料很少,除《录鬼簿》上的简略记载以及[凌波仙]吊词外,还有元末一个叫熊梦祥的江西人,他长期仕宦于大都,写了大都地区的地方志,书名《析津志》,这部书上有一点记载。其他如《录鬼簿》介绍其他人时提到,《青楼集》中点滴涉及,元人诗如杨维桢《元宫词》中也有提到。这些都是可靠的。现在文学史描述的关汉卿生活状况,把关汉卿散套[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和明人臧懋循《元曲选序》作为重要依据。[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大家很熟,臧懋循《元曲选序》说:“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3]现在看来,这两则材料,都不能作为关汉卿生平的依据。
先说[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长期以来,研究者和文学史著作,都把这套散曲说成是关汉卿的自述。根据是什么呢?只是这套散曲用的是第一人称“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其他佐证材料,至多找到《析津志》的几句话,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4]。但这远不能证明此曲是关汉卿的自述。如果没有有力的佐证材料证明,就不能断定它是作者的自述。
相反,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说明,它不是关汉卿的自述。
首先,当时有不少类似作品,都明显不是作者自述。比如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也是第一人称:“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但从来没有人说这是杜仁杰的自述。更有说服力的是姚守中[中吕·粉蝶儿]《牛诉冤》,也是第一人称:“食我者肌肤未肥,卖我者家私不富。若是老病残疾,卒中身亡,不堪耕锄。告本官,送本都,从公发付,闪得我丑尸不着坟墓。”当然,这不可能是作者自述。这些作品大多是代言的而非自言的,很多是写了给别人唱的。所以,没有根据地说[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关汉卿的自述,是难以成立的。同时,关汉卿现存散曲,也基本上是代言体的,《全元散曲》收关汉卿散曲小令57首、套数14(含残套二)中,除套数[双调]《乔牌儿》不能肯定外,其他作品都绝非自言的。最有抒情言志意味的[南吕]《四块玉·闲适》,也绝对不是自言的,因为就现在所知他的生平,他没有“南亩耕,东山卧”的经历。那么根据什么就确定[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自述呢?
其实,像[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这样内容的作品,不仅关汉卿写,元代其他人也写。无名氏杂剧《百花亭》中的男主角叫王焕,他在剧中自夸风流,唱词内容与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差不多:
[满庭芳]俺也曾寻花恋酒,鸾交凤友,燕侣莺俦。俺也曾耽惊怕人约黄昏后,俺也曾使的没才学的滑熟。我是个锦阵花营郎君帅首,歌台舞榭子弟班头。双秀才你是个豫章城落了第的村学究,柳秀才你是个丽春园除了名的败柳,我王焕是个百花亭坠了榜的鑞枪头。
[上小楼]折莫是捶丸气球,围棋双陆,顶针续麻,拆白道字,买快探阄。锦筝搊,白苎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
[幺篇]折莫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作赋吟诗,说古谈今,曲尾歌头。洒银钩,夺彩筹,攧兰攧竹,更身材十分清秀。
[普天乐]水晶球,铜豌豆。红裙中插手,锦被里舒头。金杯浮蜡蚁春,红炭灸肥羊肉。惜玉怜香天生就,另一种可喜风流。淹润惯熟,玲珑剔透,软款温柔。
《百花亭》作者佚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可能是关汉卿的作品。如果说[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关汉卿的自述,这又是谁的自述呢?王焕显然是个虚拟人物,是《百花亭》作者的自述吗?没有办法证实。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也是如此,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那是关汉卿的自述*曲和词有些相似,早期的词基本上应歌而作,多是代言的,如温庭筠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只是关汉卿写过这样似乎荒诞的作品,很多人都写过。宋代高德全才的欧阳修,也写过类似作品。他有一首《醉蓬莱》,下片整个是一个女孩子偷情中的言说,写得声口惟肖: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5]
能不能说这是欧阳修的自述呢?肯定不是。他不过是写了给人唱的,词中主人公没有具体所指。关汉卿的《不伏老》也是如此。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的关汉卿小传,就没有采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的有关内容。我们应该效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
现在说臧懋循《元曲选序》中那段话:“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这一记载不可靠,为什么?很简单,如果我们发现一则材料中有很不靠谱的话,那么整个这则材料都不可相信。这则材料正是如此。所谓“元以曲取士”是极不靠谱的话,说明臧懋循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那么这则材料可信度,就成了问题。
关于关汉卿我们知道得太少,那该怎么办?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是孔子说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6]严谨才能避免错误。
关汉卿的生平是一个小问题,但小问题对于元代文学研究来说却有大关系。因为研究者认为,曲中所写,是关汉卿的生活态度,由关汉卿的生活态度,又推广为元代曲家的生活态度,并且拔高为曲家反传统道德的斗士精神。由此推论出了崇高而神圣的结论。如下文这样的分析,大家都很熟悉: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但如果我们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这段引文不再标明出处,不是要回避什么,而是这样的说法随处可见,无需表明具体出处。这样的说法,仍流行在我们的教材中、课堂上。但如果我们稍作冷静思考,就会觉得:难道“以关氏为代表”的元代曲家真是一帮这样的人吗?生活糜烂的人还会有“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吗?我们读元杂剧,感到其主题都是那样严肃,表现了厌乱思治的深刻主题,体现了剧作家对世道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对社会混乱的深切忧虑。难道这样的作品竟然出自一批“浪子”之手吗?如果关汉卿们要砸烂“传统文人道德规范”,又怎么解释关汉卿在历史剧中对忠孝节义的呼唤和张扬呢?是两个关汉卿呢还是关汉卿人格分裂呢?关汉卿只有一个关汉卿,他也不会人格分裂,只有一种可能:上边这样的分析,是研究者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大家都很熟悉,朱权《太和正音谱》将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朴刀杆棒、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头鬼面。”[7]从这样的内容划分可以看出,元曲是提倡和维护传统道德而不是悖逆传统道德的。元代文人胡祗遹概括当时杂剧的内容是“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涉及了政治秩序、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等各个方面,未见反叛传统道德的东西,反倒是从“乐音与政通”[8]的高度认识杂剧的教化功用。研究者还进一步概括出了元曲体现的人文精神:“元曲的人文精神内涵则可用一句话概括: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浪漫情绪,审美人生。这种人文精神在剧曲与散曲中都得到体现。”[9]这样的观点曾经很风行,到现在还为很多研究者引用并相信。除了“隐逸情调”我们可以在元杂剧作品中找到并落实下来,有几部元杂剧作品表现了“浪子风流”和“斗士襟怀”呢?恰恰相反,我们从元曲中强烈感受到的,是厌乱思治的精神与情怀,是对清平之世的向往,是对重建社会秩序与人伦道德的呼唤。不管是历史剧、公案剧,还是家庭伦理剧,都体现了这一精神。那这所谓的元曲的“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经学史家朱维铮批评20世纪的一些经学史研究,是“用逻辑推论代替历史考察,先立论,后求证,乃至随意搬用某种既定模式,外来的或本土的,新异的或古旧的,而后缘饰若干历史例证,便算体系构成”*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之《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经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这种现象,在文学史研究中也普遍地存在着,其严重程度,与经学史研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窦娥、崔莺莺,都被研究者赋予了斗士精神,窦娥要和整个黑暗社会斗,崔莺莺要和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纲常斗。当我们坚信这样神圣的主题时并没有思考一下:生活在中国13世纪的杂剧作家们,从哪里获得了如此的思想高度?其实,关汉卿、王实甫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高度,那是20世纪的研究者的思想高度,关汉卿生活的时代,也不需要打破伦理纲常。那些结论,是研究者逻辑推论的结果,甚至是主观想象的结果,而不是通过严谨的历史考察得出的认识,不符合文学历史之客观。
如果作深入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元代一百多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法制缺失,社会混乱。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道德体系几乎崩溃。元代文人面对的社会问题,绝不是“反封建”“反传统道德”,而是道德重建。用当时人的话说是:“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十七,《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基本的人伦观念需要重建。忽必烈时的郝经说当时:“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余土苴,万亿之能一存。”*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二《立政议》(中统元年八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李瀚刊本。看看当时的文献记载,就知道社会混乱到什么程度,道德危机严重到什么程度。在个别地区,基本的道德规范几乎荡然无存。岌岌可危的道德观念,还需要关汉卿们去“反”、去打破吗?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不过是当时一些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关汉卿的大量杂剧作品,都不是要“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恰恰相反,是呼唤社会道德的重建。
三、以求真的执着推进元代文学研究
以学术求真的态度审视和清理这些不客观的成说,进一步要以求真的精神,下求真的功夫,考察元代文学史的真实状况,客观认识元代文学。那么,我们的元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求真?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必须切实了解你所研究的时代,必须切实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第二,必须对文献作认真甄别,从大量可靠的原始文献中得出客观的结论。
第一点,古人有所谓“知人论世”说,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0]古今对“知人论世”有各种解说,一般认为“知人论世”是为了“尚友古人”。但同时,这也是读书之法。王国维就说:“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11]鲁迅则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2]王国维和鲁迅的解说,是就认识一位作家说的。推而广之,研究并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那就更应该深入而确切地了解那个时代,深入而确切地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情绪。如此“知人”不仅仅是“知”具体的某一位诗人或作家,而是“知”一个时代的诗人或作家;“论世”就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的家世身世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是整个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状况对文人、对诗人有什么影响。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不了解那个时代不可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元代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都出在了对元代社会和元代文人的不了解上。
真正了解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人,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以求真的精神,下一番求真的功夫。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13]哲学史如此,文学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又说:“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3]文学史研究中这类问题很多,特别是元代,这类问题更为突出。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对于这些特殊性不了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误解,用主观的想象代替历史的考察。比如元曲反封建道德说,就是由于对元代社会不了解。元代的传统道德几乎崩溃,文人要救世,首先是要拯救传统道德,哪里还会有反传统道德的问题?将元曲的文人精神概括为“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则表现出对元代曲家的不了解,即对“人”的不了解。如果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曲家都是与当时社会和政权对立的,那么如何理解下边的几则文献:贾仲明补《录鬼簿》吊词吊赵子祥:“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14]杨维桢《宫词》:“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杨维桢:《复古诗集》卷四,明成化刊本。虞集《中原音韵序》:“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罗宗信《中原音韵序》:“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之未有,实治世之音也。”[15]这些都是常见的文献,研究元曲的人应该都看过。这类文献在元代大量存在,我们举胡祗遹的四首诗,两首《诸宫调》,两首《太平鼓板》,尽管所写不是杂剧,但都属俗的艺术:
谈锋衮衮决悬河,嚼征含宫格调多。唱到至元供奉曲,篆烟风细蔼春和。
古人陈迹不须言,圣代文章合剩传。留著才情风调曲,缓歌中统至元年。(《诸宫调》)
三弄桓伊声正和,猛风白雨战新荷。岁丰民乐君恩重,不让梨园法曲歌。
乐音先自得佳名,万寿筵前乐太平。更倩东风扶醉袖,一时繁剧弄新声。(《太平鼓板》)[16]
元代类似文献很多。元杂剧以及当时其他的俗的艺术形式,都不是要和当时的时代、社会和主流的社会观念对立的。元杂剧研究的有关结论,应该建立在全部相关文献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不可信的。
第二个问题也似乎是老生长谈。任何研究都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并对材料作去伪存真的甄别,如此才能得出接近于客观的结论。但是,就元代文学研究的情况看,这个似乎人人都懂、每个学者都强调的理性认识,在研究中贯彻得并不好,很多不可靠的材料被作为重要论据在使用。这个问题,上文已经涉及,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比如,元代文学研究中不是以元代文献为依据,而习惯于使用明人记载。而明人看不起元人,不读元人书*胡应麟曾批评明人不读元诗,其《诗薮》(外编六)摘录元人诗句数十联,以为这些诗可“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其实明人也不读元人书,对元代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对元代的情况有些信口开河。如史学家陈垣所说,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励耘书屋丛刻》本,第259页。。明代张燧有一部书叫《千百年眼》,里边涉及元代的东西很多都是瞎说,可是我们的研究者却愿意相信。我们以其中一条《中华名士耻为元虏用》为例,看看这部书有些内容多么不可靠:
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又欲除张、王、赵、刘、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然每每尊其种类而抑华人,故修洁士多耻之,流落无聊,类以其才泄之歌曲,妙绝古今,如所传《天机余锦》、《阳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厢》等记,小传如《范张鸡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赵礼让肥》、《马丹阳度任风子》、《三气张飞》等曲,俱称绝唱。有决意不仕者,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人不能识。又有高飞远举、托之缁流者,国初稍稍显见,金碧峰、复见心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匿,姚广孝幼亦避乱,隐齐河一招提为行童。古称胡虏无百年之运,天厌之矣![17]
这可以说是一条混乱荒唐的材料,但直至今日,很多研究者屡屡称引,深信不疑。我们看看他有多荒唐。先从有点根据的事情说起。元初有没有“欲尽歼华人”的事呢?不能说全无影子,《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有这样的记载: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官无储。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18]
别迭之言,在《元史》不过作为表彰耶律楚材功绩的铺垫。这位“近臣别迭”是什么人呢?文献中很难查到,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则作“中使别迭”*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十七,《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所谓中使,就是太监。蒙古时期的太监,在大汗帐中没有什么地位,对于大汗决策不具备大的影响力,也不是决策层的成员。就一个太监的一句话,后人却能找到并加以发挥,到张燧这里就成了“欲尽歼华人”,从行文看,似乎政府有这样的计划。“悉空其人”也不必然是“尽歼”。至于“又欲除张、王、赵、刘、李五大姓”,元代确实有过这一说法,但不是“国初”,而是元末顺帝时期,提出这一荒唐之说的是当时宰相伯颜,时间在后至元三年(1337),“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19]。这时耶律楚材去世已经快一百年了(耶律楚材1244年去世),怎么可能“又谏止之”?伯颜荒唐建议当然地被元顺帝否定,杀五姓汉人不成,他本人却在不久后被杀了。可以看出,张燧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此外,他所说的《天机余锦》是明人所编的一部宋、金、元、明词的选本,与元散曲(歌曲)无关,可见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书。《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是进士,并长期仕宦,他的老师黄溍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怎么会“流落无聊”?金碧峰是一位僧人,在元末地位很高,明人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有关于他的记载:“夫金碧峰,乃陕西乾州永寿县人,姓石,名宝金。自幼依云寂温法师为僧,及长,往西蜀从如海真公悟道。入五台山。至正戊子,元顺帝召至燕都,赐号寂照圆明大禅师,主海印寺。国朝洪武二年,召至南京,住天界寺,召问佛法及鬼神情状称旨。”*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十二,明刻本。这怎么是“深自藏匿”?另一高僧复见心就是元明之际的释来复,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僧,在元代很活跃,与馆阁大老虞集、欧阳玄关系密切,并曾主持天宁寺,也决非“深自藏匿”者。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耻为元虏用”。至于“断其右指”,更不知何据。用自残的方式拒绝出仕的案例,明初有,“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以拒绝出仕,结果遭人告发被捕,朱元璋亲自审问,“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20]元代则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类事。姚广孝就是明鼓动燕王朱棣起兵的僧人道衍,他是苏州一带人,那么他幼年避乱,是避元末东南各路乱军之乱,与蒙古军或者元政府军无关。就是这样荒唐的材料,研究者却愿意相信,拿来证明元代文人对蒙古统治者的不满与反抗。这样怎么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相关的,还必须高度尊重文献原意,不能以研究者的主观意愿曲解文献。在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中,曲解古人文献的例子是存在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引用这样一则材料:“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于是形成了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九儒十丐”说。这段话见于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是证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文化不昌明的铁证。细读原文,才知道文章原本是批判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科举程文无用之士,他们只会作场屋无用之文,造成了文化厄运,不仅“文运不明,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并且“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这“三十年”,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1279年宋亡入元,这“文运不明”的三十年主要是宋代的事。刚刚入元第九年,谢枋得就在这篇文章中断言“文运大明,今其时矣”,他为人们可以抛弃“场屋无用之文”而作“经天纬地”有用之文而欢欣鼓舞。问题很清楚:造成儒者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宋代科举造成的儒者无用。所以,谢枋得说自己宁可坐肆卖卜,也不愿与这样的儒者为伍。谢枋得坚信,如果你是有用之儒,如果你所作是有用之文,在元代就一定能为天下所重:
天地之大,无儒,道亦不能自立,况国乎?秦之后为汉,嫚儒者莫如高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为董公,为子房,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竖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贵者,不自子始乎?*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四部丛刊》续集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
他以汉高祖比元世祖,“高帝”所嫚者,是无用之儒,所尊者,是有用之儒。尽管谢枋得本人决不仕元,但他鼓励年轻的方伯载为世所用,为有用之儒。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时期,元代文学史也就具有其特殊性。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史研究界更是长期以别样的眼光看待元代历史和元代文学,由此形成了很多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这些看法长期流行,使得文学史研究界长期以来不能客观评价元代文学。这不仅影响了对元代文学史的认识,也影响着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在以往的文学史观念中,元代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断裂带,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在元代似乎中断或变得模糊了。澄清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成说,客观评价、准确认识元代文学,不仅是元代文学研究所必须,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所必须。
参考文献:
[1]王元化.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N].文汇读书周报,1999-05-01.
[2]袁行霈.守正出新及其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1999(6).
[3]臧懋循.元曲选序二[M]//元曲选: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8.
[4]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名宦传[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8.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
[7]朱权.太和正音谱:杂剧十二科[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
[8]胡祗遹.赠宋氏序[M]//胡祗遹集.魏崇武,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246.
[9]梁归智.元曲的人文精神[N].北京科技报,2004-12-15.
[10]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1.
[11]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M]//观堂集林: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25.
[1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M]//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79.
[14]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6:334.
[15]周德清.中原音韵:卷首[M]//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合肥:黄山书社,2006:227,231.
[16]胡祗通.胡祗遹集[M].魏崇武,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202.
[17]张燧.千百年眼[M].贺天新,校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99.
[18]宋濂.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58.
[19]宋濂.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843.
[20]朱元璋.大诰三编:第十:秀才剁指[M]//钱伯城:全明文: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02.
(责任编辑朱春花)
Re-Examining the Accepted Conceptions and Seeking for the Academic Truth:How do We Study the 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ZHA Hong-d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Yuan Dynasty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there still exist a lot of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 which are popular as some authoritative conclusions but detrimental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search.If they are not settled, the objective opinions cannot be accepted by the academic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examine these formed conceptions with determination of seeking for the truth and remove all the subjective demonstrations that are inconformity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order to lea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Yuan Dynasty back to the objective direction.
Key words: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 Yuan Dynasty; accepted conceptions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6)03-0084-08
作者简介:查洪德(1957- ),男,河南内黄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辽金元文学、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元代文化精神与多民族文学整体研究”(10AZW0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