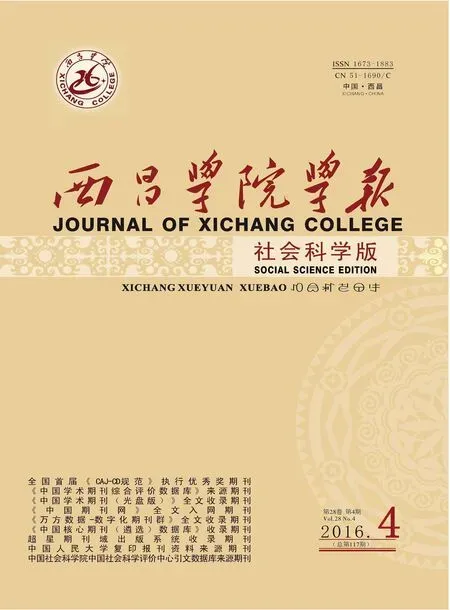石里克语言分析与禅宗超语言
钟艳艳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乌鲁木齐830017)
石里克语言分析与禅宗超语言
钟艳艳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乌鲁木齐830017)
自惠能以来的中国禅宗,无论是在自我修行的内在证悟方式上,还是在接引弟子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手段上,皆闪烁着“不立文字”的影子。通过杜绝语言文字对真如妙法的曲解进而引导信徒透过内心之虔敬而到达智慧彼岸。相较于西方20世纪开始广泛流行的以石里克等人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探究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前景时,提出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从而解决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与中国禅宗之“不立文字”似有相反而又相通之处。在双向研究禅宗的超语言逻辑与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分析路向的基础上,对二者通而不同之处进行研究,以求获得新解。
石里克;宗教体验;禅宗语言;惠能禅宗;超元思维
20世纪初,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在欧洲大陆兴起。他们强调语言分析实为哲学体系之根本,对语言的地位给予大跨度的提升,甚至将语言列为现存一切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释之源。与其说石里克意识到形而上学是不可说的,毋宁说形而上学问题是无意义的,因而他试图强调语言的分析功能来对形而上学问题避而不谈。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是无法由经验证明的,可总有人试图“把我们所不曾体验过的东西归结为我们体验过的。但这是大错特错的。要被解释的东西必定总是我们体验过的。”[1]27
而自东汉初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独具特色的抽象理性分析和超验的宗教幻想就使国人将它与中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思维模式区分开来。自惠能以后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沿袭佛教的基本教理、宗教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将凭借语言和概念的修持方式转为摆脱语言概念的修持方式,这成为惠能禅最具特色的一面。
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以清除形而上学”为口号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中汲取有利的养分,演化成为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对语言进行分析是对现有一切哲学问题最完美的解答。自德国哲学家石里克组建“维也纳学派”以降,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甚至自然科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里我们由石里克入手,研究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路向。
一、石里克:体验不是知识
后期石里克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将知识与体验等同起来的观点时,提出“体验不是知识”的思想。石里克所言的“知识”并非现在人们普遍意义上使用的知识,而是关于主体与对象间关系的表述,是一种经由语言表达的符号与符号间或符号与经验事实间的对应关系。它并非主体对对象的反映,不具有具体的体验性,只具有一种抽象的符号关系。由此进一步延伸,主观性的体验必然具有体验主体之主观性与个人性,不同个体的主观体验是不同的,且人们无法体验他人的体验。因而,体验是无法通过语言表述而互相交流的,此时体验无法表现为符号与经验事实间对应的关系。同时语言是一种由人创造并相互之间形成默认的符号,那么在面对上述这种个体独有的体验时,语言就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是无用的。将石里克的这一思想运用宗教学原理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推为:宗教信仰者神秘的宗教体验是他人无法获得的,就是获得也绝不会是相同的,因而宗教体验也是难以通过语言这种由人制定的符号进行表述的。石里克打了个比方:“一个对象绝不可能复制的恰如本身自在的那样;因为每一幅画都必须从一定的方位由某个绘画主体画出来。因而,它只能提供对象的一种主观的、仿佛是从一定视角来看的投影图。当然所使用的记号和配列的方法的确带有认知者加上的主观的性质。但所得到的配列并不显示出这种主观性质的痕迹。”[1]117
但石里克并未因此而否认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他认为,语言对于感情的直接表达虽然不能给予我们关于存在的知识,但它能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充实个体内心体验,激发人的内心情感。这种对于内心感情的激发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是属于生活本身,譬如在艺术和宗教里。在这里,石里克肯定了语言在宗教感情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语言在宗教组织中起着传播“真理”的作用,是引导信徒接近甚至走向被崇拜对象的桥梁。但也只是走到这里,因为一旦语言超出了表达宗教感情的范畴而越入宗教体验,便又会被视为愚不可及了。
从石里克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思想也可以看出些许与禅宗语言观想通之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最早由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中提出。发展至石里克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元素。石里克在区分这两种命题时指出,分析命题与经验事实无关,在逻辑上是“先验的”,也是逻辑永真的。而综合命题则是来自对经验事实的综合,根据经验事实的具体情况有真假之分,可以将其判定为“后验的”。他说:“把判断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这种划分十分精确,而且是客观地有效的,它不依赖于作出判断的人的主观看法,也不依赖于这个人的理解方式。”[3]305在石里克看来,有关实际经验事实的真理是不可能单独由先验逻辑来证明的,而关于“超验的”存在也无法通过思辨而得到证明,经验的可检验性就成为关于经验事实是否有意义的唯一标准。既然实际的经验事实在实践上无法被先验逻辑证明,那么作为宗教体验的经验事实自然也无法由思辨证明,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二、禅宗:真理拒绝语言
海德格尔曾说:“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几乎是不可说的。倘若我们来沉思这种奇怪的情形,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对此情形的任何假说初听起来都是令人诧异的、不可理解的[4]147。反观中国哲学的各家,即使他们在思想上相去甚远,但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国哲学发展脉络上的一条明显的特征:道本无言,借言以显,得意忘言。无论是庄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5]408,还是惠能的“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关照,不假文字”[6]54都表明:语言文字于人而言是有作用的,但并非是一切物之依托。
历来的学者对于禅宗的看法总是各持己见,而麻天祥先生对禅宗思想形成的看法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禅宗之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老庄思想是离不开的。“禅宗思想的形成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是任性逍遥、娴习老庄的中国知识分子,假佛教之名,对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重新整合并予以大众化阐扬的结果。”[7]6一句话,禅宗是大众化的老庄哲学。倘若我们站在他的立场来关注禅宗思想就不难发现,禅宗与老庄虽风格迥异,但都体现出一种不执著于世间万象的豁达态度。惠能禅虽讲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但也未曾执著于世间如浮云过往的表象,而追求“无住”、“无念”、“无相”。本来普罗世间的大象万千,一般事物通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可以轻易把握的,而对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和关怀,则是超出了人们意识可思考的范畴,即从“有”走向了“无”。前者用言、象可以认识和把握,后者则是超越一般思维和现象的。如果执著于表面,反而会妨碍我们对“意”的把握。那么有限的语言、事物的表面现象自然也就不能尽意了。而以“妙万物以为言”的禅的境界最终成为绝对超越的终极关怀而存在于人的思维范围之外,故有“不落言诠”“不着两边”超元思维方式之说。
惠能认为佛性本净,离言离相,对禅的认知和把握,对自心本性的证悟,只能靠自身实践,而非言教。早在僧肇时期就提出了“即体即用”的观点,他认为在人们将有、无置于对立的二元思维状态下,事物的存在并非实有。后来禅宗形成的有名的观点诸如“出入即离两边”、“说似一物即不中”就是在僧肇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可谓是一语道破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惠能以下的禅门弟子常用隐晦含蓄的诸如机锋、棒喝的手段来表达超越言象的意境,其目的不过是要启发习者看破思维中已成惯例的二物相对待的模式,直指本心,观照自性,这也是实现超越、了悟自性的方便施设或权宜手段。虽然胡适先生把禅宗发展后期衍生出的诸如呵佛骂祖这样的极端行为看作是“发疯”,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建立在禅宗轻视语言、破除二元思维对立的思想上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接引方式,将禅宗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倾向推向极端。
既然禅宗极力否定二元思维对立的模式,那么作为人类思维表现形式之一的语言符号,自然也是禅宗所摒弃、亟待破除的对象之一了。虽然禅师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语言,但他们更加追求的则是“着相”而非“离相”,“用语言”而不“住语言”。语言所能表达的无非是某一类事物,大多时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和反映,虽然语言并非机器的、刻板的反映,但是关于终极真理则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表示的。在禅师看来,禅法微妙高深,只有冲破语言、符号对人思想的束缚,才能明心见性,直了成佛。正如奥托所说:“一切语言只要是由词语构成的,就旨在传达观念或概念——这是语言的意义所在。一种语言在传达观念或概念时愈是清楚和没有歧义,此种语言便愈好。因此,用语言来探求宗教真理,便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强调上帝的‘理性’特征。”[8]2禅门真理拒斥以理性的逻辑思维力来试探不二法门,否认语言具有说明真如妙理的能力,因而导致禅师们从根本上否定理性思维对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进一步导致他们否认人思维的认识力。而他们之所以否认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则是由于在他们看来,真理是超人间、超现实的,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的基础之上的,不能通过科学实践来证明,他们夸大了人的认识力和语言表达力的局限性,认为通达真理不能依赖于语言及理性思维。这一点与柯拉柯夫斯基“在逻辑上不存在从有限世界通向无限的途径”[9]56是不谋而合的。
佛教讲八不中道,即不一不异、不常不断、不来不去、不生不灭。这里完全采用了“遮诠”的否定性方法,其目的正在于教人识破生灭断常之类的二元对立的感觉经验的虚假性,认识到逻辑思维的局限性,从而发现大千世界中超二元对立的真实不虚的存在,特别是超越生死的真实。在佛教看来,这种超现实的真实的存在,不是科学可以考证的,逻辑也无法说明,语言则更显得苍白无力了。石里克认为,如果我们对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存在产生丝毫的怀疑精神,那么一定要澄清的是,驱使我们对其产生怀疑的并非是好奇心,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我们希望由此而获得对人类意识的深处有所洞察。”
三、通而不同之我见
综合石里克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以惠能为代表的禅宗的语言观,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二人隔了漫长的时间空间的距离,但思想依然闪烁着某种类似的光辉。
惠能时期的禅宗在广泛接受由社会动荡产生的大量流民的基础上,也是出于方便流民接受禅宗思想、扩大禅宗社会影响力的初衷,惠能摈弃了以往禅师的修持方法,既抛弃了坐枯禅的宗教修习,又改革了传统上以佛教典籍为核心的教义学派。且自道信之后的禅师对禅宗游化为务的生存方式进行的改革也为禅修提供了更加稳定的修行环境。由此观之,表面上惠能废除了以往大部分的宗教修持方式,实际上是隐秘的扩大了修持范围:将外在的宗教束缚转向对于个体内心的修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10]9禅宗将宗教的修持复归于自性的清净,旨在引导人们跳出烦恼迷象的世间,透过最普通的现象把握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在这里,不仅是语言失去了作用,就连宗教团体日常的功课也只能保持缄默。
然而20世纪的石里克,这位不幸被精神病患者枪击而早亡的哲学家,在论证日常使用语言逻辑的苍白时,将绵延于西方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问题推入了不可见的深渊,从此人们再不会陷入纠结于本原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泥淖之中,而只需要分析语言便可解决哲学体系现存的一切难题。
诚然,语言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之一,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它对我们如此重要,但是在面对终极难题的挑战时它依然有口难辩。人类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的皆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么我们对关于世界的讨论,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语言的讨论,我们关于所表达的认识的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对于表达时使用的句子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从对世界的探讨转向了对语言的研究。语言分析哲学家将绵延多年的对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转向语言分析,轻松地化解了萦绕在人们心头多年的难题,这也是语言分析哲学多年来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而在禅宗看来,人所能反映并认识的客观现象及规律皆是透过心在起作用,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世间万有的模样,“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2]595也可以表述为泰戈尔的“独立于人之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一点表现在禅宗的公案上也是案例颇多。譬如有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答:南面看北斗。显然北斗星位于背面,那么禅师又为何指引弟子南看呢?弟子南看就会发现难免并无北斗,而他一回头北斗恰在其对面,这就是禅宗神秘的独具特色的内心反省功夫:无须向外用力,佛法就在心在,回头既是。而这又恰恰能体现出,禅宗重视内求内证忽视语言文字,正所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石里克在分析语言的意义及有效性时,将形而上学难题推出哲学大厦体系,在批判人们日常使用语言时造成的语义含混、逻辑表达错误的现象时,将终极问题搁置于语言表达的对立面,以语句的逻辑完整性及表达有效性来拒斥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这与禅宗在触及“真如”时对待语言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一方面强调语言的逻辑完美性而排斥虚幻、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另一方面否认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而否定语言表达,将其视为接近真理过程中的障碍,二者的破、立对象完全不同。在石里克那里,科学的语言表达可以解答一切难题,套用禅宗的话语可表述为“一灯能灭千年暗”。而惠能的禅宗虽然格外强调不落言诠,但最终也未能完全逃出语言的圈子,以至于后来的禅者会错意,将对答机锋流于形式化而产生了胡适先生认为是发疯的离奇古怪的公案、话头,最终将不立文字演化为不离文字了。
在这里,重视语言与摈弃语言的双方在论证自身理论时采取的手段及最终目的都是截然相反的,但似乎又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更多关注语言的目光。这点不难理解,生活中这样的例证唾手可得。正是由于双方对语言作用产生的两种较为极端的看法,才使得语言在不经意之间成为思想的主流。即使惠能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6]60,但在实际操练中依旧无法彻底摆脱文字的羁绊。虽然禅宗提出的“遮诠”避免了语言的过度解释、过度理解,但在修行过程中并非每个个体都生而具有禅门奉为珍宝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慧根”,因而难以避免地导致不落言全、不执两端的破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语言表达流于形式、落入俗套。就近来说,宋代以后兴起的文字禅就是“不立文字”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麻天祥先生将宋以后的文字禅视为将禅宗否定二元思维对立推向极端的代表,欧阳竟无居士也将这中禅法斥为野狐禅。
那么,既然石里克之语言观与禅宗之“不立文字”的思维方式差之千里,为何要将二者加以比较呢?或许这里使用“相反相成”一词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我们忽视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别,简单地对其思想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石里克重视语言,最终目标是利用语言的逻辑表达完满性解决哲学体系中的终极难题。而禅宗之“不立文字”是在排斥语言文字乃至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上,引导人透过二元思维、普罗现象迷雾之纷扰去接近最根本的智慧,即真如彼岸。我们可以大胆的设想,倘若惠能与石里克生活在同一时期,或许二者会产生激烈的思想论战也未可知。
[1]石里克.普通认识论[J].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道元.景德传灯录[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
[3]涂纪亮.英美语言析学概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马恒军.庄子正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6]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麻天祥.禅宗文化大学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奥托.论“神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9]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董应龙)
Analysis on Schlick's Language and Zen Transcending Language
ZHONG Yan-yan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17,China)
The wisdom of"no word"flourishes in Chinese Zen Buddhism ever since Huineng era,whether in the way of self-cultured enlightenment or guiding disciples.It allows followers to achieve wisdom by inner pietism without the misleading from words."No words"of the Chinese Zen seems to have dissimilitude but actually similarities with logical positivism in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Schlick in 20th century.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Zen and logical positivism on transcending languag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Schlick;experience;Zen language;Huineng Zen;super unit thinking
B521
A
1673-1883(2016)04-0039-04
10.16104/j.issn.1673-1883.2016.04.009
2016-06-10
钟艳艳(1993─),女,新疆吐鲁番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