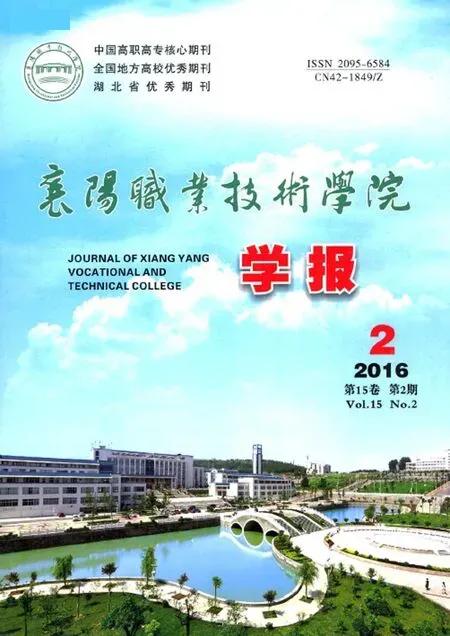2000年以来毕飞宇小说研究综述
候登登,张 培
(辽宁大学 文学院, 沈阳 110036)
自2000年到2015年,研究毕飞宇小说的论文(中国知网)共有1 108篇;自2001年,以“毕飞宇”直接作为题目构成的硕博士论文72篇,学术会议论文5篇,关于毕飞宇的访谈,共有10次。国内较早研究毕飞宇小说的批评家是汪政,李敬泽、沈杏培、吴义勤、王彬彬、张莉等批评家也对毕飞宇及其小说进行了相当透彻的分析。
一、文本透视
(一)内容层面
1.母题研究:首先,毕飞宇是个“依赖”记忆创作的小说家。记忆本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开始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1]但是记忆成为文学的材料或创作母题则十分久远,只是当时的人“只在此山中”,所以“云深不知处”。批评家洪治纲在《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提出,记忆并非一成不变,具有丰富的可塑性。毕飞宇的小说有些是写“文革”记忆(《平原》),有些带有自传性质(《那个男孩是我》)。批评家张莉深入地解剖了毕飞宇的“记忆”,将毕飞宇的创作理解为记忆的重塑,主要呈现为历史的重读、“文革”的重写、历史与现实对照等方面,这样的分类符合毕飞宇小说本身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其次,是毕飞宇对“疼痛”母题的写作。文学创作中,有关疼痛感的写作让人并不陌生,在余华、阎连科等人的小说中十分常见。周蕾说,“当代文学最迫切的‘当代性’就是直面当代的问题,书写当代的疼痛……作家选择正面强攻当代的‘症结’,书写当代的危机和痛感,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2]毕飞宇在回首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他创作的母题是两个字:疼痛。“无论是在远离现实的孤岛,还是在物欲纵横的都市与落后的乡村,毕飞宇都尊重异乡人在生存中面临的文化碰撞以及现代与传统冲突中遭遇到的伤害,把笔触伸向他们的内心深处,写出他们的不甘与挣扎,准确表达出他们梦想破碎过程中的疼痛,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的深层思考。”[3]笔者认为,对毕飞宇小说“疼痛”母题的解读很有必要,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稍显不足。
2.形象注解:毕飞宇为当代文坛贡献了很多经典形象,尤其是具有恒久魅力的女性形象。批评界对“玉米”形象的研究文章十分集中,而对于“玉米”之外的女性形象研究较少,“扎堆儿”现象反映了《玉米》在当代文坛的巨大影响。
解读玉米形象的文章有:翟传增《毕飞宇〈玉米〉中玉米形象解读》及黄河《乡村女性的生存悲歌——论毕飞宇小说〈玉米〉的人物塑造》。翟主要从玉米的身世和性格谈起,“人们习惯于说长兄为父,我以为作为长女的玉米也同样‘如父’,因为除了她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之外,她还有着强烈的父权意识。”[4]笔者认同翟的“长女如父”的观点,在阎连科《瑶沟的日头》中,“我”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姐对我甚是疼爱,凡事总能护着我,也佐证了“长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黄在“文革”的背景下审视《玉米》,将玉米和王连方、柳粉香、玉秀放置一起解读。父亲是权力的滥用者,而玉米是权力的维护者;玉米和柳粉香都是处处争强的乡村女性,都没能逃出婚姻的不幸。玉秀作为权力的“迷狂者”,和玉米一样崇拜权力。翟的研究从玉米的性格始到玉米的命运止,黄则在权力的身份认同中完成了玉米形象的解读,可谓各有千秋。
3.主题诉求:现代性是毕飞宇小说中的重要主题。毕飞宇初登文坛,就创作了《孤岛》《楚水》这样具有先锋意识和现代性的作品。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与苏童、余华等处于同一时代,却没能在当时获得太多的光环。尽管如此,毕飞宇坚持高质量的写作,最终为他带来不俗的成绩。翟文铖在《论毕飞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中把毕飞宇的创作按题材划分为:拟历史、乡村和都市小说,无论哪种题材的创作,都包含着毕飞宇写作的现代性。毕飞宇说,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最大。其实,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不仅深刻影响了毕飞宇,也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一批先锋作家,甚至当下文坛的很多作家。
毕飞宇对异化这个主题也很感兴趣。毕飞宇也曾风趣地描述自己被异化的感觉,“我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把电脑打开了,文稿跳出来之后我愣了一下。这个感觉让我伤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顾茫然……”[5]徐安辉也在他的文章中探讨玉秧生命、灵魂、人性的异化背后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合理的生存方式。他的观点是,社会呼唤着为生命创造一个和谐融洽、充满理性以及关爱和尊重的生存环境。不仅是玉秧,毕飞宇笔下的女性都是被“异化”的典型,玉米与权力、筱燕秋与执着。
(二)形式层面
1.叙事立场:关于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视角,批评家们众说纷纭,比如边缘叙事、日常化叙事、女性叙事、权利叙事等。笔者认为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和标签,仅凭几个标签式的名称难以概括。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特色和他的经验、阅历分不开,在不同的阶段会形成不同的叙事风格。文章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视角和日常化叙事视角作为研究对象。
毕飞宇被批评家李敬泽称为“最了解女性的中国作家”。毕飞宇对于女性的了解,到了令人惊讶的境界。了解毕飞宇的创作,这当然是一个捷径。对于女性书写,毕飞宇更多地关注女性生存和命运悲剧。譬如,赵林云在《论毕飞宇的女性悲剧书写——以〈青衣〉〈玉米〉为例》中,阐释了筱燕秋和玉米的性格和命运历程及二人对命运的搏击之路。“在一个人的完整生命中,肉体和灵魂应该是和谐地融为一体的,但是在筱燕秋和玉米那里却是分离,乃至是欠缺的,不自由的。”[6]也许她们抗争的结果并不如意,救赎之路遥遥无期,但起码证明了女性的存在与价值。
王春林分析了毕飞宇小说深受读者青睐的原因:将人物的心理世界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的心灵流淌中完成小说的建构,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苏妮娜细化了毕飞宇的“日常”,即表现日常百姓的生活图景(《蛐蛐 蛐蛐》)和展现时代风云(“文革”)下的日常(《怀念妹妹小青》)。苏妮娜的创新在于把“场”的概念引入研究,王家庄作为一个“张力场”,它内部环境是严苛的(村俗生活的是非和议论),还受着来自外部的作用力(“文革”时代的混沌与疯狂)。
2.言说格调:毕飞宇小说的语言特质最早引起了汪政的注意,汪政把毕飞宇的写作称为“语言的宿命”,汪政和毕飞宇在对谈中深刻探讨了小说语言对作家的重要性。毕飞宇提出小说家作为语言的实践者,要尽可能保持主体性。他的小说语言风趣,近乎戏谑,带有很强烈的批判性,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之下波涛暗涌。《玉米》里写王连方和村里的女人通奸,他只说自己“帮帮忙”,简单的三个字隐含着丰富的内容。王彬彬把这种性描写总结为“性话语”。毕飞宇小说中有很多写性的笔墨,不仅写性,还用性去隐喻别的东西。《雨天的棉花糖》把战争的惊心动魄比成男女做爱;《青衣》中把霓虹灯下的雪花比作妓女,而高楼则是嫖客。可以说,“性话语”在毕飞宇小说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二、跨学科研究和文化研究
毕飞宇小说的跨学科研究,主要体现在:运用翻译学理论考察《青衣》《玉米》在域外的传播;运用版本学的理论,阐释了毕飞宇小说版本的修改现象,如沈杏培;关于毕飞宇小说中的伦理书写也有少量研究文章。另外,近期的《毕飞宇苏北书写的文学地理学意义》说明了小说创作的地域性表征,尽管作家或流派地域性的特征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对毕飞宇研究却是一个必要的新视角,它显得姗姗来迟。
文化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毕飞宇小说中的“鬼文化”研究,如董之林《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关于毕飞宇的小说》,这来源于毕飞宇的一篇文章——《我们身上的鬼》;另一个是毕飞宇小说中“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解读,如吴义勤的《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阅读毕飞宇小说,读者总是被文本中弥漫着的浓厚的哲学气息吸引。跨学科的研究总体上不算丰富,我以为还有开拓的空间,譬如,从毕飞宇作品中看。
三、毕飞宇小说研究的空缺与展望
毕飞宇早期的创作基本是中短篇小说,写作风格是先锋的、现代的。从长篇处女作《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开始,是毕飞宇创作的转型,他形式的先锋收敛并向内转,叙事风格更接近现实主义。张莉把毕飞宇的现实主义命名为“新现实主义”。毕飞宇的前后期风格的变化,在很多学者的文章中有所涉及,但没有独立系统的论述。另外,毕飞宇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也十分欠缺。张立群把毕飞宇同苏童的创作进行比较,主要从二人共同的文化地理空间(同住南京),对历史文化的认同追忆,对短篇小说形式的迷恋及儿童视角和女性书写的维度去考察,这份研究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旗帜鲜明地进行“比较”,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
婚姻是人生的重要构成,也是小说的基本题材。毕飞宇对失败的婚姻情有独钟。他笔下的“婚姻”,因而凸显破碎的形状,既揭露故事的悲剧性,又显出强烈的批判意味。那些破碎婚姻构成的家庭悲剧背后的教训,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然而这方面尚没有学者研究,希望自己的发现能引起学界的关注。
毕飞宇的创作已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跟随作家创作的脚步,学界的批评和研究也应予以跟进,今后对毕飞宇小说的研究,可能会在毕飞宇小说创作的地域性有所体现,或是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以及毕飞宇小说中的文化现象探析。此外,毕飞宇小说中还为我们塑造了一批个性饱满的男性形象(端方、耿东亮、王大夫等),学界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对女性形象的阐释上,这或许是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J].学术月刊,2012(7):126-130.
[2]周蕾.见证“疼痛”的写作——论余华笔下的“中国故事”[J].当代作家评论,2014(6):116-126.
[3]田祝.异乡生存之痛——毕飞宇小说疼痛母题解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97-100.
[4]翟传增.毕飞宇《玉米》中玉米形象解读[J].河南大学学报,2005(5):60-61.
[5]毕飞宇.《平原》的一些题外话[J].南方文坛,2012(7):49-52.
[6]赵林云.论毕飞宇的女性悲剧书写——以《青衣》《玉米》为中心[J].文艺争鸣,2010(7):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