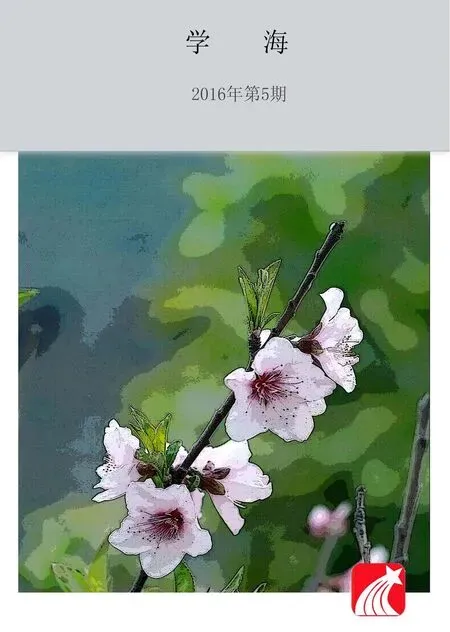迈蒙尼德哲学的当代研究路径*
约瑟·斯特恩
迈蒙尼德哲学的当代研究路径*
约瑟·斯特恩
内容提要传统观点、当代学者列奥·施特劳斯以及中世纪对《迷途指津》的解读,其共同点在于认为迈蒙尼德关注的是“元哲学”问题:即哲学与托拉(理性与启示)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迷途指津》关注的是古典哲学问题:人类的完满和真正的幸福由什么构成?人怎样或者应该如何处理其形式与质料、理智与肉体之间的张力?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寓言是被先知-统治者所充分了解的作为控制真理传播的工具,这似乎不如皮纳斯关于寓言是“表达先知自己对真理不完整理解的手段”的观点更切中肯綮。《迷途指津》中的寓言是表达人类形而上学知识的片面和局限的媒介,该书正是表达人在试图掌握不完全理解的真理时的知性体验。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寓言
1138年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的摩西·迈蒙尼德,无论在犹太律法还是哲学还是神学方面,无疑都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尽管他有阿拉伯语教名即穆萨·伊本·迈蒙(Musa ibn Maymun),他仍以希伯来语名拉比摩西·本·迈蒙(Rabbi Moshe ben Maimon)或其首字母缩略词RaMBaM而广为人知。他出生在显赫的拉比法官家庭,在安达卢西亚伟大的犹太-阿拉伯文化的孕育下长大。1148穆瓦希德王朝入侵后,他随家人逃离科尔多瓦,但一生认同西班牙,并以希伯来语名西班牙的摩西·本·迈蒙(Moshe b. Maimon ha-Sefaradi)自称。1160年前后,迈蒙家族逃往北非的菲斯(Fez),五年后前往巴勒斯坦,最后抵达开罗的福斯塔特。迈蒙尼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在埃及度过,他担任犹太社团领袖(ra’is al-yahud),与其兄弟一起经营印度贸易。兄弟去世后,他先后担任法蒂玛及阿尤布苏丹的宫廷医生,这些苏丹中最显赫的是萨拉丁之子阿弗达尔(Al-Afdal)及其维齐尔法官法兑尔(Al-Qadi Al-Fadil)。
迈蒙尼德早年流亡,继而成为犹太社团领袖、拉比权威和医生。尽管一生极度活跃而劳碌,但他著述之丰富却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他写了三部主要著作,其中任一部都足以为他在犹太文学中赢得一席之地:(1)《密释纳评注》(1158-1168)是第一部连续的对正典化的拉比律法观点选集的评注。(2)《律法再述》(Mishneh Torah,约1168-1178)是第一部,也是至今唯一全面的拉比律法典,涵盖了关于信条、仪式、节日以及安息日、婚姻、民事侵权行为、财产、洁净与不洁、献祭、管理城邦及弥赛亚王国律法等内容。(3)《迷途指津》(1185-1190)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犹太哲学著作。此外,迈蒙尼德还留有一部早年写成的逻辑学论著,关于医学、星相学、数学的著作,以及上百份律法问答和书信,其中不乏《关于殉道的书信》和《致也门人书信》(1165年)这类长篇书信。尽管迈蒙尼德的伟大贡献之一在于将哲学与拉比律法进行整合,这点贯穿于他伟大的律法著作《密释纳评注》和《律法再述》之中,但笔者将集中关注《迷途指津》。
列奥·施特劳斯
当代关于迈蒙尼德的哲学研究始于列奥·施特劳斯,这位政治理论家及政治思想史家一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他并非现代第一位伟大的迈蒙尼德学者,蒙克(Solomon Munk)、胡司克(Issac Husik)、沃尔夫森(Harry Wolfson)、古特曼(Julius Guttmann)、拉维多维茨(Simon Rawidowitz)等学者都早于他或与他同时。而且他研究迈蒙尼德的路径今天也未获得了普遍甚或大体上的接受。然而,今天没有人写迈蒙尼德时能够忽略施特劳斯:你要么从他的立场出发,要么对他持否定态度。他的路径可以通过与两个迈蒙尼德哲学的传统观点进行对比来介绍:
传统观点一(T1):《迷途指津》调和了启示与理性,或者说调和了圣典、宗教或拉比犹太教与哲学或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对立。
这一观点认为,《迷途指津》试图把启示、圣典和拉比传统所代表的那方面与理性或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希腊哲学传统——所代表的那方面综合或者弥合起来。从这一角度看,哲学并非犹太人所固有或天生的追求;相反,它是外来的、希腊的(希腊人或希腊化的人们也是第二圣殿时期的前拉比圣哲的敌人和迫害者)。然而,在12世纪或今天,哲学和各种科学不能被忽视。因此必须尝试去综合启示宗教与哲学和各种科学,去尽可能表明启示真理在何处能够被理性论证,并去将启示真理与理性在表面上互相冲突的地方尽可能表述得连贯一致。举例而言,迈蒙尼德展示了如何运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逻辑,用理性来论证上帝存在、他的唯一性、他的无形体性这类启示真理;同样,迈蒙尼德表明启示律法表达了理性要求文明社会所具有的道德价值或者其他规范。这一观点尽可能地把圣典和拉比文献中的超自然和神话的因素降至最低,并试图表明犹太教是怎样在最大程度上与科学及科学特质相一致。圣典有时会把上帝描述为具有躯体或者拟人化的特征(如说他有“大能的手”或者他会“愤怒”),从而与哲学家的上帝相矛盾,此时我们要对这些经文进行比喻性或者寓意化的再诠释。当然症结在于:圣典关于创世的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论并不容易调和。关于上帝不变以及世界必然是决定论的观念,有悖于神圣意志、人的自由、神圣赏罚以及神迹这类宗教观念。这些观点如果不能消除,或者不能以一种与理性和科学兼容的方式再诠释,就会被当作超理性的或者由先知启示的真理而无法被论证。这种传统观点认为,因为迈蒙尼德经常明确声称他接受了传统的拉比犹太教,一旦出现不可避免的冲突,通行的原则是他置启示于哲学之上。
传统观点二(T2):不用关注《迷途指津》的文学特征也能理解迈蒙尼德在此书中的哲学教义。
众所周知,标准的哲学文本完全按照带有前提、论证和结论的推论性散文写就,其排列之系统一如理性的自明科学。按照传统观点,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的哲学教义可以像研究任何其他哲学文本中的哲学教义那样进行研究,并且原则上可以用必真的证明形式加以重构。而且正如明说的那样,这种对迈蒙尼德论证的重构无需关注或留意该书的特殊文学特质就可以完成。笔者将马上回到这些特质上,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迷途指津》中的许多圣经经文依据和拉比文献中的篇章、寓言或故事仅仅是作为“化妆打扮”出现在书里,以表明哲学可以和圣典与犹太教相调和。它们的出现仿佛把哲学变成了犹太教所认可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并不起什么特别的哲学功能。为了理解《迷途指津》中的哲学,研究其直白的哲学部分便已足够,无需关注其宗教的经文、寓言或者叙事。
与传统观点(T)对照,施特劳斯的路径(S)可以用以下两个观点来表述。施特劳斯观点一(S1):撰写《迷途指津》的独特文学形式对于理解此书至关重要。
受迈蒙尼德13和14世纪的门徒及评注家(例如Samuel ibn Tibbon, Shem Tov Falaqera, Moses of Narbonne, Isaac Abravanel, Joseph ibn Kaspi)的影响,施特劳斯引导读者关注撰写《迷途指津》所用的独特的文学形式。他强调:迈蒙尼德在其导言中告诉我们,他以这种方式撰写此书,是为了对某些读者隐藏他的教义;他并未明确表明他的真实信仰,只是在“章节标题”中对此有所暗示;他将诸种议题分割并散插在书中,而非将它们像自明的科学那样系统有序地呈现;他用重复掩饰显著的差别;他运用并创作了寓言和其他修辞手段,以隐藏他的观点;他特意在不同的语境中安插自相矛盾的言论,以此隐藏它们的涵义。这样,施特劳斯把迈蒙尼德文本显白(exoteric)和隐微(esoteric)层面的诠释或意义之间的差别引入现代学术讨论,或者说重新引入了中世纪解读《迷途指津》的方式。隐微解读就是解读出文本中隐藏的意思,这才是迈蒙尼德自己真正相信的;其受众是精英或哲学家。对同一文本的显白解读是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直白或公开说的内容,但只是随口说说,他自己并不真正相信,其受众是“芸芸众生”或者整个犹太社团。对《迷途指津》的隐微写作形式而非显白写作形式的密切关注构成施特劳斯的伟大贡献之一,笔者倾向于认为如今没有人能够完全忽视这些特征。然而,笔者要把施特劳关于《迷途指津》写作形式的意义的洞见和他对迈蒙尼德何以选择这种方式写作的解释区分开来。这使得我们关注施特劳斯的第二个独特的主题。
施特劳斯观点二(S2):《迷途指津》的秘密是理性与启示——或者说哲学与托拉/律法——之间是无法逾越地不相容和对立。迈蒙尼德自己真正的信仰是在理性或哲学这边,而非托拉或律法。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事实上是迈蒙尼德本人,必须隐藏自己的真正信仰。他在表面上对普通读者呈现出一副比较虔敬、传统的姿态,与此同时隐藏自己隐秘的、隐微的或者秘密的哲学信念。
施特劳斯认为,与传统观念相反,迈蒙尼德并不相信启示托拉或者启示律法是与哲学或者理性兼容一致的,也不相信可以调和它们。相反,《迷途指津》的惊天秘密在于理性和启示,或哲学与托拉,是绝对冲突的。在这一冲突中,迈蒙尼德自己的真实信念坚定地站在哲学这边,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这边。因此,他事实上相信永恒而非创造,否认神对个体的眷顾(individual providence)和灵魂不灭,并且不相信神迹或者违背自然法则的神圣意志的可能性。托拉最多是一种大众哲学,哲学家通过它能够创造并掌控一个能让他安全地进行哲学探究而不用担心迫害、监禁或死亡的社团。哲人自己如同尼采的超人,超越宗教道德和法律之上。因此,哲人必须隐藏自己真正的教义,既为了自保,又为了保护芸芸众生——缺乏教养的大众一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哲学,将无法过有序的生活。对施特劳斯来说,这是迈蒙尼德以秘密方式写作《迷途指津》的原因所在:控制哲学真理的传播,不让它触及不适合的眼睛与耳朵。明白说出的只不过是显白之义——为了大众消费,并非是迈蒙尼德自己的真实信仰,尽管他给予哲学读者以线索,让他们可以凭此解读他的真正意图。那些真正的意图是《迷途指津》的隐微含义。施特劳斯认为,从深层意义上讲,《迷途指津》是一部政治著作,它旨在建立并控制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为其哲人-王的意志服务。
因为他相信哲学/理性和托拉/律法/启示之间存在矛盾,他也看到了迈蒙尼德著述中一对深刻的二分法。除了认为《迷途指津》“这一文本具有隐微和显白意义的不同层次”而外,他还将迈蒙尼德的著作分为为不同的读者所写的不同类型。律法著作,如《密释纳评注》和《律法再述》,是为了“一般人”而写;《迷途指津》,尤其是其真正的隐义,则是为了“一小群能够自行理解的人”而写,亦即为哲学精英所写。对于任何了解《密释纳评注》和《律法再述》的人来说,这很可能是施特劳斯所有命题中最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们绝非通俗著作;阅读它们不仅需要相当学识,而且其中也充满了哲学。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迈蒙尼德的律法和哲学著作之间具有更多的互补性。
中世纪评注家的当代回响
中世纪评注家和施特劳斯有一大差异,就是施特劳斯视《迷途指津》的秘密为哲学/亚里士多德和托拉/启示律法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而中世纪评注家认为《迷途指津》的秘密是哲学/亚里士多德和托拉/启示宗教之间的同一。也就是说,在中世纪《迷途指津》的评注家看来:
(M)《迷途指津》的秘密就其潜藏的隐义来看,哲学/亚里士多德等同于托拉/启示。
托拉浅白地以神人具有相同形体的词语将上帝描绘成一具躯体,这仅仅是为了让大众消费,除非具有躯体,否则大众不相信有任何东西存在。然而,这种描绘的真正含义在于,上帝是某种非物质性的、知性的完满存在。托拉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言说,是因为它模仿“人子的语言”以迁就人类。请注意,这种中世纪理解《迷途指津》的路径(M)并非传统路径(T)。(T)试图尽力维护托拉的显白教义。按照(M),托拉事实上相信永恒,而非无中生有的创世;神迹则不过是自然现象;神意和奖惩并不取决于或感应于个体对诫命的践履,而是人类理智完善的功能。总之,中世纪的路径既非施特劳斯的也非传统的。
中世纪这种理解《迷途指津》的路径(M)近年来有复兴之势,它将《迷途指津》的诠释领入两个新方向。第一个方向(H)试图调和哲学和律法,甚至想通过展现作为《迷途指津》作者的迈蒙尼德和作为拉比学者、法官、《密释纳评注》作者的RaMBaM之间有着更多的互补性和统一性来表明托拉的真义是哲学。然而,这一路径并不是要表明《迷途指津》可以用与托拉兼容的方式来诠释,而是要表明《律法再述》的核心是哲学。例如,哈特曼(David Hartman)、托斯基(Isadore Twersky)、哈维(W.Z.Harvey)和哈伯塔(Moshe Halbertal)等当代学者试图弥合迈蒙尼德律法著作和哲学著作之间的裂缝,他们主张《律法再述》以及迈蒙尼德的其他律法著作不仅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哲学,而且完全为潜在的哲学目的塑造并引导。事实上,他们认为,《迷途指津》给出了论据却没有径直下结论,而《律法再述》则以清晰明白的形式表达了这些结论却没有给出相关论据。因此《迷途指津》是理解《律法再述》的一把“钥匙”,能让仅在《迷途指津》中暗示的内容变得明白。
许多当代学术所采用的第二种方向(E)来源于《迷途指津》导言的开头几段,迈蒙尼德在这里描述了自己撰写此书的两个目的:(1)为了解释圣典中有歧义词语的多重含义;(2)为了辨识并解释先知书中“非常隐晦的寓言”。基于这两个明确说明的目的,近来许多学者声称,《迷途指津》主要不是一本洋洋洒洒的哲学论著(就像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文本,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化及阿拉伯的评注,或者一部独立的哲学论著那样),而是一部释经著作,亦即对托拉的诠释,尽管它并未以清晰而连贯的评注方式写作。
在这一基调下,不同的学者对迈蒙尼德的释经工程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诸如以色列学者克莱因-布拉斯拉维(Sarah Klein-Braslavy),展示了迈蒙尼德如何通过建立词语或概念之间语义的对应,来把圣典词汇或主张解读或翻译成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范畴、术语及教条:这样,“ishah/妇女”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说的质料,“tzelem/形象”则是其形式,诸如此类。通过这一路径,释经的目的与传统的及(第三种)中世纪的观点类似,都是想通过表明托拉的真义是哲学或亚里士多德,来“调和”圣典和哲学,在此特定意义上,二者可照字面意义互相翻译。
戴蒙德(James Diamond)采取了第二种路径,他主张《迷途指津》的潜台词——如果这不是迈蒙尼德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释托拉中的众多叙事和律法,迈蒙尼德常常通过引用圣经经文来暗示或影射,由此间接地呈现这种释经工程。圣经经文的引文散布在《迷途指津》中,而要诠释《迷途指津》,就要根据这些引文去推断迈蒙尼德对更大的圣经叙事和律法部分做了什么未阐明的哲学诠释。例如,《撒母耳记上》说扫罗没有杀光所有亚玛力人及其牲畜,因而违反了上帝的灭尽亚玛力人的命令;如果迈蒙尼德引用了这段经文中的一句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根据《迷途指津》中这句引文的语境来重构迈蒙尼德是如何解读《撒母耳记上》中更加令人困惑的片段。比如,与亚玛力人开战就是与偶像崇拜开战,扫罗把禁用的俘获牲畜献给上帝作祭品表明了人民的极度困惑,这种困惑因为他们的想象和他们未能领会献祭在剪除偶像崇拜当中的意义而进一步加深。
第三种路径(P)来自笔者本人,它并不试图通过把希伯来语圣经解读成(或翻译成)亚里士多德来显示圣经如何能与哲学相调和。相反,它旨在考察迈蒙尼德如何把托拉作为具有自身特点之哲学的独特作品来解读。托拉和拉比文献并非亚里士多德,但迈蒙尼德相信它们出自古代以色列曾经有过的一个丰富的哲学世界,这个世界也有各种相互竞争的学派,它们与他从阿拉伯哲学文献中得知的诸学派——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者和各种伊斯兰神学派别(即“凯拉姆”)——相仿佛。《迷途指津》中支持或反对亚里士多德学派观点以及反对凯拉姆的哲学论证,既不是用来使律法获得哲学合法性的,又不是用作解读圣典的钥匙。相反,它们为迈蒙尼德在托拉中发现的尤其以寓言形式表达的原创哲学立场提供了一个语境,他把这类文本当作垂范万世的哲学著作。换言之,这种路径把《迷途指津》当作一部释经学著作、一部评注,所评注的是圣经和拉比们阐释圣经的著作(Rabbinic Midrash),但与上述(E)路径不同,迈蒙尼德认为圣经和拉比们阐释圣经的著作本身就是哲学著作。诚然,托拉和拉比文献看上去“不像”亚里士多德或者众人心中典型的哲学文本;虽说如此,它们仍属同一体裁。如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圣经和拉比文献也是智慧的创作,因此就是哲学;它们不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是关于古代以色列历史的著作,或者是关于犹太人、诗歌或文学的著作。迈蒙尼德没有去思考“托拉和哲学”,而是将“托拉/哲学”当作一体之两面。如果存在张力,那么它不存在于两个分开的知识领域之间,而是在同一领域之内。而如果托拉自身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摩西、众先知和拉比们都是哲学家,是古代以色列和古代犹太教固有的圣哲。
一己之见
迈蒙尼德在托拉和释经著作(midrashim)中发现、并在《迷途指津》中进一步阐发的古代以色列和拉比犹太教所特有的哲学到底是什么?这里试着用三个命题或议题对笔者所持的路径(P)加以描述:
P1.按照传统观点(T)、施特劳斯观点(S)和中世纪路径(M)对《迷途指津》的解读,迈蒙尼德关注的是“元哲学”问题:即哲学与托拉的关系问题,或者理性与启示、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的关系问题。根据这一路径,《迷途指津》列举了一系列议题,由此可以提出理性针对启示的问题:对于上帝的本质、世界的起源或永恒、预言、神意等诸如此类者,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和言说什么。一些人认为《迷途指津》旨在展示这种元哲学问题能被解决,而哲学和宗教被消解了(甚至被证明是同一的);另一些人相信此书要点在于证明相关冲突是不可解决、无法克服的,但所有这些观点认为《迷途指津》的问题就是与哲学/理性以及与托拉/启示有关的问题。
但路径(P)却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迈蒙尼德的工程。《迷途指津》处理的是古典哲学问题,而非元哲学问题:人类的完满和真正的幸福由什么构成?它是物质的还是理智的,抑或其他什么东西?完满和幸福究竟是人类可以实现的,还是不可获致的理想?这种目标如何与作为一个复杂而混合的(即由理智和肉体、形式与质料构成的)人类的相互矛盾的需求进行协商?简言之,人怎样处理或应该如何处理其形式与质料、理智与肉体(而非哲学/理性与托拉/启示)之间的张力?《迷途指津》所处理的每个根本性议题引出了这一问题的一个不同维度,而迈蒙尼德为每个议题提供了一系列由凯拉姆神学家、哲学家、宗教法学者以及其他人表达的立场和论据——尽管他自己认为托拉本身是独特的哲学。简而言之,《迷途指津》是一个人尽一切可能去理解的一次尝试,这种理解本身有重大限制,是一个托拉/哲学的经典问题。
P2.当代迈蒙尼德学术研究中最活跃的争论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迈蒙尼德是否相信人的理智能够获得对于形而上或超自然的真理的科学知识或科学理解,这类真理与天体、与非物质的独立理智、与自然现象的终极原因并与神灵有关。有些人认为迈蒙尼德相信形而上学的科学知识是有可能获得的,我称这些人为《迷途指津》的独断论(dogmatic)读者。还有些人认为迈蒙尼德不相信人类有可能获得对形而上学的科学知识或者充分理解——这要么是因为人类理智有局限、要么是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亦即存在着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或冲突,我称这些人为《迷途指津》的怀疑论(skeptical)读者。尽管怀疑论的解读有其中世纪根源,但当代争论却肇端于已故的以色列研究中世纪犹太和伊斯兰哲学和科学史大家皮纳斯(Shlomo Pines)1979年的一篇文章。皮纳斯认为,迈蒙尼德采纳了据说由法拉比(Al-Farabi)主张并由伊本·巴佳(Ibn Bajja)转述的立场,这一立场认为人类理智只能通过来自感觉材料的感觉和形象认知客体。这种条件排除了人类认知纯粹的非物质存在(诸如上帝)以及任何超乎感觉世界或月下物理世界的事物的形式或概念的可能,因此排除了宇宙论和天文学。它也排除了人类对《迷途指津》中讨论的一切经典形而上学问题进行认知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包括:创造论抑或永恒论、先知预言和神意。用皮纳斯的话说,“迈蒙尼德认为关于超乎月下世界的客体的确定科学知识是不能获致的。”据说由于这些认识的局限,法拉比否定了灵魂不朽和理智完满的可能性,把最高类型的人类幸福降为政治的或公民的事务。类似地,皮纳斯认为,迈蒙尼德对灵魂不朽存疑,并且如同康德一样,把政治的或务实的行动的生活置于不能获致的形而上学沉思的完满之前。因为独立理智的存在是“仅仅可能的”且缺乏所有的“确定性”,皮纳斯推断迈蒙尼德主张“致力于理智或获得与独立理智的汇合是没有意义的。”皮纳斯解读的迈蒙尼德一如康德,也是一位批判哲学家。
皮纳斯的论点招致了众多批评。一些人质疑皮纳斯对法拉比和伊本·巴佳的阿拉伯文献的解读。一些人怀疑皮纳斯对《迷途指津》认识论的分析。其他人则对皮纳斯关于不朽和政治幸福优先的寓意进行辩驳。笔者认为,尽管迈蒙尼德关于怀疑论的论据迥异于皮纳斯所认为的,而且其含义也不同于皮纳斯所说,但皮纳斯切中了《迷途指津》之肯綮。尤其是迈蒙尼德即使也相信人类不可能理智完满,但他从未放弃这一理想。不仅如此,他为自己的怀疑论结论提供了不同种类的论据。有些论据表明了人类关于宇宙论和天体的知识有种种局限:我们永远无法获得解释性的论证,故而永远无法获得对这类主张的科学的知识和理解。而且,因为上帝存在的最佳证据是基于天体的运行,我们也不能获得上帝存在的科学知识。其他论据表明关于上帝的知识是不可能的,那些表达上帝属性或本质的命题尤其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关于真理的知识预设了我们可以在智力上表现我们所知道和为何要有关于真理的知识,被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仅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如何表现它也必须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一切表现是复合命题(composite propositions,有代表基层和属性的主语和谓语),然而上帝是至简的。因此,无论何时我们试图表现我们所知道的上帝,即表现祂是简单的,我们都误把祂表现为某种复合物。这违背了知识的条件。
即使如此,尽管我们理智活动的产物知识不足,理智的完满却通过个体的实践或者通过法国哲学史家阿多(Pierre Hadot)所谓的“精神操练”(spiritual exercises)来引导和规范个体生命,这种操练实乃控制其生命的精神过程。某些此类实践或操练训练人专注于理智,并将肉体和物质需要最小化。另一些则通过规训人的无餍足的认识欲而悬置判断,进而使人达到获得幸福的状态。最后尚有其他一些实践通过承认人类理智的局限,而达到惊奇、晕眩和赞美的境界,这种境界构成对神的崇拜,这种崇拜与独断论者所相信的能够通过获得关于神的知识来达到的那种崇拜并行不悖。
P3.构成理解《迷途指津》(P)路径之特色的最后一个主题是迈蒙尼德怀疑论的后果:他把哲学寓言设想为一种文学或口头的媒介,以表达人类形而上学知识的不完备、片面和局限。这里只大体勾勒迈蒙尼德怀疑论和寓言之间的关联。
正如上文所说,迈蒙尼德相信理想的人类完满是人的理智潜能的充分实现,这种完满可以通过先习得再不断沉思关于物理、宇宙论、形而上学(包括神)的各门科学获致。但是迈蒙尼德也相信人的质料(或者说身体)阻碍他实现这一完满状态。尤其是,诸如想象力(这是一种将得自感官的形象保存起来的记忆存储库,同时具有一种将这些形象重组成虚构意象的附加能力)这种身体官能妨碍人全面理解和如实再现形而上学、神和天体。理智的完满状态要求人时时不断而专一地反思他所掌握的真理和概念,我们必要的身体需求和欲望(饮食、代谢、男女)却干扰和破坏了绝对而不分的理智专注。这样,人的理智和身体之间高度紧张,其后果则是人——包括迈蒙尼德自己——至多拥有有限的、片面的、间断的对形而上学、非物质性存在和上帝的理解。《迷途指津》正是迈蒙尼德试图表达这种不完备知识——关于上帝、自然的终极原因和天体的知识——的状态的尝试。考虑到人的认识局限,此书也是用文字去表达人在试图掌握这些“秘密”——即难解之谜或者不完全理解的真理——时的知性体验。
迈蒙尼德用不同的形象描述探究者探询形而上学时有限的知性体验:一场针对迷惑的拉锯战、划过黑夜的闪电、眩晕。然而,他认为寓言(parable)是他的古代前辈(其中有拉比和希腊哲学家)试图表达他们的不完备知识的最初的口头形式。迈蒙尼德所谓的“寓言”(阿拉伯语:“mathal”;希伯来语:“mashal”;又译作“allegory”)有其特指并自成一格。拙著《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形式和质料》(第2-3章)对其寓言概念及相关例证详加探究,这里只撮要述之。迈蒙尼德的“寓言”与今天此词常用的意思不同,并不是指一种带有宗教或道德信息且通常能够用清楚直白和洋洋洒洒的语言加以叙述的简单叙事。它与新约中的寓言或拉丁文中的寓意解释也不同,尽管有些人将“mathal”/“mashal”译为“寓意解释”(allegory)。迈蒙尼德用寓言指任何非偶然的、具有三层意义的文本,区分每层意义靠内容,而其结构则受制于认知限制。意义的最外层——我们可称之为文本“通俗的外层意义”,它可诠释为寓言——由相关文字的语言学意义固定下来,如果它是一种叙事,其意义就以历史或神话故事加以呈现。这种意义是普通人解读出的意义,但不是寓言应该被理解成的那种意义。这个寓言式文本的另外两层寓意都表达了人们应当相信的不同层次的智慧。笔者将其中第一种称为“外层寓意”,它试图用明白的方式陈述一种真理,这要么是关于物理的真理,要么是通过寓言形象地表达出来的形而上的真理,亦即一个关于上帝的属性或神意或先知预言性质的真理。我把这个寓言的第二种寓意或解释称为“内层寓意”,它是探究外层寓意、质疑其前提和内涵的结果,这种探究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对内容的片面理解。这种内层意义不能像对待一个科学主张那样完全以命题的形式明晰而详尽的阐发;它是碎片化的、讲究悟性的、谜一般的,仿佛闪电般的知识,与此同时又抵制完整而清楚的表达。但我们只有通过寓言那影射的、间接的结构才能尽最大可能去表达这种对其主题进行有限的、火花般理解的知性体验。
迈蒙尼德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位采用寓言的文学或口头形式来表达人对形而上学、上帝和天体的有限而不完整理解的人。他认为在古代的先知文本和拉比文本中能发现更早的寓言尝试。因此,他的工程的中心部分包含了对这些犹太教经典文本的诠释,以及对它们出现的哲学语境的复原。他所诠释的这些经典寓言中,最有名的有两个:一是关于“起初的记述”,即《创世记》起首两章;一是关于“神车论”,即先知以西结所见的异象。此外,他还将不少托拉的其他章节诠释为寓言——伊甸园的故事、雅各的梯子异象、西奈山集会、以撒被缚,以及《约伯记》。不仅如此,追慕同一写作传统,他也发明了自己的寓言,以表达他自己对形而上学的“秘密”的有限理解,以及他对其前辈尝试表达他们的有限理解的有限理解。通过让读者徜徉于《迷途指津》的寓言之中,迈蒙尼德试着让他们也体验到他在试图理解形而上的真理时所经历的那种知性体验。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寓言的功能并非施特劳斯路径(S)所主张的那样,是被先知-统治者所充分了解的作为控制真理传播的工具,而是表达先知自己对这些真理的不完整理解的手段。
至此,我们应该返回《迷途指津》,一起仔细研读各章细节。这篇短文自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但笔者希望通过它,读者能获得若干走进《迷途指津》的引导。上文已经概括了当代学者阅读这一复杂论著时的五种一般路径(T,S,M,E,P)。笔者并不是说读者应该用所有这些路径来阅读《迷途指津》,也不是说每一路径捕捉到了《迷途指津》的“部分真相”。无疑,迈蒙尼德自己认为,有这么一种路径可以诠释他的论著,尽管这种路径不能下定论、不能决定性地阐明其形而上主题的真相。然而,自《迷途指津》面世之始,它就给读者下了魔咒,这种魔咒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因为它向读者提出了深刻挑战:要求读者能够把它的哲学论据和圣典诠释,以及它的旨在传递缜密的科学理解和知识的多层次的寓言写作形式,像拼图一般缀合在一起。这些任务使得《迷途指津》不仅成为迷途者的指南(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也成为迷惑的指南(a guide to perplexity, 此语又有“引向迷惑”之义——译注)——这种迷惑是一位伟大思想家在与至难、甚至有时是无解的关于人类生存和幸福的奥秘搏斗时所遭遇的。
(曹泽宇 译,宋立宏 校)
附录:迈蒙尼德和中世纪犹太哲学书目精选
一、迈蒙尼德的原始著作:
1.Treatise on the Art of Logic (1937-38/1966). Trans. and ed. Israel Efros, “Maimonides' Treatise on Logic (Makalah Fi-Sina ‘at Al-Mantiq)”,ProceedingsoftheAmericanAcademyofJewishResearch, 8: English section: pp. 1-65; Hebrew section: 1-136: “Maimonides' Arabic Treatise on Logic”,ProceedingsoftheAmericanAcademyofJewishResearch, 34: 英语介绍: pp.155-160; 阿拉伯语文本: 1-42.
2.CommentaryontheMishnah(Heb.) (1968). Joseph Kafih (ed. and trans.) Jerusalem: Mossad Harav Kook.(这是犹太-阿拉伯语原文与希伯来语译文对照本,但现在不易找到。)
3.Mishneh Torah (Heb.) (repr. frequently); Eng. trans. by Moses Hyamson of Book of Knowledge and Book of Adoration (1962), Jerusalem; The Code of Maimonides, Yale Judaica Series (1949-72), New Haven, Conn. (除了第一卷《论知识》外,已全部印行于此版。)
4.Edi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5.Le Guide des ?garés (1856-66). Trans. S. Munk, 3 vols., (Paris, G.-P. Maisonineuve &Larose).
6.Dalalat al-ha’irin (1929). Ed. S. Munk and I. Joel (Jerusalem, Janovitch)
7.Moreh Nevukhim (Heb.) (1904/1960). Trans., Samuel Ibn Tibbon, with four commentaries: Efodi, Shem Tob, Crescas, and Don Isaac Abrabanel, Vilna/Jerusalem.
8.Sefer Moreh ha-nevukhim la-Rabbenu Mosheh ben Maimon be-ha‘ataqat Shemuel ibn Tibbon (1959/1981). Ed. Y. Even Shmuel, (Jerusalem).
9.Guide of the Perplexed (1963). S. Pine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Moreh ha-nevukhim la-Rabbenu Mosheh ben Maimon: Maqor ve-Tirgum (1972). 3 Vols. Trans. Joseph Kafih. (Jerusalem, Mossad HaRav Kook).
11.Guide of the Perplexed (1995), Abridged edition. Trans. Chaim Rabin. (Indianapolis,s Hackett)
12.Moreh Nevukhim (Heb). (2002). Trans. M. Schwartz, 2 Vol. (Tel Avi,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3.《迷途指津》今有傅有德教授主持翻译的中译本(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Maimonides’ Responsa (Teshuvot ha-Rambam) (Heb.) (1986). 4 vols., ed. J. Blau, edition secunda emenda. Jerusaele: R. Mass.
15.Letters and Essays of Maimonides (Heb.) (1988-9). Ed. and Trans. I. Shaiat. Ma’aleh Adumim, Israel: Shailat Publishing.
16.Pirkei Moshe BeRefu’ah (Heb). (1987). (ed.) S. Muntner. Jerusalem, Mossad Harav Kook. 他的各种医学著作诸如《论希波拉底格言集》(Aphorisms on Hippocrates)和《论哮喘》(On Asthma)等正在由G. Bos为杨百翰大学出版社翻译。
二、迈蒙尼德著作英译精选:
1.A Maimonides Reader (1972). Ed. Isadore Twersky (New York: Behrman House). (Contains healthy selections from the Mishneh Torah, epistles, and Guide)
2.Ethical Writings of Maimonides (1975). Trans. R. Weiss and C. Butterworth (New York: Dover). (Contains “Eight Chapters,” “Laws of Trait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Guide)
3.Crisis and Leadership: Epistles of Maimonides (1985). Ed. and Transl. A. Halkin, with commentaries by David Hartman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Contains “Epistle to Yemen,” “Epistle on Martyrdom,” and “Essay on Resurrection”, with essays by Hartman)
4.Maimonides’ Empire of Light (2000). Trans. with essays, Ralph Le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三、传记:
1.Davidson, H. A. (2005). Moses Maimonides: The Man and His 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uland, S. (2005). Maimonides (New York: Schocken).
3.Kraemer, J.L. (2008). Maimonides: The Life and World of One of Civilization’s Greatest Minds (New York: Doubleday Press).
4.Halbertal, M. (2013). Maimonides: Life and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四、二手文献汇编:
1.Pines, S. and Yovel, Y. eds. (1987). Maimonides and Philosophy (Dordrecht: Kluwer).
2.Kraemer, J. L. ed. (1991). Perspectives on Maimonides: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xford: Littman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Seeskin, K. ed. (2005).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imoni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五、迈蒙尼德思想的一般介绍性研究:
1.Manekin, C. H. (2005) On Maimonides (Belmont, Cal./London: Wadsworth).
2.Rudavsky, T.M. (2010) Maimonides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六、学术文献精选:
1.Altmann, A. (1987). “Maimonides on the Intellect and the Scope of Metaphysics,” in Altmann,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zur modernen Aufklarung (Tubingen: J.C.B. Mohr).
2.Davidson, H. A. (2011). Maimonides the Rationalist (Oxford: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3.Diamond, James (2002). Maimonides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Concealment (Albany: SUNY Press).
4.Halbertal, Moshe (2007).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Esotericism in Jewish Thought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Hartman, David (1976). Maimonides, Torah, and Philosophic Quest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6.Harvey, Warren Zev (1988). “How to Begin to Study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 1” (Heb.), Da‘at 7: 5-23;(1993). “Maimonides’ Interpretation of Gen. 3, 22,” (Heb.) Da’at 12: 15-21;(1997). “Maimonides’ First Commandment, Physics, and Doubt,” in Hazon Nahum: Studies in Jewish Law, Thought, and History present to Dr. Norman Lamm, eds. Y. Elman and J.S. Gurock (New York: Yeshiva University Press);(2001). “The Mishneh Torah as a Key to the Secrets of the Guide,” in Me’ah She‘arim: Studies in Medieval Jewish Spiritual Life in Memory of Isadore Twersky, eds. E. Fleischer, G. Blidstein, et al. (Jerusalem: Magnes): 11-28.
7.Klein-Braslavy, S. (1978/1988), Maimonid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of Creation (Heb.), 2nd Edition (Jerusalem: Reuben Mass Publ.);(1986). Maimonides’ Interpretaton of the Adam Stories in Genesis: A Study in Maimonides’ Anthropology (Heb.), (Jerusalem: Reuben Mass Publ.);(1996). King Solomon and Philosophical Esotericism in the Thought of Maimonides (Heb.) (Jerusalem: Magnes Press);(2011). Maimonides as Biblical Interpreter (New York: Academic Studies Press).
8.Kreisel, Howard (1999). Maimonides’ Political Thought; Studies in Ethics, Law, and the Human Ideal (Albany. N.Y.: SUNY Press).
9.Pines, S. (1963).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vol. 1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lvii-cxxxiv;Collected Works of Shlomo Pines (Jerusalem, Magnes, 1997). Vol. II: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Jewish Thought, ed. W.Z. Harvey, M. Idel (Jerusalem, Magnes). Includes many of his most important papers on Maimonides.
10.Ravitzky, Aviezer (1981). “Samuel Ibn Tibbon and the Esoteric Character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AJS Review 6: 87-123;(1990). “The Secrets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Between the Thir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Studies in Maimonides, ed. I.
11.Twersk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9-207.
12.Seeskin, K. (1999). Searching for a Distant G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Stern, Josef (1998a). Problems and Parables of Law: Maimonides and Nahmanides on Reasons for the Commandments (Ta’amei Ha-Mitzvot) (Albany, New York: SUNY Press);(2013). The Matter and Form of Maimonides’ Guid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Strauss, Leo (1935/1995). Philosophie und Gesetz: Beitrage zum Verstandnis Maimunis und Seiner Vorlaufer. Berlin: Schocken Verlag. Trans. Eve Adler, Philosophy and Law. Albany: SUNY Press;(1952). “The Literary Character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Westport, Conn.): 38-94;(1963). “How to Begin to Study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Moses Maimonid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rans., S. Pines, Chicago: xi-lvi.
14.Stroumsa, Sarah (2009). Maimonides in His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Twersky, I. (1980). Introduction to the Code of 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Wolfson, H. A. (1929). Crescas’ Critique of Aristot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2 Vols. ed. I. Twersky and G. H. Willia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七、中世纪犹太哲学史和原始文献选集
1.Husik, Isaac (1916). A History of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一部经典的犹太哲学史。
2.Guttman, Julius (1964). Philosophies of Judaism, trans. D. Silverman (New York, Schocken). 第二部经典的犹太哲学史。
3.Sirat, Colette (1990). A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一部较为晚近的哲学史,包含众多未发表原文手抄本的翻译。
4.Frank, Daniel H. and Leaman. Oliver, eds. (2003).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世纪犹太哲学论文选。
5.Frank, Daniel H. and Leaman. Oliver, eds. (1997).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Routledge History of World Philosophies). 中世纪与现代犹太哲学论文选。
6.Frank, Daniel H., Leaman, Oliver and Charles Harry Manekin, eds. (2000). The Jewish Philosoph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原始资料选集。
7.Manekin, Charles, ed. (2007).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原始资料选集。
〔责任编辑:姜守明〕
约瑟·斯特恩(Josef Stern),芝加哥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芝加哥大学犹太研究中心主任;译者曹泽宇,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宋立宏,南京大学哲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
*本文系作者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