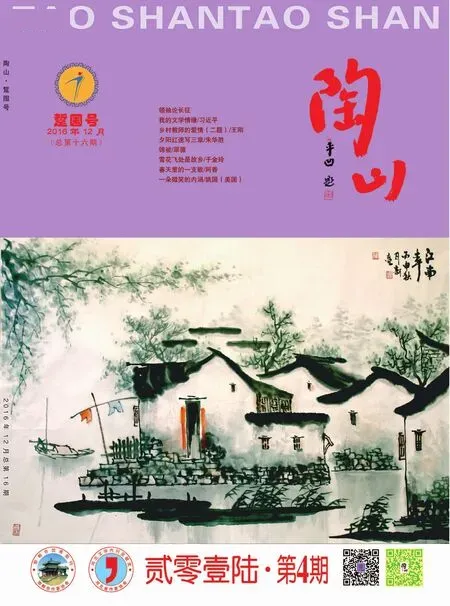女人王大花
◎邱文英
女人王大花
◎邱文英

王大花这几日那颗硕大的芳心动了又荡,害起了相思。
此女今年二十八。在高密,姑娘到了二十七八还没婆家,就会被人背地里叫“大”姑娘,用句时髦话,那就是剩女。
电影院后面有条神仙巷。巷内全是打卦算命的半仙神婆,还有摆摊开店的小商小贩。王大花的小门面靠小巷东头,卖杂粮鸡蛋时令蔬菜,还卖煎饼。她的煎饼又脆又香,远近闻名。这王大花生得牛高马大,又黑又壮,人泼实,凡事大不论。在夏天,她穿一件小花褂,胳肢窝底下开了一条缝,漏出几根又长又黑的汗毛。别的摊贩中午都买热乎乎的馄饨,或是买一碗漂着葱末的羊肉汤。大花从不,中午饿了,从摊上拿一棵大葱剥剥,把葱叶子夹胳膊底下一撸,拿起张煎饼卷起来,“咔哧咔哧”,三下五除二,不用二分钟,午饭就完活。
大花天天吃煎饼,那黑脸盘子又大又圆,活像一张地瓜面的大煎饼,所以便得了个“大煎饼”的雅号。
大花最近有了心事,看上了斜对面馒头店那个经常来送面粉的田小炮。那田小炮生得唇红齿白,脸皮白白净净,和大花站一起矮半头。大花迷了心窍一般,一天不见这小炮,心里就痒痒。怀春的大煎饼,也开始捯饬自己。胳肢窝下开的缝连上了,还买了增白的雪花膏,天天对着镜子抹搽。她那蒲扇样的大手没干过这样的细活,结果黑脸抹得不匀,黑一道白一道。用小炮的话说,那就是驴屎蛋子下层霜,埋汰!
田小炮每次送货都经过大煎饼这小摊,大煎饼就殷勤地打招呼。小炮瞅瞅大花那口黄牙,牙上还沾着一片绿色的葱叶子,漫不经心地应一声,不太爱搭理。大花无视小炮的冷淡,每次见了都小炮小炮地叫得一声比一声亲,煎饼脸笑成了一朵花。
这一日,小炮又开着电动三轮,经过大煎饼摊前。煎饼正在忙着给别人称鸡蛋,没顾上打招呼。小炮心中庆幸,三轮车提了速,赶紧跑,别让她看见。只听“咣当”一声,三轮车一阵乱晃,接着一阵稀里哗啦。小炮赶紧跳下车来一看,脸都绿了。原来,车底下一块大石头把轮子一颠,一袋面粉掉了下来,正砸在大花刚进的三筐鸡蛋上。好家伙,筐掀蛋打,鸡蛋黄子淌了一地。
小炮一改往日的冷脸:
“王姐王姐,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不起就完了?你得赔。”大花俩眼一瞪,大嗓门震天响。
“好,好,我赔,我赔,怎么个赔法?你说你说。”
“这三框鸡蛋,成本就两千多,要是卖出去,得三千,咱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两千五吧。”
“啥,两千五?你这不是讹人吗?”
“我讹人?你去别的地方打听打听,值不值这个钱儿?”大煎饼不依不饶,大手在小炮面前比划着。
小炮瞅了瞅大煎饼那蒲扇一样的大手,不敢再吱声。掏了掏身上所有的衣兜,凑了六十八元。
“就这些,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分期还,人家买房子现在都兴这个,你每半月还我一百,直到还清。”
小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愤愤地,搬起地上那块惹祸的大石头,把它当成大煎饼似地抛出去老远。
小炮每到月中月末都乖乖地过来还钱。大煎饼也不亏待他,每次都给他炒俩小菜,烫上壶热酒,热情地招呼小炮。小炮尽管不情愿,没办法,欠人家的钱,也不好跟以前一样不搭理。
一来二去,大煎饼那点小心思就有点按捺不住了。
一日大煎饼陪着小炮喝完了那壶热酒,羞答答地满眼含情望着小炮:“小炮啊,你什么时候能娶俺啊?”
小炮嘴里塞着半截馒头还没咽下,哽在了嗓子眼,一口气没上来,憋得直翻白眼:
“王姐,王姐,不合适不合适啊。你比俺大啊。”
“我比你大怎么了,女大三抱金砖,俺比你大四岁,这不得抱更大的金砖?”大花说着,就来拉小炮的手。小炮左躲右闪,大煎饼急了眼,“咣当”一声,把门一关,“咔嚓”上了锁。就“呼呼呼”地朝小炮走了过来。
“王姐,王姐,你干嘛?你干嘛?”小炮一看这阵势,吓得腿肚子都哆嗦。
大煎饼也不吱声,一只手提溜起小炮来,像老鹰捉小鸡一般,一下子把小炮扔到床上,小花褂一脱,“嗷”地一嗓子就扑了上去。
那一晚,小炮没回家。
第二天,小炮眼圈乌青,头晕晕乎乎,害怕被邻居们看见,早早起了床,贼溜溜地跑了。这一走,一连好几天,就再也没见小炮的面。
那大煎饼整天对着镜子,照着驴屎蛋子上那层霜,抹搽得更勤了。抹来抹去,却不见小炮。心里那个急呀!别人来买菜,不是算错了钱数,就是找错了零头,六神没了那个主。干脆把店外的货收进屋里,关了店门。买了一袋子水果,问了馒头店老板小炮的住处,自己找上门去了。
“咣咣咣”一通敲门,一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开门迎了出来,一看大花,像一尊大佛屹立在自己面前:
“姑娘,你找谁呀?”
“这是不是田小炮家?”
“是啊是啊,我是他娘。”
“娘,俺是王大花……”
这一声“娘”把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
“田小炮把我……那个啥了,您看,我这月都没来那事儿。小炮咋不见人了呢?我孩子他爹呢?”
“小炮啊小炮,多少如花似玉的姑娘你不找,你咋去惹乎这么一个大母汉子?”小炮娘惊得一愣一愣的,心里这样骂着,嘴里却问着:
“姑娘,你们……那个啥,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有十天了吧。俺这些日子,老是反胃,想吐,还愿意吃酸,肯定是有了。”
“姑娘,不能十天就嫌饭(妊娠反应)了吧?至少不得三个月?”
“嫌饭”是高密人对妊娠反应的一种说法。
“俺不管,反正俺就是嫌饭了。让小炮出来见我,自己做了业,抬腿就走了,算什么男人?”
小炮怯生生地从里屋出来,大煎饼的脸接着笑成了一朵花:“孩子他爹,咱俩都有了。那个什么,咱俩啥时候把事给办了啊?”
“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小炮娘连声答应,生怕大花真有了,那可不能耽搁。
“娘说话就是中听。”大煎饼乐滋滋地往外走着,“我回去准备准备。”
大煎饼走远了,小炮娘苦着个脸,拿指头剜着小炮额头:“你呀,你呀……”
成亲那天,大煎饼穿着通红的旗袍,身上的肉被旗袍勒得一圈一圈地鼓着。也没个新娘子样,指挥着来帮忙的七大姑八大姨干这干那。小炮闷葫芦一样,坐在一边。
婚礼后,小炮娘整天小心伺候着大花,生怕她有个闪失。大花搬沉的提重的,小炮娘都吆喝她放下,让小炮干。小炮嘟嘟囔囔:“不就是下个崽吗,用得着这么金贵?”小炮娘就锤他:“可不能委屈了俺孙子,让你干啥就干啥。”
晚上,小两口躺床上,小炮摸着大花的肚子:
“是不是该给儿子起个名字了?”
“你比俺有文化水,你起吧。”
“叫田二炮咋样?”
“什么二炮三炮的,你家要去收复钓鱼岛?”
半年过去了,大花那肚子也没见鼓起来。小炮跟娘嘀咕:
“让这货把咱给耍了,看我哪天,早晚得休了她。”
“你敢,别看大花那个粗实样,我看出来了,这孩子心眼不坏。”
“你咋看出来的?”
“你别管,娘看人,一看一个准。”
“准不准,咱走着瞧。”小炮自己嘟囔。
大煎饼小店的隔壁就是一开羊肉馆的,男主人姓杨。一个儿子今年五岁,名叫虎子,生的虎头虎脑,很是可爱。小两口人也热情厚道,买卖兴隆。可惜好景不长,忽然有一天,虎子发起了高烧,去医院一查,天塌了下来——白血病。这杨家买卖也做不下去了,整天往北京301医院跑。大煎饼看着这原来生龙活虎的孩子,因为化疗头发都没了,小脸蜡黄,心里那个疼呀。大煎饼从兜里抽出了五张百元大钞,递给小炮,红着眼圈:
“小炮,你看老杨家那孩子,真可怜,你给把这些钱送过去,咱邻亲百家的,尽尽心吧。”
“还用这么多?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让你送你就送,谁家还没个七灾八难的。”大煎饼白了小炮一眼。
小炮赶紧去了隔壁。
过了十几天,老杨一家从北京回来。大煎饼赶紧丢下买卖,过去看虎子。虎子妈给大煎饼一边倒水一边流着泪说:“大花,你忙你的,孩子这病,恐怕是没救了……”
“可不能这么说,嫂子,现在这技术这么先进,没有治不了的病。”
“还劳烦你们两口子惦记着虎子,上次,小炮送来了二百元钱,我也没抽上空去道个谢。”
大花一愣,安慰了老杨媳妇好一会儿,回自己店里去了。
小炮心里有鬼,不敢正眼看大煎饼。大花在屋里喊一声:“小炮,把那几个破了的鸡蛋给我拿进来,今中午咱炒了吃。”小炮一听,不像生气的样子,屁颠屁颠地拿着鸡蛋进了屋。刚把鸡蛋放下,没提防,大煎饼一个黑沙掌就抡了过来。小炮眼冒金星,嘴唇火辣辣得疼。嘴一咧,“吧唧”一声,半颗门牙掉到了地上,嘴里满是血。
“田小炮,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少干这种下做事!我王大花从七八岁就没了爹娘,不知道爹疼娘爱到底是啥滋味。我最看不得孩子哭,更看不得老人受难!虎子那孩子多可怜,你竟然,把钱给昧下了三百……”大煎饼的厉声渐渐带上了哭腔。
小炮一边擦着嘴上的血,一边唯唯诺诺地说:
“大花,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消消气,消消气。”
“再犯一次试试,看我怎么理整你!”大花眼圈通红,指着小炮。
大煎饼这买卖越来越红火,人手不够。偏偏小炮娘又得了偏瘫。小炮就把送面粉的活辞了,和大煎饼一边照看生意,一边伺候老娘。
为了不让婆婆生褥疮,大煎饼每天都给婆婆用大木盆泡个热水澡。太阳好的时候,就让小炮把藤椅搬到天井里,铺上被褥,大花把婆婆抱出去晒太阳。婆婆大小便失禁,几乎每次掀开被子,里面都臭气熏天,小炮就捂着鼻子干呕。大花不在乎,被子掀开,把脏尿布拖出来,给婆婆换上洗干净的尿布。接着把满是粪便的脏尿布拿到院子里,用小木板把大便刮个大概,放进塑料盆里,放上碱面,浇上热水,消毒。然后找来搓衣板,顾不得寒冬腊月的冷,在院子里哐哧哐哧地洗了起来。
屋内,婆婆拉着小炮的手:“炮啊,你说你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取了这么个好心眼的媳妇,大花虽然长得丑,那心地真是菩萨心肠啊。”小炮连连点头:“是咱娘俩都有福气,都有福气。”
大花洗完尿布,上搭下挂地晒了一院子。拿毛巾擦着冻得赤红的双手,冲屋里喊:
“娘,今中午想吃啥,我给你做去。”
“花儿,快过来歇歇吧,让小炮做饭。”
大煎饼坐在婆婆跟前,替婆婆拢着有点乱的头发。小炮在厨房里叮叮咣咣地忙活着。不一会儿,一阵熟悉的香味弥散了满屋。大煎饼吸吸鼻子,会心地笑了。她知道,小炮又做了她最爱吃的红烧肉。
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大花眼睛一亮,冲进了厨房,紧紧抱住田小炮大叫:“小炮,俺嫌饭了,这次,俺真的嫌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