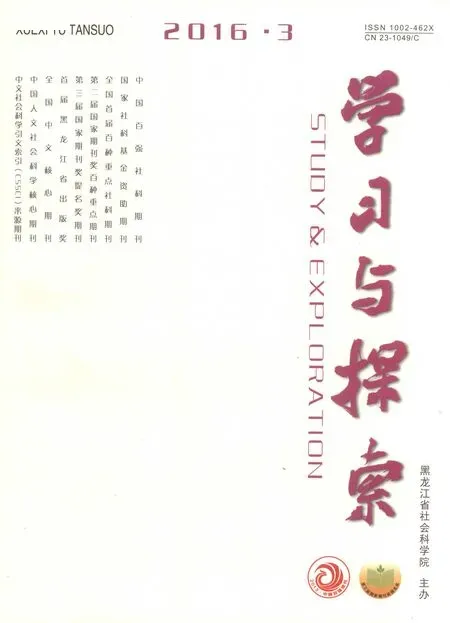艺术游戏的僭越与规约
——“艺术自律”:从康德到唯美主义(二)
王 熙 恩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艺术游戏的僭越与规约
——“艺术自律”:从康德到唯美主义(二)
王熙恩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艺术追求感官美学呈现,却以自律名义疏离感官欲求,这种矛盾既属于唯美主义也属于思辨美学。但唯美主义更强调艺术的绝对自主性,佩特的吸血鬼隐喻、王尔德的面具说,都强调艺术理念与生活的疏离,其结果不仅颠倒了艺术与人的关系,而且否定了艺术自由的基础。
艺术自律;沃尔特·佩特;奥斯卡·王尔德;唯美主义;美的本质;康德
戈蒂耶将艺术自律理解为艺术的绝对自主性,直接引发了艺术的自主权要求与人文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衍生了去人性化艺术焦虑的积聚。这种窘况直到英国唯美主义出场也未获得改观。相反,佩特和王尔德不断重返德国古典美学寻找艺术自律的证据,不仅没有解决戈蒂耶留下的难题,而且提供了更多艺术去人性化的理由。以此反观德国古典美学,它同样具有唯美主义的矛盾:艺术追求感官再现,却拒绝人的感官欲求。思辨美学赋予艺术以绝对自治权,将内在的人文性置于其自主性要求之下,从而导致以其为基础的唯美主义最终将艺术幽灵化。佩特将艺术自律演绎成审美的吸血鬼传奇,王尔德则热衷于建构面具理论,他们对艺术家与艺术作品关系的讨论更为先锋,基本预设了海德格尔、罗兰·巴特以及德里达的艺术文本理论。但从根本上说,唯美主义并未解决艺术自律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作为“吸血鬼”的艺术理念
杰夫瑞·华伦敏锐地发现,在沃尔特·佩特的文艺复兴幻象中,“总是充满着吸血鬼和流离失所的景象,充斥着流放和死亡的折磨”[1]1045。这一判断击中了佩特的要害。在佩特的文本中,“吸血鬼”不仅是唯美主义艺术的整体象征——拒绝取悦于大众正如吸血鬼拒绝日光,而且揭示了他对艺术绝对自主性的理解——吸血鬼的非实体性、与感官世界的疏离以及它的自由自主性,表征了艺术感官表象下那种不可见的精神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佩特对《蒙娜丽莎》的解读上。
她比坐在其间的石头还要老,像个吸血鬼,已经死了很多次,深知墓穴的秘境;她曾是深海采珠人,记得她周围每一片海域的没落时光;她曾与东方商人交易奇异的织物:像丽达,特洛伊的海伦之母,像圣安妮,圣母玛利亚的母亲;这一切都宛如竖琴和长笛的曼妙之音进驻她的体内,仅以纯美之形塑造她不断变化的外貌,以及色彩变幻的眼睑和纤手[2]99。
在这个著名的段落中,佩特想象性地“复活”了蒙娜丽莎。但这种复活并非是一次性的,而是像吸血鬼一样醒来很多次,或作为采珠人、交易者,或戴上丽达、圣安妮的面具,以诸如此类的隐匿方式活着。与此同时,她避免了虚构化身的变幻不定,只作为“竖琴或长笛的曼妙音”去体验不同肉身的盛装。更重要的是,她暗示着一种无法让人接近的绝对主体性,即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它是一种来自于精神锻造并显现在肉体上的美”[3]98。对于人的世界而言,这个形象并不是透明的,精神与人的照面只存在于象征的意义上;并且,精神并非是时间内的连续性存在,它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不为人知的晦暗角落,与人短暂相遇后,就很快被持久的匮乏冲蚀。叶芝在《丽达与天鹅》中暗示了同样的匮乏原则,它几乎统辖了整个历史。丽达的美瞬间激发了神(宙斯)的欲望,神在短暂的欢愉之后便不知所终,而匮乏神性的丽达的子嗣则将人类带入滚滚的战争硝烟中。蒙娜丽莎那难以捉摸的微笑也暗示了这一点:她即将离开,然后隐匿到漫长的暗夜中,不会因为人类的精神匮乏而照面。
将艺术理念比作吸血鬼,是佩特一以贯之的做法。佩特刻意强调,文艺复兴先锋皮科的作品是“投向远古坟墓的一瞥”[2]31;而在关于梅里美的分析中,佩特坚信他痴迷于“来自坟墓短暂拜访”的人,他的角色都是“半肉身的鬼——一个吸血鬼部族”[3]22,归返的幽灵们演绎着“或许是最为残酷的故事”[3]9。劳雷尔·布莱克甚至发现,即使是佩特自己的作品——讨论艺术精神的小说,也没有脱离吸血鬼叙述框架[4]。介绍中世纪大教堂的《劳塞洛伊斯》、探讨德国文艺复兴的《卡尔》、关于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斯托克》,都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死亡气息。华伦也提供了证据:在取材于海涅《诸神流亡》的小说《阿波罗在皮卡第》中,佩特暗示了太阳神在基督时代就已死去,他只能作为一个吸血鬼返回[1]1042。古代世界的美似乎只能经由鬼怪之手抵达,它们以悬空的方式紧紧缠住当下,而它的实体——精神,却早已逃出了人的感官世界。
就像黑格尔理解的那样,美的理念在某个阶段以艺术的形式显现绝不是任性的冲动所致,它在恰当历史关口的轻盈逸出乃是精神的必然举措。诸如蒙娜丽莎这类审美吸血鬼形象表达的就是美和精神的连续性:“希腊的兽性、罗马的肉欲、中世纪的神秘”以及“现代的人性。”[2]98-99显然,黑格尔美学发挥了魔力,他给佩特提供了一种作为精神朝向自我意识累积发展的艺术史观念。通过吸血鬼象征重构的蒙娜丽莎形象是美的理念在历史最后阶段的圆满完成。这正如黑格尔对古希腊雕塑、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艺术的评价一样,美的理念能够对精神的纪元予以艺术表达。
佩特理论的黑格尔基础最早体现在1867年版的《温克尔曼》中,在那里他将艺术描述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通过艺术“成为感觉对象”,美的希腊雕塑是理念现身的理想中介[5]94。随后他进一步宣称:“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建立在感官经验更新和“精神”进步的基础上[2]146。他力图表明,艺术发展需要经过若干文化阶段,它是精神的体现。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佩特并不把精神运动看作完全扬弃片面性的上升过程,也不相信艺术的终结,而是将它的每一次现身视为美的累积性呈现,如同蒙娜丽莎凝聚着兽性、肉欲、天启和人性一样。在佩特看来,人性是精神的最新纪元,“现代哲学已经理解了人性的理念,它由一切思想和生活的模式所造就,同时又是它们的概括”[2]99。因此,人性之美也就出现在现代艺术中。
那么,艺术缘何能够呈现累积的美?这需要考察艺术和印象的关系。根据佩特的阐释,印象是大千世界“残留”在思绪中的模糊记忆,是一组不能被语言形容的色彩、气味和结构。印象的本质特征是在瞬间呈现真实性与意义,它“携带着转瞬即逝的真实性遗迹,不断地在时间长河中变革自身,意义逐渐鲜明”;随着“形象、感觉不断地掠过与消失”,它最终“表现为我们自身的奇异组合和永恒的拆解”[2]187-188。这表明印象虽然驻留在人的记忆中,却不能被人左右,它是自主运转的合目的性的存在。印象寻求恰切的艺术表现方式,要求艺术摆脱单纯信息的支配及主题、材料责任,努力追求纯粹的感觉,以此确保印象的原态——形式与内容的同化(identification)。在佩特看来,理想艺术的共同特征是“不能从它的内容自身删减任何东西”,诸如音乐、抒情诗和典范绘画,它们的形式与内容一道“为每一种思想和情感”提供单一的感觉效果[2]103。这也决定了艺术门类之间的不可转译性,因为它们对应的印象状态和美不同,都有“自己处理印象的特殊规则”;至于艺术间的形式借鉴,“通过部分地疏远自身的局限性,艺术能够彼此间相互提供新动力,但不是真正的取代”[2]102。由于艺术与印象的这种同质同构关系,它必然拥有印象的功能——能够将无数瞬间的真实性打造得越来越精良。这种“打造”不是单纯的扬弃,而是对每个瞬间的真实性进行片面性扬弃后再将之累积。因此,典范艺术所表现的就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美,而是“美的累积性和综合性”。《蒙娜丽莎》如此,乔尔乔内的《音乐会》也是这样。
它是极品戏剧诗的理想部分,给我们提供了意义深刻而生动的瞬间……漫长历史的全部动因、趣味和结果,都将自己浓缩其中了,它们似乎也将过去和未来全部融入了目前的强烈意识中。乔尔乔内画派用他们令人感佩的技艺选择了这些理想的瞬间,它们来自古老威尼斯市民的狂热、喧嚣的世界……从中我们仿佛旁观了历史的全部过程[2]117。
所有的历史趣味都在《音乐会》中呈现出来,因而这一凝固的瞬间才具有丰满的意义。不过,按照佩特解读《蒙娜丽莎》的方式,这种美的聚集无疑又是一次诱人的闹鬼场面,纪元性的审美吸血鬼一同涌现在“音乐会”上,而我们如同听到了塞壬的歌声般着了魔。佩特的悖论由此昭示出来:作为美之理念的吸血鬼原本是历史和现实之外的存在,没有任何人文企图,却能够携带着与人相关的全部精神闯入现实;它以历史性的精神纪元为依托,但其现身的瞬间性和封闭性又破坏了任何确定它与历史进程发展一致的企图。审美吸血鬼超然于生活,若想领略她的全部风采,或想从她那里探寻美的理念,就必须像佩特一样,“需要培育冷对生活的超然或故作冷漠的反讽姿态”[6]。
从佩特的角度来说,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艺术的象征形式。蒙娜丽莎那不可捉摸的目光表明,丰满意义的否定时刻恰恰冻结在精美的象征中。她不可思议地抵制了全部自我的感官再现,使得不可见的剩余物无法表征。佩特关于形式携带全部内容的论断遭到了残酷解构,他被迫承认:“丽莎夫人或许能够作为古老幻想的体现,也能作为现代理念的象征。”[2]99审美吸血鬼的自持性和隐匿性拉开了它与人的距离,“如果人们在世事的流变中不能成为丽莎那样的超然存在,就无法从佩特的文章透镜中看到她的真实面孔”[7]121。这让形式背后的精神变得可疑起来——它是确定无疑的实体存在,还是想象性的虚构?
佩特对黑格尔的修正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在黑格尔那里,人与艺术都是精神的产物,这种亲缘性使人能够享受艺术上升运动的成果。但佩特解除了人与艺术的亲缘性,并坚持美的理念的累积性呈现,其结果是显著突出了艺术形式之于内容的限度,且拉开了艺术与人的距离。事实上,佩特只需要稍作调整就能实现对黑格尔的突破。
首先,印象不能被确定为人之外的自主运动实体,而是随着人之情感体验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属性决定了印象能够实现意义的累积,并能够在某个历史纪元的适当时刻被充分表现出来。印象意义的积累在于审美文化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叠加与张力,它是文化共同体的普遍性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和经验的聚集。印象的这种性质不仅使之与生命意义的表达相关,而且强化了它的历史性。只有从这个角度,印象的意义才能表现为“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和历史趣味的观照。当印象上升为艺术时,它的累积性和自持性就呈现为巴特意义上的“文本穿越”:“文本无法(像驻留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作品那样)停息;它的构成过程是径直穿越的运动,特别是能够穿越作品,穿越数部作品。”[8]因此,将印象还原成人的内部存在不仅不会损害它与艺术的自主性,而且能够强化人文性。
其次,艺术的象征形式并不是一种遮蔽,而是艺术意蕴多元性与自持性的表现。伽达默尔在阐释艺术构成体时指出:“现象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它的产生过程,或将其驱逐到不确定性中。”[9]89这意味着印象意义的累积和它的不确定性呈现都是艺术游戏本身的“规则”决定的——游戏规则本身决定了艺术的象征性和意义的不确定表达。对接受者来说,象征性作品总是意义丰满的,即“文本比起每一个其可能的阅读所要求的实在,有更多的实在”[9]73。这种敞开的封闭性也正是艺术自持性的表现,它虽然在艺术作品中“一劳永逸地……准备和任何与之相遇的人照面,在它的质中被感知”,但它自身却是“意义的隐匿,使意义不能流逝和确证”[9]125。这表明美的累积性呈现与艺术形式之间并不矛盾。
令人遗憾的是,佩特放弃了一次自我矫正并超越思辨美学的机会。当然,这对佩特来说无关紧要,他在意的是艺术的自主性及其意义:似乎只有永恒超然的审美吸血鬼才能有效地阻止19世纪的种种人道主义说教。
二、艺术精神的面具与谎言
在韦勒克的印象中,王尔德“根本没有固定的视野”,他总是“在泛唯美主义、自律艺术和装饰形式主义这些根本不同的观点之间不断转换”[10]。这种指证实际上距离王尔德相去甚远。在艺术观念上,王尔德从未远离佩特,他对审美吸血鬼的迷恋并不亚于佩特本人。卡米尔·帕里亚已经阐明: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反复运用了多种经典吸血鬼隐喻,包括神圣的贵族人物、不可抗拒的精神影响,以及性占有[11]。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部小说理解为一部吸血鬼传奇:亨利·沃顿勋爵是迄今为止最慵懒的审美吸血鬼,他深知美的奥秘,精致的享乐主义和贵族式的冷漠超然并举;他最终在道连身上发挥了影响力,使之成为冷对生命的吸血鬼。这个吸血鬼制造吸血鬼的过程,如同克尔凯郭尔描述的反讽吸血鬼一样,它“让个体在临近崩解之际获得最好的感觉……一边吸着情人的血,一边扇着凉风,使之沉入梦乡,然后用噩梦折磨他”[12]。道连的噩梦最终使他的冷漠发展为暴力,他杀死了自己的真正创造者——巴兹尔·霍尔沃德。
巴兹尔·霍尔沃德是佩特式的希腊文化崇拜者,他深信美的理念必然寻求适宜的形式,道连就是希腊精神的表征。因此,他初遇道连就感到灵魂和天性都被吸走了,隐约觉得命运的悲喜一同袭来。如同佩特审视蒙娜丽莎那样,他在道连的光辉外表下看到了抽象的美与身心和谐。当它们被巴兹尔呈现在画像中时,来自墓穴的希腊精神就被定格在艺术的可见存在中。在巴兹尔看来,其人文价值不言而喻,就像艺术的化身茜比尔·文能使时代脱俗,能赋予没有灵魂的人以灵魂,能以美感引导道德、驱除欲念[13]70-71。可见,巴兹尔更强调美和艺术的人文性。
王尔德认同巴兹尔对美的崇拜,因为“视美为美的人是卓越的”,在“美中寻美的人”都是有教养的[13]3。但他并不认同巴兹尔的人文版唯美主义——企图利用艺术建构“人间天堂”。此前,另一支英国唯美主义力量就是这样做的。约翰·罗斯金推广的哥特文化运动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14]。肯德拉甚至认为从罗斯金的有机体说到佩特和弗农·李的鬼怪美学都是种族主义的,他们都希望通过美学运动救民众于水火[15]。但佩特并不赞同罗斯金等人的观点,他在1868年的《美的诗歌》中将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田园诗《地球上的天堂》视为缺乏超越努力的表现,称他的人间天堂理念是一种“思乡病的倒置……不具有圆满生活的任何现实形式”。这种形态的美匮乏上升的运动性和提升生命的现实性,以及新诗人对静止、确定和稳固之美的渴望,实际上都是与美的自主目的背道而驰的。佩特将同样的批判标准用在了罗斯金身上,表达了他对艺术自主性的担忧[16]205。就此而言,巴兹尔已经偏离了佩特与黑格尔,他在艺术目的之上强加了人的目的,过分关注“精神的感官化”。所以王尔德不无讽刺地说:“所有的过分……都将给自身带来惩罚。那个画家,巴兹尔·霍尔沃德……过分崇拜肉体之美,他在某个人的灵魂中催生了一种巨大而荒谬的虚荣,而他却死于此人之手。”[17]
王尔德对“精神感官化显现”的拒斥源于黑格尔,后者强调音乐与文学艺术的优势就是直接向人的意识呈现美。王尔德不仅肯定了音乐的完美,而且断言文学是最终的艺术,文字是最完善的艺术媒介[18]443。在王尔德看来,语言的优势不仅在于它有乐音、色彩和造型,而且“独具思想感情和灵性”——语言就是思想和情感的本源,人们借助语言不仅可以超越自身,而且可以拥有全部的美,画家则只能借助于身体形象或传统形象表现心理情绪[18]398。王尔德的理由与黑格尔一致,认为艺术精神已经来到新的时代,造型艺术的“单一性面具”已经不适合精神的象征:“艺术本身的完美在于她的内部而不在外部,她不应该由任何关于形似的外部标准来判断,她是一层纱幕而不是一面镜子。”[18]342这一出现在《谎言的衰朽》中的观点,暗示着王尔德对黑格尔浪漫型艺术的独特理解:艺术形式作为艺术精神的面具(masks)需要采取“谎言”的面孔。这是王尔德关于面具理论的最早阐述。
在某种意义上说,佩特对蒙娜丽莎精神属性的强调已经预示了王尔德的面具理论。蒙娜丽莎的优美形象就是作为面具出现的,她只是曼妙的精神侧影而非精神的全部。审美吸血鬼需要一张精美的面具,因此,我们只有在佩特使用“喻指叙述”(ekphrasis)转化她的故事时,才获得了美的理念的消息。这涉及艺术形象作为精神媒介之条件的限度问题,如果精神被固定不变的媒介所限定,它就不能“体现”精神的无穷可能性,反而是作为遮蔽性的面具存在的,这迫使佩特不得不诉诸文学手段进行解析。王尔德对佩特的蒙娜丽莎分析赞誉有加,称其是根据“印象”和“艺术目的”的创造,如同“长笛手所吹奏出的音乐”一样[18]414。佩特还讨论了梅里美创作的面具性质,认为他“总是携带他自身,作为一种伪装和面具,给现代世界披上传统的装束——用无限丰富而傲慢的优雅装饰并隐匿现代世界”[3]9。这些讨论刺激着王尔德,启发他做出诸多惊人的判断。
在王尔德看来,艺术说谎或戴上面具的根本原因,在于她需要借此隐匿或表现自身。面具是一种艺术准则,它同时提供了伪装和丰富作品意蕴的方法。这就如同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既要有礼仪的庄重又要有其虚假性,要把传奇剧的虚假成分同剧中悦人的机智和美结合起来”;伪装“仅仅是一种丰富我们个性的手段”,它可以理解为艺术品追求复杂性[13]121。司各特的作品总是戴上各种花样繁多的面具,但是“假面具比真面孔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这些假面强化了他的个性”[18]362。面具同时增加了艺术的神秘性,“让人着迷,使人欣喜”[18]341。任何直白的艺术表达都无异于自毁,面具意识匮乏将导致艺术美的丧失,艺术的真理“就是假面的真理”,若想看到真相,必须通过假面[18]486。因此,只有说谎的艺术才具有复杂的个性和美的外观,才能真正表现自身——“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乃是艺术的真正目的”[18]357。在此,王尔德不仅发挥了佩特的观点,而且呼应了康德关于艺术是假象游戏的观点。
尽管王尔德将艺术说谎论追溯至柏拉图,但在根本上否定了柏拉图的观点。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模仿的现实只是理念的影子,这一“理念影子的影子”的性质决定了诗歌不可能提供真理。王尔德则认为,艺术对生活和真理都没有兴趣,人类感兴趣的事实、真相、意义、有用性等,艺术毫不关心:任何“对我们有用或必要”或者“使我们痛苦或快乐,或者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同情,或者组成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它就在真正的艺术范围之外”[18]333。艺术依靠想象和艺术之间的借鉴来创造美,只有“远离现实……才能揭示出自己的完美”。“最高的艺术抛弃人类精神的重担,从一种新媒介或新物质而不是从……人类意识的任何伟大觉醒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它纯粹按它自己的路线发展。”[18]352佩特将蒙娜丽莎想象为“坐在岩石中”,而不是将之理解为对画师献殷勤的人,表明佩特没有把生活与艺术混为一谈[19]81。艺术的确可以提供意义:表层的或象征的,但专注于此的人要“自己承担风险”[13]3。艺术的自主性就体现在它的超然存在上,艺术的面具与其说更好地注释了自身,毋宁说它是精神隔离现实的媒介:“它在自己和现实之间保持了不可侵入的屏障。”[18]336这才是王尔德面具说的真正用意。
艺术为何必须疏离生活?与佩特不同,王尔德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艺术遭遇了生活的不公对待:“艺术从不伤害我们”,教我们抵御现实的风险和文明的生活方式[18]429-430,给予生活“以新的形式”,而生活却将“艺术赶到荒野去”,成为“破坏艺术的溶化剂”和蹂躏艺术家园的敌人[18]335-336。王尔德将这种现实斥责为颓废,并通过亨利与道连表现出来。
亨利以艺术自律的态度看待自我,将生活目的定位在天性的充分实现上,而天性则被他解读为感官享乐,声称“只有感官才能拯救灵魂”[13]121。他将自己视为艺术家,将道连视为他精心创造的艺术品——优美的外形、高度的复杂性和条理化。在他的循循善诱下,道连掌握了全部纨绔技能,意识到生活是最伟大的艺术,享乐主义会重新创造生活。以此为参照系,无论是亨利接近巴兹尔,还是道连爱上茜比尔·文,抑或是道连根据于斯曼《逆流》中的巴黎青年作比成样,都是生活模仿、盗用艺术的证明,更不用说道连用灵魂交换了自己画像中的容貌。然而纨绔生活最终泯灭了道连的人性:茜比尔·文因为他的冷暴力而自戕,巴兹尔命丧其手。在幡然醒悟之际,他慨叹不老的青春只是一副面具,“一种拙劣可笑的模仿”[13]185。年轻、自由的外表下积聚着灰暗的现实,即使做了人道主义的善事也无法挽回他对艺术的伤害——画像中的他正在老去,露出令人厌恶的狰狞表情。由此而论,王尔德这句“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就绝不是一个口号或观念,而是一道流血的伤口。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王尔德将生活伤害艺术的源头指向人类历史。当道连漫步于乡间别墅的家族美术馆时,他发现“自我”不过是先祖的馈赠,而非自持自立:“陌生的思想遗产和激情在人体上开凿了一个涌入的小孔,使人变成了复杂多样的创造物,肉体则被亡者的可怕疾病所污染。”[13]121亡者的思想遗产隐秘地注入“自我”之中,使之陷入欲望的漩涡而不自知。同样的观点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再次被重复:人们经历的生活只是死人的生活,灵魂并不是属于自我的单一精神实体,而是“在古墓里造起居所的东西”,它将各种疾病和怪异的罪恶注入我们身上,使人充满欲望[18]433。王尔德将人类精神归结为疾病和罪恶,彻底否定了它对艺术的任何建设性作用。就此而言,王尔德面具论的实质似乎并非意在指出艺术自律的真相,而是源自他对人类精神的不信任。这也表明王尔德并非一个鹦鹉学舌者,在波德莱尔、戈蒂耶和佩特之外,他提出了独特的面具论,即面具是语言和符号编制的迷雾,是艺术疏离生活、孤立人类精神的屏障;它是艺术的准则,也是艺术自主性的卫士。
三、唯美主义的悖论
通过鬼怪形象的引入,佩特和王尔德讨论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以及它对艺术自律实现的意义。然而,艺术自主性运转的主观条件是什么?来自现实生活的艺术家如何能够摆脱人类精神?
王尔德的回答是干脆的:“揭示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13]3我们看到,画家巴兹尔始终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上。他先被道连的外观所吸引,尔后将之视为“法律”,在忘我地完成画像后,作品却逃逸了。更吊诡的是,当他指责“作品”进行自我破坏时,却被作品杀死。这种奇妙的隐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王尔德已经预示了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20]。不过,王尔德在此指出的并非是作品要求篡改自身的权力,而是作品的绝对自主性。逃逸的作品渴望回归,当他看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居所——那唯美的艺术形式——被狡猾、虚伪和罪恶的灵魂占据时,一刀刺下去。盗用艺术面具的世俗道连死去了,作品如愿以偿地回到艺术世界。至于巴兹尔,不过是道连画像实现自立的手段。多年以后,海德格尔为此提供了脚注:艺术家的本己意图就是让自身成为作品从一切外在关联中解脱、释放自身、抵达纯粹自立之境的手段,所以“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21]。
然而,我们必须辨识这一切的虚构性质。事实上,王尔德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阐述在艺术家这一环节从未明晰过。为了作品出世而自行消亡,这是王尔德对艺术家的理解之一。他的另一种理解是佩特式的印象审美者,他总是处于闲逸的沉思与孤独的造梦中,其生活是无为的,如同庄子的逍遥游,与重视行动的世俗生活截然不同:“沉思自省的生活……不是行动而是存在。”[18]435沉思、想象、造梦是艺术家生活的全部,然而王尔德所谓的想象“并非同时代气息相隔绝。……想象是继承的结果,它只不过是人类经历的聚合”[18]434。这即是说,想象根本无法脱离人类生活。他正是凭此解读威廉·莫里斯的,以此赞美他的诗充满希腊式的欢快与情感,提供了希腊式娱乐[19]62。王尔德强调美与人的疏离,但又声称“人有多少种情绪,美就有多少种意义”;“不仅是形式的瞬间的美或色彩短暂的喜悦,而且是整个感情空间、思想的所有范畴都属于诗人的领域”[18]435;“为感情而感情是艺术的目标”[18]430。这些论调几乎解构了他的面具理论,所谓美的理念超然于人类精神的历史与现实,只是偏执的玄思而已。就此而言,韦勒克指责王尔德随意、混乱的理论作风并不过分。
王尔德最终引起了佩特的不安,毕竟他的种种怪论多源于佩特的启示,而且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在《温克尔曼》中,佩特将艺术家理解为视艺术为生命的创造者,“带着一种急躁的冷酷,如此自然地欢呼远离和越过他们自己”[2]183。这暗示着艺术家必须规避世俗,完全根据艺术的意图来建构自我。达·芬奇是个出色的例子:他的生命如同“一次突然的造反”,“他的高度冷漠,对普通事物形式的偏见”[2]77使其“通往圆满的道路,被一系列厌恶所铺就”[2]81。这是达·芬奇站上审美自主性源头的根本原因。他的优美旨趣的形成,只是由于他将艺术视为生命的目的。
其他艺术家由于忘我或者将道德和政治的目的置于艺术目的之上,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掌声同样漠不关心;但在他身上,这种美的单一文化好像已经变为一种自恋,一种在艺术作品中除了艺术本身什么都不关心的冷漠[2]92。
海德格尔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是艺术家的本己意愿。但佩特在此强调的则是艺术家的个性与他的作品能够互换,艺术家的自我就是作品本身,他在释放作品的同时也将自己送达自立之境。这意味着艺术家必须销毁自我中的世俗成分,“什么都不关心”。在佩特的论述中,艺术家的死亡欲求欲盖弥彰:杰出艺术家们“那种无情和冷淡,已经有了死尸的样子”[2]179;在皮科的作品中,同样的冷漠意味着“抽象的冰冷触觉和柏拉图主义者渴望的脱离肉体的美”[2]33,他将自己描述为“活在坟墓中的人”恰如其分[2]38。这些密集的幽灵隐喻暗示着,艺术家必须“死亡”,只有成为超然于世的幽灵才能获得艺术理念的授权。这就如同康德、席勒、黑格尔意义上的天才,他们是天赋美之理念的人,远离世俗欲念才能获得精神的青睐。美的法则虽然居于天才内部,并且“绝没有建立一种适用于美的客体的自主领域”[22],但这种自我立法的审美主观性在其先验性的规约下变得似是而非。
显然,佩特的艺术家论不过是证明艺术的绝对自主性及其可能的问题。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王尔德竟然将之征用为艺术去人性化的理由。这迫使坚持艺术自律与艺术人文性并举的佩特不得不反思,《普罗斯佩·梅里美》就是这场反思的产物。其中,佩特更为深思熟虑地阐释了审美吸血鬼感官显现的主观条件——艺术家,以及调停艺术理念与人文要求之矛盾的企图。
梅里美以《卡门》等闻名,佩特在这些“来自坟墓”的故事中看到了梅里美的世俗自我克制、从始至终的超然反讽风格以及它们与暴力鬼怪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梅里美青睐不死的幽灵,他们聚合唯美与暴力为一体的性格“与作家的精神构成高度一致”,这确保了梅里美能够保卫艺术的自主性。然而,这种精神却构成了对道德与人性的反讽,成为梅里美作品背后的引导原则和强制力量。尤其糟糕的是,梅里美将隐匿的强制力量与虚无主义联系起来:“他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空洞的事物……反讽无疑是弥补虚空的恰当填充物。”[3]4他对虚无与反讽的热衷,表明唯美主义自身存在局限性。这似乎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后康德主义的继承有关,梅里美“在康德的否定判断中发现了最后一个关乎不可见世界的词——désillusionné(失望)”,如同雨果或波德莱尔以夸张的艺术形式反复召唤某些人为刺激物:嗑药、赌博、投机、冒险、斗牛[3]2,而他的冷漠风格又对福楼拜产生了影响。法国文学对幽灵、暴力与虚无的一体化表达,以及那种冷漠的反讽风格,令佩特忧心忡忡。他试图阐明,以法国文学为导向的英国唯美主义绝不该走向这条道路。可惜的是,仅在数月之后,王尔德推出了《道连·格雷的画像》,幽灵、暴力、虚无、反讽,一个都不少。
佩特郑重地表示,王尔德视野中的享乐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它不仅歪曲了他的理论,而且误解了伊壁鸠鲁主义:“真正的伊壁鸠鲁主义,其目的是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人的完整有机体”,如果丧失了道德感、罪恶感和正义感,“如同王尔德先生的英雄们如此迅速且一心想做的那样”,人必将退化[23]。作为艺术家或审美者,他不是艺术的附庸,而是为了自我完善。佩特的这种立场在《文艺复兴研究》再版时就已体现,当时他担心自己的为艺术而艺术论会被误读为感官享乐主义而删去“结论”,直到他在《马里乌斯》(1885)中对其充分阐述之后,才将“结论”稍作修改,收进第三版[2]186。但深受“结论”影响的王尔德并未理解佩特的良苦用心,执意地走向虚无和反讽。
佩特坚信,艺术理念的超然与艺术的人文性并不相悖,前者的超越性正是艺术的人文性来源。其一,艺术带来激情与智慧并举的人生。艺术体验的回报之一就是“伟大的激情”与“智识的激越”,因为“诗的激情、美的渴望、为艺术而热爱艺术,乃是智慧的极致”[2]190。这种智慧是一种沉思,它“使人生的手段与目的完全一致”,使人完全处于自由而完美的状态。其二,艺术提供最高道德的人生。艺术的沉思属性决定了这一点:“将人生目的看作是沉思而不是行动——是being而不是doing——无论何种语境,都是一切高层次道德的准则。”[16]62华兹华斯的诗从不“提供教训”,却通过抒写自然力的运行、可见宇宙的形状以及人类的共通情绪,将读者思绪“从纯粹物质的人生追求上移开”,悄然实现“教养的目的”[16]62-63。艺术体验的人文价值使佩特确信,艺术就是人生中最高的东西。他反对罗斯金与莫里斯的理由即在于此,“他们高度评价艺术与自然之美,却没有将它的生活重要性提到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24]。然而,无论佩特怎样强调艺术的人文性,这个针对唯美主义艺术僭越的规约指令都可能无效。至少,佩特本人欣赏的审美吸血鬼总是以超然于生活的假面出现的。她的刹那间现身标记的是否定时刻:戴着面具,瞬间消逝。这是犀利的反讽:人们企盼与精神照面,而她留下的只是踪迹。佩特提供的审美方式进一步增加了反讽的效果:精神不可思议地抵制感官呈现,阻止任何与之达成和解的经验意向,而佩特却号召我们乐此不疲地追寻她。这就是德·曼所说的“二度反讽或‘反讽之反讽’”[25],它是刀,也是刀赐予的创伤。艺术理念的幽灵形式让佩特的人文憧憬变得不切实际,这缘于他过分迷恋艺术自律,倒置了人文要求与自主权要求的次序,颠倒了艺术与人的关系。艺术终归是人的创造,是存在之思与人生情感的表达,它的人文性是内在的,也是艺术美的本源。无论人文性是否带来了艺术的限度,它都是艺术自由的基础。否定了这一点,将绝对自治确立为艺术游戏的首要原则,吸血鬼的威胁(去人性化)就不可避免。反讽的是,20世纪的理论家们依然热衷于此,海德格尔、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都曾阐释过文本的幽灵性。真不知何时,鬼怪们会穿越时空,来到你面前。
[1]WALLEN J.Alive in the Grave: Walter Pater’s Renaissance [J].ELH, 66, 1999(4).
[2]PATER W.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M].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PATER W.Miscellaneous Studies: A Series of Essays [M].London: Macmillan, 1895.
[4]BRAKE L. The Entangling Dance: Pater after Marius, 1885—1891[C]//Transparencies of Desire.Raleigh: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Greensboro: ELT Press, 2002: 24-36.
[5]PATER W.Winckelmann[J].The Westminster Review,1867,(31): 80-110.
[6]O’HARA,DANIEL T.The Romance of Interpretation: Visionary Criticism from Pater to de-Man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23.
[7]WILLIAMS C.Transfigured World: Walter Pater’s Aesthetic Historicism [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8]BARTHES R.From work to text[C]//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London: Hodder Arnold, 2001: 167.
[9]GADAMER.Gesammelte Werke, Bd.8,sthetik und Poetik Ι,Kunst als Aussage [M].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10] WELLEK R.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4[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408.
[11]PAGLIA C. 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 [M].London: Penguin, 1992: 518-519.
[12]KIERKEGAARD S.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M].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49.
[13]WILDE O.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6.
[14]DOWLING L.The Vulgarization of Art: The Victorians and Aesthetic Democracy[M].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15]KANDOLA S.Gothic Britain: Nation, Race, Culture and Criticism, 1707—1907[M].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8.
[16]PATER W.Appreciations, with an Essay on Style[M].London: Macmillan, 1910.
[17]WILDE O.The Letters of Oscar Wilde[M].New York: Harcourt,Brace & World, Inc., 1962: 259.
[18]王尔德.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M].杨东霞,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9]王尔德.王尔德读书随笔[M].张介明,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0]EAGLETON T.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5: 329.
[21]海德格尔. 林中路[M].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2.
[22]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81-82.
[23]BECKSON K.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 Routledge, 1997: 84.
[24]JOHNSON.Aestheticism [M].London: Methuen, 1969: 11-12.
[25]PAUL DE MAN.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M].London: Methuen, 1983: 218.
[责任编辑:修磊]
1002-462X(2016)03-0130-08
2015-12-0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2014M560273)
王熙恩(1973— ),男,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哲学博士,从事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I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