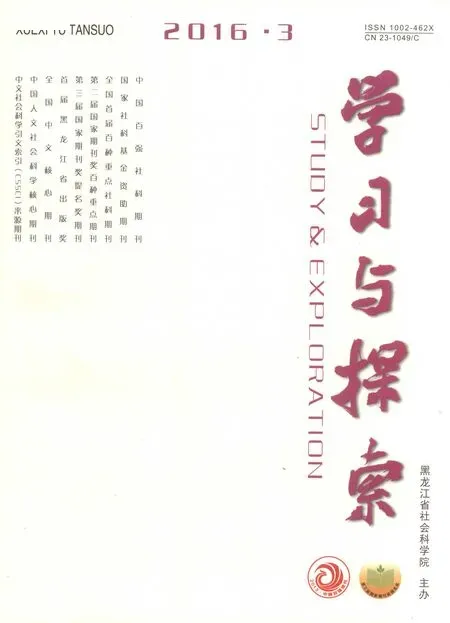国家干预生育的历史、法理与限度
吴 欢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7)
国家干预生育的历史、法理与限度
吴欢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7)
在中西方法律传统中,均能发现公民生育背后的国家干预之手,其原因在于生育法律属性的“变色龙”特征和生育问题在人类生存、国家战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近代以前国家将干预生育视为社会防御/惩戒手段和国力提升措施,到近现代国家将生育权视为公民基本人权,体现了对公民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与保护。同时,国家干预生育也有诸多伦理和法理上的依据与限度。在新形势下,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法制有必要根据中央决策和人民意愿进行法理上的正本清源,在立法、执法、司法层面进行修复和完善。
国家干预生育;生育权;计划生育;生育伦理
生育权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既简单又复杂的权利。言其古老是因为生育乃人类繁衍之基本途径,言其年轻是因为生育纳入人权谱系较为晚近,言其简单是因为生育作为基本人权本无须过多论证,言其复杂是因为生育往往承载过多考量而难以定论。作为法学研究对象,人类生育行为的法律性质就像“变色龙”一样,在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会呈现出不同面相[1]。 随着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生育权逐渐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但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法律传统还是西方法律传统中,均能发现公民生育背后那双国家干预之手。究其原因,在于生育法律属性的“变色龙”特征和生育问题在人类生存、国家战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被确立并执行了30余年,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效果[2]。 但随着中国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学界也在逐渐反思这一基本国策[3]。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的战略决策。由此,本文试图在梳理古今中西国家干预生育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探讨国家干预生育的法理伦理问题,进而剖析中国计划生育立法、执法和司法现状并提出若干完善建议,以使其运行更加科学化、人道化和法治化。
一、国家干预生育的历史演进与基本模式
生物意义上的生育现象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并将继续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社会意义上的生育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和象征;而生育权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以后,随着民主、人权与法治的进步而出现的法律概念。但同时,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归根结底,近现代生育权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人类千百年来的生育现象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类文明社会数千年来的生育制度为前提的。欲考察当代中国国家干预生育的伦理与法理依据,就必须与历史上的生育现象和国家干预生育的行为联系起来。
(一)国家干预生育的历史演进
人类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人口在社会发展延续中的重要意义,进入文明国家阶段后,各国更加自觉地采取多种手段干预人民生育。下文仅就其中具有法律史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整合,以勾勒古今中西国家干预生育的一般轨迹。
中国法律传统中虽然没有发育出近现代生育权概念,但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干预人民生育行为或生育能力的思想和现象却广泛存在。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主张人口大量增长。甲骨文关于祭祀的记述中就有浓厚的生殖崇拜思想,《诗经》也有许多篇章歌颂多子多福。儒家重视夫妇关系,将繁衍后代看作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务。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孟子主张“广土众民”(《孟子·尽心上》)。这种传宗接代思想长期支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墨子认为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富而民众,因而主张兼爱、交利、非攻、节用、节葬、力耕、早婚、反战、反殉等。南朝周朗宣称治国者“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宋书·周朗传》)。明朝丘浚指出“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因而君主必须鼓励人口增殖。同时,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较早地提出了人口适度增长的观点。商鞅认为“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商君书·算地》)。东汉王符也认为“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古代中国还存在主张控制人口规模的观点。韩非子认为人口增长过多过快是社会纷争的根源:“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明人徐光启认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农政全书·井田考》),所以江南地区日益人多地少,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清末洪亮吉则认为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办法一是任凭自然灾害减少人口的“天地调剂法”,二是由统治者采取控制措施的“君相调剂法”。尽管存在上述不同主张,但一般而言,历代统治者均认同“广土众民”的观点。
中国古代国家干预生育的手段一般是软性的,主要表现为既通过政策鼓励人民生育,也注重通过法令进行保障。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灭国后,卧薪尝胆,振贫吊死,并“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国语·越语上》)勾践通过奖励生女子和多生育来实现人口增殖和国力提升,体现了古代国家对臣民生育行为的软性干预。此后,中国历史上这种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法令比比皆是。如西汉高祖下诏:“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西汉会要》卷47)西汉元帝时为减少民间“生子辄杀”现象,将原来从三岁起“出口钱”改为自七岁起(《汉书·元帝纪》)。东汉章帝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及“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椹斛,复其夫,勿算一岁”(《东汉会要》卷28)。唐太宗发布旨在鼓励民间适龄男女及时婚配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并将户数多寡和婚配情况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唐大诏令集》卷110)。南宋规定,贫乏之家生男生女不能抚养者应予救济,官府有义务收养因饥谨而遗弃之小儿,民间收养遗弃小儿者官府出粟补助。明朝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减缓人头税负。清朝康熙帝诏令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逐步实行“摊丁入亩”,丁银和地赋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取消全部人头税。这类规定都是通过优惠或减轻赋税徭役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的例证,都在客观上免除了贫苦人民生育子女的后顾之忧。究其原因,在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下,人口的增殖既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也是社会安定的保障[4]。
中国历史上的宫刑也是国家干预生育的一种类型,只不过干预对象被特定化了。宫刑实质上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犯罪臣民生育能力的强制剥夺。传统礼法主张“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礼记·文王世子》),既体现了“刑不上大夫”的等级法思想,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宫刑对于臣民生育能力的剥夺及其意义。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思想家在论及国家治理时也强调人口因素,西方国家也注重运用法律手段鼓励生育,还曾以阉割干预特定人的生育权。
柏拉图认为,理想国要实行“共产”以使公民不因财产传递而欲添子女,实行“共妻”以取消家庭并抑制宗法势力,实行“共子女”以使公民不计较个人是否有后代;理想的城邦公民应是健康聪明之人,畸形孩子要被秘密处理;理想的城邦人口数应为5 040人,为确保此数应采取立法、强制移民和延请入籍等措施。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人口适度才有利于经济生活;适度人口的标准是政治上便于管理和经济上自给自足;调节居民数量及其相互关系是国家的职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标志,西方人口思想进入新的阶段[5]。 马尔萨斯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两大法则及其不平衡出发,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6]7进而他提出三个命题:“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长力,为贫困及罪恶所抑压,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6]43因此,他认为济贫法不利于限制工人人口增殖,反而会使失业和贫困等现象更加严重,而“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是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19世纪上半期至20世纪初是西方人口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以坎南等人“适度人口论”的提出为标志,西方人口理论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许多学者从文化、社会、法学角度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探究,其结论主要是国家应采取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
西方法律传统中还有很多旨在实现人口增殖的奖惩措施。古希腊雅典城邦不结婚的人要据其财产状况交纳不等罚金;斯巴达城邦里父亲生有三子可免服兵役,生有四子便完全免除对城邦的负担。古罗马通过授予提升行政权能和遗嘱能力的“三子权”来敦促公民履行生育义务,还规定生育三个子女的女人为自由人和生育四个子女的女人可以解放自由人免受宗亲监护并取得遗嘱能力。古罗马《关于婚姻的帕皮亚和波帕亚法》和《关于正式结婚的优利亚法》特别鼓励市民结婚和多生子女,并对独身者采取某些限权措施。为鼓励人民生育和保证战时人口,苏联于1941年开始对无子女家庭征税,并于1944年设立英雄母亲勋章,英雄母亲在退休金和食品等方面享有特权和特供。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政权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缴纳罚金,违规堕胎者将被判处刑罚。1803年英国《埃伦伯勒法》规定,胎动后的堕胎责任者将被判处死刑;胎动前的堕胎责任者将被判处海外流放。受此影响,到1849年,美国有20个州制定了限制堕胎法,但是1973年的Roe vs Wade案终审判决使得堕胎在美国完全合法化:在怀孕后6个月,女性可以完全自由或相对自由地行使其以消极方式表现的生殖权;在预产前3个月,女性的生殖行为则表现为义务,其目的首先是为了维护胎儿的生命权,其次是为了维护丈夫的生殖权,最后是为了尊重国家亲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通过一系列判决论及了男性的生育权:男性流产只适用于未婚父亲而不适用于已婚父亲,只适用于私生子而不适用于婚生子。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阉割与生育权的关系也颇具特色。查士丁尼立法规定,可以阉割并拆散与女自由人同居的男奴;东罗马帝国741年《法律选集》规定以阉割来惩治性犯罪;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则以阉割惩治嗜烟者;德国法西斯政权曾对性犯罪恢复去势之刑并作为附加刑适用于惯犯;西班牙弗朗哥政权曾长期对异议人士施以阉割之刑。这些都以剥夺生育能力的形式实施国家刑罚。但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君士坦丁皇帝亦曾规定对阉人为宦者处以死刑[1]。
(二)国家干预生育的基本模式
透过前述典型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西方历史上,均曾以鼓励生育为提升国力的手段,均曾不同程度将剥夺生育能力作为惩治犯罪和社会防御的手段,并且均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升华废除了强制剥夺生育能力的做法。这一切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伦理所致,是中西法律传统的内在暗合,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规律直到近现代仍在中西方人口和生育法制上有所反映,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从前述典型案例中,可以总结出国家干预生育的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阉割或宫刑等手段对部分人民的生育能力进行破坏,以实现对特定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与惩罚。这实质上是将国家干预生育作为一种社会防御或惩戒手段,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色彩,同时也严重违背了人道和人性。这种模式在古代中西方均有体现,在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程度遗存,但因其强烈的非人道性,已逐渐销声匿迹。这种模式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第二种模式是以积极奖励生育或者轻度惩罚不生育为表征,通过法律、经济、税收、宣传等手段倡导和鼓励人民进行生育以增加人口数量,提升综合国力。这实质上是将国家干预生育作为一种国力提升的手段,国家干预色彩较弱,符合人性和人道。这种模式在古今中西方均有体现,而且成为古今中西国家干预生育的主流模式,其中的法律干预手段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第三种模式是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加以推行。与第二种模式不同的是,这一基本国策的目标指向并不是鼓励生育,而是对其进行计划与控制。这实质上是以国家发展战略的名义推动国家权力在生育领域的深度介入,干预色彩较强,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种模式在当代中国被实行,其存在发展完善的空间。
二、国家干预生育的疑难问题与法理基础
从近代以前将国家干预生育视为社会防御/惩戒手段和国力提升措施,到近现代国家将生育权视为公民基本人权,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历史的进步。但在国家干预生育领域,还存在需要厘清的法理与伦理问题。
(一)国家干预生育的疑难问题
1.生育的法律性质问题。生育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或者兼而有之,需要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进行厘清。徐国栋教授指出:“生殖的性质随着特定国家的人口形势而变,在有的国家是义务,此等义务的轻重在各国又各不相同;而在有的国家是权利。尽管如此,国家仍把剥夺生殖权作为打击罪犯和进行社会防卫的手段。”[1]翟翌博士则认为,中国宪法文本中的计划生育兼具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包括作为社会权的计划生育权、作为社会福利义务的计划生育义务;作为社会权的计划生育权与作为自由权的生育权不同,计划生育义务并非强制性义务;计划生育权的实现以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为前提[7]。虽然两位学者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却有暗合之处。笔者认为,生育虽然并非一开始就是基本人权,但在中国经济社会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党和国家已经做出相关战略调整之际,应当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将生育明确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权利,如此才能应对多重挑战。
2.生育权的基本范畴问题。目前学界对于生育权的基本范畴依然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生育权的主体仅限于女性,有学者认为男性也有生育权,还有学者探讨了单身人士和死刑犯等特殊主体的生育权;关于生育权的内容,有学者认为仅限于是否生育,有学者则延伸到何时生育、如何生育等问题,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生育自决权问题[8]。 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权利主体应为具体公民,其内容包括是否、何时以及如何生育等与生育有关的自决权。换言之,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公民有权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公民有权选择生育方式;公民的生殖健康权利应该受到保障。所以生育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由众多相关权利组成的“权利束”。
3.国家干预生育的法理问题。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生育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是公民法定权利体系内最高位阶的权利之一,也是现代国家人民主权者地位之体现,是公民人之尊严的象征。此种权利不得随意限制、克减乃至剥夺,而必须由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司法活动加以保障,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其次,国家可以基于正当理由和程序对公民生育权加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在权利位阶上具有最高性,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全然不能够对其加以限制。从社会契约的角度而言,人民让渡部分权利,忍受国家对公民权利有限度的支配与控制,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安定社会秩序[9]。 所以国家可以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适当干预和限制,但必须经受正当性与合法性考问。
4.国家干预生育的伦理问题。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是人作为生物的第一本能,人类通过生育后代复制自身基因的权利是人作为生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种生物本能和自然权利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之根本,也是人类纲常伦理之要害。在母系社会时期,部落生存延续的第一要务就是繁衍人口,繁衍作用突出的女性受到尊崇,这就是先民社会自发地对生育伦常加以尊重和保障的表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俗语虽然一直被当做封建思想加以批判,但其中体现的对人类生育本能和伦常的观照却值得深思。在人权保障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如果要对公民的生育行为施加国家干预,除了满足法理正当性的要求外,还不得不面对伦理正当性的考问。从生育的伦理视角出发,国家政权必须尊重生育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地位。这种对于生育伦理的尊重,其实也和现代人权理论所要求的对“人之尊严”的尊重具有内在的暗合性。
5.国家干预生育的要害问题。国家对生育权的干预范围和手段十分广泛,人工授精、借腹生子、同居会见、代孕妈妈等似乎都涉及国家干预,但哪些才是要害问题?还有学者从民法角度探讨生育权问题,认为“非婚人工生育是享有生育权的权利主体实现其权利的一种方式,只要不违法,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权利人就有选择的权利或自由,无须他人的同意或许可。”[10]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些进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生育权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是私法问题,但是任何私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公法问题,任何私法问题到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公法的壁垒。“公民生育权的国家干预”这个命题本身就蕴含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公法关系、公法问题,从公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更能抓住要害。
(二)国家干预生育的法理基础
对于国家干预公民生育的法理基础,亦即国家干预公民生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问题,可以结合宪法学的“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加以探讨。
首先,国家可以对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加以干预。近代启蒙观念认为,任何针对基本人权的干预都天然地缺乏正当性;国家只需充当夜警的角色,在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侵害时提供保护和救济。但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职能,这天然地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公法学理论的变革。古典的宪法基本权利理论在应对公民对国家越来越多的权利诉求和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福利给付义务的现实面前缺乏解释力。因为古典理论一方面将国家权力束缚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要求国家对公民的权利诉求予以回应。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国家职能的全面扩张,国家权力对公民生活干预的范围与日俱增;公民在享受国家提供的全方位福利时,必须容忍公民权利伴随社会义务的后果。宪法学界因而逐步发展出“基本权利限制”理论。所谓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宪政实践中法定公民基本权利现实化的必要条件和途径;是通过一定的合宪形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范围和实现途径做出限制,从而实现权利之间的和谐和基本权利在实践中的实现;是为了避免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出现权利冲突,也使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中有裁量和权衡的依据;对那些可能产生冲突的基本权利,由立法机关对其行使和范围做出限制性规定[11]。“基本权利的不受限制必然导致社会公益的丧失和基本权利的相互对抗和妨碍。”[12]基于这一理论,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因其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巨大,公民在享受国家提供的人口政策福利时,也必须容忍国家对其生育权的适当干预和限制,这也是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宪法理论依据。
其次,国家对公民生育权的干预本身也应当受到限制。现代福利国家的现实需求为国家全方位干预公民生活提供了必要理由,但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干预和限制也必须经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考量。因为归根结底,国家进行福利行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民的自由发展与公共利益,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干预也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一个隐含的命题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本身应当进行限制。根据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基本权利为公民构筑起了一个自由的私人领域和生活空间,但也允许国家出于公益或其他价值的考虑而对基本权利予以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限制要件正是国家侵入私人领域的合宪性理由[13]。 遵循这一思路,可以得出基本权利限制的分析框架:“如果国家的一项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能够通过法律保留原则、宪法规定的限制理由、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等的审查,则该限制行为的违宪性被阻却,从而可以认定是对基本权利的合宪的干预。如果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不具备这些违宪阻却事由,则将被认定为是对基本权利的违宪限制。”[12]就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而言,尽管在现代公法理论框架中可以认为计划生育兼具权利义务属性,但是究其本质而言,它的权利属性是主要的,义务属性是次要的;即使在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的背景下,国家对公民生育权利进行干预,进而要求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也必须接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考问。换言之,国家对公民生育权的干预应当在目的、范围、手段、方式、程序等多方面全方位地满足正当性与合法性、伦理与法理的基本要求。
最后,国家对于公民生育权的干预还应当接受人类生育伦理的考问。生育行为和生育活动具有重要的人伦价值意蕴。中国古代生育的伦理价值基础定位于家族本位,即血缘延续的至高无上。从这一伦理价值基础出发,生育首先是一项伦理义务,具有极强的伦理道德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将生育行为视为是血缘传承、家族延续的伦理责任。换言之,中国古代婚姻的神圣性即在于伦理性的生育目的,生育的伦常考量重于婚姻的情感寄托。因此,生育还是一种责任担当,对于社会承担着繁衍人口的伦理责任。可见,中国古代的生育行为具有浓厚的伦理价值考量,对此不可简单地视为落后予以批判,而应当充分尊重此种民族文化心理。否则,国家的生育干预政策注定会受到传统伦常的强烈抵抗而难以收到实效。事实上,这种伦常考量也内在地与近代以来的生育权观念相暗合。近代西方生育权理论的价值基础在于个人权利本位,而以1942年“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案为起点,欧美司法实践进一步将生育权定位于人类自由、隐私权或者自决权,其背后的价值则是个人主义和人格尊严。 可见,现代西方权利话语中的生育权其实也潜在地具有对人格尊严、人道尊严的伦理考量。两者都体现了一种并不将生育简单地视为一种工具和手段的倾向,而且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类生育本身的敬畏与尊重。如何在这两种伦理倾向之间求得平衡与协调,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干预生育法制需要反思的议题。
三、对计划生育法制的省思与改良
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尊重与保护每一个公民人权和尊严的社会。生育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护。虽然国家基于人口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目标对公民生育行为进行必要干预和限制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公民生育行为的手段与范围等要素必须经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考量,经受伦理与法理的考问。
(一)中国计划生育法制的初步省思
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确立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出现了许多违背初衷的现象,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影响甚至消解这一基本国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相关立法未能充分导入和吸收有关国际法文件中的人道和法治精神,未对国家干预生育划定明确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中国生育权保障缺乏国际法层面的支撑。“二战”以来的一系列旨在加强生育权保障的国际法文件如1968年《德黑兰宣言》、1969年《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宣言等,未能恰当导入中国的计生立法。其次,宪法关于计生国策的规定较为笼统。作为计生国策宪法依据的现行《宪法》第25条之规定具有浓厚的强制计划色彩,在市场经济和保障人权条款入宪后,其面临正当性考问。同时,《宪法》第49条第2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规定忽视生育权的基本权利属性,容易滑向制定初衷的对立面。再次,相关法律对计划生育国策的规定较为空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落实计划生育国策的基本立法,但其内容多属政策宣示性质,欠缺可操作性。与之同级的相关法律也多为政策法,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有关规定”语焉不详,存在通过低层级立法将权利转变为义务,进而挤压公民生育权空间的可能性。复次,计生相关行政法规突破上位法自我授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存在突破立法权限自我授权等问题,尤其被社会公众广为诟病的就是《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本是国家依据福利行政需要,对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超生或违规生育带来的社会抚养成本的上升的一种补救,但因立法不明,在计生执法环节多将社会抚养费定性为行政处罚。最后,与计划生育相关的部分地方立法质量堪忧。各地方性计生立法是各地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直接依据,但某些地方计生立法一方面互相抄袭,呈现出趋同甚至雷同现象;另一方面倾向于突破立法权限自我授权,从而为基层计生执法侵权行为埋下隐患。在实践中,还存在大量行政规定、红头文件形式的计生执法准据,导致计生执法权力无法受到立法的有效制约。
相比而言,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层面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也是导致国际舆论和普通民众对计生执法反响强烈的重要原因。第一,服务职能空转。各级计生立法中较好的制度设计、服务职能和鼓励政策,以及需要地方政府进行的各种配套服务工作在基层遭受虚置或压缩。在某些地方,基层计生执法几乎不见服务,只见罚款。第二,罚款供养队伍。社会抚养费本应实行收支两条线,但在现实中,从名称到用途都存在语焉不详的地方,计生罚款几乎成为基层计生队伍的主要经费来源。第三,巧借罚款敛财。有报道显示,某地方政府曾集中整治计划生育乱收费乱罚款活动,主要针对摊派征收社会抚养费;故意放水养鱼、以罚代管;借病残儿鉴定进行违规收费;以经济处罚代替落实节育措施的各种收费;办理各种计划生育证明收费;非执法主体收费或存在收费打白条行为等。报道虽然从正面立论,但也折射出诸多罚款乱象。第四,依赖强力执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权威释义指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而是倡导性义务,主要采取国家指导、群众自愿,必须从鼓励和提倡入手[14]。 但基层政绩考核多年来实行“计生一票否决制”,当罚款不能解决问题时,扭曲的政绩观就会引致各种强力手段。第五,行政救济缺失。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信访等行政监督机制对计生案件设有禁区,公民生育权益和其他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无法在行政渠道内获得救济。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无法有效监督计生行政执法,导致公民生育权被侵犯后得不到有效救济。首先,受制于司法实践中的禁忌与潜规则,计生行政案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公民生育权很难得到维护。其次,某些基层法院有时会参与基层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攻坚战”和专项工作。很多地方出现的野蛮计生执法事件中,均可以看到司法机关的身影。可见基层法院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角色错位之严重。最后,基层法院各项事务多受制于地方,其法官干警计生情况是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故基层法院即使受理计划生育案件,亦无法有效承担司法审查职责。
(二)对中国计划生育法制的完善建议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可动摇,并不意味着相关政策法制无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调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顺应时势做出了“全面开放二孩”的战略决策,在老龄化危机空前严峻的当下,有必要进一步参酌古今中西国家干预生育的伦理法理和经验智慧,对计划生育政策法制进行正当性与合法性修复,以实现计划生育领域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和宪法法律的和谐统一。
第一,法理层面的正本清源。生育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不仅是国际人权发展潮流,也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定性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并不矛盾。因为后者的正当性来源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目的,其宗旨也只能是保障和促进公民基本权利。将生育定性为公民基本权利并不违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在此定性与定位下,现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也能获得正当解释。因为承认生育权的公民基本权利地位,并不否认国家基于发展战略需要对其进行正当干预,不意味着公民在行使此项权利时可以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如此定性还可以从法理上遏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执行中的诸多背离初衷之举,巩固这一国策的正当性基础,减轻国际舆论压力,回应人民权利诉求。将生育定性为公民基本权利还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进一步调整预留了法理空间。
第二,立法层面的协调完善。在立法层面,应基于人权法理和生育伦常,坚持可持续发展、权利义务相统一和法制统一等原则,对现行的计划生育立法体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清理整顿和修订完善。具体而言:在国际层面,应尽快承认和导入有关生育权保障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切实提升国内人权保障水平并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对外形象;在宪法层面,可以暂不修改有关表述,但应当发展宪法解释技术,启动宪法解释机制,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条款解释为国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可以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将夫妻计划生育义务条款进行限缩解释以凸显生育的权利属性;在法律层面,应确立和落实权利本位的指导思想,修订有关义务本位的规定,尤其应当尽快废除生育行政许可制度,加强计生服务职能及其可行性,承担起国家的伦理法理责任;在法规规章层面,应当坚持依法立法和法制统一,以中央立法统领地方和部门立法,清理修订有关法规规章;在规章以下层面,尤其应当进行彻底的清理审查工作,修改和废除违反上位法自我授权、以罚代管等内容,结束计生执法准据上的混乱和粗疏局面。
第三,执法层面的正当性修复。在执法层面,应坚持以人为本,杜绝以罚代管现象;增加执法投入,杜绝罚款养人现象;坚持公平公正,杜绝敛财执法现象;废除一票否决,杜绝强力执法现象;加强执法监督,杜绝救济无门现象。在党中央做出“全面放开二孩”战略决策的现阶段,尤其应当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充分尊重和体认公民生育伦常,在执法中保持谦逊与克制;在政策过渡期内酌情尽快停止实施计生行政许可,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停止执行有关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切实加强计生服务职能,建立健全高龄产妇生育、婴幼儿保健、新生儿入托、养老社会化等配套措施;在户籍、升学、就业、劳保等领域逐步与计划生育脱钩,使中央决策平稳落地;尽快着手实行生育奖励制度等。
第四,司法层面的正当性修复。在司法层面,应当坚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育权利。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应杜绝司法潜规则,依法将计生行政案件纳入受案范围;坚持依法独立审判和中立裁判,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杜绝地方政府干预计生行政案件审判,也避免因自身计生工作受制于地方而影响审判的公正和权威。
[1]徐国栋.论作为变色龙的生育的法律性质[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1).
[2]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中国人口,2011,(1).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4]裴倜,王冲.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及其规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5]孙秀民.简论西方人口与政治关系的思想[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6).
[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翟翌.论计划生育权利义务的双重属性——以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为背景[J].法商研究,2012,(6).
[8]于晓琪.对我国立法中生育权主体的评价与思考[J].人权,2003,(3).
[9]张翔.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J].法学论坛,2005,(1).
[10]武秀英.对生育权的法理阐释[J].山东社会科学,2004,(1).
[11]张勇.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哲学基础[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7).
[12]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J].法学家,2008,(1).
[13]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J].法学家,2011,(2).
[14]张春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65.
[责任编辑:朱磊]
1002-462X(2016)03-0064-07
2015-12-08
吴欢(1986—),男,讲师,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D90
A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