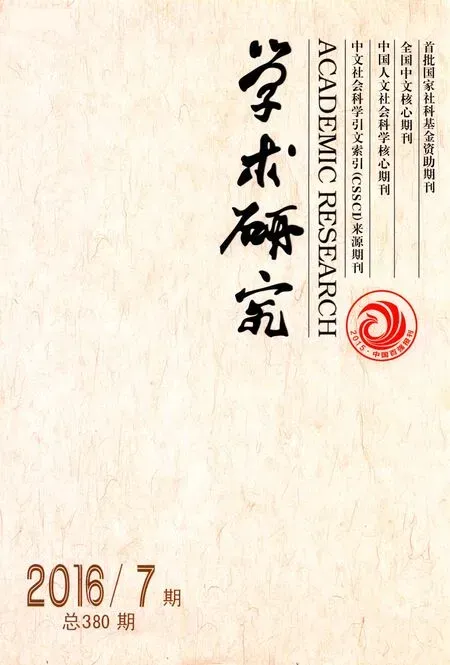近代国家权力在地域社会的建构
——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地方纸币变迁为中心*
陈海忠
近代国家权力在地域社会的建构
——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地方纸币变迁为中心*
陈海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家权力一方面自上而下向基层渗透,一方面自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张,以期实现国家对社会的 “全域”控制。在汕头通商口岸,国家权力先是在1925年迫使汕头总商会废除由银庄控制的七兑票,改发大洋本位的保证纸币,中央银行藉此得以不受地方银业的桎梏,进入市面交易各业务领域。随后在1933年金融风潮中,保证纸币陷入困境,广东省政府藉机以救济为名,最终取缔保证纸币,广东省银行纸币取而代之成为市面的通用纸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在地方金融领域的建构。这一案例显示了民国国家权力在经济社会领域建构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国家权力地域社会汕头纸币
从国家权力建构的角度看,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直是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家权力一方面自上而下向基层渗透,一方面自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张,以期实现国家对社会的 “全域”控制。学界对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的研究较多,①如杜赞奇、刘昶、王奇生等分别研究了20世纪华北乡村社会、战前江苏区乡行政,讨论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深化及其对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参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昶:《1900—1940年华北的乡村政治》,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留美历史学者学术文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较少关注国家权力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张的问题。本文拟从地方金融领域的视角,考察国家权力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张的历史过程,以期更加立体地理解近代国家权力建构问题。
汕头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入海口,1860年开埠之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华南地区第二大商港、韩江流域经济与金融枢纽。[1]民国时期,汕头先是经历了民初动荡与陈炯明割据时期,1925年东征后,广州国民政府在汕头建立地方政权,但直至1936年两广事变结束,汕头才真正被纳入南京政府实际管辖范围。在此期间,汕头地方金融发生多次变革,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在纸币问题上进行过反复博弈,以此为切入点将有助于对主题的理解。本文因此也主要运用民国汕头档案与报刊资料进行讨论。
一、民初汕头 “七兑票”的流通与调控
近代中国各地域、各行业衡制不同,①如广州使用司马平,汕头使用直平,直平每1000两比司马平少3两。参阅 《广东经济年鉴》,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0年,第6页。且白银成色高低不一,市面上逐渐产生无实银对应的虚银两作为计算单位,如官方法定的库平、漕平与关平,以及上海规元、汉口洋例、天津行化等地域性虚银两。[2]汕头的虚银两为七兑银,一元可兑银约七钱。私人银庄除了以七兑银为记账、计算单位外,②近代汕头把经营钱银找换、国内外汇兑的钱庄、银号等统称为银庄,大银庄叫汇兑庄,小银庄叫收找店。大约在1880年开始发行以七兑银为本位的七兑票。[3]
初始,银庄只是把七兑票作为同行间存欠、大宗贸易交收的凭证;后来七兑票票面金额小额化,使用方便,且银庄信用卓著,遂逐渐成为地方通用纸币。③把七兑票认定为纸币的根据是北洋政府 《取缔纸币条例》,其第一条规定 “凡印刷及缮写之纸票,书目成整,不载支取人姓名及支付日期,凭票兑换银两、银元、铜元、制钱者,本条例概认为纸币”。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金融 (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1-92页。七兑票多数为传统银票长方形样式。票面印制银庄名号,中间写 “凭票向本庄取直平七兑银若干元正”。用于日常流通、支付华侨批款的主要是1元、2元、5元、10元等小额七兑票,25元、50元、100元等则主要用于大宗交易。[4]也有的银庄仿照外国钞票样式印制七兑票,如 “一家银行 (庄)发行在伦敦制印的钞票,这种钞票采用最精心制作的式样,白线图版,图样十分细致,使最高明的伪造者也无所施其伎”。[5]
关于七兑票的使用、流通情况,1901年潮海关税务司报告说:“在汕头,人们很乐意接受这些钞票,地区内有几个城镇把它们与硬币等同使用。”[6]成书于1925年的 《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则明确地说汕头市面 “买卖交换概用各银庄发行之七兑银票为代替物。凡本市商店之买卖、佣资、屋资、保险费等之支给,全用七兑银”。[7]但纸币发行额向来是银庄讳莫如深的秘密,外界难悉其详,目前只能根据1921年各银庄上报给潮梅筹饷局的数字推测总体的规模。其时发行七兑票的有23家汇兑庄、54家收找店,总共244.7万元,平均每家汇兑庄约10万元,收找店0.7万元,[8]这应该只是最保守的数字。
由于地方政府从未干预,七兑票的发行与传统银票一样无需准备金,银庄凭股东财力与信用均可自由印发,[9]初期滥发的情况在所难免。1910年,怡和、德万昌两大银庄就因滥发七兑票相继倒闭,激起金融恐慌。[10]汕头汇兑公所在处理怡和、德万昌倒闭案后,逐步建立严格行规,杜绝银庄滥发,维持七兑票稳定,并以此牢牢掌控住地方金融。
汇兑公所是近代汕头最有势力的行会,萧冠英称其 “实为汕商领袖,即汕头市商会,亦以该所为转移”。[11]公所成立于1895年,由20多家老牌大银庄组成,[12]“一方类于证券交易所,一方类于票据交换所”。[13]汇兑公所实行会员制,且 “倘非会员全体之同意,虽有充分之信用及资本,不易参加。例如台湾银行屡欲参加,皆为否决,其团结性之强固可见矣。盖一以保障该所交易信用之确固,一以防制同业纸币之滥发。汕头纸币得于自由竞争之中,而仍有所维持者,实赖此自动之集会机关也”。[14]
汇兑公所调控七兑票的主要方法有两种:其一,换纸。换纸是公所同行间的一种结算方法,目的在于相互制衡,防止滥发纸币。每日收付终结后,银庄把收到的其他银庄七兑票提交到汇兑公所,换回自家的七兑票。如果某银庄提交的纸币数额少于同行收存的该庄纸币,则该银庄为欠,需以等额现银换回多出的纸币或向同行支付利息;反之则可收回现银或利息。对换纸的效果,民国 《潮州志》称:“苟该庄号每在欠中,又每贴人利息,其信誉自见低落。此法颇为完善,足杜银庄贪图利息滥发纸票之弊。”[15]其二,扯息,即决定同行间存欠利率。汇兑公所每月28日集会,根据国内外各埠汇票及当地市场行情,议定下一月银庄同行间存欠利率。当换纸成为行规之后,利率的变化就可以制约七兑票发行量与价格。如利率低,银庄可以多发七兑票;反之,则少发,以免支付过多的利息。
汇兑公所还与银业公所联手排挤小银庄与中外新式银行。1920年汇兑公所与银业公所联合起来,把两公所会员银庄称为 “银行”,其他银庄、商号、中外银行统称为 “杂行”,杂行发行的纸币为 “杂纸”。汇兑、银业两公所议定共同抵制杂纸:“凡已入汇兑银业两公所之各庄发行纸票,固应流通,互相授受。而其他未经入会团体以外之各号纸票,概属杂行,无从稽考。无论本埠及外埠,一律谢绝授受。如遇店前与会外交易授受者,亦须自向直接换返,不得互交同业。”[16]
通过相互制约的行规,汕头汇兑公所能够调剂七兑票数与市面需求保持平衡,维持七兑票价格不致大起大落。相反,银元价格常受国际银价波动以及市面供需状况而动荡,稳定性反不如七兑票,更加凸显七兑票的坚挺。此外,汇兑、银业两公所联合排挤杂行,不但限制了小银庄的发展,也使台湾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等在地方金融市场难以有所作为。①张和平:《纸币珍品 “中法实业银行”钞票》,《收藏》2000年第1期;邓邦杰:《汕头金融业概况》,《银行周报》第19卷第23期,1935年6月18日。例如1929年张公略称:“台湾银行虽曾发行纸币,而汕头各银业家,当日收入若干,即晚向其兑现;各行号款项来往,亦绝少与之接洽;故彼在汕头金融界,卒不能占大势力。”[17]
由此,比较于其他商埠经济命脉多为外资银行掌握的情况,民初 “汕头市金融界的权柄,仍很完整的操在本国商人之手”,[18]中外各新式银行 “完全失却商业银行辅助工商业的意义矣”。[19]这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殊属少见,彰显了在国家权力进入地方金融领域之前,汕头银业商人的强势。
二、1925年废两改元与国家权力的进入
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两次东征,驱逐占据潮梅地区的陈炯明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人认为要真正统一,“财政的整理是一项非常紧要而不容稍缓的政策”。[20]4月,东征军总司令部任命军需处长俞飞鹏为建国粤军潮梅海陆丰各属财政总局局长,总揽潮梅各属财政。随后,在东征军压力下,汕头取缔七兑票,实行废两改元,为革命政府中央银行进入汕头金融领域打开通道。
东征军在汕头废两改元的契机是 “纸贵银贱”。1924至1925年间,因国际银价连续低跌,汕头七兑票价格高企,大洋兑七兑票不断贬值,“至 (民国)十三年以后竟告削水,每元连本有重量不能保持,降至与七兑票同等行使,甚而低至六钱前后,七兑票一元反比大洋多出角余”,[21]此即 “纸贵银贱”。
“纸贵银贱”首先影响行使大洋的潮梅内地各县民生。潮梅各县百货多自汕头输入,货物以七兑银定价,货款按大洋与七兑银比值支付。七兑票价格高昂,各县物价遂无形上涨。1925年5月大埔县商会函称:“目前潮汕金融紊乱,龙银价日形低落,以致百物腾贵,生计艰难。推溯原因,皆由少数银业家用其无限制、无硬币之七兑纸为本位,操纵居奇,生出此种结果。”[22]
“纸贵银贱”还影响汕头与上海、香港货币汇率。如 “(汕头)前此常为七三七四以上之沪币港币,至此乃降而仅值直平之六钱,至毫洋价格之低落,更不堪问,目前直票 (即七兑票)一元可找得毫洋一元五角有奇”,[23]这使从上海运银到汕头的上海潮帮商人无利可图。为维护银业利益,1925年初上海潮州会馆设立 “汕市国币维持会”,多次要求汕头总商会维持大洋价格。3月18日,旅沪潮商发起组织潮汕股份有限银行,试图绕过七兑票,直接在沪汕贸易中实行以大洋为本位。[24]上海总商会、上海钱业公会也相继对汕头总商会施加压力。[25]大埔县商会、汕头公益社、旅沪潮州劳动会、上海押当公所潮州旅沪同人等纷纷痛陈汕头纸贵银贱的危害,甚而把七兑票称之为 “假币”。[26]长期在汕头无法发挥影响力的中国银行乘势而为,积极响应,呼吁政府、商界废除汕头七兑票,采用大洋本位。[27]
纸贵银贱对行使毫洋的东征军也大为不利。况且,如不破除汇兑公所对七兑票的操控,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设立后将来也难免会与台湾银行、中国银行一样被边缘化。于是,建国粤军潮梅海陆丰各属财政总局很快与上海潮州会馆、潮梅内地商人团体联合起来,痛斥汕头汇兑公所恶意操控七兑票,要求汕头总商会废除七兑票。[28]经财政总局多次严令,汕头总商会被迫于5月21日召开金融大会。在各官方机构及旅港潮州八邑会馆、上海潮州会馆等团体的见证下,潮梅各属及各行商代表80多人表决通过,自6 月1日起废除七兑票,接受中国银行汕头分行提议,改以大洋为本位。[29]上海潮州会馆随即宣布 “六月一日起,上海汇汕汇票一律废除七一半两数,以后汇票到汕概收大洋银元”。[30]
在汕头废除七兑票后,广州国民政府加速设立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进程,发行大洋本位纸币,抢占金融市场。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作为广东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1926年1月20日,中央银行汕头分行开业,初期发行毫洋本位的纸币 (即中央纸),作为地方缴纳各种税捐的法定货币。不久又遵循潮梅地区习惯另外发行以大洋为本位的大洋地名券,该券在纸币票面加盖地名,表示发行地、流通范围。至1926年12月13日,共发行大洋地名券15万元,分1元、5元、10元3种,潮梅各地凡属正杂各项收入应收大洋者,均得以大洋券征纳,原日发行的毫券仍准通行不悖。[31]
在汕头发行纸币只是国家权力进入金融领域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是要打破汇兑公所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囿于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中央银行远未具有在汕头挑战汇兑公所的实力;但在军政力量的支持下,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获得了其他中外银行未能获得的专利——汇兑公所会员权利。汇兑公所会员最重要的两项权利是:一是会员可以自由进入汇兑公所进行港汇、申汇等汇票买卖,非会员庄号 (杂行)则须购买入场券,入场券有效期1年,不得转借,中国银行、台湾银行这些银行亦不得例外。二是会员与杂行之间来往款项时,汇兑公所向杂行收取千分之一的手续费,但同业交收则免费。[32]
1926年1月,新设立的中央银行汕头分行成功打破汇兑公所延续经年的营业惯例,成为唯一一所非公所会员而享受会员权利的新式银行。[33]此举意味着国家银行在市场交易中已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不用受地方银业的桎梏,自由进入一般的款项存放、贷款与汇兑等业务领域。这是国民政府国家权力在汕头地方金融领域建构的开端,但由于政局动荡、地方银业强烈抵制,其过程一波三折。
三、保证纸币的存废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在金融大会上,建国粤军潮梅海陆丰各属财政总局宣布今后银庄发行纸币,必须有现金或不动产或同业五家以上之联保为保证。[34]因为有所保证,故称之为 “保证纸币”。随后 《保证纸币细则》经东征军总司令部核准施行,[35]汕头总商会在1925年8月组织 “银业保证审查会”,办理保证纸币事务。[36]至1929年,已有37家银庄以不动产为抵押发行保证纸币。[37]
中央银行虽然已经进入汕头,但1927年后广东政局动荡,中央银行为应付军政所需,“遂不得不多发纸币,以致准备不足,信用坠落,挤兑停兑风潮一岁数见。”[38]在汕头市面上,中央银行大洋地名券迭遭低折,除用以缴纳税捐外,流通不畅。银业公所甚至把中央纸作为货品开盘买卖,每日价格涨落无定。1928年广东省政府还专门为此训令 “银市不得开盘,市上不得低折,违者军法从事”。[39]到1929年4月,汕头市政厅还奉令布告,要求市民不得歧视拒用中央银行纸币,[40]足见其市场地位之脆弱。
相反,银庄的保证纸币却获得类似昔日七兑票的地位,在市面行使畅通无阻,而且还与大洋地名券一样可用以缴纳税捐。[41]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张智因此指责:“汕头商民常有拒收敝处发行之大洋纸币情事,调查总由于本地各银庄发行大洋纸币起见,故对于敝处大洋纸币,有歧视之心”,并拟具取缔保证纸币办法。[42]该办法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支持,1928年7月省政府借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之机,训令财政厅、汕头市政厅:(1)市政厅、中央银行与总商会组织保证纸币审查会;(2)银庄除以不动产保证外,另需缴纳二成现银为保证金,由中央银行保管;(3)按年3%税率开征纸币税;(4)保证纸币每张面额不能少于10元。[43]这一方案与其说是取缔保证纸币,不如说是维持广东中央银行计划。因为按此训令执行,中央银行将可获得数10万元现银存款,政府每年新增税款约10万元,市面一般交易只能使用中央银行纸币或硬币 (面额10元以上纸币一般用以大额交易)。
汕头总商会、汇兑银业两公所遂联合起来,一方面坚决抵制,另一方面用联保制度,强化保证纸币信用。1929年9月17日,汇兑公所成立 “保证纸币联保会”,宣布如有银庄倒闭,倒闭银庄的纸币由联保会负责兑换、收回;同时参照七兑票换纸制度,各银庄每逢星期三、星期六轮流互换各自收到的保证纸币,以防纸币滥发。[44]到1931年,陈济棠稳固了他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力谋扩充金融势力,筹划改组广东中央银行为广东省银行。①参见 [美]余光炎、陈福霖主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此背景下,汕头市政府方得以宣布成立保证纸币审查会,但附设于市商会内。[45]此时,因联保制度强化了保证纸币的信用,加之市面资金充足,1932年发行保证纸币的银庄已增至72家,总额405.83万元,其中 “联保会”48家会员发行332.11万元,占全市保证纸币总额的81.8%。[46]
保证纸币的好景随后发生逆转。1932年后,因南洋经济衰败,潮梅土产滞销,各地侨汇锐减。②1930—1934年由南洋汇入汕头的侨汇分别为:1930年1.1亿元;1931年9420万元;1932年7070万元;1933 年6280万元;1934年4700万元。详见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新编第3册,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本,2005年,第1416页;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7集),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56页。汕头市面随之银根紧绌,借款息价高企;[47]地价惨跌更直接动摇了以不动产为保证的保证纸币信用。[48]随后发生的金融风潮,使广东省银行得以全面接管汕头地方金融。
1933年5月,第一次金融风潮爆发。5月7、9日,潮阳帮两大银庄宝盛庄与阜安庄因周转不灵相继倒闭,两庄合共发行纸币17万余元,街前欠款70余万元。[49]由此引发连锁反应,5月间全市倒闭或歇业的银庄8家、其他商号14家,倒欠街前数目200多万元。[50]到了8、9月,又爆发第二次风潮,倒闭的商号、银庄遗下债务200余万元。[51]其中源大庄与成茂合记庄倒闭对市面的冲击最大。源大庄是潮阳帮最大银庄,曾被誉为 “握商界金融枢纽有年”,东家即是汕头市商会主席陈道南。成茂合记庄是源大庄总经理周毓生所开设,但市面均认为东家也是陈道南。[52]中秋节前夕,第三次风潮接踵而来。澄海帮三家大银庄光发、鸿发盛、智发相继歇业,倒欠街前债务100余万元。受其影响,澄海帮的嘉发、永发、乾兴昌及其联号广成兴也随之倒闭。其时 《申报》载:“汕头以金融之奇紧,及政局之不靖,已有银行15家及若干开设已久之商店宣告倒闭,其总数达700万元,在最近48小时内,又有银行4家及某煤油公司宣告破产,停止营业,其他商店亦多有倒闭之虞。”[53]
数月之间汕头历经三次金融风潮,本地最大的银庄相继倒闭,遗下无法兑现的保证纸币100余万元。市商会只得宣布暂停兑现,由商会盖章暂行流通,保证纸币随即贬值,每千元被低折五六十元,对香港每汇千元贴水涨至235元。[54]一些银庄如泰安庄、健源庄等开始自动回收自家纸币以规避风险。[55]一时之间,市面通货紧缩,“市面商务之冷淡为开埠以来所罕见,各大公司门可罗雀,大减价旗帜飘扬于各店门口。”[56]
藉此保证纸币陷入困境之时,广东省银行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得以乘机全面扩张。5月,汕头分行增发大洋地名券100万元抢占市场,同时运出大批毫洋至广州,加剧汕头银荒,打击银庄纸币,[57]又明确提出 “敝处大洋地名券应藉此时,取而代之”。[58]7、8月间,广东省银行指令汕头分行要乘机力筹妥善办法使各银庄所发出纸票悉数收回,免遗后患。9月6日,推出汕头商人领用大洋地名券方案,准予各银庄以50%不动产为保证加25%现金与25%保证纸币换领大洋地名券。[59]9月18日,汕头分行开始办理产业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又推出一批大洋地名券。[60]10月间,省财政厅与广东省银行商议后,同意汕头市商会 《救济汕市金融意见书》的多项要求,[61]前提是1934年3月底以前全部收回保证纸币及各项临时票据,保证纸币印章截角缴存汕头分行。[62]11月22日,广东省财政厅召开全省经济会议。此次会议批准广州市商会提出的商人以不动产为抵押发行商库证办法。因商库证不能兑现大洋,银庄可免受挤兑之苦,因而汕头市商会称之为 “绝境中一线生机”,[63]遂向省财政厅申请发行汕头市商库证。省政府最终同意汕头市商会发行商库证,前提条件仍然是必须立即收回各种临时纸票及在商库证发行6个月后收回全部保证纸币。[64]此时,汕头银业商人已经完全无力维持保证纸币,只得全盘接受。
1934年7月23日,汕头第一批商库证发行,至1934年12月累计发出794.61万元,缓解了市面金融状况。[65]遵照省政府训令,各银庄也渐次收回保证纸币或把保证纸币转换为商库证。到1936年2月1日,即省政府布告截止行使之日,汕头全市自动缴销保证纸币8.7万元,已收回并转领商库证的有188.5万元,虽未收回但已办理转领商库证的有11.5万元,[66]市面仅余20多万元尚待收回。[67]至此,保证纸币与七兑票一样成为了历史。作为过渡的商库证因不能兑现,且面额仅100元、200元两种,多作为大宗交易之用。广东省银行的大洋地名券终于能够在汕头日常交易、流通中大行其道。
四、余论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陈济棠借机令广东省银行增发纸币大肆收购白银。仅1936年,汕头分行就收购大洋900多万元、毫洋150万元,该行纸币终于成为潮梅地区通用纸币;汕头分行营业随之大有起色,当年纯收益居全省各分行之最。[68]白银尽归国库,银业更加丧失赖以运转的经济条件,汕头汇兑庄从此风光不再。陈济棠虽然统一了广东金融市场,但是很快因 “两广事变”下台,广东省归政中央政府。1937年底,财政部长宋子文完成广东币制改革,用全国通用法币取缔广东省银行纸币,广东省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汕头与广东全省进入法币时代,国家权力在地方经济领域的建构才算完成。
近代汕头地方纸币变迁的历史过程,既是近代国家权力不断向地方社会延伸的结果,也是国家权力向经济社会领域渐次扩张的表现。其间,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双方围绕经济利益与控制权的互动,既有激烈冲突,也有妥协、相互调适的过程。货币统一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区区一个汕头,其货币统一的过程就已经如此曲折,足以彰显基层社会中国民党统治的脆弱性以及民国国家权力在经济社会领域建构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国民政府名义上实现政治统一,但国家权力在地方与社会各领域的建构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这一过程将会更加曲折而艰巨。
[1][11][13][35]谢雪影:《潮梅现象》,汕头:时事通讯社,1935年,第49、49、49、63-64页。
[2]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54页。
[3]《银庄广告》,《岭东日报》1902年7月15日。
[4][15][21][民国]《潮州志》新编第3册,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第1353、1354、1343页。
[5][6]甘博:《潮海关十年报告 (1892—1901)》,《潮海关史料汇编》,汕头,1988年,第58、58页。
[7][9][14][16][32]萧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广州:培英图书印务公司,1925年,第63、60、60、60、50页。
[8]马育航:《汕头近况之一斑》商业篇,汕头,1921年,第1-11页。
[10]《汕头商会请款续纪》,《申报》1910年10月18日。
[12]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34页。
[17][18]张公略:《新商人》,《潮梅商会联合会半月刊》1929年第1期。
[19]邓邦杰:《汕头金融业概况》,《银行周报》1935年第23期。
[2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 (十四年十月本部特派员大会政治报告)》,广州,单行本,1925年,第7页。
[22]《潮州会馆汕市国币维持会来往函》,《申报》1925年5月19日。
[23]《潮梅经济界前途之危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5日第3版。
[24]《旅沪潮商筹议组织潮汕银行》,《银行月刊》1925年第3期。
[25]《请研究汕头国币贬值事致银钱两公会函 (4月30日)》,《总商会月报》1925年第5期;《汕头金融争执之总商会意见》,《申报》1925年5月14日。
[26]《旅沪潮州劳动会、上海押当公所潮州旅沪同人致潮州会馆汕市国币维持会函》,《申报》1925年5月14日;《潮州会馆汕市国币维持会来往函》,《申报》1925年5月19日。
[27]郑铁如:《论汕市急宜废弃七兑纸采用大洋本位》,《申报》1925年5月16-21日。
[28]《汕头取缔纸币与维持银毫》,《银行月刊》1925年第5期。
[29]《汕头金融大会纪》,《申报》1925年5月31日;《七兑票之废止与善后》,《银行月刊》1925年第6期。
[30]《上海潮州会馆公函 (1925年5月30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269。
[31]广东省银行:《广东省银行二十五年份营业报告书》,广州,1937年,第37页。
[33]《潮汕要讯片片录》,《华字日报》1926年1月23日。
[34]《七兑票之废止与善后》,《银行月刊》1925年第6期。
[36]《汕头总商会会议录》(第20次特别会),1925年8月7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269。
[37]《汕头金融业之调查》,《潮梅商会联合会半月刊》1929年第1期。
[38]《粤金融中枢之广东省银行》,《金融物价月刊》1936年第11期。
[39]《令各税捐承商一体知照中行一百元纸币自八月十日起一律准作现金收受由 (1928年9月15日)》,《汕头市政公报》1928年第37期。
[40]《布告市民一体遵照行使中央纸币不得歧视拒用由 (1929年4月2日)》,《汕头市政公报》1929年第44期。
[41]《汕头市政厅公函 (1929年10月5日)》,《汕头市政公报》1929年第50期。
[42]《函送取缔银庄发行纸币办法请会议见复由 (1928年7月23日)》,《汕头市政公报》1928年第36期。
[43]《训令市商会派员出席会商成立保证纸币审查机关由 (1930年7月5日)》,《汕头市政公报》1930年第59/60期。
[44]《汕头银业界维持保证纸币办法》,《华字日报》1929年9月19日。
[45]《汕设审查保证纸币委员会》,《华字日报》1931年4月30日。
[46]丘斌存:《广东币制与金融》,上海:新时代出版社,1941年,第120页。
[47]《汕头对南洋贸易概况》,《中行月刊》1933年第3期。
[48][56]《汕头金融又起恐慌》,《银行周刊》1933年第30期。
[49]《汕头市汇兑公会公函 (1933年5月7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765;《汕头市汇兑公会公函 (1933年5月10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89。
[50]刘孔贵:《汕头金融风潮与补救办法之商榷》,《银行周报》1933年第22期。
[51]《1日汕头电》,《申报》1933年10月2日。
[52]《潮汕经济又起恐慌》,《银行周报》1933年第40期。
[53]《路透社12月23日电》,《申报》1933年12月24日。
[54]《汕头钱业一年来之危象》,《中行月刊》1934年第1/2期。
[55]《泰安庄投词 (1934年5月7日)、健源庄投词 (1934年6月 2日)》,汕头市档案馆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689。
[57]《23日汕头电》,《申报》1933年5月24日。
[58]《广东省银行汕头分行公函 (1933年8月21日)》,广东省档案馆民国档案41-3-3368。
[59]《广东省银行公函 (1933年9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民国档案41-3-3368。
[60]《广东省银行汕头分行公函 (1933年10月23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93。
[61]《财政厅电商界派代表共谋挽救》,《潮声月刊》1933年第7期。
[62]《汕头市土地局公函 (第27号)》,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85。
[63]《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公署训令 (政字第8399号)》,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99。
[64]《汕头市商会会函 (1934年5月4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100。
[65]《广东省汕头市货币种类调查表 (1934年12月)》,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12-9-230。
[66]《汕头禁用保证纸币》,《中行月刊》1936年第1/2期。
[67]《潮汕金融要闻近志》,《华字日报》1936年2月17日第6版。
[68]《广东省银行民国二十五年度营业报告》,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下篇),1937年,第V106、V130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K262;262.9
A
1000-7326(2016)07-0138-07
*本文系2014年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明清以来潮汕商人与地方社会:以慈善活动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陈海忠,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广东潮州,52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