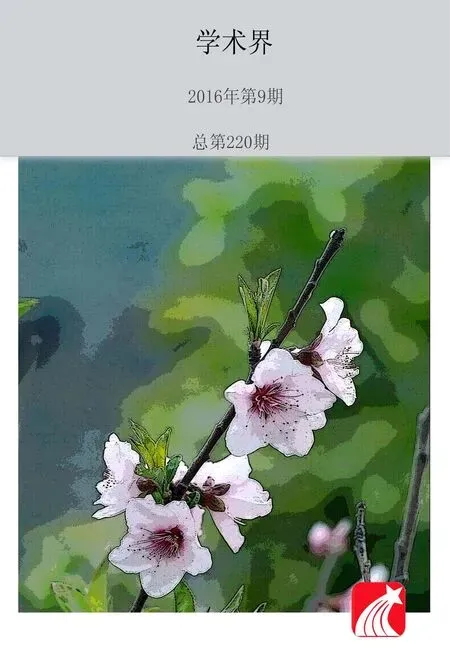文体学视域下的吕本中“活法”论〔*〕
○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文体学视域下的吕本中“活法”论〔*〕
○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710119)
吕本中“活法论”与宋代文体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宋代辨体风气兴盛,“辨体和破体”这一文体学理论范畴中的矛盾体,是一种既对立冲突又统一融洽的辩证关系,这与“活法”论中的“有法和无法”“活法和死法”之辩证关系有着极为相似的理论渊源。尤其是文体学上“定体与无定体”与活法论中的“定法与不定法”,以及“变而不失其正”这一文体通变观,都可以说是“活法论”的姊妹或别称了。吕本中的文体学思想直接受到黄庭坚辨体论的启发和影响,这与其活法论源于黄庭坚是相通的,而黄庭坚的法度论和文体论在理论表述和体系构建上,亦常常是交织融合,不分彼此的。此外,吕本中作为道学家,其儒学思想继承谢良佐并影响朱熹,而其文体观和活法论也与二者密不可分。宋人及明清学者在文学批评中往往“法”与“体”相提并论,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不可分离,足见辨体论和活法论在学理上的血脉相连。
文体学;活法论;吕本中;黄庭坚;谢良佐;朱熹
吕本中的“活法论”在宋代诗学理论和中国古代诗法理论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引起了现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相关成果颇为丰硕,如顾易生、张少康、莫砺锋、祝尚书、束景南、曾明、吕肖奂等都有所论述,尤其是“活法”论的理论来源上更成为上述学者探讨的焦点,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可研究空间已被挖掘殆尽,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点似乎被忽略和遗忘了,那就是“活法”论的文体学渊源。宋代辨体风气兴盛,辨体和破体这一文体学理论范畴中的矛盾体,是一种对立统一和冲突融洽的辩证关系,这与“活法”论中的定法与不定法、无法和有法、活法和死法之辩证关系有相通相连的理论血缘,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不可分离。尤其是文体学上定体与变体之矛盾运动的文体发展观上,以及“变而不失其正”这一文体通变观,都可以说是“活法论”的姊妹或别称了。我们说活法论与文体学有极深的渊源,是有学理根据和文献基础为证的,一方面,宋人及其后代学者往往“法”与“体”相提并论,可见二者在学术上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吕本中的文体学思想直接受到黄庭坚文体学观念的启发和影响,这与其活法论源于黄庭坚是相通的,而黄庭坚的法度论和文体论在理论表述和体系构建上,亦常常是交织融合,不分彼此的。此外,吕本中作为道学家,其儒学思想继承谢良佐并影响朱熹,而其文体观和活法论也与二者密不可分。吕本中的辨体理论是宋代辨体理论批评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从“辨体论”的角度来观照“活法论”当会有很多学术创获,以下详而论之。
一、“活法论”理论渊源研究述评及其文体学阐释
关于吕本中的活法论的理论来源研究,学者大多围绕在苏轼、黄庭坚的诸如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上,以及禅宗的定法与不定法上等,很少有学者注意到活法论与宋代文体学及其辨体与破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将其最具代表性的两则活法论文献录于下,以见大概。吕本中《夏均父集序》:“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1〕《江西诗社宗派图序》:“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在,万变不穷。”〔2〕
首先,活法论源流研究现状述评。对于吕本中的活法论的理论渊源,学界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由于吕本中活法论代表文献诸如《夏均父集序》《江西诗社宗派图序》《童蒙诗训》中明确提到黄庭坚和苏轼,故而现当代学者和批评史家大多都把其理论源头归于苏、黄,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追溯至王安石、梅尧臣、欧阳修、杜牧、韩愈等。关于苏、黄,如顾易生等云:“这一理论源于黄庭坚,而又融合了苏轼的理论。苏轼论文,贵在‘随物赋形’,所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义甚高,近于天才之不拘成法。黄庭坚矜言法度,强调准绳,又偏于有定法。吕本中后出,融合二说,以构成他的‘活法’理论的基点。”〔3〕“吕居仁的‘活法’和‘悟入’之说,是对黄庭坚诗论的继承和发展,他对山谷的创新意识和诗律句法,都是推崇备至的。”〔4〕张少康云:“所以吕本中的‘活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要把苏轼和黄庭坚在法度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互相融合起来……既肯定黄的法度,又要求参考苏的不拘法度,这是吕本中‘活法’论的主要特点。”〔5〕再如祝尚书云:“序文可知,吕本中视黄庭坚是诗歌‘活法’的样板,而这里他又视苏轼为文章‘活法’的楷模。”〔6〕
或由苏轼、黄庭坚上溯至欧阳修、王安石、胡宿及至杜牧、韩愈等,如曾明云:“欧阳修曾经论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不可拘以常格’……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或时放肆以自舒,勿为一体,则尽善也。”“所以,苏轼模仿韩愈,应该是模仿其不可拘以常格的风格,而这,正是诗学活法说的重要理念和追求。”〔7〕吕肖奂则认为“法度”论始于王安石,吕本中继之,然后再论述苏轼、黄庭坚在法度和活法这一矛盾体之间的调和与周旋,如吕肖奂云:“宋诗讲‘法度’,始于王安石。……吕本中《童蒙训》卷下也有相似的记录。”〔8〕杜牧也成为这一活法论链条上的一环,如曾明云:“杜牧《注孙子序》:‘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9〕
第二,在活法论的理论内涵和范畴命题渊源上,则大多追溯到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及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观念上,或者与苏、黄书画法度论联系起来。如胡建次云:“北宋前期,梅尧臣最早倡导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寓含活法的思想。陈师道《后山诗话》:……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苏轼《东坡诗话》: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10〕或者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观点,如莫砺锋《再论“夺胎换骨”说的首创者》一文引用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十云:“晁、黄得夺胎换骨之活法于此乎。”以及杨万里《诚斋诗话》云:“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11〕他还认为“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有一点共同的精神,即:在学习前人创作经验时要有所发展变化。……‘以故’只是手段,‘为新’才是目的。”〔12〕张少康亦云:“苏轼讲的‘无法之法’是崇尚自然天成,而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吕本中所说的‘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的‘活法’,则是在以‘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为中心的江西诗法基础上所说的‘活法’,是学习‘豫章黄公’‘左规右矩’而至‘变化不测’。”〔13〕
有学者还注意到吕本中活法论与苏轼、黄庭坚书法理论中法度论的密切关系,如吕肖奂《从“法度”到“活法”》一文引用苏轼评王衍书云:“其自得于规矩之外,盖真是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规之也。”〔14〕束景南称黄庭坚首先在书法领域里提出了“无法之法”,如在《答王云子飞》中称“鄙书无法”,《书家弟幼安作草后》亦说:“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在《论书》中,他批评学书拘于法度,而称赞右军的不为法缚,即‘皆不为法度病其风神’。”在《题颜鲁公帖》中说:“回视欧、虞、禇、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15〕
第三,在哲学思想的本体论源头上,学者多认为吕本中活法论源于禅宗“心法”。如束景南认为黄庭坚就是“用佛家这种法空观念来总结苏东坡书法艺术上的活法境界的”,称“山谷的‘心法’来自禅宗。禅宗说的心心相传的‘心法’就是一种有法无法,有定法无定法,有功无功的活法。”〔16〕祝尚书云:“据研究,吕本中的‘活法’论源于禅宗,云门宗缘密禅师就讨论过‘死句’‘活句’的问题,大意是意在言内为死句,意在言外方是活句。”〔17〕吕肖奂云:“苏轼《东坡志林》卷三《信道智法说》:‘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凝;以智先法,则法活。道凝而法活,虽度世可也。’”〔18〕
第四,近年来,有学者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探寻活法论的渊源及其关系,但大多看到某一个文体学侧面与活法的关系,未能从整个宋代文体学之辨体理论体系及其整个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演变中来观照。如曾明从苏轼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等的破体现象中考察:“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新体’更加成熟……综合考论,苏轼实为“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19〕周芸从“破体”的修辞角度出发来研究活法:“破体为文所遵循的是一种用法而又超法、有法而又无定法的修辞原则,该原则与唐宋时代兴起的‘活法’具有一种深层契合性。”〔20〕王晓骊则从宋词的“破体”现象中看待活法理论:“宋词‘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等‘破体’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活法’思想在词学领域渗透的结果。”〔21〕
其次,“活法论”的文体学阐释。中国古代诗法论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活法论与辨体论之间的关系尤为微妙,难分彼此。大体来说,活法论应是辨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都属于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文学辩证观和文体通变论。用辨体尊体和破体变体来解释活法论更容易让人理解,以及从中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比来看,辨体论的理论体系及其内涵范围要大于活法论,或者说在学诗作诗时辨体论要重于和先于活法论的。如顾易生等称吕本中“其所称‘活法’,重点是关于用字造句方面的问题”〔22〕。吴承学先生亦云:“‘先体制而后工拙’,即考察是否符合文体的规范,然后再考虑艺术语言、表现技巧等方面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种带普遍性的批评原则。”〔23〕
宋代辨体批评兴盛并蔚成风气,与活法论的提出和争鸣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同一批学人,其中黄庭坚、谢良佐和朱熹、吕本中之间的活法论与辨体观交错承传,互相影响,而吕本中、黄庭坚、谢良佐和朱熹等人相关文论文献中“文体”和“法度”的同时并提,更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活法论”与“辨体论”的密不可分。
辨体和破体,或者说尊体与变体,是中国古代辨体理论批评中一组对立的概念范畴,二者是遵守与打破、继承与创新、通与变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正如吴承学《辨体与破体》云:“宋代以后直到近代,文学批评和创作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倾向:辨体和破体。前者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辨明和严守各种文体体制,反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创作手法;后者则大胆地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使各种文体互相融合。”〔24〕这里的辨体尊体观,是指每一种文体在发展演变中都形成了恒定不变的体制规范,也叫做大体和定体;对应于吕本中活法论来说,就是学诗作诗的“规矩”和“定法”,这种体制规矩要求作者在创作时必须严格遵守。但文学是发展的,而文体的发展创新是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文体发展的历史。所以这就要打破文体的某种规矩和规范,进行文体的革新,但是这种变化和变体是有一定限度的,是继承中有创新,即吕本中《夏均父集序》中的“活法”论所谓“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规矩备”和“亦不背于规矩”是辨体尊体,“出于规矩之外”和“变化不测”是破体变体,结合起来就是一种辩证通达的文体通变观,大多古代文体学者的辨体观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宋代与吕本中关系密切的学者如黄庭坚、谢良佐、朱熹等的法度论和辨体论都秉持这种文体辩证观。
二、吕本中的文体学思想及其与黄庭坚、谢良佐、朱熹的关系
宋代“体制为先”的辨体尊体论极为盛行,即祝尧所谓“宋时名公于文章必先辨体”〔25〕。辨体尊体是主流,但大多学者都是在辨体尊体的基础上,也同样重视破体变体,秉持“变而不失其正”的文体通变观,这其实就是一种“活法论”的诗学辩证观,从黄庭坚、谢良佐、吕本中、朱熹等都是如此,吕本中是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员。最重要的是,上述诸家的“文体论”和“法度论”大多同时并提,足见文体和法度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首先,黄庭坚的文体学思想及其对吕本中文体观的直接影响。宋代第一个提出“先体制而后工拙”这一辨体论的是黄庭坚,其《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谓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赡《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26〕在这一经典辨体文献中,“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是核心理论线索,这一辨体理论是黄庭坚在王安石文体批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其中王安石在文学批评时重视文体之间的界限,即“记”体文和“论”体文体制规范不同,各自有不同的创作法度和规矩,要严格遵守这种法度和规矩。在当代学者论“活法论”的论文中就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如吕肖奂云:“宋诗讲‘法度’,始于王安石。……‘荆公诗用法甚严。’(叶梦得《石林诗话》)”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辨体观实则就是他的法度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这则极为重要的辨体文献中看出吕本中文体论和法度论与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几位大家的交织关系。
吕本中的文体学思想与黄庭坚一脉相承,首要的就是“先其体制”的辨体论,如《童蒙诗训》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27〕所谓“先见文字体式”“亦先见体式”云云,与黄庭坚“先体制而后工拙”的经典辨体论断如出一辙。这种辨体尊体观通常在古代文体学上也往往称为常体、定体等,与活法论的定法之名相似。吕本中在它文中称为常体、定则,如吕本中《春秋集解》云:“吕氏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闰月之验。然不书闰者,闰承前月而受其余日,故书闰月之日,系前月之下,史策常体,又有定则……盖预专据左氏说经,不知闰月之日,系前月之下,史策常体也。”〔28〕
此外,吕本中“常体”与“变文”并提的说法,最能看出他活法论与辨体论不分彼此的关系,如《春秋集解》:“武夷胡氏传使举上客将称元帅,此春秋立文之常体也,其有变文,书介副者欲以起问者,见事情也。”〔29〕而且其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中和美学风格,可以说是其诗法诗体理论上之活法论和辨体论的创作实践,对于这一点,陆游已经有所论述,如陆游《东莱诗集原序》云:“故其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30〕所谓“兼备众体”是指学习继承诸家文体体制,是尊体;而“汪洋闳肆”“间出新意”则为变体破体。所谓“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愈奇和震耀耳目是变化变体,愈浑厚和不失高古则为遵守体制规范规矩,是尊体辨体,结合起来说则正是其“活法论”和辩证“辨体观”的真实写照。
黄庭坚在理论上开了“先体制而后工拙”这一宋人辨体论风气之先,但在创作中却不拘守这一辨体法度规矩,而是更多的破体变体为主,最为代表的就是他的“以文为诗”的变化生新,与苏轼及众多江西诗人代表了与唐诗迥然不同的宋诗文体风貌,为历代批评家所津津乐道。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序》论黄山谷所谓“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及历代体制之变”的变体论断〔31〕,以及王直方所谓“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的破体之论等〔32〕。
值得注意的是,吕本中是第一个注意到山谷诗的“变体”特征的,并且是看到山谷诗融尊体与变体及其法度与变化于一身的,而变体和法度并论尤其证明了活法论与辨体论的不可分离与并行不悖。如吕本中《紫微诗话》:“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书不可偏废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33〕“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体现了黄庭坚的辨体尊体观,而“极风雅之变”“本以新意者”则反映了他的破体变体观,二者辩证的集于一身,正是活法论辩证诗学观的体现,尤其“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此二者当永以为法”的文学之法度文体批评标准论,与《夏均父集》中的活法论亦以苏黄为楷模理论观念相通,是“体”与“法”融合的代表。
其次,与黄庭坚同时的北宋道学家谢良佐的辨体论和活法论也对作为与谢良佐渊源颇深的道学家吕本中影响很大。谢良佐“学诗先识取六义体面”的辨体论载于其《上蔡语录》:“问学诗之法,曰:诗须讽咏以得之,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便是法。曾本云:问学诗以何为先?云:先识取六义体面。又问:莫须于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尽,更有诗中以下句证上句,不可泥训诂,须讽咏以得之。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便是法。”〔34〕所谓学诗之“法”在于先识取六义“体面”,已然将“法度”和“辨体”结合起来谈论。在这里,谢良佐的辨体论和法度论是变通活用的:一方面,学诗当先识取六义体面,是说辨体尊体为基础,必须遵守体制规矩;另一方面,他认为又“不可泥训诂”,反对过于拘泥保守,秉持辩证的文体观。在法度方面,他也同样主张儒家中庸中和的“执中驭权”的辩证理论,即所谓“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便是法”,这种“适中”的法度论本身也是“活法”的一种形式。与此相似,谢良佐既肯定“先其体制”的辨体论为学诗基础,又持权变中庸思想,认为“中无定体”,这与吕本中“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的活法论是相通的。如在儒家哲学本体之“气”“理”的体认上,谢良佐也同样如学诗一样秉持辨体辩证观,如《上蔡语录》载“气虽难言,即须教他识个体段始得。”“所谓有知识须是穷物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得他体性始得,不然被人将鍮石来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疑惑,便执不定。”“问此诗如何?曰:说得大体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说一中分体用。”〔35〕所谓“先须辨认得他体性始得”“即须教他识个体段始得”“说得大体亦是”云云,是说这种尊体辨体是基础,但以儒家中庸思想来说,又要辩证地看待,当“处为中庸”,而“君子而时中,无往而不中也”“执中无权”“中无定体”“须权轻重以取中”等论都对吕本中的“活法”论产生极大影响,如《上蔡语录》云:“问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习,故处为中庸,故无忌惮也。君子而时中,无往而不中也。中无定体,须是权以取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今人以变诈为权,便不坏了权字?’”〔36〕其中“中无定体”与吕本中“定法无定法”如出一辙。
关于吕本中和谢良佐的关系,吕本中求教过程氏门人除了谢良佐之外的“程门四高足”杨时、游酢和尹焞,是因为谢良佐去世早,无缘亲炙,“程颐的许多亲炙弟子都活至南渡以后,程门四高足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除谢良佐在1103年先程颐而死外,游酢死时已是1123年,离宋室南渡仅四年,而杨时与尹焞则死于南渡以后近十年。”〔37〕但作为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程门四高足之首,如果说吕本中不曾熟读谢良佐的著作并深受其道学思想及其“辨体为先”观念和“法度论”的影响,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朱熹的文体学思想直接源于谢良佐,并受到吕本中的影响,这既可以从吕本中和谢良佐的承传关系中看出,也能从他与吕祖谦的关系中看出。一方面,朱熹与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的辨体关系。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云:“来喻所云‘潄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淡’,此诚极至之论,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38〕所谓“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与黄庭坚“文章先体制而后工拙”及吕本中“学诗亦先见文字体式”如出一辙,其辨体观的承传关系一目了然。接下来,在此文的结语中,朱熹在此“辨体为先”的理论指导下,其辨体批评云:“记文甚健,说尽事理,但恐亦当更考欧曾遗法,料简刮摩,使其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则其传当愈远而使人愈无遗憾矣。”在具体的“记”体文文体批评中,“但恐亦当更考欧曾遗法”一句之“遗法”意味颇深,很明显是将“法度论”与吕本中和吕祖谦的“辨体观”“先见文字体式”结合起来并谈。吕祖谦辨体观直接秉承其先祖吕本中,如《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39〕朱熹与吕祖谦的关系众所周知,毋庸赘言,那么,朱熹与吕本中的辨体承传关系也不言而喻了。
另一方面,如果说朱熹“先其体制”的辨体观与黄庭坚、吕本中及吕祖谦的承传影响关系还是我们的推测和论证的话,那么朱熹“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思想直接源于谢良佐,那是毫无疑问,证据凿凿的,如何俊等云:“谢良佐,是程门最重要的弟子,所谓‘洛学之魁,皆推上蔡’。他对朱熹与陆九渊都富有影响,黄宗羲引朱熹语‘某少时妄志于学,颇藉先生(谢良佐)之言,以发其趣’证之,全祖望则引黄震语‘象山之学,原于上蔡’证之。”〔40〕
朱熹这一重要辨体论断在《朱子语类》之《诗经》一卷中反复出现四次,与上面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辨体论可以对照解读。其中两次直接引用谢良佐之论,其一云:“问: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41〕其二云:“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42〕另外两次未明确标明为谢良佐之言,所论“紧要是要识得六义头面分明”和“读诗须得他六义之体”与谢良佐之论在语言表述上也略有差异,但这也正能看出朱熹已经将谢良佐的辨体论化为己有,融入到自己的诗经诠释学理论体系中了,如盐入水,浑然无迹。原文如其一云:“问时举:‘看文字如何?’曰:‘诗传今日方看得纲领。要之,紧要是要识得六义头面分明,则诗亦无难看者。’”〔43〕其二云:“又曰:‘读诗须得他六义之体,如风雅颂则是诗人之格。’”〔44〕以上四则辨体文献中,朱熹都把“先识取六义体面”作为“读诗、学诗、看诗、看文字”的“纲领、要领、要法、紧要处”,可以看出朱熹强烈的辨体意识及其对黄庭坚、谢良佐、吕本中的继承和吕祖谦之间的互相影响。
朱熹重视辨体尊体,但也肯定变体和变化,同时把“定法”与“体制”也就是“法度论”和“文体论”结合起来探讨,尤其能让我们看到活法论与辨体论的密切关系。其《客亦抱凌云才》云:
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辈流少能及之。逮其晚岁,笔力老健,出入众作,自成一家,则已稍变此体矣。然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45〕
前文反复论述朱熹高度强调遵守体制规矩,在这里,他则认为“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所谓“变而不失其正”体现了他辩证通达的文体通变观。该文有如下关于“法度”与“辨体”关系的几层意思:其一,所谓“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是强调尊体;“笔力老健,出入众作,自成一家,则已稍变此体矣”,是肯定变体。其二,所谓“然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突出定法和尊体;“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认同变化和破体。其三,所谓“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说明了他对于变体和正体也就是辨体和破体的关系,主张“变而不失其正”的辩体通变观,这与法度上的“活法论”异曲同工,可以说是朱熹辨体论和活法论的精髓与归结所在。其四,虽然“变而不失其正”的“适度”辩体通变观是他最高的辨体理想境界,但是他觉得“然变亦大是难事”“变体”和变化的尺度分寸不好掌握,容易变体“过度”走向极端,即“不幸一失其正”;所以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主张遵守法度规矩,“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最终的结论是,在“变而不失其正”这一理想的辨体观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秉持保守的“反不若守古本旧法”的法度观念。
总体来说,朱熹的辨体论仍旧是“变而不失其正”的“活法论”观点,主张文章“奇而稳”和“千变万化”中“有典有则”方才最“为好”。如《朱子语类》:“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阘靸。”〔46〕“陈后山文如……有典有则,方是文章。”〔47〕再如“刘叔通江文卿三人皆能诗:叔通放体不拘束底诗好,文卿有格律入规矩底诗好。”〔48〕他认为变化打破体制的“放体不拘束底诗”和尊体遵守规矩的“有格律入规矩底诗”这两种辩证对立的诗都是“好”的,这与吕本中“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的诗学通变观是极为契合的,反映了其儒家中和中庸的文体文学思想。
朱熹的关于“变而不失其正”的“权变”思想直接来源于吕本中,如吕本中《春秋集解》云:“春秋者,轻重之权衡也,变而不失其正之谓权,常而不过于中之谓正。”〔49〕卷九云:“故通其变以示不失正也,不言齐命为桓公讳也,不系于卫示无讥也。若云城卫楚丘,则彼我俱非也。凡变而不失其正者,皆以讳为善。天下之大伦,有常有变,舜之于父子,汤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处其变也。贤者守其常,圣人尽其变,会首止逃,郑伯处父子君臣之变而不失其中也。”〔50〕
三、“法”与“体”及其“定法而无定法”与“定体而无定体”
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定体和不定体”之对立范畴,与“辨体和破体”及其“尊体和变体”一样,也在文体论中频频为人所使用,这与吕本中“活法论”中的“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的理论表述就更加相似了,而且很多学者常常把“体”和“法”尤其是“定体”和“定法”放在一起进行论述,其间关系不言而喻。
首先,“法度论”与“文体论”的浑然一体。前面我们已经在黄庭坚、谢良佐、朱熹等相关文体文献中,有针对性地指出其中“法度论”与“文体论”的相提并论,借以说明“法度论”是“文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活法论”和“辨体破体论”的相似之处,进而体现本文在“文体学”的视域下观照“活法论”的研究目的,同时也有感于当下学界对“活法论”全面研究中却唯独“文体学”角度的缺失或不足。如前文所述,在宋代谢良佐和朱熹所谓“学诗之法”和“读诗之法”的诗法说和法度论,都要具有“先识取六义体面”的辨体意识,可见“法度论”和“文体论”是不可分的二而一的问题,而吕本中所谓“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此二者当永以为法”之法度论与“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之文体论杂糅而论,则是谢、朱“法度论”“文体论”不分彼此的联系纽带,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在宋代“法度”和“文体”并谈还不是很多和特别明显的话,那么到了明清,随着“辨体论”和“诗法论”的臻于成熟和兴盛,许多批评家越来越注意到“法度论”和“文体论”的密切关系,并在文学批评中将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进行论述。
在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故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51〕徐师曾《文体明辨》卷首:“文章之有体裁,尤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52〕屠隆《论诗文》:“文章止要有妙趣,不必责其何出;止要有古法,不必拘其何体。”〔53〕到了清代,阎尔梅《示二子作诗之法》:“西京以还,皆变体,非古体也……此虽作史之法乎,作诗之法,实不出于此。”〔54〕李渔《一家言释义》:“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55〕田雯《鹿沙诗集序》:“学诗者宜分体取法乎前人。”〔56〕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至于文之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文体有二,曰叙事、曰议论,是谓定体。”〔57〕钱大昕《与友人书》:“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58〕姚鼐《答翁学士书》:“昨相见承教,勉以为文之法……是安得有定法哉?……此数十人,其体制固不同,所同者意与气足主乎辞而已。”〔59〕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60〕以上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明清以来“体”“法”并谈的诸多文献,主要是为了更直观地看出法度论和文体论的水乳交融和难以分开。因很易理解,故并未进一步对文献进行解读阐释。
其次,进一步来说,“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是吕本中“活法论”的核心表述,其关于“定法与无定法”这一对矛盾对立的辩证诗法概念,与文体学上关于“定体与无定体”这一对经典辨体破体理论范畴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古代文化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中,或单独表述,或相提并论,其辩证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表达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法度论与文体论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和易于理解。
第一,这种定体与无定体、有体与无体、常体与无常体的矛盾对立的辨体与破体观,最早源于南朝齐张融,《南史·张融传》云:“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自序云:‘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有其体。……’临卒,又戒其子曰:‘……吾文体英变,变而屡奇……’”〔61〕所谓“夫文岂有常体”是说文无常体定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有其体”是说文有常体定体,在定体与无定体之间,张融更倾向于变体变化,故而称“吾文体英变,变而屡奇”。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变体论正是张融的“无师法”也即“无定法”的反映,这段最早的辨体破体、常体变体、定体无定体之辩证关系文体文献,就是将“文体论”与“法度论”结合起来而谈的,这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和法度论及其相结合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其后,金代王若虚和明代苏伯衡都用设问体和对话体来探讨这个理论问题,这与张融“夫文岂有常体”的反问句式一脉相承。如金王若虚《文辨》云:“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62〕所谓有体、无体之问,当然是说有定体和无定体的,而“定体则无”指变体破体,“大体须有”指辨体尊体,二者是活法论的辩证关系。对此,吴承学先生解释道:“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大体须有’,故应辨体;‘定体则无’,故可破体。”〔63〕明代苏伯衡则明确地把“体”和“法”结合起来,如《空同子瞽说》:“尉迟楚好为文,谒空同子,曰:‘敢问文有体乎?’曰:‘何体之有?《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谟训诰,《国风》《雅》《颂》,初何法?’”〔64〕所谓“敢问文有体乎?”曰:“何体之有?”是说文体是变化不同的,文无定体;“有法乎?”曰:“初何法?”是说法度是变幻莫测的,初无定法。
第二,宋金元的“定法无定法”和“定体无定体”理论。宋人活法理论和辨体批评中,朱熹的“定法与无定法”之“活法论”与“定格常格定体和新格变格变体”之文体论最与吕本中相契合。
关于“活法”论,朱熹在评价赵蕃诗称“固是好,但终非活法尔。”〔65〕所以,在法度与无法之间,他与吕本中一样颇为辩证通达,主张“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中”的观点,如《朱子语类》云:“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中,盖圣于诗者也。”〔66〕他提倡遵守法度,即“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但认为又不能“极法度”和“太法度了”,如《朱子语类》云:“《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学《史记》’。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67〕要求在守法和破法之间要适度中和。同样,他对于“定法和无定法”的关系,也提倡辩证通达的理论,如他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认为“从上圣贤相承定法,不容变易”,但是又要变通,不能“过于循默自守”〔68〕。在历法制度法度上,如称“今之造历者无定法”,而“意古之历书,亦必有一定之法”〔69〕,所以,这就要在造历时坚持“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无定”的“活法论”。
在“定体和无定体”论上,朱熹用定格常格和新格变格这样的对立范畴来进行定义,而对其间的关系,则秉持前面所说的“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的保守观点,如《朱子语类》云:“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份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人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时先差异了。”〔70〕所谓“依定格依本份做”,即尊体,称赏前辈遵守文章体制规范,“所以做得甚好”;所谓“后来人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是变体,打破体制法则,“本是要好”,但是反而变差了即“然未好时先差异了”。
宋代其他“体”“法”并谈者还很多,如范温《潜溪诗眼》:“黄庭坚云: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后人法度。……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定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它皆谓之变体可也。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期间。”〔71〕王柏《豳风辨》:“豳实雅也……初无定体,不知圣人之法果如是乎?”〔72〕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议论”:“按议论之文,初无定体……则正告君之体,学者所当取法然。……书记往来,虽不关大体,而其文卓然为世脍炙者,亦缀其末。……其文辞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编,则华实相副,彬彬乎可观矣。”〔73〕陈起《江湖小集》:“亚愚嵩上人,穿户于诗家,入神于诗法,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诸家之体制,各随其所至而形于言。今观亚愚之集,千变万态,不梏于所见,如所谓老坡之词,一句一意,盖不可以定体求也。”〔74〕以上所列举的诸如范温“以此概考后人法度、盖布置最得正体、各有定处,定不可乱也、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期间”,王柏“初无定体,不知圣人之法果如是乎”,真德秀“初无定体、则正告君之体,学者所当取法、文辞之法度”,陈起“入神于诗法、诸家之体制、千变万态、盖不可以定体求也”等等,皆体、法并论,其间关系一目了然,读者当自得之。
第三,明清以来定体无定体与定法无定法理论。明清以来,相关定法与无定法和定体与无定体的诗法辨体批评更加繁盛,且多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谈论。如明胡直《刻乔三石先生文集序》云:“彼文者,道法之所出,不得而袭焉故也。……故规矩者,方员之母也,而方员岂规矩哉?是故道法者,圣人之规矩也,道法备而文言之,以诏诸世,此圣人由规矩出方员之迹也。方员之迹无定体,故为典谟,为彖象,为训诰雅颂,不可穷极,执之则窒。子长之雄健,则亦方员之迹见乎一体而已,乃独逡逡焉。执子长以为规矩而袭用之,是焉知规矩?”〔75〕胡直《谈言下》云:“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体乎?曰:有。然而无定体曰文,犹诸人也。夫人莫不横目而竖鼻也,文犹诸居也,夫居莫不横梁而竖栋也,而谓无定体,可乎?……曰:然则圣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圣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76〕前文反复申说道法、规矩、无定体等与吕本中活法论相关的概念范畴,后文则与前所述张融、王若虚、苏伯衡以问答体来说明“定体与无定体”这一对矛盾统一的对立范畴一样,并与“道法”这一法度论结合起来。清汪由敦《史裁蠡说》云:“史法必先体例,体例不明,笔削无据,考之前史,史记汉书南北史梁陈二书,则世学相传,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北齐北魏诸书,则成于一手,或禀承前规,或包罗全局,文随法立,义例自符。”〔77〕所谓“史法必先体例”正如“文章先其体制”的辨体表述相似,而与“史法”之“法度”放在一起谈论,其意味则更为深长。
清代徐枋可以说是“体”与“法”及其“定体无定体”与“定法无定法”并谈而且结合得最恰如其分的代表了,其《答退翁老和尚书》云:“至文章一道,不朽盛事,亦未易言,而大要可指。有无定之法,有不易之体,惟其无定,故千变万化而不穷;惟其不易,故触绪纵心而必归控驭。如钜冶然,金铁既熔,惟意所命,倏忽倾写,钟鼎斯成,而鼎不讹钟,钟不滥鼎,无定之法、不易之体具在是矣。而近世不察,多失其宗。言法者病之于泥,不言法者病之于疏,而文章之道几为不开之茅径矣。承示古无定体,非无定体也,风气有殊也,譬如古者茅茨土阶,而今者金门玉堂,奢俭美恶亦已悬绝矣,而上栋下宇,其体岂变哉?……便是雅、颂,亦何法之可循?……真能训辞深厚,咏歌盛德,必合典、谟、雅、颂。何也?是实有不易之体,古人已立其极,而吾不能出其范围也。杜少陵句有云:‘未及前贤’‘递相祖述’。不有其体,复何祖述哉?然是求之学与道,而非求之文章之法与体也。深造于学,自得其道,则有无体之体,无法之法,不假绳墨,自中规矩,不循陈筴,自合古人,游刃运斤,无所不可矣。”〔78〕所谓“有无定之法,有不易之体”“无定之法、不易之体具在是矣”“而非求之文章之法与体也”“则有无体之体,无法之法,不假绳墨,自中规矩”云云,把“体”“法”虽为两个范畴实则一个整体的理论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活法论和辨体观的辩证特点也尽显其中。
最后,要重点提到清代辨体论和活法论的集成总结者史学理论大家章学诚,其《古文十弊》云:“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之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79〕《古文十弊》的首条所谓“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之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云云,可以说是自刘勰、刘善经、黄庭坚、吕本中、朱熹、倪思、祝尧、许学夷等以来中国古代“文章以体制为先”辨体论的最后一环,是这一文体论的集成者;而第九则所谓“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无定之中有一定焉”“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云云,则又无异是自宋代黄庭坚、吕本中以来中国古代诗法论、文法论、法度论及其活法论的总结者,二者在该文中前后呼应,从中可以看出辨体论与活法论的密切关系以及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1〕〔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67、368页。
〔3〕〔4〕〔22〕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9、243、239页。
〔5〕〔13〕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66页。
〔6〕祝尚书:《论南宋的文章“活法”》,《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7〕曾明:《“师法”与“活法”——苏轼“活法”说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8〕〔14〕〔18〕吕肖奂:《从“法度”到“活法”》,《复旦学报》1995年第6期。
〔9〕曾明:《胡宿诗学“活法”说探源》,《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0〕胡建次:《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活法”论》,《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1〕莫砺锋:《再论“夺胎换骨”说的首创者》,《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12〕莫砺锋:《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15〕〔16〕束景南:《黄庭坚的“心法”——江西诗派“活法”美学思想溯源》,《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7〕祝尚书:《吕本中“活法”诗论针对性探微》,《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9〕曾明:《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等说起》,《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
〔20〕周芸:《破体为文与“活法”》,《当代修辞学》2003年第5期。
〔21〕王晓骊:《“活法”视野下的宋词“破体”现象及其接受》,《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6期。
〔23〕吴承学:《文体学源流》,《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4〕〔63〕吴承学:《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25〕祝尧:《古赋辨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
〔26〕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郑永晓辑校,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26页。
〔27〕陈鹄:《耆旧续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
〔28〕〔29〕〔49〕〔50〕吕本中:《春秋集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2、14、4、9。
〔30〕吕本中:《东莱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31〕〔38〕〔73〕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96、308、379页。
〔32〕〔33〕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第29、44页。
〔34〕〔35〕〔36〕谢良佐:《上蔡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1、2。
〔37〕〔40〕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17页。
〔39〕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340页。
〔41〕〔42〕〔43〕〔44〕〔46〕〔47〕〔48〕〔65〕〔66〕〔67〕〔68〕〔69〕〔70〕朱熹:《朱子语类》,黎德靖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0、2086、2088、2094、4316、3308、3331、2890、3320、3321、28、25、3320页。
〔45〕朱熹:《晦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4。
〔5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964页。
〔52〕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罗根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7页。
〔53〕〔64〕蔡景康:《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69、46页。
〔54〕〔55〕〔56〕〔57〕〔58〕〔59〕〔60〕〔78〕〔79〕王镇远、邬国平:《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7、99、370、380、563、571、723、209、620页。
〔61〕李延寿:《南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2。
〔62〕王若虚:《滹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7。
〔7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中华书局,1980年,第323-325页。
〔72〕王柏:《鲁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6。
〔74〕陈起:《江湖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9。
〔75〕〔76〕胡直:《衡庐精舍藏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30。
〔77〕汪由敦:《松泉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0。
〔责任编辑:李本红〕
任竞泽,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11BZW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