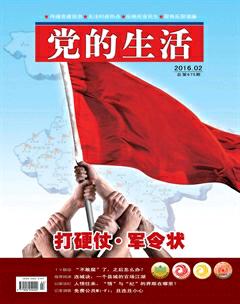雪冷血热
张正隆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且不说肥美的黑土地怎么会孕育了这样一支悲怆的歌,娩出了“满洲国”这样一个怪胎,还是让历史先定格在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那一刻,看看我们该铭记些什么。
1931年的9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在晚上8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张学良更悲惨、更凄苦、更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岗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入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个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当地有名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七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三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再说什么吗?
北大营9点钟熄灯。
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这天本是宿假,却赶上营值星官,因为营长于天宏不在营中,他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灯号响过,他到各连查夜回来已过10点。脱衣上床后,心神不宁,有种要出事的感觉,随手抓过床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催眠。这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
不好!他翻身跃起,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十多分钟集合完毕,姜明文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
事变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配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
队伍未出620团院子,中校团副朱芝荣气喘吁吁赶上来,让把部队带回去。姜明文问为什么,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姜明文等几个连长强压怒火:“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枪炮声中,赵镇藩拼命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先给在三经街的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说他去找荣臻参谋长研究一下。
赵镇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赵镇藩抹把脸上的汗水,硬着头皮又给荣臻打电话,说明官兵大都在火线上,收枪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荣臻喝道:“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是11点左右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5分钟后旅长王以哲也到了。
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不停鸣叫着。
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
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
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
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
无处不告急,十万火急!
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王以哲望着荣臻。“给北平打电话,请示一下。”荣臻边说边拿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震惊世人的“不抵抗”——还是“坚决性”的!
“北平,十万火急。副司令勋鉴:日军大举向北大营和奉天进攻。如何应付请速示机宜。”
接到荣臻的电话和这封没一个“!”的电报,三十岁的少帅那张因患伤寒病初愈而显得苍白的脸上和怦怦跳动的心头,会镌刻下多少惊心动魄的“!”和“?”?
日本人真的就动手了?!
这一天真的就到来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张学良从戏院匆匆赶回协和医院,立即向蒋介石发报请示。
半夜时分,收到回电:相应处理。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说:“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可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铁岭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更盛产“事件”,因为关东军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变成“事变”。
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段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来了个“相应处理”。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史称“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电后,转知东北军各长官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和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7月10日,张学良在给王家祯的电报中又称:“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大都谴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台湾国民党当局至今仍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大陆则认为他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铣电之前,因了张学良的“抵抗必败论”,东北军“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张学良并不是什么都听命于蒋介石的。易帜后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中原大战前,蒋介石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拉拢张学良吗?下道命令就行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也说“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抵抗”。
江桥抗战,马占山抵抗了,蒋介石又把他怎样了?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老蒋咬钢嚼铁一声“打”,少帅能不打吗?
而少帅主张的是“全国抗战论”,前提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接到荣臻“十万火急” 的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一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拥护中央;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拥兵入关,体现与实践的都不无这种主张。结果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日的巧合: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关,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战;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断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
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却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在发出那封“不抵抗”的铣电时,正在江西指挥30万大军围剿红军。
这种矛盾、对立、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忍无可忍的少帅,没了东北的“东北王”,一怒冲天,以一种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宁死”的英雄气,挥洒出一道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的闪电。
别人可以不抵抗,他张学良必须抵抗,于国于家于他个人,都必须抵抗。在中国,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强势人物,因为他的东北军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以那片丰腴的黑土地为根基的。中国的大小军阀都拼命地抓枪杆子,但若没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水土、地盘,谁也阀不起来,只能当流寇。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样随波漂流,身不由己地为老蒋去打在老蒋眼里好像比日本人还可怕的共产党,后来则像只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被拎去台湾还是只笼中鸟。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应处理” 的电报,在那决定东北命运的时刻,无论张学良想了、说了些什么,他的行动告诉人们的都是:你老蒋不出兵,让我看情况去办,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回忆录中写得明白:“从当夜十一时稍过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让出奉天城为止,中国方面由省长公署几乎是不间断地用电话向我总领事馆表明中国官民均无抵抗之意,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到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又通知说要开放城门,以示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这么拉倒了?当然不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会抗不住国际上的压力,关东军能很快撤兵。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国联”能够为他惩罚日本、伸张正义。
200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绥阳镇采访到一位“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老人叫陈广忠,93岁,当年为北大营7旅通讯连士兵。事变当夜,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腮打入,满口牙没几颗了。
老人说,开头听到枪炮声,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长官说是日本子搞演习,炮弹落大营里了。“子溜子”(东北老话,“子”即子弹,“溜子”即弹道)嗖嗖的,天底下有这么搞演习的吗?有的弟兄伤了、亡了,大家都红眼睛了。可上边不让打,叫“原地待命”,什么鸡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吗?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仓库拿枪,动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没穿上就让小鬼子打死了。没接到撤退命令,有些军官就在那儿“挺着死”——军人得服从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着跑出来的。
老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上边不让打,养兵干什么?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儿挨枪子,妈个巴子,俺们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那打到“国联”的官司在天平上加砝码——
尊敬的洋大人,你们看吧。这满营的弹坑、弹痕,是中国军队自己打的吗?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里的,兵舍里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无寸铁,而且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还有这些枪库、弹药库,这些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诸位先生可以随意查勘、检验。如此,9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鬼精鬼灵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么都筹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国联”呀,“公理”呀,“正义”呀,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嘴巴子上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腰包鼓、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有几多人愿意站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强者、胜者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话语权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他们要的是事实。而且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开头那枪炮打的都是空包弹,见你不还手,这才动起真家伙。万一攻击失利,那我就是搞演习,黑灯瞎火弄错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里,“误会”呀,“遗憾”呀,“下不为例”呀,一张嘴,两片唇,一张一合说去呗!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这是当年东北军的一支军营歌曲《上起刺刀来》,那守土卫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是何等凛然、豪迈,就像是专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写的。
“日本子打进来啦!”原为对外开放,常有外军代表参观、访问的东北国防军的王牌7旅,随着这一声声惊呼,官兵们纷纷赤着臂、光着脚去库房砸锁踹门拿枪,拿不到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拿到枪却不敢违命开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豁出命去还击的叫骂着“妈个巴子”,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
没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营再乱糟的了,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再狼狈的了。
用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夺占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