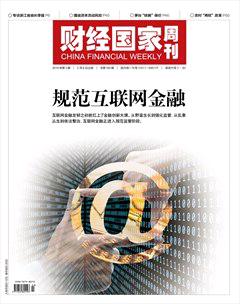走亲戚
魏新
从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每年初四,都要去姥娘家走亲戚,这一天,姥娘家叫“齐客”,意思就是客齐了。
最早的“客”只有我爸。我妈兄妹四人,她是老大,结婚后,我爸回门,家里算是有了正式的“客”,再后来我姨结婚,“客”里多了我姨夫。我两个舅舅结婚,舅妈不算“客”,舅妈的兄弟姐妹们加入到了“客”的行列,后来,我妈的表姐表妹、堂兄堂弟也凑到这一天来看姥娘姥爷,家里的“客”就越来越多。再后来,我们这一代人也长大了,带着老公老婆,抱着孩子过去。姥娘家四间堂屋,一个小院,这一天,满满的人。
“客”从上午九点多就陆续赶来,过去都是骑自行车,一停就是半院子。后来渐渐有了几辆摩托车,还有从农村过来的亲戚开的机动三轮。这几年,有了四五辆汽车,姥娘家的那条胡同窄,幸好对门有一片空地,停得满满的。从车上下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抱着东西往里走,一箱一箱的酒、牛奶、饮料,讲究的,还会专门买上几包老式点心,那种用草纸包好的蜜果子,用纸绳捆着,每一封上面,盖着一张鲜艳的红纸,小山一样堆到姥娘住的里屋。
齐客最重要的,便是中午这顿饭了。如今一般分五桌:由姥爷带着主“客”坐一桌,这一桌都是男客,女客由姥娘带着坐一桌。这两桌“客”都是我爸妈这辈人。我作为第三代年龄最大的“客”,带着一群弟弟另开一桌,妹妹们和弟媳妇们再开一桌。除此之外,还要有一桌儿童席,早些年,我算是儿童席老大,现在,桌上的孩子我快有一半认不出是谁的了。
这一天掌厨的一直是我大舅,二舅帮厨,两个舅妈负责洗菜刷碗。每桌要先上十几个菜,边吃边喝,之后,收了酒具,撤了盘子,重上碗筷,每桌上六个蒸碗,外加一咸一甜两个汤,然后挨桌发馒头。
最过瘾的,还是吃饭时才上的蒸碗。这些蒸碗都是年前就做好的,一碗一碗码在冰柜里,这一天拿出来,在一个七八层的大蒸笼里摆好。院子里专门为蒸笼搭一个灶台,烧柴禾,火光熊熊,热气冲天。起蒸笼的时候,要把蒸碗扣到盘子里,这是可是一个技术活,蒸碗很烫,里面还有汤汁,只能先拿盘子盖在蒸碗上,然后飞快地连碗带盘子扣过来,再急速把碗掀开,放在一边,扣下一个。
扣蒸碗我不行,吃蒸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是蒸鸡还是蒸鱼,我都毫不含糊,最爱吃的是蒸肉,这里的肉专指猪肉,有时是肘子,有时是蹄髈,红澄澄一层皮,白花花一层膘,再加上红澄澄一层肉,吃得大快朵颐。和红烧肉不同,蒸肉不怎么放糖,要先绰,再炸,再放上葱姜大料,上笼蒸两个半小时,蒸好后,肉的原汁原味保留得很好,虽稍感肥腻,但奇香无比。所以,每次我不管前面吃什么菜,喝多少酒,总要留着胃口吃上两三片,要不,会觉得无比遗憾。
蒸肉的美味让我理解了《西游记》里的妖怪们抓住唐僧,为什么总是要蒸着吃。确实,在蒸肉面前,别的做法都是对上好食材的浪费。
不过,爱上蒸肉是后来的事,小时候最爱吃的是蒸甜米,这道菜对孩子们来说诱惑无法阻挡。他们毕竟饭量有限,第一桌菜就毫不矜持地吃饱了,上蒸碗时,放羊一样到处跑着玩,直到有人喊“上甜米了”,大家会蜂群一样集中到桌子边,拿起筷子,直奔甜米而去,这时候,只要稍一愣神,甜米就只剩下几个枣核和一个空空的盘子。
甜米是用江米做的,加上红枣,山药片,一起蒸,红枣在碗底,扣过来,在盘子上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姥娘家的甜米还会加上玫瑰酱,上之前,再撒上一层白糖,吃完之后,半下午嘴巴都是甜的。
午饭后,“客”开始陆续走了。最先走的是远一点的亲戚,然后我妈我姨才开始走。每一家走的时候,姥娘总要回赠一两样礼品,因为按老理,是不能让“客”空着手回去的。不过,这些年几乎没有人要,派出去回礼的小表弟每每抱着箱子往外冲,要往人家的车子上放,车子边总是有一个人和他撕扯,表示坚决不收。这一幕,每一年都要重复好多次。
姥娘和姥爷退休前都是普通职工,因待人厚道,不小家子气,齐客才会来这么一大家子。亲戚们在一起,几乎从未红过脸,每年才有这么一次热闹和谐的相聚。像他们这样的福分,我这代人已不可能拥有,未来等待我们的,或许只是无比寂寥的风烛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