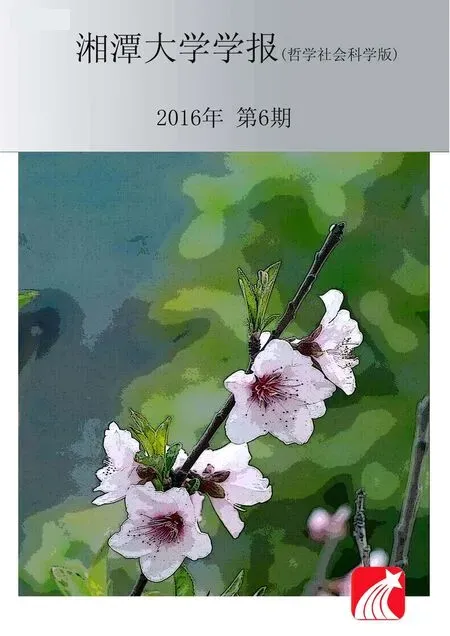论索因卡戏剧创作中的非洲传统元素*
陈 梦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论索因卡戏剧创作中的非洲传统元素*
陈 梦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尼日利亚作家渥莱·索因卡自幼接受宗教祭典、图腾崇拜、民间舞乐等约鲁巴部族的文化意识和艺术传统的熏陶。鲜明的民族色彩是索因卡创作最突出的特征。非洲神圣善变的奥贡神、奇特的祭祀仪式、复杂的循环轮回观在索因卡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鼓乐歌舞、挽歌谚语、面具雕塑等非洲传统艺术手法在索因卡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运用。传承传统文化和借鉴传统艺术为索因卡的作品带来了鲜明的宗教色彩、丰富的哲理寓意、浓厚的非理性因素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
索因卡;非洲传统;宗教;神话;民间艺术
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的戏剧作品以鲜明独特的民族特色而著称于世。在他看来,“非洲艺术家从来就是也应该是社会风习和历史的记录者,时代的理想的表达者”。[1]77-83他自幼接受约鲁巴部族的文化和艺术传统的熏陶,神话传说、宗教祭典、图腾崇拜、民间舞乐、雕刻面具等黑非洲传统文化是索因卡最重要的戏剧创作来源。他继承了非洲传统艺术的成份, 巧妙地把西方的戏剧艺术与黑非洲传统中的哑剧、闹剧、滑稽戏、宗教剧、歌剧等结合起来,善于借鉴音乐、舞蹈、假面舞、挽歌、朗诵、戏中戏、宗教仪式等非洲传统的舞台艺术手法,向全世界读者形象地展示了非洲神圣善变的奥贡神、神秘奇特的祭祀仪式、深刻复杂的循环轮回观以及富于多重意象与象征的约鲁巴雕塑面具,呈现出鲜明的宗教色彩、丰富的哲理寓意、浓厚的非理性因素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为世界文学开创了一个新颖神奇的艺术世界。
一、丰富多彩的约鲁巴神话元素
索因卡的祖辈信奉约鲁巴传统宗教,笃信鬼神、巫术和传统宗教仪式,亲族中有巫医,也有祭司。他的成长岁月中充满着丰富多彩的宗教神话故事。非洲神话特别是约鲁巴神话为索因卡戏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主题意象。阅读索因卡的戏剧作品,首先吸引读者的是丰富多彩的约鲁巴神话世界。他借鉴传统艺术,把神话、传统和仪式结合成一体作为自己的文学营养,在创作中创造性地引进神话意象、神话传说和神话思维。《沼泽地居民》、《森林之舞》、《路》和《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等都是以约鲁巴宗教神话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各路神仙和精灵鬼怪汇聚在索因卡的舞台上,其中既有祭祀神、雕刻匠的保护神、太阳神、河神、火山神、黑暗神,也有祖先的幽灵、树精灵、棕榈树精、宝石精、大象精、蚂蚁王和众蚂蚁,还有岩石魔、土地妖、草精灵、露水精、神怪们、梦魔们、女妖、风妖等。在索因卡戏剧创作中,较有影响的神话元素有至高神奥罗伦、奥巴塔拉神、奥贡神、蛇神、精灵鬼怪等。这些神话为索因卡的戏剧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森林之舞》中的民族大聚会是生者、死者、神灵、鬼怪汇聚一堂的大型活动。与聚会的组织者“森林之王”对应的是约鲁巴族信仰的至高神——奥罗伦。“森林之王”以主神奥罗伦的身份登场,所作所为鲜明地体现了至高神奥罗伦的宗旨,但与传说中的奥罗伦并非完全对应。起初,他化装为奥巴奈吉,试探世人对他是否驯服。他“抛出隐晦的暗示来保护”他的神秘身份,迫使人们接受他的“冷淡态度”。结果,他发现历史和现实惊人地相似,生者与死者的“行为几乎相同,无论是善、是恶、是暴力、还是粗心大意;动机几乎相同,无论是虚幻的、明确的、值得称赞的、还是该诅咒的”。[2]192
在约鲁巴神话中,奥巴塔拉神被认为是“原始之父”,“人类的创造者”、“社会的创造者”。索因卡称奥巴塔拉神是“人类痛苦精神的化身,虽然极度痛苦,但并不抱怨,充满了忍耐和牺牲的殉道精神”。[3]34《巴阿布国王》利用奥巴塔拉神(Obatala)来详细地说明巴阿布的角色本质。索因卡将约鲁巴悲剧的概念用戏剧演出的形式演绎出来,地狱般的巴阿布王国就是奥巴塔拉神抛弃他的创造物(指巴阿布)的背景,巴阿布糊里糊涂地命令那个杰勒德式的新娘上战场。在《巴阿布国王》的语境中,奥巴塔拉神的无私品质表达出对巴阿布式领导人的负面看法,预示着死亡与新生的杰勒德式新娘的出现给变革所带来的潜在机会。巴阿布的性格缺陷表明约鲁巴的创造之神奥巴塔拉神已经抛弃了他。巴阿布的道德和伦理缺陷是奥巴塔拉神醉酒的标志。
奥贡神(Ogun)是约鲁巴人自铁器时代以来顶礼膜拜的铁神与战神,最初具有创造与毁坏的双重象征意义。然而,奥贡神在西非人生活中的真正含义是随着历史与现实而发生改变。在索因卡看来,“奥贡神具有普遍的本质并容有不同的解释”。他拥有多种身份,既是“铁匠的保护神”,又是“冶金、金属之神”;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他又成了“闪电之神”、“机械之神”、“技术之神”甚至“路神”和“电神”。[4]250-251索因卡把奥贡神引入作品,进行多重建构,使之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意象。《森林之舞》(ADanceoftheForests, 1960)中的奥贡神降临尘世,参加森林大会,与人类共舞同欢,并且作为义人的庇护者参与“森林之王”主持的“末日审判”;《路》(TheRoad, 1965)中的奥贡神是一位具有消极倾向的神灵,极其丑恶、反复无常和邪恶,不时显现在路上,嗜杀捕食那些毫无戒心的猎物,成为“路”之主宰,兼具破坏与毁灭、创造与守护的双重身分。
“沼泽地”是古老原始的非洲文化的象征。古老的非洲居民在贫瘠而多灾的“沼泽地”繁衍生息。千百年来,沼泽地居民无比地崇拜蛇神。为了求得寒能保暖、饥能裹腹,他们把沼泽地最好的土地留给蛇神,每年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来献祭蛇神,虔诚地祈祷。然而,蛇神并未感动,灾难仍然不断降临到沼泽地居民头上。他们的生计难以维持,每年饱受洪水的危害。伊格伟祖把自己仅有的几只山羊奉献给了蛇神,把最时鲜的扁豆送上了神台,把最新榨的油洒上了祭坛”。[2]32可是,蛇神并没有保佑他和他的家人、田地和其他一切,也不曾保佑他“白头偕老、子孙满堂和生活美满”。[2]33在洪水淹没庄稼之后,伊格韦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蛇神的冷酷无情,亲吻祭司的双足、喂养贪得无厌的蛇神并不能解决沼泽地居民的苦难和贫穷。
《森林之舞》中的那片森林就是一个神奇的精灵世界。当“森林之王”召开“死者欢迎会”时,众多精灵鬼怪欢天喜地地从地下钻出来参加聚会,其中最为活跃的有树精灵、棕榈树精、宝石精、大象精、蚂蚁王等。索因卡对各种精灵鬼怪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描绘,想象力之丰富实属惊人。例如,树精灵木列提和“律师中的长者”阿格博列科是好朋友,阿格博列科经常给他送酒喝。木列提性格开朗,对森林里的动静观察仔细,还经常学说阿格博列科的“至理名言”。
由此可见,索因卡善于发挥想象,对约鲁巴族的神灵鬼怪进行新的阐释,从而使得这些拥有神格的角色并未恪守其在神话中的本分,演绎出许多生动有趣而又寓意深刻的新的神话故事。这些新的神话故事被安置在西方文学的叙述框架,与西方现代戏剧有着完美的结合,营造出一种古老神秘而又虚幻陌生的非洲神话世界。作为非洲现代戏剧的开创者,索因卡长期致力于探求一种不同于西方悲剧传统而富有约鲁巴传统文化意识的悲剧精神。他将约鲁巴族的受苦神话诗学转化为自己的创作母体,回到约鲁巴的神话里重新去寻找创作的动力,解决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创立了一种以“第四舞台”、“仪式悲剧”、“转换深渊”为核心词汇的悲剧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神话整体主义”。
二、崇高庄严的传统宗教仪式
阿凯的牧师寓所与阿芬王宫以及基督教礼仪和传统宗教礼仪,伴随了索因卡的成长岁月。除了父亲,索因卡受爷爷的影响最大。索因卡的爷爷信奉的是约鲁巴原始宗教,对上帝的福音很漠然,坚信只有“奥贡保护自己人”。繁琐的非洲传统宗教仪式在索因卡的戏剧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沼泽地居民》《强种》《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等都涉及了传统宗教仪式。
对非洲人来说,祖先的荣耀世界虽然无形,但十分真实,与现实的有形世界十分亲近。“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的各种力量互相交错,生活在“有形世界”的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肉眼看不见的东西”。[5]6国王的侍从首领的殉职仪式,是约鲁巴民族为了能让国王顺利通过通道,为了四重世界能够安稳运行,为了全民族的“生”和全民族的繁荣兴旺而进行的死亡仪式。《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andtheKing’sHorseman,1975)就是一曲典型的侍从殉葬“仪式悲剧”。剧本中反复运用喻意丰富的诗化语言、音乐、舞蹈以及哑剧,营造了一种极为神秘怪诞的宗教气氛。主人公艾勒辛(Elesin)和他的儿子欧良弟(Olunde)虽为现代人,但思想意志仍停留在古老的神话世界里。国王去世后,艾勒辛决定遵照传统习俗、服从神的意愿,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而举行隆重的自杀仪式。艾勒辛精神愉悦、语言风趣、歌唱有力,众人包围着他,合唱队为他唱赞歌,不断地向他发出死去国王的召唤。鼓声越来越激烈,合唱队的挽歌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强,催促艾勒辛上路。于是,他跳起了转换深渊的神圣舞蹈,并通过和合唱队的歌唱应答形式,向大家传递神的意愿、报告转换深渊边缘的幻相。在完成自杀仪式的关键时刻,艾勒辛沉浸在转换的记忆之中,完全没有了人世的意识,也听不见唱赞歌的人的召唤,整个自杀仪式的场面显得十分神圣而悲壮。英国殖民总督阻止艾勒辛自杀后,欧良弟服从神的意愿而自杀身亡,代替父亲完成了维护神话秩序的神圣责任。玄虚的神性意愿艾勒辛父子的个人意愿,古老的神话秩序成为他们的生活秩序。虽然,欧良弟(Olunde)替代了父亲去执行神的意志,但最后还是无法阻止艾勒辛的自杀,先进的现代文明依然无法改变非洲人神圣的传统宗教秩序。
成年礼是纪念男女从青年进入成年而举行的仪式,非洲国家的成年礼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沼泽地居民》和《强种》都描写了约鲁巴人的成年礼,特别是割礼。《沼泽地居民》中的卡迪耶是一位邪恶的祭司。他为小孩施行割礼时非常冷酷无情。按照习俗,男孩在施行割礼时不能见施礼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尤其是女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也不行。孩子在接受割礼中疼痛难忍,“嚎啕大哭,声音能盖过整个沼泽地的蛙声。”他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哭声,就从锁着她的屋里跑出来,到孩子身边去,使自己的儿子亵渎了神明”。于是,卡迪耶“只好为孩子施洁净礼,求神赦免她的亵渎罪过”。[2]28-29在《强种》中,少年时代的埃芒在森林里接受成年礼。他非常认真地学习,自己搭建茅屋,感觉自己“在变成一个男子汉”,第一次懂得了有一辈子需要自己“充分地去生活”。他深入思考,认为“男子汉就得有男子汉的样子,就得到谁也帮不了他忙的地方去考研自己的力量”。[2]253埃芒认真遵守成年礼中的传统习俗,不见女人。他催促前来看他的奥麦赶快离开,也不允许奥麦碰他的身体,因为他不想惹祸,也不想“把自己洁净的身体弄脏”。[2]253不料被老师发现了,小埃芒因破坏了严重的戒律而面临残酷的惩罚。可恶的老师企图乘机对奥麦图谋不轨,为了解救女友,埃芒只好在反抗老师后只身外逃。
三、深奥复杂的再生循环思想
索因卡的戏剧作品浸透着对个人与集体、生与死、神灵和鬼魂、历史与现在等问题的探索。非洲哲学关于生与死、祖先和灵魂、轮回与循环等问题的阐释为索因卡戏剧创作提供了哲理意象和荒诞情节的启发。深奥复杂的生死循环与轮回观是索因卡作品探讨的重要问题。《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森林之舞》《疯子和专家》(MadmenandSpecialists,1970)和《路》等都涉及到了循环轮回观念。
《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为观众形象地阐述了约鲁巴宗教玄学有关死人世界、活人世界、未来世界和“轮回通道”等四重世界的共存。约鲁巴人认为,宇宙间除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第四空间”——“轮回通道”。“轮回通道”的探明和征服是人的生命循环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世界之间和谐的保障,而人类的宗教自杀仪式是征服并打通“轮回通道”的关键环节。国王的丧葬仪式特别能展示国王的神性,国王在世时经常被视为半人半神,死后成了真的神,并加入部族和王族的祖先行列。他们相信,只有国王的侍从在国王死去的第30天通过自杀完成征服“轮回通道”的重任,才能让死去的国王在轮回中再生,从而拯救约鲁巴民族,使整个世界走向繁荣兴旺。剧中国王的马夫艾勒辛为了约鲁巴四重世界的命运决定举行自杀仪式,但是由于他对尘世的眷恋和英殖民行政官皮尔金斯的乘机阻扰,自杀仪式无法顺利完成。然而,约鲁巴人相信自杀仪式的中止会使已故国王要在“轮回通道”未经打通的情况下上路,三个世界的连接因此而中断,宇宙秩序因此而陷入混乱,世界将会永陷纷争,生命也将无法延续,约鲁巴人将会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正在危难之际,艾勒辛的长子欧朗弟遵循约鲁巴的古老传统,替父自杀,希望能为已故国王打通神秘的“轮回通道”,从而挽救四重世界的和谐。
《森林之舞》是非洲民族再生循环观念的集大成者。索因卡精心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再生,再现了历史悲剧的现实重演。在剧本中,世人本着接续辉煌历史和缅怀先人业绩的目的举行了热闹非凡的“民族大聚会”。一对300年前的幽灵夫妻应邀前来,男幽灵曾经是马塔·卡里布王国的一名武士,因反对国王发动不义战争而受到惩罚,女幽灵腹中怀有的婴孩长达数百年而无法生产。他们从森林里钻出来,与活人们直接交谈,迫切希望活人受理他们的冤案,为他们平反昭雪。女幽灵看到活人的生活现状后,感叹地说:“三百年了,什么变化都没有,一切照旧。”[6]159他们看到马塔·卡里布王国时代的许多人物在现代社会得以再生,这些再生人物的阴暗心境和罪恶行为居然与当年十分相似。名妓罗拉在几百年前是尊贵的王后,号称“乌龟夫人”,马塔·卡里布王朝的部落战争源于她的行为放荡,如今又争风吃醋,唆使追求者杀死自己的情敌;议会演说家阿德奈比在古代是宫廷史学家,曾经接受奴隶贩子的贿赂在“指头大的船”中塞进60名奴隶,导致很多奴隶窒息死亡,现在又接受贿赂把限载40人的汽车超载到70人,最终酿成惨重的车祸;古代的宫廷诗人戴姆凯如今成了一名雕刻匠,从前他强迫自己的书记官为王后抓金丝鸟爬屋顶而摔断了一只胳膊,现在又驱使自己的助手为雕刻图腾而爬大树伐木摔死。古人与今人的命运循环往复,现实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历史人物的再生意味着历史的罪恶与不幸在现代社会的重演,这种局面催人深思、发人深省。
索因卡对约鲁巴民族深奥复杂的再生循环与轮回观念持有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赞同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美德与罪恶从古到今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不断往复循环,历史传统的回顾往往成为现实问题,现实生活总是掺合着历史的阴影。世人不应该否定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不能否定传统。“过去是怎样, 将来还会是怎样, 就象事情开始的时候一样”。[6]368索因卡通过《疯子和专家》中的阿发指出,“ 哪儿轮回圆满, 哪儿就能找到As。”[2] 384《路》中的“路”是一个与往昔相关的物象,集过去、现在和未来于一体,维系昨天,经过今天,通向明天。在索因卡的观念世界里,“路”活着,始终在动态之中。“路” 既导向毁灭与死亡,同时也引发创造和新生,是贯通过去和未来、连接神界和人世的喻意性通道。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是宇宙循环中的必要环节,生与死、过去与现在都容纳在同一个苍穹里,割裂两者就会破坏周而复始的大苍穹的和谐统一;循环作为历史延续性的一种形式,势必造成历史对现在、死人对活人的困扰与束缚。在《森林之舞》中,被森林之王解救出来的半生半死的孩子就是人类希望的象征。他是连接着过去不幸的纽带,同时又预示着未来的转机。所以,世人要总结历史的教训,关注现实的生存危机,防止悲剧的重演和历史的循环。
四、鲜明独特的非洲音乐歌舞
1986年,索因卡在诺贝尔授奖演说中自豪地说:“我是非洲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非洲民间戏剧是其创作的重要源泉,非洲民间戏剧起源于古代丰收庆典,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在尼日利亚,再现宗教神话和祭礼仪式是民间戏剧的主要任务,戏剧演出往往就是古老神话的再现。从总体上看,索因卡50年代在英国的创作偏重于遵循欧洲的文艺理念和运用西方表现手法,60年代回到非洲后的创作更多地是遵从非洲传统,吸取非洲民间艺术,并企图实现非欧创作艺术的融合。为此,他大量运用音乐、舞蹈、假面舞、挽歌、击鼓、朗诵、戏中戏、宗教仪式等非洲传统的舞台艺术手法,把古希腊戏剧艺术、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黑非洲传统中的闹剧、滑稽戏、宗教剧、歌剧等结合起来,成为“非洲的莎士比亚”。
鼓是非洲人民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乐器,是非洲黑人舞蹈和音乐的灵魂。黑人舞蹈常用打击乐器伴奏,以鼓为主,索因卡用鼓乐和舞蹈来营造戏剧场景的气氛,鼓乐始终是索因卡戏剧中舞蹈场景最常用的伴奏。《狮子与宝石》《路》《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旺西尧歌剧》《欧里比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以及《巴阿布国王》等作品中都有各种形式的非洲鼓乐演奏成分。《狮子与宝石》的鼓乐演奏贯穿剧本始终,最能体现非洲传统的喜剧特色,是索因卡使用鼓乐最多的戏剧作品。《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从头至尾都弥漫着集中而强烈的鼓声,把鼓乐当作活跃场景、推动情节的重要元素。当艾雷辛为了表达自杀的决心,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鼓师即可上场为他击鼓助兴,“从他的舞步抓出节奏,击鼓加入他的舞蹈。”[2]432在《路》中,擂大鼓是流氓头子小东京召唤哥儿们的信号和娱乐方式。他在商店过完大麻烟瘾,闲得无聊,随手抓起大鼓走到篱笆边,擂鼓召唤他的哥儿们一起来吸大麻烟。他擂完鼓返回棚屋,鼓点儿的回声还在空中荡漾。
非洲是著名的歌舞之乡,非洲人的生活中是离不开音乐和舞蹈的,所有的非洲人都能歌善舞。在索因卡的戏剧中,每当节庆日来临,约鲁巴人穿上特定的民族服饰参加仪式。每逢重大的节日,黑非洲人总是喜欢戴假面具装扮亡灵,载歌载舞,热热闹闹地开展庆祝活动,把歌舞表演作为非洲民间戏剧最主要的成分之一。索因卡将非洲传统的鼓乐、舞蹈和哑剧交织运用在他的戏剧作品当中,通过音乐、舞蹈、假面和唱词来协调和推进戏剧的故事情节。如前所述,《狮子与宝石》《路》《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旺西尧歌剧》《欧里比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以及《巴阿布国王》等作品中都有丰富多彩的非洲歌舞表演元素。根据《狮子与宝石》的剧情,索因卡在剧中精心安排五段精彩的歌舞来增添喜剧效果,既有集体圆圈舞蹈和男人精力舞,也有单人耸肩舞和胜利舞。在《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第一幕开头,走唱说书人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试探艾雷辛自杀的决心。艾雷辛的情绪激昂,高喊“诸神已言明,不允许世界偏斜”,为表决心,艾雷辛跳起了一支简单、略带逗弄意味的舞蹈。他一边吟诵着“非我鸟”的故事,一边朝着市场的方向跳舞,艾雷辛的歌声巧妙,变换自如,非常形象地模仿着“非我鸟”故事中的主角。在自杀仪式即将举行的当天晚上,艾勒辛跳了一段庄严肃穆的告别舞。《森林之舞》是黑非洲万物有灵信仰的艺术化表现,索因卡精心安排的这场“森林之舞”事实上是一场奇特的蕴含着尼日利亚民俗文化意味的民族之舞。“森林”是尼日利亚的象征,尼日利亚人始终相信森林之中的地下世界是自己祖先的居住地,祖先们可以在死人世界和活人世界来去自由。因此,在这场盛大的森林舞会中,索因卡尊崇古老的民族传统,把黑非洲人崇拜的树神、太阳神、河神、黑暗神、蚂蚁神、火山神、大象精等各路森林神灵都请来了,让死人与活人相聚,人类与鬼神同台共舞。虔诚信仰原始宗教的观众们被剧中盛大的民族舞会所吸引,也热情地参与到戏剧之中,和剧中人物共同“舞蹈”,赋予作品多层的文化意蕴。
在剧本中插入以哑剧形式上演的戏中戏是非洲民间戏剧最独特的艺术方式。索因卡很善于在创作中恰当地插入哑剧。例如,在《路》中,萨姆森和柯托努两人以哑剧形式表演了一段桥头事故:车祸(货)商店的帆布在众声喧哗中从里面拉开,萨姆森戴着面具、扮演鬼魂埃贡贡,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喧嚣声渐渐消失,拨弄乐器的手停住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鬼魂。在《狮子与宝石》(TheLionandtheJewel,1959)中,女主人公希迪提出跳个舞表演一下,拉昆来被逼领街表演了一出外乡人醉酒迷路的哑剧:演员们迅速到位,大家先是哼着小曲,围着拉昆来跳舞,快速地念诵着歌词。过了一阵,鼓手参加进来。鼓声响个不停。拉昆来模拟表演外乡人进入伊鲁津来村和他在村民之间逗留的哑剧。四个女孩蹲在地上充当汽车轮子。拉昆来在中间做出开车的逼真动作。一开始,阵阵轻微的鼓声由远而近、由小变大。紧接着,四个女孩扮演四个“车轮子”,不断以圆圈的动作转动着上半身,模拟汽车向前行走。突然间,汽车失灵了,鼓声也中断了。女孩们惊恐万分,连忙把脸伏在自己的膝盖上,做出颤抖动作。无奈之中,拉昆来从车上下来,向下面张望,试着挑弄“车轮子”,双唇表现出忿怒咒骂的表情。在汽车无法启动后,拉昆来回到车里拿起照相机和遮掩帽,然后出来在丛林中边走边喝酒,野兽的吼声使他神情紧张,醉酒跌倒后又饱受苍蝇的围攻,蹑手蹑脚地拨开拦路的小树林,最后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了水里,丢了所有的东西,除了相机。拉昆来自始至终未曾开口说一句话,只用动作和表情来表情达意。这些哑剧的添加大大强化了增强了剧本的喜剧色彩。
总之,索因卡戏剧中的鼓乐演奏、歌舞表演、哑剧和假面戏等艺术形式的包罗万象,明显地透露出索因卡有着深厚非洲传统戏剧文化的底蕴。西方评论家戈特里克认为非洲传统戏剧与西方戏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艺术倾向性,非洲传统戏剧更像是一种典礼戏剧,其特点为情感性和仪式性,而西方戏剧更倾向于夸张性和无序性。在他看来,“非洲传统戏剧的显著特点不是西方戏剧的线性结构,而是在一部篇幅长的戏剧里包含几出戏。每出戏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许在阐述一个完整的故事。”[7]181索因卡的戏剧作品融合了上述多种艺术形式,使他的作品不仅是阅读的文学材料,而且是用来表演的戏剧剧本。在舞台上,演员们不时地进行即兴表演,观众则以合创人的身份参与到故事情节中,许多戏剧作品成为尼日利亚的街头表演剧,被人们广为流传。
五、精彩纷呈的非洲挽歌谚语
索因卡是出色的语言大师。他的创作特别注重吸收西非民族各个阶层、各种行业的人的口语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将英语与约鲁巴的谚语、俗语、诗歌、唱词等传统语言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既风趣幽默又寓意深刻,既轻松愉快又富于节奏和韵律,营造了一个具有非洲特色、富于传统审美的精彩语言世界。索因卡借助丰富的非洲民间语言文学,通过生动幽默的对话和独白,成功地在戏剧作品中刻画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人格的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活动。
挽歌是非洲民间戏剧常用的一种语言形式。 索因卡的许多剧本都出现有唱挽歌的场景。他用诗歌吟唱来激发剧中人物的热情。在《狮子与宝石》中,为了让拉昆来在哑剧中扮演西方摄影师来访的角色,姑娘们唱歌跳舞来激发他。她们开始合唱“你和他的穿着一样,你长得像他,你们讲一样的话,你和他一样想法,你们拉各斯的动作——一样笨拙。你能够扮演他”的自编歌曲,[2]54随后又围着拉昆来开始跳舞,并且快速地念诵者歌词,在激情热烈的气氛中,拉昆来只好答应扮演角色。
索因卡不仅用诗歌吟唱激发戏剧人物的热情,而且在许多剧本中为表达激烈、悲凉的气氛,营造更加浓烈的情感场景,大胆地运用挽歌。《沼泽地居民》中的乞丐经常独自吟唱只有曲调而没有明确歌词的挽歌,而且一边唱一边合着拍子点头。在《森林之舞》中,第一幕结尾,当戏剧情节推进到“死者欢迎会”即将开始时,场外的打击乐和鼓乐此起彼伏。鼓声始终伴随着唱挽歌者。唱挽歌者伴随着音乐和舞蹈进场,直接以吟唱的方式与阿格博列科进行对话,吟唱了三段挽歌。《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自杀仪式更是从头至尾都弥漫着洪亮感伤、蕴含诗性的挽歌吟唱,明显加重了剧本的悲剧色彩。艾勒辛在举行自杀仪式前跳的一段告别舞与合唱队不断吟唱的诗性、感伤、洪亮的挽歌共同加重了剧本的悲剧色彩。自杀仪式即将举行,走唱说书人敦促众女人开唱挽歌为艾雷辛送行。在《路》中,索因卡描绘道路很危险,车祸随时发生,路神随时吞噬路人的生命,以至路上悲怆的挽歌不断响起,集聚在教授经营的车祸商店的各色人等也不时地哼唱挽歌,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头破血流的流浪汉不断走进商店,互相搀扶的乘客招待员像败兵似的扑倒在商店。挽歌起到了很好的渲染气氛的作用。《路》还穿插了大量低调、沉闷的歌曲及挽歌,致使情节谎诞,气氛阴沉,成为索因卡最晦涩、最难懂的一部作品。
谚语是约鲁巴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约鲁巴人认为,谚语是语言的快马,可以帮助一个人克服交谈障碍。为了揭示人物的性格或身份特征,使剧本的语言更加生动幽默,索因卡常常在剧中人物对话的某些关键之处使用一些民族方言的词汇,点缀上几句谚语和格言。《森林之舞》引用了大量极具哲理意味的约鲁巴谚语,被人们称之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阿格博列科最喜欢说谚语,他一开口说话,总是满口“真可谓至理名言也”。例如:“虱子有家就不会趴在狗背上”; “年轻人保持沉默是多么的谦逊”;[2]178“因为鸡蛋孵出小鸡那天天下着雨,因此那只傻乎乎的小鸡就发誓说自己是一条鱼”,[2]179“最后一个葫芦没有打破前,我们先别提干旱”,[6]170-171“朝下看的眼睛当然能看见鼻子;伸到罐子底的手才能捞到最大的蜗牛;天上不长草,如果大地因此而把天称作荒地,它就再也喝不到牛奶了;蛇不像人长着两条腿,也不像蜈蚣长着一百只脚”,[8]134等等。在《狮子与宝石》中,健谈人物拉昆来首先以谚语“砂锅对火说的话”给出了戏剧的主要内容。“砂锅对火说的话”来自尼日利亚的一句谚语——fire-tickling-the-pot(火给锅挠痒痒)。这个谚语传授的是坚韧、行动、勇气以及经久不衰的坚持不懈的品质,拉昆来使用谚语却并未达成自己的愿望,形成戏剧的讽刺效果。希迪以“我是闪闪发光的宝石,他是只剩下后腿的狮子”的谚语表达了她对巴罗卡的完全否定。约鲁巴谚语中的“狮子的赞誉称号”是“无需刀刃的解剖大师”之意,巴罗卡的阴险狡诈证实了“狮子”精湛的猎食技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涉及严肃的玄学问题,其主题可以用一句流行的约鲁巴言谚语“如果一个负担不服从于尘世的或天堂式的解脱,那么总有一条道路围绕着它”来囊括。换句话说,伊亚洛札担忧的是艾雷辛对自己施加的威胁,因为约鲁巴文化用“前所未有的给自己创造的恐惧的东西”的谚语来表达人们预期的最坏情况。[9]96-112在解决因自我献祭仪式失败导致的复杂冲突中,注入人物对话中的谚语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
六、寓意多重的约鲁巴面具艺术
非洲的假面戏是世界最丰富多彩和最有吸引力的表演艺术之一。假面戏所起的作用是让来自想象世界的神灵现身人间,假面戏离不开面具。古代非洲面具主要用于一种严肃的宗教祭祀仪式,戴面具的人不能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非洲人相信,行动着的面具就是祖先或神灵的再现。氏族首领主持本部落的成年、祈雨、巫医、播种、收割、丧葬等重大仪式时,通常可以佩戴面具,因为面具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只要戴上面具就可以让神灵为族人服务。约鲁巴面具极具复杂与含混的象征,具有使弱者改头换面的功能和双重的服务于善恶目的的功能。索因卡的戏剧创作正是产生于具有多重特质的意象与象征般的雕塑面具与雕刻者群体。他在舞台上通过本土的面具雕塑,尤其是约鲁巴面具来演绎附身之舞中神与祖先在生者世界的显灵,戏剧化地呈现人的灵魂实质的延续。
在索因卡的戏剧作品中,面具是神仙与幽灵借以在现实世界现身的媒介,尤其是在为神灵附身之舞特设的仪式上。当灵魂附体发生时,约鲁巴人相信神灵是真实而可被感知地现身了。舞者自己的灵魂则暂时让位,有可能是短暂的离开或者是被搁置,面具的灵魂占据了身体。当面具佩戴者屈服于神的灵魂时,往往能表现出超过自己所具有的能力。
在《森林之舞》里的“欢迎之舞”中,带着面具的人们被不同的神灵附身,宣告新尼日利亚国家的命运。例如,掌之神预见了仇恨、摩擦与最终的兵刃相见。这个被预见的战乱被10年后(1970年)的尼日利亚内战所证实。除去面具后,神灵离开,人回到常态,再也无法拥有预言之神力,也不再记得自己曾说过的话。《森林之舞》中戴着面具、被神灵附身的人以神灵之音说话是典型的神显灵和神变人的现象,在结尾出现的假面舞蹈中,众多神灵互相追逐,让半生半死的孩子得到解脱,给人带来轻松宽慰之感。
在《路》中,索因卡用“埃冈冈”(egungun)来指在被神灵附身的各个时候成为一体的面具与面具佩带者。传统的约鲁巴埃冈冈和被附体的状态只能在节日庆典上执以正确的仪轨时才能出现,并伴有传达关键辞义的鼓点来营造出整个仪式的规模与地位。面具只有施以正确的礼仪才能对人友善,除了主祭司以外,面具下的舞者的身份是不允许被任何人知道的。靠近仪式中的埃冈冈被认为是危险的,如果没有正确的仪轨、合适的时间、严格的措施及祭司的主持,要组织一场面具舞来召唤神灵附身是不可想象的,而《路》中所发生的恰与上述的一切相反,其后果可想而知。在戏剧开始时,穆拉诺在年度司机节上扮演神欧根而处于被附身的状态时,被卡车司机柯托努打倒击晕。柯托努和他的同伴把穆拉诺藏在卡车后面,瞒过愤怒的祭拜者,把车开到城里。这就是为什么教授找到柯托努并把他当作搭档的原因,其目的是从柯托努那儿学到身体消失转变为支撑所有存在形式的原始能量的终极秘密。
索因卡在《路》的序言中解释说,“假面舞是转化的运动,用在戏剧中作为死亡的视觉悬念”,[10]44-49哑巴穆拉诺在剧中就是死亡悬念的载体。他起到了悬置时间与死亡的作用。教授扣留穆拉诺是希望当哑巴能说话,以便他能发现转化的秘密,因为穆拉诺被击倒时神欧根正附体在他的身上,而神灵实际上已现身。处于既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些许生迹的状态下的穆拉诺已获得了教授所渴求的存在论知识,却不能告诉生者世界的任何人。当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时,教授在没有正确的仪轨、合适的时间、严格的措施及祭司的主持的状况下,试图进行面具舞召唤其附身,结果间接的导致他自己的死亡。这些事件再一次显示了约鲁巴面具作为人与神之间交流往来的媒介的力量。在《路》的结尾处出现的假面舞蹈中,“先知”教授昏醉,小东京在狂乱中把他捅死,给人带来一种末日来临的恐惧感。
由此可见,约鲁巴面具是索因卡戏剧与非洲传统联系的证明。在《沼泽居民》中,伊各维苏在村中保留一个面具作为维系传统的具体象征,而他生活在城市中的兄弟则完全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索因卡通过本土的面具雕塑,尤其是约鲁巴面具让附身之舞中神与祖先在现实世界的显灵,戏剧化地呈现剧中人物的灵魂实质的延续,成功地制造了剧中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综上所述,索因卡的文学创作动力始终是约鲁巴族的传统文化。有学者称,“索因卡是带着热带泥土的芬芳和古老的非洲精神,急剧跃升到现代艺术殿堂的非洲大陆的第一流作家”,[11]22-27在渥雷·索因卡的作品中非洲传统因素是一大母题,尽管他的教育背景与西方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始终愿意以约鲁巴族的文化为主体来进行创作,他用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创作出来富有民族特色的戏剧。随着西方殖民的侵入,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慢慢地在非洲大陆扎根,而非洲传统的本土文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索因卡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非洲传统文化因素,让世界的人都看到非洲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目的在于促进非洲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索因卡在戏剧作品中以诗化语言讲述约鲁巴人的宗教仪式、历史文化和民族格言,成为非洲文化的代言人。
[1]张荣建:黑非洲文学创作中的英语变体[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3).
[2][尼日利亚]渥莱·索因卡.狮子与宝石[M].邵殿生,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3] Soyinka.The Fourth Stage: Through the Mysteries of Ogun to the Origin of Yoraba Tragedy[J].Art, Dialogue and Outrag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London: Methuen, 1988.
[4] 贝岭,徐兰婷.与沃· 索因卡对话[J].倾向,1996(6).
[5] [英]杰弗里·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M].张治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6] 索因卡.狮子与宝石[M].邵殿生,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7] Zodwa Motsa.MusicanddramaticperformanceinWoleSoyinka’splays,Muziki[J].JournalofMusicResearchinAfrica,2007.
[8] 渥莱·索因卡.痴心与浊水.[M].沈静,石羽山,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9] M.B.Omigbule.Proverbs in Wole Soyinka’s Construction of Paradox inTheLionandTheJewelandDeathandTheKing’sHorseman,JLS/TLW29(1) [J].March,2013.
[10] Gilbert Tarka Fai.SoyinkaandYorubaSculpture:MasksofDeificationandSymbolism[J].RupkathaJournal, Vol 2, No 1(1998).
[11]蹇昌槐,蒋家国.非洲剧坛的普罗米修斯——索因卡[J].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责任编辑:立 早
On African Tradition Elements Embodied in Soyinka’s Plays
CHEN Meng
(ChineseDepartmentofHuizhouUniversity,Huizhou,Guangdong516007,China)
Nigeria writer Soyinka accep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us rituals, totem worship and folk dancing of Yoruba tribe culture and art heritage at his early age.The brigh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is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Soyinka’s creation.Africa sacred fickle Ogun God, sacrificial ceremony, strange complex cyclic samsara are best embodied in his works.Africa traditional art practices, such as music and dance, mime, go sing elegy storytelling and religious ceremony,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his works.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ference to traditional art brought Soyinka’s works rational factors distinct religious color, rich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strong and unique language style.
Soyinka; African tradition; religion; mythology; folk art
2016-05-11
陈梦(1971—) ,女,湖南祁东人,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惠州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DXK1405);2014年度重点重大研究培育项目“索因卡戏剧创作中的非洲传统元素”(编号: HZUX201423)阶段性成果。
I437.073
A
1001-5981(2016)06-01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