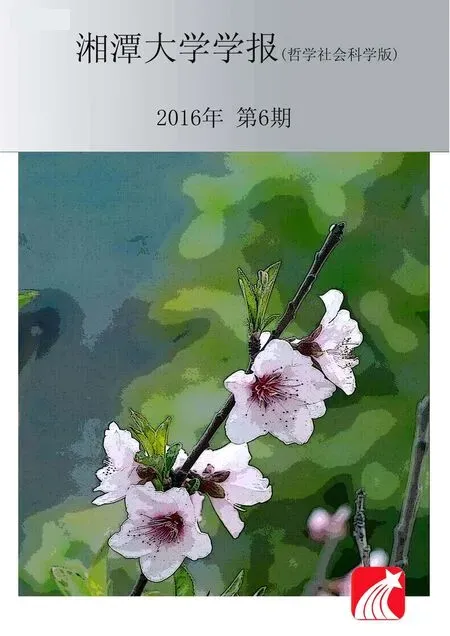《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口述戏剧史研究*
郑劭荣
(长沙理工大学 中文系,湖南 长沙 410076)
《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口述戏剧史研究*
郑劭荣
(长沙理工大学 中文系,湖南 长沙 410076)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整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戏曲家回忆录。著作采取口述笔录与个人传记相结合的写法,按照学科理论来审视,属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范畴。述作者以科学而独到的实践方式,在口述访谈、著述体例及戏曲的口头述录等方面颇具开创性,堪称“口述戏剧史”的经典之作。该著对于研究梅兰芳的生命史、演剧史以及中国戏曲史均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新时期的研究应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助推现代口述戏剧史的探索与发展。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口述戏剧史;史料价值
中国戏曲具有深厚悠久的口头传统,从一定程度而言,如果撇开口述戏剧史,我国的戏曲史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戏剧史。21世纪以来,在戏曲研究领域,口述证据倍受研究者的重视,口述史作为戏曲研究的一种新视野、新方法,正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相关著述与课题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现代意义的口述戏剧史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国伊始,戏曲改革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演员,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政治上的明确肯定,他们的从艺经验与表演体会备受珍视,纷纷以口述笔录的方式记载下来,产生了一批个人回忆录和传记。这类著作一般由艺人口述,提供口述史料或其他材料,再由专人加以记录整理。据统计,1950年代、1960年代出版的此类作品有10余部,其中以京、昆艺术名家的口述传记居多。在同类著述中,《舞台生活四十年》格外引人瞩目,不仅缘于传主梅兰芳在剧坛上的崇高地位及著作所富含的戏曲美学思想,还在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戏曲界首部个人口述回忆录,堪称“口述戏剧史”的经典之作,梨园界的活档案,其研究方法与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
一、《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口述戏剧史实践
20世纪30年代,在朋友的提议下,梅兰芳萌生了撰写个人回忆录的想法,当时因“工作重点还放在编剧和演出上,而且在艺术方面也还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没有时间做这件事”。[1]1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黄裳约请梅兰芳写自传式的回忆录(另一说法是,黄裳只是衔命催稿,《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汇报》连载实出自柯灵的倡议[2]),赴苏州找梅的秘书许姬传商谈写稿之事,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四十年》。其后,梅兰芳又得到冯幼伟、吴震修、李释戡、许伯明等“梅党”的鼓励及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的支持,1950年6月,正式启动回忆录的撰写。其写作方式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写成初稿,寄给许氏在上海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报馆发表。[1]2按照写作计划,以记述梅兰芳的艺术为主,生活次之。《文汇报》自1950年10月16日开始连载,共197天。集辑成书后,第一、二集分别于1952年、1954年出版。几经周折,第三集于1981年付梓。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现场速记而加以整理写成的“回忆录”,这种“回忆录”算不算口述史?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3]2这里强调以录音访谈作为口述史的必要前提。我国早期口述史家钟少华提出口述史书的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4]持不同意见者认为:“是否使用录音机不应该成为判断是否是口述历史的依据,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5]6此论甚是。在笔者看来,《舞台生活四十年》虽然没有可作为查证的录音、录像为凭据,但完全可以归为口述史学实践的范畴。从内容属性看,该著是“对当事人记忆的记录”,梅兰芳在写作计划中特地强调“以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为主”;就成书而言,采取了“口述者与访谈者合作互动、共同完成”的写作方式,亦相当符合现代口述史操作流程。实际上,目前戏曲研究者不仅认同其口述史性质,而且对其学术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6]
20世纪50年代,口述史学尚未进入国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口述史的“暗合”之作,这恰恰体现出述作者的创造性和匠心独具。该著是梅兰芳口述的个人“回忆录”,但他不是唯一的“口述”者,述作者融入一种近似大口述、大记忆的历史思维,使得梅兰芳的“回忆”具有浓郁的历史底色与群体特征。记忆的帷幕其实不是由梅兰芳开启的,而是他的胞姑母秦稚芬——梅巧玲最小的闺女,一位七十开外的老人。借助这位家族长者的讲述,梅兰芳首先追忆了其颇具悲情色彩的幼年生活;而其祖父梅巧玲、父亲梅竹芬的经历则由梅兰芳的祖母转述。梅兰芳显然十分看重这段历史,追述梅巧玲苦难的童年及其无比苦楚的学艺史,不无自我励志之意,亦可管窥旧时优伶真实的生存状态。这种真实性来自梅氏家族两位老人的“口述证据”,她们是知情者,见证人,无疑使历史变得愈发真实可感、鲜活动人。梅巧玲及其主办的“四喜班”是京剧史上绕不开的史实,其中有些重要的戏曲事件一直云遮雾罩,如,晚清“国丧”期间朝廷如何“禁戏”?“四喜班”如何两度挺过“国丧”带来的生存危机?萧长华与“四喜班”渊源深厚,又长期担任“喜连成”教习,梅兰芳特意请他代为口述这段旧事,同时还叙述了昆剧名丑杨三的惊人演技。梅兰芳作为京剧鼎盛时代开宗立派的艺术家,虽然熟知梨园掌故,因年代久远和囿于个人闻见,依然有许多不为所知的故实。好在梅、许在行内结交广泛,要找到知情者并不困难。除了萧长华参与口述外,还有姜妙香、王瑶卿、徐兰沅等大批老辈艺人。实际上,口述者远远不止这几人,仅许姬传便“先后访问了五十多人”。[7]不难看出,《舞台生活四十年》所构建的历史不仅仅是梅兰芳个人的艺术人生史,也不只是梅兰芳在自说自话,而是基于群体共同口述下的对时代的整体记忆。这不能不说是口述史方法的有益尝试。
比较契合现代口述史做法的是,《舞台生活四十年》自觉运用了“口述—文献”互证法。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口述历史不应该以孤证自满,研究者必须找出可用的资料来印证文字和口述两种历史证据。”[3]113唐德刚发表过类似意见:“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8]2《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述作者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异常重视。梅兰芳为人行事谨慎,著述亦如此,强调“要用第一手资料,口头说的和书本记载,详细核对,务求真实”。按照这一要求,许姬传多方搜集图书馆、报刊资料。《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谢蔚明在北京专门负责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梅的另一秘书言简斋提供了晚清社会风貌与习俗方面的资料。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文献的白纸黑字并非就是“铁证”,有时口耳相传的活史料反而更为可信,尤其在考察梨园行这样的社会亚群体时,身处圈外的文人在文字上难免以讹传讹。梅兰芳对此深有感触:“关于梨园旧事,记载固然不少,因为多半并非圈内人的叙述,往往张冠李戴,传闻失实。许多重要的资料,都藏在几位老先生的肚子里。”[9]17梅巧玲在演艺界向来以重信义、讲情谊而为时人所称道,这主要缘于他两次慷慨助人的义举“焚券”与“赎当”,但是,这两件事中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始终没有坐实,即受助者究竟是谁?尽管文人有载录,但语焉不详。后来经梅兰芳口述及相关人员提供的资料,最终澄清了这桩历史疑案。再如,关于“四喜班”在“国丧”期间的遭遇,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有简略的记载:“孝贞国卹,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慧仙举火。”这一史料的可靠性与详细程度显然不如当事人萧长华的口述。
口述历史的著述形态有着特定的规范。《舞台生活四十年》采取对话语录体表述形式,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问一答式的访谈录,它在口述正文之间插入不少现场描述,展现口述时的情景和气氛,使人物谈话具有鲜明的立体感。述作者的初衷在于,“随时插叙一点他(梅兰芳)从1950年开始述作以后的经历。这是为了不致因专谈旧事,使读者阅读时感到和生活在新时代里的梅先生离开得太远。”[10]1这种安排给读者传达出强烈的访谈现场感,是颇富创意的一种口述体例。在整个访谈期间,梅兰芳异常忙碌,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演出,期间还赴汉口演出二个月,通常只能利用表演间隙、睡前或休息日来口述。细读全书,述作者对访谈过程及背景的描述非常细致、生动,注意记录每次访谈的时间、地点,一些细节也很具体,诸如访谈场景、口述者的神态举止及情感的细微变化。如首次谈话的情景:“那天晚上,晚风透进了纱窗,把一天的暑气都吹散了,使我们恢复了旅途的疲劳,感到头目清明。我们两个人对坐在沙发上,沏了一壶东鸿记的茉莉双薰慢慢地喝着。”[9]1仿佛是老友之间的闲谈、叙旧,一下子将读者带入现场,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再如:“梅先生洗了一个澡,披着睡衣点着一支烟卷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对着书桌上放的一盏绿色的台灯,若有所思。”“我在皮包里取出了跟着我工作快有两年,老不得休息的那支自来水笔,再在书桌上铺上一张白纸,等他抽完了那半支烟卷,这才开始说他对汉口的回忆。”[11]205这种“忙里偷闲”式的插叙不仅营造了亲临其境之感,而且真切地展现了梅兰芳优雅的生活情调;同时,记录者以见证人的身份站在读者面前,更增强了口述的真实感。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口述正文部分,记录者添加了大量按语,这种体例可谓别出心裁,也体现出编者严谨的写作态度。书中“按”有两大主要作用:其一,转述他人的口述。在该书中,除了梅兰芳的讲述,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许姬传的亲历亲闻,或者是其他人的口述资料。如,民国六七年间天津昆曲“同期”曲会、民国五年梅先生演“闹学”等史实便来自许姬传的耳闻目睹,此外,还附载了茹富兰、朱传铭、孙玉声等大批艺人珍贵的口述史料。这些材料自然应与传主的口述相区别,以示不掠人之美。其二,补充、深化传主的口述。全书涉及的戏剧史实、梨园掌故及社会风俗相当丰富,梅兰芳的口述很难面面俱到,一些重要史料有时一语带过,很有必要交代完整。此类“按”介绍了不少戏剧常识,如北京戏馆戏台、科班的演唱性质、“花脸”的分类、传奇“副末登场”等,有时是补充交代梅兰芳表演及生活中的一些轶事。这些内容既充实了史料,又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与口述正文部分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旧时戏曲的表演技艺主要依靠师徒之间口耳相传,见于文献载录的历来不多。“过去有关戏剧的著作,大部分是以谈音韵、唱法、纪录工尺谱——简谱为主,至于包括全部表演的记载是不多的。”[12]148舞台表演是梅兰芳口述的核心内容,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谈剧目的编排和演出。在音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口述者如何“讲述”?记录者如何还原和表达这种“讲述”? 在这方面,《舞台生活四十年》亦作了非常宝贵的探索。在传统舞台上,剧目演出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演员的唱、念、做、表,其技艺的“经验之谈”是戏曲艺术中最具传承价值的部分。梅兰芳采取梨园界最为熟悉的“说戏”方式,依据剧中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详细介绍唱词、念白、做工、表情。身段和唱念比较好解释,唯有表情是最难说清楚的。他巧妙地借助丰富的肢体语言和细节展示,生动地阐释剧中人的情感体验。一个艺术家要真切地传达出自身精微的艺术体验,语言往往会显得苍白无力,而以形体示范为口述的辅助手段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不足。在记录身段表演和舞台部位时,梅先生往往先亲自示范一两遍,再由邹慧兰代做,进一步推敲手、眼、身、步的动作,最后用文字记录身段部位。[7]可贵的是,记录者对这一过程均作了细腻的描述,如:“梅先生说着就站起来,比了几个姿势。他不是快六十岁了吗?你看他手的指法,腰的摆动,脚步的细碎,眼神的运用,处处都还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模样。”[11]147“说戏”是我国戏曲教育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戏曲口述史的重要形式。一个资深演员不仅要善于“演”,而且要能“说”,解说剧情,带领唱念,言传身教,才能使戏曲艺术薪火相传。谭鑫培的“说戏”能力便令人叹为观止,他采取“六场通头”的方式,非一般人能办到。[11]255这些内容对当今戏曲艺术的传承教育及口述访谈不无有益启示。
口述史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有时难以做到准确可靠,追溯的年代越久,事实就越易模糊失真。梅兰芳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追忆往事尤显艰难。他的做法是旁搜博采,多方求证,借助文献资料、图片与戏单等来激活记忆,追寻往事。如戏单便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记录者在书中多次谈到这一点,每逢回忆一些演出细节,“就都要根据这本旧戏单追索往事了。他看到那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张戏单,笑着对我说。”[9]145“说到这里,我把昨天找出来的一张民国七年曹宅堂会的旧戏单递给梅先生看。”[9]168“记忆的不可靠性”一直是“口述史”为人所诟病的焦点。口述者出于种种顾虑,往往存在有选择性的记忆和失忆,从而影响和制约着口述史的“客观性”。这也是人们对这部自传颇有微词之处。譬如,晚清北京“堂子”及梅兰芳的“歌郎”生涯,在梅的自我叙述中始终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类“戏曲史”的“盲点”。[13]221这提醒我们,作为口述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口述者已经讲了什么,而且应该考察口述的历史语境、口述者的身份认同及其戏剧史观等深层次问题。考虑到本文主要是阐述这部“口述”著作的实践技术,上述问题暂且搁置。
二、《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口述史料价值
在戏曲研究领域,凡是卓有成就的学者无不重视最基本的史料收集和整理。然而,长期以来,受到推崇的往往只是文献史料,包括个人回忆录在内的口述史料常常被忽视。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的蓬勃兴起,极大地扩展了戏曲学人的视野,丰富了戏曲研究手段;尤其是研究民间戏剧,口述史料的采集与阐释成为重中之重。这种新的学术趋势,促使我们重新检视这部回忆录的戏曲史料价值。
作为一部个人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研究梅兰芳生平最直接的证据材料。梅兰芳一生跨越了几个时代,从晚清到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人生经历十分丰富,除了舞台演出外,举凡家世出身、拜师求艺、生平交游、绘画养鸽等内容构成了我们认识梅兰芳的多棱镜。譬如,考察梅兰芳的生命史,其实最难以追溯的是其祖辈及梅氏幼年的事迹。第一章“梅家旧事”借其胞姑母及祖母之回忆,比较清晰地展现了梅巧玲至梅雨田、梅竹芬两代人的家庭史,并首次披露梅兰芳自童年至青年的成长蜕变:“就说他幼年的相貌,也很平常。面部的构造是一个小圆脸。两只眼睛,因为眼皮老是下垂,眼神自然不能外露。见了人又不会说话。他那时的外形,我很直率地下他八个字的批语: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他从十八岁起,也真奇怪,相貌一天比一天好看,知识一天比一天开悟。到了二十开外,长得更‘水灵’了。”[9]9当然,这既可视为一种客观叙述,也可理解为是对后文关于其从艺生涯刻苦自励的叙事铺垫。单就史料价值而言,亦弥足珍贵,后人编撰梅兰芳的传记、年谱,《舞台生活四十年》往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相关性的参考资料。
京剧大概成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1917年这段时期,1917年至1938年左右趋于鼎盛。梅兰芳所叙述的“四十年”,恰好是中国京剧从成熟走向辉煌的时代。此时的剧坛朝气蓬勃,新戏层出不穷,舞台艺术精益求精,表演流派异彩纷呈,人才济济,特别是以梅兰芳为翘首的旦角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14]10京剧艺术从保守走向革新,新的剧坛格局渐次形成,梅兰芳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他与19世纪一大批京剧耆宿渊源深厚,如谭鑫培、王瑶卿、陈德霖、路三宝、梅雨田等,借助拜师求艺、演出观摩及同台表演等方式,梅兰芳传承了京剧艺术积淀百余年的精粹;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京剧全方位的变革探索,以旦角艺术创新为突破口,涉及服装、表演、道具、布景及剧目编排等方方面面的革新。除了表演实践,尤为可贵的是,他还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在戏曲美学与艺术方法论上具有很高的建树。[15]梅兰芳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当事人,他的记忆和叙述自然是书写京剧史的可靠材料。这方面的例证很多。脚色行当艺术是研究戏剧形态史的重点内容,按照传统唱法:“青衣专重唱工,对于表情、身段,是不甚讲究的。面部表情,大多是冷若冰霜。”“一直到前清末年,才起了变化。首先突破这一藩篱的是王瑶卿先生,他注意到表情与动作,演技方面,才有了新的发展。”[9]26梅兰芳作为京剧旦角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将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贴旦等表演技术有机融合,大大推进了旦行艺术的演化。研究京剧的变革史、演出史,离不开古装戏、时装戏等具体问题的讨论。梅兰芳是表演古装新戏、时装新戏的先行者,《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对这一变革作了专题叙述。1913年,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上海戏馆浓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对其触动颇大,回到北京后,“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这一种新思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年。”[11]1不久,即编创演出了以北京本地的实事新闻为素材的新戏《孽海波澜》,获得了初步成功。其后陆续排演了《牢狱鸳鸯》(穿老戏服的新戏)、《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穿时装的新戏)及古装新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
以往的剧目研究,更多地是从文学文献角度梳理、考辨其源流演化,至于剧目在舞台上的形态演变则少有深入探究;研究者大多因缺少亲身的艺术体验,论述容易流于表面化,难以真正揭示编创演出的内在规律。《舞台生活四十年》所提供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对于研究京剧史上经典名剧的形成演化极为宝贵,不仅能了解到梅兰芳主演剧目的台前幕后的故事,还可追踪一些骨子老戏的经典化过程。《霸王别姬》是梅派经典名剧之一,著作第三集以长达一章的篇幅陈说了该剧的编创演出史。这出戏最初名为《楚汉争》,编于1918年4月,由杨小楼、尚小云等主演。全剧四本,分两天演完。梅兰芳看后感觉过场太多,戏显得“瘟”。1921年下半年,杨小楼与梅兰芳合作,决定重编该剧,定名《霸王别姬》,由齐如山执笔撰写剧本初稿,依然分两天演完。未料吴震修看完剧本后,认为全剧分头二本两天演完不妥,必须改成一天演完。由此还与齐如山产生激烈争议。最终由吴氏将初稿的20多场压缩至20场。1922年正月十九日正式上演,但场次安排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重头戏“霸王打阵”过于松散、凌乱,主演杨小楼相当吃力。几天后,再次演出,全剧删减至十四五场,初期的《霸王别姬》暂时定型。经过逐渐修改,1936年秋,全剧已减到12场。1949年后成为8场。梅兰芳的“虞姬舞剑”是该剧另一重头戏。排演之前,为创编这一段剑舞,梅兰芳专门请武术教师教授太极拳和太极剑,融合《群英会》舞剑与《卖马》耍锏的演技,形成其表演路数。然而,要创新演法绝非易事,有观众挖苦道:“虞姬宝剑如叔宝之锏,嫦娥花锄抡如虹霓之枪。”应该说,梅兰芳对戏曲中“舞剑”的性质及其与音乐的配合均有独到的创见。殊为难得的是,1955年专门拍摄了梅先生的这段“舞剑”,并用文字详细记录了这段舞蹈的部位、动作,为后世留存了一段难得的身段谱。
“花雅之争”是近世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自清中叶以来,在北京剧坛上,随着弋腔、秦腔、皮黄轮番冲击,晚清至民国期间,曾经雄踞剧坛翘首的昆曲气息奄奄。关于这段历史,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徽班进京之后,昆剧即开始退出首都剧坛霸主地位,而渐由皮黄(京剧前身)取而代之。[16]192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先看看梅兰芳的口述:“清宫所演的剧目,在光绪九年以前,还是以昆曲为主体。咸丰十年,一度从各大徽班挑选了三十二人进宫演奏,这里面有几位老艺人是专工皮黄的,他们看到宫里一般还是很爱昆曲,所以不久就自动告退了。清宫对于京剧的认识,大概一直到了光绪十年,在杨隆寿、杨月楼、孙菊仙、谭鑫培、时小福、王楞仙、陈德霖、汪桂芬、杨小楼……这些老先生陆续进宫演唱以后,才引起重视的。”[17]1-2很显然,昆曲在宫廷的正统地位并未因徽班进京而撼动,京剧受到重视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大概在梅兰芳出身前十年左右。换言之,花、雅之间的消长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昆曲在清宫内的衰退远比民间滞后。北京昆曲“由全盛时期渐渐衰落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是在民国二三年间的事情。[9]166谈及花、雅的关系,以往的戏曲史只强调对立,而忽视了两者的融合。实际上,四大徽班进京后,“并没有歧视昆曲的意思,相反地还是很推重它,向它学习,尽量吸取它的精华部分,运用到皮黄里来。只要看四大徽班的演员们……哪一个不是唱昆曲的能手呢?”[11]116由此可见昆曲在花部艺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对京剧艺术的深远影响。此外,还解决了近代剧坛上的一些疑案。高阳昆曲是昆曲流传到北方后的一个支流,历史上的高阳戏班为何会有昆弋?梅兰芳的口述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前清末年,有一位酷爱戏曲的老醇亲王举办了一个小恩荣科班,专教弋腔,附带教昆曲,学戏的子弟大多来自这位亲王的圈地高阳。后来科班解散,这批学生返回故籍,带去了昆弋。昆曲、弋阳腔究竟是如何逐步式微的?文献史料亦大多语焉不详,《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昆曲和弋阳腔的梗概”弥补了这一缺憾。尤其是关于苏州剧坛的史料弥足珍贵。如昆曲老艺人沈盘生口述了旧时苏州昆班和弋腔班的情形及全福班从光绪至民国十年的活动史,朱传铭讲述昆曲传习所的始末经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为研究南方末代昆曲提供了有力证据。梅兰芳所关注的不仅限于京剧,对地方戏也十分重视,有意识地多方搜访剧种资料。汉剧与京剧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他尤为留意对汉剧的了解。1951年4月,梅兰芳第五次赴汉口演出,专门向汉剧名家吴天保询问汉剧的组织、脚色体制、科班结构等,与京剧作对比后,梅兰芳认为:“汉剧跟京剧的确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京剧的产生,是混合了徽、汉两种地方戏,再吸取一部分昆曲的精华,这样组织成功的。”[11]216联想到早期京剧老生余三胜唱念常带“鄂音”,汉剧组织、内容与京剧十分接近,梅兰芳更确信了自己的上述判断。
戏曲的传承教育是戏曲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往的戏曲教学主要由戏班承担,采取师徒相授的个体教学方式。清朝末年,随着演出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教育机构——科班,学徒学艺与演出相结合,注重提升艺人的综合素养,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戏曲人才。与梅兰芳颇有渊源的科班是由叶春善操持的喜连成——北京城内最大、办学历史最为长久的科班。萧长华作为该科班的元勋,又是叶春善的亲家,对喜连成的来龙去脉了然如心。他详述了叶春善三十年办学史、科班的管理运作、办学精神、教学方法及办学成果等,这些都是难得的戏曲教育史料。在传统时代,梨园界十分注重师承,讲究师出有门。梅兰芳的第一位老师是吴菱仙,其后陆续请益过的师友有秦稚芬、胡二庚、梅雨田、陈德霖、王瑶卿、钱金福、李寿山、杨小楼、乔惠兰、谢昆泉、陈嘉樑、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等。除了介绍上述师友外,梅兰芳还谈到了幼年如何学艺,师傅如何教戏,自己如何学演青衣等。依据这些材料,可以勾勒出京剧梅派艺术完整、清晰的传承谱系。
剧场作为戏剧的载体和活动空间,是戏曲研究的重要对象。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文明的渐进,传统剧场趋于新变,至20世纪初,新型剧院开始形成。梅兰芳见证了这一变迁,他的口述有助于深入研究近代剧场的沿革流变。广和楼、广德楼是梅兰芳十几岁时经常演出之所,这是两座典型的清代茶园剧场。“广和楼旧景”主要讲述这个时期的舞台情形。20世纪后,随着戏曲改良的如火如荼,传统式茶园剧场向新式剧院转变。上海得风气之先,改良剧场丹桂第一台给初次赴沪的梅兰芳留下深刻印象,而北京的剧场相对守旧。《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这些记述成为学者们难得的剧场史料。[18]164第三集“‘承华社’时期”还集中口述了当时常见的戏台类型,如北京第一座西式剧场——真光剧场、紫禁城内戏台、会馆戏台、饭庄戏台、住宅院中戏台、住宅室内戏台、室内非正式戏台及院中搭棚、搭台等,这些戏台梅兰芳大都演出过,对其特点、形态了解十分具体细致,无疑是后世研究剧场的可靠依据。梅兰芳还熟知梨园行内的各种习俗和演出惯例,在其口述中经常有意识地加以介绍,如旧时戏班的演戏方式有“行戏”“义务戏”“元旦戏”“歇工戏”等,对“堂会戏”及其“赶场”经历的描述尤为详细。此外,在戏剧演出形态上,除了介绍各种表演技术,还涉及戏曲一些独特的演出形式,如“跳加官”“跳财神”“报开场”“老旦做亲”等。这些资料不仅有助于研究近代北京戏班的演出与运作,而且极具都市民俗研究价值。
结 语
整体而言,《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成功的口述实践之作,无论是其口述访谈、著述体例还是戏曲的口头述录等均富于开创性,它是研究梅兰芳生命史、演剧史及中国戏曲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该著的示范意义显而易见,在其影响下,五六十年代的梨园界仿佛进入了一个“回忆录”时代,徐凌云、华传浩、周信芳、侯喜瑞、盖叫天、周慕莲、徐兰沅等梨园名家的口述史先后面世,出现了一个口述戏剧史写作的小热潮。
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如何推进口述戏剧史学的创设与发展,这是我们重温《舞台生活四十年》时值得深思的问题。戏曲学界引进口述史研究,不是追捧和跟风当下流行的新理论、新方法,而是基于传统戏剧特殊的生存状态与戏曲学科未来发展的需要。口述史与戏曲有着内在的同构关系。戏曲属于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在艺在,艺随人走”,无论是表演技艺的活态传承还是舞台呈现,均以口述为主要实现方式。就学科发展而言,以往的戏剧史书写,主要倚重于文献、文物资料,而口述史料趋于边缘化。深入拓展戏曲研究,必应在发掘“新材料”上下功夫。口述史料属于戏曲传承人亲述的“活态”史料,既有其独立的研究价值,亦能填补文字记录的空白,弥补文献典籍的不足,必将在未来的戏剧史书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作为戏曲研究的新路径,口述戏剧史应在充分借鉴现代口述史理论与学术规范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戏曲的口述传统,研究戏曲的传承主体、口传过程与方式,揭示口述史料与艺人“记忆·表演·传承”的内在关联,尤其要突出三点:其一,传承人(包括戏班)记忆、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规律、机制,舞台表演与口述传承的关系;其二,不同口述者、传承人的口述史料的互证及口述文本的恒稳与变异;其三,口传戏剧史料的凝固化和书面转型。口述戏剧史作为大戏剧史的有机构成,不仅仅视为一种收集材料的方法和资料渊薮,还要重视其本体价值,将传承人的个体研究合观共视,有机融入戏曲史的长河之中。这里所讲的个体,既包括梅兰芳式的艺术宗匠,也包括民间的草根艺人,直接倾听他们对戏曲历史、技艺及生命的诉说。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中国的戏曲史会变得更丰富、民主和真实。
[1]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
[2] 谢蔚明.旁证柯灵黄裳笔墨官司——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面世经过[J].世纪行.2000(11).
[3] [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 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4] 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5]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 刘祯.论梅兰芳表演理论及体系——《舞台生活四十年》个案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5(1).
[7] 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J].戏曲艺术.1982(1).
[8] 唐德刚.史学与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 梅兰芳,述 .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
[10]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编写说明.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
[11]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
[12] 梅兰芳.重视舞台艺术生活的文字记录工作[M]//梅兰芳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13] 幺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4]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上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15] 唐湜.读《舞台生活四十年》[N].戏剧报.1955-03-17.
[16] 康保成,黎国韬.晚清北京剧坛的昆乱消长与昆乱交融——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M]//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上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17]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18] 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万莲姣
FortyYears’LifeonStageand Oral History Research
ZHENG Shao-rong
(TheDepartmentofChineseLiteratureandLanguage,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Changsha,Hunan410076China)
FortyYears’LifeonStageis the first dramatist memoirs dictated by Mei Lanfang, recorded by Xu Jichua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works applied the method of oral record with biography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discipline theory to examine,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The author takes the science and original practice way,which is groundbreaking classics of oral history in the oral interview, writing style and opera oral record.The book has a very high historical value in the research of Mei Lanfang , his performance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Research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Learn from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and facilitate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oral history.
Mei Lanfang;FortyYears’LifeonStage;oral history; historical value
2016-07-10
郑劭荣(1971—),男,湖南隆回人,文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口述戏剧史料学研究”(项目编号: 15BZW075)。
I206
A
1001-5981(2016)06-01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