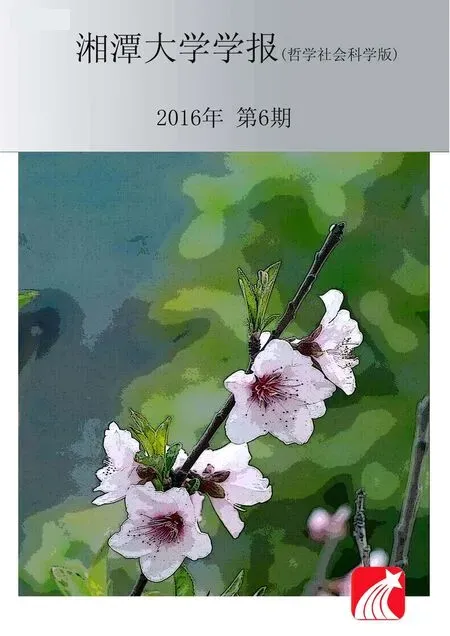“左眼”看中国的三种视像
——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文本的互文性分析*
阎 伟,谈微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中国经验与文论建构”专题研究(笔谈,3篇)
“左眼”看中国的三种视像
——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文本的互文性分析*
阎 伟,谈微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欧洲左翼知识分子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分别于1955、1972和1974年访问中国,并各自留下亲历中国的记录文本。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中国行不同的在场遭遇,他们关于中国的感受见解大相径庭。萨特的“红色中国”观、安东尼奥尼的“两种表情”中国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负片(Negative Film)中国”观,除了分别显示他们“积极介入”的存在主义文学观、“积极疏离”的间离理论和“判断悬置”的现象学方法外,还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观察中国时视点转化历时化的过程。他们中国行的三种视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国立场嬗变,也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萨特; 安东尼奥尼; 罗兰·巴尔特; 左翼知识分子; 中国观
1955年10月底,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结束了在中国为期的45天访问,随后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MesimpressionssurlaChinenouvelle(MyImpressionsoftheNewChina)一文,后来他又在《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上发表了《我看到的中国》LaChinequej’aivue(TheChinaISaw的专访文章,进一步说明自己中国行的感受[1]317。1972年5月,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开始了为期22天的纪录电影laChine,en1972《中国,在1972》(以下简称《中国》)的拍摄工作。1973年,《中国》在欧洲播出,随后在中国遭受强烈批判。三十年后的2004年,该片才在中国公开上映。1974年4月,法国哲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与法国《原样》杂志TelQuel(太凯尔)周围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为期24天的中国行。回国后,巴尔特仅写了一篇文章Alors,laChine《那么,是中国吗?》对中国再无评论。*《罗兰·巴尔特传》中曾有记录:一年以后,鲁瓦(C.Roy)接受《世界报》的邀请谈他对巴尔特的看法时,他也提到这次奇特的旅行:“我们奇怪地注意到,这个温柔、耐心、贪婪的‘揭露狂’最近在谈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时仿佛没有了牙齿。”参见该书第204页。直到2009年,他的三卷本《中国行日记》CarnetsDuVoyageEnChine在法国公开出版,并于2012年译成中文。
以上三位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都亲历中国,并即时写出中国行文本。虽然他们的中国行文本形式并不相同,其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也不一样,但都关注社会主义中国,在各自的叙述中,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判断。在评价新中国某些相似的问题与现象上,形成了可堪比照的视域。因此,本文将互文性阅读三人的中国行文本,研究其文本中构建的中国观,并历时性地梳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国立场的嬗变。同时,描述当时的中国对他们中国行文本的反应与态度,并以他者眼光为镜像,形成对自我认识的反思。
一、“访问者”、“偷窥者”和“旁观者”——三人中国行目的及文本的叙事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特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积极的亲共立场,以“同路人”身份与法共、苏共保持良好关系,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1955年9月,萨特携其终生伴侣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以社会主义阵营内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国际统战对象的身份应邀访华,并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著名的西方左派活动家”。[2]299
1971年,意大利政府与中国刚刚建交后不久,就提出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特意强调将由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这位在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在1970年拍摄的《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Point中,表现出对激进学生运动的同情。中国政府考虑到安东尼奥尼既是世界顶级电影导演,又是意大利左翼共产党人,于是接受了这一请求。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法国共产党新派杂志《原样》表现出积极的亲中国立场,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并出版和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研究专著和文章。1974年,杂志社组织了包括巴尔特在内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与萨特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全程接待不同,巴尔特一行的访问费用由参加者自理。[3]2
中国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虽不是访谈,但全文以虚拟对话的形式,采用第一人称方式叙事,将其在中国的直接、正面的感受,以“访问者”/“我”的视角向“接待者”/“你”作信息反馈,全文具有向接待者汇报总结的性质。最具“读者意识”的介入作家萨特,成文之前就已明确了自己的受众和潜在读者:直接读者是促成此行的中国政府,而潜在读者就是他曾经接触过的中国大众。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文本更具有实录的性质。《中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以全称“我们”(观察者)的视角,向一个未知的“你”(观众)讲述一个“他”(中国)的故事。中国行的目的就是以摄像机为眼,向西方世界展示未知的中国,通过镜头去表现他心中的神秘中国和眼前的现实中国。因此,电影《中国》的受众指向主要是西方民众。一方面,他遵从接待方的意愿与要求,拍摄了当时中国的某些“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安东尼奥尼也像许多西方观众一样,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拍摄时“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或者任何他可能赋予象征意义的动作和细节”。[4]100为了获取这些“动作与细节”,他有时故意越界或违规,采用非常规手段,“闯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偷窥”式的拍摄。电影《中国》中的许多桥段,都表露着叙事者由恪守外交礼节的“访问者”、向无所不窥的“闯入者”或“偷窥者”的身份挪移。
巴尔特的《中国行日记》采取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以独白的方式叙述他在中国的见闻。这种独白式的日记不会预设读者,或者说,它的读者就是作者自己。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中国行的同时,又不断验证着他想像中的中国形象,形成讲述者对自己所接受信息的不断追问,以及对内心世界的深刻反思。巴尔特曾说,他是受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的影响,才决定到中国来的。[5]67然而,当巴尔特重走安东尼奥尼的线路时,他却看到这位在中国受到隆重接待的意大利电影导演,正在遭受缺席批判。*巴尔特的《中国行日记》中有多处记录,详见该书的第47、214、215和304页。面对中国这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巴尔特既不能以中国的方式、也不愿以安东尼奥尼的方式理解中国,他采取了一种近似“零度写作”的方式,冷静地记录他在中国的见闻,不做任何评价,以期达到对这种异质文化的客观观照。
因此,如果说萨特中国行文本的叙事主体是一个热情的“访问者”,那么安东尼奥尼的叙事主体就是一个积极的“偷窥者”,巴尔特的就是冷静的“旁观者”。
二、“让看”、“偷拍”和“斜视”——中国行文本中观察中国的方式
萨特访华时的活动内容完全由中国政府组织安排,按照预定的路线和日程考察。萨特一行参观了北京、沈阳、广州、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访问日程紧张而又充实,对于此行的收获,同行者波伏瓦提供了旁证,“他们没有把中国藏在身后,他们没有在几百个农舍上涂上色彩鲜艳的油漆,也没有给上千里的乡野披上伪装网;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国。”[6]28对于中国政府的周密接待和信息提供工作,他们既感到满意,又明显表露异议。萨特并不满足只听那些“都是一样事先构想好的话”,[6]28他试图绕过困难,扩大信息源,去接触更多的普通民众。对萨特的这种努力,波伏瓦居然有两种不一样的记录版本。在公开出版物《长征》一书中,她如此写道,“我的行动自由从未受到过阻拦。我随时都信马由缰地散步,多少次都无所谓。在北京,我们经常在没有中国人陪同的情况下外出。”[6]27而在她写给自己美国男友阿尔格伦(Nelson Ahlgren)的信中,却充满了抱怨,“……他们担心我们自己会走丢,又想让我们参观,所以他们一直陪着我们,到处跟着我们。尽管他们客气友好,但我们有时感到烦了。我们愿意在街上随便走走,但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马振骋的译本中,波伏瓦的语气更为激烈,“我们不总是嘻嘻哈哈的,由于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这些中国人既怕把我们丢了,又要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好好看,跟着我们寸步不离,无时无刻不是紧紧贴着我们,以致有时实在烦他们,尽管他们很殷勤周到。我们很少能够像我们爱好的那样在街上从从容容蹓达。换了您也会像萨特和我一样好几次失去冷静。”参见马振骋编译《波伏瓦给亚格伦的信选》(续六)之《听说访问中国,我就热血沸腾……》,《书城》, 1998年第10期,第31页。[7]657
1972年5月,意大利拍摄组抵达北京后,安东尼奥尼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拍摄计划,涉及北京、上海、新疆和海南岛等17个地方,预计时长半年。这同中方原先安排的日程计划相差很大。经过和中国官员整整3天的讨论,最终他选择了“妥协”,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8] 86-87尽管如此,他的拍摄仍然受到极大限制,电影《中国》开头的旁白交代, “很大一部分中国是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我们笑眯眯的导游让我们跟随他们严格规定的路线。”
事实上,安东尼奥尼并不想受制于严格规定的拍摄线路和对象。他充分发挥摄影师的专业特长,将摄影机眼睛的功能运用到极致,利用一切机会偷拍。为了达到“偷拍”目的与中国的随行人员斗智斗法,《中国》的旁白说明就有7处之多。安东尼奥尼是这样解释他的拍摄行为的,“在我拍摄纪录片《中国》时,不是去拍摄一个我想象中的中国,而是遵循双眼看到的现实。”[9] 36为了获取他眼中的真实,他并不满足于官方的“让看”/“摆拍”安排,而是做一个失礼的“偷窥者”,经常闯入到中国老百姓未经准备的日常生活层面,表现政治之外的普通人生存状态。他用一种未经修饰的、哪怕是“带有各种缺陷”的镜头,从对比和正反两个角度介绍中国当时的现实,从而形成了“安东尼奥尼式”的中国。[9] 36
1974年4月,罗兰·巴尔特一行走的也是一条预先设定的路线。虽然他们也受到了中国一些大学和作家的接待,但那是在既定计划之内。过于周到密集的安排,使得他们接触任何既定行程之外的中国人几乎不可能。“由于旅行社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3]160-161他对这种缺少“皱痕”、缺少“偶遇事件”的旅行表示不满,信息的极度重复、单一让他大失所望。他写道,“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信息的完全封闭,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最为惊人的是,这种封闭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条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这种封闭。”[3]256人们向他介绍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毫无变化。他对中国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语言的平面即能指方面,每天的单调重复使巴尔特感到厌倦消沉。面对这样的中国,巴尔特既没有采取“内在”的方式表示赞同,也不以“外在”方式去进行批评,而是采用了“斜视”的方法观察。他提出,“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目光。”[3]278
那么,何谓斜视的目光?所谓斜视,就是要注意被观察对象第一信息之外的附加信息的特殊观察方法。巴尔特解释说,“应该区分我在第一个级次与在第二个级次学到的东西。(这差不多就是‘斜视的目光’)”[3]289巴尔特将中国视作一个文本,以符号学的方法加以解读。中国像其他所有的文本一样,以等级方式存在,呈现出一种分级搭配的层次。在巴尔特看来,中国文本写了什么或展示什么?“这便是言语活动的第一等级”,随后中国文本如何被写或被看?“这便是第二层级”。在理解被观察者的活动中,来自第二等级的信息量尤其重要。在直接接受第一层级言语活动提供的信息同时,巴尔特更多地是绕到背后,观察这种信息是如何被书写。深度的观察意味着分级活动的深入,它使被阅读文本有一种“程度上的捻动”,从而“逐渐地显示”其意义[10] 131。用这种方法,巴尔特观察到,在当时中国文革时期高度一致的政治文本符号背后,掩藏着并不一致的书写方式,他“唯一注意到的和有变化的东西,便是毛泽东的书法和人们以不同字体书写的大字报”。[3]347
三、“红色中国”、“两种表情”和“负片中国”——中国行文本中的中国印象
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大体上是按照萨特对中国的评价层次行文的。“转变”是他对新中国定下的基调,然后是以“任务的巨大”为主题展开,从“事业的多种多样性”、“社会主义化”、“深切的人道主义”新中国的“双重面貌”几个方面依次道来,最后以中法“友谊”作结。全文熟稔地使用新中国彼时常见的政治术语,充分肯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并以“无所不包”“彻底改变”“远见”等溢美之词“毫无保留地”赞扬新中国。[2]299《萨特对新中国的看法》是一篇新闻采访,采访者以问答方式追问了萨特中国行的细节,以及形成中国观感的原因。文章基本上按照萨特在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经历来叙述。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第二,关于当时的胡风事件;第三,关于农业集体化;第四,关于当时中国的 “三反”运动(“反腐化、反浪费和反脏乱”)。在法国记者面前,萨特依然坚持了新中国“积极发展”的论断,并对记者提出的一些消极问题表示不满,“对每一话题你都试图与欧洲作比较,你一直想证实你的怀疑。”[6]14在这两篇文本中,对于新中国计划“用50年的时间”,把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萨特认为“也还是可以想像得到的”。[6]3对于“建设一个新中国需要50年时间”,萨特也充满期待,“群众对此并不失望,他们有新中国的蓝图,为它而工作,似乎这一新中国在第二天就能真正实现。”[6]15文本积极乐观的语言呈现出亮丽色彩,直接象征着萨特“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立场。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镜头,就是那些中国人的生存表情——一张张“脸”。电影里面中国人的“表情”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是笑容可掬,信心坚定又情绪饱满的脸”,“一是怯懦惶惑、焦灼不安,呆滞甚至有些许颓丧的脸。”[11]94前一种表情往往出现在公共空间、公开展示的社会活动中(让看/摆拍),如下班后自动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工人,热烈展开讨论的农村党支部,整齐嘹亮步伐坚定的下乡青年,幼儿园高唱热爱祖国的孩子们;后一种表情则出现在私人空间、未经准备的个人行为中(闯入/偷拍),如秘密自由市场上抱着猪娃满脸惊恐的老汉,被抓拍到的孩童。
前者是一种公开表情,它“热情、坚定、信心满盈”。[11]94往前追溯,它出现在萨特的中国行文本中,成为作品表现的主要中国表情,如开矿的工程师和果树移植的农学家,以及众多目光坚毅、表情镇静的“你们”,构成萨特所唯一面对的“大写的主体”。往后延伸,它也出现在罗兰·巴尔特的《中国行日记》中,他称之为“可爱的大众”,[3]167如“亲切的、开放的、正派的、微笑的”工人的面庞,[3]166模范家庭中过上了幸福生活的退休女工(类似萨特采访的女劳动模范房素荣*参看1955年9月26日的《辽宁日报》中《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等离沈》一文。),向他们热烈鼓掌的少先队员以及笑眯眯、寸步不离的旅行社官员。后者是一种私人表情,它消极、颓丧、局促不安。这种私人表情在萨特的中国行文本里完全不见,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却是刻意追求的镜头。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12]64
这样的“裂缝”,正是罗兰·巴尔特在中国行过程中努力发现,却求之不得的记忆符号,他称之为“皱痕”。“皱痕Pli,或译为‘褶皱’,指的是给人留下些许记忆的东西。”[3]104虽然他也在努力寻找“完全个人的小天地”,[3]201但由于整个旅行“躲在语言与旅行社这两层橱窗之后”,[3]233他失望地表示中国是“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3]P147
巴尔特的中国行,时时处处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话语,如“砖块”(Briques ) 、“俗套”(Stereotype)和“多格扎”(doxa)。他认为,“在这个国家,只有政治说得上是文本,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说得上是能指。”[3]348所谓“砖块” 由一个个独立的单词或熟语构成的习惯性句法结构,它是俗套的、熟语的一种单位。*参看《中国行日记》第343页,以及《译后记》引文及第24页注3。全文至少有30次提到了“砖块”概念,如随行翻译的“纯粹的、不加掩饰的单子”(即当年翻译们必备的“对外宣传口径”的译文资料)*参看《中国行日记》第116页引文及译者注1。,批判林彪的政治誓言,介绍成就和经验的“统计关键词”等等。所谓“俗套”,就是“符号的重复”。[3]345它在《中国行日记》中也出现了10余次,如一些千篇一律的政治宣传话语和革命套语(“实践”、“劳动者”、“集体主义”)。[3]190在罗兰·巴尔特眼里,“俗套言语活动为说话主体提供自如、安全、不出错误的尊严,而说话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着‘群众’)变成了无侵占之嫌的主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言语活动不占据任何他人的位置,它等于是一种非言语活动,它允许主体说话”。[3]145所谓“多格扎”(doxa),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于特定时期出现的全部舆论和一般说来被当做规范来接受、因此是主导性的模式”,[3]341即通行于社会的默认规范。在巴尔特看来,“砖块”构成了“俗套”,“俗套”又构成了“多格扎”,“砖块”、“俗套”和“多格扎”的迭加又组成了当时“文革”时期中国致密的政治话语体系。
如何在“砖块”和“砖块” 之间、“俗套”与“俗套”之间发现缝隙,难道它们“就没有细微差别吗”?[3] 116他最后找到了一种办法,能够从俗套的缝隙中发现新的见解,那就是“强烈的、个人的思想应该在俗套结构的缝隙之中被解读(而在我们国家,要创新、要避开多格扎的折磨,就必须消除俗套本身)”。[3]31这种解读方法,本文称之为“负片中国”描述法。所谓“负片”NegativeFilm,是一种摄影术语,就是说摄影之后的一个影像,其明暗与被摄体相反,其色彩则为被摄体的补色。从色彩角度来说,罗兰·巴尔特并没有把注意力停留在中国自己渲染的主色调上,而是努力发现不同的色彩,并反观其间的色差。在观看幼儿园小女孩们的歌舞时,他指出,“所有颜色都是西方人害怕的颜色:红,刺眼的绿”;[3]117在观看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时,他认为里面演员的“总是过分化妆:粉红赭石色为底色,留出耳朵为白色”。[3]232对于中国当时自我彰显的颜色,巴尔特以透视式的眼睛发现,“除了古老的宫殿、宣传画、儿童芭蕾舞和‘五一’以外,中国没有色彩。”[13]46
四、“积极介入”、“积极疏离”和“判断悬置”——三种不同的价值立场
在《萨特对新中国的看法》一文中,萨特道出了他对新中国的深刻感受,“‘我为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共有目标的一致性所震惊了’。”[6]14萨特所论及的“一致性”,主要是针对当时新中国广大人民和政府领袖在政治目标上的趋同特点。虽然他所举证的事例,仅仅是关于当时中国的“扫盲运动”,感叹中国人民群众自发地配合政府,积极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的巨大进展,但纵观萨特的所有论述,可以看出对“一致性”的观察成为其中国行文本的主要线索。他历时性地叙述了他所见闻的大事件,从“胡风事件”、“农业集体化”、“三反”运动到“扫盲运动”,“每一次斗争都是像十字军一样,全体群众都动员起来了。”[6]13在亲临了诸如天安门国庆庆典等盛大政治活动之后,有类于波伏瓦的感受“即使是最玩世不恭的人也会目瞪口呆”,[7]31萨特也惊讶“已高度政治化了”[6]13的中国民众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面对中国的上下一心、共同努力,萨特不由感慨,“群众的被动性是中国正在消失的许多事物之一,他们对他们的领袖非常信任,他们正为实现那些简洁明确的具体目标而奋斗。我把这称为群众的自主决定(auto-detemination)”,“感谢这种自主决定,中国的面貌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6]14
萨特真心赞美这种“自主决定”,并对带来“惊人的速度”的政治道德高度欣赏。他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在中国亲眼去见、亲耳去听,并具有眼见为实的自信,和波伏瓦一样相信“表象也有真实性”。[6]24在这种“眼见为实的发现”下,萨特“以这种发现而形成的看法和批评”,是以存在主义积极介入的政治道德观,形成了对新中国文本“一致性”的认同,并赋予这种高度趋同的符号编码以积极的文化道德意义,反过来又用这种意义去观照新中国其他的社会符号。然而,萨特站在政治道德层面,同情式理解的中国文化符号——充满“一致性”的中国服装,在巴尔特那里,却成为“发现中国秘密”的“地下通道”。[6]24
从罗兰·巴尔特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起,他就注意到中国人着装的“一致性”。在法国巴黎的奥丽机场(Orly),“有十几个中国人,都穿着高领上衣……看上去,像是一群出行的修士。”[3] 4中国人普遍穿着制式服装,公开场合的中国人“很突出制服上的一致性,但也有细微的严格区别(干部/工人/职员)”[3] 185,“灰色或黑色的上衣:公务员、干部等。蓝色上衣:工人等。”[3] 44巴尔特还在日记中用简笔画勾勒出穿制服的中国人,描述中国人的特征是“服装上的绝对一致”。[3] 190在离开北京飞回巴黎时,巴尔特在机场又看到了一群中国人“身着制服……真有点像是耶稣会教士”。[3] 300-301从“修士”到“耶稣会教士”,中国人服装的单调刻板,“真让人印象深刻!”[3] 11
对于这种着装习俗,巴尔特的评价是“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3] 11是“爱美之荒芜”。[3] 12过于单调刻板的服装形成一副坚硬的外壳,完全堵住了通往所指的路径,形成一种只有能指的“单平面符号”。[3] 92跟他在中国见到的其他文化符号一样,中国的“服装”是千篇一律、毫无变化,只有能指,没有所指。这种只有“能指”而缺乏“所指”的文化符号,几乎成为罗兰·巴尔特观察当时中国方方面面的共相。面对平淡的身体、统一的服装、没有色彩的中国,“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3] 93
如果说在萨特那里,他并没有把“一致性”当作思考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思考政治道德观的边界,那么在巴尔特那里,“一致性”就成为其思考的核心概念,他发现从服装到中国社会其他各个领域,“一致性”成为贯穿其中的唯一价值标准后,“新颖性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3] 335那么,安东尼奥尼在纪录片《中国》中,用自己的影像语言表达了对这种价值观的立场。
对于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美国学者凯·穆尔经过历时性地梳理,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疏离逻辑”。[14]4-21在凯·穆尔看来,虽然绝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疏离特征是安东尼奥尼电影的中心美学因素,但他不是从消极去理解,而是看到了“疏离”的积极作用。凯·穆尔认为,疏离作为拒绝认同和拒绝沟通的结果, 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结局, 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14]5“消极的疏离”乃是其“第一个阶段”, 即“先把主体孤立起来进行详细考察, 以便检验是否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了新的心理阶构”,“积极的疏离”则是以发现一个新的感情“事实”为先导的最后阶段, 它反过来改变了事实的总体或文化本身……”[14]9当评论界几乎是统一地用消极的疏离概念来解释安东尼奥尼时,其作品中潜在的乌托邦式的主张就被忽略了。他援引另外一个美国学者杰弗里·诺埃·史密斯的观点指出,“安东尼奥尼的每一部影片中都有着积极的一端和消极的另一端, 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抽象的东西, 即‘思想意识’,主要在消极的一端。具体的和实在的东西, 即影片表现的生活, 多半是积极的——但往往被评论所忽视。”[14]5就是这些被忽视的疏离的“具体的和实际的”方面, 不仅显示疏离有积极的一面, 而且它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里,和吸引着人们较多注意力的消极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疏离”特征,曾经与其合作拍摄《云上的日子》的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也有评价,“‘间离’是他的主题:分离、不相容、疏远”,安东尼奥尼喜欢“以一种更冷静、更疏离的方式观察和思考”,“不是自他们中间而是俯视他们,也不是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而是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自高处摆布他的角色。”[14]67巴尔特在他写给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他对其电影中“疏离”逻辑的看法。如果说,“间隔(Zwischenraum)”是在一个新的空间获得了充分的认同感,那么,“您(指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也是‘间隔’的艺术(L’Avventuna《奇遇》),是一个出色的证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您的艺术与东方有关。”[5]66而这个与东方有关的艺术,就是指电影《中国》。
安东尼奥尼在电影《中国》中,依然坚持并实践着“积极疏离”的艺术信念。一方面,在“消极的一端”,他也记录中国文本中“抽象的东西”以展示背后的“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他遵从东道主的要求,展示那些直接、正面的中国形象。在他看来,“如果没有那些‘组织好的’场合,这部纪录片并不一定就更接近现实。”[8]86另一方面,在“积极的一端”,他又不断寻找“具体的和实在的东西”以展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于是,两端力量形成一种张力:对强制要求的“一致性”有意偏离。为了记录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他尽量摄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有意淡化这些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他所反映的中国,不单存在于大的历史事件中,也被嵌入在小故事中,存在于当时他所遇到的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影片触及中国的城市、农村、工厂、集市和幼儿园,甚至还有孕妇的生产和普通人的葬礼,以多种角度直抵中国的内心深处。这种不拘泥于追求“一致性”单一视角的解读,使得他的电影具有无限丰富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结语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萨特处于自己的政治激进时期,极力鼓吹以介入和实践来达到社会变革的主张,成为西方激进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和中国革命的青睐与赞美,可视作他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最好注解。萨特关注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实践内容,并从介入伦理观的角度,对亲历中国的“历史内容”给予高度评价。其真实性在于,他既打算做一位客观的报道者,又以热烈的信念参与其中。他很快理解了中国的政治言语活动,“接受说一种共同的、一致的、无形的言语。”[10]252-253但是由于对中国政治事件的评价过于具体直接,往往陷于时过境迁的误解或失察。萨特似乎想通过这句话,为自己的判断方式保留余地,“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6]3
20年以后的7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逐渐破灭,他们同苏共和法共的关系日益疏远。另一方面,法国在1968年发生的“五月风暴”,刺激了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参照,重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寻找“东方理想国”——“政治乌托邦”的历史旧梦,从而获得法国革命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方法。在这种心态下,巴尔特“带着自己的友善、赞同、无知和疑虑,走完了中国之行的路程”。[10]382
巴尔特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力制度以及由其决定的符号表达方式。他秉持着媒体文化批评的符号学理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象征和符号现象进行“去神秘化”的文本分析,并透视出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或二级意义。巴尔特的分析侧重于他所抽离出的符号和结构这种“历史形式”,因其较为抽象和稳定而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两者立场和方法的变化,折射出各自生存的社会和知识条件的历史嬗变,他们在丰满真实的历史社会场内必须面对个人的伦理学选择。萨特以其实践文学的介入立场,迫切进行社会性反应;巴尔特以其普遍怀疑态度,拒绝进行社会性反应。[10]313从萨特到巴尔特,显示着西方左翼对中国的观察,已由激情十足的政治预言家,让位给了冷静理智的学者。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行文本,也有意摒弃了政治取向上的观看,《中国》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在我的影片里,人总是放在第一位的”,[15]23关注“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部影片既有对中国展示自身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录,也有属于安东尼奥尼式的对具体个人真实存在状况的审视。
安东尼奥尼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观点表现中国,在电影中大量展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并未将“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艾柯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出来,由此导致主客双方态度出现抵牾,在当时引发极大的争议。*参看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后来的结果是,“看他的影片,我们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他为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另一个角度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的后代窥见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的时代。”[16] 24如此看来,与其执着于他记录的中国所产生的多义性或歧义性,还不如将它交付给它自身尚待言明的历时性。
总之,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创造者,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书写中国时,一方面试图利用和更新他者文化,来实现对自身文化的开发与回归,不乏睿智与洞见;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作为一个神性的“启示者”,将其理想化和神圣化,充满想像和误读。于是,萨特之看中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满怀激情与信仰;安东尼奥尼之看中国,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充满憧憬和好奇;巴尔特看中国,看山又是山,看水还是水,渗透着怀疑与反思。另外,也由于当时中国本身历史发展的复杂多变,他们很难深入理解中国现实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特点,所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 The Writings of Sartre[M].Contat, Michel.and Rybalka, Michel(comp).Richard C.Mccleary (trans.).Northwestern Univ.Press, 1974.
[2] 高宣扬.萨特的密码[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3] [法] 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日记[M].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孙红云.两个中国?——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J].当代电影, 2009(3).
[5] [法]罗兰·巴特,艺术家的智慧: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给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信[J].黎静,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5).
[6] 沈益洪,编.萨特和波娃谈中国[M].萨特,著.秦悦,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7] [法]波伏娃.越洋情书(下)[M].楼小燕,高凌瀚,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8] [意]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还能拍一部记录片吗?[J].汤荻,译.当代电影,2004(6).
[9] [意大利]温贝尔托·艾柯 Umberto Eco.论阐释或难为马可·波罗——谈安东尼奥尼的关于中国的影片引起的重大事件[J].单万里,译.当代电影, 2007(6).
[10] [法]罗兰·巴尔特自述[M]//罗兰·巴尔特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 张同道.中国表情——读解安东尼奥尼与伊文思的中国影像[J].当代电影, 2009(3).
[12] 崔卫平.安东尼奥尼的《中国》[J].新闻周刊, 2004(45).
[13] Alors la Chine?[M].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1975.刘文瑾,译.中国怎么样[J].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3(2)
[14] [美]凯·穆尔.对平凡现象的不完整表现——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疏离逻辑[J].叶周,译.桑重,校.世界电影,1996(4).
[15] 刘天舒,编著.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5.
[16] 肖同庆.影像史记 [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万莲姣
Three Images of China Seen by the "Left Eye"——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Sartre’s ,Antonioni’s and Barthes’ texts of their Chinese visits
YAN Wei,TAN Wei-jiao
(SchoolofJournalismandMassMedia,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430073,China)
Europea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Sartre, Antonioni and Roland Barthes visited China respectively in 1955, 1972 and 1974, and left over their recorded texts about China.They had very different feelings and opinions about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olitical stance and ideas, and in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ir visit to China.This paper argues that Sartre’s concept of "Red China", Antonioni’s theory of "two kinds of Chinese expression" and Roland Barthes’ concept of "Negative Film" of China, not only respectively shows the "positive commitment" of the existentialism view on literature, the "positive alienation"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the "suspension of judgmen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perspectives in their observation of China.The three images of China constructed in their texts, not onl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he wester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standpoints on China, but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s to view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during a particular period.
Jean-Paul Sartr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Roland Barthes;left-wing intellectuals; view of China
2016-07-06
阎伟( 1969—) ,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谈微姣(1971—),女,湖北鄂州人,武昌职业学院讲师。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萨特的大众传播思想和媒体实践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BWW004)阶段性成果。
I0-02
A
1001-5981(2016)06-00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