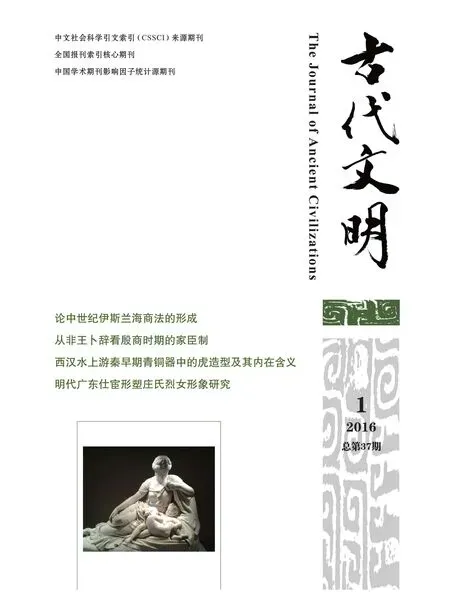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
张 弢
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
张弢
提要: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自21世纪以来呈现出了新的发展面貌。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通过探究古典学的译名回溯该学科的发展源头;强调学习古典语言、重读古代经典文献,从而构建大学中健全的古典学专业培养体系;着重梳理古典学在西方的学术史。这些均意在从头打造适合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界的新学科,体现出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者的务实学风。这些努力既符合研究型高校建设的需要,又有助于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追赶国际学术前沿。
关键词:古典学;学科现状;学科史;研究型大学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全集译注”(项目批号:15ZDB087)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的初稿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纪念卢剑波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2014年9月)会议论文,与会代表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尤其是王献华教授、王欢博士致以谢意。
中国学界对西方古代的历史文化早已不再陌生。1有学者提出,对西方古代文明的认知伴随着、也照应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见聂敏里:《古典学的兴起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哲学》,2013年第4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国自近代以来逐步走进现代性并不是了解西方古代文明、进而研习古典学的动机,而是其结果。从学理上讲,设置古典学学科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另当别论。19世纪中叶以降的西学东渐之风让国人初识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自中国设立现代大学之后,外国史、西洋史就早早地进入了大学的课程。2略见刘北成、郭小凌、蒋重跃:《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古代世界的认知方式还是以翻译著作为主,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则多为介绍和概论西洋文化和历史,研究性成果匮乏。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在动荡的百年中,对西方古代文明的研究也无从生根发芽;而该学科真正进入发展阶段是在1949年之后。建国之初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对世界历史包括西方古代史的研究有了更多的需求。不过,这反过来却又对客观地考查古代西方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和束缚。对此学界已有不少思考,3可参见何芳川:《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郭小凌:《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郭小凌:《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世今生》,《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此不赘述。概言之,学习苏联的成果、译介俄文的著作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认识西方古代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即便是国内学者自编的教材和通论性的著作也无不受此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的30余年,思想日益解放、国际交流愈加频繁,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典历史的研究状况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国内学者的著述和研究成果与日俱增,水平也在不断提高。4对1949至1999年中国学人在古典历史领域建树的梳理和评述,参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3—429页。
而21世纪最初的10年更是古典历史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突飞猛进的时期。1参见郭小凌:《“十一五”期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状况》,《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郭小凌、祝宏俊:《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近况评述》,《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除古典历史领域外,中国学界对西方古代文明的总体研究也正在高速发展。
一、西方古典学在国内学界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方古典学领域(Classical Studies,下文通称为古典学)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学界图景。
专业学术机构增多,一些大学加强了原有的机构设置或新设了专门的古典学科系与研究所,愈加独立地自主培养古典学专业的后继人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自1984年成立以来,已有30余年的辉煌历史,是国内教学和科研的传统基地,在育人与成果方面均成就斐然。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在各自的历史系也建立了古典学的培养体系。北京大学于2011年成立了跨院系的实体教研机构“西方古典学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从2010年开始着手建设,在经历了三年的实验阶段之后,于2014年初正式成立了“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形成了系统的古典学专业。此外,重庆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下附设了“古典学研究中心”。西南大学也于近年成立了“古典文明研究所”。
经过专业训练的科研人群正在不断扩大,既有本土培养,更有数位在欧美大学获得古典学及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或归国任教或与国内高校建立起科研合作,由此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当下的研究前沿引介到国内。
随之而来的是,在古典学领域,西文译作与中文论著出版数量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而且形成了持续出版的多套系列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本已包含了诸多西方古代经典文献,此不枚举。此外,尚有其他颇具代表性的系列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西方古典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日知古典丛书”则专门出版古代典籍对照本,刊本采用了拉丁文—中文、古希腊文—中文对照的形式;同社的“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则关注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西学源流”也将不少古典学著作纳入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古典学丛编”,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独立出版的“古典学译丛”都向学界译介了不少经典与研究论著。上海三联书店的“人文经典书库”亦然。2古希腊文学作品的汉译情况,可略见[英]多佛等著,陈国强译:《古希腊文学常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17—223页的阅读书目。另外,[奥]雷立柏编:《古希腊罗马及教会时期名著名言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虽然是一部学习古典语言的辅助教材,但书中的正文部分详列了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生平、著作、名言名句等,各项均附有汉译,便于初学者通览;特别是书中第169—183页的“著作总索引”,是读者查找古代著作及其汉译书名的方便工具。
中国的大学纷纷创办古典学专业期刊: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创刊于1986年,是获得国际学界认可的多语种西文期刊,该刊从2007年起又增创了中文版《古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于2010年创办了国际性的中文期刊《古典研究》(The Chinese Journal of Classical Studies);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古典学评论》业已出版;另外,大象出版社的辑刊《新史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年刊《世界历史评论》也都出版过古典学专刊。
在学术管理层面,古典学研究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的课题被纳入了不同层次的项目资助体系之中。仅以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为例,在获得立项的167项选题中,至
有“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古希腊文明与丝绸之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全集译注”、“《剑桥文学批评史》翻译与研究(全九卷,第一卷:古典时期)”等四项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古典学的研究领域,1公告及选题附件见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1105/c219469-27780781.html,最后访问2015年11月5日。约占招标总数的2.4%。对于古典学这样一门国内的“新兴学科”而言,比例颇高。
此外,中国的学术机构也主办了多次国际性的专业学术研讨会,促进了与世界古典学界的交流。仅在古代史的专业领域内,近年来在国内召开的国际性大型会议就包括,2005年8月由复旦大学承办的“第三界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6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古代文明的碰撞、交流与比较”等。
古典学的教学与研究已由过去东北师范大学一枝独秀到现在的多校并举。它在中国学界正经历着一场逐步从少到多、由弱转强的嬗变,核心舞台则是一批正在力图争创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其喜人的上升形势甚至羡煞一些古典学传统强国例如德国。笔者曾于2001年至2010年间,在德国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中接受过古典学的分支之一古典历史的学科训练,亲历了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古典学在于这所古老大学中的些许式微。原本,该大学中有一个专门的古代研究学部(Fakultät für Altertumswissenschaften),下设古典语言文献、古典历史、古典考古学、史前史等诸多系所;2Altertumswissenschaften一词在此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这个学院实际上包含的不只是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专业,还有闪米特学、埃及学、亚述学、汉学等多个研究人类古代文明的系所。现在,独立的古典学部建制在该大学已被裁撤,上述各系均并入了哲学学部(Philosophische Fakultät)。幸好,古典学的教授席位并未因此而减少,从而保障了教研水平。
从客观效果上看,在中国增设古典学的科目,不仅使中国大学的学科涵盖范围更为广泛,加强了高校人文教育的力度,而且也弥补了国内学界在研究门类上的欠缺,有助于增强中国学术的整体实力,更对在中国的学术体系内建设完整、自主、高水平的人文科学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然而,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却背负着学者们不同的期许。因此,围绕着中国应如何自主创办古典学学科的问题,也引起了学界不小的争鸣。有学者提出,应当从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回溯作为西学源头的西方古典传统,以此才能通透地审视现代西学,从而辨析受西方影响颇深下的当代中国自身。3张文涛:《古典学与思想史——关于未来西学研究之意识和方法的思考》,《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9期;张文涛:《再议西学研究中的古典学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4期。吴飞:《中国西学研究传统中的古希腊哲学》,《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还有学者提出要创办不同于欧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更远大的宏图则是期望借助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激发中国学界对世界上所有古代文明的全面重视,进而最终实现中国古典研究的复兴。4甘阳、刘小枫等:《古典西学在中国》,《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2009年第2期。这些思路不乏新意,都为古典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方式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
不过,无论强调引入西学、从根源上了解西方文明,还是志在重振国学进而开创一门新学科——中国古典学,5海峡两岸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都曾经呼吁创立“中国古典学”并设为一级学科、以正“国学”之名,可参见学者们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所作的访谈《国学=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8日。而“国学”设为学科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可参见“国学是一门学科”中的学者对谈,刊于《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其共同点是都意识到,在中国的大学内开设古典学专业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而且两者都以建设学科健全、自主发展的中国人文科学的内在需求为着眼点,并不单纯地强调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学习。无法否认的是,古典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没有古典学在西方的率先出现,中国学者也无从借用这个学科概念去定义所谓的中国古典学。6国内的学科设置中已有中国古代文献学或者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学这个概念显然是为了与西方古典学相对应而发明的,所以也有学者直接将中国古典学的时间范围定位在上古时期或者秦汉之前,以对应古希腊、古罗马的相应时代。可参见刘钊、陈家宁:《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吴锐:《中国古典学:疑古与辨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7日。所以,自主创新也一定是在对既有的学术传统和成果完成消化理解、做出批判性甄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即便是办出中国特色,也无法
绕过西方业已成熟的教研经验。古罗马的文学正是在师从古希腊典籍之后,才摆脱了缺乏创造性的顽疾,从而跃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达到了堪与业师比肩的高度。由此,学习古典语言、把握学术史和接受史的重要性就愈显突出。此外,在中国开展古典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应结合国内的实际,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巩固前行,才能加速接近国际学术前沿的步伐。
二、古典学的内涵与学科设置
尽管各家兴办古典学的主旨有所不同,但古典学近来的发展轨迹印证了一种不约而同的务实学风,呈现出的共识是从源头开始,从学习西方古典语言、阅读古代文献特别是经典著作的原文入手,步入研习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的正途,进而摆脱以往过分依赖译文和二手著作的困境。在实践当中,这种“从头开始”的决心和行动指导还在诸多方面有所体现,如从学科概念的源头将古典学引入汉语学界,在高校中从头开始学科建设、导入专门的古典学培养体系,从头梳理古典学及其所包含各分支的学科史等。而这些林林总总的工作中有些细节不容忽视。
通过考查古典学的词源和译介学术史的经典著作,国内学界对这门学科的特质和范畴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1张巍:《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黄洋:《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文汇报》,2012 年3月26日。古典学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研究的综合学术门类,而其基础就是对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文献的解读和阐释。时至今日,古典学已然综合了多个更为细化和具体的学科,主要包括古典语言文献、古典历史、古典考古、古典哲学、碑铭学、钱币学、草纸学、古代艺术史等。德意志著名的古典学家沃尔夫在1807年就将古典学概为一门由古希腊—古罗马的所有知识的总和构成的学问,2参校Friedrich August Wolf, Darstellung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 Berlin 1807; Nd. Weinheim: Acta humaniora VCH, 1986, p. 18: “…zwei Nationen des Alterthums, deren Kenntniss eine gleichartige Wissenschaft bilden kann, Griechen und Römer”。也就是所谓的“古代通学(Altertumswissenschaft)”。3[美]韩大伟(David B. Honey):《西方经学史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一本由非古典学专业人士而是西方汉学家撰写的古典学概论性书籍。不得不指出,该书作者使用的所谓“西方经学”的概念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然而,书中将“Altertumswissenschaft”译为了“古代通学”倒不失创造力,也颇为中的,本文援引此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学大师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给古典学下的定义也如出一辙:“被冠以古典二字的语文学,可以通过它的研究对象来界定,即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生命力的所有外在表现。这个文明是一个整体……古典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科学的力量令过去的生活得以重现。”4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Stuttgart/Leipzig: Teubner Verlag, 1921; Nd., 1998, p. 1: “Die Philologie, die immer noch den Zusatz klassisch erhält, … wird duch ihr Objekt bestimmt, die griechisch-römische Kultur in ihrem Wesen und allen Äusserungen ihres Lebens. Diese Kultur ist eine Einheit,… Die Aufgabe der Philologie ist, jenes vergangene Leben durch die Kraft der Wissenschaft wieder lebendig zu machen”。并参照[德]维拉莫威兹著,陈恒译:《古典学的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从总体上看,所有这些学科分支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明确的,即古希腊—古罗马两者合一的古代世界。5近两个世纪以来,更多的人类古代文明被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围,于是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个词的复数形式Altertumswissenschaften就涵盖了对所有古代文明的研究,甚至也包括了中国的古代文化。所以,德语学术界有时也将沃尔夫定义的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核心的古典学更精确地称为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单数!)。只不过每个学科分支研究的视角、路径、方法、材料各有不同。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学科分支在大学中形成了不同的院系,分门别类地对古典学进行细化的研究和教学。就欧美大学而言,对古典学研究的院系设置也各有不同。例如德语区的大学一般是为每个学科分支各设专职的教授席位。由于古典语言文献、古典历史等毕竟有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分别,
也可能分设两个教席。但一般的情况是,每位教授均可兼顾古希腊和古罗马,而又各有专攻。再以教授为核心组建教研团队、配置图书和器材等,逐渐发展成各个专门的科系或研究所,如古典语文系、古典历史系等,具有代表性的是哥廷根大学。也有一些德国大学更强调学科的分野,将古典历史作为历史系之下的一个专业方向,如柏林洪堡大学。而英美的大学则既设有专门的古典学系(Classics),系内的教研人员各有专业方向,分别承担上述的各个学科分支;同时,在历史系中也有专注于古希腊、古罗马方向的教授,这会与古典学系有所重叠,如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不过,在欧美的高校中,对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在哲学系中,没有独立的古典哲学系。作为西方大学的核心学科之一,古典哲学与西欧中世纪大学同时出现,在大学的体系中已有逾八百年的研习传统。该学科的院系建设远比其它人文学科古老。因此,哲学不会放弃其在大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古典哲学始终被归入哲学系也反映出,近现代哲学与古代思想一脉相承的学界共识。可能正是由于哲学研究传统悠久、自成体系,古典哲学在古典学这一综合学科中的权重不及古典语文学和古典历史。从西方学者关于古典学学术史的诸多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不在重点考查的范围之内。1相关的学术史著作参见下文。总之,西方大学中的院系建设并不拘泥于单一的模式。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大学恰可以藉此吸收多方面的办学经验,丰富自己的培养体系。
近20年以来,中国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追赶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成为了中国的高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化的重要途径。这势必要求中国对西方古代文明的学术性探索要逐步与国际学界接轨,在学科设置和高校建设方面与欧美强校比肩。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国的大学无法全面开设古典学涵盖的所有学科分支。例如考古学、艺术史、碑铭学、钱币学、草纸学等需要长期积累起来的实物收藏和持续的实地考察挖掘。当然,这也并不是唯中国学界所面临的困境。2例如东亚的韩日等国也是如此,只有日本在考古方面已有些自主的发掘,参见杨巨平:《韩中三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之比较——参加“日韩中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有感》,《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另外,大学中的学科设置也受到各国实际国情的影响,包括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生源基础、就业前景等诸多因素。譬如大学生在入学之前的语言准备就会直接影响其在古典学领域内的学业发展。以德国为例,传统的9年制文法中学(Gymnasium)从第五年开始设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一直到第九年,课程难度逐年递增。学生们不但可以将古典语言作为辅修外语学习,更可以作为主修外语连学5年,并将其作为中学毕业考试的主要科目。所以,大多数进入古典学门下各个专业学习的德国大学新生,在入学之前已经掌握了一门甚至两门古典语言,基本功颇为扎实。3当然也有例外,但无论如何,进了大学以后再从头补习语言的古典学专业的大学生是绝对的少数。而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只能在进入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之后,才能突击补习古典语言。而学习古典语言却又无法借助生动的对话来辅助提高,只能单纯依靠记忆单词、学习语法、阅读文献的艰苦途径。所以,在中国大学开设古典学专业必然会有与欧美大学的不同之处。如何设置适应中国学生的课程体系,换句话说如何本土化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另外,学成之后的出路与就业压力,也是学生本人以及所在高校不得不事先有所考量的因素。
目前,中国的古典学是以大学为教学和科研的核心机构,其教学过程主要分散在外语、历史、哲学等院系。当下的学科设置对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教学力度普遍存在较大欠缺,仍不足以广泛地展开针对古典文献原文的深入研究。学界对此已有所动作,包括在高校中试办古典学专业,成立本、硕、博连续的培养体系,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引进西方成熟的教学经验、聘请外教,如北京大学的西方古典学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均设立了常驻的外籍教席讲授古典语言。特别是东北师范大学,自30年前的“古典文明试办班”开始,就为本科生开设了古典学专业,一以贯之地强调对各门古典语言的研修;而该校的世
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培养古典学的研究生,人才辈出。
此外,国内学界还自主编写了古典学领域的研究手册,1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同时也将西文教材翻译引荐给了年轻的中国学子。例如当代德国古典语文学教授克拉夫特的《古典语文学常谈》一书,本是写给德国准备报考大学的中学生、以及刚入学的大学新生的引导性小册子。2[德]克拉夫特著,丰卫平译:《古典语文学常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该书的书名直译即为“古典语文学指南”(Orientierung Klassische Philologie)。该书主要是向后学们说明德国大学中的古典语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的发展简史、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以及学制的安排等等。3需要说明的是,此书的汉语译本采用的是原书2001年的德文版。德国的大学教育在当时还只分硕博两个阶段,所以书中“专业学习指导(第163—169页)”是针对两级学位制编写的。自2010年起,德国的大学引入了本、硕、博三级学位的学制,教学实践中的专业学习安排应该已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该书言简意赅、译文准确,也颇适合中国的大学生作为认识这门学科的启蒙读物。4在汉译的书籍中还有一本小册子,是两位英国的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与约翰·汉德森合著的《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而国内学界似乎已经与这本小书决绝了,汉语学术著作的参考文献中基本都不列此书。国内学者在提及此书时也主要是对它的诟病,特别是针对书中第31页“古典学的核心是旅游”一句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实,原书第36页“Tourism lies at the very heart of Classics”一句,或许译为“旅行是古典学领域的核心任务之一”会避免些歧义。原书作者是想鼓励后学通过亲身游历古代的遗迹增强对学科的认知。避开了教科书式的著述文体想必是这两位剑桥大学的古典学教授有意为之,他们想以游历这种易于吸引读者并拉近书中内容与读者距离的方式切入主题。虽然此书在西方读者群中颇有市场——笔者案头的就是2000年未作修订的再版(1995年初版),只是这本小书未必适应中国读者的需求和阅读心理。不过,对于距离西方文化的遗存有千里之遥的中国学生而言,阅读一部“另类”风格的作品,并借此了解西方的教授是如何引导初学者来认识古典学的,也并无害处。该书的问题或许是,两位作者给它起了一个——特别是对中国读者而言——容易产生误导的书名。另外,这本小书在中国所经历的种种也揭示出,即便是研习西学,中国读者也有必要阅读中国学者自己的著述才容易识得法门。
另外,古典学的资料正在经历着数字化进程,各种汇集现代研究论著的数据库日臻完善,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获取资料的障碍,使国内学人及时了解最新的发现和成果。其实,获得古典文献和古典哲学资料的便利自不待言。即便是在西方,古典历史史料的开放程度和获取的容易度也要高于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资料,通常不存在去档案馆查阅资料的需要。在资料建设方面,只要有持续的投入即可见效。5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堪称典范,参见张强:《学科建设与“文科专款项目”30年》,《中国教育报》,2013年2月26日。已知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史籍均有多种现代点校本,很多被译为了现代西方语言,而且译本还在不断地更新,更有为数不少的书籍已有汉译本。6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英译本系列《希腊罗马史料集》(Translated Documents of Greece & Rome),至今出版了5册,不但可以缓解史料匮乏的燃眉之急,更方便了有志于古典历史研究的初学者。所以,“从头开始”的古典学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也不是否定过往的学术积累、重新来过,而应是在既有基础之上的巩固与提高,应是继承中西学术传统之后的厚积薄发。再加之,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若要寻求与世界接轨,必然是扬长避短才能觅得突破口。例如,中西古史的比较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文明史的比较研究,7吴晓群:《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光明日报》,2015年4月18日。就早已被国内学界重视并反复提倡。8刘家和:《走出世界史研究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4日;刘家和:《谈中国人治世界史》,《光明日报》,2003年1月14日;刘家和:《展望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日知:《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日知先生(林志纯教授)笔下的古典学实际所指为上古、中古史,此处的术语移用与林先生的历史学家身份有关。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20余年来,为了导入规范、重整学风,中国的学界就尤为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工作。照应在古典学的引介实践中就是从头梳理古典学及其各个学科分支的发展史。将兴趣聚焦于学术史,或许恰恰是因为中国乃古典学研究的后起国家,尤为渴望迅速掌握前人的重要成果。近来,国内学界积极地翻译了多部古典学的经典著作,导论性和学术史的作品尤丰。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自觉地梳理古典学的起源和发展史。9专著类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第二版,两卷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论文类包括金寿福:《蒙森与德国的古典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赵敦华:《古典学的诞生与解经学的现代传统》,《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张强:《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有三部在20世纪产生了普遍影响
力的古典学学术史著作已然迻译为中文。英国学者桑兹的三卷本巨著《西方古典学术史》的首卷已经出版,1[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著,张治译:《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全两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余下各卷正在翻译当中。相对于桑兹的大部头,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的历史》则言简意赅,该书初版为德文,也有英文译本。2[德]维拉莫威兹著,陈恒译:《古典学的历史》。另一位德国学者普法伊费尔的两卷本《古典学术史》则是先出了英文版,后又有德文版面世,该书的汉译本业已付梓。3[德]普法伊费尔著,刘军、张弢译:《古典学术史》(两卷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此外,尚有前文提及的《古典语文学常谈》一书,其中附有简短的学术史概述。4[德]克拉夫特著,丰卫平译:《古典语文学常谈》,第156—162页。《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一书的第一部分“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亦是提纲挈领的梗概。5刘小枫编,丰卫平译:《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需要读者注意的是,该书存在不少印刷错漏,也不乏一些误译,例如“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一文的原作者并非Weisenberg,而是M. Weißenberger,又如书中第8页将博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ros Polyhistor,约公元前100—前46年)译为了波利希斯托。
三、梳理学科史的新意
中国学界在古典学的引入阶段尤为看重对学科史的回溯。在国内在教学实践当中,学术史类的书籍基本是开列给中国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书目,有心的学生也会主动寻求阅读。而在西方的大学中例如笔者曾经就读的德国大学,教学中更注重的是传授研究方法、介绍学科前沿,基本不会提及学科的发展史——它仅仅存在于研究层面。在德国大学的图书馆中,学科发展史的概览是与导论、入门、手册等书籍编为一类的,由学生在课下自发——甚至偶然——找来阅读。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大学教育忽视学术史。学生每篇论文乃至习作都会要求率先针对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做出既往研究的回顾与评判。这样的回溯工作是以具体研究主题为线索的,并不是学科发展史意义上的学术史。
其实,中国学界重视古典学的学科发展史,从学术史的角度切入该研究领域,具有多重的特殊意义。首先是国内学科建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古典学在国内学界还是陌生的学科,作为后起国家中的科研人员与学子,需要了解所在专业领域的发展历程,更何况该学科还是时空距离遥远的“他山之石”。通过回眸历史可以帮助国内学界尽快摸清学科发展的规律,掌握学术研究的前沿;还增强年轻学子对研究对象的体认,有助于他们登堂入室、进入研究领域。
而且,对古典学发展脉络的总体认知利于国内学界把握未来,找准中国建设古典学学科的自身定位和明确目标。当前,古典学已然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各类对古典学的定义、范式、走向的讨论受到诸多媒体的关注。6可参见于颖:《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文汇报》,2015年2月6日;阮炜:《古典学的学科身份从来就不单纯》,《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2日;张经纬:《古典学与中国的羁绊》,《文汇报》,2015年4月3日。其实,反观古典学于西方的发展轨迹,同样发生过各种观念的争执。19至20世纪的西方古典学界就分化出了不同的流派,重语言文字校勘的学者与更看重文献背后事物的学者在方法论上就相互对立。更著名的论争则是由尼采发表《悲剧的诞生》所引发。7有不下十位汉语学者分别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做过翻译工作,本文参考的是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的孙周兴译本。在该书出版后的两年之内(1872至1873年),维拉莫维茨、理查德·瓦格纳、古典语文学家埃尔文·罗德(Erwin Rohde)等一众德国学者先后发文六篇,就尼采著作的学术价值展开了激烈的论辩。维拉莫维茨严厉批评尼采著作的学术性,质疑其本人的学术资格,促其辞去大学教职;而尼采的友人瓦格纳和罗德则尽力为尼采辩护。在文字的交锋之中,双方同时也探讨了古典语文学(Philologie)的范式与发展方向问题。维拉莫维茨和罗德的文章分别以“未来语文学”(Zukunftsphilologie)和“后语文学”
(Afterphilologie)为题。1这些人的论辩文章现集中收录于Karlfried Gründer (hg.), Der Streit um Nietzsches “Geburt der Tragödie”(围绕尼采《悲剧的诞生》的争论),Hildesheim: Olms Verlag 1969。对这场文字论战的分析可参见黄洋:《尼采与古典学研究》,载陈恒、耿相新编:《新史学(第一辑):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虽然以实证见长的维拉莫维茨在当时颇占上风,然而这种情形在事件过后出现了极大的反转;尼采那种带着对现实的关怀去反观古人的路径在20世纪盛极一时,他所要达成的是超越语言和文字、穿透历史与文化、从而通达古希腊人的精神。可见,古典学在西方的发展轨迹既不是一帆风顺亦非一成不变,其发展模式也不是单线条的。中国学界虽然不曾经历其中的坎坷,但这不等于说过往的纠结对未来的发展毫无意义。相反,厘清古典学的学脉就可以进一步扫清障碍、少走弯路。那么,若想为古典学在中国的建设铺平前路,中国学界须更加注重对接受史的研究,更要有国人自主编写的古典学学术史著作、2在这方面,晏绍祥的《古典历史研究史》可谓开拓之作,相关版本信息参见前文。形成自身的学术史观。
如果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不难发现考查古典学的学科史对推动中国大学向研究性大学转型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而又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肇启于19世纪的德国。第一批转型为研究型的德国大学都是以人文科学见长的学府,这其中既包括建于中世纪的老校如海德堡大学,也有17世纪以降的后起之秀如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更有以研究和创新为宗旨而新建的柏林大学(1810年)。首个从传统的知识传承转型为以研创新知为导向的学科正是古典学,沃尔夫于1783年在哈勒大学开设了首个古典学的研讨班(Seminar),迈出了古典学走向科学学科的第一步。而研讨班这种教研相辅的形式从此开始流行于德意志各地的大学,并在19至20世纪传遍了全世界。直至今日,研讨班被证明为是成功的、高效的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模式之一。
古典学学科于18至19世纪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拉开了德国大学中院系和研究所的建设序幕。以古典学研讨班为典范,其它人文学科也开始设立研讨班,自然科学学科则开始建立实验室。从此,政府或经过大学或直接给予研讨班资助,包括设立固定教席、配备助手、提供稳定的预算、划拨房屋建立图书馆、大量购置图书等等。在开设研讨班、设立专业图书馆、建设实验室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一批以研究为导向的院系和研究所。3有关研讨班和实验室在德意志大学的发展概况,可参见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8—67页。当大学中的院系、研究所普遍发展为科研实体之后,一所大学从传统性向研究性的转型自然水到渠成。所以,研究型大学的出现首先是在系、所、以及相应学科的层面之上。古典学不但树立了科学学科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古代文明的同时,德国大学的师生们获得了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传统中汲取了学术创新的力量和源泉——用科学方法研究古代、形成现代人对古代的新认识,这本身就是知识创新。学者们的创新实践过程也就是大学所经历的转型历程。学科内部的革新产生了外部的动力,促进了大学的整体转型,这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为研究型大学的产生起到的推动作用。
可见,研究和解析古典学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大学中的学科发展史不但可以提高对历史的认知,从根源上理解研究型大学的成长路径,还可以为当下中国大学转型的现实工作提供参考和教益。由此可以期待传统史学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从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有益经验和借鉴,为中国当前的高校建设出力。古典学的学科史理应受到学界关注。
[作者张弢(1978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责任编辑:刘军)
[收稿日期:2014年11月25日]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