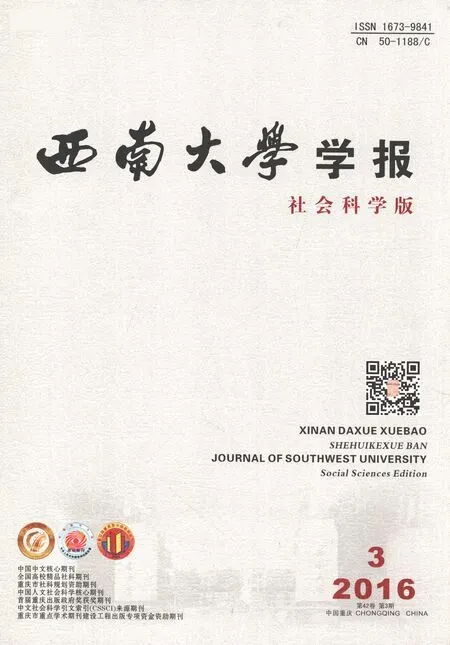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①
——以《法哲学原理》和《资本论》为棱镜
王 卫 华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市 200433)
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①
——以《法哲学原理》和《资本论》为棱镜
王 卫 华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要:要深入把握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必须对其精神内核即资本与精神的关系进行哲学追问。这其中有三个重要向度:一是《法哲学原理》赋予资本的“自由”范畴。黑格尔通过对自由层层剥茧,揭开了资本与自由关联的属性。二是对资本范畴的反思。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生产要素、预付金,而马克思认为把预付金抽象为资本无非是占有剩余。马克思资本范畴具有“二重性”,它是生产要素资本与社会关系资本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与幻化的批判,更加凸显了资本与精神的矛盾与冲突。三是历史哲学的向度——历史的普遍性与历史的特殊性的追问,历史不是简单地面向过去,不是终极审判台,而是由过去-当下-未来所组成的辩证的时间链条。这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资本与精神;现代性;自由;精神哲学;历史哲学;市场经济;资本金融化
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学者很多,然而,它们两者贯穿着的一个重要思想即资本与精神的关系,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我们要想对其有深入把握,就必须从单纯物质层面的技术分析翻转到精神层面的分析,这就离不开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因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用思想来呈现历史的理性。没有哲学追问,我们无法真正把握它们的内核。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与理论追问的时候了,以便为中国当下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指导。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首先应回溯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这部他晚年最后完成的重要著作,是一本典型的现代性问题读本,它关涉到资本与精神的关系。黑格尔将资本与自由进行关联,这对马克思有重要影响。正是针对此书中的观点,并关照到当时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作出回应与辨正。
一、第一个向度:赋予资本的“自由”范畴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赋予资本的“自由”范畴,这种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而是为理性规制了的意志所制约。谈论人的自由,也就是意志自由。正如黑格尔指出:“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1]10这里的意志是指自我意识,它是精神自我决定的,意志关联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由。意志首先呈现为一种表象,而且是一种经验的表象,当把意志的表象作为自由的前提时,“这一前提的基本特征是:精神首先是理智;理智在从感情经过表象以达于思维这一发展中所经历的种种规定,就是它作为意志而产生自己的途径”[1]11。意志的自由是由经验的表象和精神思维领域的理智所构成,并且要通达自由,必须由表象过渡到理智,用理智来规定、抽象、定义表象。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没有无意志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意志。第二,思维。在黑格尔看来,是否能思维,这是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他又认为,意志和思维有区别,体现在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上,同时两者又密不可分。思维的本质是把对象变成它的概念,所以,黑格尔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用思想去把握对象,然后把对象翻转为概念、意识。而当我们涉及意志时,它往往离不开人(自我)。没有人承担意志的主体,意志与自由只是空洞的形式,而无实质的定在。在黑格尔看来,人和生物都可以作为主体,但是,作为主体的人和生物是有区别的,生物意识不到主体性,因而生物没有主体性,而“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1]46。黑格尔在此处对主体和主体性作出明确区分,人和生物都是主体,但涉及主体性,只有人才具有,因为,主体性是对主体的内在本质进行自我意识的抽象,是自觉地把主体的存在所关涉的领域都呈现出来,显然,这是生物无法达到的,因为生物没有自由意志,而人却拥有。人高贵之处在于,人是“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1]46。“无限的东西”是指自我意识的精神,精神领域的自由才是无限的,个人只有在有限的规定中才能产生无限的精神自由。人(自我)处在市民社会中,要享有权利,而产权则是重要体现。人只有对所拥有的物具有产权,才是充盈的,才能显示人的定在。然而,产权的让渡与获得,离不开市场交换,货币作为市场交换的媒介,它具有可通约性,一切坚固的东西在它面前都变得如此脆弱,“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2]155这就是货币的魔力。当市场上出现了可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并可以用货币来购买时,货币也就转化为资本。资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从黑格尔对“自由”把握的路向上来看,他从自由中剥离出所有权、产权,并将其作为人获得自由的显现,进而从产权的让渡中剥离出货币、资本,自由与资本就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实质上体现了资本与精神的关系:没有自由、意志,何谈资本与精神,所以说,资本与自由、意志的关系,是资本与精神关系的重要读本,对自由、意志的读取,也就是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读取。
二、第二个向度:对“资本”范畴的反思
究竟何为资本?只要有资本存在,对此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就不会停止。一般来说,资本范畴有三个维度:一是一般的经济学家眼中的资本,它是一种生产要素、预付金;二是经过马克思把预付金进行抽象之后的占有剩余;三是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生产要素资本与社会关系资本的统一。
(一)资本范畴的第一个维度——作为一种预付金的资本
一般的经济学家往往对资本作这种理解,它主要偏向对资本作技术层面的框定。资本家要开办工厂或者投资实业,没有一定的预付金,这是无法想象的。预付金作为前提条件,资本家有了它可以雇佣工人,购买机器、厂房设备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这种可感觉的、可经验的、表象化的对象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多次叠加,呈现在一般经济学家视线中的资本,就被理解为预付金,并且只是作为生产要素形式出现的预付金。然而,经济学家往往无法对其进行深度抽象与内化,只能对资本作表象化与单向度理解,这必然触碰不到资本的本质,反而遮蔽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占有的事实。一般的经济学家只看见了资本的现存性,没有洞见到资本的现实性。只有撕裂资本的表面覆盖物,才能呈现其现实性,因为只有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否则只能是现存的。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指出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1]11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范畴考察较多,但是,他们更多地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预付金等物的形式。大卫·李嘉图认为:“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进行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3]476可见,在他看来,资本无非就是生产资料的总和而已。亚当·斯密对资本的理解和大卫·李嘉图非常类似,他认为资本是为了从事生产而积累下来的生产资料,是预付金的体现。不难发现,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亚当·斯密,他们都把资本仅仅当成物,看不到资本背后的社会关系属性,资本是兼有自然物的属性(显性)与社会关系属性(隐形),而在他们的视野中,显性的物把隐性的社会关系遮蔽了。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做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手册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3]476-477
(二)资本范畴的第二个维度——作为占有剩余的资本
从这个角度反思资本范畴,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前现代社会自然经济状态下对剩余的占有,它只是冰冷的财货的占有;二是现代性社会对剩余的占有,体现为通过国家工具强行占有他人与他国的剩余财富。
在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生产力落后,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更好的生存需要,时常通过武力来掠夺其他领地的财货,正如霍布斯所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4]32。领地的部落首领之间经过殊死搏斗之后,胜者一方,便对败者一方的财货进行掳掠与占有,这是对外部剩余的占有。领地内部成员之间对剩余财货的占有也很激烈,随着他们在部落中地位不同,对剩余的占有就不同。但是,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对剩余的占有,靠武力强权夺取,没有法律的规制,这具有明显的个人意志主义倾向,表现出任性、冲动、非理性特征。而过渡到现代性社会,这种非理性逐渐被理性所规制与牵引,通过国家工具来占有他人或他国剩余财富,并依靠国家军队、警察和监狱等上层建筑来确认其行为和结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这种占有剩余的残酷性,就如同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2]842马克思对使用暴力进行剩余的占有,一方面进行了控诉,另一方面又指出它的积极性:“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2]861文明社会的开启,往往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与拷问中,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迈向新的未来。
(三)资本范畴的第三个维度——马克思资本范畴的“二重性”:生产要素资本与社会关系资本的统一
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资本范畴的第一个维度时所指出,一般的经济学家把资本仅仅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认为资本增值就是资本这个“物”本身的增值,资本是自己能够带来利润的“物”,并认为资本具有普遍性、永恒性、非历史性。马克思指认了生产要素的资本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主要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来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作了大量的阐述,并认为它们也是资本力量的主要物质载体,离开这些载体,资本只是一般的抽象劳动价值。但是,如果将资本仅仅等同于生产要素,并认为生产要素就是资本的本质,那就是资本幻象的一种体现,正如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5]可见,经济学家总是陷入把资本当作“物”的单向度幻象中,他们被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导致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遮蔽。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家重要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看到了生产要素的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他透过物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批评指出:“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6]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77-878可见,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而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4]724。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资本权力关系,过去的、对象化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因此,资本才能不断地增值。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269
马克思对资本进行棱镜透视,发现生产要素的资本仅仅只是资本在斯密世俗时间里的表象与显现,而当他贯通到黑格尔的精神时间之后,发现社会关系的资本才更具有穿透力。资本不仅仅敲打着世俗的欲望,它还有着理性的狡计。只有用精神去整合资本,资本才不会盲目地任性与冲动;只有用精神去牵引资本,才能找到资本的方向矢量。资本不仅是物,它更以“符码”的形式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属性:在生产关系中,体现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劳资对立关系;在分配关系中,体现了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剩余价值;在交换关系中,体现了工人用他们所获得的少得可怜的货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以维持肉体和生存的需要;在消费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分别处于资本动力的“生产消费”与生存动力的“个人消费”中。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资本动力的“生产消费”,并且“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2]661。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158这里看似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其实,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凸显资本与精神的关系,资本由人所抛出,一方面,它激活了人性,给人以更多的自由,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命运打击不到的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了人性的异化。正如张雄教授指出:“资本与精神的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者与其劳动对象的异化关系。”[7]资本本身内含着“二律背反”的属性,要解读资本,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资本之中,才能破解资本之谜。
要深入到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资本,就不能回避马克思对拜物教逻辑的批判,而幻化则是他对资本导致人性异化的精神向度的深度批判,它实质上指向的也是资本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在拜物教逻辑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不仅涉及到作为主观原始意象的精神幻化问题,而且对之进行了剖析。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物化了的社会存在,商品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对象,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就在于它不断地被货币、资本进行抽象化之后,其使用价值的属性被弱化,而商品背后承载的社会关系属性则被强化,这种社会关系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存在并不断地敲打和侵扰到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从而使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方式、评价模式和心理期望都发生重大转变。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世界里,通过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抽象与货币对交换价值的抽象之后,它们都变得如此神奇,一切的存在只有被摆放在它们的世界里,才有意义,人被僵硬的拜物教逻辑定义与抽象,人由主体性存在降格为客体性存在。对拜物教意识的幻化逻辑的认识论根源,康德曾在《实用人类学》中有过精彩的描述。在他看来,幻象其实只是一种错觉,被误看做对象的东西其实是虚假的,这一点尽管人们知道,但它却仍然存在着。康德进一步指出,这种来自于自我意识的主体的想象力被加强之后所产生的精神幻化,“经常导致他相信在自身之外看见和感到了仅仅在他头脑中的东西”[8]53。对于这种精神现象,近代的培根和当代的齐泽克都有过相关论述。培根曾用“四假相”来说明虚假意识产生的认识根源与社会根源,而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他把这种虚假意识进一步翻转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意识形态直接就是社会存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拜物教的精神幻化问题进行了指认:“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4]246货币就具有这样的魔力,它可以使黑白颠倒,使丑陋变成尊贵,使邪恶变成伪善,使冰炭变成胶漆,使分离剂变成黏合剂。马克思批判货币拜物教的精神幻化问题,是对货币造成人性与精神异化的一种强烈的指认。人性中友善的、原在的、本真的东西,被货币过滤成欺诈的、世俗化了的、颠倒的存在。因此,货币拜物教就是把货币通兑成一切商品的能力,进而产生对货币的幻觉。为了获取货币,资本家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作为增值的能力,进而把这种增值能力误以为是“物”(资本)本身具有的能力,于是就产生对资本的精神幻觉并对其狂热地追逐与崇拜,结果造成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被扭曲。当商品变成“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2]88后,货币则变成商品交换价值的蒸馏器,于是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就出来兴妖作怪[9]。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对人类社会三大形态的划分指出,第一大社会形态属于人对人依赖的前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它反思的是“习俗”与“发展”的关系;第二大社会形态属于人对物依赖的现代性社会,实质上反思的是资本与精神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资本占据统治地位。人对物的依赖,本质上就是人对资本的依赖,第二大社会形态较第一大社会形态来说,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它剪断了人与家庭、血缘、宗法的脐带关系,人们告别了传统的习俗、家庭、伦理关系,走向了经济性的现代性社会,也就完成了从“神性”到“俗性”(经济性)的翻转: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经济人”,把社会变成市场,把所有的“存在”翻转为资源,把所有的产品转换为商品,把一切关系归属为交换关系,“我就是我的存在”已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精神标尺。
概言之,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它负载在“物”上,并通过“物”表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范畴具有“二重性”,它是生产要素资本与社会关系资本的统一,他不是把资本仅仅框定在生产要素“物”的技术层面,而是由生产要素资本穿透到社会关系资本之中,去求解使人异化——物化——幻化之根源的社会本质。这是一条从现象到本质、由显相到真相、由表层到深层的通道。马克思破解了资本之谜,他对资本范畴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一般的经济学家,这为人类自由精神的开启提供了理论支撑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第三个向度:作为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不是作单纯的技术分析,他与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的分析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单纯地放入技术分析的频道,诠释经济规律,玩转经济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偏好。而马克思从历史哲学向度来诠释资本与精神的关系,他将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有机对接,把经济规律纳入到历史进化规律的通道中思考,这样必然将经济学的范畴看成是一对一对辩证的历史范畴。在经济学家那里,劳动就是一个简单的体力支出,可是在马克思这里,他把劳动放大到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深刻的内在张力与矛盾冲突中。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劳动范畴放入历史进步的规律通道中来考察,劳动不再是那样的平面和干瘪,而变成了和人类社会进化密切相关的动力学。这一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可能思考到,这是哲学家才能够深刻地洞见到的。马克思正是在历史的宏大规律面前看到了劳动的能动性,它体现在劳资关系的异化上。所以,货币、资本在马克思的视域里就变成了具有一对一对“二律背反”的属性,显然,马克思承载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背反”哲学的精神。通过对劳动范畴一对一对矛盾厘清之后,马克思找到了经济生活的本质,这便要归属到人学的文本来加以解释:只有读懂人性,才能读懂资本,只有读懂人性,才能读懂资本与精神的关系,即人性的激活与人性的异化。
(一)历史的普遍性首先观照的是历史的特殊性
从历史哲学的向度来求解资本与精神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本质。作为历史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普遍性’不是指一个与具体个别物相区别的抽象实体,而是指异质性历史事件背后所支撑的历史共有理念或规则,是对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的哲学抽象,也意味着历史可以根据一个合理的、为人理解的计划而展开,并且朝着一个历史的理性目标前进。‘特殊性’不是指一个确定的抽象实体,或一个实体的某种确定的特性,而是指与历史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历史对抗性’,即单个人的非社会性倾向,它包括人性中所固有的私向化追求、自由意志、贪欲和情欲、利己主义行为等倾向。”[10]历史的普遍性首先观照的是历史的特殊性,因为,只有在历史的特殊性中,我们才能找到资本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据。历史的特殊性由利己主义预设下的个人的欲望、私欲、需要、冲动、偏好、任性所构成,它是历史发展的个人动力学。在阐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黑格尔看到了历史的特殊性,并给予强调和指认。他指出,当家庭子女经过教养而拥有自由的人格后,子女便拥有自己的自由和财产,这就意味着家庭在伦理上的解体,“由于家庭的解体,个人的任性就获得了自由。一方面,他愈加按照单一性的偏好、意见和目的来使用他的全部财产”[1]191,自由的个人是从家庭向市民社会过渡的重要基础,而市民社会又构成了家庭和国家链接的中介与桥梁。黑格尔在阐释市民社会时指出,市民社会是以个人的需要为前提的,而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它充分激活个人的欲望、需要和私欲;在市民社会中,“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1]197:它告别“神性”,走向“俗性”;它彰显了个人的利己主义,这开启了人们交换的自由,体现了交换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人性解放的重要标尺。
(二)历史的普遍性制约与整合历史的特殊性
历史的普遍性制约着历史的特殊性,只有用普遍性去整合特殊性,作为利己、私欲、欲望、任性等的特殊性,才不会成为杂乱无章的碎片,这也是为何市民社会必须要过渡到国家的重要原因。在市民社会中,历史的普遍性主要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利他主义精神;二是国家的普遍原则。黑格尔指出,为了国家的需要,个人必须放弃私人的欲望。没有特殊性的利己主义,市民社会就缺乏活力,而没有普遍性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国家的普遍性原则,市民社会就会无序,“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1]261。在阐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柏拉图贬斥感性经验的事物,认为不可靠,真正可靠的是“理念”,他只关注上空游荡的“理念”,也就是重视普遍性,而对特殊性漠不关心。对此,黑格尔批评指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描绘了实体性的伦理生活的理想的美和真,但是在应付独立特殊性的原则(在他的时代,这一原则已侵入希腊伦理中)时,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即提出他的纯粹实体性的国家来同这个原则相对立,并把这个原则——无论它还在采取私有制(见第46节附释)和家庭形式的最初萌芽状态中,或是在作为主观任性、选择等级等等的较高发展形式中——从实体性的国家中完全排除出去。”[1]200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历史哲学的通道中,马克思的历史范畴与黑格尔有巨大差异。在时间坐标上,黑格尔的历史范畴是指向过去,而绝不是指向未来,他是去回溯历史与总结历史,并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黑格尔所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14他的绝对精神,在逻辑上,体现为逻辑的绝对;在资本上,体现为资本的绝对;在历史概念问题上,体现为历史的绝对,因此,历史在黑格尔这里就变成了终极审判台。而马克思则不同,在《资本论》中,历史范畴有独特内涵,历史不是一个简单地面向过去,它是一个辩证的时间链条,呈现为过去——当下——未来宏大的构建,历史绝不是僵死的质料堆积,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上述三个向度缺一不可:《法哲学原理》赋予资本的“自由”范畴,为马克思以后深入思考资本的本质打开了理论视野;对“资本”范畴的反思与追问解答了何为资本,并彰显出马克思与一般经济学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思考贯穿于《资本论》的始终,对“他者”的批判,同时也要解放“他者”,作为资本的“他者”与作为劳动者的“他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在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中,“他者”(英文为other,法文为autre)包括两层意思:认识论中的客体;被主体所排斥和压抑的异质。详见张雄:《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哲学研究》2006年第10期,第27-34页。本文所说的“他者”,前者主要指资本,后者指工人阶级(劳动者)。;而对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考察,则体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历史范畴上的巨大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将历史的直线运动和历史的偏斜运动进行相契合,实现了经济规律与历史规律的有机统一。从历史哲学的向度来反思,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接纳了”经济学说、经济学的教条,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研究、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就经济规律批判经济规律、检讨经济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把经济还原到宏大的历史尺度里面去反思货币、资本、财富等经济问题,因此,马克思同时也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之所以如此重要,正如张雄教授指出:“只有从精神的高度分析资本,才能获得资本的真理,才能获得人类尊严和理性权威的确认。”[7]
四、启示与意义:正确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哲学追问,它能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下重大现实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价值。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无疑成为我们当下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市场经济发展的“欲望”动力论
当前,我们如何理性看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如果深度反思,则将涉及“欲望”问题,而与“欲望”直接关联的是货币、资本、财富等经济范畴。中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缺乏“个人”概念的发育,“个人”往往处于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语)中,这无法激活个人的欲望与偏好,沉睡的资本难以被唤醒。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非常关注“个人”概念,他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认为它具有以下基本内涵:是能动性的变革社会的个人;是在实践活动中的个人;是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是被纳入到社会大分工中的个人;是具有特殊利益、物质欲望的个人。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发展,离不开“现实的个人”。《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有利于激发“现实的个人”的欲望。在市场经济中,把欲望翻转为现实的需要与利益,通过生产与交换实现“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一。对这一点,西方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早就洞见到了。他指出:“质料是可以改造的”[11]。“质料”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过来的,此处意指“现实的个人”(尤其是指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欲望,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他人经济,生产的产品必须通过交换供他人消费,自我才能在他人中找到存在的价值。现代市场的本质是产权让渡,通过产权让渡来实现个人自由意志的定在,才能赋予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其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确证个人异质性的存在,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个人动力学。康德曾经把它看做历史发展“恶”的动力论,它是历史哲学的“恶”。他深刻指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12]
(二)在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契合中,积极应对资本金融化挑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但需要发挥物质资本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而且更要强调精神资本所发挥的示范与牵引作用。这种资本不是简单的资本,而是“大资本”概念。我们必须思考用什么样的精神资本来应对与引领市场的快速发展,来整合与弥补市场的任性与偏斜,来规避与防范市场风险,来重振与提升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它突出的贡献在于解放资本,为人们厘清了当今资本的真正内涵与意蕴,对简单而粗暴地拒斥资本的错误做法进行了理论上的辨正,从而恢复了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这将大大激活中国资本市场,为经济腾飞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这就需要我们把物质和精神相互契合,关键还在于亮出我们的精神资本,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新的制度、新的文明来整合资本,使资本能够在社会主义阳光下最大化运行。为此,政府、企业、个人都需要学习,我们的意识、精神乃至心理因素都要准备好,才能够从容应对这场资本金融化的挑战与考验。
我们正处于从货币化生存世界向资本金融化生存世界的转换时期,资本金融化的浪潮已经向我们扑面而来。21世纪,经济上的突出表现在于资本金融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金融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从西方世界到东方世界,从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从精神向度上来反思,资本金融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显现,意识有多远,资本与财富就可能走多远。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金融衍生品在型塑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有了理财意识和精算意识,有了执着精神与冒险意识。当互联网金融把时间和空间再次进行重组与编码后,我们每个人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由原来可感的、经验的、表象的时空翻转为当下日益被抽象化与符号化的时空,客体被“掏空”[13]20的同时,主体也日益被“掏空”,这不断地消解着人的主体性,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孤独性”[14]、流变性、异质性、“自反性”[13]46,使人们常常处在精神紧张与焦灼之中。资本金融化既是一场伟大的金融革命,也是一场资本与精神关系拷问与书写的历程。对资本与精神关系的哲学追问,这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唯有不停地追问,我们才能读懂资本;唯有不停地追问,我们才能解答资本与精神的关系;唯有不停地追问,我们才不会在资本强势发展的今天,迷失理想、信念和我们的精神家园;唯有不停地追问,我们才能解答历史与现实提供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4.
[7]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J].中国社会科学,2015(1):4-22.
[8]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3.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40.
[10]张雄,速继明.历史进步的寓意——关于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解读[J].哲学动态,2008(1):5-10.
[11]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册)[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59.
[1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3:70.
[13]拉什,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M].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魏峰.信息与能量——人性中的逻辑与历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255.
责任编辑刘荣军
网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02
收稿日期:①2015-09-06
作者简介:王卫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中国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建构”(12YJA720004),项目负责人:范宝舟;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资本视域下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视角”(CXJJ-2015-410),项目负责人:王卫华。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3-0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