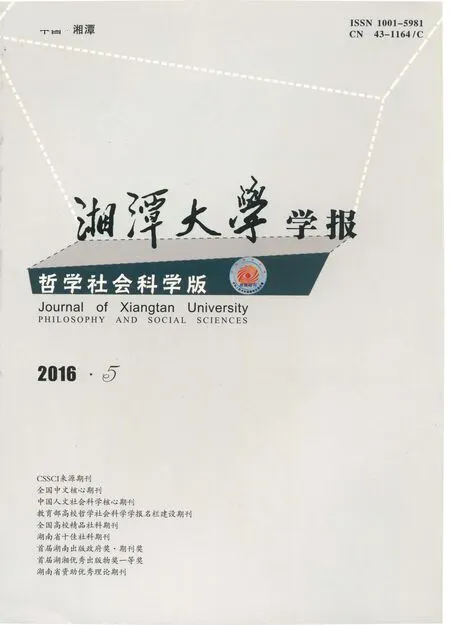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及其反思*
黄宗喜,占 凯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及其反思*
黄宗喜,占 凯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对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释。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寓言”内涵的阐述,包括公与私的关系、寓言的表现力量和文化知识分子的作用三大方面。詹姆逊关注第三世界文学,既有建立“世界文学”的需要,也有立足自身文化的立场对美国文化的批判。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能激发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自觉,同时又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立场。
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民族寓言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各种不同的文明类型与社会制度相遇。面对资本的全球扩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社会和文化的激烈对抗中竭力保全自身。美国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关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文学。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整体特点做了解读:“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1]428由此,“民族寓言”这一描述方式成了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核心。
一、“民族寓言”: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支点
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一种“民族寓言”的性质,个人和政治关系紧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本均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寓言”性质,最典型的是中国作家鲁迅的作品,个人命运的故事中总是隐含着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注。詹姆逊认为“民族寓言”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公私融合的暧昧性。在现代西方世界里,公与私之间,即公共政治和个人生活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詹姆逊通过考察发现早在中国古代,“关于性知识的指南和政治力量的动力的文本是一致的,天文图同医学药理逻辑也是等同的”。[1]431
詹姆逊发现在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中,政治和个人有着相当暧昧的关系。 “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429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力量,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2]256詹姆逊在论述第三世界文本的民族特性时引入“力比多”的概念,他认为在第三世界的故事中“力比多”被严重压制,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在第三世界的文化中,个人、力比多是不自由的缺乏生命力的附庸,它们屈服于更强劲的外部力量,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社会和政治的相关情况。与其说个人的命运是独立个体的盛衰沉浮,不如说是被烙上了深深的民族印记。
中国作家鲁迅的文学作品成为了詹姆逊在论述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时的有力论据,詹姆逊认为鲁迅文本中的“力比多”中心并不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层面的性欲,而是指向口腔阶段的一系列躯体问题,中心的概念是“吃”。鲁迅主要是将“吃”的意义运用到“吃人”的中国社会中去,“吃人”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把人撕裂、吞食。此处的“吃人”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吃人戏剧化地再现当时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同胞之间的荼毒,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有特权的上级对下级的无情盘剥,而且在受压迫的底层人民之间也数见不鲜。
在第三世界的文本中,“政治”与“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潜伏在“个人”的肉体里,是“个人”的影子,在合适的时机曝于公众的视野。在“民族寓言”这一形式中,“个人”处于严重被压抑的状态,“个人”为了表现社会和政治的创伤而存在。
其次,寓言表现力的深刻性。詹姆逊在论述第三世界文学时,经常会引入第一世界文学的相关特点,将二者作对比使差异更明显。关于民族寓言在西方文学中的存在形式,詹姆逊列举了西班牙作家班尼托·皮拉斯·卡多斯的著作。从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来看,卡多斯的小说具有的寓言性远远超越许多著名的欧洲小说。在他的小说《佛吐娜塔和贾辛塔》中,一个男人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来回周旋,妻子和情人分别是中上层妇女和人民妇女的代表。小说的政治寓意是男主人公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在共和革命和波旁复辟之间的犹豫。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卡多斯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寓言性质。然而,卡多斯的小说除了可被解读为对西班牙命运寓言式的评论外,还可理解为 “个人戏剧的比喻式的装饰、仅仅是个人戏剧的强化借喻而已”。[1]438诚然,西方也存在寓言结构,但其寓言结构不会涉及政治,因此难以感受到寓言的力量。
寓言的表现力度在于它的容纳能力,蕴含着丰富的意义。鲁迅笔下的阿Q,受到欺压之后不想着如何反抗而是自我欺骗“这并不是屈辱”,并且沉浸在“天朝至上”的极大优越感中;另一方面,那些嘲笑、戏弄和欺负阿Q的懒汉和恶霸,通过欺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从而实现心理上的满足。这个寓言式的形象可被解读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内涵,这也是寓言容纳能力之广阔的体现。
“民族寓言”的结构是用个人行为和遭遇去反映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现状,终极目标是批判。寓言具有表现主题的深厚性,它所具有的讽刺力度远远比传统的现实主义来得有效。20世纪中叶,非洲在接受名义上的民族独立之后,激进作家如奥斯曼在作品《夏拉》和《汇票》中展示,他们渴望改革和社会更新,可一旦自己方面的人同外界操纵势力勾结之后,要想找到促使改革实现的社会力量可谓是蜀道之难。于是,奥斯曼尼将讽刺性的民族寓言融入到叙事文之中,获得了比传统现实主义更好的表达效果。
“民族寓言”在非洲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一大特点是双重历史观的存在,传统和现代交织。在奥斯曼尼的作品中,古代或者部落的因素发挥着微妙的作用,詹姆逊认为《汇票》讲述传统的价值观在当代社会中的历史转变,一个穆斯林有责任对贫苦人布施,然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这种神圣职责被社会各阶层的人利用,变成盘剥他人的理由。传统施舍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变包含着传统和现代的激烈对峙,是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的冲击之后造成的结果。詹姆逊认为这是一种双重的历史观,“古老习俗被资本主义关系的超级地位剧烈地改变和变得非自然化”。[1]443-444
在第三世界文化中,“民族寓言”具有内容丰富的容纳能力,可被解读成不只一种意义;“民族寓言”所表现的主题也极其具有力度,批判和讽刺力量的深厚程度可见一斑;在“民族寓言”之中,我们也能看见双重历史观的存在,看见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复杂性。
最后,知识分子的双重作用。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探讨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第一世界文化中,知识分子是独立自由的表现个体,不受政治和社会的牵绊。詹姆逊认为在他们中间,“知识分子”仅仅就是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个体。而 “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1]434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第三世界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永远不会是单纯的“以梦为马浪迹天涯”的文人墨客,他们很难撩开身处的环境,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纵横驰骋。他们肩负着双重责任,一方面他们用笔辛勤耕耘,创造出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供受众娱乐消遣或学习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以文字为武器,必要的时候赋予文字一种真枪实弹的力量,将语言文字作为鼓舞士气的催化剂或口诛笔伐的利剑,他们是将国家和民族命运置于心中的政治斗士。
面对糟糕的社会环境和国民的愚昧以及麻木不仁,鲁迅从一开始的“医学救国”到后来的“文学救国”,拯救和改良社会的方式从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转移到改变国民劣根性,以唤醒沉睡的国民。鲁迅职业的转变,促成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双重作用的发挥。第三世界文化中知识分子的双重作用并不单单是传统遗留下来的结果,更多的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渗透时做出的回应。在他们肩负的政治作用中,除了对自身制度的批判之外,很大一部分是积极对抗外部的压迫,而压迫是西方国家殖民化的表现。
二、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国家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因此詹姆逊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1]427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第三世界的文化面对第一世界的文化侵略,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受到资本多方位的渗透。
关注第三世界文学适应了美国重新建立文化研究和重温歌德“世界文学”的需要。长久以来,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文学观。然而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加速,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们外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世界,即与他们的文化形式不同的第三世界文化。重建文学研究和建立“世界文学”需要打破这种文化强权的状态。詹姆逊提出任何世界文学的概念都必须特别注重第三世界文学,立足于世界文学,认真审视第三世界文学。
在论述第一世界文化的优劣时,所参照的准则是第一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詹姆逊认为这样一种用第一世界文学的标准去衡量第三世界文学的做法十分不妥当。第三世界的小说不会提供普鲁斯特或乔伊斯那样的满足,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小说水平的低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差异客观存在,重建“世界文学”的必要性便显露无疑。只有将第三世界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总体范畴中去,狭隘的见解便会减少,人文的贫困便会逐渐消解。
詹姆逊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批评家,他在谈到自己的基本政治任务时说他要不断提醒美国公众,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很多情况不同的民族。在论述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时,他通过和第一世界国家文化的比较,詹姆逊向我们呈现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二元对立情形。当第三世界文学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中时,无论是政治和个人关系的巨大差异,还是知识分子作用的不同,对西方世界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异己的。詹姆逊多次提醒西方国家的人要坦然地面对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差异,坦然地面对全球范围分裂的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不要酣睡。第一世界的文化知识分子就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必承担起参加实践的政治斗士的责任,因此他们也无法理解第三世界文学作品和政治的紧密关联。
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体现出第三世界国家回归民族环境、建立民族文学的需要,实质上是一种深层次寻求民族独立、平等和发展的需要。第三世界国家随着民族的独立和经济政治上的发展,势必会对文化的繁荣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世界文学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第三世界的文学应拥有其独特的姿态,而不是成为第一世界文学的附庸。
“民族主义”是一个在美国被合理清算了的问题,然而在第三世界里“民族主义”具有重要价值。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的对象,处于被殖民的位置,面对现代化的渗透,他们迫切想保持自我特色,不被西方世界的文化观念同化。第三世界的文化知识分子早就意识到文化所处的岌岌可危的位置,于是他们希望建立起属于自身的文学形式,不至于在文化侵袭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摆脱“西方中心化”的诉求十分强烈,他们希望在评判民族文学时不是以第一世界文学的准则为黄金定律。他们十分关注国家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个集合词,如何具备自身独有特性并且超越其他民族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并且,他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
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是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现代化渗透后的必然选择,是西方国家建立“世界文学”的需要,是西方世界诚实面对全球范围内分裂事实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美国公众和知识分子的善意提醒,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民族文学、回归民族环境的需要,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中心化”、寻求民族平等和发展的愿望。
三、“民族寓言”视野的重要性和狭隘性
“民族寓言”的理论内涵是在说明第三世界文学文本总是试图用个人的命运去反映集体,其实质是一种反抗,是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现代化渗透时的反抗。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既要面对外部的殖民和侵略,又要面临传统文化糟粕的威胁,由此处于传统和现代夹击的尴尬处境。文化知识分子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困境,于是他们在文学中融入自身的思考并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后给原有的集体生活方式带来无情破坏的不满,这种批判也有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性考量。“民族寓言”让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前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认识到当前民族国家的处境,从而有意识地去防范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现代化的渗透,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实现自身的价值。
“民族寓言”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条理解自身文化的途径,感受到现实和集体的力量。一定程度上,詹姆逊的“民族寓言”文学理论让第三世界国家在审视自身文化的同时,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特点和不足。一些第三世界文化知识分子对詹姆逊“民族寓言”的解读并不买账,但不可否认的是,詹姆逊的“民族寓言”提供了一种视野和方法,有助于深刻理解文本,从而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
因此,“民族寓言”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意义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文学文化上的。
詹姆逊认为西方国家正处于黑格尔所说的奴隶主的至高地位,“我们所形成的上层奴隶主的观点是我们认识上的残缺,是把所观物缩减到分裂的主体活动的一堆幻想。”[1]447詹姆逊认为用这样片面的认识去把握整个世界是有失偏颇的。认识第三世界文化有助于打破自以为是的第一世界主宰世界的骄傲,坦然面对全球范围内分裂的现实,而不是活在自我的幻影里面。
对于不习惯寓言视野的西方国家而言,有限的生活经验不利于他们去理解类型全然不同的人民和文化生活。所以,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给了西方国家人民一个机会去了解和自身全然不同的文化。虽然西方国家面对第三世界文本时是抗拒的,但这种抵制本身可以让他们看到地球大部分的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在现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理解有助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
之前一切讨论和论述的前提是詹姆逊提出的“民族寓言”视野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第三世界的文本带有“民族寓言”的性质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吗?对此,批评家介入的角度是“民族寓言”理论的非全面性,这一理论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的特点。批评家认为许多问题都无法被纳入到“民族寓言”的范畴,如性别问题、种族解放问题和区域斗争问题等。在众多批评的声音中,印度学者艾哈迈德的批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认为詹姆逊的文章归根结底带有性别色彩和种族背景,艾哈迈德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1935年至1947年这段时期,虽然时代的主题是民族解放和反抗殖民化,但乌尔都语小说未曾涉及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就他所知道的而言,“那个时期的所有小说都首先是关于其他事情的……反殖民主义的主题被包裹在许多小说中,但从来不是一个排他性甚或主导性的重点。”[3]3-25
刘禾对于詹姆逊将第三世界文学理论解读为“民族寓言”的假设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詹明信的假说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而并非纯属谬误,因为它运转于第一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取向和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实践中。”[4]267-268
王钦认为刘禾对詹姆逊“民族寓言”解读方式的批评源于他对艾哈迈德的认同,并评论他们俩的做法有犯僵化经验主义的嫌疑,他认为在詹姆逊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论述中,民族、阶级和性别的概念并不指向单一的内涵,而具有一定的外延。而艾哈迈德和刘禾固定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将趋于斗争或女性权利斗争与民族解放经验对峙起来,并以此反对‘民族寓言’的提法……”王钦提出“‘民族寓言’应该被理解成形式而非主题”,而多数批评者在解读这一概念的时候,将“形式”默认为“主题”,因此会被误认为有很多超出主题之外的内容。王钦的主要论点是:“杰姆逊的‘民族寓言’概念应当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装置,它在文学的意义上对跨国资本主义进行批判。”[5]212
“民族寓言”的理论局限性受到来自各方学术人士的批判,事实上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面临着其身份的特殊带来的尴尬,即他作为西方世界文化知识分子身份的尴尬。“民族寓言”是詹姆逊在对西方文化理解和对比的基础上,对第三世界文化特点做出的归纳和总结。虽说他尽力保持客观公正,但自身文化的深厚烙印难以消除。因此,詹姆逊关注第三世界文学,既有建立“世界文学”的需要,也有立足自身文化的立场对美国文化的批判。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能激发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自觉,同时又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立场。
[1]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Aijaz Ahmad.Jameson’sRhetoricofOthernessandthe“NationalAllegory”[J].Social Text,1987(17).
[4]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王钦.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一个辩护[J].文艺理论研究,2014(4).
责任编辑:万莲姣
Reflections on Frederic Jameson’s Third-world Literature Theory
HUANG Zong-xi, ZHAN Kai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China)
Frederic Jameson, a post-modern Marxist, has elaborated on the third-world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period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ge.Jameson’s third-world literature theo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fable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he representation power of fable and 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s.The reasons why Jameson concerns about the third-world literature result from the need to establish “world literature” and his criticism of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 own cultural background.Jameson’s third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can arouse the n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meanwhile its standpoint is obviously West-centered.
Frederic Jameson;the third-world literature theory; national fable
2016-05-10
黄宗喜(1978-),女,湖北恩施人,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文艺理论研究;
占 凯(1992-),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批评的踪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中国”(项目编号:13YJC751017)阶段性成果;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以詹姆逊为中心”(项目编号:14YBA362)阶段性成果。
I0-02
A
1001-5981(2016)05-01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