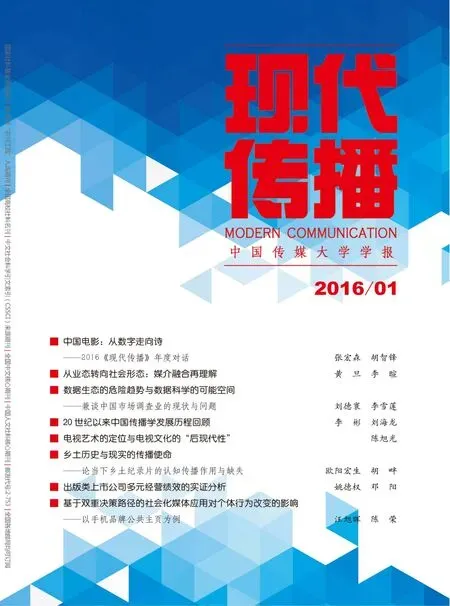艺术传播学视野下声乐表演艺术的审美心理外层结构研究
■ 赵志奇
艺术传播学视野下声乐表演艺术的审美心理外层结构研究
■ 赵志奇
在当今的音乐艺术传播活动中,声乐演唱与表演作为一个艺术实践体系,仍然是主要的音乐样式之一。在创作系统、表演系统与欣赏系统三个传播阶段中,观众审美作为声乐表演艺术传播过程中的最终环节,具有实现其传播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意义。由此,将声乐表演活动中的观众作为审美主体,对影响其欣赏心理和审美心理产生的诸方面进行探讨,便体现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一、词曲创作者
词曲作者与观众的关系依靠声乐作品来维系。创作者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以及自己的生活体验,运用音乐创作元素(语言、旋律、配器)等创作出声乐作品文本,最终形成音乐专业符号的物化载体——声乐曲谱。在声乐作品文本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的情感表达应具有一种召唤结构,具有可阐释、被解释和被表演的空间。词曲创作者往往依据自身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对接触到的生活事件或情感感受进行理解,同时产生艺术灵感,最终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表达体现出来,以构成完整的声乐作品文本形式。
在声乐表演艺术活动中,词曲创作者作为艺术传播活动的源头,是声乐表演艺术信息的制造者,而受众作为声乐表演艺术信息的接受者,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影响的互动关系。词曲创作者的最终指向是欣赏者,并且在创作活动中受审美主体的反馈来促进创作的提高,而观众也因词曲创作者的声乐作品体验到精神上的审美感受,从而满足心理的审美需求。
从艺术交往的角度而言,观众与词曲作者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观众对词曲作者个人及其作品比较了解和熟悉,这样便会很容易进入艺术欣赏活动中,并获取较好的审美体验,产生良好的审美互动;另一种则是对词曲作者非常陌生,那么观众在艺术欣赏活动中,所获取的审美体验或者审美互动的效果就会相对较差。
二、声乐作品
声乐作品作为词曲作家精神创作的产物和创作活动的物化载体,自身有着客观存在的内部结构规则,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客观基础的精神性存在,因此,声乐作品不得不依附于某种客观外壳而存在。在音像资料中,依存于CD、电脑等载体;在现场演出活动中,依存于表演者的声音等。例如,恋人之间相互表达思念之情而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乐谱中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网络音乐中某歌手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歌曲传播的媒介方式虽然不同,但是它们所负载的是同一个精神实体,即同一部声乐作品。从艺术传播的角度而言,这些相同的声乐作品,凭借这些不同的客观媒介进行传播,观众才能欣赏、理解声乐作品的精神性表达,正如英加登所说:“物质世界作为背景参加进来,并以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基础的形式展现自身。”(1)
由上可知,在声乐作品文本中,其存在的媒介物质是声乐文本结构体现的一种物质载体。声乐作品是审美接受环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连接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纽带。那么,旋律和语言作为声乐作品的本体性存在之外,声乐作品自身结构还有哪些层次和内容呢?
第一是结构音响层。无论是口头形式还是乐谱符号,语音语调都是声乐作品最外显的音响层。但是它与日常生活中的语音语调并不相同,日常生活中的语音语调是在日常语境中所产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声乐作品所表现的特殊意象,是与声乐作品的体裁、情绪等元素相联系的。第二是意义建构层。在声乐作品的文本中,歌词是诠释语义功能层面的唯一工具,而音乐所传达出的情绪则是构建音乐意义层面的重要途径。《欢乐颂》的音乐没有歌词也不会被理解成哀伤的乐曲;同样也不会把《孟姜女》的音乐理解为甜蜜的情感体验。因此,优秀的声乐作品,音乐的情绪指向与歌词的语义指向总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2)第三是意象意境层,这是词曲作家通过旋律和歌词,对内外客观存在认知的重新创造。在声乐作品中,意象意境层已从词曲作家的心理层面转化乐谱信息,观众通过欣赏,在声乐作品提供的意象意境的基础上,重新在心理层面上构建起新的审美意象。第四是思想感情层,它是声乐作品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实质性体现。经典的声乐作品文本不仅要给观众提供多层面的审美元素和审美体验,也要给观众提供对其人生成长有意义的人生哲理或感悟,所以在声乐作品创作过程中必须以真情实感表达贯穿创作始终。
三、演唱者
在声乐表演艺术系统中,声乐演唱者实质是对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通过自身对声乐作品的理解、解读与演绎,依据自身嗓音的表达和塑造,以及在演唱过程中的形体展现,统合自身的歌唱技巧与方法,运用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等方式,以二度创作的方式向受众表达词曲创作者以及自身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和精神意义。
从本质上讲,观众对声乐作品思想内容和情感内容的审美接受,是声乐表演艺术的最终目的,也是理解、接受声乐作品,获取审美感受的唯一方式。演唱者与观众虽然作为单一的主体,但统一于声乐表演艺术过程中,所以演唱者必须重视观众的审美地位。由此可见,演唱者二度创作所展现出的新的作品内涵,对欣赏者的审美接受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本文所探讨的观众审美的外层心理结构中,声乐表演者的个人技术和艺术等综合素养,对受众的审美接受与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审美主体在欣赏和审美质量上的要求,必然对演唱者在平常训练活动中促使自身艺术素养的综合提高,起到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欣赏环境
传统的剧院剧场、音乐厅等审美场所是营造审美情景的重要欣赏环境。具有创意的舞台环境,搭配协调的灯光音响,有助于观众获得更好的审美感受。
观众作为欣赏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对音乐作品的审美接受是实现声乐表演艺术价值的重要环节。同处于一个音乐厅的观众,他们之间有着隐性的同化性和目的性,同化是指观众与观众之间观赏情绪的相互影响。比如,对音乐作品具有欣赏能力和审美经验的观众,会首先发现表演过程中那些闪光或者瑕疵之处,他们的反应会使更多的人获得共鸣。
剧场和音乐厅里的观众,既有群体心理体验也有个体心理体验。在集体欣赏过程中,每位观众对于现场的音乐都有个人的审美心理体验,此时,现场的音乐信息作为一个信息源动,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共同的艺术氛围,从而形成观众欣赏音乐会时的群体审美体验;另外一种露天敞开式的审美体验场所——广场演唱会,不同于音乐厅这种审美场所。广场音乐会演出过程中演员与观众直接性的互动和交流(比如观众情动之时的尖叫与呐喊),虽然会带来些许视听干扰,但现场互动时的情感交流和宣泄,反而使观众获得更多的审美感受。而在音乐厅里的观众进入审美过程后,由于音乐厅观赏礼仪的限制,只能独自安静地观赏,即使自己觉得音乐会相当精彩,也不能表达出类似尖叫等超乎寻常的情感宣泄形式。因此,音乐厅或剧场的观众之间并不追求审美呼应,大多情况下集体审美效应是个人化的。(3)
以上的剧场和音乐厅欣赏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受众在场的现场审美,但以目前传媒技术的发展来看,就欣赏环境而言,除现场审美之外,还有一种非现场审美方式:声乐表演者通过电视、网络传播等媒介传播形式,使受众体验到虚拟环境下的声乐表演节目,这种非现场的审美虽然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在媒介传播中的声乐表演节目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受剪辑或现场切换因素的处理,受众在审美活动中欣赏到的镜头实际上是在剪辑师等工作人员的后期制作中过滤后的表演。也可以理解为,受众在欣赏过程中视线选择的主动性失去了一些(4)。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观众作为声乐表演艺术传播活动中最终的一个接受环节,在审美活动中受到词曲创作者、声乐作品文本、演唱者、传播途径和欣赏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以上环节是受众审美心理的一种外层结构,这种外层结构以一种物化载体的形式,潜意识地存在于受众审美活动的过程中,同时,它们与受众审美的心理和经验交织作用在一起,共同形成了观众审美心理活动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只有了解受众审美主体的心理外层结构及其审美需求,才能不断完善声乐艺术传播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从而更好地为词曲创作和声乐表演艺术服务。
注释:
(1) 英加登:《现象学美学:确定其范围的尝试》,美国《美学与艺术评论》1975年版,第260页。
(2) 靳相林:《声乐表演艺术中观众审美心理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4) 非现场的审美,包括记录在磁带、CD、MP3、KTV等声像工具上的审美也属于声乐审美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审美活动脱离现场后变成主要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的活动,其欣赏环境也变得极其自由。这种审美活动中的观演关系是相对滞后的,这种关系往往转变为稍后的音乐批评活动或购买的商业行为,而其心理活动则由于欣赏环境的改变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变得较为模糊,限于篇幅,在此暂不作论述。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李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