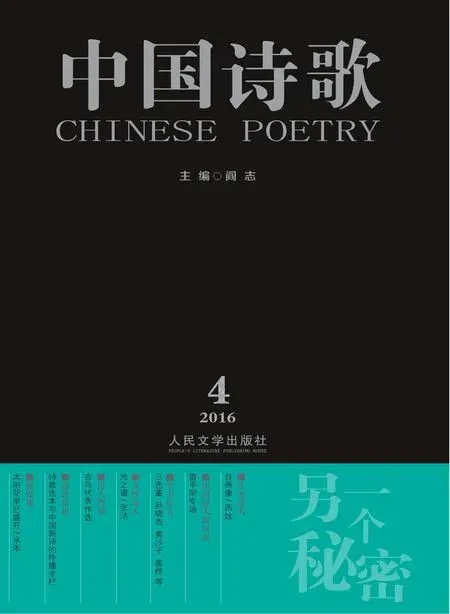邵洵美诗选
邵洵美诗选
序曲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莎茀
莲叶的香气散着青的颜色,
太阳的玫瑰画在天的纸上;
罪恶之炉的炭火的五月吓,
热吻着情苗。
莫非不与爱神从梦中相见?
啊尽使是一千一万里远吓,
请立刻回来。
你坐着你底金鸾车而来吧,
来唱你和宇宙同存的颂歌——
像新婚床上处女一般美的,
爱的颂歌吓。
你坐在芦盖艇石上而唱吧,
将汹涌的浪涛唱得都睡眠;
那无情的乱石也许有感呢,
听得都发呆。
蓝笥布的同性爱的女子吓,
你也逃避不了五月的烧炙!
罪恶之炉已红得血一般了,
你便进去吧。
你底常湿的眼泪烧不干吗?
下地的雨都能上天成云呢。
罪恶之炉中岂没有快乐在?
只须你懂得。
仿佛有个声音在空中唤着:
说不出不说出当更加苦呢,
还是说了吧!”
海水像白鸥般地向你飞来,
一个个漩涡都对你做眉眼。
你仍坐着不响只是不响吗?
五月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
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
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这里的生命像死般无穷,
像是新婚晚快乐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将比红的血更红。
啊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
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
天堂正开好了两扇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Madonna Mia
啊,月儿样的眉星般的牙齿,
你迷尽了一世,一世为你痴;
啊,当你开闭你石榴色的嘴唇,
多少有灵魂的,便失去了灵魂。
你是西施,你是浣纱的处女;
你是毒蟒,你是杀人的妖异:
生命消受你,你便消受生命,
啊,他们愿意的愿意为你牺牲。
怕甚,像锋针般尖利的欲情?
刺着快乐的心儿,流血涔涔?
我有了你,我便要一吻而再吻,
我将忘却天夜之后,复有天明。
颓加荡的爱
睡在天床的白云,
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
许是快乐的怂恿吧,
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
啊和这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
上海的灵魂
啊,我站在这七层的楼顶,
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
下面是汽车,电线,跑马厅,
舞台的前门,娼妓的后形;
啊,这些便是都会的精神;
啊,这些便是上海的灵魂。
在此地不必怕天雨,天晴;
不必怕死的秋冬,生的春:
火的夏岂热得过唇的心!
此地有真的幻想,假的情;
此地有醒的黄昏,笑的灯;
来吧,此地是你们的坟茔。
花一般的罪恶
那树帐内草褥上的甘露,
正像新婚夜处女的蜜泪;
又如淫妇上下体的沸汗,
能使多少灵魂日夜醉迷。
也像这样个光明的早晨,
有美一人踏断了花头颈;
啊,是否天际飞来的女神?
和石像般跪在白云影中,
惫倦地看着青天而祈祷。
她原是上帝的爱女仙妖,
到下界来已二十二年了。
她曾跟随了东风西方去,
去做过极乐世界的歌妓;
她风吹波面般温柔的手,
也曾弹过生死人的铜琵。
她咽泪的喉咙唱的一曲,
曾冲破了夜的静的寂寞;
曾喊归了离坟墓的古鬼;
曾使悲哀的人听之快乐。
她在祈祷了,她在祈祷了,
声音战颤着,像抖的月光,
又如那血阳渲染着粉墙,
红色复上她死白的脸上。
“啊,上帝,我父,请你饶恕我!
你如不饶恕,不妨惩罚我!
我已犯了花一般的罪恶,
去将颜色骗人们的爱护。
“人们爱护我复因我昏醉,
将泪儿当水日夜地灌溉;
又卖弄风骚吓对我献媚,
几时曾想到死魔已近来。
“啊死魔的肚腹像片汪洋,
人吓何异是雨珠的一点;
啊,死魔的咀嚼的齿牙吓,
仿佛汹涌的浪涛的锋尖。
“我看着一个个卷进漩涡,
看着一个个懊悔而咒诅,
说我是蛇蝎心肠的狐狸,
啊,我父,这岂是我的罪过?
“但是也有些永远地爱我,
他们不骂我反为我辩护;
他们到死他们总是欢唱,
听吧,听他们可爱的说诉:
“世间原是深黑漆的牢笼,
在牢笼中我犹何妨兴浓:
我的眉散乱,我的眼潮润,
我的脸绯红,我的口颤动。
“啊,千万吻曾休息过了的
嫩白的醉香的一块胸膛,
夜夜总袒开了任我抚摸,
抚摸倦了便睡在她乳上。
“啊,这里有诗,这里又有画,
这里复有一刹那的永久,
这里有不死的死的快乐,
这里没有冬夏也没有秋。
“朋友,你一生有几次春光,
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荡漾?
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
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
“四爿的嘴唇中只能产生
甜蜜结婚痛苦分离死亡?
本是不可解也毋庸解释,
啊,这和味入人生的油酱。”
上帝听了,吻着仙妖的额,
他说:烦恼是人生的光荣;
啊,一切原是“自己”的幻相,
你还是回你自己的天宫。
仙妖撤脱了上帝的玉臂,
她情愿去做人生的奴隶;
啊,天宫中未必都是快乐,
天宫中仍有天宫的神秘。
季候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
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我爱金子为了她烁烂的色彩;
我爱珠子为了她晶亮的光芒;
我爱女人为了她们都是诗;
啊,天下的一切我都爱,
只要是不同平常。
但是,有的时候,
极平常的一个肥皂泡,一声猫叫,
或是在田沟里游泳的蝌蚪,
也会使我醉,使我心跳,
使我把我自己是个诗人忘掉。
是不是把肥皂泡当作了虹,
把猫叫当作了春的笑声,
把蝌蚪当作了女人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全不知道;
你得去问那个不说诳的诗人。
牡丹
牡丹也是会死的
但是她那童贞般的红,
淫妇般的摇动,
尽够你我白日里去发疯,
黑夜里去做梦。
少的是香气:
虽然她亦曾在诗句里加进些甜味,
在眼泪里和入些诈欺,
但是我总忘不了那潮润的肉,
那透红的皮,
那紧挤出来醉意。
蛇
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
你垂下你最柔软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
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哪一边的嘴唇?
他们都准备着了,准备着
在同一时辰里双倍的欢欣!
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
磨光了多少重叠的竹节:
我知道了舒服里有伤痛,
我更知道了冰冷里还有火炽。
啊,但愿你再把你剩下的一段
来箍紧我箍不紧的身体,
当钟声偷进云房的纱帐,
温暖爬满了冷宫稀薄的绣被!
二百年的老树
在那庙前,水边,有棵老树,
光光的脑袋,皱皱的皮肤,
他张开了手臂远望青山,
像要说诉他心中的闷苦。
二百年前在这里种了根,
便从未曾动过一寸一分,
他看着一所所村屋砌墙,
他看着一所所村屋变粉;
他看着几十百对的男女,
最初都睡在母亲的怀里,
吮着乳,哭,笑,小眼睛张闭,
不久便离了母亲去田里。
待到男的长大,女的长美,
他们便会在树荫下相会,
一个忘记了田里的锄犁,
一个忘记了锅里的饭菜。
“我骑在黄牛背上吹小笛,
你坐在竹篱边上制夏衣,
春天快跨上那山头树顶,
别忘了今晚上到后园去。”
“我坐在竹篱边上制夏衣,
你骑在黄牛背上吹小笛,
春天已跨上了山头树顶,
别忘了昨晚上在后园里。”
他看着他们的脸儿透红,
他看着他们弯了腰过冬;
没多时他们也有了儿女,
重复地扮演他们的祖宗。
他已看厌了,一件件旧套,
山上的老柏,河上的新桥;
他希望有一天不同平常,
有不同平常的一天来到。
女人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
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
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