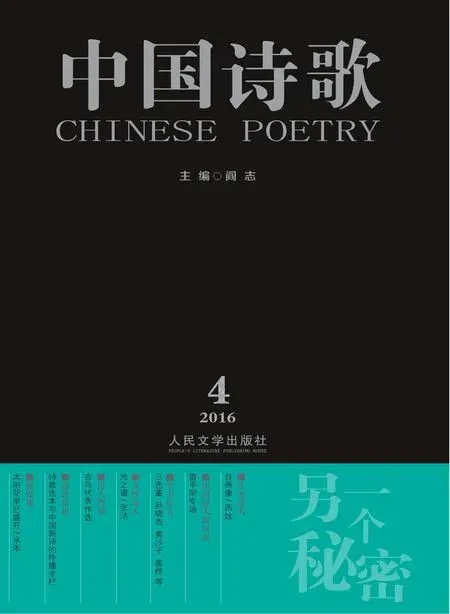中国诗人面对面
——雷平阳专场
□主讲人:雷平阳
主持人:李 强
中国诗人面对面
——雷平阳专场
□主讲人:雷平阳
主持人:李 强
时间:2015年8月16日 地点:卓尔书店
李强:大家好!虽说已经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很炎热。在这个炎热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大家聚集一堂,感受诗歌分享诗歌,说明是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人。如果有了好的主讲人,没有好的听众,没有好的互动,那么这个诗歌的盛会也是有缺陷不圆满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如雷贯耳、电闪雷鸣、雷打不动的雷平阳先生。请雷先生为我们讲讲他的诗歌创作历程。
雷平阳:这次在来武汉之前,我还去了湖北宜昌、神农架,去看了葛洲坝电站,也看了三峡电站,看的过程中,当我站在那里,其实心里是非常难受的。我知道大坝下面的江水它曾经来自我的家乡,流过我的家乡,流到这个地方,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叫《底线》,是说我一生不会割舍的东西是什么?其中就有一个南河大坝。在我八十年代开始写诗的时候,和我一起写诗的一个哥们,他曾经写过《金沙江》,他是怎么写的?就短短的几句,他说:“年轻时,我们看到过的大江,它在金属的槽道里自由地飞翔。”几句话就把金沙江的形态生动地写出来了,因为金沙江河谷的两岸基本上都是石头,就像金属的槽道一样,而大江就在金属的槽道里自由地飞翔。但是二十多年过去,我看到的大江,唐诗里面的巫峡、瞿塘峡、三峡,“轻舟已过万重山”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最快的速度,因为那是水的速度,早已不是现在的大江。现在无论三峡也好,葛洲坝也好,或是仅次于葛洲坝和三峡以外正在我的家乡大兴土木的中级容量的三个电站,都改变了大江。上个月,我曾经沿着那一带走,因为我最近在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叫《乌蒙山记》。我沿着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游走,走的时候发现,那条自由飞翔的大江已经没有了,每一处当年浑浊的江水,有肆意奔流姿态的江水,全部消失了,都变得像蓝天一样蓝。看到那种蓝的样子,我悲从中来。在大江的两岸,我拍了不下五百张照片,是什么样的照片呢?都是有人静静地坐在江边岩石上看着大江的照片。这些人为什么要看大江?因为水底下有他的故乡。所有被大坝切断的故乡都被淹没了。溪洛渡电站开工之前大搬迁的时候,我当时是《滇池》杂志的主编,我请了一个摄影师去拍摄。搬迁的关键是搬祖坟。由于计划生育,我们曾经人口繁茂的家族,现在人越来越少,但是祖坟却是一大片的,每个祖坟在搬迁的过程中政府只补贴两千元。我们平常骂人说,被人挖了祖坟,而现在却自己要去挖自己的祖坟。挖开祖坟后,捡出一堆白骨,装在一个罐子里面。我们拍到的一些镜头很惊心动魄,有些人家整个屋子里全是罐子,全部是祖先的尸骨。搬迁开始以后,所有人把这些罐子背在身上往外面走。还有一些景象也具有很大的反讽意味,在溪洛渡电站修建的时候,它会淹掉一个县城,云南省绥江县就被淹掉。绥江县在一个斜坡上面,它修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有毛泽东的塑像,很多家族挖完自己的祖坟,会走到毛泽东的塑像下面,抱着自己祖先的尸骨合一张影,然后才踏上搬迁的道路。这种为了经济的发展而改变自然的速度,比江水流得还快。
去年华语传媒文学奖颁奖的时候,邀请我去做颁奖嘉宾,在广州的一个街头,他们搞了一个诗歌朗诵会,我当时喝了一点酒,上去的第一句话我就说,狗娘养的广东,就为了你们狗娘养的广东,云南山河破碎。为了保障整个广东的工业系统能够有序运转,所有的电站都建在云南。众所周知,云南不管被叫作香格里拉也好,叫作勐巴拉西也好,都是人间天堂的意思。徐悲鸿的太太廖静文,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云南这种地方除非是为国家做过重大贡献的人,才配在那里居住。那是他们对那个地方的赞美,或者说那个地方的美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又被叫作“亚洲的水塔”,可以说除了黄河以外,多少大水系都流经那里。云南除了金沙江,还有一条大江叫澜沧江,澜沧江是往南流走的,在我们这边叫澜沧江,到了东南亚就叫湄公河。如果你们有过出国的经历,来到湄公河边就知道,那里是人间天堂。我曾经在我的一篇随笔文章里写道,我真想不通中国的古代史,整个战乱史,老是讲河西走廊,整天在那边打仗,有什么好打的?那时候为什么不把整个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国土呢?因为实在太富饶,沃野千里。在湄公河两岸的城市,寺庙林立,老百姓都信佛,民风很慈善。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母亲河,说到湄公河,其实湄公河就是整个东南亚的母亲河。但在中国,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在澜沧江边修了一个漫湾电站,接下来又修了大朝山电站、小湾电站、糯扎渡电站、景洪电站,现在又要修一个橄榄坝电站,就是一段一段地修。当然我从来不反对一个国家发展经济,但是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少道德的代价,或者多少山川的代价,我们才能满足?
我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基诺山》,基诺山我曾经去过很多次,那是我到过的感觉最神奇的一座山。比如说我们汉人的很多传说,我们彝族的很多神话传说,是无法指认的。但生活在这座山上的基诺人可以指认他们的天堂在哪儿,地狱在哪儿,人间在哪儿。在他们的文化谱记里面,曾经有过人、鬼、神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分土地的事情。把人、鬼、神分别分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分别代表人间、地狱、天堂。在天堂和人间之间的那一片荒野,也就是热带雨林,这些是鬼住的。所以,为什么人杀了山上的猎物带回家来吃之前,要祭拜鬼神,因为是从鬼的地盘上得到的东西你一定要敬它。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2000年以后,我曾经沿着他们指认的人间走到天堂去,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条路还没生成,根本走不通,两边都是热带雨林,你能感觉到那种太初的气息,那种地老天荒的感觉。到了2000年以后,热带雨林慢慢地在消失。2007年的时候,那里修起了一条公路,交通方便了很多。去年的一天,我独自坐在办公室,觉得很无聊,临时背起一个包,买了一张机票,去了西双版纳,去了以后找到当地的一个朋友,让他开车把我送到基诺山,告诉他我想再走一次天堂、人间和地狱的路,结果走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的热带雨林全部消失了,那种很古老的像桌子一样粗的树全部被砍掉了,仍在山野上面,整个热带雨林都种上了橡胶树。在我的另外一本书《出云南记》里我说过,我不反对人们生活在人世之间,但我们有权利去向往天堂,走向天堂,我不相信从人间到天堂的路两边,必须把所有的热带雨林砍掉,只栽种橡胶。难道经济作物就应该左右我们的所有?从肉体到灵魂?刚开始砍伐的时候,媒体有介入,但第二天又没有任何声音了,媒体的监督实在是苍白无力的。中国的热带雨林面积很小,只分布在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在同样经度和纬度上的世界其他地方全是沙漠。现在为了经济的发展,把这些东西全部砍掉。今天早上我还和一个人开玩笑说,我们的祖国现在真像是一个疯妈妈,她又是妈妈,又是疯子,你不爱她说不过去,但她做出来的事经常是让你没有尊严的,不体面的,她老是让你去接受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2006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跟着《南方周末》的记者重走滇缅路。大家只要有一点记忆或者对抗战史有一点了解的话,会发现整个抗战史里面,打得最惨烈的不是台儿庄战役,不是淞沪会战,甚至不是后来的长沙会战,打得最惨烈的是滇西。因为滇西一旦丧失了中国就全部没有了。我第一次到腾冲的国殇墓园去的时候,一个当地的小女孩,她知道我是写诗的,就问我,在你的印象里面,什么是战争?我说这个话题太大了,我回答不了。她说在我们整个滇西,所谓战争,就是每一片树叶上至少有三个弹孔。像你们都知道的松山会战,在松山旁边有一个几万人居住的小县城,当年战争最惨烈的时候,一个小县城里面,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总共死了六万多人。把六万具尸体摆起来可以摆满整座县城,那种惨烈景象简直难以想象。
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大理,又一路向西沿着滇缅公路走,一直走到缅甸的密支那。对密支那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上网了解一下。那片土地曾经是中国的土地,因为一些形形色色的原因,后来被划过去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仿佛是一夜醒来以后被告知你们是缅甸人了,他们现在自己建学校,用的依然是大陆的教材,授课老师是从云南找来的退休老师。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缅甸人,就算死了,坟头也一定要面向中国的方向,他们所有人都这样。他们的身体回不来,但他们的灵魂都要返回祖国。那片土地曾经是抗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那些人又是无形中被流放掉的海外民族。沿着那条道路走,走着走着会有很多感触。密支那城很有意思,你站在旁边的山头上看整座城,会发现密支那是一座看不见房顶的热带雨林,像一座原始森林,惟一空着的地方是因为伊洛瓦底江从城边流过,像上帝散步的走廊一样。当地有一种说法,只有树木、荆棘和草儿是大地最早的主人,只有树木和荆棘让出来的地方,人们才能建村庄、修寺庙和耕种。所以任何房子,即使是政府的办公大楼,不能比树高。当时有一个华人诗人住在伊洛瓦底江边,他找了一个克钦邦的饭馆请我喝酒,几杯下去他就醉了。醉了以后他站到桌子上,把上面的东西哗啦都掀掉了,他说我要给你朗诵一首诗,我后来记住了其中的一句,“看到中国的公路修过来,缅甸人民在颤抖。”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高速公路通到的地方,开山砍树挖矿,见到大江就修电站,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条美轮美奂的伊洛瓦底江。前年克钦邦和缅政府军开战,把炮弹都打到云南的土地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公路修到密支那以后,又在伊洛瓦底江上面修了一个庞大的电站。然后克钦邦和缅政府军为了争夺电站的经济收入打起来。更可怕的是,当我们在修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要路过大量远征军的陵墓,陵墓既不是国民党修的,也不是我们的政府修的,而是抗战打完以后,很多华人自发把自己的子弟兵一个一个地埋掉,埋在荒野上面。结果我们修路的时候把所有远征军的陵墓全部挖开,那些尸骨被暴尸荒野。《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当时就写了一个报道,标题是《终归无处下跪》。我们的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面前道德水平很低下,那些尸骨被抛在荒郊野外,没有人去收拾。
前年春天,我在泰国的一个靠近金三角的地方度过,跟两个华人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了两句话让我心里实在太震动了,他们说,以前想起祖国两个字心里是温暖的,是想回去的地方,哪怕肉体回不去,灵魂也一定要回去。现在提到这两个字,实在太微妙了。八十年代,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都说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想到祖国这两个字就热血沸腾。我当时是可以留校的,但是我写了一个申请,就分到了一个偏远的县城去。为什么短短二十多年间,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两个字,仿佛它们消失了一样。这种汉语言文字的伟大光辉像从阳光变成了黑夜一样,没了。那种炽热的情感,那种让你热血沸腾的冲动,找不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些景象的时候,如果你还装作无关紧要,装作没看见,只关心一夜暴富,有没有想过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杜甫说“国破山河在”,我们现在是“国在山河破”。
四年前,我带着八岁的儿子回老家,跟着我妈妈一起去给父亲上坟,结果跪在那里的时候,我妈就跟我死去的父亲开玩笑说,我们这两年烧给你的钱至少有几十亿了,你怎么用得完啊?你用不完就拿出一部分出来,把门前的这条河修理一下吧,实在太臭了。我十八岁从那条河边离开的时候,碧波荡漾,两边都是柳木,村里的人喝水都是去那里挑。结果现在这条河流变成了固体,上面结了一层壳,还长出了青草。只要太阳一照,上面就开始泛白,发出的臭味整座村庄都闻得到。终归无处还乡。当然这只是中国环境的一个缩影。
在我的诗集《云南记》中,我写过一个细节,这是真的。有一年春天我回去了,然后当年的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就来看我,我搬凳子让他们坐,没想到我妈妈说,就让他们站着,不准他们坐,那些人只好站着。后来我又去泡茶,我妈妈说不准泡茶。结果这些人站了五六分钟之后不好意思就走掉了。我就和我妈妈说,让他们坐一下喝喝茶是应该的。结果我妈妈说,谁谁谁得了淋病,谁谁谁得了梅毒等等,他们都是进城打工,然后把这些全部带回来了,还传染给了老婆,传染给了家人,很多人倾家荡产。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我们讲到的那个宝相庄严的地方,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正在消失。我有一个朋友,他拍了一个专题片,去年在西方得了一些奖,但在我们这边的电视上不会播放的。他花了五年时间,守在自己的老家拍一个纪录片,就叫《外婆的村庄》。其中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会让大家心里不舒服,但还是要讲一下。其中一个是几个老太太的旁述,说一个老太太死了,她生前养了三个儿子,都出去打工,都下落不明。到底是去了温州,还是去了东北,没有人知道,因为十年之间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带过一分钱,也没有写过一封信,仿佛消失掉一样,这种乡下人进城的大潮已经裹挟了很多人,也难说他们真的是死在了某个建筑工地上。老太太等了十年等不回来儿子,就带着一瓶农药和一把锄头,来到丈夫的坟前,在旁边挖了一个坑,自己躺进去,躺下去以后就拿出农药喝了,死在了坑里面。等到村里人发现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被野狗们吃掉了。这是真的。中国现在有很多这种空荡荡的村庄,荒无人烟。这是一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是讲一对老夫妇,也是两个儿子,也是出去打工,没了。离家七年,没有任何音讯。这对老夫妇就相依为命。他们把家里所有能够挂瓶子的地方,从卧室里的蚊帐,到堂屋,都挂满了农药。别人问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回答为了提防哪一天摔倒下去,爬不起来,可以顺手抓一瓶农药,解决自己。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哪一座青山没有做过战场,哪一条江水里面没有血水?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让一片土地荒上几年,它马上又会变得欣欣向荣。但是道德不一样,道德的败坏让我们感觉到已经置身于一个荒蛮时代。经济上去了,但是人心变了,变得丧心病狂。哪儿才是故乡?故乡到底在哪?去年我老家的一个亲戚死了,我回去了。早先我曾经和我妈妈讲,这个亲戚的赡养我愿意来承担,我妈妈说,她有五个儿子,你去帮助她,你让那五个儿子怎么过?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放?乡村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足以把他们送上审判台。我一想也觉得有道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我这个亲戚赤身裸体地死在荒野上了,在她生前五个儿子依然没有去承担自己的赡养义务。以前都说故乡是心灵的净土,在外面再累再苦,回家就可以得到安宁,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曾经在乡村长大,至少在我的老家,在云南东北山区,这种道德的沦丧,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年前段时间,微信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新闻,关于贵州毕节几个留守儿童的死,曾经让多少中国人掉泪心疼,这样的事情在广大乡村我相信还有很多。据我了解,与贵州毕节交界的云南的一个县城,也发生过三个小孩死在荒野上的事情。我把公安局的那些档案和照片调出来看的时候,内心非常绝望。三个小孩是怎么死的呢?他们放学回到家,发现家里的粮食都没了,就想到旁边一个村庄自己的姑妈家找一点饭吃,结果在路上边玩边走,就走进一座山里去了,迷路了,一直找不到出口,就死在了山里面。照片上三个小孩目光里的那种绝望、那种恐惧、那种空洞,是地狱里才有的目光。其中两个小孩是死在一个斜坡上,死之前手里紧紧抓着一蓬草。看完整个照片你会很绝望,因为当时是在夜里,到处一片漆黑,他们不知道那个坡很矮小,只要放下草,就可以摸索着下来,他们以为下面是万丈深渊,以为会掉下去,在绝望和挣扎中死去了。因为诗人的身份,我经常有机会参加媒体组织的大型公益活动,走进偏远地区,走进边缘人群。走过以后我发现对我挑战最大的是“母亲”这个词。我前面说过祖国像疯妈妈,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疯妈妈。就是在贩毒这条路上,携带毒品的基本上以母亲居多,有些甚至利用自己的孩子来藏毒品,甚至还有人借怀孕的过程来藏毒,我们以为的母亲身上所有崇高的东西,都被她们颠覆了。
今天跟你们讲这些东西,仿佛跟诗歌没有关系,仿佛这些不是诗歌中美妙的优雅的部分。在2000年以前,我曾经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的一员,我也希望我的诗歌都是优雅的、美妙的,都是没有血泪没有悲愤的,我愿意每一个诗人都仿佛是一只夜莺,歌唱着爱情,歌唱着天空,歌唱着大地,歌唱着人间最美最善的那份情感。谁不希望这样呢?当我们置身在这种表面的城市繁华里面,享受现代化高科技带来的便捷和愉悦,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走出去,你会发现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只是被我们忽视了。去年是杜甫诞生1300周年,中国作协请我写一篇纪念杜甫的文章,我写了,标题就是:《向杜甫致敬》,第一句话我说,人的身体上有两样东西永远是白的,一是白发,二是白骨。众所周知,杜甫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经历了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由盛转衰的过程,生活流离失所,他的很多作品就是产生在流亡的路上,他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遍地白骨,人间有哀痛有战乱,所以,这些白骨来到了他的诗篇中,而一个诗人的慈悲心让他的头发早早的就白了。云南大学曾经有一个教授叫刘文典,是中国研究庄子的一流大师。有人问他,什么是诗?他就回答了一句,观世音菩萨。别人不明白,于是他就进行了解释,观世,就是观察世间,每个诗人要学会观察世间,体认社会,体认世道人心。音,是语言的音韵之美,传统的精华要保持。菩萨,是指每一个诗人要有菩萨心肠。所以说,当我们茫然不知道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菩萨心肠,我们的双眼被很多假象蒙住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在这种表象之后,到底有多少道德伦理等精神上的东西在大面积地丧失。作为诗人,我们每首诗歌都应该是自己的审判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社会在蓬勃发展但是精神在极度丧失的年代,一样是乱世。
很多年前,我一个做地产的朋友搞了一个新春party,约了很多人去参加,其中有官员,有商人,也有所谓的名流,去之前,我把一个问题印在纸张上,像发传单一样每个人都发一份,我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回答。大家都笑着同意了。我的问题是:你心慌吗?为什么?结果每一个人都回答心慌。他们的财富地位家庭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但心依然慌乱找不到一个地方安放,仿佛从来没有心安理得过,老是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灾难要发生,有大的问题要出现,心就是放不下来。就像这次天津爆炸事故,即使你身在几公里之外,那一声爆炸也可能把你摧毁,没办法安心。是谁把我们的心弄成这个样子?谁把我们的心弄丢了?当然也可以拷问自己,但是我想还是这个时代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相信宗教里面讲到的轮回,所以我们可以把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东西一夜之间透支。《西藏生死书》里面说,只要你相信轮回,你会知道下辈子你还会来到人间,你就会保护这个世界,因为以后你还要在这里生活。西方的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是教人你要忏悔,你要敬畏,要有约束,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我的写作就是在寺庙旁边的写作,因为我得有一个寺庙,我得有一双神的眼睛在那盯着我,我得知道世俗的底线或者道德的底线。而我们身边有多少人,甚至我们的亲人,都在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底线。昆明有一个滇池,我在主编《滇池》杂志的时候,请了一个摄影师,把引牛栏江水洗滇池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了,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为艺术。滇池里本来就有水,我们引水来洗水。苏东坡说,以水洗水是美到极致的干净。我们现在是把一面湖泊弄脏了,然后把一条大江截断了来引水,花了几百亿。这个行为艺术真是惊心动魄,但是如果你去寻找,到底谁是污染滇池的罪魁祸首,难道就是那几家被勒令关门的排放污水的企业吗?你永远找不到所谓的罪魁祸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魁祸首,我们都是所有罪恶的同谋,我们都参与了。因为这是整体精神上的彻底崩盘。我们今天曝光了一家厂在滇池里排放污水,结果这家厂的代言人竟然是杨丽萍,谁该审判?审判这家厂,还是审判杨丽萍?杨丽萍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女神一样的人,但她代言的那家厂正在往滇池里大量排放污水。谁也不会承担结果。政府不承担,企业不承担,老百姓也不承担,但其实大家都是同谋,因为我们已经彻底地把自己交给了这个拜物教的社会了,我们只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发展。
今天在座的有“新发现”夏令营的学员,我没有教大家怎样去写诗,只是让你们怎么把眼睛打开,把耳朵打开,把心打开,来感知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不是最坏的时代,也不是最好的时代,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足够你去体会。多少故事是你想都想不出来的,多少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你不知道的,这都需要大家认认真真地去面对,去观察。当然,还需要吸取一些西方的现代诗歌技巧方法论,需要大量的阅读,写作,它们都是构成优秀诗人的必要条件。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把自己从生活的现场拉开。台湾有两所大学邀请我去做驻校诗人,一住就是两年,我拒绝了,我才不愿意在学校里呆上两年,那要错过大陆上多少事情。我一定要在现场上看到,听到,想到,认认真真地写,悲愤一点,狠一点。我们需要美,但我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它。
(整理:熊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