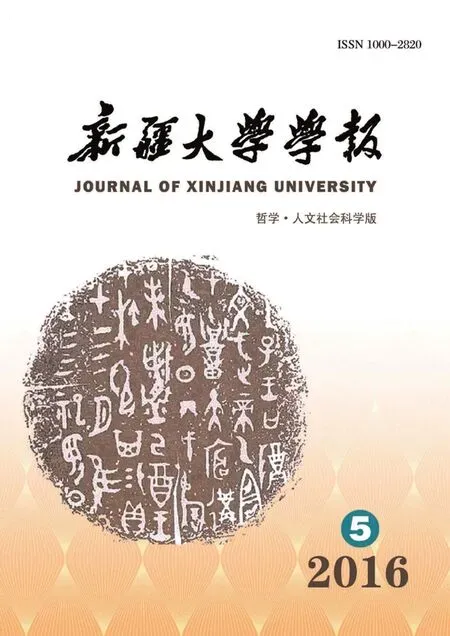国外推进区域公平发展的启示*
夏文斌,骆云强,徐 艳
(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但是,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不平衡,因为这种不平衡的背后衍生着诸多不公平的制度伦理,并成为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区域公平发展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上的一些突出矛盾时首先就指出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1],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我们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如果漠视区域公平问题,特别是不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欠发达地区的公平发展问题,将必然会对国家现代化带来致命性伤害,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不断完善我们的制度伦理,使得我们的现代化在最小的震荡中前进。
区域公平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等发展主体,在考察和比较地区间历史、自然、人文社会和区位特点等因素及投入与回报关系后,对不同地区投入自然、人力、知识等要素后的回报预估进行较合理、客观的确认。因此,区域公平发展不是无视自然禀赋、人力资源等现实条件的不同而追求区域之间的绝对公平,而是一个比较性关系概念,是在不同区域投入与回报关系的比较中形成的,其中涉及到制度政策的制定、自然秉赋权利的确认、历史关系的形成、国家总体战略的部署多重因素。深刻把握区域公平发展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问题,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如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这一制度伦理的问题。区域公平发展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刚刚被关注的重大问题,但事实上人们一直在用不同的表述指向此问题。深入探究此问题,需要我们开阔眼界,从更广、更远处把握其内在要旨和基本要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国外关于区域公平实践的得失成败中来把握区域公平发展的内涵目标,是我们建构中国区域公平发展原则的题中之义。
一、利益整合:区域公平发展的基础
在人类资源配置进程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趋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调节;二是兼顾公平和效益的政府调节。其中,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促进区域公平发展进程中,市场调节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它是推进区域公平发展的有效力量,但不是惟一因素,而且是非主动因素;其次,由于市场的利益倾向性、市场失灵、市场的“马太效应”等原因,使得仅仅在市场调节作用下的经济增长在不同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衡性。因此,区域公平发展一般不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自发形成,没有自然而然的区域公平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公平发展,必然需要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合力推进,形成国家、区域和个人的利益目标共同体。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单一调节的弊端,缩小地区差距,在公平与效益之间达到有限的平衡,当然,政府的调节与市场自身的调节应该是有机统一的。美国之所以成就今天的霸权与18世纪末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西进运动密切相关。西进运动以来,美国实现了领土面积的巨大膨胀,但同时又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西部原始落后的未知、未开垦的神秘地带,以及东部已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区域之间——巨大差距。地区间的巨大差距给美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但同时,国家整体发展需求、欠发达地区和已发展地区的发展需求,以及人民自身发展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可能的一致性,美国政府看到并不失时机地将这种需求之间可能的一致性变成一种实然状态。进而,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参与到了改变这一局面的热潮中,并实现了对广大西部的有效开发,大大地缩小了美国各个区域间的不平衡度,同时也助推美国一步步走向了强盛地位。近年来,美国为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合理规划区域发展、促进国家整体发展而启动了“美国(2050)区域发展新战略”,其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全国经济增长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目标[2]。美国以南,巴西原本也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后来通过迁都巴西利亚和在亚马逊地区设置自由贸易区而成功地在经济落后地带培植了可持续的、地区发展可依托的经济增长点,逐步从“两个巴西”的旧格局和发展困境中跳脱出来,实现了国家整体发展需求。可见,在尊重市场的主导作用、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政府的有作为(包括政府的政策导向、利益导向等)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开发、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探讨我国如何实现区域公平发展的问题上,如何将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及个人利益统筹兼顾,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合作平台,是推进欠发达地区公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二、法治政府:区域公平发展的有效保障
公平尽管存在着主体价值认知成分,但公平的实施却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离开法治的公平是不可能长久的。巴西和印度开发欠发达地区主要强调政策导向,充分发挥了政府的调控作用。但是,当这种建设模式缺乏法律保障就会过分地依赖于政治力量,使得开发进程因为领导人更换、政策更迭等政治力量的变更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巴西出现的开发项目半途而废、资源严重浪费、开发进程陷入混乱或停滞等的问题。因此,在开发落后地区的实践中,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和依据,以确保开发活动的稳定性、长效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在美国、日本推进区域公平发展的进程中,法治是欠发达地区开发建设得以顺利开展不可或缺的元素,甚至是前提保障。为了保持开发的实效性和有效性,日本还依据法律、根据实际的开发情况、按照一定的周期设定了开发计划,以不断修正和调整开发的具体进程。比如1950年日本出台国土开发基本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后于2005年升级为《国土形成计划法》),以及北海道开发的专门法——《北海道开发法》后,根据前者,从1962年开始至1998年制定了五期开发规划,到2008年又根据新法制定了“国土形成规划”;根据后者,形成了基本以十年为周期(备注:第二、三期时间较短)的“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截至目前已接近第七个开发阶段的尾声,按照近几十年的规律,预计将于2017年出台新的发展计划。“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3],不能将法律束之高阁,而应落实为具体的实践。因此,在法律及政策规划的基础上,美国、日本还依法成立了专门的开发机构以落实相应的目标和开发计划,比如美国在《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颁布后依法成立了“经济开发署”,日本则在《北海道开发法》的基础上,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相应的开发机构——北海道开发厅和北海道开发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我们明显具有更多开发欠发达地区的优势、能力和条件,适合我国国情的途径应该是有效结合法律保障和政府职能的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了依法治国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4],在促进区域公平发展的问题上,就需要改变传统的主要依靠政府政策导向的调控机制,相反,需要在完善的、稳定的而又长效的法律保障基础上,更妥善地发挥政府的有效、有限的调控作用。
三、以人为本:区域公平发展的核心要素
第一,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建设依赖于人的力量的发挥。由于天然存在的迥异的自然禀赋(自然因素),和后天发展进程中开发者(人的因素)的效益最大化趋向性,不同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自然而普遍的现象。而从根本上说,一个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在后天发展中缺乏了人的要素。当自然还纯粹属于自然存在的范畴时,它只具有潜在价值;只有当自然资源与人的要素相结合之后,才具有了实在的经济价值,缺乏人的要素,一个地区不论蕴藏着多么丰富的能源资源,或者展示为多么美妙的自然环境,都不可能得到发展;进而,自然化程度远远高于人化程度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表现,因此,改变欠发达的现状必然要发挥人的力量,人是整个开发环节中核心的、最有活力的元素。日本北海道地区是一个先天条件较好而离经济中心较远的地区,明治维新以来就有断断续续的开垦活动,但这并未根本改变其经济落后状态,二战后,大量战场军队人员被输送至北海道地区以缓和国内矛盾和粮食危机,而从这些人开始,北海道地区开始慢慢地实现了质的改变。巴西东北部、中西部和北部的大多数地区被热带雨林覆盖,开发难度较大,且远离较为发达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缺乏先天的发展优势,人迹罕至。在“向西部进军”计划和“全国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后,通过迁都巴西利亚、修建公路并沿途设置移民点、发展马瑙斯自由贸易区等措施,大批移民开始从较发达的“第一巴西”向欠发达的“第二巴西”转移,有效地开发了后者,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因此,我国要开发建设落后地区,为这些地区带来源源不断的开发者这一源动力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个地区的开发不应是简单的资源攫取和土地开垦,而更应该是繁衍生息,只有真正成为欠发达地区的一部分,才能给这个地区的发展带来不竭的、可持续的动力。
第二,开发欠发达地区必须关照人的需要。前文说到了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实际上,人同时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需要不断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并同时留住人才,而留住和引进人才的关键就在于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人、发展成果由人民享有,这是区域公平发展的核心要素。日本开发北海道地区的第一批人是战场回归的军人,这基本属于政治转移,但是,北海道的开发建设不可能仅仅依赖于这一批人及其后代,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北海道,他们多是基于北海道完善的基础设施、秀美的自然环境、宜居的生活环境等,这些因素本身无不标示着以人为本的特征。我国开发建设欠发达地区进程中必须关照人的需要,保证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在美国西进运动中产生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具体来说:第一次多是因为“未开垦的处女地”及其蕴藏丰富的自然、能源资源的吸引,再加上“未知世界”的潜在价值,吸引了大量到西部探险和到西部求生和寻求机遇的人,这些人开始了人与自然的初步结合,但对西部的长期开发贡献有限;美国贯通东西的铁路建设完成以后,西部又迎来了第二批移民——有远见而富有的投资者,他们对于长期开发西部的功能明显大于第一批移民;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将广大的西部作为军事工厂所在地,在西部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吸引了大批移民,这两次移民构成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一战后西部工业颓废并牵制了西部持续发展,二战后,军事工业迅速功能转换为民用工业,为第五次移民浪潮准备了条件;第五次人口迁移越来越倾向于科学技术领域,为西部的科技化发展带来了源动力[5]。可见,这五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中,人口结构的不同对于西部发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有明显差别,人才素质的构成与西部的发展方向基本保持一致,或者说正是不同的人口结构形成了西部的不同发展状态:农业发展时期、军事工业发展时期及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时期。因此,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开发进程中,首先应该对一个地区的开发目标做好明确而合理的规划,进而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相关人才,形成人与目标的互相促进状态。
四、务实与可持续:区域公平发展的长效机制
区域公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包容多重因素的历史问题。对此,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之,而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长远,精心设计,兼顾多重利益需求,在构建长效机制上多下功夫。
公平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性概念。区域公平发展更要考虑到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自然、人力等综合因素,做到量力而行,即开发欠发达地区是以一个国家的实际能力为依据的。巴西是联合国减贫的典范,但是这一身份却是依赖于一种超越国家实际发展能力的开发策略,通过超负荷、不切实际的做法实现的,这种方式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的同时却给国家和地方政府造成了沉重负担,使得国家和地方政府极端贫困,近年来,巴西所背负的公共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财政赤字居高不下,2015年通货膨胀率高达8.13%[6]。国家难以负担落后地区开发和贫困人口的补给,不仅使国家整体发展陷入困境,而这实际上也不利于落后地区的长期有效发展,最终使得一些项目搁置或中断,并造成浪费、无效和社会情绪。以此为戒,我国落后地区的开发计划必须以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
开发欠发达地区要以所开发地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所制定的开发政策应在最大限度地做好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巴西开发欠发达地区不仅脱离国家实际,而且一些具体政策、项目的出台明显也缺少对当地实情的考察和遵循,决策不当也是巴西一些开发项目被搁浅的根本原因之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不以所开发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想当然地进行明显不合理的行为,这对于所开发地区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要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有效合理的开发,就需要对每一项具体措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可行性评估。基于西部地广人稀、远离发达地区等特点,美国政府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通过不断改善交通条件带动沿途条件较好地带优先发展并逐渐形成城镇,同时又通过交通设施的延伸而不断发展、壮大城镇,城镇的发展又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构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我国一些欠发达地区与美国西部类似,开发这样的地区不能追求普遍发展,也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区域公平发展的目标是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可持续发展表现为发展的连续性、延续性。
第一,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7]52因此,可持续发展是要达到这样两种平衡:一是当代人之间需要的满足的平衡;二是后代人实现其需要的可能性与当代人实现其需求的现实性之间的平衡。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平衡有一个条件——“需要”的“限制”,无休止、不节制的需要追求,必然会对他人同时也对后代人的需要形成威胁,只有追求有节制的需要才是长久的、可持续的。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促进的状态。人类与自然界两者都不是单纯的主动或者被动者,人类一开始没有认清这一问题,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在每次与自然界的较量中,我们都向自然昭示了我们的能力和主人地位,而且“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人类的过度索取,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这一事实通过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表现出来,恩格斯说,“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8]相反,只有与自然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共识,自然才能与人的发展形成互相促进的状态,人的需要才能得到长期满足,否则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价值最终都会被自然的报复洗礼抵消掉。
通常情况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状态在多数情况下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必然意味着人类需要的过度化,而过度的需要追求又预示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在四个国家开发进程中都不乏过度开垦、过度砍伐、过度索取的情况,尤其是巴西对热带雨林的砍伐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关注。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曾受到自然的惩罚,20世纪30年代一场黑风暴不仅毁灭了人们的现实需要,连同后代人追求其需要的能力也大打折扣。相反,在有关北海道开发的计划中,却延续了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发展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北海道正在朝着一个良性、和谐的发展目标迈进。现实表明,“环境恶化正在侵蚀一个又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7]42,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我国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都比较脆弱,比如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高山阻隔之下的甘肃、新疆一带有着自然的先天不良性,如果在开发进程中不注重增加植被进行生态保护,就可能导致土地进一步沙化、戈壁化,使土地完全失去利用价值,并进而威胁人们生存。
第三,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连续性的发展。开发欠发达地区的实践不应该是时断时续、甚至偶尔或者经常中止的,而应该是持续的、延续的状态。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建设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依赖于外部力量为欠发达地区开发建设创造基本条件;二是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其中第一部分是一个落后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节,它依赖于国家的政策导向及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支持等,这些外部因素的稳定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开发前期阶段。巴西因为超负荷操作使得外部支持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使得开发计划时断时续,这不仅不能给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还反而给国家和欠发达地区造成了一定的负担。第二部分应和第一部分同时开始,或者至少是紧随其后的,如果忽略或缺少这一部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必将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外部力量,那么一旦外部力量丧失,就必然会形成发展的停滞状态。在开发欠发达地区进程中,日本、美国十分重视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比如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对西部的援助必然是短暂而有限度的,在有限的援助日期和额度范围内,它主要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比如《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中明确规定:“援助的目标在于创造经济机会,并使地方的参与者选择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方式,而不是依赖联邦和州政府援助。”[9]此开发模式可概括为“授人以渔”,它不是简单的资金、技术或者人员的支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就是说各援助省份扮演的不是“扶贫者”或者“投资者”,而是“教师”的角色,它们在开发援助欠发达地区进程中应该教会学生(受援助的地区)具备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