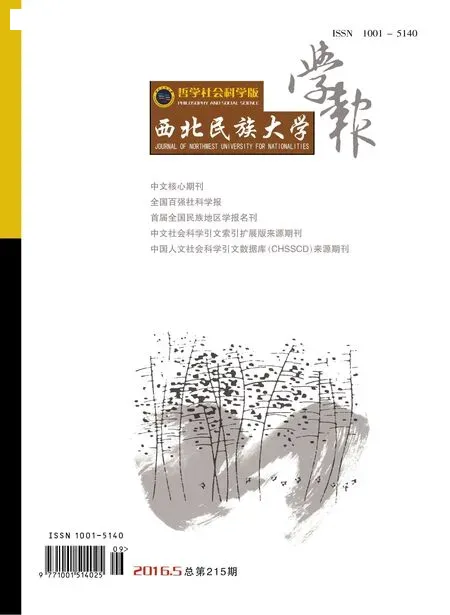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
罗 瑛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
罗瑛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族群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从国外至国内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而在国内二十多年来族群研究的语境已逐渐本土化,形成了基础性的理论系统且正向各领域拓展其理论视野。通过梳理族群、族群意识、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概念的由来、涵义和引起争论的各处意指内容,力图详细探讨涉及各个概念相关领域的理论看法,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分析视角和阐释论点。其中,关注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研究当中来自不同派系学者的研究观点,以族群建构的各要素间的差异和联系分析为基础,归纳出族群认同存在多元模式的可能,为促进族群理论研究的多线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族群;族群意识;族群认同
在族群问题研究中,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各种概念运用,而其中许多概念自“族群”这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起来的词,至今半个多世纪该词仍在学术界处于争相讨论之中,学者们根据所处的国家、区域、种族、社会背景和时代等差异角度,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族群问题研究所必须涉及到的族群意识、族群性、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等相关概念,在学界并没有最为准确无误的界定,它们和学术研究本身一样,需要在学者所关注的不同领域进行不断的阐释和更新。而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研究,是当前社会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相关理论包括族群、民族、族性(族群性)、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
一、Ethnic group:族群(相关定义)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最早出现在英语用词中,用以代替英语中Tribe(部落、部族)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族群的相关研究学术风潮才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兴起;70年代,上述研究扩展至欧洲,并在90年代影响到中国学界且慢慢变成中国学界的热点研究问题。在此过程中,各路学者所提出的族群概念十分繁杂,标准不一,许多定义和概念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论争,要论述族群研究相关问题,必先弄清楚族群概念,仅选择对我国学界影响较大,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为以下几类。
1.强调记忆认同、血统认同和信仰认同的族群概念。以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为代表[1]。2.强调共同祖先、族群内外认同的族群概念。由涩谷和匡提出,该定义比较简单,因此得到不少学者认同[2]。3.从生物自我延续性、文化价值统一性、建立交流共享领域和内外认同的类型形成四个方面来定义族群。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亦译为巴特或巴尔特)在他著名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提出[3]。4.强调族群共有的文化特质因素、社会历史因素。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N.格拉泽和D.P莫尼汉的定义[4]。5.综合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的族群概念。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中,对族群所作定义[5]。6.强调可识别性、权力差别和群体意识特征的族群概念。科威特人类学家穆罕默德·哈达德给出的定义[6]。7.强调族群边界、祖源记忆、情感与文化维系的综合性族群概念。由王明珂在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提出[7]。8.等同于“民族”概念的广义族群概念。孙九霞认为族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标准,族外人对他们的区分,一般是通过这些标准确定的。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意识即对我群和他群的认知,大多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8]9.马戎指出族群是三种认同的组合:文化认同、经济利益认同、社会和政治认同[9]。
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族群概念还有很多,可见,族群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比较广泛,而且一直尚有争论的概念。在“族群”和“民族”两个概念的对比和关系研究当中,国内学者则基本达成一致,那就是族群主要强调文化意义,而且族群在形成过程当中与国家政体没有联系,其使用也比较灵活,族群可以涵盖渊源相近民族而指一个族群集团,可以等同于某个具有政治属性的民族,也可以小于民族而指向民族的一个支系或民系,一部分学者还认为族群通常运用在政治上不占优势也没有形成国家政体的民族。而民族概念则强调其政治意义,徐杰舜指出,“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概念,其内涵及外延在政治上、学术上及民间对话中,都已约定俗成,对于“民族”概念而言,文化不是其唯一的基准指标[10]。徐杰舜还归纳出从社会效果来说民族显现为法律性,而族群显现为学术性。因此,族群和民族两个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两者所指向的理论视域和应用范围都有各自的特征,两者既有内在联系也可以相互补充,而族群和民族的使用也标识出作者的不同研究立场和意图。但不管出于何种视角,概念只是学者们研究想要研究的相关问题而使用的一套名词,一个预设工具。我们可以认为族群概念的内涵,应该是基于族群集体内部共享诸种人类某些普遍因素之共同体系,包括该族群在自我文化系统内外的认同——族群主体是某类社会(民族)集体;族群共享和向外传播专属历史文化记忆;族群内“自觉为我”与族群外他者的认同。且族群的划分,以族群认同的要素为最基本前提。
二、Ethnicity:族群意识/族群性/族属
该词在中文著作当中,不同的作者根据所持理论立场或问题探讨视野而将之译成不同的中文名,常见到的有“族性”“族群意识”“民族本质”“族群特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文译名很难表达英文原意,于是放弃翻译,在中文论述时直接使用ethnicity原词。马腾嶽在《ethnicity(族属):概念界说、理论脉络与中文译名》[11]一文中,对该词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并解释了不同的译名,他认为,“族群意识”指的是对特定族群的认知与认同,强调的是心理的、主观的层面;“民族本质”指的是民族的生物性或文化性的客观本质,重视的是其客观成分;而“族性”则让人联想到族群本质上的特性。马腾嶽通过对“ethnicity”译名困境和理论的当代价值及争议等问题的探讨后,依据“类属”“归属”“族群属别”的语义诉求,指出应将“ethnicity”译为“族属”。这个概念不管译成什么,实际上都是一个分析族群想象和理论的工具,每个人对工具的使用有各自不同的要求,所以在译名的选择上也是根据个人差异而定,我们知道,学术的概念或许有理想型,但不存在完美终结型,在概念的道路上,有的只是人们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和争论,下面简要辨析下ethnicity的一些比较通行的看法。
吴燕和在其论文《族群意识·认同·文化》[12]中指出,族群意识即族群特性,他引用了西方学界对ethnicity一词之定义:与生俱来的、靠生物遗传性而扩展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一个大社会里,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但又和其他社会组织特性相伴而生的社会关系。吴燕和认为该定义不准确,完全忽视了以文化形成的族群基础。荷兰学者尼科·基尔斯特拉在《关于族群性的三种概念》[13]一文中,指出族群性有三种看法:1.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族群性;2.作为区域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人群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文化同质性基础的族群性;3.作为某一分散了的人类群体的成员们相互认同和建立其潜在的文化歧视的、假设的或作为起因之基础的族群性。吴泽霖也将“ethnicity”翻译为“族群性”[14],认为这个概念的关键特征是对任何一种群体或人们类别进行区分或标识,并将被认同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及类别作或隐或显的对比。在使用族群性概念时,总要牵涉到“我们—他们”这一对两分标准。标识或对比的特征是动态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再作解释,所以在不同层次中存在着多种族群性。周大鸣在《论族群与族群关系》[15]一文当中,讨论了《美国大词典》《麦克米伦人类学词典》、日本学者绫部恒雄、台湾学者吴燕和以及陈茂泰等对ethnicity的不同定义后,归纳出广义的族群意识(族群性)观念源于不同的理论视野:即对于ethnicity的诠释,有的认为是实体,等同于族群(ethnic group);有的认为是族群的性质和特点;有的认为是族群意识;有的认为兼有族群及其意识。而马戎认为,人们关于族群(或“民族”)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是先天遗传而来,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萌生、明晰并不断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认同的对象与程度或者强化,或者弱化,或者在两者之间多次反复,甚至关于某个族群的认同意识也可能彻底消失。但族群意识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认同和对于其他族群的认异[16]。
通过上述梳理,ethnicity被理解为族群性和族群意识在学界的影响较大,两者皆是族群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建构,对族群的描述和建构意义都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研究者的视角和关注点。笔者认为ethnicity作为族群意识也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意识”强调了人类固有的原初认知,对于很多族群成员来说,他可能“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自我的群体归属,“意识”在很多环境下是需要被唤起的,如果没有发生社会交往,没有人我之分,族群意识不会天然地影响人的思想行为从而在互动中有所区隔。而且族群意识也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参与社会建构的一种个人和集体想法,族群意识可能是源于共同生活历史或文化渊源的思想特质,也可能是想象的和主观的,发挥着在共同体当中纽带的作用,具有标识族群特征的功能。对于一些族群集体来说,族群意识是生活在相互有联系的、在某个区域内所属族群集体占主导地位的族群成员们拥有共同文化基础的认识。而在群体内部,这种意识是自在而不外显的,只有当与其他族群集体发生社会交往的时候,社会划分个人、群体身份的条件出现了,族群意识才能显现出来。族群意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是有层次的,其萌芽、深化、不断建构或者逐渐消亡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Ethnic identity:族群(身份)认同及相关理论
ethnic identity既可以翻译为“族群身份认同”,也可以翻译成“族群认同”,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两者互为辩证,认同是身份的表述结果。巴斯认为,族群身份的社会意义是为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的社会互动提供一整套规范系统,即出于社会互动的目的使用族群身份来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而且在所有身份划分当中,族群身份是大部分身份中首先要考虑到的,因为它限定了拥有这种身份的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人格[17]。事实上,社会交往当中,个人和群体只要有差异就有身份表征,身份有各种性质,比如家庭身份、亲属身份、政治身份、经济身份和其他社会身份,但族群身份的生成显然和族群的生成是同一过程,不仅可以原生,也可以随情境变动不居而变迁,和族群认同、归属一样也是可以演化变异的,因此,族群身份是所有身份表达中较为宏观的社会分类表达。马戎曾经讨论过族群身份研究的两种视角[18]——宏观和微观,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宏观视角可以理解为族群内的自我认同和族群外的被认同,微观可理解为族群内部社会分层所涉及的地位、角色或等级概念。一般而言,族群身份是需要标识的,这种标识可能是实在的,也可能是想象的或通过意识形态建立的,而对于个人来说,族群身份可能是内在和原生的,也可能是经过权衡选择去获取的,所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族群身份与社会情境相结合,才有排斥、接受和认同等行为的发生。族群身份的社会表达背后,隐匿着最广阔的族群结构和社会秩序,尤其当族群身份以文化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历史记忆、仪式、服饰、居住形式等包括其他艺术体系都参与到族群身份的生产机制中来,在此过程当中族群意识的强弱程度,则伴随着族群身份的生成并参与其强化或者弱化的过程。当然,族群身份必然是内含于族群认同理论中的,如果说族群身份的强调属于社会文化表象,族群认同则更多地探索人类的心理情感层次,研究两者的工具手段有着明显的差异。
关于认同,有许多研究路径,如外表认同和内在认同[19],外表认同表现为可以观察到的遵守族群社会文化秩序的行为,内在认同则主要指想象、观念、态度和情感方面的认同,内在认同和外在认同大部分情况下相互验证,彼此相辅相成,但也不排除有各自独立的情况,内在认同相对于外表认同来说,更着重强调认知、道德和感情方面的因素,因此是更自觉或更高一层次的认同,但两者都是很重要的认同表现方式,对于一些个体或群体来说,两种认同可以相互转化和演变,但其认同程度的深浅则较难界定。而社会学论者认为,认同的影响和决定因素包括有企图的、偶然的和传统规范的,但衡量认同的准则和内容则非常多元,包括认知(内容、程度、主张)、排他、原生情感、理性、身份地位、群内偏爱和群外疏离、动机/需求、目标意图等,这些关于认同判定的参数是多元且变化的,因此判定认同并没那么简单[20]。故而,认同除了指出个体和所处的社会、文化及群体的同一性,还指出了群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以及更大的群体的同一性,同时还涉及与“他者”的辨异性。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理论[21]认为,族群是当事者本人归属与认同的范畴,族群认同主要源于自识(self-ascription)和他识(ascription by others),巴斯的理论在人类学史上影响甚大。族群认同具有个体的归属性和群体的排他性,族群认同在面对社会情境变迁时也需要不断的表述和验证,从而生成族群边界的同时也只能在边界内维持其与他人不同的标志性差异。因而那些用以区别族群的外在文化特征不过是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维持的一种暗示或结果。
除了巴斯针对族群认同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边界论”,围绕着族群认同发生的各种要素构成等原因,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学界形成了以下关于族群认同研究的理论方法。
(一)根基论(primordialists)/原生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希尔斯、范·登·伯格以及格尔兹。根基论认为族源、种族身份、血缘系统等生物性遗传特征,和生活于其中通过血统承继而获得的客观资赋比如语言、宗教和习俗等,是族群认同最根基性的因素,这种观点认为祖先血缘、种族体质、地域、语言、宗教、习俗是客观存在的族群共享资源,最能引起或激发族群成员的原生情感和忠诚。对于个人而言,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成为“既定资赋”,血缘纽带、语言、宗教、族属和领土的“原生纽带”是族群成员最普遍的维系力和内聚力保证,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且奠定了一切后来产生人类社会组织,对族群成员来说,原生性的纽带和情感是根深蒂固和非理性、下意识的。根基论当中又有极端派和温和派,极端派认为族群中的行为举止、文化特征等是遗传的结果,是先天的,这些观点也是后来遭到学者们反驳的原因。而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是格尔兹,比如,他说,社会存在是密切的直接关系和亲属关系,原生性归属是“先赋的”,这种先赋性还指出生于特定宗教群团中,讲特定的语言乃至某种方言并遵从特定的社会习俗等。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致,在人们看来对于他们的内聚性具有不可言状,有时且是压倒一切的力量[22]。原生论将族群认同途径主要归结到“原生纽带”和“原生情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而且基于现实场景中的非洲、亚洲和中东等众多民族国家营建现象中族裔纽带并非是万能的认同途径,从而导致原生论被新的族群认同理论不断刷新。原生论的提出有其必然的客观事实,因为无论是后来的构建论、工具论等在对原生论的驳斥当中,都不能忽略两个重要问题——族群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社会构建的产物;族群纽带是由情感主导的,还是由理性(工具选择)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回答都不能否认族群的现实存在,但绝大部分研究都不能否认,诸如地域、语言、习俗、宗教等通过家庭、族属对个人社会化能力的控制和影响,会导致族群成员最稳定的心理积淀。纳日碧力戈认为,原生论所探讨的族群认同之客观因素属于内部动力,但是却是把内部动力和外部形态混为一谈,得出“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失偏激,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个族群的“原生”性特征已经丧失殆尽,但它的成员依然保留着强烈的族群意识,也就是说,族群不是家庭、家族的延伸,而是其变形,且能够提供给族群成员强大的文化动力[23]。也正是因为在族群领域当中,族群成员的认同方式不仅仅是情感方式,还有理性或工具性等行为方式,因而产生了情境论。
(二)情境论(Cicrumstantialists)/工具论。该论点在社会学上早有其发源,涂尔干曾经论述过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所驱动的,而马克斯·韦伯则提出过人的理想型行为取向的核心是理性或感性,即对获得性的判断影响人的行为取向。族群理论中持情境论/工具论点者,正是将族群视为某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根据情境、形式是否有利于自身,来选择认同是否持续或改变,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为基础,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也就是说认同是族群成员获得政治、经济或社会资本的一种手段,在现实生活当中,认同的实际情况乃依据个人之社会处境进行调整,因而并非稳定。王明珂认为,承载社会文化特征的认同行为,作为表达族群身份的工具,常常发生在资源竞争比较激烈的地区,具有随情势变化的性质,族群核心和族群边界的认同也有明显的差异[24]。族群认同的原生论与情境论是相互结合于一起,认同有着理性工具和判断形势的用途,并不能认为和原生论观点相悖。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某个人可能会具有一种归属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深深地铭刻在此人的人格和生活经历中,但此人仍旧感觉到在某些情境下可以有目的地展现其族群认同[25]。因此,情境论/工具论强调原生情感/纽带和文化差异是被成员支配和利用的一种资源,为着其政治、经济、物质或权益的目的,成员对族群的传统或规范可以选择性记忆或结构性失忆,认同成为十分重要的手段和策略。
(三)构建论(Constructivism)/想象论。构建论得益于民族主义学说之兴起,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他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强调18世纪以来欧洲小说和报纸的流行成为想象的技术手段,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开辟了重要的想象空间。“民族”的产生对于个体的作用类似于宗教对人类苦难的回应,而宗教在18世纪业已衰颓,于是民族主义代替宗教对人的苦难进行救赎。安德森指出,克服生命死亡使之延续的同时又通过世俗的形式,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没有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了,民族的想象能够召唤出人们强烈的宿命感,“民族”的身影形象使人感受到群体大我的无私存在。人们经常提醒自己民族能激发起爱,而且通常能激发起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小说、音乐和雕塑等数以千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爱[26]。也就说,将民族主义和文化体系的构建、国家民族记忆的构建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比安德森稍后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针对“想象的关系”提出“民族主义原型”的概念,并强调这个概念首先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其次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治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27]。在此,认同从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有强烈民族(族群)取向的人们,通过想象、构建和维系并与政治发生联系的产物。虽然这些论点的产生有其深刻现实根源和诸多让人信服之处,但对于追求满意界定的批判者们总是有其怀疑,也正是其中的“虚构”“想象”等论点,为后来的批判者们提供可批评的靶子。
(四)文化论(Cultural approach)。文化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族群问题尚未大热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控制一个人和团体的种种行为观念的是文化结构。她指出,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28]。文化论者普遍认为族群拥有共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念,族群的差异则是文化的差异,并且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进行辨认。事实上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丰富,族群指在文化上同构型的一群人,宗教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较早时期,宗教和族群几乎是混为一体的,因此文化论的支撑事实也足够多,许多族群的冲突矛盾是因为文化的冲突矛盾而产生,文化认同问题则成为文化论核心。文化认同给予个人的归属就像一个“家”,无论是家庭、邻里、地方、国家,还是族群,给个人以身体、情感和心理的支撑和形塑、滋养,从无数动人的文学艺术中可找到这种积极认同的佐证。针对族群是不同社会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这一主张,庄孔韶在《人类学通论》中通过分析文化论持有者苏联学者勃罗姆列伊、美国学者戈登以及族群边界说创建人巴斯的相关论述,他认为,文化、行为差异在多族群社会交往中表现为主要问题,且强调这种问题与政治、经济和阶级的重要关联,是文化说理论的长处和贡献。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理论对于族性(ethnicity)以及与它相关的问题的认识仍过于简单和乐观,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便遭到了批评和挑战[29]。文化论所标榜的结构性同化可以消解一些族群矛盾,但自20世纪中叶至今都证明确难实现,新的族群问题、种族矛盾总会诞生,而文化并非万能。靠文化来同化异族这种事情,中国历史上汉族同化少数族群的情形一直存在,但在文化多样性维持上的成败得失和不断产生的问题,却也不曾消失。
(五)多元论(polyphyletism)。持该论点者认为族群是多元因素形成的,其认同也是动态的,在历史社会不同的环境当中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多元论的形成是伴随着主观论、客观论和根基论、工具论等的争议而产生的,也是各种观点的整合与发展。哈罗德·伊罗生是多元论较明显的持有者,他的见解是,基本族群认同的各个要素以多种方式进行融合,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们不是机器压制出来的东西,而是艺术品,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看起来神似,但实际上各有自己生灭之规则,过去它们有自己的发生原因、来源和演变过程,今天则有此时此地、这些人、这个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原因。基本族群认同是一个活的东西,会生长、改变、茁壮或枯萎,视其本身的生命力以及所属环境而定,它会消失在其他族群机体里面,也可能与原来的某个要素相结合而获得再生[30]。也就是说,族群认同处于动态模式的不断变化当中,它既是过去的,又是当下的,它承载着历史文化遗产,也置身于现代社会背景,在经历各种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变迁中,每一种族群认同都被迫调整变形以适应环境变迁,尤其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和现代性社会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变迁的广度和速度前所未有的剧烈,此种浪潮之下,不可能还有什么问题与概念、现实与想象是纹丝不动的。伊罗生的族群认同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是预言式的,他预见到未来世界风云变幻之族群形势,他深刻尖锐地认识到族群意识不仅区分人我,还切割人我,而且人我之分的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虽然族群认同的多元论影响不够广泛,但伊罗生这种宽容隐忍的逻辑值得赞赏,他的观点有助于族群理论的多线发展,对于学术话语的拓展大有益处。
对族群及其相关理论的探讨还有许多见解和观念,纳日碧力戈还归纳出“神话—符号丛论”,该论派认为,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因为这些要素是惰性的人造物和人类活动及其形式,一旦形成便具有稳定性,成为可以包容和适应各种环境和压力的人群模式[31]。可见,族群相关概念的多元认识和来源,致使认同理论复杂而难以界定,每个学者都通过自我的棱镜去观察它,但每个棱镜的位置和角度又有所不同,因此大家各取所需,各适其意,但族群讨论的普遍路径总是以进入原生论和情境论两者的套路辨析为多数。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32]中通过仔细梳理克钦山地的文化境况发现,现实中族群及认同情况确实是混乱而复杂的,所谓地图上形式齐整、疆界分明的部落族群各自独立不过是学术虚构而已。因而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的表述,更多依赖于其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也依赖于讨论者的学术视野。
[1][15]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2][美]M.G.史密斯.美国的民族集团和民族性——哈佛的观点[J].民族译丛,1983,(6):4-19.
[3][17][21]Fredr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M].Boston MA: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9.11,11-17,11-19.
[4][8]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5][14]吴泽霖.人类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308,237-238.
[6]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98-101.
[7][2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12,37.
[9]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
[10]徐杰舜.再论族群与民族[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09-114.
[11]马腾嶽.ethnicity(族属):概念界说、理论脉络与中文译名[J].民族研究,2013,(4).
[12]吴燕和,袁同凯.族群意识·认同·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47-51.
[13]高原.关于族群性的三种概念[J].世界民族,1996,(4):32-40.
[16]马戎.试论“族群”意识[J].西北民族研究,2003,(3):5.
[18]马戎.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5-16.
[19]Wsevolod W. Isajiw.Definitionand Dimensionof Ethnicity: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aper presented at “Joint Canada-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ntheMeasurement of Ethnicity”,Ottawa,Ontario,Canada,1992.April2.7-9.
[20]Rawi,Abdela,Yoshiko M.Herrera,Alastair Iain Johnston,Terry Martin.Treating Identity as a Variable:Measuring The Content,Intensity,and Contestation of Identity,Presentation at SPSA,August 30-September 2,2001,San Francisco.11.
[2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95.
[23][31]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50-52.59-61.
[2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2.
[26][28][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R.).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7][英]霍布斯鲍姆(Hobsbawn,E.J.).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5-46.
[29]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42-343.
[30][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6.
[32][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的一项政治研究[M].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69-270.
(责任编辑贺卫光责任校对李晓丽)
2016-01-12
罗瑛(1980—),女,云南昭通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艺术及艺术人类学研究。
C912.5
A
1001-5140(2016)05-00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