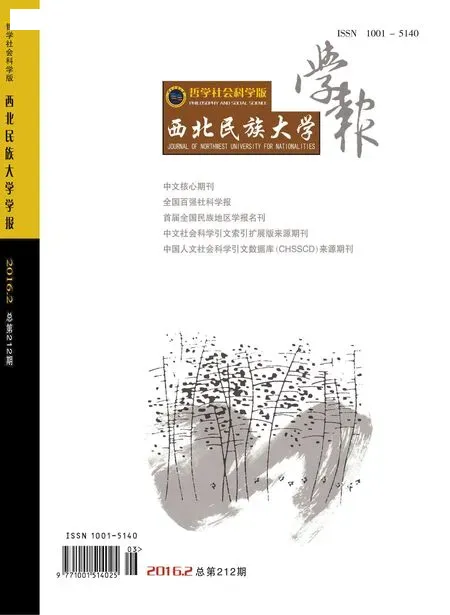二重身份视阈下的桑丹创作论
邓 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二重身份视阈下的桑丹创作论
邓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桑丹作为一名藏族女作家,她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一样,一以贯之地坚守本民族传统。但桑丹不同于其他作家,她以本民族日常生活的诗意化描写代替激烈的文化对抗,用温馨的审美态度代替沉重的伤感情绪,桑丹在宁静的心境中坚守藏族文化。此外,桑丹作为一个现代人,也偶尔闪现现代人的焦虑,然而展现得更多的是乐观豁达、坚毅执着。因而,桑丹的创作个性体现为:在宁静中坚守,在焦虑中淡定。
[关键词]桑丹;创作个性;藏族身份;现代人身份
桑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视文学为自己生命和生活方式。其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和她一同作战的文友几乎都先后放弃文学之路,惟有她不离不弃,坚持至今。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歌词,桑丹皆有涉及,但对诗歌情有独钟,出版诗集《边缘积雪》,另有散文、小说集《幻美之旅》。桑丹曾获得2001年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桑丹在当前的康巴作家群中自成风格,正如姚新勇所说,“她与旺秀才丹可能是藏族诗人中最优秀、最富艺术精纯性的两位诗人。仅凭她的《田园中的音响》和《河水把我照耀》这两首诗,就可以确定她作为转型期中国汉语诗界优秀诗人的地位”[1]。目前,专文研究桑丹创作的只有两篇文章:赵晏彪的《心音绕物,诗意如注——从<边缘积雪>解读桑丹的诗歌创作》,谢佳的《积雪的边缘,灵魂搁浅的圣殿——评康巴女诗人桑丹诗集<边缘积雪>》。此外,一些论文在论述藏族诗人或藏族文学时对桑丹略有涉及。
从现有成果来看,对桑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桑丹是一位“挚爱乡土的诗人,用生命感受高原和民族的存在”[2]。桑丹确实表现了对高原民族的神圣感情,然而,在少数民族作家群中,对本民族血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作家共同的情感取向。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的共性,还要研究每个作家之所以成为“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个性。寻着这样的思路,本文拟从二重身份(藏族身份和现代人身份)的视阈对桑丹创作个性进行思考。
一、藏族身份:在宁静中坚守
桑丹出生在情歌的故乡康定,是地地道道的藏族。她的外婆扎西旺姆是一个健康、美丽的木雅女子,她的外公是一个有着英雄家族史的加绒汉子。桑丹的父亲是驮脚娃,母亲是护士。桑丹毕业于康定县民族中学,退休之前一直生活在康定。
研究桑丹,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藏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创作原点,即书写族裔文化。桑丹的藏族身份,在其创作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隐藏于桑丹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成为她创作的“表达策略”,为她的作品蒙上一层异域色彩:银器、经幡、草原上的格桑花、清脆的马铃声、英俊的马匹、迷途的羔羊、诵经的梵音、老喇嘛、寺庙、火盆上烧着的酥油茶、空气中弥漫着的藏香味、牛羊进入白雪的栅栏、松耳、玛瑙、珊瑚珠、背水的木桶、茶马古道、古老的锅庄等。桑丹坦言,康定是一座诞生精神家园的地方,自己的创作和故乡康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认为自己是一位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上苍恩赐“我”出生、生长在月亮弯弯、情歌缭绕的康定,“故乡构成了今天我写作的审美和理想”[3],因此为藏族代言成为桑丹创作的重心所在。
此外,我们应该将桑丹的族裔文化书写放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在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族裔文化的书写都并不鲜见,尤其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语境中,中式/西化、传统/现代、边缘/中心、民间/精英、乡村/都市,二元思维的对抗与博弈构成部分文本叙事结构和审美价值等层面的艺术张力。相对于汉族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族裔文化时,将上述二元元素中的“中式”“传统”“边缘”“民间”“乡村”具体化为本民族的传统元素,并由此生发出对抗、失落,甚至愤激的情绪。桑丹作为一名藏族作家,她也坚守本民族传统,但呈现的方式迥异,她以本民族日常生活的诗意化描写代替激烈的文化对抗,以温馨的审美态度代替沉重的伤感情绪,在宁静的心境中坚守藏族文化,这种特点具体体现在下面3点。
(一)以诗意的笔调,赞赏故乡的自然人文景观。在桑丹的笔下,故乡是平凡的,“喑哑的日子如同平凡的故乡”[4],但故乡是迷人的,湛蓝的天空下,高山绵延起伏,经幡迎风飘扬,山上高高的白塔在阳光中闪耀,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秋天的木格措有湖水流动和水鸟振翅的声音,有落日余晖映照雪峰的壮丽,是一片任人想象的世界。故乡是纯净的,“像天堂的月亮高悬夜空/像洁净的雪融之水”[5]。故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鸟儿落在我的指尖”[6]。故乡是丰饶的,有“岩石的歌声,黄金的激流”[7],有遍地的牛羊和盛开的格桑花,那里的人们手捧银子的酒器,秋天的果实披挂风雨。金秋八月,田园金黄,发出金黄的音响,“青稞上流水出没,花朵丰美……阳光和草木颗粒晶莹”[8],“我的家乡,是堆满金子的地方/我的家乡,是堆满银子的地方”[9]。故乡是吉祥的,“经幡福佑的福祉生生世世”[10],大自然也具有灵性,茂盛的青稞遍植幻想,抬头看天,天上飘动着云,“让人伫立于风中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和慰藉”[11]。故乡是充满情意的,故乡有大情大爱,“没有比康定更深的爱了/没有比达则多更浓的情了”[12],这世间绝无仅有的情爱“使我心存善念,姻缘俱足/故乡啊,正是我活着的理由之一”[13],在外听到的一声抚慰就是故乡温馨的夜。桑丹带着心灵的虔诚对神山顶礼膜拜,立志要在雅拉河边守望一生,终其一生。
(二)以理想化的笔墨,刻画藏族的美好品格。桑丹笔下,故乡的人热情、豪爽、有情有义,故乡是情人和情歌的诞生地,“情歌撼动大地/只有这样的召唤……灵魂才能得到永久的慰藉……内心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14]。男人们在烈酒中为女人抽刀,驮脚娃为骏马欢喜。故乡的人有“江河一样纯净的柔情/雪山一样圣洁的胸怀/太阳一样炽烈的爱恋”[15]。雪地上亲人们的面容如此温柔。
桑丹以一个藏族女性的视角刻画了一系列康巴女子形象,桑丹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构想也包含着理想的成分。诗歌《木雅女子》《锅庄阿佳》《掂香姊妹》《卓玛》《扎西旺姆》,散文《背影》《生命中的美丽》《平常日子》《欢乐》,小说《老张的故事》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类作品中,桑丹没有涉及女人与国家这一经典的宏大母题,但桑丹笔下的女性形象外形美丽、人格健全、婚姻幸福,成为民族传统、民族血脉、民族精神坚实的捍卫者和守护者。桑丹认为,康巴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出类拔萃的女性,她们灵魂深处的共同点是,能坚持“精神领域自我人格力量完善”[16]。桑丹笔下,康巴女子美丽迷人,“红绒头绳盘结在你浓黑的发辫/珊瑚耳环摇曳着你动人的美貌”[17];康巴女子勤劳健康,能给人带来吉祥安康,卓玛能把今夜的冰雪解冻,能让小草长出幸福的绿色,荒芜的牛羊从此安静下来,能把收割的青稞酿成美酒。桑丹说,她喜欢的一位外国女作家说过一段话:“女人首先必须独立,她必须具备的不是高雅风度或迷人魅力,而是精力、勇气和愿意付诸实行的能力。”[18]桑丹笔下的女性形象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女性勤劳、善良、自立自强,并且收获了美好的爱情,阿佳白玛得到康巴汉子的爱恋,康巴汉子用一生的短暂和她相遇,用一生的漫长和她相爱,“血性的康巴汉子/把你供奉在欢乐与苦难的神殿/你是他们美到极致的爱情/你是他们无与伦比的今生来世”[19]。
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两性关系的建构,往往隐藏了深刻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认同。桑丹既颠覆了父权制文化中“红颜祸水”、妖妇恶婆、妒妇怨妻、美人淑女、贞妇烈女的女性想象,也颠覆了“五四”以来英雄救美的叙事模式,没有统治/被统治,征服/被征服的性别压迫感、紧张感。桑丹描绘了平等友爱合作的夫妻关系蓝图,维系夫妻关系的纽带不再是男性权威,而是源自两性之间的情感与责任。扎西旺姆、锅庄阿佳、掂香姊妹的爱情,男女双方彼此凝望、彼此倾心,爱由心生,幸福一生。他们彼此之间的夫妻情感真诚、直率、无机心,近乎理想化的爱情故事诠释着桑丹对藏族这个神秘的古老民族的喜爱。
(三)以神圣的文字,表达对藏传佛教的崇拜与信仰。桑丹坦言,自己之所以能不断抵御丑陋和邪恶,其力量来自“我生命里一抹温暖的亮色——那就是我的母系家族赐予我的宗教感。我经常想起我故去多年的阿婆扎西,这个30岁就离乡背井、独自拉扯着3个儿女的藏族女人,生活给她的磨难丝毫没有让她产生嗔恨之心,反而萌生了虔诚信佛、相信今生之后还有来世的慈悲心。因为相信有来世,所以活在世间的每个人要凭良心、凭感恩之心延续生命。基于这种坚定的信念,真善美的境界自然会显现出来,记得阿婆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来世我会有好报应的。这超越时空、灵魂永生的伟大深深地影响了我”[20]。“我永远忘不了我那年逾八旬的老阿婆,在清晨转经的路上,背一小口袋糌粑喂蚂蚁。在大雪纷飞的旷野中,撒几把米喂麻雀;宁肯花钱买几条鱼儿放生,也不愿贪口腹之欲。即使枯萎的花也要供养在盛满清水的花瓶里……何为悲天悯人的宽容?!何为万物皆有灵的仁慈?!因了这一切,世界才拓展了一种博大广阔的境界。直至现在将来,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是让我们无从超越,无可企及。它应该是久远的,永恒的,更接近内心的用灵魂拨弄的旋律,它们将滋养日月星辰,宇宙万物,芸芸众生”[21]。桑丹还说,她之所以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因为安徒生“也是一位富有宗教情怀的作家,从他14岁受洗礼的那一刻起,爱与悲悯一直是他作品的主色调”[22],安徒生“以真善美的宽广胸怀,宽恕了这个不那么完美的人生和世界”[23]。因为有一种信仰,“佛像前叩首,灯盏内添油。唯此,我们才有了冥冥中的愿望和祝福”[24]。从上面几段话可以得到如下信息:桑丹信仰宗教,具体而言信仰藏传佛教;受藏传佛教影响,桑丹相信生命轮回、灵魂永生,相信宽容、仁慈和感恩。
藏传佛教认为,所有生命都在降生—死亡—再生(转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圆圈中永恒流动,生就是死,死意味着生。桑丹在作品中不断演绎着这种生死轮回观。“今生宛如眼前/来生并不遥远/转瞬之间/我历经了从此岸到彼岸的远行。”[25]“我们的存在是多么短暂,我们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但死亡并非终点,它们留下来对来世的憧憬,并赋予我们生活神圣的意义”[26],活的辉煌之时就是临近死亡之日,“任何一个人在秋天目睹了自己日益流逝的生命本质后,不禁会发出良久的慨叹:灿烂的瞬间也是临近死亡的瞬间”[27]。由于生死不断轮回,因而死亡就是重生的开始,“呵,如此接近死亡的重生”[28]。因为死亡是重生的开始,所以面对死亡应该坦然、淡定,“这般轻盈的死亡风雨迢遥”[29]。《黑夜的安魂曲》集中表现了桑丹生死轮回的思想。令人恐惧的死亡,经过桑丹的点染,变得如此自然,甚至美妙。
看透生死,内心便豁达开朗,“寺庙檐头迎风招展的五颜六色的经幡,它们噼噼剥剥的声音正穿越尘世的落寂,雪芭的轻烟燃烧起来了,让那些郁积在尘世间的磨难和烦忧都随风而去吧”[30]。因有因果轮回,因而要仁慈感恩,“有福的人/渴望救赎的人/你将感恩命运赐予你的一切”[31]。读着桑丹的作品,你会得到一切复归如初的宁静与澄澈,以至让我们满怀厚意地倾情前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祛魅”与“返魅”之间的对抗与交织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危机寻求自救和自我认同的重要叙事策略。在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现代化冲击的时代语境中,尽管桑丹没有直接批判城市化,没有直接反思科技、文化和理性带来的弊端,也没有直接审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在破坏传统礼俗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影响,然而,诗意化的自然人文景观描绘,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和庄严神圣的宗教情怀,已经包含了桑丹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在民族传统文化有可能逐渐消失的现实环境中,尽管桑丹没有表现出沉重的文化失落感,没有表现出愤激、忧郁、躁动的情绪,然而,桑丹以藏族女性的视角表现“边缘积雪”,进行了一次“幻美之旅”,并赋予朴素的康定以神秘、朦胧、诗意的美,这是以审美风格的倾向性取代显在的现代性判断,这是将民族传统的坚守隐藏于宁静的叙写之中,现代性批判藏而不露,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二、现代人身份:焦虑,但淡定
研究桑丹的创作,除了看到她的藏族身份,还应看到桑丹是生活在现代的藏族。桑丹出生于1963年11月,成长于风雨文革,成熟于改革开放,现代语境、多思的性格、躁动的内心使她具有现代人常有的焦虑,桑丹的焦虑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个体永远在路上行走。“离开、归来、漂泊、找寻、战乱、失散、生死、情爱是我乐此不倦的冥想主题。这些古老的命题源自梦境中一次次喧哗与骚动,它永远存在,又好像绝不存在”[32]。离开、归来、漂泊、找寻构成桑丹作品中主体形象的人生轨迹。《幻境》一诗表现主人公背负人类的苦难独自前行。《秋天的颂歌》中说,“我把一段最后的旅程/丢进熟悉的水里”[33],又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流在阳光中的河》中,诗人将流在阳光中的河看成是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一个拒绝来路和归宿的英雄”[34]。《夜歌》中,“一盏删节了光芒的灯火/注定在我斑驳的阴影里/投下重新明亮的感动/我听见充满心灵的回声/像沿途轮廓分明的风景/我已经准备好日夜兼程/然后,抵达无限的遥远”[35],一盏灯火,一种感动,让“我”永无停止的追求。不断行走是个体的独立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已然折射出个体内心的焦虑,内心焦躁不安的一个外在显象就是永不停息的行走。霍妮提出的现代性“焦虑论”指出,当个人在现实世界产生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定感等焦虑情绪时,就期望通过行走寻找一个诗意的世界,从而摆脱焦虑情绪。
(二)个体行走时总是与孤独、失望、惆怅、无助、茫然和艰难等负面情绪相伴。《幻境》中,主人公行走是为了一个“白色的幻境”,背负着的行囊是忧伤、爱恋、祈祷、死亡。《旋律》中,主人公随着飘扬的马鬃徐徐走进不断延伸的林荫深处,“不断”一词点明了行走的不可终止。桑丹时常感慨,“与我同行的人早已荡然无存”[36],“脆弱,不堪一击的我/无法守望刀锋向前伸延”[37],“昨天的晴朗将我覆盖/今日的阴霾把我惊醒”[38],因而抒情主人公去意不定,躁动彷徨,“光明普照的大地/我将在何方伫立/又将在何方启程”[39],“谁能告诉我……远方为什么是命运的裂口/黑夜为什么是无法企及的永恒”[40],“深夜,我蹚过心灵的迷茫/那迅即蔓延的旅程将迎向何方”[41]。没有归宿令人焦虑,找到归宿内心依然不安,孤独的抒情主人公离开村庄,“在强盛的作物背后,依山傍水而居”[42],而此时的主人公却依然倍觉感伤。桑丹也写出了行走中离别的痛苦,“令人心碎的别离/是我苦难的天涯”[43]。桑丹仿佛永远漂泊的“过客”,找不到立足点而漂浮于空中,找不到家园只能奔波于路途,带着寂寞,带着迷茫,带着困惑。从心理学角度看,孤独、失望、惆怅、无助、茫然和艰难等负面情绪同属焦虑情绪。
(三)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渐逝唱了一曲挽歌。桑丹感到雪地边缘正在逐渐失去,边缘积雪正在慢慢被融化,“在我的手中,青铜的杯子早已碎裂/在我的心头一朵灵验的花瓣正在凋谢”[44]。“寂静如梦”的雪城正在逝去,成为“远去的背影……唯独雪崩真实的存在”[45]。面对逝去的雪城,诗人只能“勒住茶马古道最后一声长长的斯鸣”[46]。《河水把我照耀》集中表达了桑丹对本民族未来不可知命运的慨叹。“河水”喻指遥远的故乡记忆。诗歌前半部分抒发“我”与故乡的依恋之情,故乡已经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故乡是“我”热爱的土地,多年前是无垠的锦绣轻轻的铺展,故乡是饱满的家园。在“我”内心,故乡“透明无尘”,“我”愿用整个的身心感受亲人。诗歌的后半部分,也是诗歌的重点,表现雪地边缘的脚步正在慢慢死亡,此时的高原无人经过,无人歌唱,故乡正成为漫天飘洒的雪花,成为揉碎的云彩。前半部分叙写爱恋之情,是为后半部分写传统的消失做铺垫。藏族的古老传统已不可掌控,桑丹有一丝惶惑,有一些哀叹、感伤。
焦虑,这一现代主题代替了族裔目标的指向,使桑丹的创作穿过神秘、神圣的民族地理空间的遮蔽,具有了现代性的价值意义。然而,桑丹的焦虑仿佛夏日的雷电一闪即过,并未构成桑丹创作中的主导因素,桑丹创作的主体精神是淡定、乐观、大气,甚至是充满豪气的。
现实中的桑丹,是一位喜欢喝酒也能喝酒的康巴女汉子!作品中的桑丹,热爱自由、张扬生命激情,是一个耽于白日梦的康巴女作家。无论她的散文,还是她的诗歌都像她现实中的人一样充满豪气。虽然从小身体残疾,但她的诗文没有停留在病痛的呻吟、不平命运的嗟叹之中,而是教我们承受和品味生命以及生命之外的世界,读她的诗文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平静。当她走过花开花落的季节,哪怕一个人孤立无援地走在大地和流水的尽头,她也总是平心静气倾听遥远的声音穿透冰雪的笼罩,穿透内心的痛苦和脆弱,因为她常常用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令人愉快的人和事情,滋养她干涩的心绪,因为她知道即使一颗细长而孤独的树,在命运阴郁的天空之下,茂密的枝叶间仍会有鸟儿的歌唱。“真情的东西是不朽的,大地寂静,星空闪耀,人在俯视或仰望的一刹那,心会慢慢沉静下来,充满感恩和喜悦”[47],“即使此刻心怀苦楚,我也应当微笑”[48]。她以静谧、淡定的内心包容世间万事万物,“既然在劫难逃,就不如坦然面对吧,我觉得这些年我的心境在轻轻沉落,沉落到它该沉落的地方”[49],“当逐渐稀薄的花朵攀登在我的额头/所有的命运/无法匹敌那些相聚的死亡/让自己的灵魂皈依平静”[50]。她将痛苦看成是对人的历练,“一位河岸的歌者/需要恒久的修炼/才能让喑哑或高亢的声音/承受命运的悲悯/一个康巴女人/需要深重的欢乐和痛苦/才能将自己的一生/满怀大爱大情/爱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园/爱到哪里/哪里就是人间”[51]。既知在劫难逃,不如坦然面对;心怀苦楚,报以微笑;承受苦难,方知大爱。桑丹就是这样静谧、坦然。
桑丹对生活没有太多和太高的要求,不求大富大贵,地位显赫,轰轰烈烈,但求悠闲自得,平淡充实,能在雨雪天踩一双泥泞的鞋子回家,能边看电视,边烤几串油汪汪的干牛肉下酒,能有一种闲适宽厚的居家过日子的气氛,便心满意足。桑丹能从平常的生活中看到美丽,“平常的生命包容了动人的美丽”[52],于是她歌唱朋友,歌唱友情,“朋友们被漫长的岁月过滤以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朋友,将是上苍赐予此生的唯一珍爱,有这样的意境是一大幸事”[53]。她对亲人朋友表示深深的祝福,“我渺茫的歌声/能否使我爱着的和爱着我的人/在白雪的幻境边缘/用最后一节音符的微光/为内心的一缕忧伤照亮”[54]。当亲人扑朔迷离的脚步“被黑夜悄无声息的吞噬/亲人啊,当幽深的回忆像激流/拍打着你离去的背影”[55]时,“我的血管里总有隐隐的嚎叫响起”[56],时隔多年,“我”仍在打听朋友的消息,“我”牵来一匹草原上的骏马,希望它的马蹄声能传来朋友的消息。
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谈到,桑丹虔诚信奉藏传佛教,这里,我们还要看到,在藏传佛教生死观的影响下,桑丹面对死亡也超然平静。生死问题不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哲学、宗教和文化的问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越来越深的层面猜度死亡之谜的历史,面对死亡,有的人诧异,有的人渴望,有的人漠视,有的人直面。面对死亡,桑丹没有上述这些情绪,而是淡定自如。她认为死亡是重生的开始,对死亡充满“一种亲切”[57],死亡是“绝境中异常的”[58]。但桑丹决不是消极地对待人生,相反,面对短暂的人生和死亡,她要求坚守自我,学会隐忍,坚守内心的空寂,方能“啜饮未能倾尽的甘露”[59]。生死、情爱永远不可尽如人意,不可避免地会忧伤,但“我则用一生的哀伤/经营着短暂的时光/我就像一座水杉般清秀的村寨/内心塞满花草”[60]。桑丹认为,爱情、死亡和流浪与我们与生俱来,人具有死亡猝然降临的征兆和姿势,但“无论怎样的重逢或者分离/都让我心存敬畏与感动”[61]。
桑丹表现了行走中的孤寂、艰难,然而,桑丹更表现了行走中的执着、乐观、豪气。尽管旅途浓雾笼罩,但“我”仍然努力将黑暗分离,依然追求光明,“滑翔着月光的残骸……我的灵魂/是嘹亮到最后一刻的尘埃”[62]。虽然行走的路上“狂风呼啸,冰雪笼罩”[63],但行走者依然一路虔诚,幻影成为“记忆深处的守望”[64]。《使者》中使者并不明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但使者执着而坚定,毅然决绝地走下去,迈着艰难的步伐,本可以停止不前,“但还是愿意不断翻越高处的风雪,还终点一个神圣而悲壮的洁净”[65]。《自述》中的抒情主人公豪迈、大气,风霜雪雨,四季更替,但行进的路标依然如此醒目,铿锵的足音“从来都是波澜壮阔”[66]地跨越万水千山。抒情主人公坚毅得近乎执拗,“为了一次幻灭的爱情/舍弃了终身的向往和追寻……由此,你幸福地流泪,自由地歌唱”[67]。
虽然桑丹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渐逝唱了一曲挽歌,但她一方面伤感于传统的改变,另一方面更相信传统的改变能成为个体前行之路上“永恒的光芒……成为每盏暗夜里闪烁的星光”[68]。
作为一个藏族女性残疾人作家,桑丹在创作中没有廉价的煽情和软弱的哭泣,没有停留在不平命运的嗟叹之中,而是坚实、明澈、富于爆破力与穿透力,虽然有焦虑,但更多的是乐观、豁达、平静,这不能不叫人折服。
身为藏族,桑丹坚守自己的根,然而你看不到她因根的失落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失落之感。身为现代人,桑丹也偶尔闪现现代人的焦虑,然而时常展现的是乐观豁达、坚毅执着。在宁静中坚守,在焦虑中淡定,这,就是桑丹。
参考文献:
[1]姚新勇.朝圣之旅:诗歌、民族与文化冲突——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8,(2):163.
[2]徐美恒.论藏族女诗人的诗歌特色[J].民族文学研究,2006,(3):163.
[3][11][16][18][20][21][22][23][24][26][27][30][32][47][48][49][53]桑丹.幻美之旅[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230,231,48,71,57,5,57,58,4,21,29,4,226,15,21,27,13.
[4][5][6][7][8][9][10][12][13][14][15][17][19][25][28][29][31][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50][51][52][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桑丹.边缘积雪[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116,18,118,3,14,132,23,20,17,19,17-18,131,33,21-22,25,76,58,71,9,88,68,76,96,97,119,123,15,51,72,5,18,102,23,74,80,84,83,100,85,85-86,107,108,91,47,48,50,98,99,5.
(责任编辑李晓丽责任校对李晓丽)
Sangdan's Creation Ideas from Perspective of Dual Identities
Deng Li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
[Abstract]As a Tibetan writer,Sangdan,just like other ethnic writers,always sticks to the tradition of her own nationality. Unlike other writers,Sangdan uses poetic description of daily life of her own nationality to replace the intense cultural confrontation,uses gentle aesthetic attitude to replace heavy sentimental moods. She sticks to Tibetan culture in tranquility. Moreover,as a modern person,Sangdan occasionally has anxiety of modern people,but in most time she shows optimism,generosity,fortitude and persistence. Thus,her creation features are summed as follows: being persistent in tranquility and reserved in anxiety.
[Key words]Sangdan;creation features;Tibetan identity;identity of modern people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2-0131-06
[作者简介]邓利(1967—),女,重庆璧山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四川省“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四川残疾人作家现状调查及其问题、对策和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SC14A019);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多元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当代残疾人作家研究”(项目编号:DYWH1304)
[收稿日期]201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