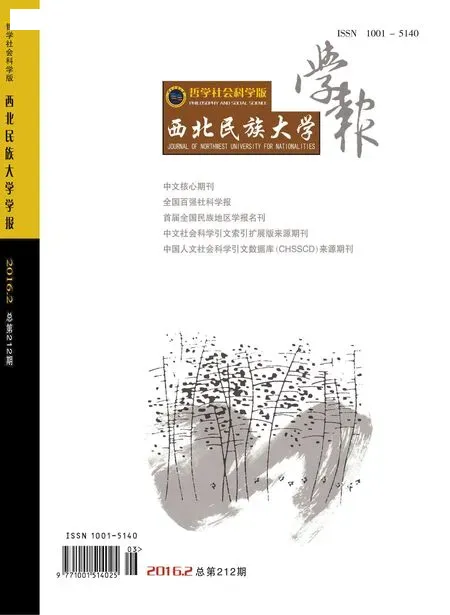新的语言观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实践
王 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新的语言观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实践
王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新的语言观正在形成,其核心是语言资源、语言生态、语言权利。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也是政治和经济资源,是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在动力。积极的语言生态观,追求语言之间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建设双语、多语和谐的语言社会。语言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对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语言观,是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思想基础,也是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
[关键词]民族语言文字;语言观;语言资源;语言生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各民族共使用着129种语言和30多种文字。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指导意见。中央精神的提出,既是对我国语言国情进行科学认识和判断的结果,也体现了新的语言观正在树立和深化。新的语言观以资源、权利、生态为核心内容,更加符合新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
一、语言资源观是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在动力
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内在动力是语言资源观的树立和深化。随着人们对语言认识的深入,过去仅被视为单纯交际工作的语言文字,其多方面的价值日益受到瞩目。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为交际工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认识不利于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如:“时代进步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已成趋势,保护和抢救有什么价值”“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与经济一体化是背道而驰”等等[1]。
但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深入,人们已经懂得,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有多方面价值的重要资源。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在信息沟通、文化传播、民族与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个体通过国家教育体系来实现“文化资本”和“语言资本”的增值。“语言资源观”带来的是对语言的珍视,而传统的语言问题观带来的常常是对语言(特别是弱势语言)的漠视与遗弃。要对语言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必须先树立语言资源观[2]。
(一)民族语言文字是政治资源
1.民族语言文字是体现民族平等的重要标志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很多民族中,民族认同往往通过语言认同才能得到体现。各民族都热爱本民族的语言,并都有维护自己母语、捍卫自己母语使用权利的天然感情。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语言不仅仅只是交际工具,还是民族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民族平等,自然包括语言平等;对民族的尊重,自然也包括对语言的尊重。而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语言是民族特征中的一个最为敏感的特征,语言和谐了,有助于民族和谐、社会和谐,语言不和谐,就会引起民族矛盾,甚至会引起社会不安定[3]。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如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实现民族平等,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由于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必将长期存在。民族平等如何得到更好的体现,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干部政策等,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也是很好的途径和形式。党和政府通过在各种场合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通过语言平等彰显民族平等,从而激发各民族的自豪感,促进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这方面,我国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例如,在国家货币上标注民族文字,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用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党和国家重要集会进行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播出和出版等。如果说,在过去人们较多地将民族语言视为一个问题,但在新时期,应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进一步强调其在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发挥其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工作中事半功倍的作用。
2.民族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
占我国国土面积70%的中西部地区,长达2.2万公里的陆上边境线,都是少数民族分布地区,这是我国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国外敌对势力和反动组织,越来越多地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对我国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的工具,试图以民族语言文字为阵地,千方百计地鼓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思想混乱,严重威胁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必须要站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工作抓手,占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阵地。如果不把民族语言文字看做政治资源,而视之为累赘、麻烦和问题,消极不作为,我们将在边疆民族工作中丧失主动权,后果不堪设想。
(二)民族语言文字是文化资源
语言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语言文字不仅只是文化成果,它还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了人,是人类传承文化、认知世界的载体和中介。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今天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
1.语言文字系统本身是各民族的文化创造
作为符号系统,语言本身就是各民族创造的最重要的文化成果。语言的书面形式——文字是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如果说有声语言也是文化成果,很多人就觉得难以理解。事实上,语言是一种结构严谨、特色鲜明、不断发展的符号体系,无论是从词根语、粘着语、屈折语、多式综合语等不同的语言类型而言,还是从语音、词汇、语法的结构特征和历史发展而言,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样品,具有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价值。语言系统的特点及发展,是各语言群体集体无意识的创造,也与各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特点相关,并深刻体现着各民族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文化交流。如维吾尔语词汇通过众多的附加成分所形成的概念的规定性和汉语词义的模糊性、维吾尔语词语搭配的严格性与汉语的灵活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著名作家王蒙在下放新疆期间学会了维吾尔语,情不自禁地感叹维吾尔语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4]。这些,都是语言符号系统自身价值的体现。
2.语言是文化发展的载体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通过语言或以语言为基础的思维能力进行。而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绝大多数都需要通过语言代代传承。有的民族还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的书写形式(即文字)来发展和传承文化,使文化成果更加精密,更加系统,流传更为久远。根据国际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90%以上是由少数民族语言及地方方言承载与传播的。我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绝大多数都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同等重要的。文化载体一旦消失,文化也将随之消失[5]。
3.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一个文化信息系统,一个知识体系
语言不仅是文化发展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凝聚体,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信息系统。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最后作为一种经验积淀在其民族语言中,因此,语言又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和文化知识的集大成的文化体系。法国著名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曾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讲,文化都是一种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文化价值要远远超过其他的民族文化现象。
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正如张公瑾先生所指出:“文化是各个民族或群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6]一种文化的特点,与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相关,也与各民族的认知特点、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知识,就沉淀在语言中,构成多样性的人类知识的宝库。例如,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有350多个,形容骏马的词语有100多个,有关马的其他特征的词语600多个,非马背上的民族很难有这样的语言奇观[7],而地处西南边疆的傣族,因生活在有动植物王国美誉的热带雨林地域,其语言中则有丰富的动植物名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都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认知成果在语言中的反映,其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三)民族语言文字是社会资源
语言是社会资源,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只有有了语言,人类社会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这是语言的基本属性,无须赘述。但在多民族国家中,语言作为社会资源还有如下价值:
1.语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一般所说的构成民族的四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要素现在已经不是确认民族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对于大多数缺乏统一宗教信仰力量来维系民族情感的民族来说,语言文字在民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反之,如果没有一定比例的民族语言使用人口,或者民族语言已经消亡,则民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同时,还可以通过促进和谐语言关系建设,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增进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和谐与民族团结。
2.在多民族杂居社会中,语言资源是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条件
在封闭的单一语言社区,语言在这方面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大规模流动与聚集,语言的社会资源属性就凸显出来。语言资源的多样性,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社会交往的需要。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向开放的社区转化的时候,人们有意识地利用和管理语言资源以便适应新的环境,这是人们社会行为中工具理性的体现[8]。人们以语言为媒介,构建社会关系,并形成特定的语言社区。这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十分常见,在新时期多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城镇地区也有突出表现。
(四)民族语言文字是经济资源
当前,关于语言是经济资源的认识方兴未艾。如瑞士人普遍掌握多种语言,日内瓦大学弗拉索瓦·格林教授的研究小组指出,每年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10%受益于语言的多样性。最近十年来,语言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引起全球性关注。例如,与西班牙语学习相关联的产业产值每年达1 500亿欧元。在我国,外语培训、翻译、出版市场产值接近1 000亿元。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文字识别、机器翻译、语言康复等正在成为新兴的语言产业领域。中国互联网中心预测,未来5年,仅中文语音市场的产值将达到1 300亿元[9]。
不是只有强势语言或通用语言才有经济价值。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绝对数量大,市场空间巨大。随着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旅游业等服务产业的兴起,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之相关的民族语言学习、翻译、出版、影视等产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只是产业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绝大多数语言的产业价值尚未得到开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作为经济资源的性质会越来越凸显,其经济价值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二、语言生态观是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思想依据
随着人们对自然生态了解的加深,社会和文化也分别被作为生态系统重新进行认识。自然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生物多样性基础,相应的,文化生态也要求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就是语言多样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将语言视为一种生态现象。1972年,豪根首先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他指出,“语言生态是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10]。所谓“环境”,并非通常所说的上下文或语境,而是使用语言的社会以及比社会更广泛的周围世界的环境,而且语言本身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后来,范莱尔(L.van Lier)进一步界定了语言生态的具体内容:(1)语言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如语言中有大量表达自然界和周围世界的性质与变化、客观世界方位与行动的方式,以及各种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的表征,都表明语言与物质环境关系密切;(2)语言与社会及文化环境的关系;(3)语言的多样性和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4)语言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等[11]。语言既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而受后者的制约,也反过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构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不论是自然、社会和文化,这些生态系统都有着类似的特征。系统中的各物种、各成分、各要素都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竞争的复杂关系。此外,这些生态系统的发展与人密切相关,人是影响这些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人们在自然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增加了对社会、文化乃至语言生态的认识,生态保护的意识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也是对各生态系统发展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体现。在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对语言生态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为语言文字保护工作提供了思想依据。主要表现在:
首先,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语言多样性是各民族语言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多样性的自然物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丰富多样、异质性强的生态系统才能协调、可持续发展,物种稀少的生态系统是失衡而脆弱的。语言生态系统则是多种语言共存并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体系,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在长期吸收其他民族语言成分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完善起来。弱势语言的消亡也必将影响到强势语言的发展。就像单一物种的自然界必将灭亡一样,“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12]。
其次,语言之间可以和谐共处、协同发展。自然生态环境中,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斗争并非生态发展的全部内容,协同进化的观点更能反映自然界发展的实际。“应该说,协同进化的观点比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进化论,在反映自然进化时更全面、更准确。”[13]协同进化论承认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的自我组织功能和维持能力,认为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密切关联,相互依存,协同进化,并包括相互受益和相互制约两种机制,在优胜劣汰的同时,也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增加,物种的共同适应,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协同进化造就了生物圈的千姿万态,维系了生物圈的持续演化发展,协调了全球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共同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语言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语言生态系统中,各种语言确实存在竞争和制约关系,但在另一方面,相互受益的机制也有充分体现:在语言发展上,不同语言间相互吸收,互为不可缺少的发展条件;在使用功能上,不同的语言存在互补关系。如果加以科学引导,完全可以构建起功能互补、和谐共存的和谐语言社会,为语言多样性奠定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三,积极的观念和措施,有利于语言生态保护。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和文化生态,都与人密切相关,人是影响各种生态环境的决定因素。人的认识和活动既能造成生态环境和恶化,也能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生态保护业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生态建设被列为我国新时期的战略工作。如果通过有效的宣传,引导人们对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持有积极的评价,进而改善语言的生态环境,弱势语言就可以得到科学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也可以得到长期保持。
三、语言权利观的强化,对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新的时期,从全世界范围看,权利意识的强化,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人们不仅要求生存权,也要求发展权。不仅要求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也要求文化权利。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权利意识的强化,对于国家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中,语言权利观念的强化,尤其值得高度关注。
语言权利是指同类人群或个人学习、使用、传播和接受本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和其他交际语言的权利的总和。它包括群体语言权和个体语言权。民族语言权当然也包括民族成员的个体语言权,但主要体现为群体性语言权利[14]。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语言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而非只是单纯的交际工具。总的来说,语言的核心价值包括交流工具、认同标记和作为文化结晶的内在价值。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时所产生的语言权利就是工具性语言权利,如使用某种语言表达思想的权利。但语言权利更多地表现为非工具性语言权利,即语言和文化认同[15],也就是人们有权以自己的语言生活,并享有安全的语言环境,相信“他们自己所属的语言群体会繁荣,人们将有尊严地使用自己的语言”[16]。对母语和本族文化的认同属于精神利益,具有不易改变和替代的特征。学界一般认为,这种认同直接地涉及人的尊严和生活的意义。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为了捍卫文化多样性,以尊重人的尊严,“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7]
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保障,主要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条文,坚持语言平等,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自愿选择使用某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把保障和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作为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载体,把促进各民族语言的和谐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体现。
权利的行使必须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依据。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保障仍缺乏立法支持。除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有原则性阐述外,在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是最高行政机关制定(或转发)的数份文件,而缺乏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民族自治地方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和实施细则。随着各民族语言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当前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立法状况难以满足新时期工作要求。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立法,将是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
四、结语
以语言资源、语言生态、语言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新的语言观,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条件下,人们对语言形成的新认识。当前,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功能弱化,使用范围缩小,甚至走向濒危和消亡。因此,新的语言观的树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形成保护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文化氛围,提高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和谐语言生活提供思想认识基础。有必要通过宣传和引导,将新的语言观从学术层面传播到社会各界。以新的语言观为思想基础,在党的“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3]戴庆厦.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N].贵州民族报,2013-05-27.
[2]方小兵.语言保护的三大着眼点:资源、生态与权利[J].民族翻译,2013,(4).
[4]王蒙.四月泥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40.
[5]黄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述要[J].民族翻译,2013,(3).
[6]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
[7]李宇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8]李荣刚.城市化对乡村语言变化的影响[J].重庆社会科学,2011,(10).
[9]陈鹏,贺宏志.中国语言产业亟待加速[N].人民日报,2013-04-25.
[10]Haugen, E.The Ecology of Language[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325.
[11]徐佳.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36.
[12]Fishman J.A.Reversing Language shift: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M].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1991.67.
[13]周光召.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报告[J].科学中国人,1995,(4).
[14]杨晓畅.浅论个体语言权及其立法保护[J].学术交流,2005,(10).
[15]Ruth Rubio-Marin. Language Rights:Exploring the competing Rationales[A].in Will Kymlicka and Alan Patten(eds.),Language rights and Political theory[C].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57.
[16] Leslie Green. Are Language Rights Fundamental?[J].Osgoode Hall Law Journal,1987,(25):658.
[17]孙宏开.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30.
(责任编辑木易责任校对戴正)
New Language Idea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Writing
Wang Fe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cial Sciences Academy of China,Beijing,100081)
[Abstract]New language idea is forming along with the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ts core is language resource,language ecology and language rights. Languages a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social resources,are the internal drive for the work concerning ethnic language and writing. Positive idea of language ecology goes for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and is use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bilingual,multilingual society.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idea of language rights puts forwards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work concerning ethn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ra. New language idea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languages,and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rive for the work concerning ethnic languag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ethnic languages and writing;language idea;language resources;language ecology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2-0108-06
[作者简介]王锋(1971—),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副研究员,博士,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藏缅语族语言和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