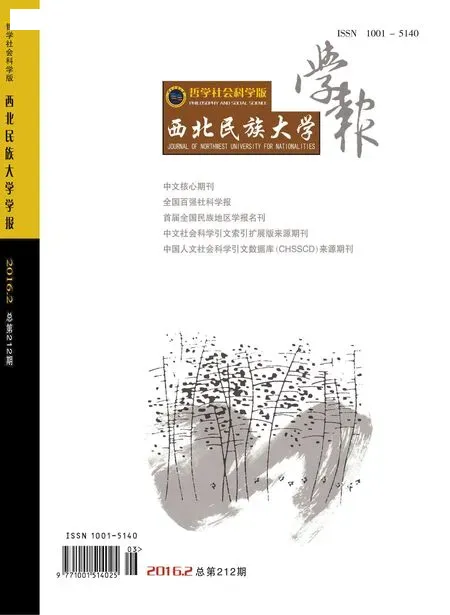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常海燕
(广东医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
——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常海燕
(广东医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现代建构论与“族群—象征”论是西方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二者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历史、现代性与地方能动性之间形成了张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场景下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撒拉族族源传说口述文本,动态地呈现撒拉族在挤压、推拉的民族关系格局中不断形塑自身的过程,揭示策略性的文化建构如何延续民族社会,并进一步说明文化机制对民族生存的独特柔性作用。
[关键词]文化建构机制;民族社会延续;口述文本;历史人类学
基于西方强调政治与国家认同的“现代性”建构论以及强调本土族群文化结构作用的“族群—象征”论两大民族主义理论路径,国内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与批判。*相关论文主要如下:叶江,沈惠平《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启迪》,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3-47页;马衍阳《〈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载于《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第72-76页;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徐大慰《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第67-69页。大体来说,现代建构论者忽视了非工业社会与非资本主义体系下共同体认同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的历史文化基础及其为民族建构提供客观历史资源的可能性;族群—象征理论则在反对现代性建构的同时,忽视了“国家”、“世界”等外部力量的作用及其所引发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易变性与适应性。针对上述的理论分歧以及中国“多元一体”的复杂历史,考察撒拉族独特、具体的演化史,能呈现出文化营造机制与国家建构之间动态性的同构关系。
一、民族记忆的符号化象征——骆驼泉传说
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一个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的重要聚居地。在其县境中东部有一块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当地汉语方言称为街子(读为gaizi,源于“街集”jieji),是撒拉族民间传说中先民最早的定居地,即“根子地”。在此地中心有一方长约40米,宽约20米的椭圆形自然泉水池,汉语称为“骆驼泉”。水池中央原来有一尊白色的喷水石骆驼,据当地撒拉人的传说,这尊白色的石骆驼是撒拉族东迁时驮过中亚故乡的水、土和古兰经的那只白骆驼“圣化为石”的[1]。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撒拉民间认为民国时期甘肃河州回族军阀马安良为了破坏撒拉人的“脉息”,把骆驼石砸断过。新中国成立前撒拉人一直以骆驼石作为治疗精神异常或不孕症的灵药而凿取食用,导致石头也越来越小。“文革”时整个骆驼石又被红卫兵砸成三段,逐渐沉入水底的淤泥中,从外面已经看不到了。原来的“骆驼石”现早已消失不见。但围绕着这方泉水及其水中的“骆驼石”却形成了撒拉族独特的民族记忆、族源传说以及民间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骆驼”成为撒拉人建构民族认同文化的核心符号与象征。
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是绝对禁止偶像内容出现的。但信奉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人却在族源传说中把认同的情感投射在“白骆驼”这样一种独特的动物身上。这种心理投射又是如何产生的?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由于撒拉族自身没有民族文字的翔实记载,“汉文”史志也不可能深入、细致地记录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所以要了解这些历史性问题,只能通过“串联”不同时期撒拉族民间口述的“骆驼泉”文本记录并结合田野调查来做历史人类学的分析。
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骆驼泉”文本,在时间跨度上从清末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骆驼泉口述文本大多是不同时期到访撒拉族社会的中外探险家、传教士、突厥语专家等搜集、记录下来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的相关口述文本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识别”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历史背景下,由获得明确独立的民族政治身份后的撒拉族首批民间文化工作者搜集、整理并加工创作的。
从不同时期各种版本的表述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文本比较古朴,表达的内容主要是部族之间的争斗与循化区域内“多元化族群互动的历史格局”;清至民初后的文本内容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始从“污名化”的陈述转向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神圣化”表达;“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本逐渐定型并不断加强宗教道德与民族意识的渲染。从以上不同社会阶段文本内容的差异化表述能够比较清楚地透视到撒拉族如何通过“口述文本”来构建“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
二、多元族群错杂时期的“分化”
据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有关撒拉族族源传说文本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该文本是由俄国中亚探险家N·G波塔宁在循化东部的孟达村采访时所记录的《撒拉族移居黄河的传说》与《阿合莽族和尕勒莽族》传说[2]。《撒拉族移居黄河的传说》中:
撒拉族的祖先在距今五百年前的大明洪武治世时来到Khatun-gol。他们是三个人。他们为了盗牝牛而被撒马尔罕追逐。以前撒拉族地区还有Sari-Mughal族。他们没有定居地,带着家畜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以后就离开了这个地区。
上述文本中的“Khatun-gol”音译过来是“唐古拉”,这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对西夏的称呼“唐兀”,后演变为对安多一带藏族的称呼,清朝早期的文献也沿用此称呼藏区的蒙古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Sari-Mughal”译为“撒拉—蒙古人”,是指撒拉族从中亚迁移到循化前在循化撒拉地区游牧的蒙古人。从文本表述中涉及的这些称呼可以看到,早期撒拉人驻地是一个“多元族群”交错游动、迁徙频仍的“游牧者地带”。
而波塔宁同时记录的另一个口述文本《阿合莽族和尕勒莽族》则更明显地传达出这种游牧性族群社会内部惯常存在的分化与斗争。《阿合莽族和尕勒莽族》中:
有这样两个种族:阿合莽和尕勒莽。阿合莽和我们(循化撒拉族)是同族,尕勒莽族有尾巴。他们之间战争不绝。(注:关于循化撒拉族,有起源于尕勒莽和起源于阿合莽这样两种传说。)
这则比较古朴的口述文本,与今天撒拉族民间文化工作者讲述、营造的“尕勒莽与阿合莽两位英勇的撒拉人兄弟先祖”的和睦论调完全不同。联系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文本所叙述的地方“孟达”至今仍是撒拉民间社会所认为的保存着蒙古、藏两族混合性特点最多的区域,可以想到早期循化社会在多元族群互动的现实中,“污名化”他族成为形成狭隘认同意识的一种隐喻式表达。
从社会结构来看,撒拉社会历史上一直存在不同层级组织单元的“分枝”特性,追述与撒拉先民历史有所关联的中亚突厥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可以发现西突厥在中亚的主体部族突厥乌古斯及其分支撒拉尔部以及由乌古斯部族建立的塞尔柱王朝的社会结构都是以“左右两厢”的方式扩展,并且在权力形态上也表现出“双王制”(dualkinship)或“两兄弟型”的传统[3]。日本著名中亚史研究先驱者佐口透也曾指出在移居中国前夕的中亚花剌子模的撒鲁尔Salur(Salor)部族就分为内Salur和外Salur两个集团[4]。
至少到清朝初期,循化撒拉族就开始以“工”*工(qaun),是撒拉族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地方组织的称呼,最早始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此前以“庄”或“沟”为村庄名,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但其范围大于村落而略小于乡。康熙末年结束茶马互市,雍正七年在循化撒拉族聚居区实行“查田定赋、设营驻兵”的直接统治,整个地区的撒拉族被统称为“撒拉十二工”。清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后,撒拉族人口锐减一半,十二工并为八工,此后至今循化撒拉族仍以“撒拉八工”来号称。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上下六工”的两分型社会形态;清中后期撒拉族又以“撒拉八工、外五工”来统称撒拉社会整体,而“撒拉八工”即清初“上、下六工”人口收缩为“上、下四工”,又被称为“内八工”。而“外五工”一般指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迁移到黄河对岸后的化隆县甘都镇的撒拉人后代[5]。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游牧性部族还是农牧定居社会,撒拉族都存在着这种“两分”的独特分裂式社会结构,并且在分裂中又与循化周边其他外族不断融合。这些分裂过程中的融合为“污名化”的叙述模式提供了社会土壤。尽管相关历史研究表明撒拉族先民定居中国循化与1219年成吉思汗首次西征中亚的军事行动紧密相关。*撒拉族学者马成俊《关于撒拉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1卷第2期;芈一之《撒拉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日本中亚史学者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09页。一些国内外其他撒拉族研究者基本都肯定这一历史事实。但这样的历史事实却改变不了循化地区早期社会不同族群混居环境中撒拉族被“污名化”的社会认知。并且这一传说一直沿袭到1957年。此年苏联突厥语言学家E·R·捷尼舍夫在循化街子采集的《撒拉族移居的历史》的传说中,循化西部的撒拉人仍认为东迁中国是被诬陷后的抗争[6]。
在捷尼舍夫记录的文本中还反复讲述了撒拉先民迁徙途中经过了许多地方,如兰州、西宁等等,但因这些地方的水土都不符合故乡圣水、圣土的重量,不适宜居住,只能不断迁徙,直到最终找到循化这样水土和牧草都理想的地方。佐口透认为这种反复诉说迁徙旅途艰苦的传说模式在内陆亚细亚诸民族的始祖传说中是常见的,具有始祖传说或者部落传说的性质[7]。撒拉人通过这种模式化的讲述记忆群体的历史并形成对新居地的认同意识。
随着明初“蒙古人”的军事撤离及其势力淡出循化撒拉人的视野,循化撒拉族又历经明朝270多年作为“番族”之一的“土司”制度的羁縻,撒拉社会也逐渐完成从“多元性族群”交错的局面向一体化的撒拉社会转型。“两兄弟”对立的故事模式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只讲述其中的一位始祖尕勒莽,循化境内东、西各地区也演化成传说中尕勒莽的各直系子孙的属地[8]。
三、清末民初撒拉社会的“伊斯兰化”
明至清初,地处藏文化“环抱”的撒拉社会在清中后期越来越受到来自西北甘、青两地民族军事集团势力的渗透与影响。到了清末民初,着手统治青海的马步芳家族为了结束青海地区苏菲派各门宦互相争夺教权导致的内讧局面,强行在青海穆斯林社会推行伊赫瓦尼新教,尤其是在包括青海循化撒拉族聚居区之内的海东穆斯林民众聚居的农业区域,严格实行“尊经革俗”“回归伊斯兰”的主张[9]。
从清中后期撒拉人参与“苏菲门宦”教争开始,撒拉社会原有的“多元混杂性”特点就不断通过神秘化的苏菲门宦与伊斯兰新教被一步步“清洗”掉。在循化撒拉社会被整合进西北穆斯林族团的过程中,“偷牛说”的叙事模式也不断被“去污名化”,修正为“骆驼圣化说”,强化了“白骆驼”在族源传说中的神秘性与神圣化的宗教色彩。
在1921年基督教传教士安德鲁记录的撒拉族族源传说文本中,还未出现至今已在撒拉族社会普及化的“白骆驼变石头所以定居循化”的传说情节,而骆驼是以“山上岩画”[10]的形式显示奇迹并引导撒拉先民们在此定居下来的。
到了1957年,这个历经30多年的“白骆驼圣化”传说在“白骆驼显圣”的细节上不断被完善并逐步定型,此年捷尼舍夫在循化街子调查时记录的《撒拉族移居的历史》的文本中不但有了“白驼化石”的情节,而且明确表明“水的恩赐是骆驼跨过的地方得来的”。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色彩的传说表述与一些相关的仪式开始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成为撒拉族社会文化的核心。传说文本中有关“白骆驼”从“山岩画像”到“石化雕像”的变化,在实质上都表明撒拉族在周边社会伊斯兰化情景的逼迫下策略性的建构了自身的文化。
仅以传说文本本身的表述来看,放弃早期代表游牧色彩的“牛”,选择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白骆驼”这个象征符号,大致存在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与伊斯兰文化传统中骆驼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及其宗教意义相关。骆驼在沙漠阿拉伯人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性被吸纳、具象化到闪族宗教及其伊斯兰教的精神体系中,“闪族宗教的雏形,是在绿洲里发展起来的,不是在沙漠里发展起来的,这种雏形宗教,以石头和源泉为中心,那是伊斯兰教的玄石和渗渗泉,以及《旧约》中的伯特利的先河”[11]。因此,骆驼与石头、水的关系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就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这是“白骆驼”能够被严禁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社会容忍的根本原因。
二是,与当时西北甘、青社会主流的伊斯兰化趋势以及中央王朝汉儒正统的“德化”情景紧密相关。清中后期,中国西北穆斯林社会在与西方伊斯兰教中心地带交流松弛后,开始接受内地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义相结合“以儒诠经”的符合汉语社会语境的“道德”解释方式。如清乾隆时期南京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回儒”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就用“五德”阐释伊斯兰教义中的“骆驼”[12]。这种富有“德性”向度的“儒学化”解释使得“骆驼”这个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在中国西北这样一个处于伊斯兰文化与汉儒文化中间地带的双重边缘社会获得了生命力与适应性。
三是,“骆驼泉”的符号意义与撒拉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是紧密相关的,围绕着它已经生长为一种甘青社会“地方性知识”体系。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在西北陕、甘、宁、青穆斯林聚居区传教、考察,可以从他所拍的照片中看到当时许多学经的穆斯林男女儿童都手持骆驼肩胛骨牌,在上面学写经文[13]。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马麒主政青海时在民间寻访“骆驼寺”建筑模式的知情者,依旧遵循其风格,在故址上了重建西宁大寺[14]。可以说,在清末民初那段时间,甘青穆斯林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种以“骆驼”作为圣洁宗教品格与高尚道德象征的文化建构高潮。因此,撒拉族在泉水中塑造“白骆驼”雕塑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应此社会文化浪潮的表现。
同时,撒拉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以“白骆驼”为核心的复杂仪式。从田野调查获知,大致有三类相关的仪式行为:专门用于婚礼上娱乐表演的“骆驼戏”;*撒拉语为tūye oina或tūbe oina,即“对委奥依纳”,tūye是“骆驼”,oina是“玩”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玩骆驼”的意思,一般在撒拉族婚礼晚宴后表演,所以逐渐成为“婚礼”的代名词,其具体内容主要是以简单的对话与动作表演族源传说,多为戏谑,其起源时间不可考。参见常海燕《撒拉族骆驼戏的历史形态探析兼及民俗文化的生存法则》,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197-201页。干旱时在“骆驼泉”的祈雨仪式;*在循化街子马家村做田野调查时,六十八岁的沈阿卜杜老人及其老伴(他们都属于格的目老教)给我讲述了他们早年没有灌溉设施时亲身经历的求雨仪式的片段:天气干旱时,全村的男人由寺里的阿訇领着到“坦库”(街子东边的沙子坡上)求雨,头戴柳条帽,挽着裤腿,赤脚走到荒郊,由阿訇带领大家礼拜,念“胡图白”(阿拉伯语,指祈祷经文)。村里的妇女不让婴儿吃奶,牛羊不让吃草料,尽量让发出喊叫声。如果还不下雨,就由几个庄子上的阿訇们一起彻夜念《古兰经》经,还要在一匹母马头骨上写下经文。老人还特别强调必须是母马头,其他牲畜的头都不行。参见常海燕《作为“文明”流动的“水”——撒拉族“骆驼泉”的人类学研究》,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8-109页。最后是把“骆驼石”作为治疗精神异常或不生育的“都哇”。*都哇”,也作“都阿”,阿拉伯语,意为祈祷、祷告,这里引申为“药”。凡属神经异常或精神失常的“脏病”,尤其讲究吃“都哇”,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西北甘青宁穆斯林居民广为奉行的一种医疗习俗。撒拉人深信族源传说叙述的白骆驼化成的骆驼泉中的“骆驼石”具有神奇的功能,特别是对治疗不孕症及“脏病”。所以,附近村落以及方圆十数里外的村民有这些“病症”时都来此凿一些粉末回家作为“都哇”服用,时间一长,石头也越来越小。“文革”时整个骆驼石又被砸成三段,(民间还有说法,民国时期马安良为了破坏撒拉人的“脉息”,把骆驼石砸断过。)逐渐沉入水底的淤泥中,从外面已经看不到了。参见宁夏大学杨文笔民族学硕士论文《西北山区回族“都哇”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所以,撒拉人对于“骆驼石”的文化情结有着深远、宽广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信仰基础,它作为撒拉族的文化基石,只要现实社会结构需要,可以以此作为“原浆”,混合其他多种因素,酿造适合自身的“甘泉”。然而在当下社会情境下,由于撒拉族从西北信奉伊斯兰教的“族群”中被分离“识别”出来,导致他们在重新建构“白骆驼”的民族认同的文化活动时遭到来自周边其他方面的批评微词。
四、新时期作为单一民族“撒拉族”的文化重建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以“民族识别”政治框架应对国族需要的合理化并巩固现实人群利益的历史背景下,撒拉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及其自己“书写历史”的机会。
在完成国家按照“一民族一文化”预设框架下的民族遗产保护、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民族工作任务时,单一化族体的局面使得撒拉族自治县政府及其本民族精英们必须“自说自话”了。因此,为了与周边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作出明显区分,撒拉族社会开始由上层精英主导重新撷取能凸显出自身传统的“骆驼泉”作为民族文化建构的重点对象。
早在1984年,由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省、市、县展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大普查、大采录工作中,撒拉族最早参与搜集民间文学口述与编辑的撒拉族首批民间文化工作者就在当时的民族意识语境下,开始自觉抵制了民间传说中还存在的“偷牛说”,并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
在1981年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2分册的《骆驼泉的故事》,用采取避免谈论迁徙原因的表述方式[15];1982年出版的《撒拉族简史》中《关于撒拉族族源的口头传说》,则采取了和当时社会语境紧密相关的“阶级迫害说”的表述模式,尕勒莽和阿合莽被改造成“被忌妒他们威望的统治者国王诬陷、迫害的民族英雄”[16]。
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文化旅游热以及本世纪初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等一系列“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经济或政治背景下,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政府以及掌握本民族“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开始从不同角度达成共识:重新打造“骆驼泉”以作为对外宣传撒拉族文化的名片。但这种重建与撒拉社会日常生活积淀下来的对骆驼泉“混融”与神秘性的地方认同是相背离的,因此在“传统的发明”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
1988年后,由于民族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循化县政府曾多次想把骆驼泉列为民族特色旅游项目,争取各方面的投资。但是迫于经济条件与街子清真寺寺管会和当地乡老们的压力,被迫放弃。2009年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决定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作为观摩会现场,为了这次国家性的会议以及借此机会对外宣传撒拉族文化,循化县政府下定决心要把骆驼泉扩建成唯一一个撒拉族民族特色旅游点。为了取得民众支持,县政府首先召开会议号召各族干部和工作人员要向“前”看,超“前”走;会后又组织发动一些撒拉族退休干部、民间文艺爱好者组成专家、顾问团,征求他们的建议与方案。除了骆驼泉的扩建外,循化县政府还在这些撒拉民间精英团体的协助下重新规划撒拉族特色的服饰、音乐、饮食以及建筑样式等等,实行以“撒拉化”与“伊斯兰化”为主流的“文化营造”活动,重建撒拉族自身的对外形象。
但此次扩建之初同样也遭到街子村民们和街子清真大寺寺管会成员的反对,虽然县政府以增加拆迁补偿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等经济手段解决了此次争端,但在调查中,很多老年人仍然在心里认为骆驼泉和清真寺是不能分开的。古兰经是骆驼驮来的,现在因为搞旅游被分开了;一些宗教人士则明确表达他们反对的原因:撒拉族民俗展览处处放着与伊斯兰教法相悖的“苏热体”(有眼睛之物),效仿其他地方“立塑像”、搞“祖宗崇拜”,严重违背伊斯兰教义;旅游娱乐与神圣、清静的宗教氛围是相悖的。但也有一些外出务工多年的年轻人认同县政府的开发行为,认为可以通过旅游对外宣传,让别人了解撒拉族,应该加大开发力度。
由此可知,骆驼泉的这次扩建几乎是县政府官方机构与精英阶层对撒拉族在现代性社会场景下生存境遇的反应,原本拥有骆驼泉“混杂生活资源”的当地民众只能“无语”,一些教职人员的主张也同样抵抗不了世俗化与市场化的进程。
但与此同时,虽然新扩建的骆驼泉景点让当地一些撒拉人有些“神伤”,但随着外来游客涌向“骆驼泉”旅游的热潮下,特别是千年手抄本《古兰经》成为国家文物局立项保护的国家级文物之后,除了带给附近居民经济利益外,也给当地的撒拉人带来了以往难得的喜悦与自豪。并且这种民族自豪感又引发了撒拉族学术研究知识的更新,2008年在由循化撒拉族民间学术组织青海撒拉族研究会召开的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参会成员们重新讨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撒拉族史汉族研究专家芈一之的历史观点,“撒拉族先民是中亚西突厥乌古斯部的分支撒鲁尔部的后裔,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后被签发为西域亲军驻防在循化”[17]。一致通过决议推断在被西征的成吉思汗签发之前撒拉族先民本是撒鲁尔王朝成员,并以拥有的千年前的手抄本《古兰经》作为某种事实依据,肯定自身民族历史的源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在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下,撒拉族一些企业家和民间精英又开始敏锐捕捉到新的契机,准备以“中国土库曼斯坦人”的独特身份积极与中亚诸国展开经济和文化联系。
综上所述,对不同社会时期围绕“骆驼泉”所发生的文化意义的创造与变化过程,可以发现民族文化的建构是随着社会具体场景的变化而不断被加工、转换与营造的。但是,选择用以转场的文化要素或象征符号却体现出民族主体特别是精英阶层的能动性策略。骆驼泉从“文革”被毁、官方组织重建以至当下的扩建,其一波三折的经历折射出“地方传统知识”在国家政权与周边族群格局变迁过程中的断裂与延续。
五、结语
“传统发明”主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的“现代性”论题有着联系。在西方经典民族理论的创造者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那里都把它视为一种“相当晚近”的“人为”构建民族的重要途径。他们都强调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18]。对于盖尔纳与霍布斯鲍姆来说,“传统发明”这种文化机制是“现代社会”生发“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手段”,是植根于“现代社会经济过程与新的意识形态、社会热情的强有力的政治文化表述”方式。但没有“在民族主义的新的工业化文化和民族主义宣称为其来源的神话似的‘消失的文化’之间看到其连续性”[19]。
对于这两位理性政治民族论者来说,其抽象、宏大的“叙事”都直接源于欧美世界社会历史经验的一般性归纳与思辨,但面对中国“多元一体”的漫长、复杂历史传统,那种“植根于工业文明的同质性文化要求”的深刻而简单的论点显然缺乏完全充分的说服力。“撒拉族”的“传统发明”与“工业化或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并非如此直接、清晰。
与西方现代建构论的民族主义理论比较,撒拉族的“文化建构”并非仅仅是现代国族时代开始的“新生事物”,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群体延续其生存的动态机制与能动性策略。在争取政治地位、生存资源以及社会名望等利益的驱动下,每次“文化建构”会呈现出与历史上或当下日常生活实践等业已稳定格局不同程度的“脱轨”状态,并以此应对民族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与改变。特别是各类民族精英群体敏锐而灵活的“表述”与“创造”,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正是他们的创造性活动联通了“国家”与“地方”民族,并产生了多样性可能。
所以,如何维系民族稳定格局,总结历史上处理复杂民族关系格局时期的有益经验与智慧,并掌握灵活机制的民族策略尤为重要。对文化构建活动“量体裁衣”般的“拿捏”与“平衡”也应该是“国族时代”应有的政治考量。在这种考量背后,应该看到“地方”或“他族”并非被动的镶嵌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块积木,他们也同样是历史与国家能动的参与者。
参考文献:
[1]马成俊.骆驼泉与撒拉族[J].文史知识,2006,(2):82.
[2][4][6][7][8][10][日]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M].章莹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59-73,109,62-67,75-77,65-67,62.
[3]王治来.中亚通史(上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197,207.
[5]韩得福.孔木散:撒拉族基层社会组织研究[J].中国撒拉族,2008,(1):48-49.
[9]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96-100.
[11][美]希提(P.K.Hitti).阿拉伯通史(上册)[M].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1-17.
[12][清]刘智.天方典礼[Z].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69-170.
[13]王建平.中国陕甘宁清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77.
[14]勉卫忠.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之“骆驼寺”的千年传说[Z].绿荫(内部资料).2011.
[15]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A].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二分册)[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370-371.
[16]撒拉族简史编写组.撒拉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8-9.
[17]芈一之.撒拉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6-8.
[18][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
[19]罗伊德·克雷默,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意义[A].陈启能,倪为国.历史与当下(第二辑)[C].邱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5.22-23.
(责任编辑贺卫光责任校对马倩)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2-0077-07
[作者简介]常海燕(1978—),女,山西临汾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文化再造与民族格局稳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伊斯兰民族撒拉族为个案”(项目编号:14JYC850003)
[收稿日期]2015-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