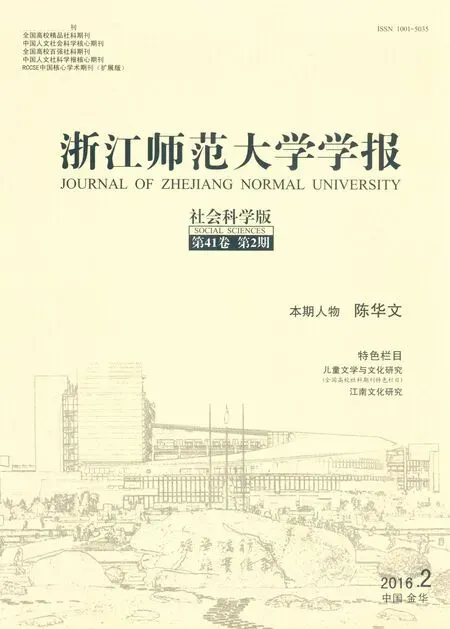破、立、持:《庄子》生死观的“三段论”
王 锟, 邵林凡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破、立、持:《庄子》生死观的“三段论”
王锟,邵林凡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把《庄子》一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认为《庄子》书中的生死观内涵着“破、立、持”三段论:“破”的阶段以“物化”对世俗的生死观进行摧毁,“立”的阶段以不灭之“我”的肯定来建立积极的生存观,而“持”的阶段以“人故无情”的阐明使 “我”在“物化”的过程中保持对生死不作是非、好恶的念头。“破、立、持”三段论既区别又融贯,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死观。
关键词:《庄子》;生死观;物化;我;无情
如何看待生死,一直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共同话题。对生死的哲思是《庄子》一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该书最深邃、最迷人的地方。对《庄子》生死观的讨论,学界观点不一。本文与学界的不同之处有两方面:就内容而言,学界探讨多集中在“物化”[1]61(即本文所谓“破”的方面)的研究,而对后两个方面,即不灭的“我”[1]381(即本文所谓“立”的方面)和“人故无情”[1]121(即本文所谓“持”的方面)鲜有涉及。就文本而言,本文并不严格区分为内、外、杂篇,而是将《庄子》一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融汇诠解。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庄子》的生死观存在着较为独立的几个方面,只是力求在逻辑上对其进行贯通,考察其是否存在较为融贯的系统。
一、“物化”——破的阶段
“物化”是《庄子》生死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涂光社先生说:“‘物化’的要义是,宇宙万物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中,万物以至各种生命个体虽然各具形质,但都是互相转化的某个阶段的一个暂时的存在形态。” “对于人来说,‘化’常指由生而死化为他物的变异过程。”[2]事实上,“物化”概念在《庄子》中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是化为他物的意思,即上文涂光社所指的“物化”;其次是万物化育的意思,同于《老子》37章里的“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中的“物化”;最后是随波逐流而被外物干扰的意思,如《天地》篇中所说,“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1]226“物化”的这三层含义主旨是“化为他物”,这也是上述涂光社所说的。笔者采纳他对“物化”的定义来讨论《庄子》的生死观。必须指出,除了“物化”概念,《庄子》生死观中还有与之类似的其他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气变”[1]334和“万化”,[1]381因此有必要澄清“物化”与“气变”“万化”的关系。“物化”强调的是“化”的结果,即由一物化为他物。“气变”强调的是“化”的承载者,即气,所谓“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1]334也就是说,生死是气的聚集与消散而已,气是这一变化过程的承载者。而“万化”强调的是“物化”过程的恒久无息的特征,所以用了“万”字来强调这一特征。本文将根据具体语境或使用“物化”,或使用“气变”,或使用“万化”来阐述相关内容,但后两个概念可以归纳于“物化”这一概念之下,所以“物化”概念在《庄子》中是最主要的。
在《庄子》中,“物化”(一物化为他物)的方向具有各种可能性。比如《大宗师》里说:“反覆始终,不知端倪。”[1]148“伟哉造物!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1]144也就是说,“物化”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保证下一次“化”所造就的就是人而非他物。“物化”的这种可能性消除了人与他物之间的价值的不平等,在“物化”中,一切之“化”都有可能,人并不具备优越性。所以《大宗师》说:“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1]145
总而言之,庄子认为生死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虽然死后不一定再一次转变为人,但死后有生,生后有死,生死相扣若环,生是向死的状态,死是向生的状态。因此生中有死的潜在,死中有生的潜在,基于这样的认识,庄子认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1]35“方”体现了人生的短暂,也体现了生死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的一生在“物化”之中,不过是一环,所以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1]397但是庄子并不是泯灭生与死的区别,他只是将生与死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考察,放在“物化”中去考察。在这种背景中,生和死的那种不平等的价值被拉平了,人与他物的不平等的价值被拉平了。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于“物化”的论述通常是将其划分为几个方面并分别加以探讨的,即“物化”大致归类为:必然的生死观、气变的生死观、道一的生死观、超越的生死观。这种探讨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这几个方面实际上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的几个侧面,而非庄子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或逐层递进的思想。因为,气变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是自然界不可逆的过程,气变观只是强调了这一过程的活动主体是气。而这一过程的结论则是生死无贵贱之别,不必执著,即以道视之,万物齐一。换言之,根据气变的客观必然过程所得出的主观结论是道一的生死观,而道一的生死观本身又是对生死的超越。所以,《庄子》生死观的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前二者偏重于对自然的客观方面的描述,那么后二者则是根据描述所得出的主观方面的结论。这四个方面合而为一,则是本文所谓的《庄子》生死观中“物化”的方面。
综上,《庄子》生死观的根据是“气变”,客观结果是“物化”;据此而得出的主观结论是齐生死,齐万物与人;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超越生死、看破生死,不再执著于生死。
除了上面已经提过的“物化”“气变”之外,《庄子》的生死观中还存在其他内容。从逻辑上讲,取消了生与死的价值的不等价,取消了人与他物或万物之间的不等价,剩下的等价就能够使我们看破生死吗?价值的逝去难道不会造就一片虚无吗?从文本来看,《庄子》中的生死观也确实不止于此。除了把生与死、人与万物之间的价值等价之外,《庄子》某种程度上在这种拉平的范围内又重新建立起去面对“物化”的勇气,使人乐于去“化”去“变”。而这种勇于、乐于去“变”去“化”的东西正是变中之不变、化中之不化。这个不变不化,就是——“我”。
二、不灭的“我”——立的阶段
不灭的“我”是《庄子》生死观中对“物化”的进一步深入,《庄子》对这方面的论述并不直接、明显且涉及不多。虽然不多,但在以下的文字中,我们仍能强烈地体验到《庄子》为这个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的“物化”所注入的永恒的主体:
《田子方》:“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1]378又说:“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1]381
《德充符》:“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104
《大宗师》:“假于异物,托于同体。”[1]148
《刻意》:“圣人……其神纯粹,其魂不罢。”[1]292-293
《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1]407
…………
从“不忘者”“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守其宗”“托于同体”“其魂不罢”“一不化”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强调在变化不息的“物化”之中存在一定的不变或永恒。但是这个永恒到底是什么?其具体的规定却似乎很难由现存的这些文献中得出。依据《庄子注疏》中郭象与成玄英对这几句的解释,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永恒的东西,即是一个主体——“我”,即使在《庄子》那句“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中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观点。郭象注“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时说:“不亡者存,谓继之以日新也。虽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1]378可见这个不变的东西正是——“吾”。
那么这个“我”是如何能够看破生死的呢?笔者认为,虽然在“物化”之中,形体发生了变化,甚至是根本的改变,但是无论变作什么,都有一个主体,即“我”。纵然这个“我”与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之间不能保持任何记忆上的连续性。正如郭象所言:“所贵者我也,而我与变俱,故无失也。”[1]381也就是说,每一个生物它都是具有自我肯定性的,如《大宗师》中说:“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1]152换言之,无论“物化”为什么生物,都可以自得其乐,每一生物都有其自我持存的本性。所以,万物都具有一个“我”,即使它的形态和记忆都发生了彻底的洗牌。这个“我”不是一个小我,即个体的我;也不是一个大我,即集体的我。“我”既指每一个个体,指“万化”当中的每一个个体,也指每一个体中所体现着的个我,即每个个我对自己个体或类的肯定。所以“我”是小我中的大我,大我中的小我,集二者为一体。或者换种方式也可以说,《庄子》的“我”重在形式上,即每一“我”所具有的自我持存的规定性上,而非某一具体的内容的“我”之上。
在这一观点上,《庄子》的观点与世俗的生死观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世俗的恋生是因为“我”,《庄子》认为生死并没有使我们失去什么,也是因为每一物化都有一个“我”。换言之,他们认为人生的可贵之处都在于“我”。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世俗的恋生只在乎此生此世的“我”,是一个“小我”,而《庄子》的“我”既是个体的“小我”,又是每一物化后的“我”,是一个“大我”。这一“大我”正是对物化恒转不定之虚无感的克服。
《庄子》不灭的“我”的观点在《齐物论》的庄周梦蝶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庄周在梦中有一个蝶“我”,却感受不到庄周“我”;当他醒来时,感受到一个庄周“我”,却感受不到一个蝶“我”,虽然记得自己在梦中为蝶“我”,但无法再重复那种置身于蝶中的“我”了。但是,无论是蝶是庄周,都有一个“我”,庄子似乎由此悟出“我”既不依赖于蝶也不依赖于庄周,同时“我”既在于蝶又在于庄周。在这一点上,生与死是一致的。①生死转化都将有一个“我”,俗世之人乐生恶死,只知道此生之“我”,而不知来生亦有“我”,万化皆有“我”,虽非一“我”,然“我”不息也。在这个“我”中,笔者以为《庄子》似乎看出了每一个“我”都具有自我肯定性,既然此生的你肯定今生,你又何必担心物化之后的你不会肯定那时的一生呢?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说:“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1]152正是这种化为一物则肯定“我”之所在之物的特点,在《庄子》看来是看破生死必然性及形体之不相续性的突破点。
对于这种具有不连续性的“我”,而又永远不会消失的“我”,《庄子》用了两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个即《养生主》中的“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1]70“指”和“薪”是“火”得以燃烧的载体,但火可以脱离载体而存在,在其他不同的载体上重新燃起,虽然重新燃起的不是原来的“火”。这与生死转化的情况是一致的,形体虽异,但万化皆有“我”,而“我”无穷,亦犹火之“不知其尽也”。第二个即《寓言》中“罔两问于影”[1]500的故事。在这一部分想要说明影不待于火、日,犹蛇可以脱离蜕而存在,蜩可以脱离甲而存在。这个意思正如世俗之人以为有“我”必有此生此身,而不知“我”不待于此生此身。
通过这个在物化之中具有永恒性的“我”的自我肯定,使《庄子》在拉平了生与死的价值的区别、我与他物之间价值的区别之后,又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陷入此生此世因这种万化而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坠入自我否定与消极悲观的情绪中去。可是现在还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看破生死必须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即对拉平生死价值区别的认识,对不变的“我”的认识,那么请问:是否能认识的才算看破生死,而不能认识的便不能看破生死?既然物化中的每一个“我”都不具有记忆上的连续性,那么如何确保下一次的“化”后之“我”也能够认识并看破生死或者起码有要去看破生死的想法呢?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庄子》中找到了其生死观的另一重要命题——“人故无情”。
三、“人故无情”——持的阶段
《庄子》生死观中的“人故无情”是对“物化”和不灭的“我”看破生死后所得到的主观境界的保持。如果说“物化”重在对世俗生死观的“破”,那么不灭的“我”则是重在建“立”庄子自己积极的生死观,而“人故无情”则是对“破”与“立”所得到成果的保持,我们可以称之为“持”的阶段。
庄子与惠子有一段著名的“人故无情”的对话。在《德充符》中,庄子主张“人故无情”,而“道”和“天”只授“与”人以“貌”和“形”,并没有使人“以好恶内伤其身”。[1]121-122在《田子方》中,老聃给孔子讲了一些“死生终始将为昼夜”和“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1]381的道理后,孔子感慨说,老聃这么厉害的人物都需要“假至言以修心”,[1]381那么“古之君子,孰能脱焉”。[1]381孔子这里的问题,可以放入我们刚才的问题来理解,即如何使学到的《庄子》思想在下一次转化中也能得到保持?老聃的回答是:“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1]381成玄英解释道:“汋,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润,非由修学。至人玄德,其义亦然……夫何修为?自然而已矣!”[1]381也就是说,水的本性是清澈的,只要保持住,其实并不需要外加修炼就能做到。正是基于这种“本性”清净的思想,庄子才会认为“人故无情”。
也就是说,人本性是好的,当然,这种好指的是:没有多余的是非、好恶之心,这些好恶、是非之心正是庄子所谓的“情”。如果不受到污染,根本不用去看破生死,甚至连要看破生死的意向也不具备。正是这种“人故无情”的观点,《养生主》中秦失才会批判那些哭老聃的人,倒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解释的,这些人的哭是假的、“虚伪”的,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人故无情”的本性。这与“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而不哭,而民不非也”[1]285-286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庄子》看来,真正能看破生死的人连想看破生死的念头也没有。《赓桑楚》中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是三者虽异,公族也。”[1]424-425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出,“未始有物”的最高境界是看不出生与死的区分,将之合二为一。所以生死在某种意义上或最高境界上而言是不可说的。这种“不可说”的原因并不是说要靠直觉去悟而非用理智去理解,而是因为一说(这个“说”也包括“想”)则有“分”,分则不再是“一”,但又不能不说,所以《庄子》认为可以说到“三”。至于为什么只能说到“三”,这涉及《庄子》的是非观,兹不赘述。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在《庄子》看来,本性纯洁的人并无必要去看破生死,因为纯洁的本性对生死并没有作是非、好恶式的区分。但是面对已经沉沦的世俗,《庄子》又不得不说,所以它只好说到“三”,但这一“三”毕竟还是与“一”具有本质的联系的,所谓“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1]45亦如以上引文所言:“是三者虽异,公族也。”[1]425
总而言之,《庄子》认为,人本来就没有是非、好恶之情,每一次“物化”之后的“我”如果不受后天的污染,那么他便不需要获得那些看破生死的认识,所以也不会去区分生死的价值。只有对于已经区分生死的不同的价值的社会,只有靠对生死“真相”的理解和认识才能做到看破生死,对上古那些纯朴之世或人来说则不需要;而每一次“化”的“我”从开始或生命的起点来说,都是“混沌”的,不需要去看破生死的,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住这份纯洁。
四、总结
根据文章的论述,我们可知:首先,庄子将生与死、我与万物在世俗那里不平等的价值放到“物化”中去拉平,使它们等价。甚至可以说,这种等价使今生今世变得渺小化。其次,紧跟着渺小化的则是在不确定的、存在各种可能性的“物化”中注入一个确定的永恒的“我”,而这个“我”使今生今世变得具有可忍受性,甚至带有可欢可乐的性质。最后,为了保证前两方面,即对生死的渺小化与万化有“我”的可贵性认识,《庄子》认为“人故无情”,认为纯真人并不需要多加反思,便能以自然的心态顺应“物化”。也就是说,前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对那些看不破生死的人或社会说教用的,这种说教并不需要在下一次“化”中得到延续才能使“万化”中的每一个“我”都能看破生死。
综上所述,保证《庄子》看破生死的其实有三样法宝:即生死、物我价值的平等化,这是“破”的阶段;万化有我而使万生万死变得可以忍受,即万化有我的可贵性,这是“立”的阶段;以及最后“人故无情”对前二者的保证,即人的本性并不需要通过后天的认识来看破生死,这是“持”的阶段。此三者所构成的是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有机整体。如果只有“物化”,而没有不灭的“我”,则人生终将陷入无法自救的必然性的虚无中去,而“人故无情”则使生死实现忘的境界,不需要通过后天学习来获得。所以,《庄子》生死观最终可以归结为“破、立、持”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注释:
①庄周梦蝶这段文字中刚好有“物化”二字,而这一术语在《庄子》中是与生死相关的。
参考文献:
[1]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涂光杜.庄子范畴心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77.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9.
(责任编辑吴月芽)
Breaking,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Syllogism” of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WANG Kun,SHAO Linfan
(CollegeofLawandPoliticalScienc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studies Zhuangzi as an organic whole, and argues that there is the connotation of “breaking,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syllogism in 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t the “breaking”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destroys the secular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t the “establishing” stage, the imperishable “I” is used to create a positive view of survival. At the “sustaining” stage, the elaborations of “people having no feeling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keep people away from holding such ideas like being right and wrong, likes and dislikes about life and death. The three stages are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coherent, constituting a uniqu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Zhuangzi; view of life and death;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I; no feelings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2-0033-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论现代新儒家对怀特海哲学的绍述和融合”(12YJC720035)
作者简介:王锟(1973-),男,甘肃天水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史学博士;邵林凡(1987-),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