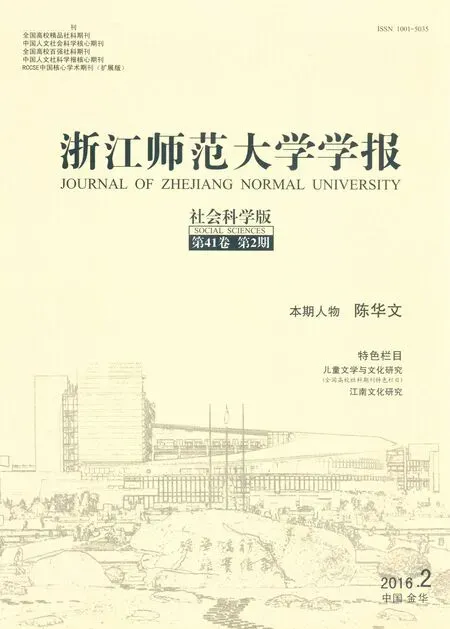口碑、牌子与品牌: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化问题
耿 波, 史圣洁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口碑、牌子与品牌: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化问题
耿波,史圣洁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民国时期北京非遗的“口碑”现象明显,“口碑”体现了人们在对非遗之谈论性交际中产生的地方认同。建国后公私合营运动破坏了非遗“买卖”的交际性,人们获得非遗产品的方式是经济配送,经济配送使人们对非遗产品无所谈论,因而失去了地方认同,“口碑”变成了“牌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非遗产业转向非公有制经济,非遗消费指向满足人们的独特体验,非遗品牌化的实质是对人们获取消费独特性的满足,品牌化的非遗使人们产生的是虚假的地方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建设的目的,应是实现地方认同与形成产品标识的同行并进,现代产业发展的递深反回逻辑,为此目的的实现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递深反回的结果,必然是超越非遗产业化的野蛮牟利性,向非遗产业的交际性、公共性回归;在递深反回逻辑中呈现的非遗品牌,是人们实现地方认同、对抗现代资本冲击的文化界碑。
关键词:差异的聚合;地方认同;品牌化;公共性
品牌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核心要素。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之路,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建国前主要是作坊(班子)式经营;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产品经营基本上是国家经济集权下的产品配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公司制)成为非物质文化产业处身其中的基本格局,市场自由为非遗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同时也带来极大挑战。在产业大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标识正被逐渐抹去,成为通常意义上的消费符号。非遗产业品牌化并非简单的产业问题,品牌包含“产品标识”与“文化标识”的双重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建设的实质,是不同群体的“文化身份”在产业发展中实现文化再生产、形成产品标识的品牌化过程。
一、作为“口碑”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将“品牌”视为包含“产品标识”与“文化标识”双重内涵的意义上,探讨当前北京非遗产业的品牌问题,应先对其“口碑”现象进行讨论。所谓“口碑”,即是大众对某物的趋同性评价。与通常意义上的“评价”类似,“口碑”也表现了公众意见,但与情境性明显的“评价”不同,“口碑”体现出鲜明的地方认同。首先,“口碑”行为中地方认同的发生来自于其展开的无所指向性。“口碑”总是发生于人们的闲谈中,这是考察“口碑”现象的基础。在泛泛的闲聊中,人与人之间的欲求充分凸显,形成了丰富的言谈上的差异性。其次,“口碑”展开的无所指向、非功利性使闲谈中呈现的差异并行不悖、求同存异。在有所指向的功利性场合中,言谈间的差异必将是对立的,但在闲谈中,“差异”之间相安无事。再次,“口碑”展开中相安无事的“差异”分而不离,形成了“差异的聚合”,在此“差异的聚合”中“整体”体验得以发生,人们也获得了栖居于整体中的地方性认同。最后,“口碑”中由“差异的聚合”而产生的地方性认同根本上乃是“趋向”,这种“趋向”只有获得现实空间载体时才能真正“落地”,由“趋向”成为“现实”。在古典社会中,口碑的“落地”之处,作为人与人相互遭遇的“位置”,常常是促使人与人之间发生言谈“差异”的地点。
北京非遗产业的“口碑”现象集中发生于民国时期的“老北京”,建国后日渐消失,此一变迁,乃是北京城市产业结构发生巨变从而导致非遗产业属性变化的结果。
在“老北京”,今日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根本上是个体赖以“谋生”的手段。近现代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城市。自元代以来,虽然北京的城市集权日益强化,但城市本身的休闲、消费性却是有增无减。元、明两代及清代初、中叶,京杭大运河为庞大的城市消费发挥了强大的支撑作用。沿着运河,中国南方物品被运送到北方。从通州到积水潭,运河槽船经过的区域成为元、明两代及清初、中叶商业贸易的“黄金河岸”。运河之外,北京周边省份,尤其是山西、山东、河北等也因北京消费高原区的贸易往来成为北京商贸网络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传统北京的基本产业结构是以消费休闲产业为主的产业模式。但到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运河漕运在1853年、1855年两次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及黄河改道最终停摆,这使得北京消费物资来源的渠道被切断。
1928年前,国民政府仍在北平的时候,北京的商业贸易繁荣主要得益于“首都”号召力,山西、山东、河北等地的消费资源仍能源源涌入,北京产业结构仍能维持基本稳定。但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后,北平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国民政府南迁,皇室贵族及其他社会名流随之散去,这使北平具有高等消费能力群体锐减,在这种状况下,晋、鲁、冀等大的商业贸易不再留恋于此,最终使北京城里只剩下大量只有低等消费能力的人群。1928年7月的《大公报》感叹:“从此北平城内,大有伯乐一过,冀北空群之慨。”陶孟和也在《北平生活费分析》的调查报告中说:“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坏之区域矣。此次所调查之家庭,多聚居于两中心点,一为外城花市之四周;一为内城东城墙附近一带。内城贫民,介于富户住区与城墙之间,如富户区域继续扩张,则彼等必被迫而迁居于城厢也。”[1]低等消费能力的人群,从其所能适应的产业供给来说,也对应着低等产出结构。
因此,1928年的国民政府南迁,其实是为北京本地的低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些低端产业的特点是投入小、手工性、流动性较强,适应平民大众的需求,而这些低端产业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形式。在传统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所有的种类都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但在北平迁都后所造成的巨大物质贫困中,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从作为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谋生”手段的需要。当时的北平,城市的振兴也需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产业契机。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云游客)在《江湖丛谈》中曾对此有这样的评论:“不怕某处是个极冷静的地方,素日没有人到的,只要将江湖中生意人约去,在那个冷静地方敲打锣鼓表演艺术,管保几天的工夫就能热闹起来。如若得罪了他们,或是由空地净盖房,盖来盖去将生意人挤走啦,管保不多日子,那个繁华热闹所在立刻就受影响,游人日稀,各种的买卖就没人照顾,日久就变成个大大的垃圾堆。江湖艺人有兴隆地面的力量,有吸引游人的力量,有繁华地方的力量。”[2]这些“江湖卖艺”的内容大部分是当代北京非遗名录的内容,这些“江湖卖艺”之所以会在当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民国北京城特殊的产业结构。
在传统北京特殊的产业结构,即物质贫乏、低端化消费占主流的格局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地成为了“谋生”手段,而不再是抽象的“传统”。这就造成了在民国北京社会中,通过消费(买卖)关系,非遗成为了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联接,非遗以“活”的形式联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因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功利诉求上,吹毛求疵、睚眦必争,“差异”缤纷,“聚合”罕见,因此,由“买卖”关系而形成的“差异”需要实现“聚合”还需要特别的契机。
这种契机来自于传统北京所形成的独特空间结构。在民国,北平的休闲消费网络主要由以下几类交织而成:一是固定日期开放的庙会;二是新旧式综合商场;三是皇家名胜蜕变的公共休憩景点;四是中、西式消遣游乐场所;五是流动性的街巷摊贩。[3]111在五大类消费空间中,其中尤以庙会、新旧综合式市场影响最大,而流动性的街巷摊贩则是群体最庞大,影响市民最深切者,前门外的天桥可说是流动摊贩集中聚集的地方。在民国北平的消费空间分布中,庙会的聚集性意义特别值得关注。台湾学者许慧琦曾对北平消费空间的分布做过详细考察,她指出:“就北平城内的公安分区而言,庙会主要分布在内二、外二与内五、外五区……恰好将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及天桥市场形成的商业金三角地带,包覆在其中。”[3]129并引王宜昌的阐解说:“在此三角形区域中,无任何庙会之存在……在此区域之外,则为城内边隅之区,隙地既多,市廛盖寡。而中下等人家,则多群居是等地带,其日用所需,须有市集为之供给,其低下智识,每藉宗教为之慰安,故有庙市香火存在之必要。”[3]130这两段话说明了庙会在老北京休闲消费空间中形成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大略将民国北京的休闲消费空间单元分解为两部分:即庙会等神圣场所,以及由庙会而团聚起来的消费商贸区,而后者就是非遗“谋生”展开的场所。
但这个描述还不全面,其实由上述从庙会到消费商贸区的逻辑,再扩展开去,就是在消费商贸区的边缘或者间隙存在着专门的“谈论”区,比如茶馆等。这些“谈论”区正是京城“闲人”们互动的场所。以民国时天桥为例,当时天桥人群的第一个层次是城市市民阶层。天桥虽然长期处于北京外城,但因为内城严格的规划格局,浓厚的皇权气氛,一直以来对于市民的自由集会和交往有所限禁。明代时期,内城尚可以在积水潭湖畔、鼓楼地区自由买卖和娱乐,但在清初,朝廷颁布了“内城逼近城阙,例禁喧哗”的禁令,不准在内城设立会馆、戏院、妓院,于是这些体现着市民情趣的活动多设在了外城,其中以天桥地区最为集中。加之天桥发达的贸易活动,在内城被重重限制的市民阶层自然对天桥充满了希望,纷至沓来,构成了天桥广场数量巨大、成分复杂的市民层次。第二层次比较特殊,也至关重要,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城市闲人”。所谓“城市闲人”就是城市社会中的有闲阶级,他们经济上相对宽余,同时又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对于对象能够抱着超越现实的眼光去审视,他们在有目的的从事生活与无目的的欣赏生活的意义上构成了与城市市民的区别。自元代至民国,旧北京天桥广场上的“城市闲人”基本上有三种人群组成,即文人、游客以及清末民初没落的八旗子弟。
对于天桥广场的“买卖”活动而言,如果说城市市民阶层提供了基本的观众群体的话,那么,“城市闲人”的意义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谈论”区,“城市闲人”借助听戏听书,畅所欲言,谈论的仍然是刚才“买卖”的事,但因为是“闲谈”,自然祛除了其中的功利性竞争,而是对共同所经历“买卖”事件的“谈论”从而“说到一块去”。在“谈论”空间中进行的“谈论”,实现了将非遗活动中因“差异”而“聚合”的功能,在“差异的聚合”中,地方认同油然而生。在“谈论”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围绕非遗“买卖”展开的“谈论”,自然有所扬抑褒贬,其中所扬所褒者就是某非遗的“口碑”。因此,发生在“谈论”空间的“口碑”不单纯是对某“买卖”的评价,而是人与人之间围绕非遗“买卖”所发生的“差异的聚合”中自然溢出的“谈论”。这种“谈论”启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性,使人产生了地方认同,如同一块碑石一样,让人凭此而标出自己的“家园”。
二、作为“牌子”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北京”特殊的产业结构(低端消费)与独特的空间结构(“谈论”空间)的存在,使得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碑”出现,成为人们实现地方认同的家园界石。随着时代演进,北京非遗“口碑”的演化也正来自于作为前提的这两大要件的变化。
首先,建国后北京公私合营运动使非遗产业产权发生改变,从而改变了非遗的社会属性。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12月21日,北京召开了全市工商业联合会会员大会,传达了过渡时期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北京的公私合营运动从此开始。
建国初的公私合营运动对传统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异常巨大,其效应犹如工商业领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削弱并最终剥夺了传统工商业的私人所有权,确立了国家在工商贸易中的产权主导地位。传统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卖”,在根本上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产权的基础之上。非遗产权的私人化,使得人们与非遗的“遭遇”既是“买卖”关系同时又是“交际”关系,正是这种富有人情味的“买卖”关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唤起了人们“谈论”它的兴致,通过“谈论”,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差异的聚合”,“口碑”得以形成。
但公私合营改变了非遗产权,也取消了非遗“买卖”之社会“交际”性,这体现在:
第一,公私合营取消了非遗传承中的“角儿”,消解了非遗“买卖”的人格象征。在民国北京的非遗“买卖”中,那些身怀绝技、认同感高、影响力大的人通常被称为这个行业的“角儿”。他们往往掌握着这项非遗“买卖”的要诀,因此,能力既高,收入也高,有的行业中“角儿”的收入甚至高出本行业中最低收入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建国后公私合营的经济改造首先要改造的就是这些人。1958年10月由提交申请并获北京市政府同月批准的《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关于进一步改造民间职业剧团、零散艺人以及公私合营和私营文化企业的请示报告》就很能说明这个导向,在该“请示”中写道:“剧团内部的分配制度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主要演员的高额薪金还普遍存在(有的每月高达3 000元)。剧团的民主管理制度也未树立起来,多数剧团还是主要演员说了算,个别剧团甚至还是旧班主的经营管理方法。”[4]公私合营中这种通过推行体现经济平等的“工资加奖励”制度,以此来限制“角儿”的收入的方法,看似进步,其实对非遗传承的影响是负面的。因为,这些“角儿”以自己的高超技能、经营能力及行业操守在成为这个行业中“焦点”人物的同时,也使这个行业本身人格化了,而他们的高收入本质上乃是一种行业荣誉,他们的收入越高越增加了这个行业的荣誉度。因“角儿”而人格化了的非遗“买卖”,带给人们的是一种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交际”感,这种“交际”感正是非遗“买卖”之“口碑”展开的基础。
第二,公私合营改造了非遗传承中的师徒制,消解了非遗“买卖”的家庭象征。建国后的公私合营中,对传统非遗“买卖”做重点改动的就是非遗传承中的师徒制。在民国北京的非遗传承中,师徒制是主要形式。在当时的各个行业中,师徒授受的制度不仅广泛而且严格。在当时,师徒即父子,甚至比父子关系还要严肃。这种师徒如父子的关系限定,在技艺传承上当然有利有弊,但在以此来缔造社会关系方面却是非常重要的。师徒如父子使得师徒两人搭班的行业具有“家庭”的象征意义,非遗“买卖”因这种“家庭”象征而抹除了它的功利性,变成了“串门”,因此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自然丰富多彩,人情味十足。但公私合营对此做了改变。当时规定:“学徒期限为三年,学徒在学习期间的生活补贴,按照管伙食另加少量零用钱为标准,学徒在学习期满,考试及格转为正式工人、职员以后,第一年的工资待遇执行所在单位工人、职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这个框架内,徒弟的收入与考评完全交由企业本身来管理,师徒间的关系已失去了“父子”的象征意义,因此,行业之“家”的象征意义也被抹去了。而这对于“买卖”关系转换成的“人际”关系无疑是极大障碍。
第三,公私合营取消了小商小贩,削弱了非遗锲入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活力。在北京非遗行业中,游商摊贩的意义不可小觑。他们所推销的产品虽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他们无孔不入,游走在大街小巷,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游商摊贩的利润非常微薄,它们的存在意义很明显不在于产业层面,而在于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锲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振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游商摊贩在许多描写“老北京”的作品中出现过,它带给了人们美好的家园记忆,原因也正于此。在北京非遗行业的公私合营中,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政府把小商小贩分门别类地安排在大棚里营业,使他们彻底丧失了主动锲入市民生活世界、振动日常交际关系的契机。
其次,公私合营时代北京城市空间的改变使人们失去了可进行“谈论”的“地方”。如前所述,传统北京的城市空间,以庙会空间为中心形成了完整的单元空间,依次为庙祠形成的神圣空间、围绕庙祠形成的庙会非遗“买卖”空间及作为最外缘的“闲谈”空间。“闲谈”空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口碑”的形成至关重要。建国后的公私合营取消了非遗产权的私人化,从而使人们对非遗“买卖”的“交际”体验被遏制,造成了人们对非遗“买卖”是“谈”无可谈。不仅如此,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城中的“闲谈”空间逐渐被扫荡干净,使得人们即使有的可“谈”,也无处可“谈”。
建国初北京的城改运动,根本方针就是“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在此方针指导下所呈现出的北京城市空间与民国的北平城市空间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建国后的北京城市空间体系变成了“控制严格、滴水不漏”的密网城市。这个密网城市通过“一个中心,两条轴线,三圈环路,四方周正”的严格把控,使北京城的一切空间都被整合到极其严格的空间集权中去。在这个密网城市中,与集权借助空间实现的控制相配合,公私合营的经济改革很有效地对城市内相对自由的产业行为进行了取缔和荡平,通过将非遗“买卖”的产权转变为公有,将大批摊贩纳入大棚统一管理,这一切都为政治集权做了很好的配合,从而使建国初北京城的集权空间顺利地夯定下来。
在这样的密网空间中,原先填充在城市空间间隙中,以“庙会”为中心的单元空间已无可避免地被挤压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庙会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期,在经济上成为一种对国营商业的补充手段。然而随着东四人民市场等摊商集中管理的商业企业的兴起和公私合营的深入,众多商贩脱离了庙会经济形态。十年“文革”彻底断送了传统庙会一脉香火,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庙会香市急剧衰落,传统庙会不仅寥若晨星,而且鱼龙混杂、形式古怪,有些甚至沦为市场经济的产品倾销地。
在建国后的北京密网空间中,庙会空间的丧失不仅造成了非遗“买卖”的断根,而且使原先附饰在庙会单元空间结构中的“谈论”空间也逐渐销声匿迹。没有了人们在非遗“买卖”中鲜活的交际性“差异”体验,没有了将此“差异”实现“聚合”的“谈论”空间。人们获得非遗产品的形式是国家经济集权的配送,在这样的配送中,人与人获得了平等同质的经济待遇,因为没有“差别”所以没有什么可“谈”,即使有所“谈”,也是个人向管理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人们失去了“谈论”的对象和空间,相顾无言,“口碑”消失,在建国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在表达对一个商品的夸誉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牌子货”!
三、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
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持续至1966年左右,随后是十年“文革”,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本断绝。“文革”结束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逐渐转向强化以经济建设为主。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非公有制经济构成了非遗产业处身其中的基本格局,非遗产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属性使其转向了品牌化。
在传统北京,非遗“买卖”对人与人之间“交际”关系的缔结取决于一个前提,即在非遗“买卖”中,非遗产品是作为生活必需品而呈现的;在非遗产品是“生活必需品”的意义上,这种产品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并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占据突出问题,因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在于“有用”,所以它的存在感会随着其使用价值的消失而日渐磨损,而它的磨损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获得了共在的完整结构;这种共在的“完整性”潜藏在人们共同对产品的使用中,并将在“谈论”中显现出自己的形式,即“差异的聚合”的整体性,并由此产生地方认同。
然而,“非公有制”经济格局中的非遗“买卖”却正是在此前提上出现了差别。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典型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在公司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经济活动的主要问题,在于强化对自己产品“独特性”的保护而并不是它的“有用性”,因为这是其与“公法体系”绾合的必然要求。当人们在产品制造商的鼓吹下,确信自己是在消费一个有着“独特性”的商品时,对“独特性”的占有,将使他忽视或拒绝他人对这种“独特性”的共享,而这必将导致人们在这样的产品消费中相互疏远,使人们认为他人对于自己的意义,仅仅在于是自己对占有“独特”商品的炫耀对象而已。
在公司制的经济格局中,非遗产品变成了拥有“独特”性的幻象,人与人之间既疏离又因共同的孤独而杂凑在一起。在公司制的经济格局中,非遗“买卖”所凸显的不再是其建构整体性的“口碑”性,而是强调其“独特性”的“品牌”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北京非遗“买卖”之“品牌化”的大行其道,乃是其脱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性”,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而成为人们猎获“独特性”体验的载体。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北京,我们可以发现,公司制经济体制中这种通过非遗“买卖”所缔造的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关系,正符合此时北京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即北京逐渐变成了一个众多“游逛者”在此猎奇“独特”体验的城市。
1994年左右,在北京“城内”,外来人口突然激增,使北京的“游逛”人群与“游逛”行为空前繁盛。1984年北京外来人口只有84万,1992年达到150万,1993年8月底达到155万,而1994年激增到329.5万,其中在北京暂住3天以上的有115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市外来流动人口已达308.4万人,尽管与上海市的387.1万人相比,少78.7万人,但较1997年的229.9万人,增加78.5万人,增长34.1%。[5]外来劳务人员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京城新兴“游逛者”人群的一部分,更具“游逛”特征的城市人群则是数量更为庞大的来京旅游人群。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来京旅游人群的旅游行为的变化,使其本身从“朝圣者”变成了“游逛者”。于“游逛者”群体而言,北京成为了猎取“独特”性的地方,北京本土“非遗”成了人们获取“独特”体验的绝佳载体。在北京非遗商品成为人们想象“老北京”的载体以此获取“独特”体验的时候,它的所谓“独特”性就构成了它的“品牌”性。“品牌”是公司制体制中经济行为为凸显自我之独特而建构起的幻象。在这样的幻象中,人们借助非遗“买卖”而“独赏”,相互隔膜但相互需要,他们因为炫耀而需要对方。这样的非遗“品牌”因为切断了人与人之间通过“交际”而呈现“差异”的可能性,于是“差异的聚合”不可能,在“差异的聚合”之“整体性”中“能栖居”也不可能,地方认同则更不可能发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非遗活动倾向于消解自身扎根于“真实”地方的诉求,而热衷于在那些“游荡”的空间中幻生所谓的存在意义,这种“游荡”的空间在当时的北京城市层层产生,为其所用。
因此,新时期以来北京城市产业结构的改变促生了北京非遗的品牌化,而非遗的品牌化,其本身作为满足人们猎奇性的象征符号而存在,还与北京城市空间在这一时期的变迁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的城市空间集权就一直在强化。城市空间的集权强化必然地产生了“逃避”,空间“逃避”的重要策略是“游荡”空间的产生。当代北京城市中的“游荡”空间丰富多样,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先锋艺术所拓出的多样空间,“798”“宋庄”都是其中典型的“游荡”空间。相比而言,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当代北京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兴同样也产生了丰富的“游荡”空间。最典型的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复兴的传统“小剧场”。1996年,相声名家李金斗提出了“相声回归剧场”的想法,但相声回归剧场的真正实现是在新世纪,2001年9月,中国广播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与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等公司联袂在民族宫大剧院连演五场《相声欣赏晚会》,场场观众爆棚,这是回归剧场的开始。这些“小剧场”或“新剧场”在本质上就是典型的“游荡”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对出现的那些“老玩意儿”鼓掌、欢呼,甚至尖叫,这种热情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些“老玩意儿”有多欣赏,他们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现实社会中遭到压抑,他们在此要发泄出来,并将这种“发泄”表演化、炫耀化,在这种炫耀的相互观摩中,达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实质并非是凸显各自“差异”性体验的“交际”,恰恰相反,人们在各自的“孤独作乐”与“相互孤独”中被统一抹平了;在共同被抹平的遭遇中,人们以相当奇观的方式“共存”,他们因此而获得了意义感和存在感。但这样围绕非遗体验所发生的“共在”意义只是缺乏地方认同的幻象而已。
这种滋生着丰富幻象的非遗之“游荡”空间,除了使人们得到暂时的宣泄与抚慰之外,在现实中到底留下了什么?于非遗本身而言什么都没留下,于人们借助非遗而实现地方认同而言无从谈起,真正从中获得巨大回报的是拢摄整个城市的资本势力,他们将这种“游荡”地方中的幻象转化为可消费的“资源”,并通过产权法体系使之成为了“品牌”;还有城市中的政治集权集团,对他们而言,这些满足于幻象,不再对真正的“地方”感兴趣的人群正是其实现稳固集权的最佳人选。
四、资本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建设内涵
资本时代,非遗商品品牌化所产生的“独特”幻象,使得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交际”性体验,人与人沉浸于对非遗商品之“独特”体验中,等到无“差异”,就没有了“差异的聚合”之“整体”性,也没有了由“整体性”而产生的地方认同。因此,如何由非遗产业化而重获地方认同成为资本时代非遗保护的根本问题。从非遗产业的“品牌”打造角度而言,非遗“品牌”的产业经营如何建构人们的地方认同便成了核心问题。
如何由非遗产业化而重获地方认同?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对现代产业的社会属性进行辨析后得以解答。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曾检讨19世纪以来的市场自由主义,他指出,因为现代产业对唯一经济属性追求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必然地激起人们对传统社会组织保护和建构现代社会组织的热情。这是令人感到乐观,同时又是异常深刻的结论。这一结论对非遗产业化的启示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非遗产业化的发展趋向必然是对非遗社会组织的普遍唤醒。
按照波兰尼对现代产业双向运动的分析,非遗产业化本身包含着一个递深反向的逻辑。在非遗产业化初期,产业自身追逐利润的冲动必然裹挟着非遗前进,比如对非遗资源的野蛮开发与买卖,如此等等,这其实形成了当前非遗保护的典型景观。针对这样的现状,有人指责,却缺乏理性的预见。事实上,非遗产业化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向运动,即通过产业化的激发而产生围绕非遗进行社会关系的建构。我们看到,由产业化激发的社会建构之反向运动使得非遗产业化本身具有了“公共性”特征。非遗产业的“公共性”涵义在于:非遗产品成为了公共物品,但这种“公共物品”并非指消费的共享性,而是指非遗产品开放了人们对其参与的广度,人们经由产业框架获得非遗产品,但将对其是否是“真”展开平等的讨论。西班牙学者比尼亚斯在《当代保护理论》中对此有这样的论述:“遗产应该属于我们,但不是我,不是我们中的某些人。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方式利用遗产,但此处的我们不仅仅是拥有权力的少数决策者或自己,而是指一个更大的群体的人群。事实上,从原初位置去除祭坛,从墓地走向遗体、用电灯照亮雕塑等严重改变原有模式的更动都是社会广泛接受的决策……(遗产)保护中的主体互涉模式可被视为主体共识的结果,保护对象对这些主体具有意义。而且保护的责任也落在这些受影响的人群(affected people)或其代表身上,他们有保护或修复保护对象的责任,保护也应当以他们为主导。”[6]比尼亚斯的这段话凸显了围绕“保护”而建构起的“我们”的共在感与社会感,是对所谓“原真”性保护或追求“客观”性保护观念的一种超越,是将当代社会的遗产保护的上升到了当代公共性建构的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保护,在其唤起各方参与、相互协商的意义上,是典型的公共性行为。
非遗产业化递深反回的结果,必然是超越非遗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向古典时代非遗之“交际”性的回归。这种“公共性”交际关系呈现一种“差异的聚合”的“整体性”,在此“整体性”的“能栖居”的意义上,人们倾向于地方认同。而现实空间中“战斗的地方空间”的存在则使这种“地方性”认同得以落地、夯实,非遗地方认同得以真正实现。
以此视野来反省资本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建设的问题,则会有新的认识。
随着非遗产业的递深发展,非遗产业的“品牌”内涵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非遗产业的深化,即非遗产业的发展使其自身的败坏与局限得以呈现,因此导致了自身的反向社会化运动,让人们自觉地去开发非遗产业中的社会交往意义,即以非遗产业为载体而展开丰富交际活动。这样的非遗“交际”与古典时代的非遗“交际”有所不同,后者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社会交往,本身有古典伦理体系约束其“差异”而呈现“差异的聚合”;但在资本时代,非遗“交际”缺乏伦理体系之收束的前提,多样“差异”的“聚合”只能是诉诸公共性的“谈论”。
而关于非遗产品的公共性“谈论”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关于非遗产品的质量评价问题,这个层次的“谈论”往往因各自的使用体验不一而有分歧;另一个层面则是关于非遗产品之“真”与“假”的“谈论”,这种“谈论”往往掺杂在前一种“谈论”中,但因为“真”与“假”之“谈论”是超验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故关于非遗“真”与“假”的“谈论”会在谈论的“差异”中逐渐走向“聚合”,形成公共性层面上的“差异的聚合”。最终导向“差异的聚合”的非遗产品公共性“谈论”,就是资本时代非遗产业递深层面上的非遗“品牌”之内涵。作为公共性“谈论”的非遗产业“品牌”本身实现了“差异的聚集”之“整体性”,在“整体性”体验的意义上,这样的非遗产业“品牌”必然是倾向于地方认同的;在此意义上,非遗“品牌”成为一个区域中人与人之间实现公共性聚合,从而成为对抗资本冲击的界碑。
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非遗产业的“品牌”毕竟是经济软实力,如果非遗“品牌”的真正内涵是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共性聚合的话,那么这种“品牌”的经济效益如何评估呢?事实上,这种足以引起人与人之间公共性“谈论”的品牌公共性,正与当前最前沿的品牌观念、品牌生态位观相契合,既具有社会效益又具有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
[2]连阔如.江湖丛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3]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M].台北:学生书局,2008.
[4]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关于进一步改造民间职业剧团、零散艺人以及公私合营和私营文化企业的请示报告[J].北京党史,2006(5):45-46.
[5]张铁军.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知多少[J].北京统计,2002(6):21.
[6]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北京: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34-135.
(责任编辑傅新忠)
Reputation, Sign and Brand:a Survey on Brand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
GENG Bo,SHI Shengjie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24,China)
Abstract:In old Beij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reputation” was an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 “Reputation” indicated the “local identification” which generated from people’s social intercourse through talking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 the public-private movement broke the communicative fea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siness, as people acquired the products only through economic distribution and had little to talk about,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local identification” disappeared, and the “reputation” turned into “sign”. In the late 80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 shifted to the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at aimed at offering people unique experience. The essence of brand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s to satisfy people’s consuming uniqueness; howeve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randing” only offered illusive “local identific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im of brand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reach both “local identification” and “product identification”, and the recursive logic of modern industry has provided good opportunity. The outcom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cursive industrialization will definitely transcend the brutal profit-orientate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lead a return to its communicative feature and publicit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brought in recursive logic will be a cultural bounding monument to fight against the shock of modern capital.
Key words:aggregation of diversity; local identification; branding; publicity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2-0019-08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招标项目“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著名文化品牌研究”(HW12087)
作者简介:耿波(1976-),男,山东沂源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史圣洁(1990-),女,安徽颍上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1-27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