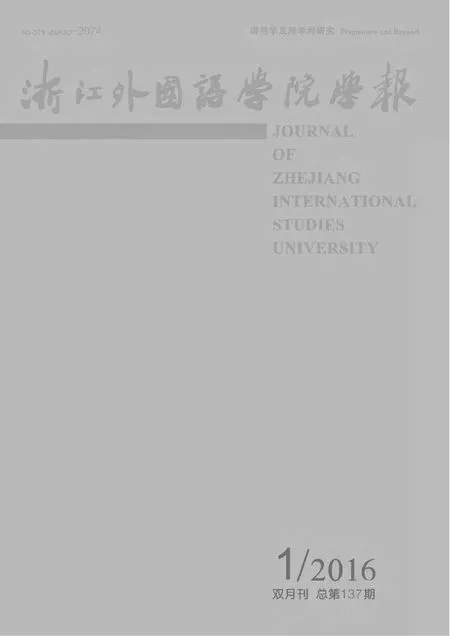街区·家宅·公园——E.L.多克托罗《纽约兄弟》对都市生存空间的书写
孟姜玲,朱荣华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街区·家宅·公园——E.L.多克托罗《纽约兄弟》对都市生存空间的书写
孟姜玲,朱荣华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E.L.多克托罗的《纽约兄弟》对纽约的都市生存空间进行想象与建构:街区的剧变折射出瞬息万变的都市面貌,反映了都市生活的疏离隔膜之感;兄弟俩家宅的变化与其命运息息相关,是现代文明对家庭的入侵与破坏的具体象征,但也是传统生活对现代生存空间的一种审视;中央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休憩、沉思和冥想的空间,象征着现代人精神荒漠中的绿洲。E.L.多克托罗在对科利尔兄弟故事的改写中聚焦于人们在现代化都市空间中的生存状态,作品展现了其对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生活的体察和反思。
都市生存空间;街区;家宅;公园
一、引言
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曾说:“长久以来,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因而,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了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1]45当代美国著名作家E.L.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2015)于2009年出版的《纽约兄弟》(Homer&Langley)①独辟蹊径,以眼盲弟弟霍默的口吻进行叙述,对纽约科利尔兄弟的怪诞故事进行改写,以此串联起20世纪美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并聚焦于复杂多变的都市生存空间中的个体生活,通过对都市变迁中小人物在日常空间中的活动过程加以细致的观察和描画,表达了对都市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生存环境快速变迁的关注与思考。多克托罗被称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汇集了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点和时间,表达了我们国家的多重声音。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幅生动的油画,充满缤纷的色彩和剧情。每部小说中,他都以编年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2]161。而在《纽约兄弟》中,多克托罗从纽约典型的街道、家宅、公园等方面对都市空间进行建构,这些空间不仅构成了现实生存空间的物质符号,也蕴含了沉淀于城市之中的精神文化因素。因此它们也担负着呈现现实生存面貌和记载社会变迁历史的功能。对这些空间及穿梭在空间中的个体状况的描刻,既能直观明了地展示都市发展给人们生存带来的影响,又能揭示都市中人们的灵魂所向和精神需求,避免落入城市书写“欲望”“物质”等刻板形象之中。
二、街区:都市善变的面孔
得益于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于纽约东卵(East Egg)优越的资产阶级和西卵(West Egg)野心勃勃暴发户的描绘,读者可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资本主义明珠城市中存在着的不同阶层。《纽约兄弟》中虽无特别的贫富地区差异对比的描写,只交代兄弟俩的家坐落在纽约繁华喧嚣的曼哈顿心脏地带,但多克托罗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街区的面貌随城市发展的历时性变化:“这个农场早就消失了,现在那地方成了兵工厂”[3]34,观察到都市公民在庞大的城市中显得异常孤零和落寞的精神状态:“这个现在离我如此遥远的城市,如此心浮气躁的城市,而我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长大。”[3]158都市较于其他地区,最明显的空间特点当是拥有更加庞大纵横也更具变化流动性的街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浸润和侵袭着纵横交错的街区,街道两旁宏伟的建筑物拔地而起,拆迁与重建此起彼伏,洋溢着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物不断地替代着原有的城市结构,冲刷着都市的面孔,使城市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不仅看似威严的建筑物时刻有被拆迁的可能,街区的业主或租赁者也更换了一批又一批,每日上演着谈判营销、破产吞并、改弦更张、阴谋策划的戏码。穿梭于纽约日益庞大的建筑群中,人们就愈加清晰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彷徨,街道上行人急促的步伐和日益快捷的交通工具加速城市节奏律动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
在小说中,当兄弟俩的父母被西班牙流感夺去性命而哥哥兰利还因战事下落不明之时,失明的霍默被推到一家之主的位置上,他需要穿越纽约大道,与律师事务所、家族银行、谷物交易所等城市机构打交道,他甚至在失明后戏谑地调侃道:“我很高兴可以不用再看到我家南面那些无良巨富令人羞愧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楼。”[3]21这些宏伟壮观的大楼既显示了现代文明的理性秩序与物质辉煌,又有着与人类诗意生存所不相容的冰冷和僵硬感。
小说中多克托罗让失明的霍默获得了听觉嗅觉异常发达的补偿,同时利用这种补偿去发现常人所容易忽略的变化过程。他通过对街道上交通工具在气味和声音上的变化来展现都市的飞速发展,如过去四轮马车和马车车队“嘶嘶的、吱吱的或者是哼哼的声音”[3]21与现在“一切都是机械的了,那些噪音,汽车从你两旁飞速驶过,喇叭的嘟嘟声,还有警察吹哨子的声音”[3]22的对比,又如“摩托车的突突声加了进来,空气中渐渐地少了那种动物皮毛的有机味道,大热天里也不再有马粪的臭味飘得满街都是。”[3]21这些段落的描绘生动展现了城市工业机械化的发展:起初,城市依旧需要借助动物作为劳动力时,霍默在街道上听到的是马蹄嘚嘚的声音,是人与自然相融不分的景象。当机械与技术占领城市,人们可以制造出机器来代替人完成生产时,轰鸣的机器便成为城市的主宰,所发出的庞杂、混乱的噪音让人烦躁不堪。小说通过关注霍默由听觉和嗅觉感受带来的内心私密情绪变化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旧的世界正在瓦解,一个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正在形成,但工业机械化文明导致人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基础遭到破坏。”[4]79-80这让人们倍加怀念人与自然仍能亲密相处的时光:“当我们的国家上空冒出越来越多的工厂黑烟,煤矿里轰隆隆地运出越来越多的煤,越来越多机车轰鸣着在深夜里驶过,越来越多的收割机划过稻田,越来越多的黑色汽车充斥街头,摁着喇叭横冲直撞时,美国人民就越发崇尚大自然。”[3]7
在霍默掌管家中大权时,他与外界的联系最为紧密,这种联系也让他不断地回想自己曾怎样探索世界、感受自然:“突然间我想起了位于麦迪逊大道和第九十四街交叉口的那个种植蔬菜的农场,当时作为一个视力健全的孩子,我每年初秋都会和母亲一起随人群去那里采摘蔬菜……我嚼着草药的小叶子,这明媚阳光下盛放的生动色彩,湿润的绿叶气味和潮湿泥土的味道让我沉浸在幸福的微醺中。当然,和我的视力一样,这个农场早就消失了,现在那地方成了兵工厂。”[3]34这是霍默父母双亡后独自坐在餐桌旁的追忆,是小说所有景观描写中色彩最为斑斓的一段,也是表现母亲形象最为温暖慈爱的一段,这里多克托罗将霍默对乡间蔬菜园的色彩观察发挥到极致,但他在大段美好回忆后添上了一句冷硬的收尾——“现在那地方成了兵工厂”,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城市化进程中拆迁重建带来的粗暴割裂之感。农场的拆毁代表着城市人与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的告别,兵工厂的建立则代表着城市正往追逐机械文明与金钱暴利而又暗含最终毁灭的方向前进。霍默常去的谷物交易所也几经易名,最后变成冰冷生硬的切斯曼哈顿银行。这些城市中高楼的崛起与场所机构的更迭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工具主义和技术统治论占领城市街区的无言体现,它们切断了与传统生活的联系,侵占了人们精神上的生存空间,使得城市呈现出一片水泥森林的荒原景象。
三、家宅:个体与时代命运的交错
小说中,两兄弟的“维多利亚晚期风格设计”[3]4的家宅坐落在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却最终沦为“积灰的房间”“成捆的报纸”“迷宫般走道的墙”和“地下室霉菌渗透过地板”组成的垃圾场。
豪宅由盛转衰的过程体现了一种个体生存与时代命运的错位。一方面,家宅变迁过程象征着都市发展对传统生活的摧毁,孤零零的家宅不仅反映了兄弟俩与世隔绝的状态,也折射了兄弟俩内心空间景象。
起初,父母在世时,他们将家装潢为维多利亚式富丽堂皇的豪宅,使之洋溢着英国贵族般奢华绚丽的气息:“悬垂着装饰性吊穗的皇家直背靠椅,高至天花板的落地窗上的厚重窗帘,镀金的悬杆上挂着的中世纪的挂毯,带弓形窗的书柜,厚波斯地毯,配着流苏灯罩的落地灯和配套的漏勺和双耳瓶。”[3]5维多利亚风格扬弃机械理性的现代美学风格,代表着一种对古典美学的回归。但这种繁琐装饰风格的家居也更容易令人感到压抑,附属物件占据着家庭空间的角角落落,周游世界得来的纪念品和其他收藏品也悉数陈列,窗户和家具都挂着厚重的织物,让房间显得布局狭窄且昏暗。厚重的靠垫、壁炉的悬挂物和幕帘及工艺品等容易藏污纳垢,长期生活在此种环境中易导致幽闭恐惧症,似乎这一切的空间布景就已暗示了豪宅日益封闭、逐渐败落的命运。
霍默执掌家中大权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平衡开支、维持家宅原貌,家宅成员之间也因此为捍卫生存而相互算计:“城市生活已经将人为了生计而与自然的斗争变成了人为了获利而与其他人的斗争。”[5]181霍默为减少生活开支,找借口辞退了父亲生前喜爱的马车夫沃尔冈,老佣人西沃恩生怕年轻女佣茱莉亚取代自己在家中的位置而不断向霍默告状,而茱莉亚野心勃勃,为了能在都市扎根而成为霍默的情妇,随后又因被发现擅自佩戴霍默母亲的珠宝而被逐出家门。此时的家宅秩序涣散,进入了无法掌控的混乱之中。
兰利归家后接替霍默成为一家之主,但参战经历和诗人般的悲观气质让他在面对都市生活时不知所措、本能般地去抵制,而这又影响了整个家宅。当他战后归来打起精神主动约会女校友时,家中洋溢着生机和轻松的气氛;当他带着霍默放荡于酒吧,与黑社会、妓女打交道时,家中呈现出偏离社会主流的衰败景象:“似乎没有任何事值得去做,这栋房子此时就形同坟墓”[3]57,“我们的居所,外面是第五大道而里面则让人想起废旧仓库”[3]58;经历黑帮老大的威胁后,兄弟俩感到“一种人生徒劳无用的感觉转化成排山倒海的绝望涌上心口……彻头彻尾的横遭侮辱,完完全全的无助无望”[3]141;终于,当兰利对警察的勒索、银行的骚扰、消防署的调查、电力和自来水部门的催缴欠费感到不胜其烦后,他选择彻底地对外隔绝,在闹市中自我隐退,拒绝消费水、电、煤气、通讯等现代基础服务,不与邻居来往。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兰利越是想在都市中简单化生存、回归自我,越是举步维艰。兰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肄业生,拥有哲学家般的智慧,他坚守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梦想(出版“永恒之报”以结束信息爆炸的混乱境况并启示现代人)。强烈的不安全感让他不断捡拾废弃物以备不时之需,他捡拾的小物件也饱含时代意义,如古董台灯、一战的防毒面罩、工业时代的福特T型汽车、打字机、唱片机、紫外线照射灯等,使家宅变成了一座凝结历史时间的博物馆。他强硬抵制城市现代化工业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这种抵制又使家宅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抛弃。都市中,高工业机械化使社会愈发强调即刻性,一次性物品充斥着人们生活,“这意味着不止是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废品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6]357。
金钱是产生这一困境的根源,它霸权式地支配着现代社会中的时间与空间。企图反抗这一压制的个体往往寄望于社会运动,这就解释了小说中涉及到的各种社会运动、街头生活和文化艺术实践等的蓬勃发展,兰利爱上了狂热的激进分子安娜,与一群不屑于遵守都市秩序、生活放荡的嬉皮士为伍,在公园参加反战集会等,然而这些旨在把空间和时间从当前的物质机械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运动都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安娜被遣送回国,嬉皮士“贫穷”“年轻”,“根本无心去想这个社会最后会怎样报复他们”[3]167。“因为金钱社会加上理性化了的空间和时间,不仅按一种相反的意义来解释自己,而且各种运动也必须面对价值的问题、它的表现以及适合于他们自身再生产的空间与时间的必要结构……简言之,资本在继续支配着,它这么做部分是通过控制空间和时间的优势,甚至是在反对运动暂时获得了对于一个特定场所的控制之时。”[6]298
最终兰利为了节省开支解聘了厨娘,被迫放弃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带着霍默去快餐馆解决温饱表明他不得不屈从于金钱支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他们一度痴迷于电视娱乐节目,去地下酒吧放纵,享受廉价的酒水与性服务,此时开放的风气俨然与“奇装异服、女性抽烟喝马蒂尼酒都还是不可想象的”[3]3过去形成对比。都市随经济发展,资本也无休止地流动,瓦解了家园、社区甚至国家,使空间结构有序化。兰利无法彻底地顺应现代都市生活,又无法逃脱都市里金钱霸权式的支配,种种力量的对抗使得家宅在空间上陷入混乱,最终沦为闹市中的垃圾场。
另一方面,矗立在第五大道旁的败落家宅又以其独立完整的空间审视着现代人的居住场所。
家宅不同于外部世界,它是一个可以由生活个体随意布置的空间。法国文学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里对家宅的意义作出了详尽的探讨,他认为“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7]31。同样,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之所以两兄弟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从他们不同的居住环境就可以找到答案。城市人已经搬进现代化的公寓,他们的居所既没有周边自然空间也没有自身垂直型的屋宅(如阁楼、地下室等),他们漂浮在空中,他们的家没有根,对家的状态体验总是单纯的水平性,他们与大地和宇宙的联系是如此的疏离,以至于感受不到对家宅这个小宇宙的原初依恋。反观霍默与兰利的家,有着父亲的书房、母亲的会客厅、楼下管家的厨房、铺地毯的楼梯、哈罗德乐队曾演奏过的地下室、富丽堂皇的餐厅、温馨舒适的卧室和可以自由畅想的阁楼。虽然日后房子颓败,但家宅给予兄弟俩的生命体验和最初启蒙是无法磨灭的,就像霍默在小说末尾提到:
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的家:洋溢着一种光辉的优雅,静谧与欢乐同时存在。生活在房间之间流动着,不受恐惧的侵扰。我们男孩子互相追逐着,上上下下楼梯,穿梭于每一个房间。我们捉弄仆人们也被他们捉弄。我们惊叹于父亲装在罐子里的标本。作为小孩子,我们常坐在厚地毯上沿着毯子上的图案推动着我们的玩具汽车。我在音乐室里上钢琴课。我们从大厅里偷看着我们父母耀眼的、点着蜡烛的晚餐派对。我哥哥和我可以跑出前门奔下台阶穿过马路进入公园,就好像那也是我们的,好像家和公园,两个都被太阳点亮着,是同一个所在。[3]237-238
兄弟俩的家宅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金碧辉煌的维多利亚式装潢风格,更在于它在兄弟俩的启蒙之初就以自身垂直的空间感培植了兄弟俩的内心空间,有助于他们场所美学的形成。在他们回忆过去时,背景保留了那些在场所中接触的人物角色和故事。回忆中空间覆盖了时间,仿佛空间里保存了压缩的时间,如看到钢琴就会想起兄弟俩为玛丽倾心的那段时光,置身书房会想到父亲的从医生涯和周游列国的经历,在厨房则会想到慈爱的罗比洛奶奶照料一日三餐的场景和文森特逃难中警觉又嗜血的本性。内心情感丰富的兄弟俩在这独立完整的家宅中开启了人生中爱与痛的体验;日后他们在都市中遭遇种种不公,对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持矛盾回避的态度时,家宅又替他们将外面变化发展的世界挡在门外。也因而兄弟俩独立完整的家宅与周围拔地而起的大厦公寓越发显得格格不入。当霍默提到“褐石公寓”中的邻居对于他们举办下午茶舞会的举报时,多克托罗借霍默之口对现代公寓中的居民心态加以批评:“现在他们又去报告我们的后院着了火,碰巧还真是这样。为什么这帮人就不能只管好自己的事呢……”[3]184
现代人搬进公寓这种狭小水平的空间后便失去了垂直场所的体验,矛盾与冲突丛生的都市里鲜有原始家宅的淳朴体验。失去了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即使纽约人口成千上万,楼宇鳞次栉比,但在大都市中人们却没有家宅,它已成为一个异化的、非人格的场所。
四、中央公园:物欲都市中的精神绿洲
中央公园号称纽约“后花园”,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岛的中央,被第59大街、第110大街、第五大道、中央公园西部路围绕着,是一块完全人造的自然景观,拥有树木郁郁的小森林、庭院、溜冰场、回转木马、露天剧场、小动物园、可以泛舟的湖、网球场、运动场、美术馆等。事实上,在中央公园酝酿出现的19世纪50年代,纽约等美国城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公园绿化等公共开敞空间不断被压缩,传染病流行等各种城市问题使得满足市民对新鲜空气、阳光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设计者借鉴了英国伯肯海德公园的田园主义风格,为厌烦都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静、清洁、纯朴的田园环境。
身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多克托罗自然对中央公园在都市居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切身的理解和体会。在小说中,霍默对纽约的描绘就从中央公园开始,“那年冬天我站在中央公园结冰的湖面上”[3]1。小说结尾,他与法国女记者杰奎琳在中央公园聊人生,在他意识的最后一刻他又重新描绘了儿时与哥哥在公园玩耍嬉戏的幸福光景。在小说整个谋篇上,中央公园起到使结构完满的作用;在内容表现上,霍默总在公园里遭遇新奇的人和事,中央公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在对于表现城市现代性主题上,中央公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杰奎琳与霍默的交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央公园是“如此规整,如此有计划,有着如此严格边界的几何对称的建筑——像是自然界里的天主教堂”[3]213-214。但与周围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高层公寓、购物中心相比,中央公园实在太过低矮,“这里似乎是一座沉没的公园,在一个上升的城市里慢慢沉没的自然天主教堂”[3]214。多克托罗将中央公园比作天主教堂,意指它是都市人的精神家园,人们在繁华浮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寻得的一片绿洲,在此他们可以逃避现代化的围剿,纯粹地拥抱自然,稍作休憩,进行冥想反思。镶嵌在高楼大厦此起彼伏的纽约腹地中的中央公园,在信仰日渐失落的都市中起着净化心灵的作用,因而也就显得格外珍贵。
作为守望人们精神家园的最后一块净土,中央公园虽没有像蔬菜园那样遭遇拆迁,也没有像兄弟俩的家宅那样败落,相反它愈发成为都市人游玩放松的乐园,但是它也已不同往日。五花八门的现代化游乐设施正逐步蚕食着原始淳朴的田园风光,体育场、滑雪场、溜冰场、塔楼、喷泉、三轮车、儿童车、雪橇等的出现,使如今的中央公园失去了许多田园风味。白天它是都市人休息嬉戏的乐园,各种文化集会运动也常云集于此,但夜晚它也包庇着黑帮、流浪汉、失业游民等各色人群,成为犯罪重灾区。小说中,多克托罗通过霍默与杰奎琳之间的对话,揭示纽约中央公园正遭受摩天大楼等建筑群的合围,逐渐在城市中央沦陷。但无论如何,在像纽约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中,人们依然能享有如此优美的大公园是非常可贵的。故事结尾处霍默回忆起小时候温馨欢乐的家庭时光,“好像家和公园,两个都被太阳点亮着,是同一个所在”[3]238。在霍默心中,中央公园和儿时的家宅一样已经成为其心灵上的故园,家宅日渐败落而公园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造依旧焕发出勃勃生机,履行着守护现代城市人精神家园的职责。尽管多克托罗在小说中再现了都市人面临的种种来自生存空间方面的挑战和压迫,但他仍对中央公园寄予希望,希望人们能感受到中央公园在他们的都市生活中发挥着的精神上的启迪作用,能在这一绿色的天然屏障中回归自然,在繁忙的都市中借以调节适应外部压力,达到自我平衡。
五、结语
多克托罗在《纽约兄弟》中描绘了光怪陆离、川流不息的现代都市生活,对都市中的生存空间进行了丰富的想象与建构。街区的剧变折射出都市的面貌处于恒定的瞬息万变中,加剧了现代人之间的疏离隔膜之感;兄弟俩日渐败落的家宅和主人公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现代文明对家庭的入侵与破坏的具体象征,但也是传统生活对现代居住场所的审视;而中央公园为现代人提供了休憩、沉思和冥想的空间,是现代人精神的绿洲。小说以细腻复杂的心理刻画、独特细致的空间描绘表达了对现代都市进程中各类变迁的关注与思考,再现了现代人在日趋恶劣的都市生存空间下的糟糕生活体验和心灵空间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种种冲击压制。但在结尾处多克托罗还是留有一丝想象的余地,表达了其对未来改善城市生存空间的期冀,从而展现了作家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人文情怀。
注释:
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版权,徐振锋翻译,中文版于2011年出版。
[1]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林莉. 《安德鲁的大脑》解读:E.L.多克托罗访谈录[J]. 当代外国文学,2014(4):161-165.
[3]E.L.多克托罗. 纽约兄弟[M]. 徐振锋,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Worth L. The City in Literature[M].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5]Simmel G,David F,Mike F.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C]//Simmel on Culture:Selected Writings Theory,Culture & Society. London:Sage Publication Inc,1997.
[6]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BlockHomePark:OnUrban’sLivingSpaceinE.L.Doctorow’sHomer&Langley
MENGJiangling,ZHURonghua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udies,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116,China)
E. L. Doctorow’sHomer&Langleymakes an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living space:the great changes of block reflect the capricious urban landscape,showing a sense of estrangement in urban life;the fading of Collyer Brothers’ luxury home,in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protagonists’ destiny,not only is a specific symbol of modern civilization’s impact on families, but also shows an interrogation of traditional life about the modern urban living space;the Central Park provides a tranquil space for urban people’s meditation,which is regarded as modern people’s oasis on their spiritual wasteland. In this novel based on the Collyer Brothers’ story,Doctorow focuses on modern people’s living situation in urban space,showing his observ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urban life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urban living space;block;home;park
I106.4
A
2095-2074(2016)01-0101-06
2015-08-2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WWB001);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2014YZD006)
孟姜玲(1990-),女,江苏连云港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朱荣华(1977-),男,江西广昌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