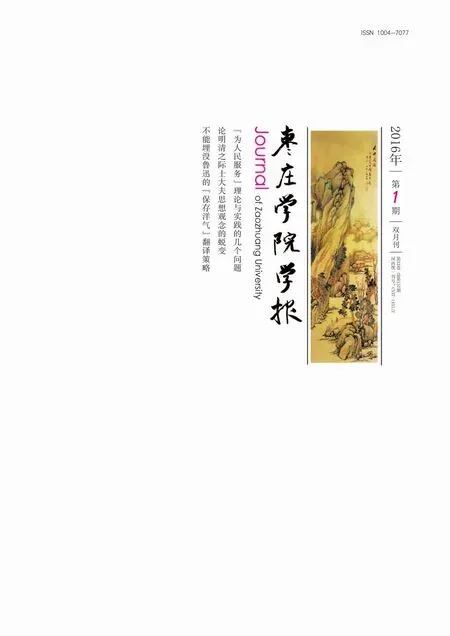论高行健《灵山》的火神崇拜
丁文俊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论高行健《灵山》的火神崇拜
丁文俊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241)
[摘要]高行健作品《灵山》的叙事建立在“寻根”母题的模式下,表达对前现代的自然状况的崇拜与向往,具体表现为对“火神”的怖惧。对“火神”的敬畏作为特定的历史记忆,并无法延缓崇高灵魂在世俗演进过程中的堕落。在当下的现场,火神传说以“火——红——血”的方式发生转义,以女性身体的鲜血向火神献祭,表达了追求身体放纵的解放诉求与向受难者忏悔的救赎祈求。因此,火神崇拜是一种嵌入当下的自然宗教观。
[关键词]《灵山》;火神;鲜血;自然宗教观
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讲述了作为旅行者的“我”,出于观赏独特自然风景的考虑,寻找以“灵山”为地名的一个原生态地方,在旅途中与一名女性相遇,两人互相讲述各自的往事与见闻,历史传说、前述往事、现场的自然探险与及身体的爱欲构成了小说的多重叙事线索。“灵山”是旅行者所梦寐以求的自然圣地,“我”认为置身灵山可以让自己得以摆脱人伦俗务的纷扰,在原始森林直面自然的时刻探知源初的秘密,因此,“我”追寻“灵山”的行动,朱崇科认为这“恰恰是对被压抑、边缘化的根的召唤与再现”[1](P87~92),表达了对植根于前现代文明的“根”的向往。然而,原初自然并非作为孤岛般的乌托邦圣地存在,而是嵌入至当下的在场,具体体现在旅行者与女游伴的游历过程、往事回忆、性爱交合之中,隐匿于怖惧的面孔之下,对自然的追寻因此又与创伤记忆的流变结合在一起。
“火”作为自然力量的某种象征形式,构成了旅行者所讲述的多个故事的主题,火神崇拜正是“寻根”期待的一个组成部分。火神通过颜色相似规则延伸,与“鲜血”相同一,与死亡、纷争、性爱缠绕,正是自然力量在文明时期的隐匿表现。
一、火神:作为命运的象征
高行健以第一人称——“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向旅途期间的女同伴讲述了太爷爷的死亡以及伴随发生的火神传说。故事的梗概为,由于山民忙于生计而无暇、也不愿意免费奉献食物祭奠火神祝融,火神生怨而在丛林中现身,“我”的太爷爷在打猎时目睹火神之后,向家人预言灾难即将发生,第二天凌晨太爷爷惨遭枪杀,当夜树林发生漫天的大火,山民与栖息林中的动物仓皇逃生,仅余下一片废墟。
从火神现身的缘由看,“这红孩儿火神祝融正是这九山之神。那呼日峰下,原先的一座火神庙年久失修,人们忘了祭祀,酒肉都只顾自己享用。被人遗忘了的火神一怒之下,便发作了。”[2](P220)从“我”的讲述中可以归纳,火神的现身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从一般的理解看,山民忙碌于谋生,不再有时间与精力组织祭祀向火神致敬,火神因为缺乏食物而向人类问罪。再从深层次的角度看,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描述,“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3](P1)尽管“我”的太爷爷生活的年代并不具有《启蒙辩证法》所批判的西方启蒙现代性,然而,根据小说的情节,在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中国,人类的行为方式同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有着无限的敬畏,而到了现代,则转变为借助知识的力量对自然进行征服,并予以无节制地索取,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祛魅的历史进程具有相似性。山民在打猎杀戮生灵的行动中,逐渐不再畏惧自然,相信人的智力与体力足以占有意图攫取的自然资源,因此变得唯利是图,具体例子包括了贩卖林木资源谋利,使用猎枪射杀老虎、豺狼等猛兽,自然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褪去了曾经具有的神秘面孔,不再被认为具有可以压服人类的力量,沦为了人类不惜通过战争的手段进行争夺的财富。由此,传说中的火神顺理成章地在世俗社会中被驱逐,山民怜惜钱财,不再执行以火神为祭祀对象的供奉之礼。
然而,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逐利逻辑,不仅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同时征服自然的手段也被应用到对他人的算计之上,人类将享受着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着人与人之间因为利益而产生的纠葛,由杀戮动物、欺骗他人的内疚意识转化为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恐惧。这是对杀戮生灵、欺诈行恶等所为可能引发轮回报复的畏惧,时间无休止的向未来线性发展,人类无意识深处的畏惧感无法得以排解,火神的重新现身恰好验证了山民潜意识中的怖惧心理。从“我”的太爷爷初见火神即发出灾难预言的行为可以看出,山民自知亵神的行为并不具有合法性,这是对命运轮回报应的潜意识笃信,也是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潜意识畏惧。火神代表着惩罚的力量,他的现身意味着曾经前文明时代具有主宰地位的命运之神重新出现。
回到小说所叙述的火神故事,“我”的太爷爷目睹了火神现身之后,哀叹“看见红孩儿了,那火神祝融,好日子完啦。”[2](P216)这是人类对命运的天然恐惧,火神以惩罚者的面相出现,对山民而言,这预示着无法避免、必须承受的命运即将降临。其后的灾难印证了太爷爷的预言,狩猎为生的太爷爷死在的黑枪之下,枪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猎杀猛兽的最有效的工具,最后成为杀害人类自身的凶器,这是对人类的反讽式惩罚。其后,深夜山林大火,彻底断绝了山民短期内在该地区继续牟利的可能,林木被毁,野兽或葬于山火或逃离,火神代表自然向人类报复。然而,由于现代工具的快速发展,祛魅的社会已经无法恢复到曾经存在的神人和谐的状况,火神的惩罚并非要将山民拉回到敬神的传统中,仅仅是通过毁灭山民财富、乃至生命的方式施以报复,这是人神关系的决裂。这可以从“我”的太爷爷死亡方式中得到启示,他并非死于山火,而是被他人枪杀,然而家庭更愿意将其死亡归罪于火神的现身,而非遵循他的遗言追究施暴的仇家,与其说火神现身预示的命运对文明罪恶的掩盖,不如说这种因利益冲突引发的杀戮常常以敬神为名发生,此后也将在现代性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变得习以为常的随处可见。神灵的现身已经不再具有启迪的作用,不仅无法调解自然与人的矛盾,也无法使人类心生敬畏而不再把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火神的报复并没有减缓伴随现代性延续所引发的崇高灵魂的堕落进程。
“我”与旅伴互相讲述的故事进一步验证了人类灵魂堕落的事实,包括了纵欲发生的轮奸、长辈师长的诱奸,乃至伪造溺水而掩盖事实,以及由于政治风暴所导致的畸形恋爱的发生。共和国所塑造的领袖,并没有真正完全取代自然之神的地位,个体的力比多冲动无法在以禁欲为特征的政治运动中得到合理释放,反而酿成了更广泛的人伦悲剧,表现为阶级关系走向异化。汪晖认为,“唯身份论、唯出身论或血统论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所包含的那种主观的、能动的政治观的否定和背叛”[4](P36),异化的阶级关系被视为天然存在的对立,资产阶级、地主与其后代不得不永久接受阶级敌人的帽子,无法通过自身的思想转变与行动在政治上完成自我改造以转变阶级身份。由此,所谓的“革命者”的施暴就具有了正当性,将受压抑的能量转化为施暴时候的欲望满足。“我”的叙说中包括了亲眼所见的诸多暴力事件,例如,发生在五七干校的惨剧,梁伯伯在接受批斗时候被从板凳推倒在地,门牙被丢落,导致满嘴鲜血;一个小女孩在母亲病故不久,被包括一群同龄男孩以相约游泳的名义,在桥底洞奸杀。这是一个神灵退隐的罪恶时代,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受到了无情的践踏。
二、现场的转义:向自然献祭
对于集体创伤记忆与当下情景的关系,加布丽埃·施瓦布精辟地写到,“集体创伤以各种曲折的方式传给个体。有些个体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灾难性创伤的重创。”[5](P136)火神现身及其后的灾难故事,作为一种历史创伤记忆,以传说的形式在代际之间传播,并在小说中反映在“我”的言说中,与现场的语境发生了交互作用,女旅伴关于血流满地的自虐幻想正是又一次伤害的表现,同时创伤记忆又蕴含了“关乎作为群体的民族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对人性本质的反思”[6](P50~59),因此自虐的幻想在小说中也引申出对革命政治的检讨。
根据《灵山》的叙事,当代人所亲历的彷徨、恐惧、迷惘的状态,将重新激活先辈传说的火神传说及灾难记忆,火神以转义的方式在现场重现。根据原始思维相似性传递的法则,“火”与“血”二者因为同具有鲜红的颜色,根据原始思维的相似性原则,发生了“火——红——血”的转义,先辈对火神的崇拜与怖惧,转化为当代人对鲜血的敬畏与恐惧,再与女性经血的特异特征结合,火神崇拜与身体之间构成了隐性的转义逻辑。
这是关于女旅伴的讲述:“她说她要让你见血,叫血流到你手腕上,再到手臂,再到腋下,再到胸脯,她要在白胸脯上也鲜血横流,殷红得发紫发黑,她就浸在紫黑的血水中让你非看不可——赤身裸体?就赤身裸体坐在血泊之中,下身,股间,大腿上都满是血,血,血!”[2](P240)该段叙述呈现了一幅类似原始祭祀的图景,她幻想以身体、鲜血作为自己呈现的特征,寻求回归自然、皈依神灵的途径。我们需要结合高行健的“没有主义”理念予以理解,他谈到,“作家不必成为社会的良心,因为社会的良心早已过剩。他只是用自己的良知,写自己的作品。”[7](P23)在小说中,火神象征着过去的自然神灵,在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已经为人类所驱逐,当下的个体受锢于过于沉重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失去了自我的本身情性,陷入苦闷与忧惧,无法再次召唤神灵的现身救赎自我,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地感知纯粹的原初自然。她以自残的方式让鲜血在身体外奔流,并裸体置身浸满大地的血泊之中,这是对古代献祭仪式的模仿,与中国主流道德观念相悖。她企图以鲜血作为中介,使身体得以摆脱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规训力量,从而得以激活代际记忆中的火神传说,让象征自然神谕的力量、已经为自然文明驱逐的火神在当下重新现身,而不仅仅存在于“我”讲述的传说中。“火”与“血”的颜色均是鲜红,高行健通过这种隐秘的相似性关联,以鲜血奔流的景象唤起对火神的怖惧,从而在作品中的当下现场营造了神秘与恐怖的幻觉。
进一步看,小说中直接用于献祭的就是女性的赤裸身体,女性因为经血的体异性特征,更具有激活神秘自然力量、并与之对话的先天条件。她的身体曾经为长辈通过诱奸所占有,因此她的身体同时也是文明罪恶的暗喻。她通过自毁身体的方式,让鲜血大量流出,这并非简单的自残行为,而是要激发“自身存在的意识”[8](P437),在向神灵致敬的同时,唤醒自身被遮蔽的感性意识与建立在个体性基础上的独立灵魂。这一行动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她期望在痛感的感官刺激与及鲜血满地的视觉刺激的双重震撼之下,恢复为世俗规训所禁锢的身体感觉,营造怖惧的气氛,从而得以体验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自由意志。体现在小说的叙事中,她深情地向“我”倾诉,“她要的是爱,需要全身心去感受,哪怕跟你下地狱”[2](P241),因为“当人确认自身乃是脆弱的个体时,便产生一种拒绝的力量——拒绝带假面具以掩盖自己的脆弱,于是获得真诚与真实。”[8](P435)“她”渴求真正的爱欲,不再为世俗得失所顾虑,而是听任自身的沉沦,期盼能在地狱的暴栗中得以体验真切的自然欲求。其二,这也是通过自我惩罚的方式,为自己、也代表族群向自然赎罪,这是对杀戮生灵、掠夺自然资源等所为的真诚悔过,也是为在文明、理想的名义之下被摧毁的个体招魂。在小说中她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县革委会主任的女儿与地主孙子相爱私奔,最终在围捕时双双殒命,而此刻她选择再次营造了相似的鲜血淋漓的场景,在潜意识里希望通过“血——红——火”的巫术思维的过渡,同时召唤象征着火的自然神与象征着鲜血的受难者重新出现,实质上这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掘。她以现代人的身份,在回顾历史记忆的时刻,分别向被驱逐的自然神、受难死者真诚悔罪,从而使受难死者的灵魂得到救赎,族群曾经犯下的罪孽得以弥补。正是在自由与救赎的视角下,高行健从人性论与道德伦理范畴,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进一步解放身体、释放爱欲提供了合法性论证。
由此可以看到,在文学形式的层次,《灵山》运用了以原始主义为基础的写作手法,通过自残的幻想与对自然神现身的期盼,以诉诸原初本能的方式,为解放身体与救赎罪行赋予了合法性。我们可以再参照方克强对原始主义文学批评的阐述,“以原始来对比和批判现代文明为其思想内涵的主要特征,以返归神话的超现实想象方式及表现形式为其艺术追求。”[9](P95~101)由此可见,作为文学形式的原始主义书写,有其文化政治的诉求。《灵山》的叙事建立在分享创伤记忆的基础之上,关于创伤记忆的分享及其社会影响,则可以如此理解,“而与他人分担苦难记忆不仅帮助社会扩大了‘我们’的范围,而且共同的创伤记忆也具有维系社会正义和团结的作用。”[10](P110~119)因而,《灵山》在文化政治层面的价值,则是通过原始主义的文学书写形式,以分享创伤记忆的方法,向遭受破坏性开发的大自然及无辜受难者表达忏悔,并进而选择回归纯然自然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放弃对物质利益、政治符号利益的追求,进而在公共生活层面建立以自然德性为基础的美好政治。
三、结论:嵌入现实的自然宗教观
在高行健看来,“生命的意义,与其说在这谜底,不如说在于对这一存在的认知。”[7](P84)他反对尼采的超人学说,主张通过亲自对生命隐秘意义进行探究,以寻找生命与人伦的终极意义。中国社会并没有西方社会那样的宗教传统,高行健自身也非基督徒,《灵山》在寻求心灵避难所的过程中选择了自然崇拜,火神就是高行健所着力塑造的自然之神,并以转义为鲜血、女性身体的方式在当下现身,构成反思政治运动与世俗牟利的彼岸世界。然而,这个彼岸世界并没有真正脱离当下的现场,而是不断通过“我”与女旅伴的性爱与及相伴随的热烈感情而嵌入现实。因此,对火神的崇拜,是一种嵌入现实之中的自然宗教观。高行健对自然宗教的皈依又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禁欲色彩,诉诸身体的解放以召唤自然神的现身,追求的是不受拘束、顺应本性冲动的自然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朱崇科.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以高行健、李碧华、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J].扬子江评论,2008,(2).
[2]高行健.灵山[M].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3]马克斯·霍克海默,等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加布丽埃·施瓦布著,陶家俊译.文学、权力与主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赵静蓉.记忆的德性及其与中国记忆伦理化的现实路径[J].文学与文化,2015,(1).
[7]高行健.没有主义[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
[8]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9]方克强.原始主义与文学批评[J].学术月刊,2009,(2).
[10]赵静蓉.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J].文艺理论研究,2015,(2).
[责任编辑:吕艳]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16)01-0049-04
[作者简介]丁文俊(1988-),男,广东东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