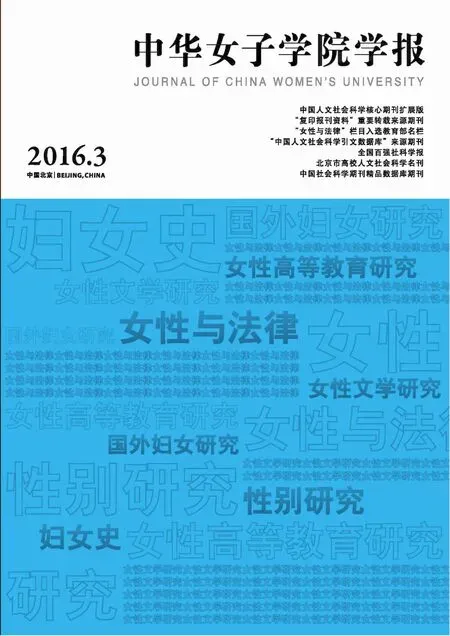论大庭美奈子文学的流亡主题
——基于《浦岛草》中的战争孤儿的研究
侯冬梅
论大庭美奈子文学的流亡主题
——基于《浦岛草》中的战争孤儿的研究
侯冬梅
摘要:大庭美奈子文学中充溢着二战后的各种流亡元素,其作品把漂泊异乡、毫无生活根基的人比喻为“无根草”,“无根草”是大庭美奈子文学中处于流亡状态的主人公。《破烂博物馆》中的战争新娘是其“亡命文学”中的一类“无根草”,而《浦岛草》中日美混血的战争孤儿是另一类“无根草”。大庭美奈子的《浦岛草》关注日本战后时空中的战争遗留——战争孤儿问题,聚焦并思考战争、女性和人生,表达了作家对战争和社会的反思,其关注、思考女性命运的特殊视角在日本战后文坛别具一格。
关键词:大庭美奈子;流亡主题;《浦岛草》;战争孤儿
一、大庭文学中的“无根草”和流亡主题
1959年10月至1970年3月大庭美奈子跟随丈夫旅居美国。与那霸惠子在作家“总年谱”中记录到:“1959年10月,(大庭美奈子)移居美国阿拉斯加州巴拉诺夫岛的锡特卡城。她对自然和人类一体化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世界观产生了兴趣,此后,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多方调查。在旅居美国期间遍游美国各地。”[1]691因为历史的原因,锡特卡居住着大量亡命的俄国人和俄国东正教的主教们等。此外,还有二战期间从欧洲流亡的人士在此安居。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期间,这里还陆续来了一些反对越南战争以及为逃避兵役流亡到此的美国人;二战后以及越南战争后,还有不少战争新娘来到此处。大庭美奈子在阿拉斯加生活期间和这些人的交流影响了她对流亡的思考,其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流亡色彩。《三只蟹》用“无根草”形容在异国他乡过着漂泊生活的人群。因此,“无根草”在大庭美奈子文学作品中被用来比喻处于流亡状态的主人公。大庭美奈子的《破烂博物馆》特别关注了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战争新娘,这些战争新娘是作家文学中的流亡主体,是作家笔下的一种“无根草”。然而,1970年大庭美奈子回到日本后,反观日本社会,经历过战争、感受到战败的作家突然意识到日本社会中的一种隐形流亡——日美混血的战争孤儿。大庭美奈子的《浦岛草》中刻画了日美混血儿夏生的流亡人生,在为广岛原爆镇魂的背景下刻画日本的战败体验,战争孤儿成了作家笔下的另一种“无根草”。
大庭美奈子作品中的流亡主题与社会以及时代密切相关。从大庭美奈子的成长时代来看,她和日本文坛的第一批战后派、第二批战后派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直接的战争体验是大庭美奈子这代人所不具备的。然而,幼年时期体验过日本政府的战时体制,少女期到青春期经历过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以及日本为摆脱战后贫困进行的苦苦挣扎。在激烈动荡时代下成长的这批人具有凝视战争面目的独特视角。站立在战败后的焦土上感受被崭新竖立起来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察战败后的别样风景成了大庭美奈子等作家描绘战后社会的一大特色,为日本战后文坛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描写流亡的作家当中,出生、成长在外国尤其是日本旧殖民地的作家为数不少。如古山高丽雄(1920—2002),后藤明生(1932—1999)出生在朝鲜。五木宽之(1932—)生于福冈,成长在朝鲜。日野启三(1929—2002)出生在东京,五岁时随家人迁居朝鲜,日本战败回国。三木卓(1935—)出生在东京,1937—1943年在大连生活6年,二战日本战败后回国。以上这些作家活跃在当今日本文坛,他们在作品中描写的流亡和他们本身的战败体验和异国文化体验密切相关。大庭美奈子作品中的流亡和这些同时代日本作家比较来看有很大的不同。从成长经历和个人体验上看,大庭美奈子称不上是遭受压迫的流亡者,她所谓的流亡是为了反抗无形的社会压抑,主动脱离既属共同体。从主观意识看,她有意背离日本、自我放逐。因此,大庭美奈子作品中的亡命现象书写和文坛上所谓的普通意义上亡命文学、离散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1974年,《三田文学》刊登了大庭美奈子和平冈笃赖的对谈“亡命的文学——创造性语言和前卫”。[2]平冈笃赖认为,大庭美奈子在登上文坛之时就让人感到其作品中一种亡命者的东西,作品中的主人公以亡命者和漂泊者居多。对于平冈笃赖的评论,大庭给予爽快的回应,她自认为自己也是精神上的亡命者。“Exile”具有流亡和自我放逐等含义,国内学界将这种类型的文学称为“流亡文学”或“离散文学”。大庭美奈子在作品中对“Exile”现象早就有着关注。她认为,当下被作家用特写的方式表达的流亡内容当中充满了作家从本国文化和语言当中解放出来的兴奋感。通过创作流亡主题的文学,作家脱离了本国文化和语言束缚,表达得到了解放。大庭美奈子的笔触描写了社会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流亡主体和流亡风景。
因为日本战败,《浦岛草》中的夏生作为美国占领军的种子诞生在日本土地上。由于一出生就父母双亡,夏生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战争孤儿。夏生被冷子、龙、森人一家收为养女,在日本长大成人,与冷子和森人的自闭症儿子——黎过着混沌不清的同居生活。日美混血儿夏生存在本身就是刻印在日本社会的战败印记,她作为日本战败的符号生活在战后日本社会。
二、日本战败符号:日美混血的战争孤儿
《浦岛草》的“白色水獭”章节中,留学美国十多年的雪枝返回日本东京,暂时住进了森人和冷子位于东京的家。她从机场回来的出租车上听到了森人讲起自己有个30岁的患有先天自闭症的侄子黎和一个25岁的日美混血儿侄女——夏生。
在明亮的地方观察夏生,她面相具有立体感,白白的肌肤上透着一点血色,一看长相就知道是白种人。不经意间夏生一下就消失了,就像隐匿在繁密深处的水獭一般。刚这么一想,她却又突然出现的眼前,瞪着大眼睛盯着这边看。不知为何,虽说是初次相见,她忽而变成白色的树精,忽而看起来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忽而看起来像一只大蛾子。但是,她就像以极快的速度撤退的动物一样,紧盯着我看的那双眼睛闪着狡猾的光芒。[3]41
夏生的亲生母亲雪是森人老家蒲原的一个孤儿,当年15岁的她从农村老家来到东京的冷子家做帮佣,照顾冷子和森人的儿子黎。她在森人答应照顾她的婚姻以及其他一切事情的前提下离开家乡来东京做女佣。结果,来到东京后的雪受到占领兵约翰的引诱并怀孕,在生下夏生后气竭身亡。森人把夏生的户口安在了自己名下,收她为养女。从伦理关系看,夏生是森人的养女、雪枝的侄女;从血缘来讲,夏生和森人、雪枝兄妹没有任何关系。
1945年,日本的战败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是日本政府在最后时刻仍然想方设法粉饰战败结局。所以,日本天皇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把战败日宣告为“终战日”。天皇的“终战日”宣言给日本国民造成了不少精神困惑,导致不少人把8月15日理解为:日本没有战败,仅仅是“战争结束了”罢了。时至今日,日本还能时而听到战败论和终战论的纷争。由于对战争结局的认知不同,也影响到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当前,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中依然把战后日本文坛的战争责任、战争认知当作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然而,经历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大庭美奈子是坚定的日本战败论者。她没有被政府的终战粉饰言论所蛊惑,她体验到的是不折不扣的战败。《浦岛草》中的混血儿夏生暗示被占领时期美国兵和日本少女之间的情事,大庭美奈子用被占领的日本女性身体表达刻骨铭心的战败体验。混血儿夏生作为日本被占领时期的遗留符号生活在日本,不管政府如何粉饰战败,夏生的长相就说明了一切。夏生直白地告诉雪枝:“我是占领军留下的种!”可以说,此话一语击中日本政府极力掩盖的战败伤痛。王新生在《战后日本史》中记录到:日本被占领时期因为“盟军总部”颁布废除公娼的指令,1946年3月,特殊慰安设施关闭。迫于生计,日本的许多性工作者以及非职业女性变成街头流浪的娼妓,成为主要向美军士兵出卖肉体的“邦邦女郎”。①邦邦女郎,指的是二战后在日本大城市街头出现的向占领军卖淫的妇女。结果出现了大量日美混血的儿童,据估计总数有15万—20万人。[4]14这些混血儿童的成长和经历,虽然大多数不为人知,然而,作为千千万万个混血儿童中的一人——夏生在《浦岛草》中的符号意义是非常特殊而又寓意深刻的。夏生们的存在,提醒着战败的事实。而实际上,战后的日本政府却一直在极力掩盖战败的事实。
从1945年8月,日本二战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已经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从表面上看,日本已经从战后的一片焦土上获得了重换新颜。“雪枝紧盯着东京的街头。仓库和污水,新铺设的没有花草装饰的街道,没有窗户的气派大楼,墙壁剥落的高层公寓和加油站。除了仓库、高架线、单轨车和广告牌上的字以外,东京和美国任何地方的城市没有区别。这是日本吗?这是东京吗?”[3]23不仅东京变化特别大,好像变成了美国的某个地方城市,就连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广岛也是旧貌换新颜。《浦岛草》在“海市蜃楼”章节中主要描绘了原子弹爆炸30年后的广岛。“冷子和森人在那里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一个城市,一个美丽的近代大都会兀然矗立在他们眼前。美得宛如一座海市蜃楼。他们的确曾亲眼目睹过这座城市的毁灭结局。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座近代大都市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认为是现实的东西。现实中,眼前存在着的是比东京还要漂亮的街市,这让他们觉得很虚幻。”[3]237
东京和广岛的繁华似乎已经把战败的伤痛全部掩盖起来,普通的日本人也似乎忘记了当年的战争教训。然而,作家对时代发展时刻保持着非常警醒的知觉,承担着表达社会的时代重任。大庭美奈子没有被日本社会呈现出的繁荣表象所蒙住眼睛,其文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浦岛草》是对日本社会遗忘战争、掩盖战争伤害的抗议和警告。混血儿夏生的存在隐喻着日本的战败体验,“夏生”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日本国民,让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没有走出战败的现实。混血儿夏生在日本的流亡人生是作家在《浦岛草》中表达的战后问题之一。
三、战争孤儿的不伦身世与伦理困境
夏生的不伦身世和战败紧密相关,战败是导致她不伦身世的前提,并给她造成终生的伦理困境。[5]夏生的母亲雪在冷子家做女佣时的主要任务是照顾黎。“雪坐在旁边的长凳子上守护着一天到晚都在那里玩弄着树叶的黎,约翰是在看到了雪的身姿后才来到公园的。当时东京的街头到处都是向美国大兵提供性服务的邦邦女郎,和她们比起来,十八岁的约翰对在公园里落寞地守护着孩子的姑娘更感兴趣。”[3]66在夏生出生前,她生物学上的父亲——年轻的美国占领兵约翰从日本又被直接派到朝鲜战场,并死在前线。
不管夏生的母亲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生下夏生,夏生天生就是一个私生子,因为夏生的真正父亲是外国兵。十八岁的少年兵死在了朝鲜战场。总之,他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感,好不容易才让日本少女怀孕,然后自己也死去了。也许,除了日本少女,这个少年兵还让朝鲜的少女、美国的少女都怀了孕。[3]49
生下夏生以后雪气竭身亡。“美国占领兵+贫农孤儿=私生子夏生”,这个公式里隐藏着多重意义上的不伦,如此不伦的身世是战争带给夏生的无奈宿命。
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美国占领军推行的民主主义观念的冲击。尽管如此,传统伦理观念依然根植于日本国民的内心深处。《浦岛草》中森人的身份是龙的徒弟,在龙去前线期间森人照顾遭遇原子弹爆炸的师母冷子。在抗拒原子弹病症的过程中,冷子企图用性爱逃离对死亡的恐惧。结果,冷子怀上了森人的孩子,并且在龙从前线回家的那天,孩子黎出生了。黎是森人的亲生骨肉、雪枝的亲侄子,同时也是胎里带的“原爆症产儿”①《浦岛草》中“黎”的母亲是主人公冷子,“黎”是冷子遭受到广岛原爆辐射后身体出现“原爆症”病状时候怀孕并生下的孩子。小说一直强调“黎”之所以不正常是和冷子在广岛原爆时遭受到原子能辐射有关,所以,此处称黎为“原爆症产儿”。——患有先天性自闭症。按照日本婚姻法,离婚后三百天以内出生的孩子会被追认为是前夫的孩子。所以,从前线回家的龙巧遇妻子冷子和徒弟森人之间的孩子出生,于是他强行把黎的户口放在自己名下。出于对儿子黎的身份的顾虑,森人放弃了主张父权。此事充分说明,尽管已经是实行民主主义的战后社会,但是,日本所谓的世道人心依然注重身份和血统等伦理关系。龙回家后,尽管一直主张自己的夫权、父权,可实际上,他和森人、冷子保持着三人同居关系。从表面上看,冷子依然是龙的妻子,森人的师母,龙和森人保持着师徒关系。冷子和龙住主房,森人住偏房。冷子、龙、森人三人在考虑黎的问题上,尽量给他一个符合日本传统文化的伦理身份,三人之间在表面上依然保持着符合法律和世间的伦理关系。然而,外观和形式上保持着和传统伦理观念一致节奏的表面现象未必是事实的真相。作家大庭美奈子的任务是要打开冷子家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将隐藏其中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在众人眼下。
日本是个崇尚血统的民族,尽管已经是战后,但是传统观念在国民内心深处依然根深蒂固。夏生是非婚出生的私生子和日美混血儿,同时还是战争孤儿。在日本,夏生的不伦身世本身就决定了她的边缘人、外人身份,不会被社会容纳。所以,森人考虑到世人的眼光,他将夏生的户口放在自己名下,当作养女抚养。而冷子却怀着自私的欲望把照顾自闭症儿子黎的重担加在了夏生身上。如此一来,冷子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更加复杂。冷子和森人的自闭症儿子黎和养女战争孤儿夏生名义是兄妹,实际上成了男女关系。夏生的命运被养母冷子用养育之恩强加给她的情债所左右。由于是战争孤儿,夏生在世上失去了与任何人在血统上的关联。虽然存在和养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然而,养父母却胁迫她照顾黎,并做黎的玩偶。
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啥事都敢干。把别人的孩子抢来给自己的孩子吃,这种事也不稀奇。简直是太恐怖了!母亲真是可怕的自私自利主义者!(……)假如那个人是我的母亲,绝对不会允许那种事情的发生。而那个人却默默地看着,不管不问。正因为黎不正常,所以她更加恐惧——既然我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请帮帮忙吧——她想得到解脱。她假装没看见。——她下定决心要将我们两个人——让我成为黎的同谋——一下子关进洞窟中。[3]55-56
因此,夏生的出生和成长都面临着诸多的人生迷茫。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夏生的人生遭遇,冷子的前夫龙都感到愤愤不平。“在日本,血统可是关键问题。若不能证明你们具有同一祖先的血,谁都不会理你。对于长着白人面孔的人,连问路的人都没有。在选举中也没有人在乎你把票投给了谁。他们可能是客人,不可能是常住民。”[3]162战争孤儿夏生,在日本这个拥有血统崇拜的社会中,找不到可以皈依之所。因而她深陷在养父母为自己编织的复杂的伦理关系网当中。
四、战争孤儿的救赎愿望和认同渴求
虽然夏生一直身处困境,如今已经二十五岁的她对这样的困境源自自己的不伦身世和血缘这点具有深刻的认知。
世上那些俗男人,一旦了解到我是占领兵和贫农孤儿之间生出来的混血,他们反而会蔑视我。可是,若我说我是森人父亲的亲生,不知为何他们就把我当成浪漫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般崇拜我。并且,因为我皮肤的弹性好,汗毛都闪着金光,他们都看呆了,说我的身体和日本人不一样,极力讨好我。……我告诉他们:我是占领兵的种。我还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活证人,是被征服民族遭受强奸历史的活证人。他们反而觉得我不仅幽默而且又有知性,反而为此开心不已。[3]54-55
《浦岛草》的夏生没有像养父母冷子一家那样在战后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反而表现出强烈的救赎愿望和认同渴求。小说中的夏生是个日本通,做翻译工作,专门接待来日本旅游的外国观光团。夏生通过工作默默地找寻反抗宿命的契机。从美国归来的雪枝带给了她一线生活的转机。“不过,我很长时间以来就想见见你,无缘由地……”[3]47对夏生而言,雪枝也好,姑姑也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来自美国。夏生先天直觉让她在潜意识中对从美国来的雪枝充满了期待,并且对雪枝的男友马莱克发起了情感攻击。
夏生和马莱克之间的情感纠葛中暗藏着夏生诸多的复杂情愫。其中之一,是夏生对“美国”抱有难以言表的伦理认知。她对雪枝的隐隐期待、对马莱克的好感中隐藏了她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渴求,即对美国人血统的认同期望。从她的伦理选择过程来看,在众多的男性当中为何非得对姑姑的男友下手不可呢?《浦岛草》中多次叙述了夏生和马莱克之间的相似、相同并且可能相通之处。为此,两人之间的人生体验、身份困惑、生活际遇成了他们相互吸引对方的纽带,并且两个人都因为对方的存在缓解了自己因身份困惑引起的内心焦虑。
从血统来看,马莱克是“混血,是波兰人和法国人的。……现在他是美国人,因为户籍上的父亲是美国人的缘故”。[3]99就成长经历和身份来看,马莱克出生在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在波兰被纳粹杀害,马莱克是战争遗孤。后来,母亲带着年幼的他逃回法国,结识了现在的美国人丈夫。于是,四岁的马莱克在战争遗孤身份之上又加上了养子身份和美国人身份。所以,当夏生遇到马莱克以后,她终于从封闭的自我世界中看到了一丝亮光:发现了和自己具有相同境遇的人——混血、养子、永远的“外人”。夏生和马莱克见面后直白地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雪枝。我企图对你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3]173这是夏生对马莱克情感的表白宣言,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马莱克的回应。马莱克遇到夏生时,同样产生了和夏生相似的情感,并且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夏生的情感表白。
“马莱克仅仅为了夏生,那么强烈地想去广岛参观,这事情让雪枝颇感惊异。”[3]255遇到夏生以后,马莱克不仅在行动上无意识地追逐着夏生。马莱克凭借直觉感到自己和夏生是同类,是自己喜欢的“动物性”的存在。“总之,我有着和动物相似的感伤,偶尔遇到同类的、要自己觅食的那种类型的人,我感觉就像邂逅了伙伴一样。她低沉的呻吟、闪闪发光的毛皮和发红的喉咙深处,无不让我感到亲切。这和看到的不能动的大树不同,不管多么美丽的树,那都不是我的同类。马莱克嘴上说着如此的话,心里想着‘夏生可不是植物性的人’”。[3]259在情感上,马莱克对夏生也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为她在日本的生活和境遇打抱不平。马莱克明显地感觉到夏生在日本遭遇到的歧视:夏生的不伦身世,她同时又是日本战败的耻辱符号,在日本社会永远得不到正常人该得到的尊严和尊重。
从莱利的话中,马莱克知道夏生和她的客人之间很有可能发生诸如肉体的买卖关系。可以想象得到,日本企业好像若无其事地利用着像夏生这样的女人。一想到这里,马莱克不由得非常不痛快。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号称是夏生父亲的森人不可能不知道。也许,明明知道实情还故意让她这么做。马莱克一想到森人还是雪枝的亲人,更加不痛快了。[3]283
因为同是战争遗孤的关系,增强了马莱克和夏生之间的连带感。“我的父亲和夏生的父亲,把自己的种子植入女人体内以后,变成了草丛中乌鸦的食饵。”[3]272不仅马莱克自己感觉和夏生如此靠近,就连附近的老婆婆都期待着马莱克和夏生能有些什么关系。雪枝和马莱克从广岛——京都的故乡之旅结束返回东京后,冷子一家消失了。向冷子家邻居打听冷子家去向的时候,邻居“老婆婆好像知道雪(夏生的生母)以前跟外国兵相好这样的往事,好像把马莱克误以为是夏生已经死去的父亲的亲戚了”。[3]360
由于战争遗孤身份、养子身份和混血的缘故,夏生和马莱克在自然情感上有所共鸣,并由此两人之间产生了难以言表的连带感。这样的连带感是通过马莱克回忆和夏生之间的甜蜜场面描写表达出现的。然而,夏生追求的却不仅仅是马莱克身上具备的自己能够认同的东西。对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夏生来讲,日本人的血统崇拜伦理已经渗入骨髓,不知何时,她想要通过血脉增强生命的存在感。在和马莱克一同去美国还是留下来和黎一起生育孩子的选择中,她最终放弃了去美国。夏生决定利用女性孕育的方式在世界上制造出属于自己的血脉。
五、《浦岛草》中的共同体意识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Community)是一种“感觉”。[6]1两人之间拥有的共同体感觉可以合理地解释夏生引诱马莱克以及马莱克回应夏生的行为。《浦岛草》中战争孤儿、日美混血儿夏生在小说中面临的人生困境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从情感上能够和她产生共鸣的、能够为她的存在感到不平并且付诸行动的人只有马莱克。夏生日本的养父母森人和冷子都各自怀着不同的残酷目的胁迫了夏生的人生。在日本,战争孤儿——日美混血儿夏生难以找到可以认同的共同体。在上文分析她和马莱克相互吸引最后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两人在对方身上“求同”的情感特别突出。即,夏生和马莱克都因为对方的存在感到了某种解放感,这显然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讲的“共同体”的感觉。
《浦岛草》中描写的战争孤儿、日美混血儿夏生和马莱克身上的模糊的“共同体”意识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有对认同的渴望和需求。《浦岛草》的雪枝在美国留学十一年回归日本,尽管是日本人,然而,在小说中雪枝也是外来者,是作家笔下的“浦岛太郎”。常年不在日本生活的雪枝几乎完全失去了和日本社会的连带关系,她感叹日本“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外来者绝对无法进入的世界”。[3]255“她和马莱克一样,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惊奇到目瞪口呆。当然,在对此感佩不已的同时也会摇头表示不满。对她而言,在日本感受到的痛苦、悲伤和开心的记忆少得可怜。她人生中的二十三年里,有十一年的记忆全都在美国。如今,对她而言,或许美国才算得上是故乡。假如她在日美两个国家之间脚踩两只船,中间的水势一旦涨高,自己的身体可能会被卷走。”[3]260那么,是选择和马莱克一起返回美国,还是选择在日本留下,雪枝在最后不得不做出人生的选择。雪枝选择不离开日本,也是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共同体”意识在发挥作用的结果。
《浦岛草》的最后一章“烟雾”的文学原型来自日本民间传说“浦岛太郎”。浦岛太郎经历了龙宫之旅以后思念母亲和家乡,带着仙女送给的玉匣返回故乡,回到故乡的浦岛太郎发现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万般无奈的他打开了仙女送的玉匣,于是,里面冒出一股白烟,浦岛太郎一下子变成了白胡子老头。故乡无疑是人类的共同体之一,浦岛太郎的回归情节最终归根于故乡对他而言的共同体意义。不言而喻,小说中的雪枝是作家笔下的“浦岛太郎”式的存在。安达瞳子指出:“我感兴趣的是大庭氏和植物的关系。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一本书中就出现了大约七十种植物。题目“浦岛草”就不消说了。”[7]8浦岛草的名字是因为这种草长着常常的丝线,宛如浦岛太郎的垂钓的线,所以得名浦岛草。浦岛太郎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情节是回归故乡。所以,作家用“浦岛草”作为小说的名字,其中的主人公的回归意识是理解小说内容的不可忽略之处。
从小说的题目可以得出作家对回归意识的暗示,《浦岛草》中主人公的生活和选择也一直向着回归的方向发展。夏生在处理和马莱克的关系上,在选择是否接近马莱克的伦理选择过程中,两人之间存在的相通之处的确推动她向着马莱克发起情感攻势。然而,当马莱克回美国的时候,虽然夏生也可以跟随他一起去美国,但是,她却放弃了。与美国相比,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夏生已经和日本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连带关系。她下定决心在日本扩展自己的关系,制造自己的存在感。“当我刚遇到你的时候,妊娠反应让我胃里难受。如今,经过了这么一番闹腾,感觉那毒素似乎消失了,浑身都轻松。我肚子里的硬块确确实实在长大。因为有冷子妈妈的教训在前,而且我自身也有证据,我想,唯有在孩子这件事情上,我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办,所以就决定生了。前不久,我才发现怀孕了。”[3]386夏生最后选择在日本生活,在黎的身边养育她和黎的孩子。
分析夏生的伦理选择过程,可以发现决定她选择过程的砝码是血脉,是她对血脉的认同。而且,小说中不仅战争孤儿夏生的选择过程表明了有血统认同的倾向,雪枝最后也决定留在日本,不跟随马莱克返回美国。“当前,她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在她的心思中大概多少带有一些自虐的因素。不是自己对祖国有多么执着,她想切切实实地观察、真正地看到自己本身的根部脉络到底是怎样的。这种感觉和看母亲的阴部、父亲的男根的感觉相似。本可以转过眼去、用块白布盖上、把他们放进棺材放把火一烧,完事以后就可以去异国他乡了。可是,雪枝却想要盯着这些看清楚。”[3]348雪枝心中的“根部脉络”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她努力找寻的“共同体”。
小说主人公在去美国还是留在日本的选择中,夏生和雪枝都选择了日本。夏生背负着养父母的伦理恩情,没有把黎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要和黎一起生养他们的孩子,在世上扩展属于自己的血脉,增强自己在日本社会的连带感。雪枝作为留学多年后返回故乡的“浦岛太郎”式的存在,她回国的探亲之旅实际上唤醒了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日本之根,如今她要留在日本关注自己日本之根的发展。即雪枝像浦岛太郎一样最终回归到故乡。然而,战争孤儿夏生的认同找寻是通过孕育生命的方式建造一个共同体,而雪枝是回归到日本所谓的共同体中。夏生和雪枝对共同体到底是什么虽然尚不清楚,但是,她们在无意识的朦胧状态下均采用血缘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然而,无论她们的形式如何,其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她们都有对认同感的追求,对共同体的渴望。
在国籍复杂、血统复杂、身份也复杂的战后社会,单纯的民族认同、家国认同已经难以囊括人类面临的所有的认同焦虑问题。似乎唯有共同体可以表达这个问题。然而,共同体到底是什么呢?大庭美奈子在十年后创作的《球兰草》,多次提及共同体。但是,作家也是仅仅讲述了什么会让人失去共同体,而没有给出共同体的具体模样。大庭美奈子在《浦岛草》中捕捉到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共同体意识以及人类对共同体的不懈追求。共同体是什么的问题,或许我们从齐格蒙特·鲍曼的解释中得到些启示。
今天,“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的别名。失去的天堂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因而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堂的道路的别名。
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绝不是一个我们栖息的天堂,绝不是那个从我们自己的经历而得知的天堂。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些原因,它才是一个天堂。[6]1
大庭美奈子是日本战后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对她经典作品的解读是理解日本战后社会以及战后女性文学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近年来,伴随着国内日本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和发展,对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情逐步升温,可以说,中国当下的日本女性文学研究面临重要的机遇。
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日本女性日益觉醒,自我寻找、自我言说、自我塑造,女性的生存境界和情感世界,国家、民族、个人身份的认知,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同性和异性之间的关系,生存与死亡、欲望与节制、失节与守节、越界与突围等二元对立关系都成为日本女性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热点问题还包括日本文学中的女性生存状态、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日本文学中的女性解放、二战后的日本女性文学等。[8]
上述引文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当下日本女性文学研究中需要充实和发展的问题。大庭美奈子文学作品对这些问题都有过探讨。其文学中的流亡主题描写二战后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战争新娘,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日美混血的战争孤儿。她们作为大庭美奈子笔下的“无根草”,既反映了战争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态。《浦岛草》流亡主题建构中,作家的流亡意识和回归意识相互交织,流亡的结局主人公的日本认同——延续或找寻日本之根。由此可见,大庭美奈子在《浦岛草》充分发掘女性在孕育问题上具有的先天优势,在主人公身份认同以及“共同体”的建构中凸显了血脉认同意识。《浦岛草》中夏生的孕育行为以及对血脉认同的思考,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对大庭美奈子的“反母性”文学解读模式。在《浦岛草》之外,大庭美奈子还创作了若干家庭主题小说,主要有《铁杉之梦》(1971)、《山姥的微笑》(1976)《寂兮寥兮》(1982)、《鸟啼兮》(1985)等,探索战后日本社会中的婚姻和家庭、家庭主妇、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家庭模式的再建构等问题,为实现日本社会的家庭和谐做出了各种文学探索和尝试。可以说,大庭美奈子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权主义作家。
【参考文献】
[1]与那覇鳪子.総年谱(生活·事项年谱/著作一覧)[A].大庭みな子全集(24)[Z].东京:世界経済新闻出版社,2011.
[2]大庭みな子,平冈笃頼.亡命の文学—创造的言叶と前卫[J].三田文学,1974,(61).
[3]大庭みな子.浦岛草[A].大庭みな子全集(5) [Z].东京:讲谈社,1991.
[4]王新生.战后日本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7]安逹瞳子.本の中の植物——「浦岛草」[A].大庭みな子全集(4) [Z].东京:日本,済新闻出版社,2009.
[8]杨春.人文情怀与格局多元:女性文学研究趋势及其栏目策划——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女性文学研究栏目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2).
责任编辑:杨春
Study on the Theme of Exile in Oba Minako’s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War Orphans in Urashimaso
HOU Dongmei
Abstract:Oba Minako’s literary works are filled with elements of various exiles follow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Oba’s work describes the people who lead a wandering life away from their hometowns without any foundations as “rootless grass”. The war brides in Shabby Museum is such an example of Oba’s“exile literature”, whil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orphan in Urashimaso is another. Urashimaso focuses on one of the remaining problems of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 namely the issue of war orphans. Besides, it reflects on the harms brought by war, women’s fate and life.
Key words:Oba Minako; the theme of exile; Urashimaso; War orphan
DOI:10.13277/j.cnki.jcwu.2016.03.010
收稿日期:2016-03-06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3-0066-08
作者简介:侯冬梅,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276826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2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生态女性批评视域下的日本女性文学研究——以大庭美奈子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