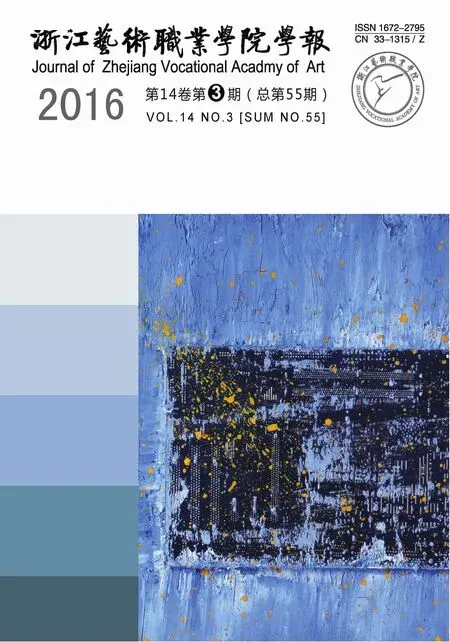女性心灵救赎和个性自由的探索
——中国舞剧女编导的女性身份表达
陈雪飞
女性心灵救赎和个性自由的探索
——中国舞剧女编导的女性身份表达
陈雪飞
中国近现代虽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文化启蒙,女性主义逐渐被人们关注,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触及到艺术领域,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没有得到自由民主精神的洗礼的中国,中国女性没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经历长时间的女性主义运动和文化启蒙,因此说女性的个体解放和自由还没完全自觉,此下谈女性主义是奢侈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反观中国舞剧女性编导在“红色经典”时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改革开放后对女性身分的表达的对比,通过解读女性编导舞剧作品中女性人物视角的不同,可以窥见作品人物主体自觉和作品创作主体自觉如何同化的心路历程,意在描述女性舞剧编导在革命文艺向人的主体性的文化启蒙和人文关怀上艺术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女性主义;舞剧;女性编导;文化启蒙
来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是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掀起的政治思潮之一。从狭义上说,女性主义就是站在性别视角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原则,通过批评和建构来刷新观念。先于女性主义的是个人主义,是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现代启蒙主义运动。人权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权利,是女性主义的基础。西方经过上百年的文化启蒙和女性主义和女权解放运动洗礼,西方女性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自觉程度较高,反映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权解放运动是艺术作品是西方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虽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文化启蒙,女性主义逐渐被人们关注,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触及到艺术领域。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没有得到自由民主精神的洗礼的中国,中国女性没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经历长时间的女性主义运动和文化启蒙,因此说女性的个体解放和自由还没完全自觉,因此谈女性主义是奢侈的。“五四”运动后的现代中国,具有启蒙意义的艺术作品遭遇太多的曲折,从发端之时就生不逢时地遭遇民族存亡的历史境遇。初具启蒙意义的文化艺术转身投入战斗文艺和民族形象塑造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女权是通过男女平等的宪法立法手段得以确定的,这一时期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是革命的典型,但在精神层面上,距离女性思想自觉还很远。自觉是文化的自觉,也可以说是思想的自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20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主义,推崇个人主义与主体性,标举人权、民主和自由等人性主题。很多艺术编导认为我们应该回到“五四”,去走完我们应该完成的过程。舞剧女性编导在舞剧创作实践中,或多或少都在履行这一文化启蒙和人文关怀的责任。
在舞剧创作群体中,女性编导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相对于电影编导男性一统天下的局势,女性舞剧编导的比例还是算高的。因此对女性舞剧编导及其作品进行解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记得鲁迅用“清丽而越轨的笔致”①鲁迅:关于萧红《生死场》评价语句。来形容女性文笔。这一遣词用在舞剧女性编导身上也十分恰当。对女性命运的细腻刻画和关怀是女性编导下意识或者本能的一种行为,也可以说具有潜意识特征。
女性身份的舞剧编导,代表人物有戴爱莲、胡蓉蓉、蒋祖慧、舒巧、杨丽萍、王玫、马家钦、杨威、佟睿睿等。本文从女性编导手下的女性人物刻画为切入点,以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红色娘子军》《胭脂扣》和《雷和雨》为例,解读女性编导舞剧作品中女性人物视角的不同,力图总结作品人物主体自觉和作品创作主体自觉如何同化的心路历程。
一、非女性化身份的塑造
在舞台剧创作领域,从文化启蒙转身为革命文艺服务的舞剧艺术,在新时期初期诞生了一批表现中国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红色经典”叙事作品,其重要特点就是革命和反启蒙性质。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小刀会》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舞剧作品,就其对女性描写而言,其最突出的反启蒙特征就是“非人化”和“非女性化”形象的塑造,是彻头彻尾的革命人物,没有明确男女性别身份的区分。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吴清华、白毛女、周秀英是红色经典作品中女性的典型代表。从人物外在形象设计上看,浓眉大眼、犀利眼神、棱角分明的脸部线条和刚劲的动作等是她们的共性特征。这些在当代人看来适合于描述男性的字眼,是红色经典时期被普遍接受的女性革命形象描摹。女性编导蒋祖慧承担了该剧序幕和第一二幕的编导任务。她编导的序是“琼花逃跑”。在这场戏的编导过程中,蒋祖慧贯彻了舞剧民族化要求,南霸天的狗腿子老四追打琼花的双人舞,解构了芭蕾舞中逐步展开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和双人舞语汇,而是模仿京剧艺术的手法,在剧一开始就把人物鲜明的性格展示给观众,在双人舞的开头用了一个激烈的抄旋子的动作让老四上场,从而将恶霸爪牙的凶恶表现的淋漓尽致。其次是利用人物精神描摹,鲜明而强烈表现了剧中人物的敌对关系,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枫在听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人员在构思之初汇报时发言:“我看《红色娘子军》不错,一是题材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二是该剧的主题歌很好;三是娘子军的故事片很感人,家喻户晓,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1]这段话讲了三个意思,一是芭蕾适合表现女战士,二是主题音乐很好,三是故事容易被人们接受。其实这三点是符合舞剧艺术规律的概括。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主要艺术团体领导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是到位的。就是在当代创作领域,这样的提法还是符合艺术创作要求的。此外,该剧在音乐上采用了海南民歌曲调,把芭蕾舞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交融于民族斗争的现实题材,这正是《红色娘子军》的成功之处。但是该剧在凸显女战士的女性身份表达上,舞剧没有给予特别的强调。在该剧完成初稿后部队领导提出意见,说是娘子色彩太浓,“军”味不足,然后建议演职人员进驻部队体验军队生活两个月后再修改的版本,明显增强了“军”味,因“革命”味更浓受到领导的肯定。娘子军作为在海南当地家喻户晓的一支女性队伍,表现其革命的一面自然没错,但女性有女性特有的性别特征,诸如感情细腻,温柔、忍辱负重等品质,在红色经典时期女性的这些天然品性是没有舞台展示空间的,在那一片红色海洋中,女性的这种天性是被忽略的。
《红色娘子军》在定型为样板戏的过程中,是非女性化形象塑造的凸显和强调的过程。经历若干次的修改,包括对原有的音乐、舞蹈,以至服装、布景,加进了许多概念化的表现所谓高、大、全的东西,删除了一些表现人物个性的优美音乐、舞蹈。甚至因为主演吴清华的演员脸部线条过于柔和而被线条更刚毅的演员代替。在普通意义上,女性人物形象端庄、线条柔和是女性身份的象征,但在红色经典时代的女性,那是不符合需要的。例如,琼花诉苦一场,原来有一段充满觉悟的音乐和舞蹈,因被江青视为太软、太抒情而删除,以一段哑剧代替,大大减弱了女性人物自然的表达。女性人物形象在革命样板戏时期是单一的,纯粹的,除了对地主阶级和压迫阶级的仇恨,没有其他情感的表达。人性的感情被强调到简单归一的非人性的程度。
以《宝莲灯》《小刀会》《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作品为代表红色政权统治下的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我想主要是因为这样三点:一是满足政治实用性,二是兼顾了民族审美习惯;三是做到了文化风格的塑造。做到这些在当时实属不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艺术家满怀胜利喜悦后全身心投入的结果。
二、女性心灵救赎的尝试
舒巧创作的19部舞剧,题材基本上都涉及女性。舒巧偏好于表达女人的剧。有学者甚至认为“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对女性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和性格刻画最终是为了对女性的心灵进行救赎,这是她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最大的人文关怀。
于平先生多年跟踪关注舒巧的创作和心路发展历程,通过对舒巧的舞剧创作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在新进发表的文章《舒巧大型舞剧创作感思》中总结:“谈舒巧的舞剧和舒巧对舞剧的认识,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的舞应当服从于现实的人,服从于舞剧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当代舞蹈家艺术个性的发挥。这其实也是我们感思舒巧大型舞剧创作时最质朴的认识。”[2]结合福柯说的:“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3]来理解这句话,可能更能容易抓住这句话的要核。舞剧叙事内容的历史性要服从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性,说的通俗点则是舞剧人物的性格是创作者眼里的性格,是创作者自己性格的同化。舒巧在自传《今生另世》里也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舞剧中,舞为剧服务,而剧是为了写人,写人是要写人的情感和思想,用舞蹈揭示人的情感和思想。我的理解,这是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创作思路,而非“剧”加“舞”等于“舞剧”的简化思维,简化思维带来的后果是,以为适合舞蹈表演的情节都可以拿来拼凑,或者为了讲述一个貌似感人曲折的故事而编配舞蹈,因此,就会出现“见舞不见人、见事不见人”,甚至连人和事都见不着(看不懂)的现象,这样流于肤浅的舞台展示瓦解了舞剧思想的厚度、深度,能留给观众什么感动和思索呢?”[4]这里她想表达的是舞剧要突出“人”,舞剧是“人”的剧。
另外,她在总结创作体会的文章中对此提到:“舞剧要写人,写人又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记者采访式的客观陈述;第二层是介于客观陈述与主观表达之间;最高层面是以客体为载体表达编导的主观意志。”[5]这段话和于平先生总结的“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结构上升为语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乃至观念的变革,是为着这样一个目标的:写人物——写自己理解的人物——写自己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干脆就是写自己的内心世界。”[2]是一回事。
李碧华的《胭脂扣》是演绎舒巧舞剧理想的重要作品。“李碧华小说具有比一般言情小说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等层面都超越了一般言情小说。”[6]李碧华擅长写激情、浪漫、离奇、诡异交织于一体的“畸情”。将悲情与凄艳发挥到极致。她笔下的女性挣扎于宿命与理性之间,其中倾注了作者对女性境遇与命运的思考也折射出她对女性境遇的反思。从这些另类的非传统女子身上,挖掘另类美,从而实现对传统审美的颠覆,也因此李碧华被誉为新女性主义的视角的代表人。通过对坏女人的变形解构,颠覆男性眼中被欲望化、妖魔化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李碧华笔下她们的多彩生命得到还原,重新绽放。李碧华的女性主义立场还体现在对男性形象的鄙视与不屑,她笔下的男性懦弱和不可信,与女性的坚贞、大胆和执着对比强烈。他对男权社会的道德理想和心理需求进行无情地揭露,这些也正是关锦鹏、张艺谋、陈凯歌、陈果等众多著名影视导演青睐其作品的理由。《胭脂扣》是舒巧继《玉卿嫂》后又一部表现女性关怀的力作。但与原著比较,女性主义立场减弱,或许有舞剧艺术的特征的因素,也有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度因素,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作品在表达女性主义立场上是温和的,不像西方作品那么猛烈。舒巧想表达女性,但在手法上是谨慎的。
舒巧擅长从细节表达人物感情,从寻常小事领略到人生的真实与无奈。“这些年,中国舞剧的创作数量非常多,但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人物面目模糊,感觉雷同?因为没有细节。另一方面,我也经常说:“舞蹈是最容易堕落的!”——最方便的就是用道具、服装、舞美背景的变幻,来哄骗观众。同一段舞,差不多的几个动作,换个场景、换套衣服,再跳一遍,有时候观众也不会较真。这种“通用”的舞,舞剧中很常见的有“悲痛欲绝”舞、“欣喜若狂”舞、“思念若渴”舞、“奋发图强”舞等。这种我称之为“干舞”,没有细节,脱离了人物身分、性格,干巴巴地一个劲傻跳。”[7]她是那种少年老成的作家,一部分来自她的人生经历,另一部分来自她超人的感悟。她的艺术触角远比他人敏感细腻,表现力也惊人的老道,观察力精细而深刻,常常道人之所未道。她在轻描淡写中把那些在寻常人看来毫无意义的身边琐事写得妙趣横生,并让读者看到这些俗事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她看来,真实的人生并没有多少大事,人生就是由这些小事琐事组成的。她甚至远比一般人更能享受这些人生琐事,而这些人生琐事也成就了她的艺术。
《玉卿嫂》是舒巧另一部代表作品,“《玉卿嫂》把民族的、芭蕾的和现代舞的三种因素融合在一起了。因此令人感到亲切而有新意,当然我是指既令人感到传统,又感到对现代派艺术某些原则和语汇的吸收。现代舞往往令人感到语汇晦涩难懂。《玉卿嫂》的成功之一是把具体和抽象、散文和诗结合得好,如庆生与玉卿嫂在小屋里打手、亲抚,这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也很动人,揭示了人物心灵的动作。随着音乐的发展,舞蹈动作进入诗的层次,语汇开始抽象化,这种抽象恰是人物和舞剧编导自己的情感的深化与升华。”[8]女人玉卿嫂在无私付出自己所有之后,看到心爱的人移情别恋,她无奈但坚定地要让自己的这份情感永恒,所以选择了死亡,是与心爱的人一起死。这是那个历史时期女人的选择,看看当代社会的女性,有多少女人在不能掌控自己情感时,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放弃,选择忍耐的远比选择自由的多。
中国传统文学“重情蕴而不执着于事理”,要紧的不是对事物作出如何判断,而是主观上采取什么态度,在于主体精神的确立。看重的是浑涵、旷达、神理超越的精神境界。所谓“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强调创作主体的心态平衡与情志的自然流溢,进入无我同一的境界,进入艺术的自由。隐喻创作者饱经沧桑又平易恬淡的心境。悠然淡泊的体貌下凸显的是作者的自我反省与人格修炼的主体精神。这就是舒巧舞剧创作的核心精神,也是她对中国女性生存现状的表达。
三、自由精神和个性强调
王玫作为当代女性编导在现代舞领域的代表人物、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编导班的创建人之一的身份让她的舞蹈创作带有很多的规定性。首先在舞蹈类别上的定位是现代舞,发源于西方的现代舞在源头上离西方的女性主义比较近。“现代舞的崛起尤其令我触动,以前不曾深及心灵的、对生命模糊的看法得以渐渐清晰起来。现代舞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它作为一个舞种的意义。”[9]她强调内心体验的描述与生命本质的表达。其次,现代舞作为西方解构传统的一种艺术方式,在艺术内核上具有反传统和启蒙意义。因此,她的舞剧创作在思想和文化自觉上应该成为当代舞剧创作人文关怀的先锋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她的《雷和雨》作为例子阐述她在女性身份表达上的独特视角。
《雷和雨》以三个女人的情感为主线,以繁漪与周萍、四凤与周萍、四凤与周冲、繁漪与侍萍四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舞剧需要用象征的方式组织身体语言的暗示或隐喻,如何有所突破是王玫在构思《雷和雨》时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扬舞蹈之长,避舞蹈之短,用舞蹈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舍弃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突出表达人性和给予关怀是该剧的宗旨。按照人物出场顺序自报姓名交代身分,是这出剧的开始。在《雷和雨》的开篇,营造的是时间长达4分钟多、繁漪、周朴圆、周萍、四凤、周冲、侍萍等只有呼吸没有肢体动作的压抑氛围。和传统群舞演员整齐对称在舞台中心的构图不同,《雷和雨》在圆型的空间中,用强烈的、极具张力的动作表达人物间的接触、挣脱、纠缠、对抗、渴望、惊惧、无奈、愤怒。在沉寂中蕴含爆发力的表现方式是现代舞强调的形式感,《雷和雨》正是通过这种自由形式表达自由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对海外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逐渐深入,然而由于海外客源市场统计资料的缺乏,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甚少.目前学界对海外客源市场的研究大多将目光聚焦于省域[4-8]和市域[9-14],对景区景点海外客源市场的研究关注很少[15-17],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海外客源市场的拓展研究更为薄弱.
《雷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体记忆,而王玫的舞剧是唤醒这个记忆的续写和重组的形式。三个女性:繁漪、四凤和鲁侍萍,繁漪极端、彻底,敢爱敢恨的性格,具有鲜明的“雷雨”特征,有那种可以摧毁一切的原始的“蛮力”。她与作家刻意设置的背景氛围始终相通。从一开场时“喘不过气来”的郁热和压抑,到最后的不顾一切的“报复”,一种“雷雨”式的渲泄,她的情绪心态始终与作品的气氛融为一体。繁漪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处在冲突的中心,是她引出了侍萍,又是因为她使周萍、四凤走上绝路。繁漪复杂、独特的形象使她具备主人公的条件。她的性格是两个方向上的极端:极端的压抑与极端的报复,逼到绝路忍无可忍。她最后还是在“宇宙这口绝望的井”中挣扎,无力拯救自己,这就增加了悲剧的层次感与意蕴深度。侍萍坚守自己,执着自己的感情和信念,最终赢得了恒久,但也毁了自己的儿女。四凤明亮的眼睛单纯期待和周萍的感情有所归宿,最终无辜走向死亡。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现实周围似曾相识。所以编导发出哪个女人不是从四凤到繁漪,又从繁漪到侍萍。这是女性编导对女性人物的宽容,也是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剧中的女性似乎难得遇到几缕关注的目光,选择了又再放弃,想要逃脱却又缺乏勇气,她们的命运似乎注定随波逐流。”[10]“‘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只是打破旧习的一个支派。其本身并不是一个有体系的思想根基。甚亦不代表一个成熟、有系统的政治或哲学理论。因此,在评估其价值时,‘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或许应该被看作是当时知识分子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11]正是这种普遍的精神状态的出现,为中国女性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但《雷雨》中的女性处于新与旧的交界处最多只是挣脱了一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对女性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反映在戏剧主题上,则是对女性悲剧的省察与剖析。
从发现自我、追求爱情到顽强跋涉、摸索求生,再到困惑茫然、诘问人性,舞剧女性形象在逐渐觉醒,亦即在觉醒的过程中遇到困惑与求索。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章中曾经告诫男人:到女人那里去之前,先带上你的鞭子。这固然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猜忌,也客观反映了女性绝非生来具有屈从的天性。自有人类以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天然的矛盾,一种绝对的共存,一种永远的纠缠,一种费解的悖论。[12]
王玫用现代舞诠释《雷雨》:“哪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当初没有周冲和四凤的影子?最后又没有周朴园和鲁侍萍的情结?站在繁漪的位置上蓦然两望,世态炎凉透人心髓……如此一个世界不禁让人怀疑就不曾真的轰轰烈烈?既然轰轰烈烈,凄凄清清又从何而来?到底哪个是真?……当我们也都成长了的时候,这才嗟叹《雷雨》里的故事竟然和自己息息相通。”[13]
特纳所说:区分苦难和苦痛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苦痛被界定为“身体在遭受伤害、疾病等打击下所感受到的不幸”,但苦痛有时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女性在分娩的时候,身体的伤痛伴随着的是新生命的诞生的喜悦。女性主义所认为的女性的韧性和忍耐力比男性强,基本上是基于这个层面。苦难则不同,苦难是“涉及到自尊的丧失”。[14]自尊的丧失是女性精神和灵魂的痛苦。王玫抓住“点”,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用肢体动作诠释人物心灵世界的苦痛,具有强烈的现代人审美体验。
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意识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观念、认识和追求如何在历史中呈现的问题。但在既有的历史中,文化建构往往凸现的是男性视角、价值、意识和男性经验。女性的视角、价值、意识和经验则往往是被掩盖与被遮蔽的。
当代中国女性渐渐走出“男尊女卑”传统意识的樊篱,在寻找失落的女性自我中,在宣告女性不再是一个“失声的群体”的经历中完成自己作为当代女性的确认。女性慢慢开始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文化主体,女性人物也开始从边缘走向文化主体的旅程,并从女性主体意识性的自觉走向了人的自由。严格说来,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真正出现以“主义”为特征的女性艺术,但却涌现出一群像舒巧、王玫和杨丽萍这样的才华横溢的女性艺术家。中国女性主义的提法没有西方世界独有的文化语境,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创作更多的是强调感受的独特性和表达的个性化。作品往往只是揭示女性艺术家在“自我探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男性的“话语”。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表达对生命的关切态度。她们关切的“生命”,是指某个人或某类人的生命,对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关注还不够到位。二是她们不再关注那些宏大的与个人情感生活不相关的社会主题,而是更注重挖掘内心资源。从个人经验及至躯体语言中获取灵感,作品更具个性特征。三是她们能从理性分析的角度介入题材,但更注重艺术的感性特征,注重直觉的、感官的呈现。今天的舞剧艺术,我们既可以看到与传统的审美意识相联系的艺术风格类型,也可以看到无论在造型力度上还是视觉强度上都不亚于男性的具有扩张感的风格类型。诗意的、抒情的、浪漫的、唯美的、还是神秘的、富有思想锐气的、直面现实的等作品类型向我们展示了更为广阔的艺术风景线。最终是为了表达“我”是女性,但在“主义”的征途上还需要付出更多。
[1]袁成亮.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记[J].文史春秋,2004(9).
[2]于平.舒巧大型舞剧创作感思[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2(1).
[3]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93.
[4]舒巧.今生另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230.
[5]张莉.舒巧访谈[J].上海舞蹈报,2008.
[6]刘登翰.香港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496.
[7]邢晓芳.王安忆与舒巧谈舞剧创作:细节给灵魂栖息的枝桠[N].文汇报,2010-12-02(12).
[8]徐晓钟.感情的深化与升华[N].新晚报,1988-10-09.
[9]钟瑛.浅谈现代舞舞剧《雷和雨》的现代精神[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6(1).
[10]朱鸿.现代舞剧“雷和雨”倾情献演,看用女性视角全新诠释的名著“雷雨”[J].中国女性(中文海外版),2002 (6).
[1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上海:三联书店, 2001:45.
[12]宋宝珍.传统的祛魅与现代的困惑:两度西潮与中国女性戏剧形象的嬗变[J].戏剧丛刊,2012(3).
[13]于平.无声的雷和不湿的雨一一由王玫的《雷和雨》引发的联想[J].广东艺术,2003(5).
[14]布莱恩特纳.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M]//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90.
(责任编辑:李 宁)
Women’s Spiritual Salvation and Individual Freedom—Expression of Women’s Identity of Chinese Female Choreographers
CHEN Xuefei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n the new period,feminism had been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to and influenced the art field in a positive way.But Chinese women did not experience the feminism movement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s long as the women in Western society.They were not fully conscious of the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freedom.In the cultural context,Chinese female choreographers bear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humanistic care throug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Red Classics Period and expression of female identit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eminism;dance drama;female choreographer;cultural enlightenment
J723
A
2016-05-17
陈雪飞(1971— ),女,浙江常山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戏剧影视学研究。(金华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