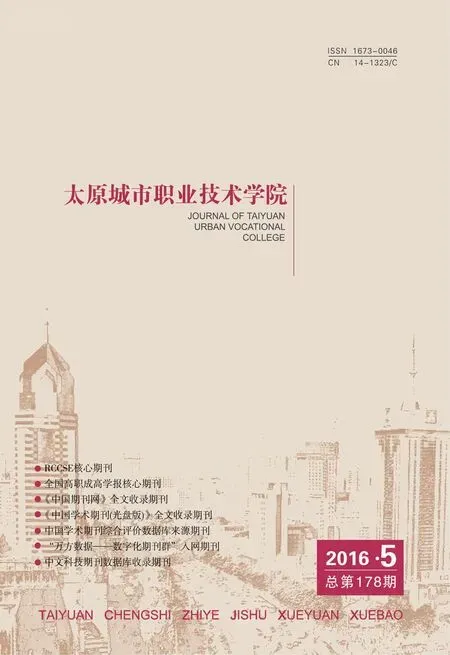论《琐事》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
刘春秀
(商丘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论《琐事》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
刘春秀
(商丘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琐事》是女剧作家苏珊·格莱斯佩尔颇受赞誉的一出独幕剧。它通过对一起凶杀案调查的描写,以平静的口吻和异常简约的笔墨,揭示了无比深邃的社会主题。文章通过对剧中的女性人物进行深入分析,对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以及两性二元对立的矛盾进行揭示。
父权制社会;两性;悲剧命运
《琐事》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格莱斯佩尔的著名作品之一。这出独幕剧短小精悍,全剧只有五个人物出场,故事情节也颇为简单明了。在一个偏远又破落的农场,农夫约翰·赖特被发现在睡梦中被人勒死在家中的床上,而让人诧异的是睡在他身边的妻子米妮·赖特却声称对丈夫的死毫不知情。为了探寻事件的真相,乡村律师乔治·亨德森、警长亨利·彼得斯、案件证人刘易斯·黑尔进入案发现场找寻米妮的犯罪证据。而彼得斯太太和黑尔太太则负责收拾些生活用品给被拘押在狱中的米妮·赖特。
格莱斯佩尔的多数作品以女性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及两性矛盾为主题,《琐事》也不例外。在剧中,男人四处忙碌着搜索犯罪证据,从而给米妮定罪,而两个帮不上什么忙的女人,则絮叨着无关痛痒的琐事。《琐事》表面上看是一出侦探剧,然而,作者无意布局紧张的故事氛围和精巧的情节设置,而是力图带领观众直面更加严肃的社会问题,敦促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格莱斯佩尔用无比冷静和平淡的笔触,透过两个女人的观察和繁琐的对话,貌不经心般地将米妮所遭受的沉重苦难缓缓道来。
《琐事》创作于1916年,当时,整个西方社会依旧笼罩在女性主义意识尚未蓬勃发展前的黑暗之中。不仅仅是戏剧主人公米妮,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成为当时时代环境和社会道德约束的牺牲品。从剧中三个女性角色的身上,观众得以窥探到女性身处那个时代中不得不面临的悲戚和无奈,整个女性群体以其羸弱纤细的身躯奋力抵挡着来自男性社会的摧残和歧视。米妮将丈夫扼死的举动,是她在长期受到身心迫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激烈抵抗,是宁愿不顾代价、与之同归于尽的决绝。
一、痛苦压抑的婚姻
在极为保守的年月,家庭和婚姻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最终归宿。没有婚姻的老姑娘要忍受来自他人的质疑和诟病,然而,步入婚姻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得到幸福的眷顾。黑尔太太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米妮少女时代的美好过往:“米妮·福斯特穿着白色长裙,系着蓝色腰带,站在合唱队里唱歌。”米妮曾经是一个活泼开朗、充满魅力的姑娘。她热爱唱歌,乐意身着光鲜亮丽的衣裙参加集体活动。从米妮·福斯特到米妮·赖特,所改变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随着时光流逝,家庭生活的琐碎繁杂悄无声息地打磨着少女曾经盎然的生机。
从案发现场遗留的未完成的百纳被以及厨房柜橱中的果酱来看,米妮在家庭中一直担当着贤惠妻子的角色。她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家务之中,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地歌唱,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装扮上五颜六色的衣裙。婚后多年没有孩子,丈夫对她的不闻不问以及单调乏味的家事,虽然使得米妮的婚后生活压抑繁重,但她在生活的夹缝中努力追求色彩和希望。遗留在针线篓中的百纳被有着漂亮的图案和整齐的针脚,暗示了米妮对色彩和美的欣赏。从已经死去了的金丝雀身上,可以感受到米妮对丈夫禁止她继续歌唱的无声反抗。如果说米妮是失去自由的鸟儿,那么家庭就是牢牢禁锢她的樊笼。剧本中对米妮家的环境描写,就形象表明了那里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环境。作者将这座房子描写成冰冷、凌乱的所在,丝毫没有一个家该有的温馨。而随后,黑尔太太的话更加深化观众对米妮生活环境的印象:“我从来都不喜欢这地方。也许因为它在山谷里,看不到它的通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个偏僻的地方,而且一直都是。”
丈夫赖特对米妮的控制使得米妮如同一朵枯萎的花,怀着麻木的心境日复一日等待最后的凋零。在生命中最卑微的乐趣也被夺走后,米妮最终忍无可忍地爆发出她一再被压抑的愤怒。不止是米妮,对所有女人来说,一旦结婚就只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贤妻良母的本分。黑尔太太和米妮是邻居,却苦于家务琐事的纠缠,一直无法前来探望,就连身份尊贵的彼得斯太太也因为丈夫是警长,被男人们取笑说是嫁给了法律。如果说女人是商品,那么男人就是标签,是烙印。
二、被轻视和剥夺的话语权
除了利用家庭琐事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男性同样剥夺了女性发出声音、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且不说案件的关键人物米妮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场,完全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在戏剧中有这样一处细节:证人黑尔向律师描述案发当天的详细情形时,提到自己进入赖特家中是为了劝说他同意共同装一部公用电话。黑尔首先遇到的就是米妮,但他却没有同米妮讨论装电话的想法,而是执意要见赖特。这一情节鲜明地暗示了米妮在家中是没有地位和发言权的,一切都要丈夫做出决定才能算数。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黑尔在潜意识里认为同女人谈论这种问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一细节显然对于探究米妮的行凶动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律师却极为不耐烦地打断了黑尔的描述。与更为重要的证据和线索相比,他显然认为这种无关紧要的琐事对于案件侦破没有任何帮助。观众最开始对米妮的了解完全是建立在男性对她的描述之上。通过黑尔太太和彼得斯太太两人的观察和回忆,米妮才逐渐摆脱了男人对她杀人凶手的单纯定义,观众也从感情上自觉地接受了米妮从犯罪者到受害者两种不同身份的转变。
在写作手法上,格莱斯佩尔十分巧妙地采用了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推动故事的发展。戏剧反讽简单来说是指在读者(观众)、作者或叙述者都已经充分明了故事原因和走向的情况下,作品中的人物却对此一无所知。韦恩·布斯对此有更加直接简要的表述:“其最简单的形式……是直接描绘一个人物如何曲解另一个人未说出的思想或动机。”在整出戏剧中,女人们在男人面前总是噤若寒蝉,只有当男人们离开后才会畅所欲言。男人们一边为搜集米妮的犯罪证据,进而侦破案件这件“大事”忙碌,一边不忘嘲笑和奚落她们只知道在家务这种琐碎的小事上费心思。这实际上反应了男权社会一种极为荒谬的悖论:他们一方面用琐碎繁杂的家事锁住女性的身心;另一方面,却又大言不惭地讽刺着女性的目光短浅和毫无建树。在故事的开始,警长彼得斯就不无嘲弄地说:“真搞不懂女人啊!都已经被控谋杀了,收押期间还在担心她的果酱。”黑尔也多次嘲笑女人只爱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十分讽刺的是,男人们跑上跑下毫无收获,被他们认为没有头脑的女人们却从许多不起眼的小细节中揣测出了案件的真相。她们从百纳被上原本漂亮、平整却突然变得歪斜的针脚窥探到米妮一定是受到十分剧烈的心理刺激;从被扭断脖子的金丝雀身上感受到米妮在生活中的唯一乐趣被剥夺后绝望愤怒的心境。作者对戏剧反讽别具匠心的运用,使得男性的无知、自大受到无情的揭露和嘲弄。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瑞盖莱(LucyIrigaray)认为:“西方的主导话语对女性十分虚伪,一方面,把女性当成负面因素,作为自己的反面;一方面,又以男性代表女性,使之完全失去自己的身份。”她认为女性语言具有“发散”特征,所以男性认为女性逻辑混乱,表达含糊,殊不知,女性天生就具有多元性,她们说话充满差异,意义表达更加微妙。在《琐事》中,男性经常采用命令式口吻同两位太太说话,他们喜欢决定和控制谈话的内容和主题,并将自己的想法和评论粗暴地付诸他人。两个女人的对话则给人一种犹豫、凌乱和词不达意的感觉。同男性话语的强势相比,女性话语权明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值得庆幸的是,两位女士恰到好处地利用了男性对女性话语的轻视与不屑,以女性间的理解和默契,成功地帮助米妮掩盖了相关罪证。
三、被流放的女性群体
男性自诩是俗世的上帝,他们乐此不疲地创造出适用于自身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和思想体系。长久以来,女性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社会中的流放者,游离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外。在男女地位极为不平等的父权制社会,女性群体就别无选择地成为这些制度和规范的祭品。《琐事》一剧是作者根据一个真实案件进行改编的。在当时的案件中,虽然法院找不到明显的犯罪证据,也给不出有说服力的证词,却仍旧将米妮的原型赫塞克夫人定罪。因为赫塞克夫人曾经未婚先孕,又曾经向邻居抱怨过婚姻不幸,法官就因此判定她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具有杀人动机。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论断是荒诞可笑的。很多时候,冰冷又残酷的法律同其缔造者一起,对本就受到压制的女性群体进行毫无悲悯的迫害。
作为男性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准则的受害者,米妮所遭遇的不公对待在剧本中是有迹可循的。黑尔太太对米妮在案件刚刚发生就被捕入狱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把她关在镇上,我们却到这儿来,为的是利用她自己的房子来给她定罪。”且不论事件真相到底如何,所谓的长官们已经先行认定米妮谋杀亲夫的罪行,唯一欠缺的就是能给她定罪的证据而已。黑尔太太随后发现了被扭断脖子的金丝雀,这对米妮十分不利。当与彼得斯太太讨论如何处理这一罪证时,黑尔太太犀利地指出:米妮虽然犯下罪行,但这是她积年累月在不幸婚姻中所承受的压抑所造成的。米妮也是受害者,从一个鲜活的少女成为麻木的妇人,丈夫正是扼杀她鲜活灵魂的侩子手。因而黑尔太太发出不满的抗议:“这是犯罪!谁将来惩罚这罪孽?”法律只看到米妮所犯下的罪过,谁又能为她的不幸讨公道?彼得斯太太一开始努力尽着自己作为警察妻子的本分,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应该无条件遵守。但基于对米妮的同情和理解,她逐渐对一直坚持的法律产生质疑,并最终加入了抵制男性道德价值约束的阵营。
[1](英)苏珊·格莱斯佩尔.琐事[J].潘静,译.译林,2008(4): 162,163.
[2]许丽莹.《琐事》中两性关系的对比[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9).
[3]王若兰.琐事颠覆男权:论《琐事》中的女权主义意识[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4]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I106
A
1673-0046(2016)5-01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