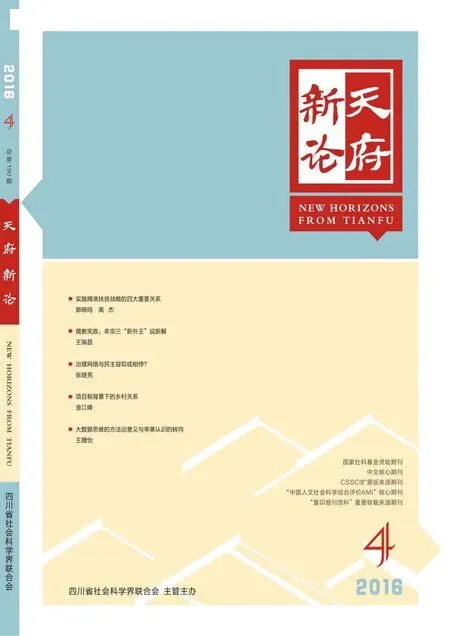视觉快感与狂欢体验:社交网络成瘾的社会学探索
田林楠
视觉快感与狂欢体验:社交网络成瘾的社会学探索
田林楠
摘要:以“低头族”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成瘾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已有的研究详细地勾勒出了哪种类型的用户更可能社交网络成瘾的图谱,但未能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本文认为,“祛除巫魅”的理性化进程及其所带来的目的论宇宙观的瓦解使现代人陷入到虚无和无聊的存在性体验之中,催生了一套依靠外在新奇事物来获得即刻满足和填充空白自我的存在性需要。社交网络的非主题化、实时更新性、碎微化和真人秀特性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景观世界,能够随时带来直接的视觉快感;社交网络的阈限性则可以让用户在狂欢体验中暂时摆脱单调无聊的日常生活。此外,社交网络成瘾还可能与互联网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
关键词:社交网络成瘾 虚无 无聊 视觉快感 狂欢体验
一、问题的提出
灵长类动物的社交性行为 (social behavior)占所有行为的比重从20%到90%不等,其中只有简单的社会组织的环尾孤猴最低,被认为是相对高级的社会动物的豚尾猴和残尾猴最高,〔1〕而作为最高级社会动物的人类现在被认为正面临社交网络成瘾 (SNSs addiction)的问题:Facebook、微信等的用户们可能过度使用社交网络,其症状与物质上瘾几乎无异。〔2〕无论社交网络成瘾这一判断在医学和社会学上是否成立,人们确实在社交网络中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微信平台数据化研究报告》发现“微信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中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的次数超过10次,而每天打开微信超过30次的微信重度用户比例高达24.9%。①该报告基于腾讯科技、企鹅智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于2014年6月对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微信用户所做的抽样调查,详见http://www.woshipm.com/it/133777.html。佳能电子公司社长酒卷久甚至写了一本名为 《不要一大早就刷微博》的职场指南。与此同时,调查显示,人们手机上使用时间和打开频次最多的APP前几位无一例外都是社交类应用,②详见https://www.techinasia.com/top-smartphone-mobile-apps-in-china/和https://www.yahoo.com/tech/new-study-says-we-pick-upour-smartphones-1-500-times-a-99412542979.html。无怪乎会出现所谓“低头族”(Phubbing,由phone和snubbing合成)现象,即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而冷落了所处场景中的其他人。因此,本文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何以会对社交网络如此依赖?是什么导致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点开社交网络,乐此不疲地浏览“好友”更新的状态?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一是从用户的性格特征上寻找原因,具体来说,是以各种心理量表为基础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外向性程度高、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程度低的用户具有更高的社交网络成瘾趋势,〔3〕高自恋和低自尊的用户更可能在社交网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4〕其次,还有学者关注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性与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例如,有研究发现相对于神经质的女性,神经质的男性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交网络;〔5〕第三,从个体的情感体验或心理状态出发,佩林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在社交网络中寻找归属感与社交网络成瘾密切相关,〔6〕还有研究发现孤独感与校内网的使用频率及每次使用时长显著地正相关。〔7〕总结而言,已有的研究详细地勾勒出了哪种类型的用户更可能社交网络成瘾的图谱,但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科尔曼所批评的“个体行动主义”的问题,“变量间的统计相关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事件之间有意义的关系”,〔8〕最终未能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或未能进行真正的病理学分析。〔9〕
根据使用—满足理论,受众之所以选择使用某种媒体是因为这一媒体满足了受众的某种社会和心理需要。〔10〕因此,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实质性的解释,首先要对社交网络的社会性功能或社会性意蕴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要切实把握时代背景下个体微妙而真实的社会心理需要或精神状况,并就个体心理需要与社交网络的社会性功能之间的使用—满足关系进行分析。
二、社交网络:当代人的“拱廊街”与“狂欢广场”
波伊德和艾里森坚持认为社交网络应该是social network sites,而不是 social networking sites,因为networking强调的是关系——尤其是与陌生人的关系——的建立,但这无法使社交网络区别于其他以电脑为中介的沟通方式;〔11〕相反,他们认为社交网络的区别性更在于能够使参与者对已经建立联系的“用户生成的内容流”(streams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s)进行消费和互动。〔12〕因此,本质而言,社交网络就是彼此加为“好友”的用户之间通过评论、点赞、转发等方式就各自生产的内容进行互动的网络空间,其区别性并不在于“加为好友”,而在于“各自生成,互相观看”。就此而言,社交网络中不再有制作者—消费者和演员—观众之分,并且社交网络本身也不再是一个播放、传播由少数专业人士制作的文字影像的媒介,而是一个全 (网)民参与和聚集的网络社区。因此,社交网络的规定性特征一方面在于其内容生产的“各自生成,互相观看”,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构造方式的“全 (网)民参与,众声喧哗”,而这正在影响着社交网络的社会性功能和效应。
首先,在社交网络中,我们所观看和凝视的,正是“好友”所生成和发布的。在创立伊始,Twitter将其自身定义为一个回答“你正在干什么”的应用,而我通过观看我的朋友们的实时更新来获知,并且我看到的是一个限制在140字以内的短讯——Twitter希望用户们能迅速地、立即地、频繁地回答这一简单问题。在微信朋友圈中,我们可以“发现”(微信将观看朋友圈的行为称为发现)好友日常生活的点滴踪迹——购物、吃饭、感冒、加班、看演唱会,好友日常生活的情境片段一一散落于此。可见,在社交网络中,好友提供给我们的或者说我们所观看到的内容或信息一方面具有非主题化的倾向,呈现的是每个人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用户们所关注的五花八门的内容,而非基于同一主题的共享和交流;另一方面则是更新的不间断性,有学者将其称为社交媒体中纪录片式的生活风格(documentary lifestyle),个人生活的每个瞬间都被频繁地分享到社交网络以回答“我正在干什么”。①Jacob Silverman.Pics or it didn’t happen’–the mantra of the Instagram era,http://www.theguardian.com/news/2015/feb/26/pics-or-itdidnt-happen-mantra-instagram-era-facebook-twitter,2015-05-26.第三,社交网络如微信中的信息构成还呈现出碎微化特征,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关联的信息不再是主导的信息形态,而是代之以短小但数量惊人且快速传播的微型碎片化信息。〔13〕第四,用户对于“我正在干什么”的详细记录和报道也使得社交网络具有了“真人秀”的特性,观众可以随意进出表演者的所谓私密生活和真实自我。
由此,社交网络用户基于各自的时空坐标、审美品味、当下情境“啁啾”(twitter)自己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使社交网络中川流不息着碎片性的、令人目不暇接的各式内容,每当用户打开社交网络,总有永不枯竭的“新鲜事”(人人网将好友的更新状态称为“新鲜事”)在手机屏幕的另一侧实时滚动,就像本雅明笔下让闲逛者(flaneur)们流连忘返的“拱廊街”。在这一“小型世界”中,丰富的“展品像一段段色彩斑斑的长诗”,〔14〕行走于其中的人们遭际着很快出现而又很快消失的各种意料不到的现象,而在社交网络中,用户们也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中目不暇接。
其次,在电视、报纸、门户网站等“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播放型媒介中,用户只是一个被动的观看者,而在作为Web2.0产物的社交网络中,用户们不仅“观看”而且“使用”,即社交网络不再仅仅是“信息源”,而且成为了“参与性的平台”。〔15〕因此,在社交网络中,被动的观看者获得了自主性和主动性以及互动的空间,社交网络本身也成为一个用户在其中聚集和互动的虚拟社区。而在社交网络这一虚拟社区中,虽然用户并非以匿名性的方式互动,但其身体的无需直接在场 (因此免除了面对面互动的可见性及其带来的各种限制和约束)、行动的脱域性 (因此行动不再处于带有社会结构烙印的社会空间及其间惯常的社会关系之中)和互动的异步性 (因此互动卸除了同步互动中的礼仪束缚和紧迫性)仍然使进入社交网络构成一个“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通过仪式指明并构成状态间的过渡”,它“意味着个人或团体离开了先前在社会结构中的固定位置或一套文化环境”。〔16〕因此,进入社交网络就使用户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摆脱了地方性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压力和角色期待,此时,“例行生活的规则和限制有一些为之松动,被其他的行为规范所取代……这就有可能带来新鲜刺激的交往形式和玩乐形式”。〔17〕在社交网络中,这就体现为自黑和卖萌 (如早上上班时更新状态“快点起床,工头叫你搬砖了”)成为常见的话语策略,戏谑性甚至粗鲁的遣词 (如“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天了噜”、“亮瞎了”)成为主要的话语形式,也即社交网络的阈限性催生了一种新的不拘形迹的“言语生活形式”,而这是“对官方智慧、对官方‘真理’片面严肃性的欢快的戏仿”。〔18〕
社交网络的全民参与性和能动性、与日常现实生活相隔离的阈限性以及其话语体裁的戏仿性和解构性使其成为当代人的“狂欢广场”:在“全民性”和“节庆性”的狂欢广场中,人们取消了日常生活,而进入到了第二个世界、第二种生活也即一种对日常生活戏仿之中,这是一种由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在官方世界的彼岸自我建构的生活,“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充斥其中,渗透着也制造着狂欢式的世界感受。〔19〕
那么,作为“拱廊街”和“狂欢广场”的社交网络何以导致当代人对其如此依赖,甚至沉溺其中难以自拔?这首先需要追溯到当代人的存在性体验和精神状况。
三、从虚无到无聊:现代人的精神状况
现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魅”,在这一“通过计算掌握一切”的理性化进程中,科学以经验观察、逻辑推理和数量计算进行的实证探索取代了神秘的和浪漫的神话、宗教和哲学对宇宙和人类社会所做的目的论解释。〔20〕但是,目的论宇宙观不仅是一种解释体系,更是一种坚实的心理基质,它赋予人类生活从生到死的所有普通和特殊的事务和经验以意义和正当性。〔21〕因此,科学的实证探索在解除了这一目的论框架的魔咒,使人获得现代自由的同时,也使现代人的生存碎裂为苍白、干瘪且互不相连的片段,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也没有了本体论的支撑和先验的承认,而是沉沦为冰冷的手段—目的计算,“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22〕
现代人的生活因此日益狭窄和平庸,不再渴望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而是成为追求“贫乏和肮脏,以及一种可怜的惬意”的“末人”,他们“发明了幸福”,白昼和黑夜里都必须找到自己“小小的快乐”或“丁点乐趣”。〔23〕除魅后的虚无和怀疑不仅导致人类失去了渴望超越自身的东西的能力,而且使人类失去了“历史延续感”,只为目前和当下而活,“人们不断受偶发欲念的驱使,抛弃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只想尽快实现眼前的一些小欲望”。〔24〕换言之,现代人的生命活动日趋封闭于片段性的当下和狭隘的自我,不再拥有、也不再渴望由于与他人、与其他造物、与过去和未来的有机联系和强烈共鸣而产生的丰富而深刻的生命体验,而是寻找即刻的满足,没有耐心去体味、去沉潜涵泳,注重的是心理和情感体验的速度、烈度和强度。
与这种狭隘平庸的生命体验以及追求当下即刻满足的心理情状相伴随的则是无聊。“无聊时,并不是毫无作为让我们感到空虚,恰好相反,我们几乎总在行动,即使是看着一幅油画慢慢变干。空虚感来自于意义的虚无”,〔25〕在此意义上,无聊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性症候,正是现时代精神状况的虚无导致了现代人的普遍无聊。前已述及,从伟大的存在之链中脱嵌而出的个体一方面摆脱了蒙昧主义,主体性得以觉醒,另一方面也失却了整体性宇宙秩序所赋予个体存在和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觉醒的主体对于意义的需要只能依靠自己去建构,但这个除魅的世界里除了快捷而廉价的临时货色,一切坚固的、意味深长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意义需要的无法满足和价值的阙如让个体无所适从,自我和世界都变得贫瘠、苍白、混沌一片,无论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是毫无兴味的,时间成了可怕的囚笼和不得不打发的东西。换言之,对现代人而言,在没有外物填充或刺激不足的空白时间里直面自我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理折磨,此时的自我是清醒和自由的,但却没有目的和方向,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此时任何刺激性的感官体验对自我都是一种解救,尽管只是暂时的。
总之,在这个由科学和技术支配的“力学化”和“数学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沉沦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之中,深感空虚与无聊,用尽各种手段去寻求意义的满足,但日益狭隘化和平庸化的现代人“手脚被束缚,思想被禁锢”,只能暂时性地为自己找到“可怜的惬意”。然而,在这些片段性和境遇性的“小小快乐”之后,人们仍要面对那绵延无尽的存在性无聊和虚无的折磨。因此,更多的、更随手可得的、时效更为长久的乐趣或感官刺激成为了现代人的必需品。同时,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生活的外在化,内在的虚无和现代技术文明的成功“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人们企图通过对新奇事物的贪婪占有来驱赶无聊和空虚,〔26〕其结果就是克尔凯郭尔所预言的新闻界正在成为一种“精神的王国”,“人们阅读日报的三四个版面、收听广播新闻,或者夜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明早的新闻,新闻事业成了这个时期的巨神”。〔27〕对当代人而言,社交网络则接替或涵盖了新闻事业而成为新的精神巨神:无论是地铁里的几十分钟时间,还是电梯里的几十秒钟,不管是在车站等车,还是在超市排队,甚至在马路上行走,人们都将头“埋”在微信朋友圈里。
四、社交网络中的心理体验
在鲍曼看来,“电子设备满足的需要并不是它们自身造就的;它们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一种已经充分形成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和显著”,〔28〕因为技术并不是脱离于社会脉络仅仅依靠技术自身的逻辑而出现并流行的,相反,技术是对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特定目的和图景的追寻和发展,并且这些目的和图景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性的需要。〔29〕就此而言,人们对社交网络的沉溺症状之明显正是因为社交网络为现代人对获得当下即刻满足的需要和逃出存在性无聊之禁锢的需要提供了可能和出口。因此,在本节我们将就作为当代人“拱廊街”和“狂欢广场”的社交网络是如何满足现代性状况下个体的这两种存在性需要进行分析。
(一)景观世界中的视觉快感
当闲逛者 (flaneur)们走进拱廊街,他们所流连忘返的或者说诱惑他们进入其中的东西,并不在于具体商品的某种功用或特定人物的某种魅力,而是在于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刺激体验,“这些人 (指闲逛者,引者注)走进人群并不是为了功能意义上的有效前行,而是为了享受人群带来的簇拥和惊颤”。〔30〕同样,人们对于社交网络这一当代人的“拱廊街”的着迷和依赖也并不主要在于它能否为自己提供制作精良的视听内容、全面及时的信息或深刻的评论,而是在于它是一个随时可以进入并有各种新奇的景观可以观看的世界。
社交网络对于用户的吸附性首先在于其内容的非主题化使它更多的是一个观看性的视觉空间,而不是内容性的新闻或信息中心。具体来说,在社交网络出现以前,我们是通过分门别类地或主题化的方式接收信息的,不必说报纸和电视,仅以同属互联网一代的大众媒介如门户网站和论坛而言,他们的内容总是按一定主题而组织起来的,如门户网站新浪是分新闻、体育、娱乐等版块,而天涯论坛也分娱乐八卦、情感天地、国际观察等版块。但社交网络的内容不再是大众媒体和专业人士按照市场需要以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的,其形式也不遵循文化工业中那种标准化的思路和模式,而是每一个用户根据自身喜好、一时之兴甚至冲动随意发布。因此,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或内容呈现一种无主题的碎片式的混搭,其排列组合完全随机任意,内容或信息之间只有时间上的偶然联系,因而也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状态。在社交网络之前,人们是按照索引去寻找特定信息或观看特定内容,人们打开新浪主页或天涯社区的主页,是带着特定的内容期待或者至少是主题式的内容期待的。但点开微信、Facebook的APP时,用户们则并不意图从中获知或观看到特定的内容,或者说人们的心理预期并没有任何内容指向性,进入社交网络的页面进行观看这个动作本身就能够带来满足,就像酷爱逛街的女性不带有任何具体购物目的地在商场中闲逛本身就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快感。此时,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或内容更多的是作为被观看的景观或奇观(spectacle)而存在,而不是作为被阅读、被理解的新闻或信息而存在。换句话说,恰恰是社交网络中内容和信息如碎片一般毫无规律、毫无主题地散落和堆积使其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视觉空间,其中的文字、图片所构成的景观作为一个纯粹的观看对象为用户提供着直接的、即时的、接连不断的视觉快感和心理刺激,而至于这些文字和图片作为观看对象之外的内容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则是第二位的。
其次,社交网络的吸附力还在于它所构成的景观世界是实时更新和动态性的。前曾述及,外在世界的除魅和内在世界的虚无使得现代人不再关注行动的延续性和意义的整体性,而是更渴求当下即刻的满足和心理体验的刺激性,因此,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和永不重复的对于感官而言是新奇的事物。按照克尔凯郭尔的划分,这是一种按照“审美模式”生活的人,“他的生活状态是典型的漫无目的。他只‘为眼前’而活,总是通过享受、兴奋、兴趣去打发每个瞬间。他不会献身于任何永恒或清晰的东西,而是消失在感官的‘即时’中”。〔31〕不断更新和碎微化的社交网络则正好为人们的感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事”或曰景观,社交网络中的事物永远只在指尖划过屏幕的瞬间昙花一现,在用户的目光捕捉到它的同时也就让位给另一条“状态更新”。因此,在社交网络中的每一个即时的当下,人们都在体验着新的也因而总是有趣的事物。社交网络的运营商也意识到只有社交网络中流通的信息流能够永无止境地实时更新才能维持甚至增加访问量,其竞争力的核心就在于能够“发布越来越新鲜,越来越丰富的信息”。Facebook公司面对Twitter的快速发展做出的应对策略就是“提高数据流动速度”,并向其用户保证,Facebook将会“继续让信息以更快的速度流动”。〔32〕
第三,穆尔维认为电影带来的快感之一便是通过将他人作为观看的对象置于自己控制性和好奇的目光之下,从而使观看本身就成为快感的源泉,〔33〕而社交网络的真人秀特性也使得用户在观看好友发布的日常生活的断片中获得视觉快感。“社交网络的核心是个人信息的交换。用户乐于展示他们个人生活的私密细节,贴出准确的信息和分享一些图片”,鲍曼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在忏悔室里安装了一个麦克风——个体的秘密和隐私被主动地放置于公共空间供他人观看和审视。〔34〕因此,社交网络是这样一种空间:即使彼此之间互为陌生人,只要互相在程序上加为“好友”,就自动获得观看对方主动展示的日常生活的资格。这在Instagram和新浪微博这种有大量名人和网络红人存在,又可以单向关注的社交网络中尤为明显,有些网络红人甚至意识到其中的商机,通过絮絮叨叨地讲述或暴露自己的日常生活来吸引粉丝。①《GQ智族》杂志所做的 《段子手的权力游戏》报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使用这种策略获取粉丝的段子手称为日常派,以新浪微博的“粽粽粽粽粽粽粽”和“休闲璐”为代表,“休闲璐写的也全是日常生活。她记录了自己在泰国游玩的经历,以及自己结婚与离婚的过程。她妈妈这么评价她的微博内容——‘不要老在网上写月经,多写写高雅的事情’,但粉丝就是买单”。就此而言,社交网络的吸附性还在于它可以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存在于“窥视的幻想”中的视觉快感。
总之,在社交网络中,人们可以在观看他人生活的断片和不断更新、永无穷尽并因此就感官而言总是新奇的各式景观中获得视觉快感,这既满足了也使现代人追求即刻和强烈情感体验的存在性需要变得明显可见甚至非常醒目。
(二)戏仿世界中的狂欢体验
无聊就是自我成为一个醒目的问题,人们不知道在这没有外物填充的的时间里如何安放自我。对于当代人而言,社交网络则成为人们在无聊的并且是无所适从的碎片化时间里十分急切的去处。人们上瘾般急切地刷着社交网络,正是人们在社交网络中可以获得甚至自己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单调无聊的日常生活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和“集体欢腾”,〔35〕为身处无聊时间囚笼里的人提供了出口。
在费瑟斯通看来,虽然现代社会带来了商品的过度膨胀,但这并不意味着涂尔干意义上的欢腾力量和神圣性就消逝殆尽了,“现代社会绝不是一个符号匮乏的世俗物质世界,商品、产品及其它事物也绝非被当作纯粹的‘使用物’”〔36〕,相反,艺术、消费文化场所与景观及电影电视等媒体中保留了大量被改头换面了的“狂欢”要素,在电视转播、音乐节等具有节日性气氛的热闹景象中,“常规性日常世界转变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神圣世界……它如同蓄电池一样,为较为世俗的日常世界中的人们,提供炙热的情感源流”。〔37〕而各色人群聚集其中,彼此互动方便快捷、线下世界的各种约束和控制不同程度减弱、充满着戏仿性话语形式的社交网络与主题乐园、音乐节、夺冠游行等“有序的失序”的场所一样,形成了一种“集体聚合”的欢腾力量和狂欢体验。
“狂欢——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戏的演出”,〔38〕而在“各自生成、互相观看”的社交网络中,人人都是主动的内容的生产者和热烈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报纸、电影或门户网站中被动的消费者和观看者,而且这一空间的阈限性特征和时空脱域性使得所有人可以同时聚集在屏幕这一尺寸之地,并以一种戏仿语言和“民间诙谐文化”的体裁,不拘形迹地分享、表达和互动,互相传染、激荡和放大各自的情绪和感受。在微信朋友圈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所有人用同一个流行语或“梗”刷屏的现象,比如发状态更新时都要加上“那么问题来了”,“元芳,你怎么看”,甚至十分粗俗的“我真是日了狗了”等诸如此类的流行语,或者特意以流行语来造句,如某明星出轨事件期间,朋友圈中就充斥着“吃饭虽易,减肥不易,且行且珍惜”、“上课虽易,听懂不易,且行且珍惜”这种格式的句子,每个人都热情而兴奋地投身于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狂欢之中,赋予本来平淡无奇的词语和事件一种爆炸性的效果,从而硬生生地使每个人都获得一种节日氛围般的狂欢体验——这里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件发生,词句本身也毫无深刻意涵,但所有人整齐划一的戏仿性或恶搞性的再创造和使用或者仅仅是大量的病毒式的重复就足以使其获得巨大能量。这种狂欢体验在那些流行语或“梗”的新鲜感丧失之后也迅速回落以致于心生厌倦,但社交网络会迅速出现另一个话题供大家狂欢,当由范冰冰引爆的“我们”式照片的狂欢淡去之后,“反手摸肚脐”的病毒式戏仿和滑稽模仿 (travesty)又接踵而至,“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也是没有终结的……狂欢体的形象是不断重生的”。〔39〕
社交网络中的戏仿 (parody)不仅仅发生语言层面,而且是把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上去“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降格和转移到“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40〕或者说就是把渗透着主流价值意识的严肃深刻的东西进行贬低化和民间化的解构和颠覆,从而以一种颠倒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作为官方日常世界的戏仿性世界。在社交网络这个戏仿和颠倒的世界中,用户暂时摆脱了社会所定义和规训出来的主体性,剥离于那种“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沉浸在一种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脱离常轨的”和“充满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的生活之中,〔41〕从而获得一种“狂欢节式的自由瞬间”与自我的“解脱与放松”。〔42〕
总之,社交网络中的这种能量巨大的集体狂欢体验对于身处无聊中的用户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使其在压抑、平淡、无精打采的日常体验之外获得一种强烈而直接的快感,并使其被社会结构化了的自我获得暂时的解脱。因此,人们不仅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里迫不及待地要打开微信,甚至在工作和学习时也难以集中精力,以至于需要频繁中断手头之事去看一眼朋友圈里的新鲜事,从狂欢体验中获得暂时的能量或者说在狂欢中“再生和更新”之后再继续手头之事。
五、社交网络“成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麦克卢汉看来,那种以为媒介只是工具,媒介将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人如何使用的观点是典型的“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相反,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用户“行为的尺度和形态”不可避免地被媒介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控制。因此,媒介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其内容对人的意见和观念的改变,而且是媒介本身“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43〕就此而言,人们对社交网络的着迷和依赖除了上述的情感/心理体验原因之外,还与互联网这一媒介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印刷媒介的出现,使得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口耳相传的媒介模式所塑造的非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文化特性,〔44〕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使得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就位于社会、科学和艺术中心的“线性思维正在被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取代,这种新模式希望也需要以简短、杂乱而且经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发信息,其遵循的原则是越快越好”。〔45〕换句话说,构成当今世界运行基础的互联网媒介可能正在改变人的存在样态,而所谓的“社交网络成瘾”也许只是一种正在显现的新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简短、杂乱和爆炸性的信息收发方式正是碎微、非主题化和不断更新的社交网络的基本运作方式。
此外,当社交网络的用户数量不断扩张,社交网络的基本功能不断拓展,如微信在社交网络的基本属性之外还加入了打车、购买电影票和支付等功能,其结果就是人们的线下人际关系和线下活动日益复制和集中到社交网络之中,社交网络正在成为当代人的另一个日常生活空间,甚至居留更长时间、投入精力更多、完成活动更多。那么,随着互联网以及社交网络对日常生活基础和个体思维方式的进一步重构,我们今天以不解甚至怀疑眼光视之的所谓“社交网络成瘾”会成为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吗?
参考文献:
〔1〕O.Wilson,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8.
〔2〕〔9〕Daria J.Kuss&Mark D.Griffiths,“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nd Addiction—A Re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1,vol.8(9),pp.3528-3552.
〔3〕Wilson,K.,Fornasier,S.&White,K.M.,“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young adults’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 Social Networking,vol.13,no.2,2010,pp.173-177.
〔4〕Soraya Mehdizadeh,“Self-presentation 2.0: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on facebook”,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 Social Networking,vol.13,no.4,2009,pp.357-364.
〔5〕Teresa Correa,Amber W.Hinsley&Homero Zúñiga,“Who interacts on the Web?:The intersection of users’personality and social media use”,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vol.26,no.2,2010,pp.247-253.
〔6〕Emma L.Pelling and Katherine M.White,“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pplied to young people’s use of social networkting web sites”,CyberPsychology&Behavior,vol.12,no.6,2009,pp.755-759.
〔7〕Candy Wan,“Gratifications&loneliness as predictors of campus-SNS websites addiction&usage patter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M.S.Thesis,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2009.
〔8〕〔美〕赫斯特罗姆.解析社会 〔M〕.陈云松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2.
〔10〕Thomas E.Ruggiero,“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00,vol.3 (1),pp.3-37.
〔11〕Danah Boyd&Nicole Ellison,“Social Network Sites:Definition,History,and Scholarship”,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13,no.1,2000,pp.210-230.
〔12〕Nicole Ellison&Danah Boyd,Sociality Through Social Network Site,William H.Dutt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58,p.159.
〔13〕周宪.时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 〔J〕.学术月刊,2014,(12).
〔14〕〔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M〕.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14.191.
〔15〕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4-86.
〔16〕〔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 〔M〕.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93-94.
〔17〕〔英〕布莱恩·特纳.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 〔M〕.李康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18.
〔18〕〔19〕〔40〕〔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 〔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6,12-21,24.
〔20〕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 〔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8.
〔21〕〔26〕〔27〕〔美〕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M〕.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1,39,40.
〔2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 〔M〕.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1.
〔23〕〔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M〕.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12,18,19.
〔2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684.
〔25〕〔挪威〕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 〔M〕.范晶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2.
〔28〕〔英〕鲍曼.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 〔M〕.鲍磊译.漓江出版社,2013.8.
〔29〕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London:Routledge,2003,p.6.
〔30〕王才勇.现代性批判与救赎 〔M〕.学林出版社,2012.76.
〔31〕〔英〕加迪纳.克尔凯郭尔 〔M〕.刘玉红译.译林出版社,2013.44.
〔32〕〔45〕〔美〕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M〕.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172-173,8.
〔33〕〔法〕麦茨,〔法〕德勒兹,等.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 〔M〕.吴琼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34〕〔英〕鲍曼.此非日记 〔M〕.杨渝东译.漓江出版社,2013.234-235.
〔35〕成伯清.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性 〔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2).
〔36〕〔37〕〔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175,176.
〔38〕〔39〕〔41〕〔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M〕.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1,221,161 -170.
〔42〕〔美〕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 〔M〕.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0-101.
〔43〕〔44〕〔加拿大〕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19-30,25.
(责任编辑:邝彩云)
[收稿日期]2016-05-15
[作者简介]田林楠,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情感社会学、社会理论。江苏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