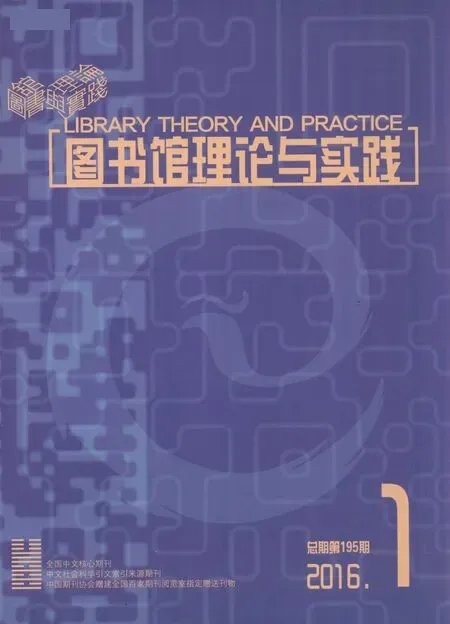稿本《荀子微言》成书流传考
康廷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稿本《荀子微言》成书流传考
康廷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荀子微言》是惠栋仅存的一部荀学著作。此书当是惠氏晚年在校阅《荀子》时摘抄其中精要之言并稍加注解而成。书中讹误颇多,可见其成书后并未加校正。此书未曾刊刻,其稿本先后保存于沈大成、梅春、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等处,今藏上海图书馆。
关键词:荀子微言;惠栋;沈大成;梅春;松江韩氏
《荀子微言》不分卷,清惠栋撰。该书未刊印,稿本今存上海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32册影印出版。书首有韩载阳跋文并钤有“上海图书馆藏”、“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梅春之印”﹑“华亭梅氏藏书”﹑“学子”﹑“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诸印。[1]463书尾署“丙子三月清明后三日阅松崖”并钤有“百耐眼福”一印。[1]483惠氏此书多以《易》解《荀》,颇能发明荀意,且所录《荀子》正文当包含其校勘成果。然其后诸家荀子校注著作中,均无采用惠氏注解意见者。可知其成书后一直藏于深阁,并不广为人知。今对其成书及流传情况加以考察并请正于方家。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易汉学》《周易述》《易例》《荀子微言》等书。惠栋曾多次校阅《荀子》。《荀子微言》书尾亦署有“丙子三月清明后三日阅松崖”一语。可知此书当为惠栋在校阅《荀子》时摘抄其中精要之言分作《荀子微言》与《荀子训格之言》两类,并稍加注解而成。故从体例上讲,此书可视作惠氏校阅《荀子》时所作的读书笔记。
书尾识语中所言“丙子”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则《荀子微言》成书时离惠栋去世仅余两年,此后惠氏又忙于他书之写作。故其成书之后似未加校正,以致错讹之处颇多。例如,《荀子微言》部分:《儒效篇》“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466句“之”前衍一“达”字,“而师法者所得乎积”[1]467句“师”误作“归”。《王制篇》“夫是之谓至乱”[1]468句“夫”后衍一“妇”字,“能以事兄谓之悌”[1]469句“兄”误作“亲”,“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1]469句“姓”“有”二字互乙。《解蔽篇》“卷耳易得也”[1]471句“卷”误作“采”。《天论篇》“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473句夺“能”字。《荀子训格之言》部分:《劝学篇》“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1]474句“谓”误作“为”。《君道篇》“韩婴以为周书”[1]477本为注语,依例当为双行小字,却误写为单行大字。《议兵篇》“慎终如始,始终如一”[1]478夺“始终”二字,“诸侯为臣,无他故焉”[1]478句“他故”二字互乙。《天论篇》“愚者为一物一偏”[1]479句“偏”误作“篇”。《礼论篇》“有一国者事五世”[1]481句夺“者”字。
惠栋身后,此书归其挚友沈大成。沈大成(1700~1771),字学子,号沃田,江苏华亭人。诸生。校定多部书籍,著有《学福斋集》。沈大成与惠栋既已相识,晚年二人又皆寄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下,分居一院内左右两房,互相切磋学术,并结下深厚友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同时与先生(惠栋)友善者,沈彤﹑沈大成。”[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亦云:“沈大成,字学子……与惠栋友善,栋称其学‘一物一事,必穷其源’。”[3]可见二人交情之一斑。乾隆二十三年(1758),惠栋离世结束了两人重聚的时光。此后沈大成曾多次在其诗文中追忆亡友惠栋。惠栋故后,卢见曾为惠栋刊印了其《周易述》。而此时仍在卢见曾幕下的沈大成亦将《荀子微言》手稿保存下来,并于书首页右下角钤下“学子”一印。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卢见曾离任,沈大成开始馆于巨商江春家并在此度完余生。沈大成有一子,名一震,字东发,又字伯高。然早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沈大成在其《亡儿一震窆志》中说:“吾今畴畀宗绪一线,吾老何倚?天乎酷哉!”[4]王昶《湖海诗传》卷十八亦曰:“(沈大成)后馆于江鹤亭春家,编次诗文集共六十八卷。无子,没后鹤亭刻以行世。”[5]可知其只有沈一震一子。沈大成身后无子,故所藏《荀子微言》难免流落他家。
书首所钤“梅春之印”、“华亭梅氏藏书”二印属清代华亭藏书家梅春。沈大成之后,此书归华亭梅春所有。《历代藏书家辞典》:“梅春,清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健男,一字寿柟,号小庾。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幼嗜学,长洲王芑孙来官教谕,授以文章原本,益自奋。聚书数万卷,手自点勘,日夜披诵。藏印‘华亭梅氏藏书’。”[6]386梅春为华亭绅士,与姚椿、王庆麟等均为当地藏书家。
梅春之生卒年各书并无记载。王芑孙曾于嘉庆十一年(1806)携梅春﹑周谟﹑改琦等诸友同游松江西北之横云山,其后周谟﹑改琦二人据此事绘《横云秋兴图》,王芑孙为之作《横云秋兴图记》。记中有描绘梅春之语称“坐而垂杆者,华亭梅春小庾,年三十二”。[7]据此推算,可知梅春当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梅春与沈大成同为华亭人,则《荀子微言》流入他手中合情合理。但因其出生尚晚于沈大成离世四年,故梅春于何时获得此书已不可考。梅春生前好友张祥河(1785~1862)《小重山房诗词全集·诗舲诗外》卷一有《挽梅小庾同年》一诗。此诗虽不知作于何年,但其中有“中年哀乐半侵寻,话别燕山强自禁”﹑“石火流光悲过客,楹书旧学付佳儿”[8]两语。可知梅春当为中年早逝,而遗所藏之书于其子。
《荀子微言》书稿后归于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其书前有跋文曰:“《荀子微言》□□有家大人笔记。五月二十五日偶于低桌抽头中检得,恐面页遗落,取下置书内。即日载阳手记。”[1]463其中“载阳”为松江读有用书斋主人韩载阳。“家大人”即韩载阳之父韩应陛。韩应陛(1813~1860),字对虞,号绿卿,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少好读周秦诸子,为文古质简奥。既从同里姚椿游,亦精于译算学及声光化学等书。家藏书颇富,有四百多部善本,大半为士礼居黄丕烈旧物。所藏书编为《读有用书斋书目》。”[6]431-432
从此跋可知,早在韩应陛时,此书已归于韩氏读有用书斋。韩应陛曾大量收书,缪荃孙《华亭韩氏藏书记》云:“当乾嘉盛时,苏州黄荛圃士礼居藏书甲天下……殁后书尽出。先生(韩应陛)与常熟之瞿﹑金山之钱﹑上海之徐﹑郁同时收书……所积约十余万卷,校雠考订,手不停披。”[9]则《荀子微言》稿亦当为其所购。缪氏又云:“(韩应陛)得书,即识缘起于书衣。”[9]则韩载阳跋中所云“家大人笔记”当为韩应陛购得此书后记于书衣之缘起。其中当记有此书之详细流传过程。惜韩载阳虽“恐面页遗落,取下置书内”,却依然未能保存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微言》在韩氏收藏期间虽几经浩劫,竟终未散失。例如,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松江,“君之藏书板片﹑古器书画与所居俱毁。君遂郁郁以殁”。[9]而此书却承韩应陛﹑载阳父子携带外逃而保存下来。又如1924年的江浙战争及1926年北伐战争曾两度威胁到韩氏读有用斋藏书的安全。然此书亦有幸在韩氏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的保护下幸免于劫难。书首所钤“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为证。
《荀子微言》书尾所钤“百耐眼福”为邹百耐之藏书章。“邹百耐名绍朴,清末翰林邹福保(字咏春)之子。早年随父居京师,也算是世家公子。辛亥革命后,百耐随父南下。”[10]1933年,韩氏后人韩绳夫开始出售所藏之书。时为书贾的邹百耐曾经手韩氏售书之事,并作《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百耐眼福”一印当钤于此时。华亭韩氏对《荀子微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收藏亦告一段落。
1939年,为保护受战争威胁而濒临毁灭的珍贵图书典籍,张元济﹑叶景葵等在上海筹建合众图书馆,并大量接受诸藏书家及社会各界之捐书。所捐书中包括各大藏书家散出之古籍。华亭韩氏藏书地处上海,故其散出之书后流入合众图书馆者较多,《荀子微言》亦在其列。叶景葵作为合众图书馆的筹建人之一将其所藏之书悉数捐献。而其所藏之书中又以名家稿本﹑抄本著称,故在各藏书家中最有可能为《荀子微言》的捐献者。新中国成立后,合众图书馆于1953年被捐献给国家并易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又并入今上海图书馆。《荀子微言》今存于此。
《荀子微言》自成书后历经沈大成﹑梅春﹑韩氏读有用书斋﹑邹百耐等人之数易其主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江浙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数次劫难,却仍能在二百多年后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实属不易。今略作以上考证,以示该书流传之脉络。
[参考文献]
[1](清)惠栋.荀子微言[M]//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影印惠栋稿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钟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29.
[3](清)李斗.扬州画舫录[M].汪北平,涂雨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277-278.
[4](清)沈大成.学福斋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2册.影印乾隆三十九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98.
[5](清)王昶.湖海诗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435.
[6] 梁战,郭群一.历代藏书家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7] 莫道才.骈文观止[M].北京:北京艺术出版社,1997:594.
[8](清)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1册.影印清刻民国间补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4.
[9](清)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癸甲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6册.影印民国江阴缪氏艺风堂递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86.
[10]李军.三世云烟翰墨香百年丘壑腹笥藏——纪念苏州“文学山房”旧书铺一百一十周年[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6):114.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Writing and Inheriting of the Manuscript of
Kang Ting-shan
Abstract:is Hui Dong’s only remaining work about the studies of XunZi. It should be a collection of the essence in XunZi andnotedby Hui Dong whenhe was revising it. This work mighthaven’t beenverified after its writing as there are many errors in it.Ithasn’t beenprinted andthe original manuscript was conserved by Shen Dacheng, Mei Chun, Songjiang HanShi ect in turn and now conserved in Shanghai Library.
Keywords:XunZi WeiYan; Hui Dong; Shen Dacheng; Mei Chun; Songjiang HanShi
[收稿日期]2014-07-09[责任编辑]李金瓯
[作者简介]康廷山(1987-),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5-8214(2016)01-00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