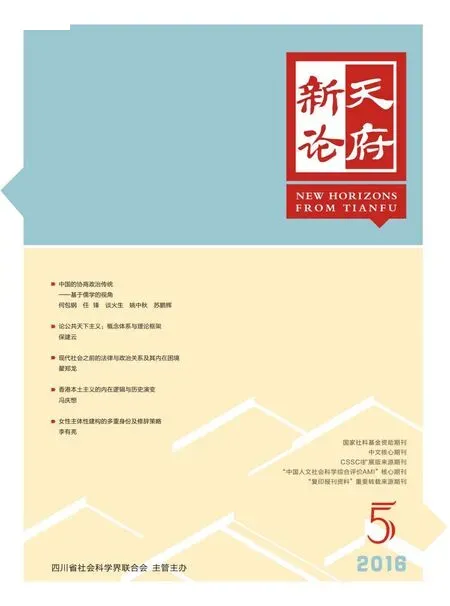访王晓波教授:台湾保钓运动与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
访王晓波教授:台湾保钓运动与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
编者按:1970年代的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日趋逼仄,而岛内又因奉行“戒严”时期钳制言论、打压结社的高压政策而暗流涌动。1970年10月,因台大哲学系研究生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保卫钓鱼台》的檄文,而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1972年底,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在校园里首次开展关于统、“独”的论战,后因政治势力的介入逮捕王晓波、陈鼓应等多位台大师生而结束,人称“台大哲学系事件”。本期访谈对象王晓波教授是台湾保钓运动的推动者和“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他对两次事件的背景和始末的口述,不仅展现了台湾高层的政治斗争和台大哲学系的学术流派纷争,也揭示了两次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台湾哲学学科发展乃至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通过这篇访谈,我们可以管窥台湾民众在民主化进程中爱国意识、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台湾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干预学术、学术影响政治的双向关系。
受访者:王晓波,男,1943年生,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1971年获硕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因卷入“台大哲学系事件”,1973年2月曾被台湾当局逮捕,1974年6月被台湾大学不续聘。后任教于世新大学。1997年“台大哲学系事件”平反,复职重回台湾大学哲学系授课。2009年退休后,再次任教于世新大学。王晓波教授被称为台湾 “统派”代表人物,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家哲学、儒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台湾史,主要代表作有《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史论》《台湾史论集》《台湾抗日五十年》等。
采访者: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杨澜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干春松:王教授,您好。听说您和郭齐勇老师等将一起编辑徐复观先生的全集在大陆出版。因为学术会议的原因,我和徐复观先生的公子徐武军先生认识。他说,在台湾,最能体贴徐先生思想的是您。
王晓波:我是徐复观先生的门外弟子。
干春松:相比于牟宗三先生,研究徐复观先生思想的人并不是太多。您是研究法家著称的,我就好奇徐武军先生对您的评价,不过他解释说,您是比较有革命精神的,有对抗强权的精神,所以,您跟徐复观先生那种精神气质比较能对得上。
我们还是从哲学系事件开始讲吧,这个事情您可能已经讲过多遍,但是我们特别想了解。我这次介绍台湾大学的哲学研究状况,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
王晓波:哲学系事件必须从理论问题入手。这个事应该从几个背景来看,从一些哲学历史和背景来看。
一、台大哲学系的历史背景
王晓波:哲学系事件的背景,第一个是台大哲学系的历史背景。
干春松:我看过资料中说,台大哲学系在一九二几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时期就有。
王晓波:没有,原来有哲学科,但是没有哲学系。
干春松:就是说,台大哲学系其实是台北帝国大学延伸下来的?
王晓波:对。台大哲学系后来主要有几个人:吴康、范寿康、方东美、殷海光。原来台北帝国大学留下来的人不多。
谈到哲学系事件,当时台大哲学系有两个老师是受到学生敬重的,一个是殷海光老师,一个是方东美老师。殷海光老师是金岳霖的学生,后来他强调自由主义,强调罗素,强调当时流行的逻辑实在论,而且还当过《中央日报》的主笔。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西南联大,是比较靠向政府的,他听到蒋委员长名字要立正嘛。
干春松:最近大陆出了一本何兆武先生写的《上学记》,描述殷海光先生时,就是您说的那样,他那时候是跟国民党跟蒋介石走的……
王晓波:他之所以转变,是由于徐蚌会战,当年叫做淮海战役,他就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国民党“退守”到台湾来,党内有一些反省,为什么大陆会丢掉?反省的结果是什么呢?大概当时候有几派的知识分子的反省。殷海光跟雷震他们的反省,得出大概的结论就是蒋介石没有走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而徐复观他们当时的结论呢,是认为中共之所以取得政权,主要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共产党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在。
干春松:对。
王晓波:以前不是。以前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的、专制的,中国文化需要彻底改造,要改造成马列化。说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狗屎,大约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们的看法。共产党取得政权,实际上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后来新儒家们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完蛋了。所以,他们要开掘所谓的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个人向全世界发表申明,为中国……
干春松:《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王晓波:对,徐复观和新儒家是另外一种检讨,他们那边好像就有一个刊物叫做《民主评论》,还是《民主中国》?
干春松:新儒家的刊物叫《民主评论》。自由派有一个刊物叫《自由中国》。
王晓波:《自由中国》刚开办的时候,说徐先生的《民主评论》拿了国民党的钱。其实自由派也拿。《自由中国》当时在台湾一直发到连队,就是连级的单位。像国民党有多少个连啊?所以,它的销路保证没有问题。
当时办《自由中国》是干嘛?是胡适希望建立一个流亡到海外去的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团结这些反共知识分子。徐复观呢,认为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他的意图是要收拾这些花果的。当然,从《自由中国》这边来讲的话,胡适的知识背景跟美国比较接近;另一个重要人物雷震是蒋介石在南京当选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国民大会的秘书长,等于是蒋介石的操盘手,他们办《自由中国》,当时是受到国民党支持的。但后来雷震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吃错药了,讲什么“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得罪了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边缘化。
再后来,《自由中国》对蒋介石有很多时评的意见,或者说有很多抨击的意见。再到雷震被捕,这有一个过程。蒋介石到台湾来,认为军队叛变太多,他曾经加强军队里面的侦控,让他儿子蒋经国去做侦探部主任。后来,蒋介石又让他儿子去抓校园的学生思想,叫青年反共救国团,控制校园思想。而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蒋介石的接班人还轮不到蒋经国,应该是台湾省主席陈诚。这就有陈诚跟蒋经国之间的权力矛盾和摩擦。雷震的问题,其实一直延伸到后来所谓的中西文化论争,这个论争跟哲学系的事件是一种明线和暗线的关系。
干春松:我们前几天去“中研院”参观访问的时候,那儿刚好做了个胡适之特展。特展里面包括1949年之后大陆对于胡适的批判,特别是顾颉刚的批判文章,很唏嘘。还有许多胡适与蒋介石的照片,里面也有几张照片是关于雷震、胡适和蒋介石,也有《自由中国》的创刊号在那儿陈列。
王晓波:雷震是胡适的粉丝啊。胡适之所以要办这个东西,你去看《自由中国》里面应该有描述。他离开大陆的时候,在船上思考如何团结流落在海外的这些反共知识分子,就是要办一个刊物。后来办这个刊物的意念被雷震知道,雷震就办这个刊物。但是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包括殷海光在内,实在是很瞧不起胡适。当时殷海光还是《中央日报》的……
杨澜洁:主笔。
王晓波:现在我没有去查《殷海光全集》是不是包括他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当时殷先生有一个绰号“别字主笔”,他别字很多。不过呢,因为受过逻辑方面的训练,所以他的文笔非常细腻。殷先生从《中央日报》转到《自由中国》之后,他口才很好,而且上课讲话表情又很丰富,很受学生的欢迎,影响很大。当时殷先生在台大文学院。我听李敖他们讲,在我进台大之前,殷先生当时还定时在文学院召开类似读书会的研讨会。在文学院里面,包括历史系、中文系(中文系比较少)、哲学系的一些学生,当时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探索问题的一些学生,他们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李敖也有参加过那个讨论会,所以李敖也一直叫殷先生是殷老师。还有像陈鼓应等等也是。我后来跟殷先生在一起,也是受到殷先生的那种思想的激励。而国民党当局对于殷海光以及《自由中国》,一直认为他们是异议分子。
台湾大学哲学系另外一个受到欢迎的是方东美老师。方东美老师是美国的哲学博士,他是研究人生哲学的。方先生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方面都非常博学,比较偏重于欧洲哲学。方先生是当年“少中会”的。而且在抗战时期,他还做过哲学方面的广播。我跟方先生并不是很接近。我们知道方先生很高高在上、很孤僻、不太接近学生的样子,但是很多学生非常尊重他,他上课整个教室统统坐满,校内外的学生都来旁听。我选过他的课。他上课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上课的时候方先生抽烟,一根接一根不停的。
干春松:那时候课堂上还可以抽烟,是吧?
王晓波:那时候方先生在课堂上抽烟,一根洋火就点到底了。但是方先生到台湾来以后,有很多这样的教授到台湾来以后,都噤若寒蝉,都不讲话。
干春松:到了台湾就不敢说话?说明国民党的言论控制是相当严厉的。
王晓波:都不说话,也不写论文。方先生后来的著作是靠他在上课的时候演讲,跟亚里士多德一样,这样记录下来的。
这里台大哲学系就有两派的学生不一样。对于现实超越的就倾向于方东美先生,对于现实比较热衷关心的就倾向于殷海光老师。这是后面的哲学系事件的一个背景。
以学生的角度来讲,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哲学系的一些学生有像我——不瞒你讲,我母亲是受过白色恐怖袭击的,有苏庆黎,他的父亲是当年的台湾共产党,后来“二二八”之后逃到北京去,是台盟的创始人之一。
干春松:您几个都是红色后代。
王晓波:所以国民党就认为台大哲学系有问题啊。
二、台大保钓运动
王晓波:哲学系事件的第二个背景是保钓运动。当时钓鱼台运动起来了。钓鱼台运动是我们台大哲学系的学生搞起来的,保卫钓鱼岛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写的。1970年10月,我在《中华杂志》发表《保卫钓鱼台》的文章,把一些钓鱼台的资料整理以后,呼吁保卫钓鱼台。那篇文章中,我引述了罗家伦的《五四宣言》的一句话: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句话引在文章的前面。后来很多人回应,说他们都是被《五四宣言》当中的两句话打动的,而不是被王晓波的文章打动了。
当时台大哲学系的一些同学,钱永祥,还有郑鸿生他们,在办《大学论坛》。后来就由《大学论坛》发起台大的保钓运动,在台大旧体育馆开一个大会。那一天,整个运动场所有的位置都排满了保钓运动的材料,所有的看台坐满了台大学生,来讨论钓鱼台的问题。结果,他们扯来扯去争论要不要形成组织。你要知道,在这个时期是不能搞组织的。
干春松:这我们知道,国民党应该很害怕学生搞组织。
王晓波:当时争论是否要成立“保钓委员会”。有人说我们有代联会(台湾大学的学生组织)就可以了,不必成立保钓委员会等等。我知道大家怕形成组织,后来我一个箭步上去,把麦克风拿过来,我说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人请鼓掌,啪,现场鼓掌。
杨澜洁:那您就是委员长?
王晓波:我不是。
干春松:但是您宣布成立的。我刚才特别留意,您说一个箭步。
王晓波:大家当时拼命鼓掌,宣布成立,然后各个社团推选代表。马英九当时是代联会的秘书长。
干春松:马英九跟您是前后年级?
王晓波:他比我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研究生了。后来马英九就常常到我们那边去抽烟喝酒,我们那个时候住他家隔壁。这个学生运动起来了以后,就一直不停地发展,几个月之后告一段落。
保钓运动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很快就受到胡秋原、徐复观、任卓宣的注意和支持。任卓宣是老共产党员,胡秋原是共产党退党,跟中共闹翻的。我1988年见到邓颖超,她还要我跟秋原问好。
三、哲学系事件背后的台湾社会思潮
王晓波:在台湾来讲,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文革背景。文革今天在大陆被称作“十年浩劫”。可你要知道,当时文革红卫兵的运动在全世界蔓延,日本有赤军派,美国有共生军,欧洲有3M,3M就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哲学家马尔库塞,3个M。
当时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内心有一些疑问,就是那时美国要跟大陆建交。之前,美国选举中的候选人一直强烈地妖魔化中共,所以,当他们要跟中共建交时,也必须要说服他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过一阵子的中国热。中国热,讲老实话,我们到今天为止过了几十年了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很激动、也很感动,因为有联合国的宗教什么分会到大陆去访问,回来报告还引用《圣经》的话:“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好比行在天上。”哇,天堂出现了。联合国的医疗组织去大陆访问,看到赤脚医生,结果回来报告,中共在大陆建立了一个覆盖数亿人的、人类最伟大的医疗系统。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台湾的反共教育中大陆人不是吃草根树皮吗?不是这个样子啊!而且杨振宁去大陆访问以后说,他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认为人民士气最高的是以色列的国家,但是到了大陆去以后,发现中国人民的士气比以色列还要高。
杨澜洁:这倒也是。
干春松:杨振宁这个口气一直没变。
王晓波:还有很多的小道传说,说有一个留学生回去探亲以后说:大陆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贪污的地方。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反越战;美国要正常化宣传中国大陆;几年前“珍宝岛事件”,大陆把苏联的一个团长给干掉了、一个团打垮,对比保钓运动时国民党畏畏缩缩,当时思维敏感的同学都马上就会想到,我们凭什么今天还来受日本这样的侮辱,八年抗战被我们打败的国家又重新来侵占我们的领土,凭什么?那是因为中国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不团结,国家分裂。如何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领土,那就是中国人要考虑的。这样很自然的逻辑推导下来了。但是我们在台湾不能讲。那些留学生在美国讲的话,蒋介石天高皇帝远,他管不了。所以,美国很快有一批学者的思想热情从保钓、支持国民党到跟这边的所谓的分裂,分裂成两派。这批最有代表性的人就是现在台湾同学会,比如吴国桢他们。那时他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从美国回了大陆。
干春松:对,那时候回来很多人。
王晓波:另外一批叫做“反共爱国联盟”,包括马英九是参加“反共爱国联盟”的。那么,在岛内来讲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美国留学生油印的的小字报邮寄进来,我们也都看到了。另外就是钱永祥他们,到今天为止,钱永祥他们还没有交代一个东西,我什么时候要问清楚。他们居然可以带进来《毛泽东选集》、《资本论》。 据说是由外交邮袋寄进来的,那就一定跟美国有关。具体我们不清楚,但是美国没有理由插手。
干春松:下回我见到钱永祥老师也会问他一下,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王晓波:钱永祥他们在《大学论坛》社,这些东西就在校园里面开始流传。但是,我们也不敢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不敢主张中共。而且统一都不敢主张,因为只有官方的统一论。官方的统一论就是消灭共匪、反攻大陆。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开始有一些人号召,我们要爱国就要爱民,要对弱势团体、弱势阶级同情。所以,当时台大学生就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
干春松:也要上山下乡。大陆有一个运动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王晓波:不是上山下乡,是三大面向:面向高山、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除了百万小时奉献以外,还在各学校成立了很多国事社、国文社等等,关心国事、关心社会。还有所谓的社会调查团,到著名的高山区、到农村、到最艰苦的地方,而且还到台中市里面的一些最龌龊的地方去做调查、做了解,然后回来写报告。社会运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统一运动的思潮也在校园里面蔓延,只是扑不出来。后来,台湾内部发生了统运的问题。在1972年12月4号,《大学论坛》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讨论是不是台湾要提倡民族主义。
我们事先知道这是陷阱。但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也比较勇敢,虽然知道是陷阱,我们还是踏进去了。当时我准备讲习的内容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说统一不是只有中共统一台湾的,我说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说民族主义如何、民权主义如何、民生主义如何。结果就成了政治犯。
时过境迁,结果到了1981年,陈立夫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从上到下再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来,我1988年去大陆访问,要做演讲,出入境管理局的人找我去,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讲三民主义统治中国。我说我当年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被你们铐进这里来,我还讲啊?
四、台大哲学系事件的三个层级
王晓波:我们现在来谈论哲学系的这个问题。哲学系呢,当时成中英客座,来当系主任。后来他回美国去了,就由赵天仪副教授代系主任。这里要有一个说明,根据我们台湾的规定,副教授是不能担任系主任的,必须是教授才行。 成中英又介绍他的一个同学孙智燊来任系主任,孙智燊是方东美的学生。
之前已经说过,殷先生在学术上面来讲,比较倾向逻辑实证论、自由主义这一带,方先生不是这样的。所以,方先生对于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为首在台大以逻辑实证论当道,不以为然。在这个时候,孙智燊回来又被冯沪祥包围。
干春松:冯沪祥那时候已经是老师还是?
杨澜洁:学生。
王晓波:冯沪祥的背景又跟当时情治系统的王升有关。当时情治系统一向主张在思想上对学生进行镇压。后来,学生校园思想转成社会运动——国民党是最怕社会运动的,对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是最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系事件发生了。我事后把这些事件分成几个结构的层次。第一个结构的层次,蒋经国大概是最高的层级,他认为要安定社会就必须要稳定校园,不然的话,就会像美国、日本、欧洲那样一塌糊涂。要稳定校园呢,就要先找到地震的震央。他认为地震的震央在台大哲学系,要拯救台大哲学系。第二个层级呢,是蒋经国当时两个重要的助手,一个是王升,一个是李焕。这两个人是对头。李焕是救国团的,后来当救国团的头,兼蒋经国的主任,而且是组织工作会的主任,有点类似大陆的组织部的主任。跟王升不同,李焕是比较主张帮扶的,因为李焕的儿子李庆华是跟我们一起搞保钓的,他在政大、我在台大。王升是总政,我们这里叫做总政治部主任,军中的,有点像大陆军中的总政。蒋经国下来一个层级就是李焕和王升。李焕和王升又斗争得很厉害,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第二个层级。第三个层级呢,就涉及到我们哲学系内部,涉及到刚才讲的方先生和殷先生的两派学生。
干春松:就是他们这两个老师之间的问题,是吧?
王晓波:对,两个老师之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最后一个层次呢,凭良心讲,国民党并没有要整肃那么多人,国民党当时最多整肃陈鼓应和王晓波,再加上一个赵天仪而已。结果,后来把孙智燊一船打翻了,过瘾了。
干春松:扩大化。
王晓波:扩大化。好在他扩大化,不然的话,我们就……
杨澜洁:不能平反。那么,如何看待保钓运动和台大哲学系事件之间的关系呢?
王晓波:哲学系事件,不应该只是一个保钓运动的枝节的问题。就像五四运动后来的发展一样。保钓运动之后,哲学系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人事上的事件,唯一的影响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中国哲学的路子被中断了。
五、政治和学术
干春松:现在我有时候看网上讲哲学系事件,也涉及到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些瓜葛。
王晓波:但这里可能有更大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战后台湾思潮的问题、台湾思想史的问题。国民党在刚到台湾来的时候,还是受到台湾同胞的欢迎的。但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之后,热烈欢迎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开始对白色祖国失望,而对红色祖国产生期望。所以,“二二八”事件之后,这些群众运动的头头逃到香港,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志士同盟,由谢雪红带头,1949年4月到北京,在10月1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台湾国民党方面,1947年“二二八”镇压之后,开始戒严。之后开始白色恐怖,到处都贴着标语“匪谍就在你身边”,好恐怖,要匪谍自首,既往不咎。
这个白色恐怖的期间,你要晓得,当时是在戒严时期,我研究这段台湾的思想史和历史,我是用期刊作为观察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不能成立组织,不能办报纸,不能掌握媒体,——除了自己私人办的期刊,像《自由中国》半月刊、像《维新》杂志。期刊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宣传,而且有总编辑、编辑委员会、社务委员会,又有社长。《美丽岛》杂志当时就是一个组织。其实台籍的知识分子还办了《公论报》,社长是李万居,总编辑是郑士镕。郑士镕是什么人呢?是陈仪的机要秘书。李万居是什么人呢?李万居抗日时期是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副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个谍报组织,侦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就是这个组织。后来李万居回来接手台湾《新报》,改名为台湾《新声报》,“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时候,他就辞了台湾《新声报》的社长,创办台湾《公论报》。他的总经理陈其昌是台湾民众党的秘书长,末代秘书长,在抗战期间到大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派在上海的干员。他们三个人办的台湾《公论报》。台湾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地方选举,台湾《公论报》基本上是专注在台湾地方选举上。《文星》杂志的发行人是萧孟能,萧孟能是国民党的中央社的创办人萧同兹的儿子。而当时救国团是支持《文星》杂志的。
干春松:这些期刊有太子党背景,又有官二代背景。
王晓波:其实这些都跟陈诚和蒋经国的角力有关。在这个期间,台大发生了自觉运动。《自由中国》被镇压以后,本来在台湾来讲,一年反共、二年胜利、三年扫荡的说法已经轮了好几轮了,国家统一没有希望了,在台湾这个小岛玩的自由民主也没得玩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青年非常沉闷,有一点像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青年一代,削尖了头要出国。所以,当时有一个标语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干春松:现在大陆的顶尖高校的学生也有这样的去向。
王晓波:所以,在台湾开不成校友会,要到美国开。在这种情况下,自觉运动起来了,呼吁大家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怎么讲呢?当时候大家很苦闷,就是一天到晚准备要出国,最优秀的青年就是一天到晚准备出国,而且都是单程票,出去就不再回来了。当时有一个美国到台大来的留学生叫做狄仁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人情味与功德心》,他说台湾人非常有人情味,但是没有功德心,台大上公厕不排队、垃圾乱丢、脚踏车乱停……讲了一大堆。还有一个考试作弊。——凭良心讲,为什么要考试作弊?当时很穷啊,你不拿奖学金根本出不了国,奖学金一定要高分啊,所以只好作弊。——这样的话,学生对国家、社会完全没有关怀。这篇文章引起台大学生的自觉运动,有自觉运动,然后才有保钓运动。我是参加自觉运动的。自觉运动完了之后,学理工科的就由林孝信带头,后来在美国创办了叫做《科学月刊》,这个杂志现在在台湾。当时我就是担任自觉运动期刊《新希望》的主编。那时我的同学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喊出了一个口号“重新扛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个词是我写的。
后来自觉运动被镇压、被查禁,林孝信带着一批学理工的去搞《科学月刊》。邓维桢台大毕业,拿了一笔钱到台北来创业,办了一个刊物叫作《大学杂志》。后来,《大学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初,扮演着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平台。在保钓运动的时候,《大学杂志》也推波助澜,变成一个阵地。《大学杂志》在哲学系事件之后被镇压掉了。我跟陈鼓应应该是《大学杂志》的……
干春松:主要撰稿人。
王晓波:《大学杂志》完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杂志叫做《夏潮》,我跟陈鼓应都是主要的人。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刚才我们讲的民族主义座谈会之后,就开始分裂成左右两派。《夏潮》杂志是比较倾向于左派主张统一的,有陈映真、蒋勋,杂志总编辑是苏新的女儿苏庆黎。另外一边就有《台湾政论》、有《美丽岛》杂志。党外杂志遍地开花。《美丽岛》杂志发起的美丽岛事件后,《夏潮》杂志也被查禁。《夏潮》杂志一直到今天我的《海峡评论》,是这个系统的。这个系统里面,在组织上、在社会运动上就有劳动党,在统一运动就有中国统一联盟。那么,《台湾政论》、《美丽岛》下来就是民进党。
所以,我刚才讲保钓运动是一个转变点,而台大哲学系事件只不过是整个保钓运动这一个大运动中的一个事件而已。
干春松:这个事件对台大哲学的最大打击就是台大哲学系一直没有博士班。
王晓波:对。成中英当时到哲学系来,他是想有所作为,是有一个构想的。当时来讲,他想发展中国哲学的研究。那时台大并没有博士班。
干春松:对,那时候辅仁有博士班,台大没有。
王晓波:台大没有博士班,当然要求就比较严格一点,很多的学生念到了硕士毕业,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念博士,只能出国。而世界范围内,从黑格尔以来,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哲学。
干春松:对。
王晓波:所以,那个时候说谁到哪国去留学,去念中国哲学,那都是吹牛的。出国留学学的都是汉学,汉学不等于中国哲学。所以,当时成中英是有远见的。他说我们台湾至少——当时大陆又是文革——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台湾建立起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基地。如果学生一出国,统统都是念西方哲学去了。我们这些不出国的土包子开中国哲学的课,每一家统统都有人。我是开法家哲学的课,道家是陈鼓应开,儒家是黄天成开,墨家是钟友联开。这些都由年轻的讲师、副教授轮流开课。大概几轮课以后,先秦诸子、两汉、魏晋这样开下去,教学相长,这样来培养中国哲学的师资。
老实说,如果不是哲学系事件的话,今天台湾的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是领先的。这个挫折下来,一直到我跟陈鼓应回台大哲学系,台大哲学系里面也是两派在斗争,为选系主任斗得一塌糊涂。我跟陈鼓应一回去,成了关键少数,压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赢。所以,我跟陈鼓应平反回去,他们很紧张。后来我放话给他们,我说,不必紧张,不影响历史的政治,王晓波没有兴趣。我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推动、我要干的,这不是学术的本身,这是学术的政治。我要台大哲学系研究所分组,分为中国哲学系、外国哲学系,要抢出一个中国哲学的基地出来。
这件事在讨论的时候,还很有争论,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后来有人说,我们的佛学是什么哲学呢?佛学是算中国哲学,还是算外国哲学?最后又有人说,佛学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后来又说是东方哲学组、西方哲学组。后来有人说,佛学当然要算东方哲学。有人反对,他说,你说是东方哲学,是从英国格林威治算起,那么在中国来讲,像西天取经,就是西方哲学。哲学家吵架吵不完。后来我对于这一点,我说有就好,分组就好,管它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只要能够分出来。但是我跟陈鼓应离开了之后,现在哲学系聘教师也受到台湾的这种制度和风气的影响,结果就请一些洋人学汉学的博士。
干春松:请了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来。
王晓波:对。都是请了一些洋人,念了汉学的来。所以我就奇怪,我说哲学系变成土人教洋哲学,洋人教土哲学。
干春松:这个批评比较有道理,我认为洋人教土哲学肯定是不行的。土人能不能教洋哲学,因为我不研究洋哲学,我不知道。
王晓波:凭良心讲,都很难,尤其是就哲学来讲。所以,现在虽然台大哲学系是分了,但是现在的师资不是很理想。应该说,台大哲学系事件打断了成中英当年的设想,当时不中断的话,只要有一个五六年的时间积累下来,台大成立博士班没有问题。博士班起来,我们就可以自己培养中国哲学的师资了。中国哲学,哲学就是哲学,汉学不见得是中国哲学,哲学还是要有本体论、形上学,要有知识论,这个才叫做哲学。现在不讲别的,现在搞了半年,统统都是一种教化了。教化是一种硬的东西,怎么能是哲学?这个叫做规范,这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不是哲学。讨论为什么要有这种道德规范,这个才叫做哲学。
后来我到大陆,我看大陆的情况,有一些好一点。我到北大去过半年,做客座。我看他们有一些也搞不太清楚,例如,哲学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它的知识论在哪里,它的形上学在哪里,它的本体论在哪里,琢磨不出来。我觉得哲学系事件最遗憾的,大概就是这里。
哲学系事件完了之后,只有世新大学收容我当兼任讲师。我好几本著作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譬如《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史论》。《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当中,我们抽出两篇来,在夏威夷大学英文出版,还有在《东西文化期刊》的一篇书评。另外,最近在台大,黄俊杰帮我出了一本《道与法》,在一个国际期刊也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书评。因为在世新上课,我没有哲学系的课上,又不能够做社会活动,被看管了,三不五时就被请进吃饭。还好,可以加加营养。
干春松:您也是经常被情治部门请去?
王晓波:对啊,所以很闲。又由于台大民族主义座谈会发生台独论战,开始有所谓的台湾认同问题。你要认同台湾,那你必须要认识台湾,你不认识怎么认同啊,是不是?认识台湾,当然要研究台湾的历史。我除了中国哲学的专业之外,台湾历史研究方面我应该还算可以,尤其是有关于台湾抗日时的这一段。我越研究台湾历史,我越认同台湾,我越不认同台独。所以,我还把这一段台湾历史推广到大陆去。现在北京的台湾会馆,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现在的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还有一个特别的展馆要建立,就是台湾抗日展馆,那也是我去催的。你们去过黄帝陵没有?
干春松:我去过陕西那个。
王晓波:黄帝陵有一个香港回归碑,有一个澳门回归碑。还有第三个碑,往后面退一点,有一个台湾光复纪念碑。
干春松:那是您去树在那里的?
王晓波:我去推动的。我们还组织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包括丘逢甲的后人,包括罗福星的先人,都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一直在台大的话,也许会变成一个学究。因为对于台湾史的认识,所以我才知道台独都是乱扯。然后由对台湾史的研究,深入两岸关系。
干春松:刚才有一个问题,您稍微提了一下。就是1988年的时候,您说邓颖超接见过您?
王晓波:对。
干春松:我记得后来邓颖超也接见过陈鼓应,是同一个时候还是?
王晓波:接见他在前。当时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经常主持中国统一联盟。
干春松:跟台大哲学系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王晓波:台大哲学系事件,相传当时是周总理下令停止中央广播电视台对台广播的。
干春松:因为大陆一广播,国民党以为你们真是共党派来的。
王晓波:不过这里也很妙。开法家哲学课,我比共产党早;而且保钓,我也比共产党早。结果,他们说我跟共产党唱和,我说,我比他早啊,我说是他跟我唱和,不是我跟他唱和。
干春松:您和陈鼓应老师从1997年平反,复职以后,还继续在台大教了一段时间的课?
王晓波:对,我1997年回来,2009年退休的。
干春松:现在又回到世新去了?
王晓波:还是去投靠老东家。
干春松:您后来为什么没有想建一个党,更进一步地进入到台湾的政治事务中?您刚才说不能改变历史的政治,您不感兴趣。但是您刚才说他们那个《台湾政论》、《美丽岛》就变成民进党了。你们《夏潮》的左派,像陈映真、包括您,反倒是都转向比较学者的,不太实践的一个政治的……
王晓波:台湾的空间有限。我们还有一个劳动党,劳动党现在只有一个现议员。
干春松:您自己现在是什么党?
王晓波:我无党无派,我只是劳动党的顾问。
干春松:左派就进入这种具体的社会救济活动。怎么说呢,民进党就比较偏自由主义那个色彩,你们劳动党就是比较关心下层民众,还是左派的色彩?
王晓波:当然,我不太喜欢用左右派的分法。
干春松:标签比较没意思,但也不能没有,因为标签背后是思想倾向。说这个人是左派、主要看他是不是注重平等、公正这一块。关键是关不关心农民和那些弱势群体。
王晓波:对,劳动党大概都是做这些工作的。我们大概还有国家的事情,就是国家统一的问题。
干春松:我在大陆也听到,说您是台湾这边的大统派。
王晓波:讲不上,真统派。
干春松:还有些假统派,是吧?
王晓波:有,呵呵。
(责任编辑:谢莲碧)